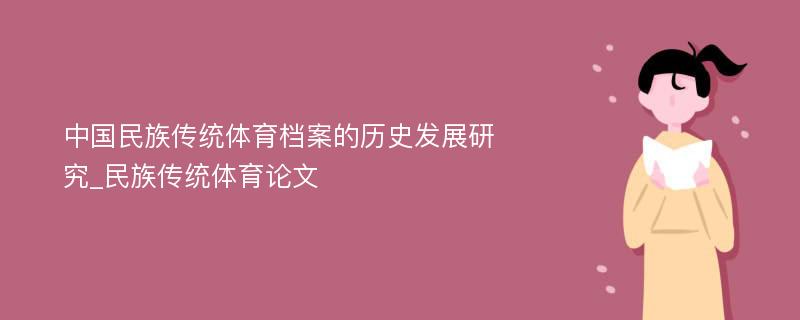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的历史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传统论文,我国论文,体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498(2011)06-0061-05
修回日期:2011-08-11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1]。《周礼·春官》记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之志。”[2]在此的“志”或“方志”,均是指“认识和分类记述特定区域情况的资料性著述”[3]。我国传统体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夏、商、周时代“礼、乐、射、御、书、数”6种科目的教育和记载,是目前文献资料可以考证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的最早源头。《战国策·齐策》中“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4],用白描式的简单手法,生动勾绘了春秋战国时期,如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市民经常开展传统体育的活动场景。秦汉时期,我国开始出现“志”的雏形,并将传统体育作为志书编纂的重要内容体系。中国修志历史经过2 000多年的传统文化沉淀,现在已经发展成以民族传统体育事项为主体的体育专门志。“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15],探索民族传统体育志新旧替代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志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发展规律,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长期规划和战略决策制定,更有利于转型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1 盛世修志: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历史发展阶段
就方志的发展历史而言,秦汉出现方志的雏形,发展于隋唐,承前启后于宋代,体例定型于元明[6]。清朝之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经历了4次历史性飞跃,发展成为以民族传统体育事项为主体的体育专门志。
1.1 第1阶段:清朝政府意志,旧志统一体例的出现(1661年-19世纪中期)
清朝视修志为著述大业、官修私撰,形成浓厚的修志风气,对地方志编纂的重视程度远超于前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建议各省纂修通知,以备编纂《大清一统志》,并参照河南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统一格式,提出严格而明确的要求。清雍正六年(1728年),再一次诏令各省“命天下督修直省通志,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送上一统志馆”[7]。至乾隆时期,“下至州府县,虽僻陋荒岨,靡不有志”[8]。各府、州、县地方政府都编纂志书,蔚然成风。目前中国大陆境内,清朝存世的地方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以及一些具有志书体例和内容的方志初稿、采访册、调查记等志4 889种,约占地方志古籍存世量的69%[9]。
清朝的方志统一了编纂体例和格式,主要分成“山川形式、建制沿革、农田水利、物产田赋、灾异情况、军备疆域、风俗信仰、名胜古迹”等条目内容,而民族传统体育大多分散载入各地地方志的军事、武备、艺文、风俗等条目之中。我国55个少数民族绝大多数是仅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目前,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资料,除了考古文物之外,能找到的早期古籍文献基本出自这个时期的地方志。
1.2 第2阶段:新文化运动,新志体例内容的变革(1929年-20世纪30年代末)
19世纪早期,整个中国政局不稳、局势多变、战事频发、生活动荡,方志纂修活动基本停滞。1919年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用“德先生”和“赛先生”重新编拟和定位地方志,成为当时地方志编纂的主旋律。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向全国颁布《修志事例概要》22条,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10]”上报内政部,作为全国各地修志之准绳,对民国方志的纂修起到了督促和推动作用。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全国普遍开展了修志活动,成果累硕,范围博广。
民国时期的志书有通志、县志、乡土志、镇志193种,3 132卷[11]。相对于明清时期的方志,民国时期的方志体例做出了较大调整,如删除了祀典等旧事项,增加了实业等新内容。新方志门类分为“疆域、地理、气候、人口、物产、实业、行政、教育、金融、风土、人物、艺术、著述、金石、故事、外侨16门类”,民族传统体育的史料记载,绝大多数就分布在风土、艺术等条目之中。此外,民国时期还出现了比较典型的专门志,如大事记、地理志、建置志、政务志、财务志、生计志、教育志、司法志、氏族志、人物志、礼俗志、宗教志、救恤志、实业志等分志的史料辑录本[12],各种专门志的编纂出版,为后来体育专门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条件。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大地上战火不断,社会格局满目疮痍,群众生活贫困潦倒,志书的编纂工作也随炮火纷飞烟灭。
1.3 第3阶段:改革开放,体育专门志茁壮成长(1985年-20世纪8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各地的修志工作陆续展开。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编写新方志列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的20个重点项目之一。1958年国务院颁行《新修地方志体例(草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随即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地(市)、自治州、县也大都建立了修志机构,组织、指导和开展全国新修方志的工作。但是,建国初期的修志工作,中间几经停顿。1966年之后的10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方志被列为“封、资、修”的批驳对象,刚刚兴起的方志修纂工作也因此而停滞。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盛世之况,修志之风迅速复苏。1985年,在福建漳州,国家体委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联合召开体育志编写工作座谈会,要求全国各地积极收集、整理、编纂各地的体育志资料。全国25个省区市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由省一级体委承担了省志中体育专志的任务。1989年9月,《广西通志·体育志》出版[13],成为全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省级体育专志,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版了体育志,并将民族传统体育细分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甘肃省志·体育志》记载了回族、藏族、东乡族、裕固族等10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志[14];《云南省志·体育志》记载了独绳秋、爬油杆、上刀山、堆沙等6万多字的民族传统体育志[15]。《湖北省志·体育》[16]、《湖南省志·体育志》[17]不仅记载了民间、民族传统体育,还加附了武术之乡、传统体育项目单位介绍等志书资料,各地体育专门志的发展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
1.4 第4阶段:世纪之交,民族传统体育专门志破茧化蝶(1990年-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志编纂热潮的推动之下,民族传统体育志发展诞生划时代意义的作品。1990年8月,由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体育博物馆共同编纂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出版,是民族传统体育志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以民族传统体育事项为主体的体育专门志,由全国近200位体育史志工作者,历经4年搜集、整理、编纂而成。共收条目977条,其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目676条,汉族传统体育条目301条,约60万字,是我国目前收录条目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志书,并于1991年4月由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奖”[18]。随后,1998年出版的《中华文化通志·教化与礼仪·体育志》分别从养生体育、军事体育、武艺武术、古代娱乐性竞技体育、民俗节令和民间体育等方面进行了体育专门志的编纂[19]。《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分10“典”,《体育志》是《教化与礼仪》典所属的10个“志”之一,共计20多万字。1999年《中华文化通志》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4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这也成为全国性的传统体育专门志获得的另一殊荣。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实施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取得了飞速发展,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民族传统体育志在新的历史时期,也肩负着传播和繁荣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粹的历史重任。
2 存史、教化、资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历史发展的价值与诉求
2.1 存史: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的根本属性
“方志乃一方之全史”[20],是围绕一个具体事项记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系统、准确的社会综录。“存史”,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的根本属性。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史的表述而言,“史”和“志”是记录传统体育发展历史的2种不同体裁形式。传统体育史强调以时为经,史体纵贯,关注传统体育主体对象,重在论证、总结经验和探索历史规律;传统体育志强调以类为经,志体横剖,关注传统体育的社会与自然,重在记述,以收集整理资料见长和反映历史规律[21]。
编纂民族传统体育志的具体项目时,横排竖写、资料准确、述而不论是其主要特点。比如,在编纂侗族芦笙舞具体条目时,包括侗族芦笙的材质与制作、古代场地(侗族鼓楼)、文物遗迹(岩壁画、画像石、陶瓷、画轴、拓片等)、活动形式与规则、流传区域与历史演变、社会文化背景及影响、不同地域间的异同点,甚至是不同民族之间芦笙舞的异同点等内容,要求背景资料、综合资料、典型资料、统计资料齐备(简称“四材运用”)。资料的数量、正误、真伪、衍缺是决定民族传统体育志质量的关键因素,具有很强的历史印记、时代特征和存史属性。我国史志,同源异体、源远流长,长期以来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民族传统体育志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继史之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无论从规模、速度、深度、广度都远远超出历史的任何时期,许多弥足珍贵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逐渐消失,民族传统体育志存史的根本意义和重要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日益显著。
2.2 教化: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的衍生价值
我国悠久的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56个民族伟大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缩影。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和阅读,可以激发每个人爱乡土、爱民族、爱祖国的热情,具有很强的教育衍生价值。比如,广西河池地区的瓦氏夫人率兵赴沿海,利用板鞋训练士兵,抵抗倭寇的英雄壮举,逐渐演变成现代壮族的板鞋竞速[22];白族兄弟3人用打糍粑的杵棍打退了残暴的官兵后,手舞杵棍跳舞的动作,逐渐演变成现代白族的仗鼓舞等等[23]。
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不仅仅以项目的形式孤立存在,它的演变过程孕育了许多感人肺腑、振奋人心的,能体现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的历史重大事件。这些重大历史题材的考证,在丰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之余,具有振奋人心的教化功能。明朝时期的于乃仁认为志有“三日启发后进,敬恭桑梓之心也”的重要作用,“凡表扬先辈德业学艺,以昭示后进,作精神上之鼓舞浚发者,往往视逖远者更为有力。直接养成一地方特殊之学风,间接造成人群团结进步之因素。方志实具此效用焉[24]”。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行《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了志的价值:“新方志可以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有助于各行各业全体干部、职工提高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新方志可用以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25]”。
2.3 资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的时代诉求
民族传统体育志书具有专门志和综合志二重属性。专门志属性是指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逻辑紧紧围绕民族传统体育事项搜集、整理、编纂资料的特性,通过严谨的史料信息反映传统体育的历史发展规律;综合志属性是指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内容涉及民族传统体育事项的地理、地形、水文、气候等自然环境资料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人文环境资料,具有历史学、方志学、体育学、民族学等学科交叉的综合属性。民族传统体育志属软科学,即决策学范畴。民族传统体育志的价值就在为决策提供全面、系统、准确的信息,以促使决策的科学化,具有“类似软科学的为决策服务、咨询等功用”[26]。
著名学者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说:“今案地方志所记一域之事,亦甚详悉,尤重现代,有裨实用。典章制度,旧事先例,并载书中。地方行政,即引以为准绳。一切纠纷,咸取决于此。古人所谓‘观民设教,体国经野’者,是诚足以当之。名为‘地方官吏之资鉴’亦无不可也”[27]。每个社会形态都存在民族传统体育,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传统体育都体现出时代特有的特征和印记。社会对体育的需要,体现了政治的控制,制约着体育的目的和性质,因而使传统体育的目的、性质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特点。编纂民族传统体育志要对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民族传统体育的史料认真鉴别、仔细分析、不避隐讳、如实记载。作为一个民族传统体育志的普通读者,都能通过大量、翔实、可信的历史素材,了解一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兴衰起伏以及制约其发展的内在因素,进而深刻地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体育文化发展政策的伟大意义。
3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的发展任重道远
3.1 发展困境之一:成果数量偏少,编纂时间太长
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民族本位文化的日益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成果方兴未艾。近20年,有《民族体育集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教程》《北方民族传统体育集锦》《民族传统体育集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论》等众多反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成果出版。这些研究成果从某一侧面介绍了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内涵,研究内容倾向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知识普及或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训练,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更缺乏志书应有的体例、篇目、元素、格式、要求和规范。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管辖的地方政府,在整理地方志的同时,也独立编纂体育的专门志,并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地方志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地方体育志的内容更倾向于体育行政、体育组织与管理、学校体育、竞技竞赛、人才培养、体育国际交往等篇目和内容,并没有将民族传统体育事项作为志的主体进行专门编纂,所以,真正具有民族传统体育志书意义的研究成果还是显露出数量偏少的弊端。另外,从1990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诞生至今已20年了,目前还未见到与它同样具有志书属性的民族传统体育志。理论上,我们也就无法考证20年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数量、流传范围、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功能价值等方面发生了哪些改变,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长期规划和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特别是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有些濒危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果不注意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可能就会存在消失的危险。
3.2 发展困境之二:体例编纂不规范,篇目设置难度大
体例,或称体裁、凡例,是志书编纂的组织形式、编纂方法、基本要求与格式,具体说就是写作构想、写作要求与写作形式。《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2章明确规定:“志书的体例共涉及志书的类型、名称、断限、体裁、框架和篇目、大事记、立传、文体以及资料引证,篇幅字数,开本版式等”[28],并做出了一些原则性要求。体育志是当代志书中新增设的专志,民族传统体育志更是由于历史源远流长、运动项目众多、活动形式多样、涉及面广等问题,目前未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合乎规则的体例编纂形式。《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在当时的编纂过程中,由各个地、市、县体委收集、整理材料,上报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最后统一汇总到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纂成书。由于编纂之前没有明确、细化体例,各地体委及其工作人员编纂水平参差不齐,造成了体例设计不统一的诸多问题。比如回族的“打铆球”、“木球”、“打抛俩”、“打梭儿”分成4个条目编纂,而它们之间是同一项目在不同地区的存在形式,或是同一项目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表现,应汇编成1个条目。白族有“龙舟赛”和“洱海龙舟赛”2个条目,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是令人费解。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作为我国第一本民族传统体育专门志,出现体例设计不统一的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未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还是要强调体例设计的统一性,提升志书编纂的水平和质量。篇目设置难度大,也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书目前存在的重要问题。比如,以“民族—项目”的篇目设计容易造成项目运动特色不鲜明、大量类同项目重复列入志书等问题;而“项目分类—项目”的篇目设计容易造成项目分类不合理、同一项目不同民族之间异同点考证难等问题。1997年,《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明确“篇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形式上不强求一律”[29]。哪种篇目的设置更清晰、更合理、更科学,符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特点,是未来民族传统体育志编纂工作者急需解决的命题。
3.3 发展困境之三:发展阶段不清晰,体现规律效果差
我国民族的历史发展尽管有很大差别,但民族发展的基本趋向和规律性却十分清晰。作为民族发展进步历史缩影的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志具有“存史”的根本属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阶段进行清晰划分,才能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才能体现不同社会制度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制约和影响,进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在民族地区稳定、民族团结进步、民族群众幸福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志书的具体编纂内容,还是倾向于民族文化内涵的解读,没有体现清晰的历史发展阶段或缺乏社会文化背景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的977项条目中,有的条目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单介绍,但是没有结合相关史料进行发展阶段的区分,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效果比较差。有的条目仅仅2~3行,20多个字,发展阶段的划分更是无从谈起。我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缺乏相应的历史文献记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对体育文物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增加田野实地调查工作量,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访谈等综合方法的运用,总结归纳传统体育发生、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如生产、生活、军事、风尚的兴衰起伏,政治的动乱与安全,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和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30]。这样不仅可以说明当地传统体育历史的悠久,体现传统体育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还可以增加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和时代色彩。
3.4 发展困境之四:资料存真求实,史料多元不足
“志者,记也”;“志者,一邑之实录也”[31]。民族传统体育志具有存史的根本属性,资料的真实性直接决定着民族体育志编纂的质量。民族传统体育志的资料应是那些能反映当地时代特点、真实情况,反映事物发展规律或发展趋势,有借鉴、查考、教育和存史作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材料,“存真求实”是志书资料收集的原则。1985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四条,新方志应当批判继承我国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1997年5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四条,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坚持改革创新,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上述2个文件都把“存真求实”当作新方志编纂方针列入规定。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中许多传统体育条目,介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起源和发展时,都用到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其在志书中的运用,是值得商榷和辨别的。那些能够通过文物实物和文献古籍考据求真的民间故事资料,具有“存真求实”的特点,能够反映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时代特征,可以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资料;那些不能辨别真实性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只能作为文学作品供读者品阅,而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资料显然是不可取的。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所运用的史料类型和来源,也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比如在编纂过程中,可以对历代地方志中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记载资料做系统化整理,从而丰富条目的历史文献;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有关岩壁画、画像石、陶瓷、画轴、拓片等文物考古资料进行考古学甄别,从而增强条目的可靠程度;对传统体育原始形态保存较好的地方进行田野工作,可以“礼失而求诸于野”;对传统体育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进行有效的实地访谈,可以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民族传统体育志编纂资料在存真求实的原则和基础之上,力求史料的多元化,丰富民族传统体育志内容体系的同时,能够增强民族传统体育志所沉淀的历史文化气息。
3.5 发展困境之五:机构设置不全,编纂人才缺乏
明确机构设置和规格是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志编纂工作的必要基础,精干的民族传统体育志编纂组织机构是实现组织职能的基础和保证。2006年5月,《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并规定:“制定区县地方志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以适应新的区县地方志工作职责要求。”从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志的机构设置来看,大体上分2种:一种是地方志编委会为虚设机构,地方志办公室是实体。如安徽、福建、江苏、湖北、广东、四川、贵州、黑龙江、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一种是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为实体,全国只有吉林省是这样[32]。
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工作一般由各个地区的地方志编委会联合同一行政级别的体育管理部门统一开展工作,但是,“一些地方在最近的机构改革中,把地方志机构撤销了,或留有牌子,有名无实。这样是不可能做好地方志工作的”[33]。“一些地方至今还没有开展工作,存在一些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如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等,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34]。“与其他省、市、自治区相比,云南地方志在基本建设、工作格局、条件保障方面,却有着很大差距。其中从省到县,地方志机构设置及其归属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省级层面的问题尤为甚也!”[35]。民族传统体育志编纂工作要注意优化组织机构、配备编纂人员和提供条件保障等诸多方面。此外,各级地方政府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相对稳定、专兼职相结合的民族传统体育志工作队伍,对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工作也极为重要。由于民族传统体育志编纂的特殊性,急需历史学、方志学、体育学、民族学等学科交叉的编纂人员。可以从各部门抽调热心地方志工作、具有一定素质、熟悉本地本行业情况的干部充实地方志队伍;同时注意吸纳新生力量,从高等院校毕业生中吸收一些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也可根据需要聘请一些具有较高的文字水平、熟悉情况、身体好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修志,保证编纂人才需求的相对稳定性。
3.6 发展困境之六:理论研究滞后,决策咨询率低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6]。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传统体育志科学,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重任。积极摆脱民族传统体育志理论研究滞后的局面,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民族传统体育志编纂这个系统工程。从理论研究整体的情况看,体育志的理论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如《体育志篇目的设计和科学分类的探讨》[37]对体育志的篇目、分类、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关于编写体育志的若干问题》[38]对体育志的目的,体育志的特点,体育史、志的区别,体育志的范围划分,体育志的布局与归属等问题展开了理论研究。这个时期,各级体育志编纂的工作人员也在学术期刊上积极总结一些体育志编纂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和心得。如《熔地方古今体育文史于一炉——谈〈福建省志·体育志〉》[39]《山西体育的百科全书——简评〈山西通志·体育志〉》[40]《博采精取——编写巴楚县〈体育志〉的一点体会》[41]《略评〈黑龙江省志·体育志〉》[42]。
21世纪以后,体育志的理论研究逐渐淡出了学术视野。民族传统体育志是全面记载某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历史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历史文献书籍,是一种学科独立的体育专门志。民族传统体育志出现的时代比较晚,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学术研究成果凤毛麟角,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实际发展情况相去甚远。此外,志的价值在于为决策提供全面、系统、准确的信息,以促使决策的科学化。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志的决策咨询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希望未来能加强民族传统体育志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升决策咨询率,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制定长期规划和战略决策作出应有的贡献。
4 结语
在2000多年的修志传统中,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经历了从旧志—新志—体育志—民族传统体育志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从旧志中的一个从属内容,形成了以民族传统体育事项为主体的体育专门志。这种变化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日益强盛密不可分,谓之“盛世修志”。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更替中,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充分发挥着“存史、教化、资政”等方面的价值与诉求。1990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诞生至今20多年,民族传统体育志从无到有、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忧虑重重。可喜的是,2010年12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2批),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崔乐泉(负责汉族部分)和吉首大学白晋湘(负责少数民族部分)合作主持的“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获得立项,研究工作随即展开。希望课题组在未来几年中,能够克服困难、总结经验、勇于创新,创造民族传统体育志发展历史的再一次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