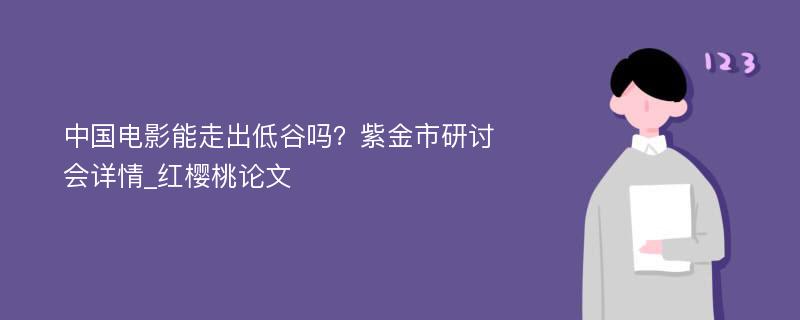
中国电影能否走出低谷?——紫金城研讨会详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紫金论文,低谷论文,中国电影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电影发行部门老板出面召集一场学术性很强的理论务虚会上,高级研讨了一些什么?连电影究竟是什么还没有搞清,却有“中国电影人妖化”语惊四座;谈锋甚健的理论家和学者在为中国电影牵肠挂肚的时候,不知道被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中国电影骄子们在忙乎些什么;相当数量的专家好几年没好好看电影了,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无奈和失语状态”,是否得“跨世纪”……
在进口大片冲击下惊魂甫定的中国电影界,1995年秋末冬初出现了一件挺耐人寻味的事件:由长江六市电影发行公司作东,在古都金陵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冠以“西方电影与当代中国电影”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级别很高,与会者除了电影理论评论界的几位专家外,几十位人文学者皆是学贯中西的大学、研究院、文联和出版社的教授、编审等,以及《光明日报》、《文艺报》、新华通讯社、《中国电影周报》和当地新闻媒介的众多文化记者。不容忽视的是,在此同时,因发行体制纷争引发的江苏省电影公司与下属六市公司的笔墨官司方兴未艾;《红樱桃》抢滩南京海报连天接地风头正劲;夏刚携他的那部有很大争议的新片《与往事干杯》刚刚来宁准备首映式;一场名曰“世纪之交的影视艺术”学术报告会已在南京进入尾声;而在近邻上海,第二届国际电影节辉煌落幕仍余音绕梁。红红火火的影坛盛况,仿佛一扫近年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预示着一个复兴时代的到来。
然而,透过三天的这场近乎论战的研讨会,笔者敏感地觉得,在影院门外重新聚集起大批观众的外表下面,中国电影仍在世纪的低谷经受着沉重危机,这种危机也许隐藏在电影这个怪物的各处,但作为电影头脑中枢的电影理论,电影观念,其混乱、无原则性和各执一端的固执,突出显示着中国电影的世纪末情绪。
尽管我们谁也不愿意承认这个痛苦的现实。1995年11月9日下午
郑雪来、邵牧君两位理论权威首先开战:——商业第一?艺术第一?
“我和邵牧君经常在一起争论。我们是好朋友,但他的不少观点我不同意。”郑雪来,这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院的教授,享有盛誉的电影评论家,以其平稳、清晰但略显苍老的嗓音拉开了一场波及全场的论辩战序幕。
郑雪来先生是一位资深电影专家,也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1945年起在美国军队当了两年战地翻译官,在史迪威将军指挥的缅甸战区沐浴战火,所以他对《卡桑布兰卡》、《魂断蓝桥》等二战经典片情有独钟,他的战区经历和娴熟的英语,为他日后翻译、研究西方电影提供了帮助。近年来,郑雪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颇引人关注的电影评论,其中尤以当年对现代派艺术的批评(现今他对自己幼稚的批评提出批判),为中国电影获国际大奖辩护的言论而为人瞩目。
他的论辩对手,近来竭力倡导“电影是一种商品”的邵牧君先生,一副深色眼镜遮去了大理论家应有的深邃目光,同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院教授,邵牧君先生言辞直接、干脆、掷地有声,与他的同事形成鲜明对比。
郑雪来先生指出,邵牧君近来发表的一些文章,把电影认定为是一门工业,商品属性是第一位的,应该遵循市场规律生产、制作影片,这些言论是错误的。电影首先应该是一门艺术,文化属性居首要位置,列宁曾经说过“电影是大众化艺术”。商业与艺术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要求没有文化的普通观众和有文化的电影制作人欣赏水平一致。他认为电影在中国是一门文化,负有社会责任,不能简单地当作工业化产品。
郑雪来先生承认,由于电视的冲击,录像带、影碟的发行,中央台电影频道的开通,大片的进口,导致中国当代电影步入困境。他主张,不要对进口大片惊慌失措,同时要有选择地进口,要进口真正的艺术片,郑先生对中国电影低谷是商业化不够所致的观点不以为然。他举例说,电影低谷是一个正常现象和必然趋势,欧洲80年代上半期重复过。郑雪来先生用诙谐的语言说,邵牧君先生善于提出一些新观点。他80年代提出电影的娱乐性就给陈昊苏的“电影娱乐人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邵牧君先生在台下冷静地听完郑雪来先生的点名“批评”。轮到他发言,他出人意料地针锋相对:“郑雪来先生讲话中提到我的频率太高了,我不得不‘应战’。”邵牧君先生的讲话节奏很快。他开宗明义:“电影是消费时代的产物,这个结论我不是随便下的。电影不是在沙龙里,由少数人拨弄的东西。今年我写了篇《电影万岁》,发在《世界电影》杂志上,为电影百年而作,我觉得有些新观点,奇怪的是居然一点反响都没有。理论、评论界很寂寞。”
邵牧君洪亮的声音在四壁回响:“这些年人们对电影的看法是电影完了。其实,电影死亡论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好莱坞那么兴旺,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研究好莱坞就成了当务之急:电影在经过百年之后在好莱坞为什么还生机勃勃?”
电影到底是什么?邵牧君一字一顿地发问道,是商品?是艺术?是商业行为?是美学行为?
邵牧君肯定地阐释,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艺术,是西方在后工业化大消费时代所产生的一门工业化艺术。没有哪一门艺术像电影这样需要这么大的资金投入。格里菲斯(音)拍了几百部电影,但他从来没有称自己创造了一门艺术。当他意识到想创造一门艺术的时候,拍了一部《党同伐异》,恰恰他完了,完全背离了以前路子,结果没人看,债台高筑,一辈子还不清,再没有制片人来找他了。
在郑雪来先生和邵牧君先生舌辩的过程中,会场是一片寂静。或许像类似的文人聚会难得一见火药味如此浓烈的场面;或许是“商业和艺术”的关系搅乱了与会者的惯常思维;或许每个人在审视本我观点的同时咀嚼逆论的涵义。总之,由两位权威理论家引发的一场关于电影基本属性和原则定位的争论掀起了几十位人文学者的心澜。寂静,意味着思维的启动,意味着爆发即将随之而来。
《文汇报》资深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首先向邵牧君的抗辩“发难”。“看了三遍《电影万岁》,有一阵冲动。电影的艺术根本就是要尊重观众。我们现在的电影,离开我们的审美追求太远了,离开表现我们的生存状态太远了……”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院年轻的女教授纪令仪女士则提出新颖大胆的观点:“美国电影成功的最大秘诀是:电影的教化。斯皮尔伯格谈到《辛德勒的名单》为何获奖:一切一切之外,主题是最重要的。美国电影最重要的是弘扬一种精神,比如‘阿甘’,这是支撑美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纪令仪女士隐晦地否定了电影的商业价值第一的观点。
北师大艺术系教授尹鸿在发言中责问道:“站在不同的立场,对电影有不同的认识,政治家当作工具,制片商发行商当作商品,人文知识分子当作艺术。如果人文知识分子还不当作艺术,谁来当?”
由郑邵发端的论争牵动全场乃至余波不息,延至后面议程,让人不得要领。也许,南京大学教授潘知常先生一语道白了问题的实质:(论争)可能是一种语言解释两种现象,商业和艺术不是第一第二的位置,是不同特性的。艺术是指电影内在的内容品位,商业是指电影在流通领域里独有的特性问题。
不论怎么说,电影理论界在中国电影陷入低谷的世纪之交时期,也陷入一场“先鸡先蛋”的逻辑怪圈,这不能算是幸事。中国电影的转轨变型,迫切需要理论和评论的先导,倘若理论家们纷争迭起,莫衷一是,是叫电影手足无措的。复旦大学影视中心副教授张振华坦言:“中国电影史上几次论争都促进了电影的发展,希望邵郑之争能引起更深入的论争。”但愿张振华先生的判断恰如其分。因为,对理论而言,沉默才是最大的不幸。1995年11月10日上午
青年评论家王干语惊四座——“中国电影的人妖化”
中国电影理论营养不良的状况并未妨碍新型观点的出现,与会学者的那一番番不成型的或者说是不成体系的电影阐释,吸引了他们自身。然而,当《钟山》杂志编辑、知名青年评论家王干抛出他的语惊四座的“人妖化”概念,不啻掀起轩然大波,新老理论权威们被撼动了。
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王干先生近年来在文坛崭露头角,几次大的文学论争,都有他乡音未改的呐喊。而且,他以思维敏捷、观点新奇见长。
王干先生在他的“关于中国当代电影的‘人妖化’”长篇论述中,把“文革”前对西方文化全力排斥称之为“撒达姆式文化”,而把80年代后迎合西方媚俗倾向的称之为“人妖文化”。他说,早在张艺谋拍竣《大红灯笼高高挂》时,他从友人苏童处先睹了录像,便提出其为典型的“人妖文化”,撰文给《文汇报》,《文汇报》压了3个月才发。 王干认为,中国电影媚俗倾向很严重,有媚政治俗,媚大众俗,人妖化是媚“洋人俗”。
王干在发言中几乎全盘否定了第五代导演的惊世之作,他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营造奇风异俗的人妖文学引伸开来,把《黄土地》称为中国电影人妖化的开端。他说,“灯笼”“菊豆”为迎合洋人,竟制造伪民俗;《秋菊打官司》不仅制造伪民俗,还制造伪法律;“二嫫”是“秋菊”生出来的儿子。民俗卖完了,怎么办?卖“家丑”,卖给西方的还有一个——“文革”,《霸王别姬》一半是民俗,奇风异俗,后半是“文革”,政治家丑,在西方一举成功。《霸》的儿子便是《活着》。
王干认为,从《红高粱》直到最近的《阴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一直未摆脱媚洋的人妖倾向。他特别把声誉鹊起的近作《红樱桃》拿出来解剖。他认为《红樱桃》的成功一靠洋语言(俄语,表明中国人心态太不自信了),二靠洋人物(跟中国没什么关系,换成哪国人都可以),三靠洋题材(在国际共产主义低潮期,表现共产国际的背景),四靠国际化的主旋律(二次大战胜利50周年)。王干对《红樱桃》未获上海电影节大奖表示理解。然而王干对《阳光灿烂的日子》却大为推崇。他认为该片媚俗倾向不像张艺谋明显,既不媚政治俗,对政治反而有一种反讽。中国电影5——10 年再也出现不了《阳光》这样的里程碑影片。
王干惊世骇俗的发言不可避免地招来了抨击,尤其是几位大家更是不敢苟同。邵牧君正声道:“人妖化”是一种对电影的诬蔑,不能对电影提出人文的、道德的要求。不能认为电影界的人追求的就是金钱。王干先生这样说是过头了。《红樱桃》我是很肯定的,用人性的剖析来看战争,讲俄语我看不出媚什么俗,纹身可能有一点“卖点”,但娱乐包装绝对不会影响艺术内涵。郑雪来先生也对《红樱桃》未获奖深表遗憾,对孙道临对该片未获奖的解释不以为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朱青君女士对王干全盘否定第五代明显不快:“好的电影必须有好的人文精神。陈凯歌、张艺谋、夏刚他们毕业时说过:站在电影操作立场上是搞不好电影的。可见他们是很追求人文精神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雁则也出语惊人:“中国电影媚俗得不够!”他认为,中国电影应该媚的是整个市民社会的价值取向,但在中国电影观众还没有真正形成社会群体时,电影还不能恰如其分地媚俗。梅朵老先生也认为:一定程度上,媚俗就是尊重观众,尊重观众的趣味。当初,陈凯歌拍《黄土地》时,根本没意识到要去国外获奖。《霸王别姬》表现了人性扭曲的内涵,不能将它们简单理解成媚洋俗。
作为唯一与会的导演,夏刚冷静地表示:王干的话虽有点偏激,但有一定的意义。中国电影面对的既不是一个完全政治的、商业的、艺术的环境,可谓一仆三主。导演应该坚持艺术良心,创作个性。虽然电影是商品,但导演不是商人。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媚俗。
有趣的是,对王干“人妖化”理论展开争论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词“媚俗”,引起了几位学者的推敲,因为许多人在发言中使用的“媚俗”,并不是一个界定的词汇。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光肯定:媚俗是否定性的价值评判。当前,批评媚俗是有积极意义的。潘知常教授同意朱光的定义,他说,媚俗翻译过去,就是“畸型的趣味”。明申当代文化所副教授许纪霖从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引伸,认为王干的“媚俗”是从道德的概念上界定,其实应该从美学的概念上来理解。尹鸿教授也认为,不能用“媚”这个字眼。他认为应从文化现象上来分析,来提倡电影批评的文化氛围。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是好事,获了奖还指责人家,电影还怎么发展?
纪令仪女士几次即兴插话,她的发言言简意赅,直中要害。她以美国电影为例证明“露家丑”并非媚洋俗的动机,而是意识形态电影化。她说,《现代启示录》一开始就是一军人在“拉大顶”,意即“人生是颠倒的”。关于越战,美国从《全金属外壳》、《出租汽车司机》到《野战排》、《生逢七月四日》一部比一部反思,不怕“露丑”。
由于王干是文学评论家,由此经邵牧君“看电影不能用文学的眼光来看”的提醒,又一场关于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论争应运而生。王干坦言:以前我说“电影剥削文学”,现在我说是“文学与电影狼狈为奸”。由于与会者大多是人文学者,对邵牧君鄙夷文学家研究电影的做法基本上义愤填膺。
坦诚地交换观点,争先恐后地发言,这种学术气氛是感人的,但笔者隐忧的是,贯穿会议始终的一种焦虑情绪,一种强加于人的学科倾斜,一种各自为阵的认识盲点,是难以达成共通以至共识的。有的时候,理论的学术的研讨,理性非常重要。理论尤其需要思考。1995年11月11日下午
夏刚“与往事干杯”,学者“与夏刚干杯”
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一些电影专家、创作者对这个品位较高的学术讨论会不屑一顾,或者说不为所动。邀请名单上如田壮壮、叶大鹰、管虎、王小帅等皆未与会,夏刚是为他的《与往事干杯》行销而来的,在会场上竟如坐针毡,几次欲提前离席都被执行主席挽留住。作为南京人的著名作家苏童,因几部电影改编自他的小说而与影坛打得火热,这次,他行色匆匆地开幕式上露了个脸(还是迟到)就再也不见踪影了。
“清闲”的理论家和学者们在为中国电影牵肠挂肚的时候,不知道被“诊疗”的那些中国电影骄子们在忙乎些什么。从这个比较来看,艺术和商业的脱节,远远不足为虑,因为中国电影最要命的症结不是影片本体,而是理论和电影制作实践的隔膜。一方面是书案前的文人自命不凡地著书立说,一方面是编导演们乃至发行商们我行我素地“玩弄”电影这个神奇的魔方。人们不禁要问,理论界面对创作界的坚拒的冷淡,继续谈“深沉”是否对牛弹琴般地滑稽?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王宁霄在先前的讨论中振臂一呼:“中国电影已与世界电影接轨,但电影理论和评论还未接轨。”其实这话挺值得玩味,作为先驱者的理论严重滞后于电影作品被世界接纳,也算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夏刚总算没让主办者下不了台,他毕竟代表了创作界,毕竟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使两极对话成为可能,尽管在座的都是他的导师和先生。何况,以他的《大喘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遭遇激情》、《大撒把》以及近作《与往事干杯》,被评论家们喜爱地称之为有品位的文艺片,那么,至少在目前电影界,他还称得上是一位学者型的导演。
夏刚很谦逊,他首先菲薄了一番同行,说,现在电影界内部孤陋寡闻,有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他对大家议论焦点的《红樱桃》是这样评价的:《红》是市场操作最成功的一部影片,从选题、镜头设置、市场推销等,全是商业因素。
他的一番冷静的剖白,明显令刚盛赞过《红樱桃》的学者们尴尬,有人立即提问:你说《红樱桃》没有教育功能,但你的《大撒把》给人以心灵的启迪,怎么说没有教育功能呢?
夏刚说,《大撒把》我是觉着好玩拍的。但我个性是善的,拍出来的片子是不会丑恶的。也许有教育功能,但拍片前不会有教育的动机。《红樱桃》与《辛德勒的名单》相比,《红》就是商业行为,枪毙女教师、裸体刺激,是商业考虑,而《辛》片不用这些。
许纪霖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与往事干杯》,陈染的小说很有意蕴,但夏刚拍出来的片子令我很失望,影片很肤浅地理解陈染的小说,演绎出一个浅薄的爱情故事。
夏刚说,陈染小说很有特点,但小说有很大局限性。电影不是十全十美的东西,但是它可以是一个很动人的作品。一年之后我看它还是很感动,这部电影有很大争议,有些观众很喜欢,有些非常不喜欢。它是否肤浅,我想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许纪霖对夏刚的批评引起邵牧君先生的不快,他以圈内人的口吻道:电影历来被文学家瞧不起,认为电影是比较肤浅的东西。海明威著作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他认为没拍好,自己改编《老人与海》,结果一败涂地,这下服了:文学和电影不是一回事。
潘知常教授则不同意邵牧君的意见:许纪霖谈《往事》并不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的。
《与往事干杯》是夏刚近年倾心制作的一部少女心理片,他对它呵护有加。据他介绍,《与往事干杯》是一部低成本制作,他请电影学院几个专门学发行的同学在太原选了两个小厅作试验,放映很成功,票房非常好。这次在南京,他对他的影片上市倾注了很大热情。他频频接受记者采访。休会间隙,总有几个漂亮的记者小姐与他攀谈。但是在会上,他的《往事》却遭受了不留情面的批评。一位女影评人当面责问他:“这部片子看了很不舒服,把婚外恋拍得那样美,这可能吗?”
尽管笔者相信一定有人非常喜欢《与往事干杯》,尽管夏刚在会上表现得虚怀若谷,但是,他的“觉着好玩”的拍片理想与学者们博大精深的电影概念形成一种碰撞。关于“电影是什么”的原始定位居然在学者中动摇了起来。
夏刚似乎受了学者们对电影痴迷状态的感染,他主动作了一番长谈,他说,听了先生们的话,觉得每个人都讲得有无可辩驳的道理,电影很难用一句话讲清,很难从一个角度就阐释清楚。邵牧君老师说电影“进入流通领域就是一种商品”,这是很明确的,电影应该是多样的,有针对一般大众可看性较强的,也有高品位的。不能把电影当作低品位的消遣来对待,把原来低层次的观众引导到高品位层次上来,是电影创作者、消费者、经营人员的责任,好莱坞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个研讨会对我有启发,我愿有更多机会与大家讨论。
夏刚是聪明的。如果说刚与会时他心神不定是为了他的《与往事干杯》,那么,最后一天洗耳恭听直至真挚感言,想必他是被会议气氛“镇”住了。尽管他的先生们“为夏刚干杯”。
在今后的导演生涯中,夏刚会记住这一天吗?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由于长期的落寞(有人称之为“无奈和失语状态”),眼下的脆弱、无序、乏善可陈令人震惊,这如何成为电影人鏖战沙场的盔甲?这如何迎接或应付世纪的挑战?
我记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细节:相当数量的学者声称已有好几年没好好看电影了(有人竟两年未看一部国产影片)。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几年没摸过手术刀的医学专家来给学生们上解剖课。他的意见能够被影坛尊重并成为权威思想吗?
我还惊讶地发现,在研讨会晚间放映的6部美国资料片中, 我早已看过其中或当红一时或独具一格的4部,然而, 像我这样的离席者寥若晨星。我,只不过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记者和业余影评人。
对至尊的理论界及其导师们提出疑问,是很需要勇气的。但是,如果大家都作安逸的村夫,中国电影又有什么复兴的希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