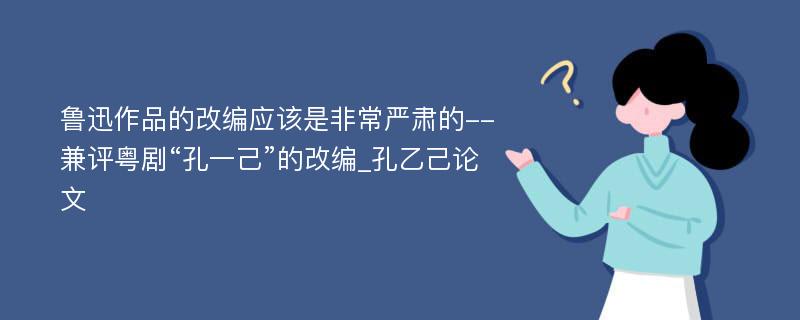
改编鲁迅作品要十分郑重——评越剧《孔乙己》改编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越剧论文,郑重论文,作品论文,孔乙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导演郭小男特别强调:“对《孔乙己》的改编,所采取的并不是当前那种流行的‘戏说式’的方法”(《文学报》1037期),但我面对着越剧《孔乙己》的改编本,却怎么也抹不去“戏说”的强烈印象,只不过这种“戏说”在理论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改编者的《后记》中和导演对记者的介绍中,作了一种时髦的“文化”的包装。至于剧本本身,却并不见有多少“文化性”,恰恰相反,鲁迅原著中所蕴含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现在却被不伦不类的人物和情节搅得荡然无存。
鲁迅的作品不易改编。众所周知,鲁迅不但是新文学的巨匠,而且是新文化的旗手,他在《孔乙己》、《阿Q 正传》等小说中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的高度,后来的作家无人可及,遑论超越。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不争的事实。靠增添一些人物、改动故事情节等技术手段,是无法再增强“孔乙己”这一人物的“文化性”的,而现在改编本中的这种“改编”的随意性,其结果只能落入“戏说”的俗套中。
还在六十多年前,就有人尝试改编鲁迅小说。最先有洪深等人想把《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但都没有成功。1937年,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有两个人同时改编《阿Q正传》,一位是许幸之, 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田汉。1937年1月29 日的《东方快报》(北京)上有人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特意忠告:“不过,我们希望改编者务必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勿多事更动,以免丧失了原作的精神”,因为该消息的作者也注意到,“许幸之改编的,将鲁迅先生自选集中孔乙己等人物全拉了进去,据说,这是为了要增强戏剧性的原因,同时在原作中阿Q 不大说话的,现在舞台上的阿Q,已变成罗唆多话的人物了。”8月1日, 欧阳凡海撰文在《文学》(上海)上详尽地批评了许幸之的改编本:“许幸之的剧本,无论在原作的立场上看,无论在编剧的立场上看,我敢断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将‘失败’这个字眼加于作家的作品上,在一个批评者是应该十分郑重的事。我真非常抱歉!”欧阳凡海同样也批评了田汉的改编本:“田汉的剧本应该相当改写,倘使他愿意,则对许幸之的指摘,于他也不无用处。”欧阳凡海强调指出,把鲁迅的《阿Q 正传》改编成剧本,是非常困难的:“阿Q 的性格可说比什么人物的性格都难把握,倘使一不小心,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可笑或无聊的角色搬到舞台上供观众一哄而散”(《评两个(阿Q正传)的剧本》)。
欧阳凡海的意见与鲁迅自己的看法是吻合的:“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信》)。事实上,此后一些改编本的演出也未有成功的。北京的《华光》第二卷第三期(1940年9月15日)曾刊有署名佩寒的文章, 谈其在北京长安戏院观看《阿Q正传》公演的感受,觉得“意味索然,看剧本感觉, 和看原著时感觉,相差太远。”作者在文末感叹,把鲁迅的小说“搬在舞台上,想保存其真意,不损其价值,我想,是很难的。”而当时有的评论者,更尖锐地把这种改编后的走样,称之为一种“危险”(1937年4月22日, 《东方快报》《论阿Q搬上舞台》,作者唯易)。
在我看来,眼下的越剧《孔乙己》的改编也是完全失败的。改编者张正钧似乎不甚了解新文学史上的已有的教训,它的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几乎重蹈了当年《阿Q正传》改编的复辙。
小说《孔乙己》比之《阿Q正传》,显而易见, 更缺少剧本的要素,如果说《阿Q正传》还因有9个章节,多少提供了一些戏剧性情节,不足三千字篇幅的《孔乙己》,则仅仅是“小伙计”回忆中的几个生活情景的断片,那是更难拉成一个剧本的。“戏不够,设法凑”,于是在改编本中,60年前的故伎重演,《药》、《明天》,甚至《肥皂》等主题不完全相同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跑到”《孔乙己》中间来了。改编者不仅仅把鲁迅各篇小说随意拆散,重新组装,而且令人惊愕地任意“演绎”,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改编本的主要情节线索是“三个女人一脉牵,一张瑶琴三组弦”。其中之一的“小寡妇”与孔乙己“同床‘死’片刻,生当永相依”,“小寡妇”拥抱孔乙己,女声伴唱:“徒有相怜意,恨无玉成计,……是悲情?是苦命?是奇遇?”“三个女人”中的第二个是夏瑜,改编本写孔乙己初见夏瑜即觉似曾相识,“警幻人生,迷离风尘”,直如宝玉初见林黛玉,匪夷所思。后来孔乙己又探得清政府欲害夏瑜,他不顾伤痛和安危,通风报信,而夏瑜在血洒刑场前,特意又把玉扇留赠孔乙己。鲁迅的经典之作,经改编者如此“戏说”之后,变得面目皆非。鲁迅的《孔乙己》这一类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魅力,已在几代的读者中形成深刻的印象,我想,广大的读者在情感上是无法接受这样随意“戏说”的“文本”的。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孙伏园当年曾问鲁迅,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鲁迅的答复很明确:《孔乙己》。
“何以鲁迅先生自己最喜欢《孔乙己》呢?我简括的叙述一点作者当年告我的意见。
《孔乙己》作者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对于苦人是同情,对于社会是不满,作者本蕴蓄着极丰富的情感。不满,往往刻画得易近于谴责;同情,又往往描写得易流于推崇。《呐喊》中有一篇《药》,也是一面描写社会,一面描写个人;我们读完之后,觉得社会所犯的是弥天大罪,个人所得的却是无限同情。自然,有的题材,非如此不能达到文艺的使命;但是鲁迅先生自己,并不喜欢如此,他常用四个绍兴字来形容《药》一类的作品,这四个绍兴字我不知应该怎样写法,姑且写作‘气急虺聩’,意思是‘从容不迫’的反面,音读近于‘气急海颓’。”
(《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对照孙伏园的回忆,我们可以发现改编本《孔乙己》恰恰违背了鲁迅原来的创作意图,在立意和人物形象上与原作背道而驰。鲁迅原意在写“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写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就是鲁迅始终关注的“国民性”问题。
孔乙己活得很苦,他的存在价值只是可以让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几声,“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苦人儿,苦人让人同情,但仅此而已。鲁迅不愿使这种同情流于“推崇”,这正显示了鲁迅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然而,《孔乙己》的越剧改编者,不理解鲁迅的这种创作特色,不了解鲁迅所以最喜欢《孔乙己》的原因,不仅没有力求避免这种“推崇”,而且竭力地加以扩大。剧本不仅把孔乙己写得风流倜傥、才气横溢,而且慷慨大方、见义勇为,乃至与革命党人一见如故,同气相求,俨然是个准革命党人。剧本中孔乙己尚未出场,一副“大手笔”的对联已先声夺人;出场后又补题横批,艺压群贤,形成一个“精彩”的“亮相”。孔乙己虽穷困潦倒,还欠着酒钱十九文,但却视金钱为粪土,补题横批之赏钱,随手悉赠小寡妇,慷慨潇洒之状可掬。接着又是“智救小寡妇”,虽惊叹“亭亭玉立一佳丽”,但终于“坐怀不乱”。到探得“夏瑜竟是个革命党……命在旦夕屠刀下”,明知“给革命党通风报信,是要掉脑袋的”,仍奋笔疾书告急信,甚至不顾自己腿折,“神情俨然”地声称“我自己去送!”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引得“半疯子”为之喝彩:“好!有种!”
另一方面,原作最根本的“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则是大大地被淡化了。“长衫帮”中的“花白胡子”“丁举人”等对孔乙己的才气是赞誉有加,“短衫帮”中的“半疯子”及“小寡妇”、“女戏子”对孔乙己也是钦佩不已。特别是剧本中对有关情节的处理,与原作的意思更是背道而驰。例如关于“茴”字有四种写法,在小说中作者的意图非常明白,因为掌柜和酒客都只拿孔乙己取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得向孩子们说话”,于是便有了和“小伙计”关于“茴”字的对话,然而“小伙计”也“不耐烦”,“毫不热心”,小说深刻地描写了孔乙己处在这种冷漠之中的寂寞和悲哀。然而,剧本中关于“茴”字有四种写法的戏,却变成了孔乙己卖弄学问滔滔不绝,众人听得“颇有兴趣”“目瞪口呆”“乐不可支”,整场戏气氛十分热烈,鲁迅原作中的一片匠心被改编得完全变了味!
越剧《孔乙己》何以如此走样?从改编者的《后记》来看,我以为一个原因是他犯了一个“时髦性”的错误:在当前谈论“文化”成为一种风尚时,改编者尽管承认“《孔乙己》究竟传递着怎样的思想密码?剧本作者还难以准确地把握,顶多只是一种可能的读解,并附加时间之维所冲击的情思”,然而还是相当大胆地对经典之作《孔乙己》重新作了一番“文化”的“包装”。
在《剧本〈孔乙己〉后记》中我们看到,改编者非常“宏观”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番“文化思考”,并把这种“文化思考”“渗入”到剧本的改编中。改编者先是轻易地否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民主性精华,去其封建性糟粕”的“二分法”:“这种抽象的二分法,在这座庞大的迷宫面前,没有做出多大的业绩”;紧接着就指出:“本世纪中国的志士仁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西绪弗斯的劳作,从事着可歌可泣的启蒙、救亡、重铸文化的战斗,同时也可以看到一批又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各种黑暗专制势力面前,精神上集体大逃亡。”
如果说,这种“文化思考”并不能让人看出其与“二分法”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那么,在“渗入”的具体办法中,改编者则改“分”为“合”:一是“合二而一”,即“剧本将《孔乙己》与《药》两篇小说的人物相聚在咸亨酒店”;二是“合三为一”,即“三个女人一脉牵,一张瑶琴三组弦”,“小寡妇”、“夏瑜”、“戏子”由同一个演员扮演,并且由此构成全剧的一条情节主线。改编者认为这是“一种相同命运的直喻:美丽中的苦难和苦难中的美丽。这也是传统文化给予中国女性唯一的馈赠和最大的厚爱。”而且这种“馈赠”与“厚爱”,“也许能激活羸弱的文人性格中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坦率地讲,我对剧中所表达的这种“文化思考”,是相当怀疑的,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思考”,倒不如说是剧作者充分考虑到了越剧这种剧种的特点,以及对这种剧种特色已形成了固定的期待视野的观众的需要。
一般而言,所谓改编,主要只是艺术样式的改变而已,主题思想、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等应该充分尊重原作并保持原作精神,特别是对于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更应如此。近读《文学报》1045期载金庸在台北会见影视明星萧蔷,谈及“您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字作品被改编的影像?”金庸说:“很难,其实演员的问题不大,但整个故事情节都改掉就很不好。我很喜欢的作品,就像我的儿子女儿,今天我们有事出门,把他托人照顾,结果却被人打了,你说痛不痛心?作品被加东加西,东改西改,感觉就像儿子被打。”说越剧《孔乙己》的改编者对原作不尊重是不为过的;对于广大热爱、尊崇鲁迅作品的读者来讲,《孔乙己》被戏说成如此模样,不能不令人痛心!我们希望文艺界在改编鲁迅作品时要十分郑重,否则,有可能变成一种糟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