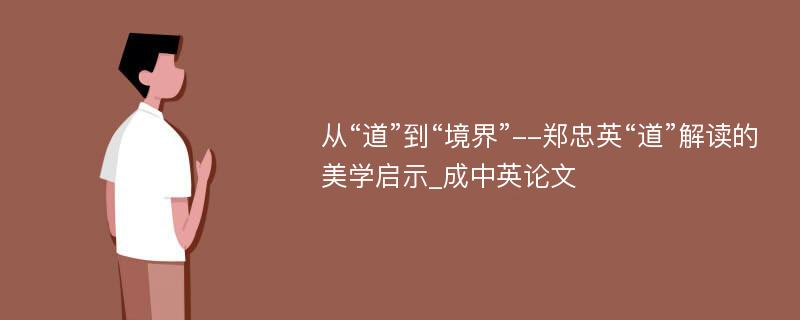
从“道”到“境界”——成中英关于“道”的诠释的美学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迪论文,美学论文,境界论文,成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04)05-0001-08
一
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成中英教授提出的“本体诠释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这一学说与时下在中国哲学研究中颇有力量的“理性重建”的方法有重要的区别。“后者集中关注于中国哲学大的框架对中国哲学的术语和观点进行理性的分析的理解,真理和真理性的问题不是其重点关心的问题”(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中国哲学中的诠释和重构[A].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9,10,43,25,11,16,12.)。“但就本体诠释学而言,我们必须使真理和真理的境遇问题成为中心问题”(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中国哲学中的诠释和重构[A].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9,10,43,25,11,16,12.)。“真理的境遇”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成中英教授的重要贡献。绝对的、超越时空的、所有人的理解都一样的真理其实是没有的,人们只能在大致相同的思维倾向下,遵从大家基本上认同的思维路线对某一问题得出大致一样的认识。这中间,各种影响人们认识的客观的与主观的因素,都会参与到对真理的理解之中。这所有对真理理解可能产生的因素,我认为就是成中英说的“真理的境遇”。
相对于西方哲学对于真理的认识,中国哲学更为注重真理的境遇,也许这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不存在严格区分有关。成中英教授说:“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不甚关注逻辑的以及认识论的、方法论的问题。”(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中国哲学中的诠释和重构[A].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9,10,43,25,11,16,12.)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逻辑的、认识论的、方法论的讨论,而是说从中国哲学的主流学派儒家、道家来看,其逻辑的、认识论的、方法论的讨论与本体论的讨论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实际上,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就融会有逻辑与方法。成中英甚至认为,中国儒家与道家的学说中蕴含着一种渊博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是什么呢?“它是那种观察和体验内容丰富的实在性的方式,在这种实在性中万物各得其所,而没有任何东西的被剩下和抛弃。它采取了一种内容丰富的观察和反思来理解这种最终被命名为‘道’的内容丰富的实在”(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中国哲学中的诠释和重构[A].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9,10,43,25,11,16,12.)。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道”与其特殊的逻辑、方法论密切联系,说穿了,道即存在于对道的言说或者说把握之中。悟道的过程与悟道的结果密切相关。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儒家哲学强调“诚”这个概念,认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作为人道,是修炼成圣的工具,作为天道,它又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只有以诚去求诚才能得诚。也就是说,只有真诚的努力才能把握真实的存在。
成中英先生说:“‘本体’是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兼含了‘本’的思想与‘体’的思想。本,是根源,是时间性;体是整体,是体系,是空间性,是外在性。‘本体’因之是一切事物及其发生的宇宙系统,更体现在事物发生转化的整体过程之中。”(注:成中英.从真理与方法到本体与诠释[A].本体与诠释[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0.5,41.)中国哲学表示本体的概念其实不只是“道”这一概念,道是本体的动的写照,《周易》中说的“太极”则是本体的根源的涵义,而就其质料言,本体是气;就其秩序言,本体是理。这些概念都是相互联系,又是可以相互解说的。
在所有关于本体的概念中,“道”这一概念无疑居于中心地位。比之于本体的其他概念,“道”更为人们所关注,更多地成为诠释的对象。先秦诸子百家都论道,但对道的阐释不一样。道家说的道更多地指自然,而儒家讲的道更多地指名教。这种对立在先秦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但以后的学者试图圆融儒家道家对道的诠释。魏晋玄学就做过这种努力:或是将名教归于自然,或是将自然归入名教。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儒、道两家的精神营养,形成特有的相当完善的心性体系。宋明理学虽然也有诸多的派别,对宇宙本体的理解也不一致,但基本路线是整合、圆融自然、名教、心性,实现天道、人道的统一。
在中国美学的研究中,境界作为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现在基本上成为美学家的共识。中国美学的本体是境界。美学的经典提问“美是什么”,在中国换成“美在什么”这种转换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统一密切相关。“在什么”是方法,但在什么决定了它是什么,所以方法即是本体。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方法比本体重要,事实上,是什么也决定它在什么。关于“美在什么”的提问,中国美学的回答是“美在境界”。整个一部中国美学史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没有采取讨论的形式。
境界这个名词来自佛教,佛教将成佛所达到的精神世界称之为境或境界,而其整个的理论营养可以说集中国文化的精粹。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这棵大树的根,那么,境界就是这棵大树的花。境界其实也不只是审美本体,也是伦理的本体。中国传统文化将圣人的精神世界也称为境界。“境界”作为审美的本体与哲学本体“道”就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只要稍为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的美学,就会发现,关于境界的种种解释都通向道,中国美学认定的“美在境界”,究其根本也就是“美在道”。成中英先生认为,中国的本体——方法论“将展示某种实在的广阔范围和广阔视域而有时被指称为‘境界’的东西”(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中国哲学中的诠释和重构[A].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9,10,43,25,11,16,12.)。境界生根于道,道展开为境界,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化包括哲学天然地具有浓郁的美学色彩。
中国哲学不仅有本体——方法论和本体——认识论,还有本体——伦理学和本体——美学以及本体——逻辑学。在诸种本体论中,成中英认为,本体——宇宙论居于基础的地位。中国哲学中的善与美的概念归根结底都要从“本体——宇宙论”所要探讨的宇宙之本去寻找解释,或者说寻找母体。成中英运用他创立的“本体诠释学”成功地诠释中国哲学的宇宙本体“道”,他的诠释开启了对中国美学本体“境界”的理解。
二
中国哲学讲的“道”作为本体,它的基本属性是生命性。成中英说:“我们本体论需要被理解的‘本体’(最初的真理或实体),即一个指称产生我们关于世界显现经验的终极实在性概念。作为本体论,‘本体’在中国哲学中被经验和描述为一个万物从其创生的源头以及万物有序地置身于其中的内容丰富的体系。而且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万物仍被创生。在这种意义上‘本体’最好被表现为‘道’。”
中国哲学将道理解成生命的源头,强调它的不断地生成性,这在《老子》中得到明确的阐述。他把道比喻成“玄牝之门”,说“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周易》虽然没有明确地用道这个概念作为宇宙的本体,但是它说的“天地”就是道。《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中国哲学将道的基本性质定位于生命之母。但没有将道人格化,使之成为有神论的上帝。成中英先生说,我们当然可以把所有“道”的特征都归于上帝并使上帝成为一种“道的上帝”,同样,我们也可以把上帝的特征归因于“道”,因此使道成为“上帝的道”,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将一者还原为另一者(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中国哲学中的诠释和重构[A].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9,10,43,25,11,16,12.)。在中国哲学中,万物的生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没有意志的参与,没有理性的主宰。我们须通过信仰和权威崇拜去认识上帝,然而我们对道的体认却主要是通过现实生活的感悟,甚至可以说诗性的感悟。中国美学虽然重视生命,并不简单地将物比喻成人。中国美学对物的生命性的理解更多地将其理解成“生意”——生命的意味。我们说道具有生命性,准确地说,应是具有生命的意味。比之于人的生命,生意是含蓄的、隐晦的、深层的、自然的。
在中国人看来,整个大自然都充满着生命的意味,人与自然的交流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流,准确地说,是有形生命与无形生命的交流,或者说是生命与生意的交流。中国人这种生意交流说与西方的移情说有所区别。西方的移情说认为对象本无生命,人之所以从对象看出生命来,是将自己的生命移情过去的。中国哲学的生意交流说,强调的是人对物的感动,简称为“物感”或“感物”。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刘勰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刘勰强调感是双方的,既“随物以宛转”又“亦与心之徘徊”。同时,感不只在物,亦进入到心,所以人与物的交流,不只是在目,也在心。“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用来描述意境的概念绝大部分是属于生命的。其中“气”这一范畴也许更应格外重视。“气”这一概念首先是对“道”的生命性的描述。虽然中国哲学史上对“气”的理解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没有脱离生命。成中英说:“气乃逐渐形成天地万物动力本体,更为生命体生命力的本质。”(注:成中英.从真理与方法到本体与诠释[A].本体与诠释[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0.5,41.)在中国古代更多地用“气”而不是用诸如“生”、“命”、“神”这类概念来描述生命,也许因为“气”更能显示生命的弥散状态、灵动状态、整一状态。宋代的张载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篇》)气动为风。我们发现,在中国美学中,“风”也被用来表述生命的状态。《毛诗序》说的“风以化之,教以动之”将“风”看成情感的教育。刘勰据此导出“风”的新义,他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文心雕龙·风骨》)。于是,“风”与“骨”的结合,就构成了艺术生命的两个基元。
在中国哲学中,“气”的观念与“阴阳”观念相联系。《周易》说,世界之本为太极,太极分阴阳,阴阳为二气,阳气上升为天,阴气下降为地。阴阳两分不仅产生了天地,同时也产生了男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系辞上传》)。有了天地,万物自然就有了;有了男女,人类社会自然就形成了,子子孙孙繁衍不绝。《周易》的重要价值是将道展开为阴阳。“易以道阴阳”。阴阳可视为本体性存在,但不能理解成实在的物,也许理解成“气”是最好的。作为生命的两种基本因素,阴阳的重要性质之一则是刚柔。阳为刚,阴为柔。刚柔是生命力的两种形态,在中国美学中,刚柔衍化成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种形态。
有关道的生命理念在道的感性存在——境界中得到充分体现。境界不仅接受了“气”的观念,还派生出“韵”这一概念,“气韵生动”成为艺术境界的首要要求。气韵二者,气重在生命的进取的一面,外在的一面,强大的一面,刚健的一面,而韵重在生命的退让的一面,内在的一面,坚韧的一面,含忍的一面,智慧的一面。气更多地通向阳,韵更多地通向阴。二者的关系构成了生命的大千世界,美的大千世界。而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却又是中华民族最高的审美理想。实际上,阴阳和谐、刚柔相济也是生命的最佳状态。
三
作为宇宙之源、生命之本的道,从本质上来看,它应是抽象的、无限的“无”。但是,它又必然展现为具象的、有限的“有”。我们正是通过这具体的有限的“有”,才能把握抽象的、无限的“无”。
老子说的“无”不是静态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着,生成着,变化着,按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反者道之动”的模式创造世界,永不停息。所以,道其实并不神秘,也不抽象,这世界上有形的、无形的一切无不是道的体现。日出月落,云飞云散,潮涌潮息,春去夏来,生老病死……这一切都是道的体现,成中英先生说这是“道的意象”。我认为,成中英提出“道的意象”这一概念是深刻的。成中英先生在论述老子道论时指出,老子不仅用“有”、“无”这些抽象概念对道的基本性质作出规定,还用一些具体的事物比喻道,这些具体的事物有水、赤子、母、阴性、朴等。这五者都可以看成道的象征(注: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154,139.)。在笔者看来,这几种道的意象正是审美境界的雏形,也是艺术的雏形。
成中英说由于对道的意象认识的角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学科诸如,“道”的美学、“道”的伦理学、“道”的政治学(注:成中英.怀特海之象征指涉论与易经、道德经中心思想[A].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C].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134.),等等。我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但是我想强调,由于“道”是作为意象而存在的,它首先属于美学研究的对象,“道”论必然地通向美学。由于道不只是审美的本体,也是伦理的本体,认识的本体,因此,道的伦理学、道的认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学化了。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
成中英先生认为:“从古老的《易经》开始,中国思想家没有对实在和现象作分析的区分,并把所有事物持续不断的变化延续性的道体现在万物的具体变化中。”(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中国哲学中的诠释和重构[A].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9,10,43,25,11,16,12.)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中“现象”与“实在”(本体)是区分得很清楚的,而中国哲学不将现象与实在区别开来。在中国哲学家看来,现象即本质,即实在。没有离开“有”的“无”,同样,也没有离开“无”的“有”。老子为表达这一问题煞费苦心。他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既然“无声”为何要说是音,而且是“大音”?既然“无形”,为何要说是象,而且是“大象”?他的意图是清楚的:让你从现有的声音、形象体会到道,但又不能让你将“道”归之于现有的声音与形象。他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是一个提醒,让你意会:这“道”是“象”与“精”的统一体,千万不要把它看成纯粹的象或纯粹的精。庄子说:“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逍遥游》)既然“咸共自取”,又何来声音?然而庄子说它是“籁”,是声音。庄子的意思是,道是一种似有声又无声的东西,在感性之中又超越感性。
强调“象”与“精”的统一,现象与实在的统一,对于理解美学的境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审美境界作为心造物,它的本质应是理性的,但不能是抽象的理念,须具有感性的意味,具有意象。朱熹喜用“气象”表达人的精神面貌,表示心中之道。“气象”就很类似于境界。
审美境界当其物态化为艺术时,它就显现为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与一般的审美境界有联系又有所差别。一般的审美境界只存在于人的心中,完全是虚像,然而艺术境界则须将它物化为艺术意象,相比于一般的审美境界,它是实像。然而相比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它仍然是虚像。清代学者叶燮说诗的意象不外是理事情的结合,然而这进入诗的理事情不是实像,而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原诗》内编),也就是说,它是虚像。这种虚像虽然虚,却深刻,特别富有审美情趣。它“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编)把握虚像是需要另一种思维的。杜甫的名句“月傍九霄多”,按生活的逻辑不通。月只能言明,言高,言升,言落,哪有言“多”的呢?然而换一种思维——美学的思维,你就会觉得这“多”字绝妙,远不是明、高、升、落等日常用语能比的。然而它的意味究竟何在,它到底好在哪里,又只能心会,难以言明。这正是艺术境界的魅力。
艺术境界就其构在来说,是实与虚的统一,实为景(事),虚为情(理)。如何处理好景与情的关系是艺术境界创造的关键,而这又通向中国哲学的道论。艺术境界的景与情的统一,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道的“象”与“精”的统一、“有”与“无”的统一。中国美学关于景、情统一的论述非常之多,其中以王夫之的论述最为深刻。他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姜斋诗话》)“情景一合,自得妙语。撑开说景者,必无景也。”(《姜斋诗话》)在这里,景可以理解成现象,情可理解成实在。景是有形的,情是无形的。这无形之情就在有形之景中,而且两者切合,景即是情,情就是景。“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王夫之《姜斋诗话》),同样,不能作情语,也不能作景语。正是因为情景相合,所以王夫之才提出“现量”说:“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真实不参虚妄。”(《相宗络索·三量》)“现在”重在静态,“现成”重在动态。因为是“现在”,“现成”,所以它是“有”,然而这“有”显现出“无”。有只是无的现象,本质是无,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才是真实。王夫之说“现在”即“现成”,是说没有绝对静,也没有绝对动,静在动中,动在静中,而这样一个现象的展现过程,也就显现出事物的本质。
道作为有与无的统一,不仅表现为现象与实在的统一,也表现为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成中英教授认为,道表述为无,可以理解为无限创生力的原初实在性。道将自身显现为已构成之物和未构成之物的总体,并表明构成之物是可能的,因为存在着未构成之物。未构成之物和在内容及形式上未确定之物恰恰是作为能被构成和被确定之物和在内容及形式上被确定之物无限和永不枯竭的源泉而存在。这个观点是很深刻的。
对于道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如果限于物理时空是无法理解的,必须打破物理时空进入一种特殊心理时空才行。按物理时空,不知晦逆的朝菌怎么能与冥灵比长久呢?只能飞几步的蜩与学鸠怎么能与翼如垂天之云的鹏比大小呢?但是如果打破物理时空,按悟道所需要的心理时空观来看这一切,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物理性的时空是有差别的,而心理时空是无差别的。如果能理会“无极之外,复无极也”,那朝菌与冥灵、蜩、学鸠与大鹏的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呢?道虽然显现为有,为有限,但它的本质是无,为无限。这种无、无限,只能存在于心灵中。没有比心灵更广阔、更自由的了,庄子的“逍遥游”其本质是“心游”。
道的这种性质在境界理论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梁启超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造之境为真实。”(《自由书·惟心》)在中国美学中,象与境来源是不一样的。观物取象,游心造境。象是有限的,境是无限的。中国美学对境界的认识其基本点就在于这无限。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司空图说“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王国维说“言外之意”、“弦外之响”,都是为了强调境界的无限性。中国人所认为的美最为重要的性质就在于从有限性中见出无限性。刘勰将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归之于秀与隐的统一,“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文心雕龙·隐秀》)。宋代学者范温论韵,说韵为“美之极”,而韵的基本特点为“有余意”(《潜溪诗眼》)。
四
中国哲学所理解的存在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我们不能脱离某物的被定位和被描述的背景来单独地理解事物。背景的重要性在于它从根本上规定此事物为何不是彼事物。背景即关系。成中英说:“事物就在于它们是事物才拥有关系。事物与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关系来理解事物,并且按照事物来理解关系。”(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中国哲学中的诠释和重构[A].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9,10,43,25,11,16,12.)
我们所说的宇宙本体——道就是一个关系。道不是柏拉图说的独立的理念,也不是黑格尔说的绝对精神。道是关系的概念。道拥有多重关系,最基本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纯粹从客体或纯粹从主体的立场来理解道都是不恰当的。成中英说儒家的认识世界不外乎“内省”、“外观”(注:成中英.知识与道德的平衡与整合[A].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1.)。内省与外观都可以把握道,前者可以称为悟道,后者可以称为观道。成中英十分看重“观”的本体诠释学的意义,曾著专文《论作为本体性诠释学的“观”》论述观的性质与作用。他说:“‘观’是一种事物自然存在呈现的境界,但也可说蕴涵着一种超脱理性与意向的(也可说是不受理性与意向性干扰的)、主体与客体综合为一的直觉方法。”(注:成中英.从真理与方法到本体与诠释[A].本体与诠释[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0.5,41.)观,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感性与理性的两面。感性的观只能得道之“有”,理性的观才能得道之“无”。中国化了的佛教也强调观,《般若波密多心经》开首一句是“观自在菩萨”。“自在”在这里是本体,是佛道。佛道在哪里,在观之中。自然这观为心观——一种具有感性意味的思辩方式。
由于道在观之中,这道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的道,只能是渗透主体理解的道,一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道。中国美学谈的审美与观道是统一的。南朝画家宗炳说:“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双称仁者之乐也。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画山水序》)这里说到三种对待山水的态度:圣人以神法道,贤者澄怀味像和普通人的游山玩水。虽然圣人、贤人、普通人对山水的感悟层次上有别,但都能从山水中悟出道来。由此,宗炳谈到山水画。山水画虽然不是山水,但可以作为山水的替代品,好的山水画不仅要画出山水的貌来,更重要的是画出山水之神也就是道来。“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画山水序》)。不仅山水画如此,一切艺术都以体现道的意味为最高追求。这样,欣赏艺术也能像欣赏山水那样观出道来。
成中英强调道的诠释中的“心智性”。他说:“这样一种诠释一方面参照了世界,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人的心智经验(无论是以感觉、情感或思维的形式)。”(注:成中英.怀特海之象征指涉论与易经、道德经中心思想[A].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C].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134.)作为对世界的参照,它是一种知识体系,作为心智经验,它又必然地通向信仰。作为知识体系与信仰体系的统一构成了道。这就关涉到道的基本性质,作为知识体系,它应是真理性的;而作为信仰体系,它应是宗教性的。知识体系所追求的是真,宗教体系所追求的是善。审美体系追求的美其实就在这两种体系之中。
道作为人的心智经验的构造,总是含有理想的成分的。道的不可预见性、不可知性,就含有理想的意义。理想包含有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与渴望。这点在境界中也得到了体现。境界在生活中总是标志人格修养的最高精神层次,这种最高层次有下线但没有上线,它启示人们不断地升华,不断地追求。王国维将境界的理想性用于艺术,提出艺术境界有“写境”与“造境”之别,说写境重在摹写现实,造境重在表达理想。然而他也指出这两者其实是可以统一的,“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
五
道的关系性以整一性为特点。成中英先生非常看重“道”的整一性。他强调指出,中国哲学对本体的诠释是宏观的、体系的、非语言的,而西方哲学对本体的诠释是分析的、概念的、微观的、语言的。
“道”的整一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道的整一性体现为类似生命的有机性。我们在前面谈过,道具有生命性。生命性总是体现为一种有机的结构。这是不可分解的。《庄子》中写了一个生命体——浑沌,浑沌没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待到好事者将这些一一刻出,浑沌也就没有了生命。中国哲学反对将灵与肉区分开来,而认为灵就在肉中,因此,中国哲学所理解的人是统一的人、活生生的人。中国哲学理解的宇宙是一个生命的宇宙,生命的宇宙最重要的性质之一,是它的有机整一性。
第二,道的整一性体现为真善美的统一性。真善美在中国哲学中从来是不可分的,虽然它们三者各有所不同。我们在中国哲学中经常看到它们的互训、互释的情况,以致于让人疑惑:在中国哲学中真善美三者,到底何者最高?何者最为根本?常有人讲儒家以善为最高,道家以真最高。其实也不尽然。儒家其实是非常看重真的,它说的善最后还是落实到人的天性上去。而天性就是真。道家也是非常看重善的,只是它不把善理解成儒家所鼓吹的仁与礼,而理解成人的生存与发展。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当然也就是善,而且是最大的善。美似是处于真善之下了,其实也不尽然,虽然,儒家与道家经常以善释美,或以真释美,然而它们也经常将美看成人生的最高境界。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就排在“礼”之上,“乐”主要价值是美。儒家典籍《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高于礼也是显然的。荀子说“美善相乐”就没有将善与美区分高下。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最高,然庄子又明确地讲“天地有大美”,将自然归入美。这种价值观也影响到中国美学,在中国美学中,真善美是统一的,中国的艺术创作既讲真,又讲善,还讲美,三者缺一不可。
道是真善美的统一体,作为自然性的存在,它是真,而作为人所理解的存在,它是善与美。这一点也影响到境界。境界作为审美的最高层次,既应是真的,也应是善的、美的。中国美学所理解的“真”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宇宙精神之真;第二,客观物象之真;第三,主观思想情感之真。这三种真,以第一种真为根本,为最高。客观物象之真中所包含的形之真与神之真,形真让于神真。神真包括物之精神与宇宙之精神,中国美学要求将这二者统一起来,从物之精神见宇宙之精神。至于人的主观思想情感之真,即为“诚”,它既是构成真的重要成分,更是实现真的方法、途径。中国哲学对善与美的理解最后都要归结到道,也就是宇宙精神之真上去。
中国哲学既将至真给予道,给予天地,也将至善与至美给予道,给予天地。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在这里为道,为自然而然,它不能解释成自然界,但自然界最为自然而然,所以它成为美的典范;人类本来自自然,也有其自然而然的天性,然因种种原因其天性遭到扭曲或残害,就与自然对立了。庄子强调以鸟养鸟,就出于对鸟的天性的尊重。他反对伯乐治马,因为伯乐的治马从根本上违背了马的天性。庄子据此提出“天放”的概念,“天放”顾名思义,就是自然本性的解放。
天放即“天为”。道家虽然倡自然天放,倡无为,但并不一概地反对有为,只是要求将有为纳入无为的轨道。无为并不是放弃功利,相反,无为才能取得最大功利。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既然“无为”的效果是“无不为”,那就是至善,也就是至美了。
中国美学强调的艺术真实从来不是物象之真,而是宇宙精神之真,而宇宙精神之真,就是道,就是自然。于是,在美学上就有李贽的“画工”与“化工”之说。“画工”与“化工”都是人工,只是画工尚有违背自然的地方,因而现出某种不和谐,而化工则达到类似“天工”地步。天工当然是大工,但不见其工,因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和谐的,所以,化工无工。无工之工乃为至工。宋代黄休复为画制定品评等级,有逸、神、妙、能四格,逸格最高,其原因是:逸格“得之自然,莫可楷模”。
第三,道的整一性体现为差异的统一性。道的功能表现为一个两极分化的创生过程。在这种分化的过程中,道作为“一”,仍然在万物的多样化中表明和持存。“道”的唯一性产生了“和”的概念。在中国哲学看来,“和”最基本的性质是差异的统一,据此中国哲学将“和”与“同”区别开来,同是同一反复,不创造新质,而“和”作为差异的统一,则不断地创造新质。由此影响到中国人的审美观。《国语》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这里说的“一”指同。中国人强调的“和”,其状态是“化”。中国文化创造“化”这个概念是耐人寻味的。“化”强调“异”的界限的消泯,强调新质的产生。审美的境界通常称之为“化境”。这个境界中,一切都是圆融的,统一的。处于化境中的审美者,在精神上完全消泯于境界之中,“物我两忘”,而进入审美的极致。
我们注意到成中英在谈道的整一性、和谐性时总是强调这种整一与和谐的动态性。成中英说:道的本体宇宙论在一种连续和持久的进程中产生了万物的世界,它永远保持着为万物的不断分化和个体化的实在的潜在和谐。因而万物不仅仅与道相联系,而且在一种宇宙时间的本体生成意义上彼此相联系(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中国哲学中的诠释和重构[A].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9,10,43,25,11,16,12.)。这就涉及到道的两个性质:一体性与个体化;永恒性与变异性。道虽然是整一的,但这种整一总是以观念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理解中,而它出现在我们面前都是个别事物。这个别事物互相联系,相因相果,构成一张生态的网络,一个有序的和谐的世界。然而我们从这张生态网络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能感受到道的整体和谐与生命力。所以,一只飞鸟、一片白云、一朵浪花、一缕清风都会引起我们的情绪波动,逗起生活的遐想,甚至有所感悟。故孔子临黄河而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作为个体,其生命的存在总是有限的,但因其生命通向永恒的道,永恒的宇宙,因而它又是无限的。古往今来,人类的哲学思辩总离不开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而当这些问题触动人的情感之弦,又与自然景观联系起来,就构成一种境界,一种特别让人魂牵意荡的情思。于是就有了屈原的《离骚》,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李白的《将进酒》,苏轼的《赤壁赋》,李清照的《声声慢》……它们各有其声调,各有其格律,各有其节奏,但合起来却是一曲和谐的生命之歌、天地之歌、宇宙之歌。
标签:成中英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体感觉论文; 读书论文; 姜斋诗话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阴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