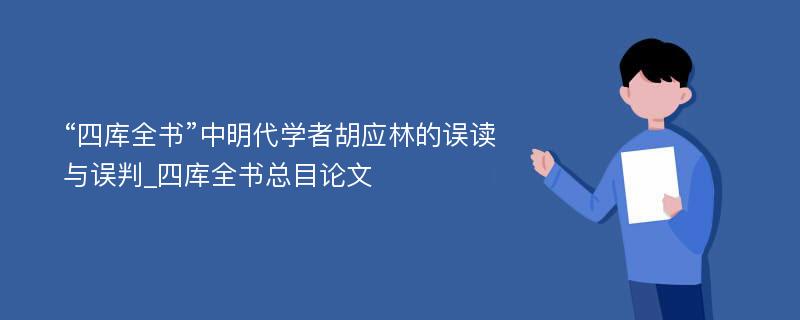
《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误读与误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目论文,误读论文,明代论文,四库全书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中国古代一部集大成的书籍解题目录,范围之广,收书之多,价值之高,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建树,也有对前人失误的指正纠谬,因而成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案头必备之书。但因种种原因,它在指出前人失误的同时,自己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其中,在考论明代学者胡应麟的学术成就之时,就有着比较集中的表现,诚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①。但学界尚未对此进行专题辨正。本着《总目》自身“既悉其谬,即当显为纠正,以免疑误后人”②的态度和原则,笔者谨将该书对明代学者胡应麟成果的误读误判问题疏通董理,敬请学界方家教正。
一 疏忽错谬,有失检点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是其10余种笔记的合集,《总目》卷123《少室山房笔丛》提要,称其中有《史书占毕》、《经籍会通》两书,这是正确的,但却在卷48《世史正纲》提要中误为《史学占毕》、卷85《目录类·序》中误为《经义会通》。在《少室山房笔丛》提要中,曾讥讽胡应麟“捃摭既博,又复不自检点,牴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显然,《总目》自己也犯了它所批评于前人的错误。
《总目》卷140《嘉祐杂志》提要:“宋江休复撰,休复字邻几……明胡应麟《笔丛》云‘江邻几《杂志》,宋人极推之,今不传,略见《说郛》’。然《说郛》所载止十页,而《稗海》、《唐宋丛书》与此抄本皆三倍于《说郛》,应麟殆偶未见也。”所谓“此抄本”即四库馆臣所采用的明内府藏本,当然不是布衣胡应麟所能见到的。而《稗海》、《唐宋丛书》,胡应麟更不可能见到,因为胡应麟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夏,而商濬编辑的《稗海大观》正好成书于当年,《唐宋丛书》则更晚,乃是钟人杰、张遂辰在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编辑,胡应麟又如何能见到呢?《总目》以胡应麟死后才出现之书,批评胡应麟观书不广,“殆偶未见”,未免强人所难了。
关于《阴符》一书的真伪,宋以来诸说纷呈。《崇文总目》疑后人依托;黄庭坚认为出自为此书作注的唐代李筌,绝非黄帝书;晁公武赞同黄庭坚之论,并认为是糅杂兵家语,又妄说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训注,尤可笑;朱熹认为,恐皆李筌所为,是他着意去做,自做自解;陈振孙认为非古书;黄震认为是异端之士掇拾异说而本无所定见之伪书。胡应麟则云:“《阴符经》称黄帝,唐李筌之伪也。筌嗜道好著述,得《阴符》注之,而托于骊山老母以神其说。杨用修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遂良书,则既盛行当世,筌何得托于轩辕?意世无传本,遂良奉敕录于秘书,人不恒睹也。余案《国策》,苏秦干诸侯不遂,因读《阴符》,至刺股,则此书自战国以前有之,而《汉·艺文志》不载,盖毁于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未知孰是,当居一于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权术,而《阴符》兼养生。夫《阴符》实兵家之祖,非养生可概也。此书固匪黄帝,亦匪太公,其为苏子所读则了然,而前人无取证者,故余首发之,俟博雅士定焉。”
对此,《总目》评论说:“胡应麟《笔丛》乃谓苏秦所读即此书,故书非伪,而托于黄帝则李筌之伪。考《战国策》载苏秦发箧得太公《阴符》,具有明文。又历代史志皆以《周书阴符》著录兵家,而《黄帝阴符》入道家,亦足为判然两书之证。应麟假借牵合,殊为未确。至所云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者,考文征明《停云馆帖》所刻遂良小字《阴符经》,卷末实有此文,然遂良此帖自米芾《书史》、《宝章待访录》、《宣和书谱》即不著录,诸家鉴藏亦从不及其名,明之中叶忽出于征明家,石刻之真伪尚不可定,又乌可据以定书之真伪乎?特以书虽晚出,而深有理致,故文士多为注释,今亦录而存之耳。”③《总目》以考证高自标置,但于《阴符》之真伪却不再深做考察,其考证求真之勇气已远逊胡应麟,而其误谬尚有下列诸点:首先,其所谓“历代史志”云云,实际情况是《周书阴符》见诸《隋志》、《新唐志》兵家类;《黄帝阴符》始出于《新唐志》道家类“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书之注释,“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于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帝阴符》,本题云‘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此后,《宋志》才开始于正文著录《黄帝阴符经》一卷,注云“旧目云骊山老母注,李筌撰”。从《新唐志》著录看来,《总目》所称《周书阴符》与《黄帝阴符》为“两书”之说属实。然胡应麟原文为“《隋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考《隋志》道家类无“阴符”名目,此二书均著录于兵家。《总目》所称“《黄帝阴符》入道家”是据《新唐志》和《宋志》,而所指二书又是《周书阴符》与《黄帝阴符》,并非胡应麟所说的《周书阴符》与《太公阴符钤录》,故《总目》讥胡应麟“假借牵合”,乃是自己读书疏忽而错怪了别人。其次,褚遂良曾写一百本之事,胡应麟明云“或以”,并非他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明确指出,“夫曰遂良书,则既盛行当世,筌何得托于轩辕”?明显是反驳褚遂良书一百本以传世之说,而下文紧接着又说:“意世无传本,遂良奉敕录于秘书,人不恒睹也。”更是对上述观点的补充说明。总之,胡应麟是反对“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的推论的。他引《战国策》及褚遂良事,是要说明《阴符》之书,战国时已有,唐时流行不广,所以李筌作注时,才敢假托于黄帝,如果真如“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之说,则世人已见此书,李筌又焉能托之黄帝以欺世人?《总目》不为仔细推寻,而一概误指和归咎于胡应麟,又不惜笔墨,考“石刻之真伪尚不可定,又乌可据以定书之真伪”。此诚为自己误读误解,胡应麟又何尝据褚遂良事以定《阴符》之真伪耶?
二 肤浅表象,不做深求
《云仙散录》,宋人陈振孙称其所引书名皆古今所不闻,《总目》遂径沿袭其说,也称历代史志不载,④。实际上是没有深入考求。胡应麟通过细读其书,指出:“其前六卷所引诸杂说,无一实者,盖伪撰其事,又伪撰书名以实之。至末二卷所引,则诸书大半尚存于今,胡以云悉诞也?”⑤其结论,亦得到了余嘉锡的认同⑥。
胡应麟在世时,天台王太仆曾向他谈起自己在峨嵋山所见日出景象,其言云:“尝宿(峨嵋)绝顶光相寺,于时早秋,晓起远望……时寺鸡三号耳,残月犹在。远见西极荒垂,有一点尖明若火光者,因以问僧,僧云此天竺雪山为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顷之日出,而此山隐隐,炫耀天际。已而,日色遍满大千,则山光不复明矣,但见一粉堆耳。”胡应麟即以此考证佛经之文:“余味此言,乃知佛经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刚山顶’为足证也。”⑦之后,稍晚于胡应麟的沈德符,竟据此指责胡应麟误以峨嵋山为佛经金刚山,《总目·少室山房笔丛》条,也直接征引沈德符之说,以证明胡应麟考证之舛讹。实则胡应麟此条文义甚明,其金刚山之称,乃指“天竺雪山”,而非王太仆当时所在的峨嵋山。沈德符误读胡应麟原文而妄讥,《总目》未能核对胡应麟原文而深加考索,就径直引录了沈德符的误读误解,以致再次以讹传讹了。
关于南朝梁元帝《金楼子》一书,《总目》卷117提要云:“《隋书》经籍志、《唐书》、《宋史》艺文志俱载其目为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谓其书十五篇,是宋代尚无阙佚。至宋濂《诸子辨》、胡应麟《九流绪论》,所列子部皆不及是书,知明初渐已湮晦,明季遂竞散亡。”《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分别著录了所属时代的国家藏书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某书在史志目录上的著录与否,探寻该书的存佚情况。《总目》在此考察《金楼子》一书“明初渐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使用的就是通过目录考察书籍存佚的方法。但问题是,这一方法本身固然没有问题,可是宋濂《诸子辨》、胡应麟《九流绪论》有无作证的资格呢?宋濂《诸子辨》作于元末明初,时间上符合《总目》所说的“明初”,但它只是一部辩论诸子学说是非得失之书,是儒家正宗思想与诸子“邪说”之辨,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决定对诸子的存留取舍,使道术咸出于一轨。因此该书对所考辨的古籍是有所选择的,并不是周秦以来直至宋代的全部子部书籍的目录,还不能把它同其他目录著作等同看待。所以,《总目》把它作为考察《金楼子》在明初存佚与否的证据,从方法和原则上说,是根本错误的。胡应麟《九流绪论》的情况更是这样。不但胡应麟本人生活于嘉靖三十年至万历三十年(1551—1602年)之间,与《总目》所说的“明季”时间不符,至于《九流绪论》本身,胡应麟在序中述其编纂缘起云:“子书盛于秦汉,而治子书者错出于六朝、唐、宋之间,其大要二焉,猎华者纂其言,核实者综其指……余少阅诸子书,辄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于二家之弗能合。则于诵读之暇,遍取前人铨择辩难之旧,以及洪氏《随笔》、晁氏《书志》、黄氏《日抄》、陈氏《解题》、马氏《通考》、王氏《玉海》之评诸子者,及近粤黎氏、越沈氏题词,复稍传诸作者履历之概,会为一编,时自省阅。第诸家之外,古今文人学士单词片藻,品骘尚繁,并欲类从……辄捃拾其中诸家见解所遗百数十则,捐诸剞氏,备一家言。”其中前二卷是对先秦、汉唐子书作者、篇目、流派、主旨及真伪的考证辩驳,特别对前人的铨择辩难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第三卷专论小说及类书,对二者的源流演变做了系统考证论述。显然,它也根本不是子部书籍目录,又哪里有《总目》所要求于它的证人资格呢?因此,要想知道《金楼子》在明代存佚与否的情况,就必须寻找《诸子辨》和《九流绪论》以外的其他资料,《总目》把这两部著作拿来作为考察《金楼子》在明代存佚与否的唯一证据,其结论只能是肤浅表象,似是而非。
《总目》卷135《太平御览》提要,称此书“征引至为浩博,故洪迈《容斋随笔》称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书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不传者十之七八。胡应麟《经籍会通》则以为,是编所引大抵采自类书,非其书宋初尚存,力驳迈说之误,所言良是。然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或言国初古书多未亡,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诸家类书之旧耳。以《三朝国史》考之,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而《御览》所引书多不著录,盖可见矣。是迈所云云,振孙先已驳之矣,应麟特抄袭其说耳。”《总目》所引陈振孙之论,系其《直斋书录解题》卷14《太平御览》条原文。如果只就此立论,当然是胡应麟抄袭了陈振孙。但是考证事件原委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在没有考察胡应麟原文之前,就遽然下此结论,未免过于草率。胡应麟《经籍会通》卷4说:“洪景卢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华,或未晓此曲折,诸家亦鲜论及,漫尔识之。”显然,这段议论是胡应麟通过自己“钞拾类书”的编辑工作得到的认识,因而他说是“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胡应麟一生从各种类书中辑佚、整理而编辑成多种古书,虽然未能全部传世,但却证明他所言是有事实根据的。他认为洪迈之所以失误,或许就是因为不了解“钞拾类书”这一编辑工作的个中原委,而其他人也很少论及此点,所以他才借《太平御览》一事加以说明。由此可见,虽然表面上胡应麟与陈振孙结论相同,胡应麟也读过陈氏之书,但他们得出结论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是各自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的,因此不能径指是胡应麟抄袭了陈振孙。此外,据《总目》卷142《搜神记》提要:“胡应麟《甲乙剩言》曰,姚叔祥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乎?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匮幽岩土窟掘得耶?大抵后出异书,皆此类也。斯言允矣!”胡应麟把从类书中辑佚、整理而编辑成古书的情况,视作“后出异书”的一种类型,对此,《总目》态度鲜明、言简意赅地指出其言允当,揭出了这类“后出异书”的来源本质。由此也可以证明,胡应麟所说“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之言,绝非虚论。从而再次证明,他对洪迈之说的反驳,确实是来自于个人的编书实践,而不是抄袭自陈振孙。但《总目》却删去了胡应麟《经籍会通》中“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的一段自我表白的话语,又没有对胡应麟的学术实践做通盘整体的考察,未能仔细推寻其所以然之故,从而误判成胡应麟抄袭陈振孙的冤假错案。
三 曲解文义,以显己功
《总目·类书类·序》云:“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但实际上,胡应麟并没有说过要将类书列入集部。其原文曰:“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佛、道)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⑧显然,《总目》是曲解了胡应麟的原意,由此对胡应麟所作的“无所取义,徒事纷更”的批评也就站不住了,而其关于类书在“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的认识,则显然又与胡应麟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自《隋书·经籍志》纵横家明确著录有《鬼谷子》一书后,柳宗元首先怀疑其为伪作,然其依据只是汉代没有著录此书。北宋《新唐志》以为苏秦作,南宋晁公武、明代宋濂均依《史记》,以为是战国时鬼谷子撰,但亦都列出《新唐志》之说以存异。胡应麟总结前人之说后进一步加以思索:“余读之,浅而陋矣,即仪、秦之师,其术宜不至猥下如是。”“《汉志》绝无其书,文体亦不类战国,晋皇甫谧序传之。案:《隋志》(应为《汉志》)纵横家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隋·经籍志》已亡。盖东汉人本二书之言,会萃附益为此,或即谧手所成而托名鬼谷,若子虚、亡是云耳。”⑨并批驳了杨慎把《汉志》中的《鬼容区》指为《鬼谷子》的附会之说。对此,《总目》卷117《鬼谷子》提要云:“胡应麟《笔丛》则谓《隋志》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必东汉人本二书之言,荟粹为此,而托于鬼谷,若子虚、亡是之属。其言颇为近理,然亦终无确证。《隋志》称皇甫谧注,则为魏晋以来书固无疑耳。”在肯定胡应麟“颇为近理”的同时,却将胡应麟原文“盖东汉人本二书之言,会萃附益为此,或即谧手所成而托名鬼谷”,歪曲为“必东汉人……托于鬼谷”,然后又引“《隋志》称皇甫谧注”云云,得出“为魏晋以来书固无疑耳”的结论,炫耀这是自己考证的成果。其实只要将两处文字比堪对读,即可发现,《总目》所做的,恰如其批评于明朝学者的“抄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乃窃前人论断为己有,因为“谧手所成”当然就是“魏晋以来”了。
《总目》卷85《史部·目录类序》云:“郑元(即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题,胡应麟《经义会通》谓始于唐之李肇。案《汉书》录《七略》书名,不过一卷,而刘氏《七略别录》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题而何?《隋志》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序,推寻事迹。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其文甚明,应麟误也。”这就不但纠正了胡应麟所称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错误,还考证出正确的事实,即刘向、刘歆时即已作有书目解题,这当然是《总目》显示自己的考证功绩了。不过,胡应麟书名本为《经籍会通》,并非《总目》这里所说的《经义会通》,这很可能是出于一时笔误,不值得深究。真正成问题的是,《总目》对胡应麟的这一考证纠谬,是否真的与胡应麟有关呢?
首先,不但胡应麟《经籍会通》中根本没有提到唐代李肇,就是其所有传世遗文中也没有说过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话,因此,《总目》所指胡应麟称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说法,就成了无中生有的捏造。当然,这也可能是《总目》记忆有误,将别人的错误说法张冠李戴地加给了胡应麟。但是,不管哪种错误,胡应麟与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说法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关于刘向父子与书目解题的关系,胡应麟有着清醒的认识。其《经籍会通》卷一原文如下:“书目第记书名,卷轴概不能广。唐《群书四录》乃至二百余卷,何以浩繁若此?盖各书之下必有论列,若歆、向所编者……郑(樵)《(二十)略》有刘歆《七略》七卷,又《七略别录》二十卷,岂七卷者目,《别录》乃论列与?”卷二又云:“《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耳。向、歆每校一书,则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近世所传《列御冦》、《战国策》皆向题辞,余可概见。因以论奏之言,附载各书之下,若马氏(即马端临)《(文献)通考》之类,以故篇帙颇繁,惜今漫无所考。”显而易见,只要把这些话完整地读过来,就能清晰地看得出,胡应麟已经明白指出了书目解题起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事实。但《总目》却对此视而不见,先是给胡应麟捏造一个“李肇”云云,然后再自己考证一番,以耀示己功,最后又反过来对胡应麟大加批评,未免是错上加错了。
四 因袭前人,不注所出
明代学人,援引前人常常不注出典,《总目》对此多所讥切,指出此乃“明人著书之通病”,“盖明人好抄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以后,往往皆然”。就连以博洽著称当时及后世的焦竑,也被《总目》指认为“多抄袭说部,没其所出……亦足见明之无人”⑩。实则,《总目》自己也有不少这类行为。
《总目》因袭前人而不注所出,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因袭前人的方法和原则。如对《世说新语》,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论云:“《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11)刘知几是史学理论家,一再强调实录和真实,这本没有错,但他以实录征实之史法来衡评并非史学专书的《世说新语》,未免强人就己,自然大为偏颇。《总目》卷140《世说新语》提要:“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这显然是因袭了胡应麟的认识方法和原则。
北宋官修《新唐书》行世以后,五代时所修《旧唐书》渐被废弃,幸好明嘉靖年间有人对《旧唐书》加以搜集、重刊,才得免于失传,而明代学者杨慎、李梦阳、何良俊等竟认为旧书远胜新书,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清代顾炎武、王鸣盛都认为二书互有短长(12),《总目》卷46《旧唐书》提要亦持各有优劣、相辅而行的评价。此后,新旧《唐书》此优彼劣之论息。不过,最早重新提出新旧《唐书》评价问题的并非顾炎武、王鸣盛,更非《总目》,而是他们之前的胡应麟。胡应麟在其《史书占毕》卷1、《艺林学山》卷5《二唐书》、《少室山房类稿》卷101《读新旧<唐书>》和《诗薮》杂编卷4中,从史料价值高低、文笔优劣、体例妥当与否等不同角度,对二书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二书得失,犹齐楚鲁卫”(13),“两存之备考可也,举一而废一不可也”(14)。显然,《总目》的评价态度和原则,与胡应麟并无二致。
二是因袭前人观点。如《竹书纪年》记有“虞九年,西王母来朝”之事,胡应麟在《三坟补逸》卷上为之作注云:“西王母已见于此,不始《周穆》(指《穆天子传》)也。以余考之,盖亦外国之君。”此后《总目》卷142《穆天子传》提要亦云:“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至于前人是否已经有此观点,则一概不提。
《鬻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道家、小说家并有著录,说明此书初有名同实不同之二家。宋人叶梦得和明初的宋濂都注意到《汉书》两载《鬻子》之事,但因不明《汉书》类例,并不明白其初本有二家,反而认为是班固自相矛盾,莫知孰是,更不明白今传为何本。胡应麟明确揭示出《鬻子》古有二家,今传者“非道家言”,“然道家固实有《鬻子》”,由《列子》所引三条看,“其为道家言,居然可见”,“班氏以列道家,亡怪也”(15)。“盖《鬻子》道家言者汉末已亡,而小说家尚传于后,人不能精核,遂以道家所列当之(按:汉后诸史《艺文志》及诸家目录皆将《鬻子》著录于道家),故历世纷纷,名实咸爽,《汉志》故灼然明也。”(16)亦即今传《鬻子》乃小说家,不过,“其书体兼儒杂,既绝不类《列子》所引语,而《列》所引语亦略不见篇中,故知其决匪道家,然亦未必小说家之旧。大概后人掇拾残剩,而补苴缀辑之功亡万一焉,故其章次、篇名皆混淆错乱,视他子书,特寥落无足观”(17)。此后,《总目》也发表意见,指出:“考《汉书·艺文志》,道家《鬻子说》(应为《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是当时本有二书。《列子》引《鬻子》凡三条,皆黄老清静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文格略同,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18)此说显然与胡应麟之论相合,用《总目》自己的话说,就是“特抄袭其说”而“没其所出”,但它在分类时却将《鬻子》归入杂家,又与它在这里的考证结果自相矛盾。
《子夏易传》,《总目》称:“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今本又出伪托,不但非子夏书,亦并非(唐代)张弧书矣。”(19)实则胡应麟早已指出:“据陈氏所论推之,当是汉末人依托,至隋残缺,唐宋人复因隋目,取王氏本伪撰此书。正犹《乾坤凿度》,本汉世伪撰,至隋唐亡逸,宋人复伪撰以行。伪之中又有伪者也。”(20)
《洞冥记》,晁公武、陈振孙皆认为汉郭宪撰,《总目》则云:“所载皆怪诞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又词句缛艳,亦迥异东京。六朝人依托为之。”(21)此论不虚,但亦属承袭前人而来。胡应麟即已指出此书“题郭宪子横,亦恐赝也。宪事世祖,以直谏闻,忍描饰汉武、东方事,以导后世人君之欲?且子横生西京末,其文字未应遽耳。盖六朝假托,若《汉武故事》之类耳(自注:《后汉书》,宪列方技类,后人盖缘是托之)”(22)。清初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直接引用胡应麟之说作为辨伪之语,相比《总目》的缘饰手法,姚际恒显然坦白明快得多。
传世本《遂初堂书目》只录书名,不录卷数,就连各书的作者也大多不予著录,即便著录,称谓亦不整齐划一,如有的以名,有的以字,有的以官衔,有的以姓,可谓极为疏漏。对此,《总目》认为:“惟不载卷数及撰人,则疑传写者所删削,非其原书耳。”(23)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因为《遂初堂书目》全载于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而《说郛》对所收录的前人著作确实有删节,又很少做出相关说明。不过,最早发此疑窦者并非《总目》,而是胡应麟。胡应麟不但多次指出《遂初堂书目》的这种“疏略乃尔”的著录情况,而且明确指出,这与其作者尤袤“颇负博洽称”的实际身份并不相符,考虑到《遂初堂书目》全载于陶宗仪《说郛》,胡应麟认为,此“或陶氏《说郛》所节也”(24)。这比《总目》说得还要直白清晰。
因袭前人,不注所出,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误读与误判,但它既然构成抄袭,当然就是对前人研究工作的不尊重,是在内心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实质性承认而表面上却不予承认,从而有意无意地形成一种间接的、特殊形式的误读与误判。但不管如何间接与特殊,仍然是一种错误,诚如《总目》自己所说,是“病”态的表现。
宋末元初的史家胡三省曾经说过,“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25)。胡三省是在注释《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体认到这一点的,因而他使用了“前注”、“吾注”二词。实则他此言也可以推广而应用于所有撰文著书之事。《总目》的学术价值是相当高的,“衣被天下,沾溉无穷”,“功既巨矣,用亦弘矣”(26),已为二百年来的学术发展所证明。但迫于期限无力从容研究,乃恃其博洽,率尔操觚,高自标置,也正是犯了“人苦不自觉”而又不能时时严谨克己的毛病,因此仍存在种种失误,这是我们后人不能不引以为戒的。
注释:
①此为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语,见《史通》卷8《书事》,《史通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②永瑢等《总目》卷119《卮林》,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同)。
③《总目》卷146《阴符经解》。
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云仙散录》,《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总目》卷140《云仙杂记》。
⑤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下,《少室山房笔丛》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17《云仙杂记》,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⑦胡应麟《甲乙剩言·王太仆》,王文濡辑《说库》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⑧(11)(16)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下,《少室山房笔丛》本。
⑨(15)(17)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中《鬻子》,《少室山房笔丛》本。
⑩分别见《总目》卷119《名义考》、卷132《珍珠船》、卷128《焦氏笔乘》。其他如《总目》卷50《春秋别典》、卷60《苏米谭史广》、卷62《吴中人物志》、《献征录》(焦竑著,“或注或不注”)、《廉吏传》、卷123《清秘藏》、卷127《览古评语》、卷128《紫桃轩杂缀》、《书蕉》、卷131《谈资》、卷132《稗史汇编》、《偶得绀珠》等条,均指责明人不注出典之弊。
(12)顾炎武《日知录》卷26《旧唐书》、《新唐书》,《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9《二书不分优劣》,丛书集成初编本。
(13)胡应麟《艺林学山》卷5《二唐书》,《少室山房笔丛》本。
(14)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101《读新旧〈唐书〉》,1924年永康胡氏梦选楼刊《续金华丛书》本。
(18)《总目》卷117《鬻子》。
(19)《总目》卷1《子夏易传》。
(20)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中《子夏易传》,《少室山房笔丛》本。胡应麟和《总目》都认为《子夏易传》初本即是伪撰,因为他们都认为《子夏易传》的最初作者子夏,即是孔子弟子卜商。实际这完全是误解,见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8页。
(21)《总目》卷142《汉武洞冥记》。
(22)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下《洞冥记》,《少室山房笔丛》本。
(23)《总目》卷85《遂初堂书目》。
(24)胡应麟《经籍会通》卷1,《少室山房笔丛》本,并参其《少室山房类稿》卷116《报童子鸣》。
(25)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中华书局1956年版。
(26)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见该书卷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