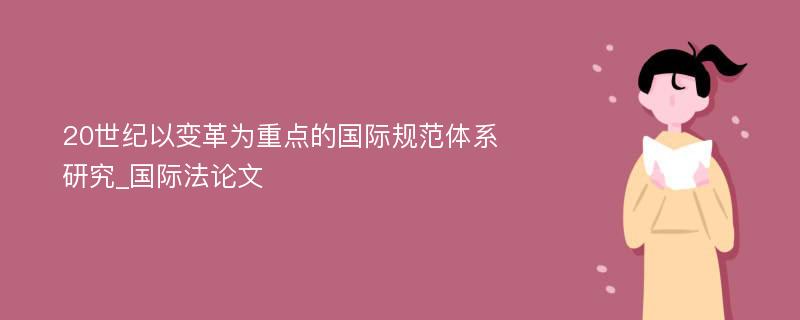
论20世纪国际规范体系———项侧重于变更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重于论文,体系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同先前的国际规范体系一样,20世纪国际规范体系当中最带根本性的部分是国际社会成员资格认定,也就是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的载体认定。它们最具时代特征和世界政治影响的结果,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式问世并且迅速扩展的人权国际规范。当然,像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国际法学家承认的那样,主权国家即使已从先前据有的现代国际社会唯一种类成员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也仍然是其主要成员和国际权利与义务的主要载体。因为,“国家是对人口和领土的合法权威之所在。只有依据国家的权势、特权、管辖界限和立法权能,领土界限和管辖、官方行为责任以及各国间共处的许许多多问题才能够得到确定”。(注:Walfgang Friedman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Law (London,1964),p.213.)然而,瓦特尔在18世纪中叶宣告、奥本海甚至迟至20世纪初仍在宣告(注:“国际法是关于国家彼此间存在的权利和与这些权利相应的义务的科学”(瓦特尔语);国际法“只是、并且完全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奥本海语)。 见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 New York,1977) ,p.34; L.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 (London,1905),V.1,Chapter 1.)的那种清一色状况,毕竟业已结束,国际社会成员资格回到了格老秀斯时代那种含糊、混杂的状况。各种政府际组织、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团体和公司以及个人,都被广泛认为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和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载体,而这总的来说已具有颇为厚实的法律和道德依据。就其完全形式来说,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载体(在法律上就是国际法的对象或国际法人)是这么一种实体:能够拥有这权利与义务,能够对国际侵权行为提出惩罚或赔偿等要求,能够在国际上缔结有效的条约和协议,并且享有不受国家管辖的特权和豁免权。世界性或地区性的政府际组织就大体上符合这些资格条件,尤其是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注:Ian B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4th edition(Oxford,1990),pp.58-59,680-681.)事实上,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就已经开此先河,它同联合国一样,是“对国家及其行动自由乃国际体系之绝对必需这一前提的挑战。”(注:William D.Coplin,"International Law and Assumptions about the State System,"in Phil Willaims et al. eds.,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Clif.,1994),pp.223-224.)个人成为国际权利和义务的载体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复归,因为格老秀斯时代就是如此。(注: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pp.30-31; H.Lauterpacht,"The Grotia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in Richard Falk et al.eds.,International Law: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Boulder,Colo.,1985),po.16-18.)个人重新承担国际义务或责任直接源于法西斯大肆侵略和疯狂施暴造成的刺激和警示。(注:尽管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法学界就相当广泛地认为国际法将某些罪行的责任加诸于个人,并且可以由得到适当授权的国内或国际法庭施予惩罚。见B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p.561.)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章程(附于1945年8月缔结的《起诉和惩罚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协定》)规定,必须追究反和平罪、战争暴行罪和反人类罪的个人罪责。该法庭针对纳粹主要战犯推脱罪责的辩辞和相关的国际法传统观念,声明必须拒绝下述主张,即国际法只同主权国家而非个人的行为有关,国家犯罪行为不能由其贯彻者个人承担罪责。该法庭宣告:“国际法对个人如同对国家加诸义务和责任……章程的根本,就在于个人有国际责任,它们超越一个国家加诸的服从本国的义务。”(注:Ibid.,pp.561-562.)上述规定和宣告由联合国大会确认为国际法原则。1948年,基于反人类罪这一概念,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和惩罚大规模屠杀罪公约》,它同1949年《日内瓦公约》一样,都规定了个人罪责。然而尽管如此,要将个人当作完全的国际法对象仍是不正确的,因为个人显然缺乏这种角色的某些资格条件,而且个人的国际义务只是就某些问题和在某些情况下才存在。(注:Ibid.,pp.67,69.)
与这义务相比,政治和社会意义上更重要的是个人及其群体(种族、民族、社会阶层、性别群体等等)的权利,即人权。人权在世界政治和法律议程中所以取得重要地位,起初同样归因于法西斯肆虐造成的刺激和警示,同时当代国际法自然法学派泰斗劳特派特等人起了引人注目的先驱作用。(注:劳特派特在1945年大力倡导制订“国际人权法案”。见H.Lauterpacht,An International Bill of the Rights of Man (London,1945).)在当时人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出的教训当中,非常突出的一条就是法西斯对内大规模剥夺人权与其对外大规模破坏和平密切相关。联合国宪章体现了这种认识,并且由此将维护人权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一起,规定为联合国的主要目的,从而开始了当代人权国际规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注:Lung - chu Chen,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 New Haven,1989),p.204.在此以前,人权国际规范只存在于一个相当狭窄和次要的领域,即保护境内外国人的国民待遇权利,或者“最低限度国际标准”权利。见ibid.,pp.201-204.)这个过程以现代人权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且其演化序列同现代人权观念的演化序列基本一致。(注:下面关于这后一个演化序列的阐述主要依据Stephen P.Marks,"Emerging Human Rights:A New Generation for the 1980s?" in Falk et al.eds.,International Law,pp.501-513.)第一代人权观念是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弘扬的个人公民和政治权利及财产权利,它们的主要特征“按照大多数自由主义的表述,是无虞某物(政府、他人干预)‘之自由’,即可以在其中实现一个自己的目的的一块个人天地,而另一些表述方式还加上参与某事‘之自由’,即可以在其中通过公意享有某种更大的自由的一块公共天地。”(注:R.J.Vincent,"The Ideas of Rights in Interantional ethics,"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Mapel eds.,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1992),p.254.)第二代人权观念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一代人权之恶果——国内外自由剥削权的反应和抗议,它主要由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部分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者倡导,内容为借助于国家的积极干预甚至组织来实施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人权。第三代人权观念问世于20世纪非西方对西方造反的伟大浪潮,用1977年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表述,在于人权包括免于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外国侵略和侵略威胁的权利,以及民族充分自决、各国行使充分的经济和自然资源主权的权利。第四代人权观念同全球性问题意识密切相连,它将享有和平、发展、健全的生态环境、人类共同资源的利用开发和在人道主义灾难中获得援救的权利包括在人权当中。(注:人类共同资源即“人类共同继承物”(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包括公海海底、 南极洲、 外层空间甚至文化传统和科技进步等。 见 Marks,"Emerging Human Rights,",p.509.)
基于人权观念的当代人权国际规范首先以根本原则的形式,见于《联合国宪章》,它开宗明义地规定联合国致力于促进全世界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其他某些条款中予以重申。1948年,联大通过《普遍人权宣言》,其最大意义或许是为说明宪章的笼统规定提供了一个权威指南。16年后,经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机构长期准备,联大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议定书,由许多国家政府签署后于1976年生效。这两个对缔约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使人权比较全面、比较细致地法规化了,尤其是后一个公约“在权利的界定方面更具体,对尊重这些具体权利的义务的陈述更有力,较好地提供了检验和监督的办法”,并且规定了国家和个人进行控诉和申诉的程序。 (注: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pp.574-575.)它能做到这些,颇大程度上是参照了区域人权公约——1950年底缔结、近三年后生效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欧洲公约》,而它本身也同这欧洲公约一起,成了另一个区域人权公约——1969年问世的《美洲人权公约》的参照蓝本。1981年,《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由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五年后生效。这第三个区域人权公约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既具体规定了个人权利,也具体规定了个人义务,以政治调解而非司法审理为解决一般人权争端的途径,并且强调非洲各国人民有自由处置本国财富和资源的权利。这些都反映了欠发达国家的特殊性。(注:对欧、美、非三个人权公约的较详论述见ibid.,pp.574-577.)
按照一位国际法学家的看法,人权国际规范到20世纪末期应被认为已取得不容违反、不容置疑的普遍国际法规范(jus cogens)的地位,任何与之抵触的单方面行动或国际条约和协定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注:Chen,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p.215.)现在可以认为, 至少在原则上认同并且大体遵守基本的人权国际规范,正如大体奉行自决原则一样,成了国家的一大合法性标准,尽管它在这方面的地位同自决原则相比, 仍是较有争议的。 (注:参见B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p.601; 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Ten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1993),p.201.)应当说, 人权观念的大普及,人权国际规范的迅速发展和较广泛实施,是世界史上特别重大的进步之一。然而也应当看到,人权国际规范在其现有的、被西方国家片面展示和解释成过度偏重个人及其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形态上,既给维护国际秩序造成困难,也阻碍国际正义的全面实现。很明显,个人人权只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且它的实现一般有赖于集体人权(例如民族权利、社会阶级权利、年龄或性别群体权利、甚或国家主权)的实现。同样很明显,公民和政治权利也只是人权的一部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至少同等重要。还有,对个人人权乃至所有其他人权的理解,连同其实现的途径和速度,都分别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制度内必然多有不同的具体条件。不顾所有这些情况,依凭自己在政治、经济、信息传播等方面的优越权势,力图使世界其余国家和人民接受和奉行关于人权的上述片面解释,有时甚至是出于同人权大致无关的政治目的,那就难免引发或加剧国际紧张。不仅如此,如杰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海德利·布尔所指出:“关于国际法之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信条推至其逻辑的极端,那对人类组织为一个主权国家社会的整个原则便是颠覆性的。因为,如果每个人的权利都能被申张于世界政治舞台,盖过他所属的国家的权利要求并与之作对,而且他的义务能被宣布为与他作为该国的一名忠仆或公民的地位无关,那么国家作为一个统治其公民,并有权得到他们服从的实体的地位便会受到挑战, 主权国家社会的构造便会陷于危险。 ”(注: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p.152.)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贬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重要性,漠视它们往往作为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基础的价值,并且不顾这么一个事实,即有时不得不通过限制或损害个别人的“人权”来促进实现一国全体人民的人权,(注:这一点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见B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p.601.)显而易见有背于一大国际正义要求——决定性地改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包括发达国家的部分人民)的贫困、缺乏教育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状况。至于象西方国家所主张并不时照此行事的那样,将人权、特别是个人公民和政治权利置于欠发达国家的主权之上,更是有背于国际正义。尽管事实表明,当代无论何种形态的国家,其权利的行使有时都导致国家对人权的无理压制,然而事实同样表明,当代大多数国家,无论其形态互相间有何不同,都是本国人权的主要保护者和促进者。对于世界上许多数十年前还处于殖民半殖民统治和中世纪式国内奴役之下的欠发达国家人民来说,他们现在的国家差不多可以说是他们的人权所曾有的第一个保护者和促进者,其主权、安全和稳定对他们的生命、自由、财产和福利来说至关重要,(注:时殷弘:“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J〕,《欧洲》1996年第1期,第15页。参见 Hedley Bull,"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Politics," Daedalus,V.108(Fall,1979).)虽然与此同时,其不同程度上的赢弱、低效、不成熟又往往是充分实现或维护这些价值的首要阻碍。 (注: K. J.Holsti,The State,War,and the State of War (Cambridge,1996).)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人权高于主权,同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主权高于人权一样,是不正确的。
二
20世纪国际规范的根本来源尤其在于先前历史时代里被称为自然法的那种可谓普遍甚而绝对的根本伦理。(注:它们的根本内容,见自然法大师格老秀斯的表述:Michael Curtis ed.,The Great Political Theories,V.1(New York,1981),p.321.)它们实际上就是世界所有(或差不多所有)各民族在其文明时代共有的根本道德规范或道德概念。这些规范或概念以人的理性、特别是社会亲和倾向为前提,以公正为精神实质,以实现、维持或促进和平的和尽可能较为公正的社会生活为根本目的。(注:参见 Lauterpacht, "The Grotia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p.18;J.L.Brierly,The Law of Nations,6th edition(Oxford,1963),p.17.)就社会的规范体系来说,它们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据以补充已有的具体规范的常在源泉,并且判断这些规范是否合乎道德和理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是否终将保持或取消之。 (注:参见 Lauterpacht, "The Grotia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p.17; 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 and Values (Dordrcht,Netherlands,1995),pp.280-281.)在国际社会中,这样的根本伦理非常概括地说意味着尤其给予个人和其他弱小的国际行为体起码的尊重,并在国际关系中厉行公平、通情达理和守信。(注:Oscar Schachter,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 (Dordrecht,Netherlands,1991),pp.55-56.)它们对于国际法至少起了四大作用:第一,它们使国际法能够扩展到国际关系的“社会”领域,特别是扩展到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之中;第二,它们有力地促成了人权国际规范和贯彻自决原则的各类禁止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国际法规;第三,它们不仅像下面将论述的那样,为20世纪决定性地加强对国际暴力的法律限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基于人类共同体观念,促成了对核武器之类大规模毁灭性暴力工具的限制或禁止;第四,它们促使那关系到世界多数人口生存和幸福的国际分配正义问题开始进入国际立法领域,同时促使这正义成为世界南北两方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道德共识。(注:参见ibid.,pp.49,54-55.)归根结底从根本伦理出发来形成一系列新规范,这就使当代国际规范同18和19世纪相比具有了鲜明的根本特征,即侧重道义规定而非现状确认,侧重弘扬正义而非维持秩序,侧重促进变革而非追求稳定。(注:“应当注意,国际法(可以)是一种媒介和工具,用来谋求国际秩序以外的、并且的确可以是与之相反的目的。法律工具有时被用来例如促进世界政治中的正义……而这一目标对国际秩序可以是破坏性的。 ”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p.145.)这样的特征完全符合决定20世纪世界政治面貌的三大主要新力量——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和兴起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与苏联——的政治性质,也完全符合对形成新规范贡献颇大的西方国内和平与人权等类运动的伦理追求,(注:具体的论说见时殷弘:“现代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第三节。)虽然所有这些势力在许多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价值观和正义观。
必须着重指出,在传统国际规范的很大部分基本成份(特别是关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规范)依然保留下来、或者仅被作了并非本质性的修改的情况下,上述重大变化必然导致当代国际规范体系在总体和多项局部上新旧相间,自相矛盾, 含糊不清, (注:参见Coplin,"International Law and Assumptions about the State System," pp.288,231.)尤其是在国家主权与人权、与民族自决权、与国际组织权利这三对非常重要的关系上。一方面,人们不应当象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保守派那样,在早已改变了的时代里墨守国家主权绝对观,因为这样既有违历史潮流,也不利于消除世界许多地方由国家行使或保护的国内不正义。另一方面,人们更不应当像当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思潮那样,信奉国家主权过时论,因为这种理论说到底,反映并促进着美国或其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的世界霸权目的,它代表当今和未来可预见的时期里最大的国际不正义。这里所以说“更不应当”,不仅是由于美国及其西方伙伴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而且是由于国际规范已经在限制和侵蚀国家主权的方向上有了很大更动,以致两者加起来使得在此谈论的变化与稳定之间过于失衡。20世纪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法的改变除前面已阐述过的权利与义务载体的扩展外,包括国际法的范围与其来源(或曰立法方式)的变化。国际法所涉及的范围已扩大到一整系列原先不存在或少有国际法规则的经济、文化、通讯和生态问题上,并且已将一些新的跨国性、全球性政治和安全问题包括在内;在某些方面,国际法的立法程序、即国际法的来源也有所变化,有关的绝大多数主权国家(而非原先那样所有有关主权国家)的赞同,甚至多半由联合国大会决议体现的“占压倒优势的国际舆论”,已成为连保守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国际法学家也予承认的国际法立法依据,战后在清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等方面的情况尤其如此。(注: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pp.145-158;Henkin,International Law,pp.280-281.关于联大决议的法律地位,参见Falk et al.cds.,International Law,pp. 127- 128,146;Brownlin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pp.14-15.)
三
同18和19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时代相比,20世纪全球国际社会规范的主要新内容大致集中在关于国际暴力和国家主权的规则两方面,它们合起来构成了国际法中新的国际共处规则。关于国际暴力的规则的主要新内容,首先在于重新引入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这区别在18和19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时代被弃置,因而只要是主权国家进行的战争便都具有合法性。(注:几乎没有什么人比美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汉密尔顿更明确.更透彻地表述了关于战争的道义平等和法律平等。这位“现实政治”(realpolitik)思想家在1784 年写道:“至于战争的外在效应,国际志愿法完全不知道这种争斗有什么正义不正义之分,而是在和约中把争斗双方放在同等地位,因为既然它们不承认有任何公共裁决者那么媾和时倘若双方不站在同一权利地位,就绝无可能调节分歧或结束战争。这是一项确立不移的原则。”引自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p.222.Arthur Nussbaum,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al (New York,1961),pp.182-183.)从国际联盟盟约开始,经1928年非战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最后到联合国宪章,战争终被区分为正义和不正义的(也因而被区分为合法和不合法的):侵略战争是不正义战争,应予禁止或受到国际社会制裁,自卫战争和对侵略国的集体武力惩罚则是正义战争,所有爱好和平和遵守法律的国家都应予以支持。(注:关于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限制国家自己决定何种形势下需要自卫以及为何自卫的权利,见Schachter,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pp.136-137.)由此,在法律和道义上,战争本身受到了严重限制,甚至可以说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限制,因为使用武力不再能被当作国家从事国际政治的天经地义的日常工具。正因为如此,一位权威的国际法学家在60年代初宣告,“过去半个世纪的突出特征,在于一种对战争之发生……无动于衷的法律体制决定性地转变为一种对国家诉诸武力的权能施加颇大限制的法律体制”。(注:Ian Brownlie,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cs (Oxford,1963),p.424.)也正因为如此,另一位国际政治学家断定“当代对正义战争信念的法律承诺代表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或者说代表了“国家作为独立实体这一法律概念的全盘革命,因为它将废除主权特权中最本质的一项,即施加强制的自由。”(注:Coplin,"International Law and Assumptions about the State System," pp.229,231.)新的国际规范不仅禁止侵略战争,而且如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那样禁止以武力威胁侵害别国领土完整和独立以及解决任何国际争端,并且为和平解决设立了一系列在经典外交之外的国际组织干预和调整程序。所以有这些历史进步,一要归因于一战以后许多国家和人民对战争越益巨大的生命、财产和心理代价的沉痛认识,二要归因于30和40年代法西斯国家罪行引起的对武力强暴的广泛憎恶和警觉。
然而,如国家实践、尤其是超级大国实践屡屡表明的那样,新国际规范在防止和制止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方面所起的作用仍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武力威胁,即使在二战后也仍然是一些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常用手段。不仅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际规范固有的局限性(首先是缺乏一般国内社会中中央权威那种对法律的强制贯彻)使然,而且关于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规则本身相当含糊宽泛,以致有时如同虚设。这方面最成问题的应说是所允许的例外,包括单边的和集体的自卫,以及根据国际组织授权、当事国政府邀请和其他理由所作的援他性战争行动或武装干涉。二战后不少侵略性军事行动就是以这些“例外”方式取得了似是而非的合法性。当然,联合国宪章规定,成员国行使自卫权利的措施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安理会随时采取行动的权威和责任,只要这行动在安理会看来是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实际上成员国往往不立即报告、或根本不报告行使自卫权利的措施,甚至像北约就科索沃问题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大规模轰炸那样根本撇开联合国,而安理会本身也常因大国间的歧异或对立作不出必要的决定,更何况自卫这一概念本身从未得到联合国的详细界定,以致往往由动武的国家随意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
即使如此,从长远观点看仍可认为,“诸国精英逐渐转而倾向于无偏袒地接受世界共同体的法律标准,这可能是当代最富意义的——即使有时无法明辨——支持世界秩序的趋势。宪章的构想以其权威的支配性规范是鼓励这一趋势的一个关键因素。”(注: Falk et al.eds.,International Law,p.125.)另外, 虽然宪章的有关规定屡屡遭到违背,但可以肯定它们也成功地阻遏了不少战争和武力威胁行动的发生。或者说,假如没有这些规定,世界的情况会更糟。(注:Louis Henkin,"The Reports on the Death of Article 2 ( 4)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in ibid.,pp.389-393.)对于被宪章当作威慑和惩罚侵略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也可以采取类似的看法。的确,它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如一战后的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体系,基于某些虚妄的前提, (注:关于这些前提的权威的理论分析, 见 Inis L.Claude,Jr.,Swords into Plowshares: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Orgnaization (New York,1964),pp.223-225,227-238.)因而很少见效。但另一方面,主要在美苏冷战结束以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空前影响,大国对立有所缓解或消退,和平与反侵略的国际舆论总的来说更加有力,与此相关的全球性跨国价值观念更加流行——所有这些因素都多少有利于集体安全,使之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情况下多少起作用,尽管它们仅仅有限地减小、而非消除了集体安全体系固有的困难。
四
说到底,关于国际暴力的新规则就是关于国家主权的新规则,只不过前者是集中在后者所派生的某一单独的具体领域之内,即国家对外使用暴力的权利和义务领域之内。20世纪关于国家主权的新规范首先包括扩大、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法律规则,虽然与之相比这个世纪里产生的限制和干预国家主权的规则更多,也更具时代特征。所谓扩大国家主权,主要指许多沿海国家的主权管辖范围扩大到原先属于公海的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可以说,17世纪格老秀斯往后,公海自由原则很大程度上既基于海洋的不可分割性和可得性,(注:用格老秀斯本人的话说,“海洋象空气一样,无法被占取,因而不能被归属于任何个别国家家所有。”引自Schachter,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p.275.)又基于由人类技术和海洋资源利用之时代水平。可是,随科技的迅速发展、人口的巨量增长和由此对食物及能源供给的追加需求,情况有了变化,而“对外国人经济剥削很敏感的国家那加剧了的民族主义”(注:Ibid.)使之更是如此。40和50年代, 便有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宣布本国海岸外200海里海域为排外的专有捕鱼或捕鲸区, 以后这类举动被许多沿海国家仿效, 专有权利的覆盖范围也被扩大到200海里海域内的所有其他自然资源。从1973年开始,联合国构架内的十年谈判导致了《海洋法公约》的缔结,它同至少70余个国家各自单方面的权利宣布构成的、关于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国际习惯法(注:有关的国际法学阐释见 Brownlie, PrinciplesofPublic International Law,p.210.)一起, 代表着国家(至少一大批实际宣布有此类权利的沿海国家)主权的显著扩展。在造就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的新规则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同样起了主导作用。1965年,由它们占大多数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其中规定“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有权力任何原因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外事务。 由此, 对国家人格(the
personality
of states)或其政治、经济、文化要素的武装干涉,或所有其他形式的干预或威胁企图,都是对国际法的违背。”(注:Ian Brownlie,ed.,Basic Docu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3rd edition (Oxford,1983),p.40.)这是一条非常明确和严格的基本原则,它实际上将若干关于国家义务和权利的具体新规则集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不得以侵害受援国主权为条件提供经济援助,反干涉(counter—in—tervention)(注:即应遭受外国军事干涉的国家之邀请、为保护该国独立和主权而进行的军事干涉。)必须局限在发生内战的国家领土之内,联合国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权之内的事务”,也不得要求成员国将此类事务提交联合国解决等。(注:引语出自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段。 同国联盟约的同类条文相比,这一规定在维护主权方向上走得远得多。)然而,在实践中主要由于强国、尤其是美国的优越权势和干涉主义意识形态,不干涉原则及其派生的具体规则往往遭到破坏或贬抑;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当代国际规范包括不少同它们抵触的规定,或者说这规范体系多少自相矛盾。
作为国际法的一项核心,国家主权概念在其创始者让·博丹那里本是有限制的,即在神法之外受到自然法、万国法(jus gentium )和包括王位继承法在内的本国根本大法的限制,虽然与此同时它更强调主权是“国家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是最大的支配权”。(注:博丹语,引自William Ebenstein ed.,Great Political Thinkers:Plato to the Pressent,3rd edition (New York,1960),p.349.)从70 余年后的霍布斯开始,国家主权在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中逐渐被绝对化了。即使主权的载体由君主变成了国家全体公民或民族,但主权无限制的观念没有改变,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法律上的绝对自由这一信条没有改变。(注:Brierly,The Law of Nations,pp.12-16.)然而在20世纪,特别在其后半叶,发生了被一位国际法学家称为国际社会与其各个成员之间“权威纵向分配”(注: Chen,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p.224.)的大变化, 而这变化中最突出的就是“国际关切”(international concern)概念逐渐扩展, “国内管辖”概念则饱经侵蚀。除开超级大国或其同盟集团的干预外,此类事态的主要媒介便是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和行动。自问世以来,联合国越来越多地将一些领域(特别是集体和个人人权领域)内的重要问题移出国内管辖范围,使之成为国际关切和干预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应当由谁决定某个问题究竟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拥有一种几乎不受疑问的权能,决定什么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由于如此决定而拥有将一个具体问题国际化的能力。”(注:Falk et al.eds.,International Law,p.130.)尽管这一说法不免有所夸大,但联合国确实已在涉及许多人类价值范畴的一整系列问题上行使了它的权能,其中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土争端、非殖民化和民族自决、政府组织形式、人权、国际经济和文化合作等等。联合国的干预和干涉大多被相当普遍地认为是合法的,或者说是国际社会干预和干涉那些被它认为是国际关切对象的内政问题,以此保护各国的共同利益或贯彻它们的共同伦理。在人权问题上,当代国际规范体系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和干预尤为显著。这里毋需复述前面已谈论的种种人权国际规范,只需补充说明若干新情况。例如,允许用武力拯救无辜者的性命,使之免遭任何国家的大规模屠杀和其他暴行,成了自卫和集体惩罚侵略之外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暴力这项通则的另一大例外。又如,根据一项权威的解释,前述联合国宪章内关于国内管辖权的规定(或曰对联合国干涉权的限制)并不适用于经联合国机构确认存在某些违反人权行径的场合。在实践中,这种规定有时更加脆弱,以至很可能变得如同虚设,起不到合理保护国家主权的作用。(注:B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pp.553-554.)还有,联合国大会1975年通过《保护所有人免遭拷打和其他残酷、非人道或使人堕落的处置或惩罚的宣言》,其中将此等行为谴责为违背人权和基本自由。从一战结束时起,保护一国国内的少数民族已成为国际法话题,凡尔赛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即由主要协约国同东欧诸小国及土耳其之间有关的专门条约和条款构成。二战结束后,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它规定少数民族享有维持本民族文化、信仰本民族宗教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总的来说,上述这种种限制和干预国家主权的新国际规则体现了当代世界的道德进步和组织改善,反映出多数国家就一国特殊利益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的合理认识。但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引起了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个人人权和民族自决的规则包含着过度损伤国家主权的颇大可能性,而其受害者一般都是或将是相对落后、贫弱的欠发达国家,它们特别需要国家及其主权的三大功能即安全保护、民族认同和国民福利。 (注:这三大功能见 John H.Herz,"The Territorial State Revisted: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al State,"in Williams et al.eds.,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06.)主要因为如此,直至90年代还未有任何联大决议支持一国有权对另一国进行“人道主义”武装干涉,如果这干涉未经后者同意,也未有足够的国家实践及相关的法理舆论作为证据,表明一国可以人道主义为由非自卫地使用暴力。(注:Schachter,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pp.124-125.)美苏冷战结束后,权势大增的美国及其西方同盟体系更倾向于滥用和曲解人权国际规范,来干涉和破坏一些欠发达国家的主权,以此实现或顺便促进它们的战略和意识形态目的。至于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贯彻民族自决可能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欧的历史提供了明证,二战后至今许多国家的战乱和瓦解也是如此,它们导致了难以名状的国内苦难和国际动荡。(注:参见Alfred Cobban,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New York,1969),pp.66-68.)关于20世纪新国际规范的理论和实践告诉人们,任何权利,不管是国家主权还是人权和民族自决权,都不是绝对的,都不应无条件地和一成不变地被置于至上地位。它们之间互相有所抵触的必然性决定了使它们互相妥协、互相协调的必要性,无论从政治还是从伦理角度来看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