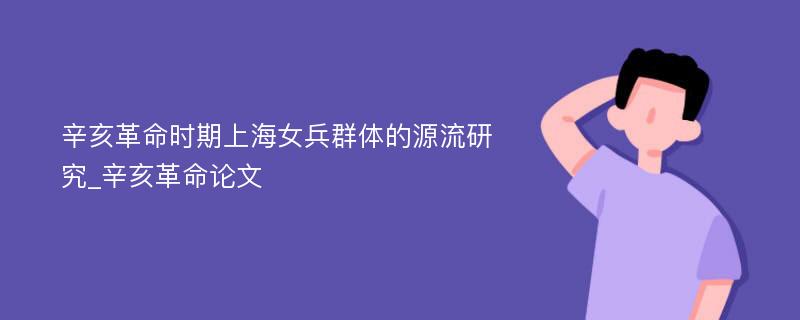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女子军事团体源流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源流论文,上海论文,团体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1873(2006)01—0037—06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女子军事团体是近代女权运动的新生事物,一般是指编入作战序列的女子军队、接近于军队编制的女子军事预备团体以及明确以军事为目的的女子学校。① 由于存在时间短暂,内部关系复杂,名称演变迅速,况且许多团体本身也存在多头统属争取资源的情形,因而在各种论述中,实同名异和名同实异的情况很多。关于上海的女子军事团体,梁占梅、林维红、霍海燕、刘巨才等在相关论著中均有所列举,但各论著都以其鼓动女权的意义分析为主,史实考订不是重点。况且多数论著过于重视名号而忽略实际演变,易造成望文生义、张冠李戴的错误,② 一些专门介绍的文章又过于简略。③ 本文试图比勘各种报章、回忆、档案、公报等史料,弥补既往研究以名证实的缺失,从人脉关系入手,厘清各支女军的名实和源流。
一 林宗雪、辛素贞统领的女国民军及北伐队
厘清这一支女军最为不易,但依据以尚侠女学为中心的人脉线索,亦可大致勾勒其源流。据《申报》报道,1911年11月13日尚侠女学辛素贞向沪军都督陈其美上呈要求组建“女民国军”(这是在上海最先出现的女子军事团体名称,呈中以“女民国军”为名,是为和当时已经出现的男民国军相应,“一切如男民国军办法”)。④ 11月12日,陈其美批示:“诸女子既具此热心,不妨详拟章程呈候酌核。 如别无窒碍,即当照准施行。”⑤ 辛素贞向沪军都督府提交开办章程后,于11月15日下午,由辛素贞带领尚侠女学学生五、六人到沪军都督府请愿,要求对前日的呈词予以批复。当晚陈其美批示准其成立,并承诺“如果教练完善,确能御侮折冲,枪械经费各节自应代为设法。事关军务,希即照章切实办理”。⑥
这一名称并不确定,筹建的过程也较长。从11月18日起,实际以“女国民军”名义开始在《民立报》刊登招募广告,计划先招第一队500人, 报名地点为上海南市万裕码头西首荣福里1号尚侠女学校,及嘉兴东门外西街陈志权处、 嘉兴王店商学保卫团查以成处。⑦ 11月20日起,女国民军于上海南市丰记码头8号设招待所,供来沪等候考核者居住。⑧ 招募的范围主要面向浙江,除嘉兴外,11 月下旬又分别派陆鸾如至湖州(以湖州北门准提巷为联络地点)、⑨ 派林澹烟(尚侠女校教员)到宁波(以宁波府女学堂为报名处)代征队员。⑩ 11月30日至12月9日,在上海南市丰记码头该团体事务部对报名者进行考核选录。(11) 至12月10日考验完毕,始于120余人中选得30人,其中多为各省学堂学生。(12)
在上海辛素贞倡建女军的同时,浙江军政府已经组派军队参加攻打南京的战役。黄元秀回忆,浙江援宁军队属下有一队女子先锋队,由尹维俊、尹锐志、林宗雪、张馥桢等30人组成。(13) 但尹维俊并不仅仅是女军统领,在整个浙军中也是领袖之一。女军的领袖则是林宗雪,1912年1 月刊印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中记有:“民军攻击南京时,有女子国民军领袖林宗雪等,随同浙军,颇著劳绩。”(14) 林宗雪的妹妹张馥桢(林随母姓)回忆:“浙军之攻南京也,姊氏林宗雪亦参加后勤工作。”(15) 不过黄元秀的回忆清楚地提示出各人之间的关系,即林宗雪率领的女子军就是随尹维俊参加攻宁的浙江军队。当时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发至上海的各份电报中所提到的“女子国民军”,(16) 以及推举徐绍桢为联军北伐总司令时的“女子国民军”,(17) 就是这支队伍。(18)
南京光复后,女子国民军经济困顿,林宗雪进谒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给予川饷以便北伐,并号称所部已达千人。(19) 此举并未奏效,这支女军终于12月底即行解散。(20) 林宗雪又回到上海,向沪军都督陈其美请愿,继续招募女军, 准备北伐。张馥桢回忆:“迨南京攻克,……姊(林宗雪)乃返沪申请沪军都督,批准招致青年女子三十余人训练之。”(21) 此时辛素贞的女国民军正在考核、组建, 辛素贞与张馥桢均为上海尚侠女校的创办者。(22) 张馥桢与林宗雪为胞姐妹, 况且都是浙江背景,在上海组军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上海地方和沪军都督府的资源。遂共同率部赴南京参加北伐,推林任司令,于12月30日到达南京,驻在神策门内绿筠花圃。(23) 当时这支女军又被称为“浙江女子国民军北伐队”,(24) 或因林、张、辛三人均为浙江人,队员也以浙江人为主体,续用攻宁女子国民军的名号有助于壮大其声势。
这支队伍在南京较有影响。1912年1月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至其驻地阅视。(25) 后辛素贞、张馥桢两人还曾至总统府晋谒孙中山,并向孙补呈新政条陈五项,应孙之邀向其推荐尚侠女学“遗逸之士”数名。(26) 此军先属于江浙联军徐绍桢部下,1月16日南京卫戍总督府成立后,徐绍桢任卫戍总督,林宗雪遂开列名册及详细编制情形具呈,请示善后。1月28日, 陆军部以“身体孱弱未经训练之女子随队遄征,诚恐一有疏虞反致滞戎机而累全局”,下令徐绍桢将其解散,每人发给遣散费10元。(27) 此后余下的二、三十名队员分赴临时病院及卫生队作看护妇。(28) 林宗雪仍心念北伐,又向徐绍桢上书,望其设法维持,徐代为向黄兴说项。(29) 2月16日,陆军部再次下令将女子北伐队一律取消,(30) 为安置队中的女子,林宗雪拟以驻地绿筠花圃作为校地,募款开办女子蚕桑学校,特向大总统孙中山请呈,孙转发教育部会同内务部办理。(31) 林此举引起了元宁农会的不满,纠纷不断,开办女子蚕桑学校也无下文。
二 陈婉衍统领的女子北伐光复军
陈婉衍统领的女子北伐光复军统系最为清晰,具有十分明确的光复会背景,附属于李燮和的光复军下。陈婉衍,江苏上海人,革命前曾开办宗孟女学堂(具体创办时间未详,应在1904年以前),(32) 拒俄运动期间与童同雪、 郑素伊等人以该学堂为基地,组织对俄同志女会,后改为慈航社。(33)
1911年11月14日,陈婉衍奉李燮和之命召集女子军,以“女子北伐光复军”名义刊出招募广告,拟“特招女军四队,以襄北伐之师”。要求报名者年龄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报名处设于李燮和开创的吴淞军政分府。(34) 这一团体组建较快, 至11月21日,“已招得成队”,齐集于吴淞军政分府。(35) 投效者有七、八十人之多,其中有50人编队前往攻宁前线。(36) 11月26日《申报》报道, 李燮和派出吴淞军政分府中女子敢死队50人赴南京助战,该队以攻取南京为目的,又称荡宁队(在称颂她们的“文苑”作品中也有称为“荡宁军”的),应指这一支女军。(37) 12月4日,该队进入南京。(38) 1912年1月中旬,孙中山下达北伐令后, 李燮和又从女子北伐队中“遴选强干堪任军事者数十人,分编临阵、补阵、侦探、卫生四队,归陈畹(婉)衍女士督带北上”,(39) 作北伐之预备。1月16日,陈婉衍发表《女子北伐队宣言》,表明志向,激励士气。(40) 后南北议和达成,北伐终止。
梁占梅虽列举了吴淞军政分府领导下的“女子光复军”,但同时又列有以“陈也月”为司令的“女子北伐队”,并指认其附属于柏文蔚部下。林维红《同盟会时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动(1905—1912)》文中沿此说。梁占梅所引以为证的女子北伐队宣言,从文本上看就是李张利侬发表的《女子北伐队缘起》。(41) 这支女军确属于柏文蔚部下,但是由刘慧英任总司令。(42)“陈也月”的“女子北伐队”实际上应是陈婉衍的女子军。《民立报》1912年1月13 日载有吴芝瑛复女子北伐队陈司令的书信,抬头为“贵重之也月陈先生”。(43) 吴芝瑛在另一件复女子北伐队邵绮心的书信中又提到:“陈司令风怀磊落,平时教育以提倡民贵为宗旨,往年曾与吾友秋君抵掌谈天下事,引为同志。”(44) 从中可以看到, 她们与秋瑾的光复会系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位“陈司令”革命前的所作所为与陈婉衍开办宗孟女学堂的事迹相符,因为“宗孟”即“以孟子主张‘民为贵’之说,盖亦暗射民主主义”。(45) 由此基本可以断定,这位陈也月即陈婉衍。同样, 刘巨才将李张利侬发表的《女子北伐队缘起》一文中之女子北伐队视为陈婉衍所带的女子军,也不确切。(46)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下令解散女子军后,由李燮和于3月向教育部提出,将其改组为女学堂,(47) 命名为复心女学, 校址设在光复军司令部旧址南京大中桥韬园,仍由陈婉衍负责。女学于3月26日进行招考,28日开学。(48) 学校对以前诸烈士及旧隶于光复军女子队的志士各亲眷都有特别照顾,免收学费和伙食费。(49) 凡不从学者一律遣散,这支女军可能是当时安置较好的一支。
三 沈亦云发起组织的女子军事团
女子军事团是一个在当时与沪军都督府有密切关系的军事组织,1911年11月18日由沈警音(即沈亦云)等发起。(50) 根据该团章程,该团专为军事而设,故定名军事团,并以“驱攘残恶、救助同胞”为宗旨。所招团员年龄在16—40岁之间,办事处设于上海爱文义路新巡捕房斜对门59号,报名处除办事处外,还有爱而近路均益里两等女校、西门外黄家阙路12号徐宅。(51) 后又借定上海城西尚文门口体操学校为编队操练之处。(52) 该团的发起人或素识,或相闻知,葛敬诚、葛敬华是沈亦云的姨母,
其他骨干成员如天津女师的郑仲完(璧)、陈允仪(淑),上海爱国女学的曾季肃、范慕兰,北京女师的黄绍兰,苏州振华女学的倡办人王谢长达,胜家缝纫女学的吴振球等,都可谓志同道合。(53) 队员以务本、爱国、民立各女校的女学生居多数。(54) 初设战斗、军医二部,后增设募饷、缝纫部。范慕兰主持战斗部,王谢长达主持募饷部,吴振球主持缝纫部。(55) 女子军事团最初本拟邀张默君为团长,张因有“更重要的工作而未允来”,但仍以张作为挂名团长(女子军事团最初上沪军都督文即以张的名义发出(56)),以曾季肃(曾孟朴之妹)任团长,后曾季肃辞职,由沈亦云接任团长之职。(57)
杜伟曾有题为《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的回忆资料,提到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活动积极,受到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参谋长黄郛的重视和支持,沈警音担任队长。(58) 杜伟这篇回忆所记述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女子军事团的事迹,但其中有许多混淆、失实之处。女子军事团在当时是否也自称“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报章所见,均用女子军事团名义。1911年11月28日,沪军都督府嘉许其“章程已简而易成,组织亦完而且密”,准予立案。(59) 其募饷部成为沪军都督府承认的少数募饷团之一,(60) 并多次向沪军都督府缴纳饷金。(61) 还曾应沪军北伐先锋队商邀,派人分赴苏州、常州等地劝募。(62) 女子军事团能得到多名革命党要人如陈其美、黄兴的关注,沈亦云在此中的作用始终十分重要。沈的继父是周肇甫,寄母是沈缦云的妹妹沈毋隐,为发行沪军军用票而致信用破产的信成银行即为周家产业。女子军事团受到各方之优待,当与沈亦云寄父一家对革命的贡献有关。
女子军事团在上海时参加过许多活动,如1911年12月参加沪南商团公会为会员张沛如、荣九松、俞志伟三人召开的追悼大会、(63) 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明伦堂召开的追悼诸烈士大会。(64) 1912年1月30日,训练仅及两月的女子军事团奉陆军部檄出师北伐,战斗部向南京进发,驻铁汤池丁宅。(65) 后因南北和议告成, 大家认为“不宜再虚掷时光”,即向沪军都督府报告解散,“各归各位,教者归教,读者归读”。(66)
四 沈佩贞发起组织的女子尚武会
女子尚武会是带有女子军事教育性质的机构。发起人兼会长沈佩贞,辛亥革命前曾参与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政治活动,并提倡革命。武昌起义时在天津谋集同志起事,因泄密,被清直隶总督陈夔龙所捕。后陈恐激起风潮,释放沈佩贞。(67)
1911年11月28日,沈佩贞在《申报》发表《创办女子尚武会绪言》。(68) 该会“以养成女子尚武精神、灌输军事学识为宗旨”,目的是要培养女会员“足以辅佐女子军进行,而协助女子军出发以后之后方勤务,如输送枪械、协济饷粮诸事务,令女子军无后路援绝之虑,而得以勇往直前,借收克敌逐虏之效”。开办经费及日常费用由沈自行解决,如果有热心捐助的人,则被定为此会的名誉会员。报名处设于望平街中外报馆。招募的学生在25至35岁之间,不收学费,拟招500人。 计划以两个月为一学期,三学期毕业,毕业后编队,随女子军出发征战。学科多与军事有关,或可服务于军队,主要有输送、捆载教程、兵站配备、体操、测量、绘图、琴歌、侦探等。(69) 1912年1月下旬奉沪军都督批准,开办在即,广告招生,以江苏省教育总会间壁该会事务所、望平街中外报馆总发行所等处为报名地点。(70) 1月26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沈佩贞为首任会长,詹寿恒为副会长,张汉英为监学,叶慧哲为书记,钱秀荣为庶务,刘既嘉、李元庆、杨露瀛3人为干事,张振武为名誉总理。(71) 其后活动不详,霍海燕与刘巨才均认为女子尚武会随军北伐,但未列明资料来源。(72) 南北议和后解散,沈佩贞转去进行参政运动,参与组建女子参政同盟会。后参与各种实业、女子团体,曾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告密杀害革命党人,此是后话。
五 吴木兰发起组织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
吴木兰组织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隶属于中华民国女子同盟会。中华民国女子同盟会于1912年1月10日在上海成立,吴木兰为会长、林复为副会长, “以扶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唯一宗旨,并以普及教育为前提,以整军经武为后盾”。(73) 其中设评议、内务、调查、执行和纠察五部。“调查部主任调查各项事宜”,“执行部主任执行各项事宜”。(74)
女子同盟会附设经武练习队,以“练习武学、扶助国民为宗旨”,“为女子同盟调查、执行两部之预备,俟练习已成,即服调查执行之职务”,驻于上海西门曹家桥。(75) 经武练习队的名称是暂时草创,留待扩充时再改定名义。(76)
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实际上也是具有女子军事教育性质的机构,所学科目有演讲、补习、操法。(77) 队内拟设队长1人,队员80人,实际只有队员74人。(78) 所需一切款项由女子同盟会承担,非女子同盟会会员,不得为该队队员。2月6日,在上海西门曹家桥立校开课。(79) 2月12日,开会商议进行方针,举定吴木兰为正会长,林复为副会长。(80) 设有内务、外交、调查、执行、财政、评议、文牍等部,另设驻鄂女子经武练习队,由张振武任总务部下长,夏鲲任副长。(81) 该团体在辛亥时期的具体活动未详。解散后转向参政运动,吴本人也参加了女子参政同盟会。1912年5月25日,吴还发起男女联合教育会,以谋“男女教育平等”,出任会长。(82)
六 其它几支昙花一现的女子军
除上述几个主要的女子军事团体外,从报章上还可见到几支昙花一现的女子军,例如:1、上海闸北守卫团女侦探队。1911年11月上旬,上海光复不久, 闸北的守卫团曾拟招募女侦探一队,专派在沪宁、沪嘉车站侦探奸细,每月薪水洋20元,盘费在外。要求能够通晓数省方言。(83) 但未见其有进一步报道。
2、陈秀珍的“女界国民军”。1911年11 月中旬《民立报》报道了陈秀珍发起的“女界国民军”。陈秀珍,广东人。持有武昌军政府驻沪代表陈君印信,在上海虹口乍浦路多孙里第末家设“女界国民军”,声称主要活动是“派员在沪宁铁路协同民军抽查行李”。(84) 因有人指责其以女军名义“以甘言甜语欺骗妇女”,(85) 陈还特意到《民立报》辩诬。
3、张侠琴、唐六琴的“中华女子侦探团”。1911年12 月出现的“中华女子侦探团”之倡导者为张侠琴、唐六琴。两人均为妓女,声言“挟红粉为行军之饵,借美人为诱敌之谋,必牺牲驱壳,始克为此”,“因择我国良家妇女所不能为不肯为之事,发起女子侦探团,冀稍尽国民之一分。”其《简章》云:“本团专以探取行军时之敌情及国际上之秘密为宗旨,团员先行额定五十人,以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粗识文字者为合格。”(86) 张、唐甚至将《缘起》、《简章》具禀沪军都督,但陈其美以“侦探学有专门,殊非易易,且组织成团,恐滋流弊”(87) 为由,未允其成立。
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军,是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现象。虽然存在时间短暂,然而在突显革命党人思想开明、体现社会进步、调动男子的爱国热情方面,意义重大。在考订史实、厘清源流的基础上,对这一对象展开研究,可以再现中国妇女运动发展之实情,并通过考察女子军的沉浮消长,反映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所进行的考证,旨在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史实基础。
注释:
① 至于对军事行动虽然关系重要,但纯粹为平民性质的赤十字队、各种募饷机构、为军队提供装备服务的女子学校等,不在此列。
② 梁占梅:《中国妇女奋斗史话》,重庆建中出版社1943年版,此书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但成为后来者研究的重要依据;林维红:《同盟会时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动(1905—1912)》,载张玉法、李又宁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1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霍海燕:《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妇女界》,《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华强:《辛亥前后上海青年妇女的解放运动与从军运动》,《史林》2002年增刊;朱心明:《辛亥上海的女军》,《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
④ 《尚侠女学代表辛素贞上陈都督书》,《申报》1911年11月13日。《时事新报》在报道中则直用“女国民军”的称法,并“一切如男国民军办法”(《时事新报》1911年11月15日)。辛的上书应在1911年11月12日前,《陈英士先生文集》,中收录的《覆尚侠女校辛素贞等函》是陈1911年11月12日的回复 ( 秦孝仪主编:《陈英士先生文集》,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7年版,第15页)。
⑤ 秦孝仪主编《陈英士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7年版,第15页;《照录沪军都督批词》,《时事新报》1911年11月15日。
⑥ 《申报》1911年11月16日。
⑦ 《时事新报》1911年11月17日。
⑧⑨(11)(17)(19) 《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1911年11月26日、11月30日、12月12日、12月14日。
⑩ 《时报》1911年12月1日,《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日。此篇报道中,使用了“上海中华女国民军”名义。从同属尚侠女学的人脉系统以及同时在浙江开展工作的事实来看,它与辛素贞倡建的女民国军应为一家。
(12) 《时报》1911年12月10日。另见《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9日。
(13) 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3页。
(14) 吴门天笑生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元年一月), 上海有正书局1912年版,第100页。另见《天铎报》1912年1月30日;《民立报》1912年1月29日。
(15)(21) 张馥真:《辛亥前后江浙妇女界的革命活动片断》,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16) 1911年11月25日电称:“义勇队、女子国民军投效行间,勇义奋发。”(马长林编《辛亥革命时期江浙联军电报辑要》,《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3期。);11月26日电称:“今日已派兵攻取幕府山,兵气甚壮。现编义勇队五百人,又有女子国民军三十人来投效。”(《本馆接关于南京战事特电》,《民立报》。);12月2日电称:“我军苦战六昼夜,女子国民军亦入战线,已将乌龙、幕府两炮台占领。”(《本馆接南京战地报捷要电》,《民立报》。)
(18) 在当时的报纸中,别有林素皑(恺)之称,且偶与林宗雪混用。1912年1月16日,在南京下关商会召开徐锡麟、陈伯平、马子彝三烈士追悼会,《申报》报道称林素皑出席,并发表演说,《时报》则称林宗雪在列。(《宁垣新纪事》,《申报》1912年1月18日;《南京开徐陈马三烈士追悼大会》,《时报》1912年1月20日。)另,《民立报》曾刊登“中华女子国民军发起人林素皑(宗雪)肖像”(《民立报》1912年1月11日),据此亦可以判定林宗雪与林素皑实为一人。
(20) 《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造成移交所统军队清册》,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26,卷号:064。
(22) 《民立报》1912年1月19日。
(23)(24)(25)(26)(27)(34)(36) 《民立报》1912年1月9日、1月7日、1月7日、1月19日、1月29日、1911年11月14日、12月1日。
(28) 《时事新报》1912年2月3日。
(29) 《大公报》(天津)1912年2月8日。
(30) 吴门天笑生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元年二月),上海有正书局1912年版,第150—151页。另见《时报》1912年2月27日;《大公报》(天津)1912年3月2日。
(31) 《大总统令教育部会商内务部核办林宗雪呈请募赀开办女子蚕桑学校并恳拨绿筠花圃为校地由》,《临时政府公报》第19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2)(32)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6日、4月18日。
(35) 《时报》1911年11月21日。
(37) 《申报》1911年11月26日。次日又有报道称:“沪军亦派女敢死队五十人亲往前敌与张军一决生死。”应当是指前日的荡宁队,《申报》1911年11月27日。
(38) 《民立报》“文苑”中,一位署名菡芬词馆生尘的人作《女子军并序》,提到“苏人陈婉衍女士编制女子北伐军,于月之十三日(即12月4日——引者注)徒步入宁”。《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
(39) 《申报》1912年1月18日。
(40) 《时报》1912年1月16日。另见《时事新报》1912年1月16日。
(41) 梁占梅:《辛亥妇女革命史述要》,《妇女新运》第8期,1942年10月。
(42) 《民权报》1912年4月1日。
(43)(44)(48)(49)(50)(51)(52)(59) 《民立报》1912年1月13日、1月7日、3月16日、3月16日、1911年11月18日、11月19日、11月22日、11月28日。
(45) 张馥真:《辛亥前后江浙妇女界的革命活动片断》,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46)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338页。
(47) 《教育部批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请将光复军女子队改组女学堂酌给开办常年经费并请出示保护呈》,《临时政府公报》第30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另见《民立报》1912年3月16日。
(53)(55)(57) 沈亦云:《辛亥革命知见》,《传记文学》第7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6页、第6页、第7页。
(54) 《天铎报》1911年12月23日。
(56) 《申报》1911年11月29日。
(58) 杜伟:《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60)(65)(70) 《民立报》1911年12月7日、1912年1月30日、1月24日。
(61) 有关募饷的情形,在《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12日、17日、18日、19日、23日的报尾(第8页)皆有记录。
(62)(63)(64)(67) 《申报》1911年12月25日、12月13日、12月18日、12月20日、1912年1月11日。
(66) 沈亦云:《辛亥革命知见》,《传记文学》第7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6页、第7页。
(68) 沈佩贞:《创办女子尚武会绪言》,《申报》1911年11月28日、29日。
(69) 《创办女子尚武会简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0页。
(71) 《时事新报》1912年1月27日。
(72) 霍海燕:《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妇女界》,《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
(73) 《吴木兰林复呈孙中山文》,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页。
(74)(76) 《中华民国女子同盟会章程》,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1—412页,第413页。
(75)(81)(84)(85)(87) 《民立报》1912年2月13日、1月14日、1911年11月13日、11月12日、12月23日。
(77) 《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简章》,《民立报》1912年2月13日。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一书中收录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简章》与之略有出入,内列所学科目较为齐全,有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侦探学、炸药学、历史学、地理学、算术学、代数学、几何学、图画学、国文学和体操学。
(78) 《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队员名册(1912年2月14日)》,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5页。
(79) 《吴木兰林复呈孙中山文》,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页。
(80) 《天铎报》1912年1月14日。
(82) 《时报》1912年5月27日。
(83)(86) 《申报》1911年11月18日、12月19日。
标签:辛亥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历史论文; 时事新报论文; 沈亦云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