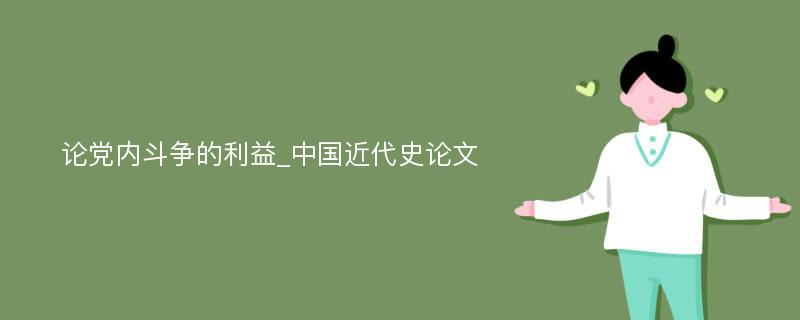
论党内斗争效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效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内斗争理论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邓小平在丰富、发展这一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党内斗争效益的思想。然而这一思想至今仍未得到理论界应有的重视和发掘。正确、充分地认识党内斗争效益对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提高斗争效益是开展党内斗争所应遵循的总方针
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说:“以更少的代价和痛苦换得党内斗争更大的成绩和党的更大的进步,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研究中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中所应确定的今后党内斗争的方针。”(《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60页)这个论述告诉了我们在开展党内斗争时所应确定的方针,这个方针有两个要求:其一是“换得党内斗争更大的成绩和党的更大的进步”;其二是“以更少的代价和痛苦”。这两个要求不是相互隔离、互不相干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用一句简明、通俗的话来概括这两个要求就是:以尽量少的付出换取更大的获得,这就是效益。正如经济效益就是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一样。党内斗争效益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斗争效益=党内斗争的成绩和党的进步(获得)/代价与痛苦(付出)。
刘少奇认为,提高斗争效益是我们“所应确定的今后党内斗争的方针”。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毛泽东曾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开展党内斗争所应遵循的方针,后来又把这个方针概括成为“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那么,这两个“方针”是什么关系呢?这两个方针既有相容、一致的方面,又有相异的方面。首先是相容性,这两个方针都表达了党内斗争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二者都要通过一定的手段达到一个良好的目的,一个是通过付出代价和痛苦来实现党的进步,取得党内斗争的成绩,一个是通过“惩”、“治”、“批评”来达到“毖后”、“救人”、“团结”的目的。为了实现斗争的目的,采取一定的手段时,必须有节制,有限度,付出代价和痛苦不是越多越好,“惩”和“批评”不是越严重、越厉害越好。但是这两个方针又有不同的地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往往是针对犯错误的人而言,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提高斗争效益是针对党内斗争的总体而言。二者相比较,后者更抽象,更具有宏观性,是更高层次的方针,而前者则较为具体,是较次层次的方针。另外,我们须注意到,毛泽东在提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时,用法是不固定的,有时说是“方针”,有时说是“宗旨”,有时说是“原则”,等等。刘少奇在提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时,也是指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但都说成是“原则”。而刘少奇在讲到前面所述的斗争效益时,是很明确的,说它是“所应确定的今后党内斗争的方针”。我们应该把这个“方针”,理解成是统帅、制约其他各项党内斗争中所应遵循的具体方针和原则的总方针。这是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的基础上,对毛泽东党内斗争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贡献。
为什么说提高斗争效益是开展党内斗争的总方针呢?党内斗争是政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必须讲效益。党内斗争的效益好,就会使党在达到斗争目的的同时使党更加进步,更加兴旺发达;反之,党内斗争的效益差,党就会在斗争中造成内耗,党自身受损失,同时也很难取得“党内斗争的成绩”,实现党内斗争的目的。前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党内斗争效益差的典型事例。而“延安整风”和近几年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是党内斗争效益好的典型例子。如“延安整风”,党针对当时党所面临的中心任务和当时党内存在着的矛盾和问题,采用整党整风的方式和手段,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既解决了矛盾,达到了预定的目的,获得了优异成绩,又使党在斗争中进步、发展、壮大,从而确保了党完成它的中心任务,真是以很小的“代价和痛苦”换取了党内斗争非常大的成绩和党的巨大进步。
把提高斗争效益作为党内斗争的总方针是“我们今天从研究中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中”所得出的结论。刘少奇得出这个结论是在1941年,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若干次低效益的党内斗争,有着沉痛的教训。最突出的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所搞的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国民党上百万军队办不到的事情,而错误的、低效益的党内斗争做到了。大批身经百战的革命干部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下失去了生命。党在错误路线和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的作用下,自我损害,自我削弱,几乎走到绝境。历史经验证明,低效益的党内斗争只能把党引向毁灭。
我们常说的“党内斗争是党发展的动力”是指那些效益好的党内斗争,而不是指那种代价沉重、害党误民的低效益的党内斗争。
二、提高斗争效益必须紧密围绕党的正确基本路线开展党内斗争
斗争效益等于“党内斗争的成绩和党的进步”与“所付出的代价和痛苦”的比值,因此,提高斗争效益无非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可能增大分子——“党内斗争的成绩和党的进步”,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分母——“所付出的代价和痛苦”。
首先是增大“党内斗争的成绩和党的进步”。这里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党内斗争。党的建设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条基本原理。理所当然,做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之一的党内斗争也就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开展。党内斗争的根本目标是推进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否则党内斗争就失去了意义,成了无目标的乱斗和争权夺利。能否促进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是衡量党内斗争的成绩的一个主要标准,同时党只有在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并将之贯彻下去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进步。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他在领导全党制定、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同时,一再强调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也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来进行。他指出,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125页)他还说,实现四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181页)“现在要横下心来,……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91页)他在南巡谈话中又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就为|加强党的建设,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找到了目标和归宿,从而为增大党内斗争的成绩,提高党内斗争的效益创造了条件。
三、不搞政治运动是提高党内斗争效益的重要前提
提高党内斗争效益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小所付出的“代价和痛苦”。在党内斗争中付出的代价和痛苦大小多少,主要取决于遵循什么样的具体方针,依据什么原则,采用什么方式方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采用什么方式。在我党历史上,曾多次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党内斗争。实践证明,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党内斗争有很大弊端。政治运动有时效性,从发动起来到结束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而党内斗争主要是同志间的思想斗争,解决思想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用政治运动方式来搞党内斗争往往达不到党内斗争所应有的目的,使斗争流于形式。不仅如此,由于政治运动要放手发动群众,革命大批判开路,并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预定的任务,就很容易促成党内机械过火斗争的出现和发展,造成各种形式的扩大化,把党内斗争搞成“你死我活的斗争”,造成一批批冤假错案,就连党内斗争的理论家刘少奇同志都成了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此外,搞政治运动还会影响、破坏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每当运动到来,一切工作都为运动让路,在运动中突出强调书记挂帅,大权独揽,使得党内的民主生活不能正常进行,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倾向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搞政治运动很容易冲击、干扰党的中心工作,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影响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使党内斗争偏离正确的方向。党内斗争如果冲击了党的中心工作,是绝对得不偿失的。
实践证明,政治运动方式不是开展党内斗争的一个好方式,所以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不搞政治运动。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和建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损失时就说过,搞很多政治运动,并把政治运动几乎当作党的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是不好的。(参见《红旗》1987年第4期,第11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和政治路线的制定,邓小平的不搞政治运动的思想更加明确。无论党内斗争的任务重点是什么,他都强调不搞政治运动。1980年,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同时指出:“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6页)。在几次重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他都强调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和惩治腐败现象问题上,他仍坚持“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238页)
彻底否定、摈弃政治运动的方式是邓小平同志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一大贡献,是他在否定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的基础上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巨大丰富和发展。这为党采用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所付出的“代价和痛苦”,提高党内斗争效益提供了另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四、搞好制度建设是不断提高党内斗争效益的基本保证
要不断提高党内斗争效益,就必须像刘少奇所说的那样,“彻底纠正过去党内斗争中的各种偏向和错误”。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指出并剖析了三种党内斗争中的偏向和错误:第一是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第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第三是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其中以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最为突出,对党造成的损失最大。建国以后,这三种偏向并没有被克服和消除,反而出现了两种更为严重、危害更大的偏向,这就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搞党内斗争和在反错误倾向中重反右轻反“左”。产生这些偏向的根源是很复杂的,有理论上的,也有社会历史上的,又有领袖个人的,等等。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根源是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论述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150、151页)邓小平的制度建设思想既为我们找到了以往党内斗争偏向的最终根源,也为我们指明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高党内斗争效益的根本出路。这是关于党内斗争乃至整个党的建设问题的极深刻的重大转变,也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又一重大贡献。
当然,说“制度是决定因素”并不是否定思想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我党传统的开展党内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实际上邓小平也一贯重视思想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只不过相比之下,制度更带根本性。如果没有科学的、健全的制度做保障,思想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不是流于形式,就是被引入歧途。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才能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以及组织建设有了可靠的依托和保障,才能保证党内斗争遵循正确的方针,才能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和错误发生,才能不断提高党内斗争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