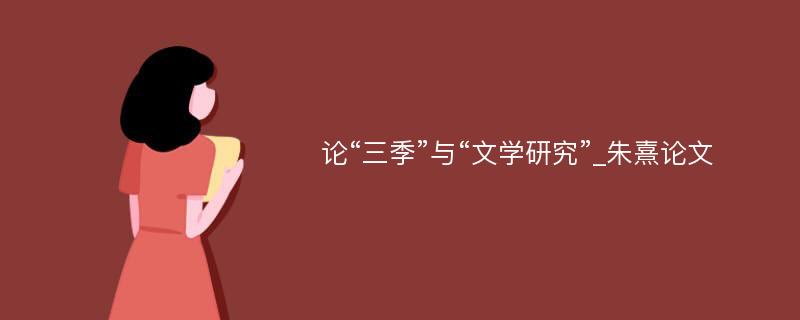
三蘇經學與文學述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蘇經學與文學述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蘇洵(1009-1066)、蘇軾(1037-1101)、蘇轍(1039-1112),乃一門父子,人稱“三蘇”。“三蘇”在經學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只是爲文名所掩而已。其主要經學著述如下:蘇洵有《洪範圖論》一卷(佚)、《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與姚辟合撰,存)、《嘉祐謚法》三卷(存)、《孟子評》一卷(存)、《六經論》六篇(存)等;蘇軾有《東坡易傳》九卷(存)、《東坡書傳》十三卷(存)、《東坡論語解》十卷(佚)以及《中庸論》三篇(存)、《四營十八變解》一篇(存)、《隱公是攝論》一篇(存)、《公子翬弑隱公論》一篇(存)、《鄭伯以璧假許田論》一篇、《管仲相齊論》一篇(存)、《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一篇、《墮三都論》一篇等;蘇轍有《詩集傳》二十卷(存)、《春秋集解》十二卷(存)、《論語拾遺》一卷(存)、《孟子解》一卷(存)以及《易說》三篇(存)、《洪範五事說》一篇(存)等。
三蘇父子,自相師友,蘇轍曾說過:“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①他們的學術旨趣是基本一致的,所謂“父子談經,無(劉)歆(劉)向异同之論”;②而且,有的著作如《東坡易傳》,還是父子三人合力完成之作,四庫館臣在該書《提要》中即指出:“蘇籀《欒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而卒,屬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轍乃送所解于軾,今《蒙》卦猶是轍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爲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所以,將三蘇合起來考察,是可行的,甚或也是必須的。
蘇轍曾對其父兄之學作過這樣的評價:“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于世,治氣養心,無惡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③此論可謂知言。三蘇之學即在治心和治世兩個層面展開,而這兩個層面實不可離,即共同構成所謂的“內聖外王”。
具體說來,三蘇經學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懷疑經傳與義理解經
在前人懷疑經傳風氣的基礎上,三蘇又有所推進。陸游曾談及慶曆前後經學風尚的變化:“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毁《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况傳注乎!”④據皮錫瑞《經學歷史》所言,此處毁《周禮》謂歐陽修與蘇軾、蘇轍,譏《書》謂蘇軾。而黜《詩》之序,蘇轍亦有力焉。由此可見三蘇疑經惑傳之一斑。
具體說來,蘇洵有《洪範圖論》一卷,《郡齋讀書志》卷一稱其“三《論》皆援《經》擊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蘇軾稱《周禮》“非聖人之全書”,“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天子六軍之制》)。蘇轍也認爲在《周禮》中“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凡《周禮》之詭异遠于人情者,皆不足信”(《歷代論一·周公》)。蘇軾還懷疑《尚書》,《東坡書傳》卷六稱“《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予于《書》見聖人所不取而猶存者二,《胤征》之挾天子令諸侯與《康王之誥》釋斬衰而袞冕也”。蘇軾常能不取陳說而自出己意,如其《東坡書傳》十三卷,《四庫全書總目》評該書曰:
晁公武《讀書志》稱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异其說爲多。今《新經尚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异。但就其書而論,則軾究心經世之學,明于事勢,又長于議論,于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其釋《禹貢》三江,定爲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遠有端緒。惟未嘗詳審經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遂以啓後人之議。至于以羲和曠職爲貳于羿而忠于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誥》服冕爲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爲證,則蔡沉取之。《朱子語録》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後《與蔡沉帖》雖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録》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者。”則又未嘗以簡爲病。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惟于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于此可知《東坡書傳》別出新解之概况及所受之肯定。舒大剛還進一步認爲《東坡書傳》在考訂《尚書》錯簡和訛文方面卓有成績,肯定其從文意語氣上審查脫文,從篇章結構上考證誤分一篇爲二,從事理上懷疑錯簡,從文理上審察錯簡,從史實上考察闋誤,以及從文字上考證訛誤等。⑤至于蘇轍,其《詩集傳》力删《詩序》,四庫館臣稱:“其說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録。因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從删汰。”相較歐陽修等人懷疑《詩序》,蘇轍可謂更進一步矣。蘇轍有云:“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其所撰《詩集傳》、《春秋集解》,也確是不囿成見、多有發明之作。朱熹給予蘇轍《詩集傳》較高評價,稱“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毛、鄭)之區域。至于本朝,劉侍讀(敞)、歐陽公(修)、王丞相(安石)、蘇黄門(轍)、河南程氏(頤)、橫渠張氏(載),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四庫館臣也談到《春秋集解》權衡《春秋》三傳,以《左氏》爲主,兼采他說,斷以己意的特點,其云:“先是劉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更捨傳以求經。古說于是漸廢。後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于學官。轍以其時經傳並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意測者也…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于奮臆遽談者遠矣。”
另外,三蘇解經不務章句而推重義理。蘇軾指出:“夫論經者當以意得之,非于句意之間也。于句意之間,則破碎牽蔓之說反能害經之意。”⑥這可以看成三蘇的共同主張。蘇洵有《六經論》總論群經,“以聖人之道爲前提,著眼于《易》之幽,以明禮爲綫索,而遍求‘六經’之旨,而後出諸己意”。⑦再如三蘇合力完成的《東坡易傳》,四庫館臣稱其“大體近于王弼,而弼之說惟暢元[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可知此書延續了王弼不取象數而以義理解《易》的特點,是義理派《易》學之作。四庫館臣還高度肯定該書“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文辭博辨,足資啓發”,“李衡作《周易義海撮要》、丁易東作《周易象義》、董真卿作《周易會通》,皆采録其說,非徒然也”。
(二)以權變解經,兼融佛道
以權變解經,在蘇洵身上有著突出的表現。歐陽修在《薦布衣蘇洵狀》中對蘇洵有過這樣的評論:“議論精于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宏偉,博于古而宜于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這裏指出了兩點,一是蘇洵善識權變,二是蘇洵以經世爲務,所論甚確。蘇洵曾公開宣揚權變思想,稱“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諫論上》)。這種權變思想,與戰國縱橫之學有密切聯繫,王安石即指出“蘇明允(洵)有戰國縱橫之學”。⑧在蘇洵解經中,這種權變意識有著充分的體現。他在《六經論》中將“六經”的形成都看作是聖人權變下的産物,如他認爲聖人作《易》,“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之無窮”,又說:“《禮》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于强人而有《詩》焉。”權變思想如此鮮明,以至于朱熹嚴厲地指斥道:“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⑨再如蘇軾,其《禮以養人爲本論》反對提倡古禮,批評好古禮者“牽于繁文,而拘于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主張“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其《禮論》强調根據風俗變易而修禮,提出“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仿以爲法也”,“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這些都可說是用權變思想來解經。于《東坡書傳》,四庫館臣評曰:“軾究心經世之學,明于事勢,又長于議論,于治亂興亡披抉明暢。”可謂是對其善識權變,以權變解經的肯定。于《東坡易傳》,歷來研究《周易》分作象數和義理兩途,蘇軾却采用由象數分析進而探求義理的路徑,其《易論》云: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于八卦,至于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于卜筮,而聖人開言于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無用之數哉!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權變思想,對蘇軾爲人處世也有影響,有論者即指出蘇軾之所以和程頤勢不兩立,認爲程頤“拘”,缺少權變,是“不盡人情如王介甫”者,即與這種深厚的權變思想有關。⑩
三蘇期于致用,發明儒學,不免夾雜佛老之學。朱熹指出蘇氏“性命諸說多處私意,雜佛老而言之”(《答汪尚書》其四),貶之爲“學儒之失而流于异端”的“雜學”,並作《雜學辨》,專門辯駁其《東坡易傳》及《老子解》。四庫館臣亦謂“蘇氏之學,本出入于二氏之間,故得力于二氏者特深”。(11)蘇氏常有三教合一之論,並以之注解經書。如蘇軾說,“儒、釋不謀而同”(《南華長老題名記》),“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争爲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說”(《上清儲祥宮碑》),“孔老异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祭龍井辯才文》)。三蘇合力完成的《東坡易傳》,即是兼容佛老的解經之作,譬如關于《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解釋,蘇氏說:
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藉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有無之際也,始離于無而入于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于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幾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12)
在這裏,蘇氏不僅借用了老子“道”的概念,援引老子的“水幾于道”的觀點來解釋“道”,認爲“道”是陰陽未交的狀態,是“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而且還很明顯地吸收了佛教無不絶虛、有非真有、非有非無、有無合一的思想。(13)蘇轍也主張三教“道並行而不悖”(《歷代論四·梁武帝》),在其晚年所撰的《老子解》中有充分體現,蘇軾跋語稱“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晋、宋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蘇轍的《論語拾遺》爲補《東坡論語解》而作,亦多有三教會通之語,四庫館臣即指出:“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邪’爲無思,以‘從心不逾矩’爲無心,頗涉禪理。以‘苟志于仁矣無惡也’爲有愛而無惡,亦冤親平等之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爲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如之義。蓋眉山之學本雜出于二氏故也。”(14)
(三)以人情解經
以人情解經,有時是與權變相聯繫的。如蘇洵在《詩論》中指出: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于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使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于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
此論即認爲,權變也要從人情出發來考慮。而蘇軾、蘇轍,對于以人情解經則有更多的發揮。如蘇軾《中庸論》指出:“聖人之道,自本觀之,則皆出人情。”他又說:“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途之人皆可以爲禮。”(《禮以養人爲本論》)蘇轍也指出:“夫‘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又說:“《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詩論》)他還在《進策五道·臣事下·第四道》中從宏觀上指出:“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蘇轍甚至以是否合乎人情來衡量經書,其《歷代論一·周公》即云:“凡《周禮》之詭异遠于人情者,皆不足信。”
在具體的經書注解中,蘇氏多有以人情爲基準者。如《東坡易傳》釋《無妄》卦《彖傳》“‘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曰:“無故而爲惡者,天之所甚疾也。世之妄也,則其不正者容有,不得已焉。無妄之世,正則安,不正則危。弃安即危,非人情。故不正者必有天灾。”(15)再如釋《升》卦“六四:王用亨于歧山,吉,無咎。《象》曰:‘王用亨于歧山。’順事也”曰:“上有所適,下升而避之。失于此而償于彼,雖不争可也。今六四,下爲三之所升,而上不爲五之所納,此人情必争之際也,然且不争而虛邑以待之,非仁人其孰能爲此?太王避狄于豳而亨于岐,方其去豳也,豈知百姓之相從而不去哉?亦以順物之勢而已。以此獲吉,夫何咎之有?”(16)在蘇氏《東坡書傳》、《詩集傳》等書中,如此類以人情解經之例尚多。這正如朱熹《答汪尚書》其四所說:“若蘇氏之言,髙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
以人情解經,其根源在于蘇氏的性命之學。朱熹說:“蘇軾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答呂伯恭》)秦觀在《答傅彬老簡》中則指出:“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與世周旋,至粗者也。”蘇氏在《東坡易傳》、《中庸論》中對性命之辨多有涉及。在蘇氏看來,道、性都是不可以善惡言的,因而反對孟子的性善論。(17)蘇氏還指出所謂性乃是“其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是“不可得而消”、“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東西;所謂命,乃“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並云:
情者,性之動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無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爲,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無我,則謂之命耳。(18)
這裏不僅反駁了所謂的性善情惡說,還把情、性、命置于同一層面,賦予情以本體的地位。蘇軾在解釋《尚書·虞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時說:“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放之則二,精之則一。”所反映的同樣是情、性、命合一的思想。既然如此,以人情爲本,以人情解經,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三蘇經學,推闡義理而期于經世,明于事勢而洞達人情,發明儒道而兼容佛老,議論雄辯而文辭精要,在熙寧以來的學壇獨具風采,更是在南宋初年興盛一時,正如朱熹《答汪尚書》其四所云:“蘇氏之言,髙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
三蘇經學,對其文學觀念和創作都産生了深遠影響。
就文學觀念而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經世致用的觀念出發,要求文章有爲而作;二是從本于人情的觀念出發,要求文章自由地、無限制地抒發情感。先說第一點。如蘇洵,從前引歐陽修的薦詞,已不難看出蘇洵爲文經世的旨趣。而蘇洵在《寄歐陽內翰第一書》中提出來要獻給歐陽修閱讀而自己也頗爲自得的文章,即是《洪範論》、《史論》等文字,這些文字顯然是“不爲空言而期于有用”的。再如蘇軾,他在《答虔倅俞括奉議書》中指出:“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于濟世之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由此當不難想見蘇軾爲文致用的旨趣。蘇轍也同樣提倡有爲而作,他在《詩病》一文中專門批評了“唐人工于爲詩,而陋于聞道”。其實,蘇軾《鳧繹先生詩集叙》所記的一則事例,更能反映三蘇有爲而作的主張,其云:
(蘇洵)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焉。”
據此文“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尤存”云云,可知蘇洵教諭蘇軾寫作有爲之文時,蘇軾還是個不到十歲的小孩子,對其所産生的影響當然會很深刻了。
再看第二點。情感的自由抒發,就是既不刻意求之,也不故意阻之。相應地,在文學主張方面,前者就表現爲無意爲文,蘇洵曾用風水之喻來比擬“無意爲文”而自然成“至文”,他說:“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殊狀异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仲兄字文甫說》)蘇軾《南行前集叙》也指出:“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至于後者,則表現爲隨意揮灑成文,這在蘇軾身上表現得尤爲明顯。他在《自評文》中說道:“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這既是蘇軾對自身文章的精準評價,也是蘇軾頗爲自覺的文學主張,他在《答謝民師推官書》中也表露出對“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的文章的贊賞。
再從實際創作來說,也多體現出了上述的文學主張。三蘇都寫作了大量的切乎人事、關乎道義的有爲而作的篇章,如蘇洵《權書》、《衡論》、《機策》,蘇軾《留侯論》、《續朋黨論》,蘇轍《三國論》、《上皇帝書》等,都是議論謹嚴、辭辯宏偉之作。與之同時,他們文學創作的整體風貌,也多表現出了激情澎湃、縱橫恣肆且又變態萬千的一面。蘇軾是其中的代表,在詩、文、辭、賦方面都明顯帶有“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的特色,至于以文爲詩、以詩爲詞,以文爲賦等,對蘇軾來說,幾乎是很自然而簡單的事了。如蘇軾的詞作,與他的權變思想和以人情爲文的主張都有關係。其詞之所以能够“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倒不一定是蘇軾對抬尊詞體有多麽自覺的意識,更爲根本的,當還是他在直抒胸臆、通達權變方面所作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們對蘇詞的評論,如李清照貶之曰“句讀不葺之詩爾”(19),或如晁補之贊之云“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20),雖得其事實,然未免皮相。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蘇軾的詩歌是宋詩“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的杰出代表,尤其在以議論爲詩方面,更可謂達到了極致。因蘇軾的博學多識和長于議論,常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出現了諸如《題西林壁》、《飲湖上初晴後雨》、《琴詩》等理趣詩。而這,與蘇軾長期浸淫于經學,且以議論雄放見長有著很大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三蘇經學與文學的相通,有著哲學層面的根源。蘇氏在《東坡易傳》中曾援引老子以水喻道,在注釋《習坎》卦《彖傳》時說:
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爲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爲信,而以無常形者爲不信,然而方者可斫以爲圓,曲者可矯以爲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爲信也如此。今夫水雖無常形,而因物以爲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無常形,是以迕物而無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由此觀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所遇有難易,然而未嘗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盡,而是心無已,則終必勝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勝物者,維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剛中。(21)
“柔外是靈活性,名曰曠達,剛中是原則性,名曰執著,剛中而柔外,執著與曠達的統一,這就是水所象徵的聖人之德”。(22)不難看出,三蘇尤其是蘇軾,一生的爲人處世、治學爲文,都體現出執著與曠達相融合的特徵,而其哲學根源,即在于此。
最後,有必要指出蘇氏文學對其經學的影響。前引陳善論荆公、東坡、程氏三家之文時已指出蘇文特色在議論。長于議論,在蘇氏經學中同樣是一大特色。朱熹評蘇軾《論語說》曰:“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亦煞有好處。”(23)朱熹又云:“東坡解經(一作解《尚書》),莫教說著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24)朱熹《答汪尚書》其四還指出:“蘇氏之言,髙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我們知道,朱熹傳二程衣鉢,是道學的集大成者。出于門戶之見,朱熹對蘇軾多有尖銳批評,如說蘇軾“說什性命,全然惡模樣”(25),且指斥蘇氏爲“雜學”,專門撰《雜學辨》來批駁蘇氏之說。而在這裏,朱熹除了肯定蘇氏義理解經的精深,又特別贊許其文辭的議論雄放、筆力過人,以致于“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由此,當不難想見蘇氏經學的卓异風采。譬如,《東坡易傳》解《乾》卦爻辭“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昔惕若厲,無咎”云:
九三非龍德歟?曰:否,進乎龍矣!此上下之際,禍福之交,成敗之决也。徒曰龍者,不足以盡之,故曰君子。夫初之所以能潜,二之所以能見,四之所以能躍,五之所以能飛,皆有待于三焉。甚矣,三之難處也!使三不能處此,則乾喪其所以爲乾矣。天下莫大之福,不測之禍,皆萃于我而求决焉,其濟不濟,間不容髮,是以終日乾乾,至于夕而猶惕,然雖危而無咎也。
從中我們不難感受到雄放恣肆的行文措辭和堅挺沉毅的擔當情懷。略如冷成金所評,“這的確是詩一般的語言,表現出的是那種銳身自任、不畏艱難的經世情懷”。(26)由此可知,作爲私學的三蘇經學,之所以能和作爲官學的荆公新學鼎足而立,其文筆縱橫是一大關鍵。而這,對于豐富經學著述的品類、促進經學的傳承與繁榮,顯然是有利的。
注释:
①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12頁。
②樓鑰:《攻媿集》卷七十七《跋袁光禄(毂)與東坡同官事迹》,《四庫全書》本。
③《欒城集》,第1212頁。
④王應麟撰,翁元圻等注,欒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點:《困學紀聞》卷八《經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95頁。
⑤舒大剛:《蘇軾〈東坡書傳〉述略》,《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
⑥蘇軾《東坡易傳》卷七,《四庫全書》本。
⑦郝明工:《蘇氏蜀學之經學考察》,《成都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
⑧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録》卷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1頁。
⑨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本朝四·自熙寧至靖康用人》,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118頁。
⑩胡昭曦、劉復生、粟品孝:《宋代蜀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第34頁。
(1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六,“《道德經解》二卷”条,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43頁。
(12)《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上》。
(13)僧肇《肇論·不真空論》云:“(万物)雖無而非无,無者不絶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有無稱异,其致一也。”
(14)《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論語拾遺》一卷”条,第292頁。
(15)《東坡易傳》卷三《無妄》。
(16)《東坡易傳》卷五《升》。
(17)詳參《東坡易傳》卷七《繫辭傳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句解。
(18)《東坡易傳》卷一,《乾》卦《彖傳》“保合太和乃利貞”句解。
(19)李清照撰,王仲聞校注:《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95頁。
(20)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六《樂府·黄鲁直詞謂之著腔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第469頁。
(21)《東坡易傳》卷三。
(22)余敦康:《内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77頁。
(23)《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本朝四·自熙寧至靖康用人》,第3113頁。
(24)同上。
(25)《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朱子十七·訓門人八》,第2899頁。
(26)冷成金:《蘇軾的哲學觀與文藝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13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