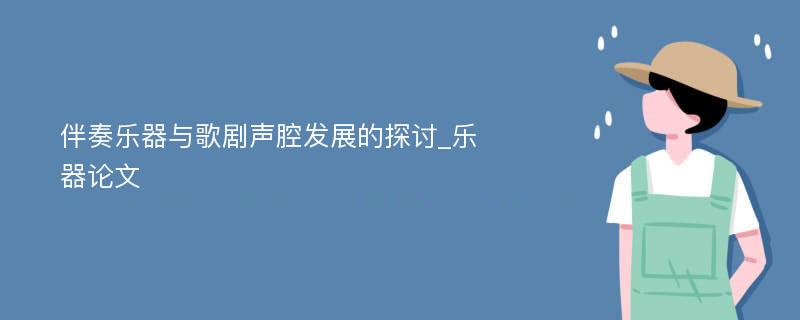
伴奏乐器与戏曲声腔的发展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腔论文,戏曲论文,乐器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的工具,戏曲声腔所依托的物质手段——伴奏乐器,其发展不仅对戏曲声腔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戏曲声腔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南弹北曲,还是梆子皮黄,抑或昆曲京剧都盖莫能外。因而,戏曲声腔的演变发展过程是和其伴奏乐器的变迁、更新与改制过程相依相随的。
关键词 伴奏乐器 戏曲声腔 演变发展
戏曲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中综合性较强,形态结构较复杂的一个门类,戏曲音乐的两大组成部分,声乐与器乐是有机的统一体,唱伴相融是我国戏曲艺术的特色。从我国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看,早在远古舜时代出现的“韶”乐舞,称“箫韶”,就是以吹奏乐器“箫”伴奏的一种舞蹈;汉王褒《洞箫赋》所述“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龢”,则是用吹管伴奏民歌[1]。这充分说明,我国古代先民,在繁衍生息的劳动实践中,不仅自发地创造谣曲、舞蹈和乐器,而且已将三者融为一体,唱伴相随。由原始歌舞演化而成的戏曲艺术,很自然地形成以伴奏乐器“托腔、节舞”而唱伴交融的传统特色。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的工具,戏曲声腔所依托的物质手段——伴奏乐器,它不仅对戏曲声腔风格的表达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戏曲声腔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质言之,戏曲声腔的发展演变,是和伴奏乐器的变迁、更新、改制、发展相伴相随的,回顾这一历史进程,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南北曲、昆腔——弦索、吹管
从北宋宣和年间到南宋长达一百六十年的期间,由于金人入侵造成了自南北朝以来又一次南北文化对峙局面,南北地域分别处于不同政治统治之下而被隔离,从而在戏曲音乐上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两种风格迥异的声腔——南曲与北曲。造成这种差别不仅有语言、地理、风俗、习惯的差异,伴奏乐器的不同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北曲在弦索,南曲在笛”,“南主箫管,北主弦索,北曲仅可以入弦索,而不可以协箫管。”(清·徐大椿《乐府新声·源流》)“弦索流于北部,北力在弦”(王世贞《曲藻》)。早期,弦索是弹拔乐器总称,后特指三弦或琵琶等,北曲音乐实践及众多论著表明,这里的弦,主要指三弦,如以三弦为主奏乐器的戏曲称为“弦子戏”。“北主弦索”,即是指北曲重三弦,以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北杂剧深受民间说唱音乐影响,是从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诸官调是一种大型说唱音乐!伴奏乐器早期用鼓、板、笛等,后改用“弦索”三弦,故史称“挡弹词”或“弹唱词”。北曲中的弹弦乐三弦伴奏“节节排排,弹弹有准”,音乐平直,节奏感强,而音乐富于跳跃性,形成北曲声腔硬挺直捷的特点,“其曲以顿挫节奏胜……”。
源于民歌小调的南曲,是“不仗弦索”而以竹笛为伴奏的。竹子产于南方,取材极为方便,并且自然成形,制作简单。同时更由于竹子中空有节,坚韧而顽强,早在古代就被人们赋于很高的人格品位。因此,艺人们采用竹子制作乐器,并以之伴奏歌舞和戏曲唱腔。早在远古时期,黄帝就“使伶伦伐竹昆溪,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2]。管乐器在我国传统中很早就被重视,在远古的记载中就有埙、苇籥、管、笙等。对管的重视,直接影响到多种竹管乐器的制作,并成为南曲的主要伴奏乐器。“且笛,管稍长短齐声”它乐音柔和,音色细腻,气息连绵,南曲在笛子的托腔伴衬下。声腔音乐委婉清扬,亮丽柔远……南曲与北曲两种声腔风格,诚如古人所论:“北之沉雄,南之柔曼,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形成如此不同的南北二调,伴奏乐器的不同,是其重要原因。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作为剧种的北杂剧日益衰弱,但作为声腔的北曲音乐以及为之伴奏的三弦,却被源于南戏的昆腔所吸收、容纳,昆腔集南北歌调于一堂,形成昆腔化的南曲与北曲,从而使昆腔成为集南北戏曲音乐之大成的大声腔。史载,昆腔“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场面大成”。不仅改革原伴奏乐器上的简单,形式上的不完整,而且对北曲的伴奏乐器并非全其照搬,而是保持南曲声腔风格的同时,对乐队和乐器进行改制和创新。将原大三弦改制为小三弦,“更定弦索音节,使与南曲相近”[3]。伴奏中一切乐调仍以笛为主,笛色上用统一的种种润饰。把南北音乐伴奏融合起来,艺术地统一于一个声腔中(昆腔),“有弦索唱作磨调,又有南曲配入弦索”。“恒以深邈助其凄唳”[4],唱伴互助交融,南北音乐互融互补,南曲柔曼与北曲激越之揉合,以北曲刚健劲切补南曲优柔婉转之不足,使昆腔在委婉清丽中,透出刚健沉雄,音乐更富有层次、变化、对比。形成了笛、三弦、鼓板为主的昆腔伴奏三件头。“笛管、笙、弦按节而歌”,采用多种乐器,丰富伴奏场面,乐队组织进一步完备,形成我国戏曲音乐早期较为完整的民族管弦(弹弦)乐队。伴奏方法和技巧得到发展和提高,使唱腔色彩,舞台气氛有了更加复杂的变化,音乐的乐器场面,分为直接配合衬托唱腔和陪衬舞蹈动作的文、武场。致使昆腔进入了一个灿烂光辉的极盛时代,在数百年中领袖一代曲坛。
(二)弋阳腔——锣鼓节拍
弋阳腔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属南戏系统。弋阳腔在我国戏曲音乐史上另竖一帜,走了一条全然和昆腔不同的通俗路子,它的舞台不在宫廷、厅院,而是活跃传播于民间。弋阳腔承袭了我国古代徒歌形式,其唱腔无弦管伴奏,只以打击乐按节拍,后台众人帮腔。因“其节以鼓,其调喧”,唱腔置之金鼓喧闹之中,紧锣密鼓,声如爆竹,造成了“锣鼓喧闹,唱口嚣杂”的热闹气氛,真所谓“半台锣鼓半台唱”,正是这种别具一格的唱伴形式,形成了弋阳腔特殊的艺术效果,以及声腔系统的传统风格。
打击乐最初只是直接对劳动场面和自然界音响的简单模仿,因此是我国器乐中发展最早的乐器。从石器时代古磬的出现,到战国时期编钟出土,显示出几千年前我国打击乐艺术已得到高度发展,在原始乐舞里,“帝喾乃令人抃,或击鼓,击钟磬……”[5],《吕氏春秋》就有了击乐器伴舞的记载。随着打击乐器的变迁、发展,种类增加丰富,在我国戏曲雏形期,唐代的百戏、歌舞戏,除了笛之外主要是击乐器伴奏称为“鼓架部”,宋代以后,戏曲的成熟,声腔的发展,击乐器广泛运用于戏曲音乐中,成为烘托舞台气氛,配合唱、念、做、打,是戏曲音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特别在弋阳腔这种以大地作舞台、兰天当背景的高坡土场演出中,各种击乐器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巧相鸣和”,尤有气势声威,集中凸显出打击乐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艺术功能,因而成为弋阳曲调最有特色的伴奏形式,而且成为唱腔结构重要的要素。[6]
由于弋阳腔只以“锣鼓助节,不托管弦”之故,行腔、用字不受格律及乐器转调所限,音乐上局限性小,适应性强,唱腔自然可灵活多变,可顺口而歌,或“改调歌之”,随意运用,随心入腔。因此,在流变中繁衍出众多的变体与支流,许多声腔都是弋阳腔基础上的产物。如弋阳腔流入安徽,演变出安徽的弋阳腔名曰“四平腔”;废去帮合,以双笛伴奏托腔,演变为“吹腔”;吹腔伴奏又改为胡琴随腔,演变为“四平调”(又名胡琴腔,平板二黄)。后又演变为皮簧戏中二簧腔等。这些腔调的逆变,论源流,基本源于同一音乐材料,由弋阳腔一脉相承蜕化而来。而促成其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伴奏乐器的不同变换、更新,声腔随伴奏乐器转化而音渐递改,在性能不同的新伴奏乐器推动下,另出机杼,竞翻新腔。
(三)梆子、皮黄诸腔—拉弦乐器
明清时代,戏曲声腔迎来了历史性变革,这是从以秦腔为代表在我国北方兴起的梆子戏的伴奏,“其器不用笙簧”,而“以胡琴为主”开始的。由于拉弦(板胡)乐器作为主奏乐器激弦繁音,强化了梆子高亢、激越的音乐声腔风格,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由此,逐渐形成了我国戏曲音乐伴奏以拉弦为主的昌盛局面,对我国戏曲声腔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拉弦乐器的出现晚于击、吹、弹、弦乐器,最早的拉弦乐器,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奚族于唐代传入中原的奚琴。宋。陈旸《乐书》载:“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为“奚部所好之乐”。最初是以竹片拉弦“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宋代始有了马尾胡琴在我国西北地区流传。《元史卷》有:“二弦以弓捩之,弓子弦以马尾制”。清代拉弦胡琴在戏曲音乐中得到广泛运用,并从胡琴母型中派生出各具风姿的拉弦乐器,胡琴的发展逐渐取代了吹管、弹弦在戏曲伴奏中的主要位置,成为我国诸多声腔剧种的主奏乐器,被称为“主胡”或“正场胡琴”。使剧坛面貌为之一新。如各地梆子戏采用各型制不同的板胡;皮黄戏用京胡,粤剧用粤胡,吕剧用坠胡,花鼓戏用大筒胡,琼剧用竹胡,陇剧用四胡,以及柳胡、椰胡、擂胡,高、中、底各类胡琴等,变种繁多,不胜枚举。形制各异的拉弦胡琴在戏曲音乐中的运用,推动了地方戏曲声腔的极度繁盛发展。
拉弦乐器在戏曲声腔中的采用,更适宜梆子、皮黄中创造的板式变化特征的音乐结构形式,突破了始戏曲音乐形成的规范,更有益于音乐戏剧化的要求。由于拉弦胡琴弓子运动快慢伸缩自如、灵活多变,既能伴以柔和流畅曲调,也能演奏跳跃、有力的旋律,更适应各种板式曲调不同节奏的多种变化伴奏,充分表达抒发音乐戏剧性。而且在伴奏方式上,起唱之先,乐器引奏,歌唱之尾,器乐尾奏,句逗间歇均以乐器伴奏联缀间奏,形成引奏、间奏、尾奏的器乐形式。并且,与吹管弹弦乐器相比,拉弦乐器随腔伴奏,更贴近人声演唱,更便于声腔融合和弥补演唱之不足,正所谓“工尺伊唔如语,旦色之歌喉声,每借以藏拙焉”[7]。较之不用拉弦剧种丰富了声腔艺术表现力。从声腔的创腔发展上看,运用拉弦乐器更便于改弦换调,创造新腔。因为拉弦乐器比管乐器在旋宫转调上更为灵活方便,笛等管乐器“竹声不可以度调”,“管律不甚精确,由于受笛孔限制,均孔律并不能彻底解决整个调性转调问题[8]。而拉弦乐器通过胡琴的不同用弦,“高弦低唱”“改弦换调”产生新的曲调,发展新的声腔。如皮黄腔的反调唱腔“反二黄”、“反西皮”是二黄、西皮的变化形态,是将二黄的sol re弦换奏do sol弦,即换成反弦,造成低音区呻吟悲诉的旋律,产生悲愤凄凉情绪,形成“反二黄”腔。粤剧中的“乙反调”,越剧中的“弦下调”,沪剧中的“反阴阳血”腔,楚剧中的“西皮迓腔”,长沙花鼓戏的“木马三流”腔,皆都是通过拉弦胡琴灵活便易地改弦换调、利用调式、调高的不同变化形成情调、色彩不同的新唱腔,繁衍了同腔种之正反调,丰富了音乐唱腔表现力,它是伴奏与声腔发展上的一种新创腔,使我国戏曲音乐向着纵横的方面深入发展。
(四)京剧——各种伴奏乐器的综合与创新
京剧作为皮黄腔代表性剧种,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剧种,有国剧之誉,它是我国戏曲艺术发展的最高结晶,也是我国戏曲音乐发展较完善的声腔体系。从京剧音乐声腔的形成演变中,我们可以综合地看到伴奏乐器在剧种音乐里,在声腔演变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机制。
第一、声腔风格定型于主奏乐器
几经演变的京胡,成为京剧的传统伴奏乐器,由于京胡的构造特点和特殊的演奏方法,日臻完善定型,使京剧成为独具特色的声腔剧种。京胡结构精巧,音色清亮明丽,京胡特殊的演奏,多用滑指滑音,其弓法则往往急促快捷,节奏跳跃感强,多用分弓,讲究一字一声一弓一音,即使一个长音也作分弓拉奏。京胡这种基本的演奏风格,把京剧中兼具南北音乐、来源多样化的各种不同声腔融合、协调,统一于主奏京胡的风格中,京剧化的梆子没有了梆子戏里那样的高亢、激越,拨子也没有徽班戏里的沉雄,变弋、秦、徽、汉为京,形成统一的京剧风格。同时,又通过主奏京胡对各不同声腔的不同用弦,在京剧整体音乐中又体现出个性化的特征色彩。京剧中不同风格流派如梅、程、尚、荀四大名旦,梅派唱腔雍容华丽;程的唱腔幽吟婉转深沉;尚的唱腔刚健;荀的唱腔妩媚。它们在唱腔上的不同风格,均借助于京胡伴奏的“托、衰、衬、垫、迎、包、让、送”高低轻重,抑扬顿挫,得到充分地发挥和发展。
第二、改制(变)伴奏乐器,强化声腔风格。
伴奏尤其是主奏乐器,是表达声腔风格特色的物质手段,演奏者(琴师)们在艺术实践中对伴奏乐器常常对其作某些改造甚至改变,使声腔特色逐渐强化。京剧音乐中的两大基本声腔,西皮和二黄,一个源于北方,一个形成于南方,虽经融合初期仍有各自的渊源。在昔京剧继承着徽班的衣钵,因而在它以京剧声腔出现的早期,只是用笛子拖腔伴奏,但源出于北方曲调那种粗犷、豪放以及板腔体音乐节奏多变的特点,竹笛难以尽意,故后来改用胡琴,在改用胡琴的早期,使用的是厚筒软弓,因不宜表现京剧声腔中急速快捷、跳跃峭拢、明丽嘹亮的特色,故对胡琴本身进行改造,变为薄筒硬弓[9],以扫传统京剧唱腔中闲逸散淡、萎靡不振的病态之气。发展到梅兰芳时代,为解决伴奏音乐单调的弱点,加进了二胡随腔,以京胡和二胡协同伴奏,由于二者构造特征的不同、音色、性能上的不同,曲调旋律必然有所不同,二者伴奏乐器协同使用,刚柔相济,浓淡相宜,使声腔伴奏更加富于表现力。就京胡本身的制作和结构上也经历了多次的改制,才定型下来的。京剧声腔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强化和定位的。
第三、多种乐器综合运用,使声腔丰富多彩。
中国戏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在各地出现了各具特色的伴奏乐器,而这些乐器到京剧中得到了综合运用。如早期北曲的“弦索”(三弦、琵琶等),南曲的笛箫,弋阳腔的锣鼓,梆子腔的拉弦胡琴等,在京剧中都得到综合发展运用,在保持原传统主奏乐器京胡为主要特色的同时,充分发展各种民族乐器的特殊功能,形成以京胡、二胡、三弦、月琴为主的四大件以及不同色彩乐器的文场伴奏,和以鼓、板、锣、钹为主体的武场四大类,拉、弹、吹、打各种乐器的运用,使京剧音乐极为丰富多彩,并对各地方戏曲的文武场面以重大影响和指导。
第四、吸收外来乐器,在创新中推动声腔发展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汇入自己文化体系的国家。从乐器来看,笛原叫羌笛,板鼓原叫羯鼓,胡琴原叫奚琴,从蒙古传来,唢呐从波斯传入,以及随着歌舞音乐的发展吸收了较多的打击乐器,锣、钹各种定音与不定音的鼓和弹弦乐器各种各样的琵琶类等等,这些乐器经过改造都已汉化或华化,成为地道的中国乐器,在戏曲乐队中都得到广泛运用,而现在戏曲乐队文武场面的编配,基本上是唐吸收西域音乐后打下的基础[10]。今天,时代发展变化,人们审美情趣也发生着变化,声腔发展必须跟上时代要求,除了唱腔的旋律结构上进行创新外,在伴奏乐器上同样需要吸收外来乐器,加以融合创新。本世纪六十年代,京剧现代戏进行了艺术革新,在伴奏乐器以及乐队形式上,大胆吸收西方音乐立体化的思维,吸收西洋乐器,运用交响乐的手法为京剧唱腔伴奏。同时还出现了钢琴伴唱京剧唱腔《红灯记》,交响乐《沙家滨》、《智取威虎山》等,可以说是具有中国戏曲风格、中国民族气派的清唱剧,使京剧音乐耳目一新,展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风采。客观地看,这是新老音乐工作者一次大胆有效地探索,它的意义不只是丰富了京剧音乐伴奏,为刻画音乐形象增加了一种有效手段,而且为戏曲声腔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艺术实践经验。以历史的眼光看,古老的戏曲艺术和西方音乐形式间交融贯通,这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必要桥梁之一。
结语
伴奏乐器与戏曲声腔相伴相随发展的历史轨迹,清楚地显示出,伴奏乐器对戏曲声腔的兴替、蜕变、发展的重大作用。在历史上,随着艺人们的创造和引进各种新的伴奏乐器,或者在实践中对原有的伴奏乐器进行局部改进,或是整体改变,以及在乐器改革基础上技法的探索和积累,都推动戏曲声腔音乐的不断发展。“曲不离器”,唱伴交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戏曲声腔在这种相互影响交融里,不断经历着内衍与外化的改造中得到定位。伴奏乐器的完善是一个过程,戏曲声腔的成熟也是一个与此相随富有生命力的历史流变过程,它总是在不断的扬弃中,在不断的发现及否定中,使之不断成熟、繁盛。
通古鉴今。当我国人民叩响世纪之门迎接新时代,工业技术蓬勃发展,工艺制作不断更新,给戏曲声腔所依托的伴奏工具——民族乐器的创造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前景,随着民族乐器的不断改进,必然会使古老的戏曲声腔在新的物质依托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时代风格,取得新的突破和长足的发展。
[稿件收到日期:1996年7月15日]
注释:
[1][2][5]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
[3]明·宋直方《琐闻录》。
[4]明·沈宠绥《弦索辩讹》。
[6]高腔每一曲牌由帮腔、唱腔、套腔锣鼓三要素组成。
[7]清·吴初《燕兰小谱》。
[8]庄永平著《戏曲音乐概述》,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9]周眙白著《皮黄戏的变质换形》,中华书局出版,1952年版。
[10]马可著《戏曲乐队的作用和发展》,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
标签:乐器论文; 京胡论文; 音乐论文; 艺术音乐论文; 艺术论文; 京剧演出论文; 京剧论文; 三弦论文; 戏剧论文; 弋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