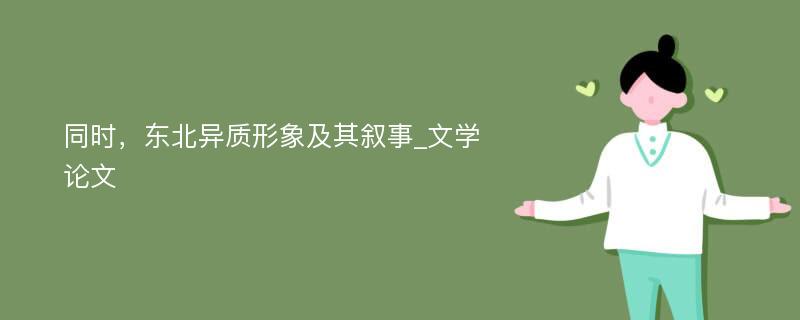
同时而异质的“东北”形象及其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作家和文人、特别是身在东北和关内的东北籍作家以及主要以他们为主构成的东北作家群,对广袤而神奇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少有描写的东北的历史、现实、自然、土地、人民、生活、社会,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叙述与书写,在这些叙述和书写中,其实构筑和呈现了一个鲜明的、包含着多重色彩和意义与价值的东北的形象,这个形象第一次以如此的规模和色调出现在中国文学中。与此同时,在所谓的“满洲事变”之后,在日本国内和伪“满洲”,一些日本的文化人和知识者以及非文化人的人士,陆续写作和出版了一批兼有游记、考察和文化民俗调查成分的“满洲风土记”之类的作品和著作,对东北(满洲)的历史与地理、自然与社会、民生与风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略不一的记述和书写。还有随着日本对东北的移民而出现的所谓“开拓文学”,也对东北的自然和移民生活作了描写。这些以日文写作的、在日本和伪“满洲国”出版的林林总总的文本,在整体上同样描绘和塑造了一个东北(满洲)形象,一个与中国东北作家和知识者的描述和叙述,在视角、视点、内容、色彩不一样的东北形象。借用美国学者安德林《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概念,“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文化人和知识者的东北—满洲形象,是同时而异质的,这个同时而异质的东北—满洲形象的出现,反映出中日两国知识者和文化人,在面对同一个对象时,他们的观察与看视的角度、视点和摄取装置存在结构性差异,由此带来书写和摄取内容的显著差异。这样的摄取角度、装置和内容的差异,构成了有关东北书写和形象的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认识内容,值得加以辨析和研究。
“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后果,是整个东北成为所谓的“满洲国”——日本殖民地的一个尽人皆知的“幌子”,因此,在东北作家的书写和叙事中,“九·一八”是一个将时间与空间的性质扭结在一起的不可拆分现象,代表和象征着一场巨大的民族和历史的灾难、苦难的“到来与开始”,似乎可以说,从30年代东北作家开始,现代中国以中日战争为背景和题材的文学,大都以“灾难降临”为叙事的起点,时间性与灾难性共同构成叙事的时间模式与意义模式。萧红1935年出版小说《生死场》时,她自己设计的封面上,就是一幅东北地图被斜着拦腰斩断,右半部紫红,左半部空白,在小说内容和结构上,也是一分为二,前十章写的是“九·一八”之前东北乡村农民的生死挣扎,第十一章“年盘转动了”以电影蒙太奇式的手法叙述了时间的转动与随后灾难的到来。“九·一八”作为时间的界限成为划分东北土地苦难与灾难性质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其他东北作家的作品,如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大江》、短篇小说《浑河的急流》,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李辉英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罗锋的短篇小说《呼兰河边》,白朗的短篇小说《伊瓦鲁河畔》等,以“九·一八”为标志的民族灾难的降临和苦难中的觉醒与抗争成为它们基本的、共同的叙事焦点和模式。
与这种以“九·一八”事变为临界点、以民族灾难和苦难降临为模式、以悲愤和激昂为情感色调的文本叙事相联系,沦陷的东北自然首先是作为“受难者”的形象而出现和登场的。这个受难者所遭受的苦难,一方面,是整个东北的山河易色,土地和家园被异族侵略者占领,萧红在《生死场》中以简洁和力透纸背的笔触,从东北农民的见闻感受的角度对此作了描绘。
另一方面,诚如鲁迅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作的序言里所指出的,这部小说“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的,有“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更有“受难的人民……”。① 土地与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是人类栖居的家园。土地、自然与人的生活和命运是紧密关联的。因此,在东北作家笔下,山河易色、灾难降临的受难的东北,更多地、具象地表现为人民蒙受的异族压迫和蹂躏的苦难。罗锋的小说《第七个坑》描写了日本殖民者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屠杀的暴行,他的其他小说也大都有这样的描写和内容,所以当时的评论家认为“罗锋大约是身受了或目击了敌人的残酷待遇罢,他常常悲愤地描写敌人的残酷”。② 其实不仅是罗锋,其他东北作家作品里也经常出现对日本殖民者杀戮暴行的描写。这样的描写一方面源于生活真实——日本占领后制造的平顶山屠杀等一系列惨案和东北大地上到处存在的“万人坑”就是血写的事实,同时更是对侵略者的所谓“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和“东亚共荣”的文学化暴露与“证伪”。罗锋和他的妻子、女作家白朗还较多地描写了“满洲国”林立的监狱、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被捕入狱,以及监狱存在的饥饿、苦行和酷刑,揭示出“满洲乐土”掩饰下“黑暗王国”的狰狞现实和“地狱”景象。端木蕻良的小说对土地和人民的受难的描写是多视角和多方位的,《大地的海》描述了东北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殖民者对农民土地的剥夺,《鸷鹭湖的忧郁》写了沦陷后东北农民的贫穷和孤苦无告,《浑河的急流》描写了“满洲国”的横征暴敛和暴政,《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述说了东北人民由沦陷带来的精神苦闷和亡国之痛。端木蕻良的这些作品里并没有直接和正面描写日本殖民者的具体化的“施暴”和虐杀,但是,在这些由压抑、忧郁、贫穷、丧失土地和尊严构成的“受难图”中,无一不有殖民者的蹂躏、压迫和施暴的“黑色存在”和影子。
在聚焦和描写东北土地和人民的受难中,东北作家还“愤写”了侵略者对东北妇女的蹂躏暴行。东北作家群里最有名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里,都有日本军人对妇女搜捕奸污和杀害的情节描写。相比于其他的苦难,妇女的被侵略者蹂躏和奸杀,是殖民地人民受难中最难堪、最残忍、最屈辱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苦难。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在现代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民族战争,妇女往往成为大规模野蛮奸污和施暴的对象,这种性侵害的施暴现象既是入侵者生理性、个体性的本能的兽性发泄,也是集体性的超出性侵害范畴的包含着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社会现象与国家现象——强势和侵害一方对被侵害民族和国家妇女的身体奸污和施暴,与他们对被欺侮的种族、民族和国家的蹂躏、占有、征服的现实行为,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想象之间,具有“意义”的联系和建构。因此,出于兽性的性本能发泄和民族施暴的双重目的对被侵略国家、民族、种族的妇女进行的大规模身体侵害和施暴,在现代的民族国家战争中屡见不鲜。同样,对被侵略和被侮辱的民族与国家而言,他们的妇女受到侵略者的身体侮辱和侵害,既是个体性、生理性的受难与侮辱,也是集体性、民族性的道德、文化和国家的受难与耻辱,被侮辱的女性躯体与被蹂躏的民族国家之间,在受害国的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意识与想象中,更具有意义的联系、象征和建构性。东北作家所写的东北女性的身体受到侮辱和摧残,既是异族侵略和压迫下“亡国”的东北人民受难的事实与写实,同时在具象的情节之上,也寄寓着流亡作家的诉求和文学的隐喻功能:被侮辱的女性躯体,在想象和象征意义上与受到侵占和蹂躏的土地山河、与遭到肢解和施暴的民族和国家具有意义的同构性,就是说,东北女性身体受到的侮辱和伤害是被从中国版图上遭到肢解和占领的东北的象征,也是整个民族和国家受难的象征,躯体的受难寄寓和具有了超越身体和个体的政治、民族和意识形态意义。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东北作家创作的以“九·一八”事变和沦陷的东北为背景的抗日文学,以及此后出现的抗战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中经常出现的被侵略国家和民族妇女身体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情节,往往都具有这样的写实和象征与隐喻的意义。特别是对现代中日民族战争中最早因故土沦陷而饱尝流亡之苦的东北作家而言,他们创作中的类似描写更具有、或者说他们更愿意追求和强调这样的意义。
不过,作为流亡作家和流亡文学,东北作家在对东北形象的书写和描绘中,不甘心仅仅止于“受难”的层面。故土沦陷的心理创痛和被迫流亡的特殊人生经历所产生的强烈的乡情,民族危机和国家遭难所产生的时代共鸣性的民族情,以及他们当时隶属的左翼政治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要求,都促使他们在写出一个“受难”的东北的同时,更要写出一个咆哮和抗争的东北,一个最先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并揭示出中国的“生路与死路”意义的东北形象。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批较早出现的“反日文学”中,左翼作家艾芜就曾写出了小说《咆哮的许家屯》,着重描写东北人民的“咆哮”和抗争。但由于作者没有东北生活的体验和不熟悉东北地域文化,致使小说出现理念大于形象之弊。而东北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体验和由此带来的优势,他们那“愿用文字的流写下你们热血的流”、为“故乡兄弟英勇的脚步,英勇的手”构成的“粗拙的力量”③ 讨回土地的壮举所激动的情感状态,使东北作家写下了《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大地的海》、《边陲线上》等一批表现不甘于做亡国奴的东北农民、学生、市民和义勇军反抗民族侵略的战争文学,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描绘与塑造了一个真实具体的、反抗侵略的“咆哮与战斗”的东北土地与人民的形象,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东北”形象。
这个形象的出现,首先在近代中国的反帝反殖的战争文学里是具有独特价值与重要意义。截止东北作家群出现之前,百年来中国的反侵略或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学,还没有比较像样的、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来提供这方面的文学经验和文学形象与图景,那些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表现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主题的作品,缺乏直接正面的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与战争场面、过程和形象的描写与叙事,有反帝反殖的“理性”主题却没有题材的、情节的、细节的和叙事的具体可感性,往往流于空泛和情绪的宣泄。因此,东北作家描绘的“咆哮与战斗”的东北形象,因为有生活的底蕴和切身的体验,有斗争与战争的场面和过程,有粗犷但又不乏山林泥土气息的感性经验和形象,因此东北作家的抗击民族侵略和压迫的“东北形象”的书写,为中国近代反帝反殖文学提供了新鲜的、独特的文学经验、形象和景象,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和意义。这一点,当时的一些读者和批评家已经有所认识,认为东北作家的这些书写,“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④
其次,30年代以后,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上海“一·二八”事变、华北危机、整个中国都面临民族危机和战争的时代,中国需要表现民族危机、鼓吹和振奋民族精神、张扬反抗与战斗的“抗战文学”——一种特殊时期的、中国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文学。在文坛占据重要地位的左翼文学此时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与主张,都反映了时代、政治和社会心理对于文学的这种要求。不过,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关内作家此时还无法完成这种使命和任务。而东北作家在关内文坛虽有理论要求却还没有生活积累和创作实践、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适时地推出了以沦陷和战斗的东北为表现对象的中国最早的抗战文学,中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侵略性质的战争文学,并成为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文学的滥觞和先声,同时为中国文学即将出现和到来的抗战文学、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提供了文学书写和叙事的经验与样板,尽管这经验和模式还不十分成熟,远非尽善尽美。因此,东北作家群的这类作品,受到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普遍重视和欢迎,作为左翼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和周扬尽管对民族战争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看法不一,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两个口号”的提出和争论,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把东北作家描写东北及其人民挣扎与抗争的创作,作为自己文学主张的来自创作实践的“实证”,说明和证明自己一派的文学主张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第三,最早身受沦陷之痛和流亡之苦、故乡情与民族情悲愤交织的东北作家,在描绘和塑造挣扎与抗争的东北形象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东北沦陷的这种地方性、局部性灾难与整个民族国家性危机和灾难的联系,地方性灾难具有的民族国家性意义,舒群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就包含着这样的意蕴和“所指”;一方面描绘和揭示东北作为“民族战争战地”和抗争的形象,对整个民族和国家具有的警示意义,即鲁迅在《八月的乡村》的序言里指出的,“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将来,死路与活路”。⑤ 当然,东北的“战地形象”所具有的这种价值和意义,是形象自身所包含和东北作家所追求的,同时也是被鲁迅和左翼文化与文学界所刻意解读和阐释出来的,这种解读和阐释无疑为形象的意义作了引申、增值和扩容,扩大了形象的影响力与鲜明性。
与上述激情化的描写和表现“受难与战斗”宏大叙事中的东北形象相比,在东北部分作家作品中,还存在着一种非宏大叙事、非主流的和非时代话语性的有关东北形象的描写和叙事——沦陷后的东北及其人民苦难无告的、类似于“孤儿”和“弃儿”的境遇与感受。这样的描写与叙事既是当时部分东北流亡作家悲愤交织的情感心理状态的真实映现,也是东北形象、处境和命运的一种历史真实性存在——“九·一八”事迹后,“东北王”张学良兵强马壮的军队没有做像样的抵抗便撤退到关内,将生养他们的家乡土地和父老乡亲抛弃于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国民党中央政府没有收复东北的意图,只把东北的沦陷作为地方性的局部事件,不希望事件扩大,不希望以明确的言论和作为刺激日本,更不希望由此引发中日战争,尽管这些意图可能有种种的理由。一句话,这些意图和理由的潜台词是让沦陷的东北作为代价和牺牲,将这一“国难”事件低调化和局部化,尽量避免由此引发更大的、全局性的国难。另一方面,在东北及其人民于民族压迫的苦境中挣扎和奋斗的时候,在国内的很多地方,照样是歌舞升平,正如鲁迅所说: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⑥ 还有,当部分东北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而逃亡或流亡到关内的时候,却遭到了一定的歧视与厌烦,鲁迅在为萧军小说作序时就提到“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⑦ 不愿租房给逃难的东北人,或者把他们叫做“亡国奴”或“亡省奴”而加以歧视和蔑视,这样的现象在当时并非个别,当时的报刊和一些记者文人的文章里,就曾多有记载。⑧ 这样一些令人悲愤的事件的存在、刺激和感应,引发了部分东北作家的东北叙事中出现了另类的声音和形象。端木蕻良的小说《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的老人,在“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而茶饭不思,“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苦吟既表达了家国之痛,也表达了年年盼望而“王师”不至、无人来光复失地解救“遗民”——被外族压迫和本国遗弃之“难民”的痛苦现实和心境,东北和人民的孤苦无告的牺牲者与“弃儿”的形象,在漫天的“胡尘”和老人的眼泪中曲折地、委婉地映现出来。他的《乡愁》写东北难民身在北平而心在故乡,有家难归的流亡处境和绵绵不尽的思乡之情,道出了东北人民难言的心曲,而北平的繁华安宁却难以使难民安心与安住,这虚构的小说叙事背后却掩藏着并不虚拟的难堪事象。其他如萧军的《樱花》,舒群的《老兵》等,也都描写了一些发生在东北人、东北爱国人士身上的令人心酸的故事,在一首诗中,萧军甚至表达了自己及其代表的东北人“没有祖国”、“哪里是祖国”的激愤心情,表现了流亡者在“感情冲动增强了一倍”的极端情感状态下对国家认同的忧郁和模糊。当然,东北作家通过有关东北形象和人民的述说表达的“祖国怨”并非不爱国,而是骨子里极端爱国却又暂时对“祖国”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对部分关内人歧视东北难民和人民的行为感到失望和愤懑的一种极端化的表现,虽不乏激愤中的偏颇,却也具有历史与处境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全面抗战时期的到来,这样的东北形象、叙事和色调自然随之消逝。
由“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所导致的特殊的人生经历、流亡生涯和心理情感状态,使得东北作家群描绘和塑造了如上所述的、慷慨激昂和金刚怒目似的东北形象,但随着流亡生涯的延长和中国抗战的爆发,特别是进入40年代以后,东北作家对东北的叙述,发生了一些有意味的变化——视野由沦陷的现实东北向历史的东北延伸和回顾,在历史与文化“寻根”、批判与乡情眷恋中,不约而同地书写和叙述了一个历史的、风土与风俗色彩浓烈的、日常状态的东北,展现了这种视野下东北形象的丰富多姿的面貌。尽管在描绘和塑造这个历史和日常视野中的东北形象的时候,东北作家的着眼点和意图不尽相同,但是回忆性视角和历史性视野,却使叙事中的东北形象既纷繁多态,又具有某些共性化的“东北风情”。
这个东北形象给予读者最鲜明的阅读震撼和撞击的,是东北大地山河和自然环境的寥廓雄奇。早在描写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和压迫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里,端木蕻良就曾经如此描写东北的大地:
假如世界上要有荒凉而辽阔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要不是那顶顶荒凉,顶顶辽阔的地方,但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
多么寂寥!啊比沙漠还要幽静,比沙漠还要简单。一支晨风,如它高兴,准可以从这一端吹到地平线的尽头,不会在中途碰见一星儿的挫折的。倘若真的,在半途中,竟尔遭遇了小小的不幸,碰见了一块翘然的突出物,挡住了它的去路,那准是一块被犁头掀起的淌着黑色血液的泥土。
这样的东北土地的形象和深情的描写,曾受到中外论者的高度赞誉。刻意展现和诗意描绘东北大地草原的雄阔与壮美,已经成为端木蕻良的创作追求和诸多作品的风格特色。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也以如椽大笔描写与刻画东北的大草原与平野,被当时的评论家赞誉为“把科尔沁旗草原直立起来”。⑨ 如果说端木蕻良善于和长于描写东北的辽阔大地与平野,那么萧军则善于把小说的内容放置于险峻的山林背景中,他的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发表后,著名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在评论中也提到作品山河的壮美、严肃与内容和主题的关系,⑩ 40年代萧军的同样被批评家誉为“史诗”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以更多的笔墨描绘了东北的河流山林的神奇伟岸及其孕育的人民的“无教养”的“粗野”和强悍。萧红在《呼兰河传》则准确而真实地描写了那把大地都冻裂的东北的冬天和严寒,也诗意地描写了东北夏天傍晚的变化无穷的火烧云。身在沦陷区东北的作家梁山丁,在长篇小说《绿色的谷》的开篇,描绘了东北山野夏秋之季迷人的景色和丰饶的物产。总之,把东北作家这些回忆性的(也包括现实性的)、分散和断片的有关东北自然环境的描述集中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立体、完整和神奇壮美的东北土大自然的形象:土地辽阔,山河壮美,森林茂密,物产丰饶,四季分明,一派充满魅力和神奇的北国风光。当然,这样的风光景物是东北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同时也包含和浸透着东北作家的流亡者和游子的心理情感——浓烈的乡情眷恋。
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和社会总是密切关联的。在部分东北作家的回忆性和寻根性的作品里,他们描写和展现东北大野自然的雄阔与壮美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展现和描述历史的、日常的东北,其社会与人生内容的丰富与“浩大”。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和萧军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之所以被称为“史诗”或具有史诗的风范,是与他们刻意追求和作品表现出来的“宏大”叙事分不开的。首先,它们在遥远和宏大的历史长河与背景中对广阔东北的历史和生活内容作了“寻根”式的追述和叙写,具有“大河小说”所特有的时间与空间的浩大性。《科尔沁旗草原》从清朝山东的灾荒、难民向东北艰难困苦的逃亡、曹家在东北的创业和成为科尔沁旗草原上大地主家庭的历程,一直写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构筑了创世神话般的东北大地主的发家史和历史的东北形象。萧军的《过去的年代》(又名《第三代》)和骆宾基的长篇小说《姜步畏家史》(又名《混沌》),也都在上下百年的历史视景和氛围中,在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土匪、东北人与来到东北的外国人、东北的关内移民和朝鲜移民等诸多社会形态和生活形象中,寻根般地展现了百年东北的形象和历史,具体而感性地描绘出东北的历史与现实交融的复杂多态、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风貌。其次,东北作家的作品还表现出描写内容和主题的时代性宏大与思想性浩大。由于东北社会本身的客观存在、由于受到左翼意识形态和文学思潮的影响,部分东北作家在这些对东北历史进行寻根与回忆的作品里,往往从“阶级压迫与抗争”的视角和图式去结构作品,凸现主题,去展现“九·一八”之前东北的社会形态、生活风貌和东北形象与历史的原生态。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和《憎恨》,萧军的《过去的年代》,梁山丁的《绿色的谷》等小说,在东北的大地山川的粗犷的背景上,描写和叙述地主与农民旷世迭代的疯狂压迫、尖锐对立、刻骨仇恨和烈火般的强悍复仇与反抗。这一主题和意识形态性话语是如此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以至于女作家萧红早期的小说《王阿嫂之死》,也在阶级压迫与对立的构图中描写东北的农村与妇女。不过,即便是表现这些流行的主题,东北地域的文化与生活内容本身的奇特性也赋予了它们以东北风格:以大地主家族为代表的“阶级”压迫往往带有野蛮性与残酷性,而农民的反抗则具有与大地山泽相应的原始性的强悍性与酷烈,带有家族和血亲复仇的色彩。因此,东北作家的这种叙事和描写,曾被认为与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俄罗斯的大平野和强悍的哥萨克,有相似之处。(11) 同时,也由于受到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作品和思想的影响,在部分东北作家描写的那些充满野蛮和疯狂性“原罪”的地主家族中,不时出现民粹主义的、忏悔贵族式的叛逆者和赎罪者的形象。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和山丁《绿色的谷》里,都出现了这样的力图弥补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的裂痕、甚至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年轻一代的地主形象。这样的地主形象及其行为,在30年代关内的左翼文学、或者以阶级压迫和斗争为主题模式的表现农村生活的文学里,是很少见到的,毋宁说,这也是东北作家和文学描画的东北社会与形象的特色之一。
如果说上述作品描写的土地、自然与阶级斗争等,因表现对象和内容的宏大与酷烈而带有雄壮和激情的特点,展现的是东北形象壮美传奇的一面,那么,在萧红的《呼兰河传》、骆宾基的《混沌》等作品里,则诗意盎然地描画了非激情状态的、日常世俗的、风俗画卷和乡土歌谣的东北形象。没有民族侵略与反抗、阶级压迫与斗争这类严酷和宏大的叙事,少有暴力与复仇的血腥场面,有的是日常生活的平凡、安稳、生老病死和岁月流转,是没有大波大澜只有小小风波和涟漪的人生之流。《呼兰河传》在浓浓的回忆性笔调中,以童年女孩的视角,委婉地描画了冬天的严寒冰雪、夏天的晚霞和家里的后花园火等自然景色,跳大神、唱秧歌、盂兰节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冥纸铺等民俗风情,老祖父、有二伯、小团圆媳妇、歪嘴冯磨倌等芸芸众生,以及由他们演出的生活的悲剧与喜剧,随岁月和四季流转的波澜不惊乃至单调灰暗的人生。萧红的呼兰河小城叙事,确如茅盾所说,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12) 也是历史的东北的部分社会人生的缩影。《混沌》同样具有这样的风土画和叙事诗的特点,它把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之前东北一个中、朝、俄三国交界的小城的社会与人生,描画得多姿多彩,在看似平凡和日常的生活内容的叙事中却暗涌着历史动荡与变迁的风云,具有文学化、叙事化的东北边陲史的图景。而端木蕻良的《初吻》和《早春》,则以自己的少年生活为原型,叙写了东北大地主家庭性意识初醒的少公子与贫寒少女的朦胧爱情,对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情与叹惋,虽然间或有一点“阶级”的痕迹,但在整体上却展现了往昔东北的另一番人生景象,特别是这种少年情的描写,配以鲜明的东北风物民情的渲染,《早春》还以萧红《呼兰河传》里的一句优美的叙述作为题记,显示出对风土画和恋乡歌谣的主动追求,从而使作品充满了浓浓的东北风味,为东北形象和历史画卷的描画增添了多彩的一笔。
当然,在这些叙事诗与风俗画般的东北叙事中,东北作家如萧红等人,出于启蒙主义的思想和创作追求,也如实地、痛心地展示了东北社会与人生落后、停滞乃至野蛮的一面,一种文明形态和社会进程中的非现代、前现代状貌。《呼兰河传》里那种现代文明的缺失,社会进步的缓慢,畸形的传统礼教的存在,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单调和贫困,不思进取与改变的苟安和普遍性的麻木,及其萧红早在《生死场》中就曾描写的自然与社会法则下的浑浑噩噩的奴隶状态,也是历史的东北的社会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完整全面的东北形象的描画和塑造而言,这样的东北书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有了这样的描写,东北的形象和风貌才是完整和立体的,才是“直立”起来的东北形象。
日本的作家和知识者对中国东北自然和风土的书写,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就已经开始,从那时起直到日本的昭和初期,包括正冈子规、森鸥外、夏目漱石、田山花袋、与谢野宽、西村真琴在内一批作家文人,以和歌、俳句、日记、歌集、游记等文体样式,吟咏或描述“满洲”(东北)的风土。
随着“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和开始对东北进行移民,在日本文人和开拓民中随之出现了所谓“开拓文学”,对东北的风土与生活进行了记述或描绘。其中报告文学作品有岛木健作的《满洲纪行》,德永直的《先遣队》,山田清三的《我的开拓手记》,菅野正人的《土地和战斗》,小说有打木村治的《制造光的人们》和《草席物语》,汤浅克卫的《先驱移民》和《青上衣》,和田傅的《年轻的土地》和《殉难》,荒木巍的《北满之花》和《百姓魂》,伊藤整的《呼吸》,林房雄的《大陆的花嫁》,田村泰次郎的《猛男》,钎田研一的《镜泊湖》,福田清人的《日轮兵舍》和《松花江》,等。诗歌有岛崎曙海的《地貌》,甲斐水棹子的《花灯》等。
非文学的纪实性、科学性的对东北的风土调查、考察和记述,也早在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对以大连为中心的南满的占领和殖民化,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有关方面就已经开始进行,风土考察和记述的著述陆续出现。但是,大量和集中地写作与发表有关东北风土考察的记述,却是“满洲事变”以后的事情,如满洲日报社编纂的《满洲风土记》(上中下),春山夫行的《满洲风物志》,千田万三的《满洲文化史点描》,田口稔的《满洲风土抄》、《满洲风土》、《地人庄记》,满洲铁道总局旅客课编纂的《满洲风物帖》,藤山一雄的《新满洲风土记》,金丸精哉的《满洲岁时记》,长与善郎的《满支近顷》、《满洲见学》等等。这些冠以“风土”的文本中,有一些是文学化的游记、随笔,更多的则是以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视野和方法进行的著述,或者在学术化的考察记述中穿插和夹杂着若干游记性文章,与中国的“风土记”大都是文学性散文的性质有所不同,属于学术散文或大文化散文。
文学性的“开拓文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日本移民的农业耕作和包括花嫁在内的日常生活,以及北满自然气候、风土景物的特异性。应该承认,就一般而言,日本民族特有的对自然万物精于细细观察与体味的“民族性”,使他们对东北自然景物风土岁时及其变化的描写,既全面广泛又细致入微,在以往的中国文学里还很少见到。而那些以考察、游记、印象记、民俗调查的姿态出现的有关“满洲风土”的纪实性或描述性的著述,也相当全面、细致乃至不乏一定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在这些风土记中,东北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物产、交通、教育、产业、语言、民俗、风土的方方面面,包括地方病的情况,无一不在被介绍、描述、研究和整理之列,有文字的解说陈述也有大量的图片和照片。说实话,我们中国人自己在此前和当时,还没有如此认真、全面、精细与生动的对东北风土的研究、整理和记述。
但是,不论日本人对东北自然景物的体味和描写如何深入精细,也不论他们的“风土记”调查和记述如何全面、深入与科学,他们的侵略者、占领者和殖民者的身份,使他们的东北风土描写和记述的目的,不是为了纯粹的知识和学问建构,而是为永远地霸占和殖民东北的“帝国”的根本任务和使命而服务的,由此,这些风土记述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帝国主义的、殖民的视野和逻辑,由这样的视野和逻辑,构成了一种摄取、记忆和书写的装置,通过这种装置而被描绘和记述的东北风土,以及东北的形象,表面上具有类似于田野调查的客观性、缜密性、全面性与科学性,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具有这样的因素,但是那种殖民和帝国的逻辑与隐含性话语,往往就包含在这种客观性、科学性的描述当中。
首先,不论是文学性描写还是纪实性描叙,都突出“满洲”的日常性和平和性,而刻意回避和遮掩民族侵略与压迫的尖锐问题,遮蔽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九·一八”事变,“满洲国”的建立,日本的统治和移民,都必然引发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东北抗联与日本殖民者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就是这种尖锐的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矛盾的集中和暴力形式的反映。可是,在日本的“开拓文学”中,反抗侵略与殖民的东北人民被污蔑为“匪贼”,民族的矛盾和斗争被“矮化”为新土地的开拓者、新社会和生活的建设者、新秩序的守护者对破坏性“匪贼”的驱逐与剿灭,由于东北历史上确实土匪众多且横行,这种“匪贼”的说辞和描述实际上进行了概念与内容的非逻辑性连接、混淆和并置,将抗击殖民压迫性质的人民和行为不动声色地进行了“妖魔化”处理。而且这样的“匪贼”描写也只是在开拓文学的初期存在,后来则基本不见和消失了。纪实性的风土记述里也偶尔提到东北历史上的“马贼”现象,但对现实中的“匪贼”现象则忽略和遮蔽,而且,在记述东北人民受到的祸患和压迫时,则往往提到张作霖父子和军阀这种本民族之内的“阶级压迫”现象,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忽略和遮蔽了现实中的民族压迫问题。或者是以所谓“五族协和”的“满洲国”建国精神置换和消解民族压迫问题,并把“五族协和”作为新的满洲“风土”现象。如果说,民族感情和道义责任使中国东北的作家更多地描写和强调了日本侵略东北带来的殖民性的民族压迫的苦难和反殖民压迫行为的壮烈等宏大叙事,而忽略了即使是在被占领和殖民的情况下,生活也有日常的平凡的一面,不全是悲痛啼哭的一面,尽管这日常和平凡不能脱离沦陷的整体环境和苦难性质;那么日本的东北风土叙述则遮蔽和压抑了民族压迫与反抗的矛盾性、尖锐性与现实性,着重在风景和风土描叙中流露出太平岁月的日常性、普通性与平和性,似乎殖民下的生活都是欣然的一面,或者在风土的调查、展示和叙述中将其“历史化”、“客观化”、“抽象化”和“风景化”,抽掉和抹去了风土民俗中的现实性气息。
其次,在那些开拓文学和“九·一八”以后出现于东北文坛的日本人的诗词歌赋中,对中国东北的风光景物、大地自然、风土民俗多有细致的考察和描写,特别是对于东北土地的辽阔、山河的壮丽和四季景物的变迁与特异,从来自国土狭小的岛国国民的心理视野,进行了充满赞叹、惊奇的描绘。而那些纪实性的风土文本,更对“满洲”大野之辽阔、历史之悠久、民俗与民族之多样、资源与出产之丰饶,进行了“客观性”调查与记述。但是,在这些风土描述里,透过表层的文字与图像,无一例外地存在或暗含着具有价值等级差序的叙述和描绘的主体与客体的结构性装置。在这样的装置的制动和作用下,那些风土作品和文本的作者、叙述者和调查者,是以来到和占领东北的殖民者的身份、意识或者潜意识,从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和视角出发,作为殖民地占领者、开拓者和优越性的“看者”,对被殖民的他者“满洲”进行俯视性的“看”——描写、考察与调查和纪实记述,都是这种广义的“看”,而“满洲”则成为充满新奇性、特异性、异国情调的被观看对象即被看者,这种看/被看的关系本身就是由现实中不平等的关系决定的,两者的地位和性质本身就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和具有差别性的地位。质言之,他们的殖民者的身份地位使他们成为优越性与“科学性”的俯看者和主体,而沦陷的被殖民的东北只能成为低等位的、失去自己话语权的被看者和客体。
由此出发,殖民者身份的“看者”所看到的广阔的土地与纷繁的风土民俗,一方面不乏真实与客观,一方面又带有殖民者与征服者的优越感所造成的“视景”特征,即在这样的视野中,满洲的自然与风土,显现出一种处女地的原始、洪荒和旷野的性质,一种史前性即历史的空白性。因而,在那些开拓文学的风景叙述的深层逻辑里,就包含着为日本的殖民主义的移民和开发制造和寻找历史与“自然”的合理性的因素:他们是在原始洪荒的、辽阔无际的、非中国特别是“汉族中国”所有的土地上创造新的生活和历史,是在进行征服性质的“探险”与发现,是在开拓新边疆和填补历史的空白,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行为当然不是侵略和殖民而是人类和世界历史上常见和共有的行为。而那些纪实性的风土描述,那些调查与游记,在科学与客观的名目下,自然不能无视东北历史与民族的悠久和丰富,于是在他们的描述里呈现出同样包含帝国和殖民逻辑的若干特征:一是强调和突出东北风土与原始和洪荒相联系的土著性、非中国性或者去中国化的“满洲性”,比如在对民族及其源流关系的叙述中,一方面详尽描述了东北历史上那些原住和土著民族的来龙去脉,意在说明或暗示这些民族和人民是这块土地的过去的主人,一方面在描述东北已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时强调他们的外来性、移民性和非土著性,有些作者在叙述汉族历史上从关内向东北的移民时,甚至用了“汉族的侵入”和“殖民”这样的词汇,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对南满的占领却是“进出”。固然有一些著述表面上以“五族协和”的所谓满洲国建国精神归纳满洲国民族关系的特点,但却强调日本民族在五族中的指导和领导使命。这样,过去的满洲的主体和主人是土著和原住民族,现在的指导者和领导者即主人是日本人,汉族在东北的历史和现实中被置于尴尬和另类的地位,如此的民族与风土的叙述里,东北的非中国化和去中国化的“满洲形象”就被“科学”地“客观”地制造和暗示出来。二是与这样的原始性和土著性相联系,东北历史与民族和民俗等风土尽管悠久多样,却也在日本人的风土调查和游记的深层话语逻辑中,具有了不被明说但却实际存在的文明形态上的“野蛮”性状。而他们这些调查者、记述者和“满洲”的看者,却是代表着高级文明形态的文明、先进的文明人,他们是在以文明人观察落后的价值态度和文明“自大”的目光,在考察和看视低级文明形态的“原始与野蛮”的“满洲风土”。这些“野蛮化”和“落后化”的“满洲”风土与民俗和文化,以自身的存在和状态反衬出日本的文明、先进和开拓满洲的合理化。殖民者的视野和“帝国逻辑”在这样的转折和叙述中成为这些“满洲风土”叙事的深层话语。这样的以科学和客观考察张目、在深层却暗含帝国和殖民逻辑的殖民地风土调查和描述,当然不是日本人的首创。在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时期,以科学考察和探险为名义的西方白人,在他们的猎奇日记、探险游记、调查报告和小说电影中,就是以具有殖民与现代双重性的文明和野蛮的对立性话语和目光,去看视和描述他们所看到的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亚洲的印度人与中国人及其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占领与压迫,被说成是推广上帝福音、推进现代文明和开拓新边疆。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为了抗击和赶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解放亚洲人民,建立和实现大东亚共荣,但是,在他们的“满洲”风土记中,如上所述,却同样包含和具有与西方帝国和殖民主义者相同的话语逻辑,那些被科学考察、精确调查、认真描述出来的“满洲”风土,与西方的发现者探险者和随之而来的殖民者眼光中的黑非洲和美洲一样,成为日本帝国和殖民视野中的“他者”与“风景”,一种与黑人、印地安人的文化和形象具有同一性质的“域外风景”。
当然,差别也是存在的。西方的探险者、调查者和殖民者在他们的海外冒险和风土记述中,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天然鸿沟,他们与他们看视的非文明的对象不存在任何历史与文化的联系。日本的这些“满洲”风土记,在描述、展示和暗示历史的“满洲”的非中国化与土著化的时候,也描述东北历史上的渤海国、高勾丽等政权与日本的交往和联系,为“日满”友好寻找历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也是为现实中日本的“进入”满洲的殖民行为制造历史的、法理的根据。但这样的“不掩饰”历史和寻找根据,却又“历史地”和“科学客观”地暴露出风土描述的殖民目的和逻辑,这恐怕是作者们所没有料到的。
与上述的在“客观”和“科学描述”中隐含帝国殖民的逻辑和话语相比,在某些风土记文本中,其殖民逻辑和话语则是明显公开和不加掩饰的。像《新满洲风土》、《最新满洲写真》和《满洲风土帖》等文本,竭力要描绘和塑造一个“新满洲国”的形象——所谓大东亚共荣追求下满洲的开拓、建设所形成的新的满洲风景与风土。在文字和图景里,农田的开垦、矿业的开发、铁路的铺设、资源的勘探、城市的建筑、乡村的劳作、街市的面貌、民众的生活,甚至日本移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村落,等等,都作为新风土而被呈现出来。但是,这些新的满洲风土景象,带有明显的、不打自招的殖民色彩,比如,伪满政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等日本殖民者的各种机构和建筑,是赤裸裸的殖民统治的权利表征,日本开拓民的生活场景和村庄,固然是“满洲新貌”,但尽人皆知这些开拓民是如何来到、为什么来到东北的,那些开拓民耕种的土地,确实辽阔而肥沃,但这些土地无一不是伪满政府和日本当局以低价强行购买而送给日本移民的,富饶的土地下面掩盖的是殖民的暴力和血腥,甚至那些照片上的开拓民的中国式房子,也是从中国农民手里强行征来的。还有作为风土新貌的“集团村落”,那图片上凝固而又宁静的景象,其实只有形式的真实,它的内在真实却是殖民统治和暴力压迫的野蛮与残酷:为了孤立和围剿东北抗日联军,隔断抗联与人民的联系,强迫农民离开原有的村庄、土地和房屋,住进这合并的集团村落——类似于集中营。不仅如此,在这些风土描绘的很多文本的前言后记里,甚至在对一些具体风土景象进行的叙述中,作者毫不讳言其风土考察、记述和描绘的目的,是出于实现日本天皇和国家“八纮一宇”的精神和建设大东亚共荣的“满洲基地”的目的——殖民逻辑的国家性和时代性表述。《满洲的见学》则公开地把“满洲”称作“日本的生命线”,而作为生命线的理由,是日本国土狭小,土地贫瘠,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相反,“满洲”面积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口不过日本的三分之一,因此,作为指导者的日本应该率领“满洲”人民建设新国家,以支持日本完成大东亚共荣的使命。但是,“满洲”既然是独立的新国家,那么它是否作为日本的生命线,应该由这个国家和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该由该作者所代表的日本来“先在”地决定,而作者却迫不及待地在叙述中提出了满洲的“生命线”地位和命运,如此自相矛盾的叙述透露出的,恰恰是直接的殖民逻辑和企图。《满洲风土》在记述“村落与都市”时,直接宣称“满洲国的出现给都市吹入了新的生命”,创造了新的都市风景与“成就”。也有的风土记的作者不这样直接,而是假借伪满洲国皇帝和政权的话语,以说明日满不仅在现实中亲善如一,连日本的天照大神也成为满洲的护国神灵,成为满洲宗教和风土的新内容。可是,不管如何“婉转”,这些风土记述的动机性和目的性说明与言辞,还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殖民帝国的意图与逻辑。
注释:
①⑤⑥⑦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2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周立波:《丰饶的一年间——1936年的小说创作》,《光明》第2卷第2号。
③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第20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④乔木:《八月的乡村》,《时事新报》,1936年2月25日。
⑧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的文章里也有类似的记述。
⑨黄伯昂(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转引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5辑。第153页。
⑩刘西渭(李健吾):《咀华二集·八月的乡村》。
(11)[美]葛浩文:《漫谈中国新文学》。
(12)茅盾:《呼兰河传·序》,《茅盾论创作》第3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科尔沁旗草原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端木蕻良论文; 呼兰河传论文; 生死场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东北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