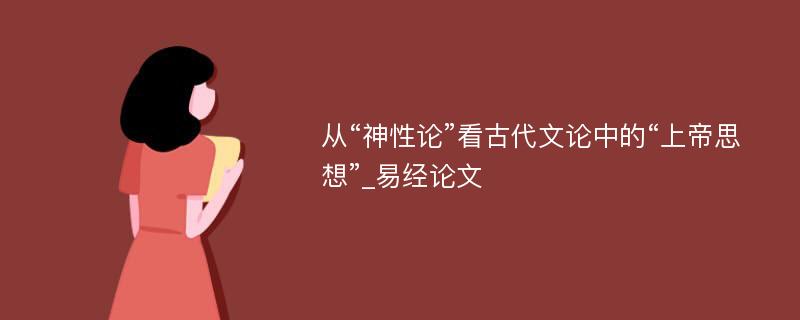
从“神感说”探讨古代文论的“神思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神思论文,古代论文,神感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溯自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起步之后,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已经从通史的梳理到范畴专题的开掘,日渐深入。然而,中国古代文论还有一块有待深入探索的天地,这就是其内在的精神意蕴与哲学理路。中国古代文论既是一种文学文论,更是一种哲学文论,古代中国人是从整个大文化的思路去创构文论体系的,其内在的精神意蕴与哲学理路,是文论灵魂之所在。深入寻绎与激活这种精神意蕴,是使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相融会的核心课题。《易传》中的“神感说”是可以与古代文论中的“神思说”相并列的一种从思维方式推演到文论领域的范畴。“神思说”明显地受到《易传》“神感说”与佛教“重神说”的浸润。本文试以《易传》中的“神感说”与古代文论“神思说”作为范例,对于其间存在的内在精神意蕴,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进一步弄清楚中国古代文论一些重要范畴的精神来源问题。
一
“神感说”是《周易》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它建立在万物一体,自然神妙,互相感应的原始思维的观念之上,大致指的是精神灵性的互相感应,体现在物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的互动上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它大约与当时中华文明的宗教习俗有关。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国古代文明中有一个重大的观念,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是‘天’和‘地’。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不相往来的。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1](P4)张先生认定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文明的说法尚有待研究,不过张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以沟通天地人不同层次为旨归,很能给我们看待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学说的特性以有益的启示。作为沟通的使者是巫觋,所谓“神”自然也就具有了灵感与直观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感说”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之上的一种关于思维方式的理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论与“神感说”有着直接的关系。《周易》中保留着十分清楚的中国远古时代筮占方式,透露出我们的祖先对于外部世界的体认与感受。生活在四季分明的黄河流域的先人,既对提供给自己生活资源的天地山河、万千生物有着亲切的感情,也对这些随时会给自己造成伤害的环境感到恐惧忧虑。诸种复杂的意念,通过梦境的折射,构成先民对于外界事物难以言说,只可冥感的神秘感受。这种感受中既有认识的成分,也有宗教的情绪;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审美的因素在内,种种成分,不一而足。这也是为什么《周易》中透露出来的智慧和诗性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具备博大精深、见仁见智的精神蕴涵。
中国古代思想史对于精神问题的看法,明显地与西方理性主义的价值观不同。它将精神现象与宇宙之气相联系,将精神视为整个天地自然所共有的产物,并不只是人类所专有的意识范畴。从生成论来看,人类本身也是天地万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意识当然也是天地所赋有的。即《周易》的《序卦传》中所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先有人类才有人类的精神意识,这是很简单的事实与道理,古人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了。对于人与自然所共有的精神现象的产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一般说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它视为精气或清气的凝聚与转化;另一种是将气与心志相提并论。后一种看法也没有否认心志与气的衍生关系。这类将精神问题泛宇宙化的观点也是古代希腊人与古代印度人所持有的看法。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精神无非是精气的产物,是从天地之气转化而来。从更深的人类精神发展史角度来说,人类早期总是将自我意识淹没在与宇宙同在的泛自然与泛精神的模式之中。这体现了人类早期思维的特点。老子与庄子的“物化说”就是建立在这种思维状态之上的。“物化说”的基点是否定意识与自然界的对立关系,主张回到无知无欲的原始混茫状态之中,重构精神与自然的同一性。这种将精神与自然置于一体化的思路,在《周易》中所凝结的中华民族思维的方式中,清楚地呈现出来。《周易》中解释易经的《易传》部分,大约是秦汉时期哲人对于《易经》中创作成因的探讨,从解释学的原理来说,既有对于元典文化的揭示,更有自我意识的激活,是当时人借阐发《易经》来宣示自己对于天道人事精神现象的看法的篇章。它明显地吸取了道家的天道观与儒家的社会观之精华,具备再造中华精神世界的恢宏气概。
《周易·系辞》在总结《周易》以筮占方式冥会与感受世界的特点时指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这段话气势不凡,它提出了这么几点意见用以解释《周易》中精神蕴涵的博大精深,用之不穷:首先它提出《易经》是圣人仰观天象,俯瞰地理,中观人事而悟出的不刊之道;其次,这种道不仅在于它的认知价值,更在于它是一种人类获取自由的精神境界,具有仁者之心的道德价值。如果说西方哲学家从康德到黑格尔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将自由与必然作为一对重要的范畴来探讨,前者是从人类学的解放高度来看待自由,后者是从唯理论的方面来解释自由,那么《易传》的作者在探讨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千古之迷的自由问题时,可以说是兼有二者。它既不将自由仅仅视为意志的产物,重视人类在认识必然的过程中获取自由,以趋利避害,亦不完全主张在必然性面前无所作为,一筹莫展,陷入宿命论的怪圈之中,而是力倡在无法逆料的变故与必然性面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意志,以趋利避害,张大精神意志的力量,克服老庄哲学中过分消极悲观的因素。《周易》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毅力去实践人生,体认自然,参天地,赞化育,显然这是儒家思想精华的升华。而《易传》中所提出的“神”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范畴。“神”既是对于变化莫测的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内在规律的描述,更是主观精神对于外部世界的自我体悟与参与,是主观精神与客观实在的统一。世界是实在的,并不是先天神怪的主宰。东晋哲学家韩康伯注曰:“夫变化之道,不为而自然,故知变化者,则知神之所为。”[2](P69)这实际上是用老庄的自然之道消解了殷周以鬼神左右人事的迷信思想。老子尝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后来佛学也常用“神理”来说明自然之道。在《文心雕龙》中,“神理”基本上指自然之道,与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融合。
然而,《周易》的作者又认为世界的本体又是有超验的一面,是可知与不可知的统一体,人们对它的感受不可能是一种理性式把握,更无法穷尽天地人之奥秘。就此而言,《周易》中的经与传部分都还残留着原始思维与宗教意识。从人类精神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周易·说卦》中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是《周易》中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也为后来的许多人所称引。在作者看来,所谓“神”是万物体现出来的造化神力,万物生成与运动,其根本的奥秘是不可穷诘、出神入化的,它非意识所能控引。这种超验至妙的精神境界,最易在自由无方的艺术精神中出现,因而往往引伸到工匠制作与文艺创作学说中。所谓“神”是指神妙无方的境致。从庄子学说到杜甫诗论的重神说,其哲学思想来源,是与《周易》的“神感说”相联系的。韩康伯注曰:“于此言神者,明八卦运动、变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则无物,妙万物而为言也。则雷疾风行,火炎水润,莫不自然相与为变化,故能万物既成也。”[2](P82)韩康伯的解说与王弼的解释《周易》,明显地有援用老庄与玄学的意味在内。庄子也常用“神”的概念来说明天地的变化莫测,神妙无迹。如《庄子·知北游》中云:“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昏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庄子认为,天地变化各得其所,这种自然之道表现在现象上则是“油然不形而神”。从认知上来说,人们可以感知其表面的神妙而难以穷尽其中底蕴。《周易·说卦》中所云:“神无方而易无体”,可谓说尽了世界的奥秘与神奇,也传达出人们对于它敬畏而感叹的复杂情感。既然“神”是超验与经验的统一,那么对它的体认也就不可能采用理性的方式,而必须另辟蹊径,神感则是一种接近于灵感的思维方式。
所谓“神感”是基于《周易》中感应论的一种思想。朱存明先生在《灵感受思维与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易·系辞》的神是有原始文化作为根基的,它不是与人同形的,却是有史前灵感观念的表现,它与古代灵气交感观是相类似的。”[3](P82)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感”(咸)在《周易》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周易·咸卦》云:“咸:亨,利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为《周易》下经之首,是作者从天地而推演人伦之义,故王弼注曰:“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在《周易》的作者认为,天地万物化生最根本的是来源于万物所感,感是阴阳二气的交感化生,在男女两性的交配中得到最典型的表现。作者认为从感应的角度可以说尽万物演化与生存的要义。而神感是指从一般的感应意义衍化而生的精神交感,万物的感应首先是内在精灵的共鸣互感,而不是外部现象的感应。这一思想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易学与佛学中,显现得尤其明显。《周易·系辞》提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韩康伯注曰:“明蓍、卦之用同神知也。蓍定数于始,於卦为来,卦成象于终,於蓍为往。往来之相成,犹神知也。”韩康伯提出了“神知”的概念,认为《周易》中用蓍卦来推断吉凶运变是一种特殊的领会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用神知的方式。而神知的方式,在主体来说就是感应,感应是主体用非理性的方式来对于世界冥感与直观,毫无疑问的是它保留有原始思维的成分,有时候亦可用灵感的概念来说明。
从主体的角度来说,为了把握这种神,则必然要通过虚静的心态来达到。故《周易·咸卦》的象辞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王弼注曰:“以虚受人,物乃感应。”对于“道”与“神”的感应,《易传》的作者与老庄的思路是一致的,这便是将至高的境致理解为不可言说、不可理知的精神实体,而只能通过虚静无待的心态去感受。虚静乃感受精神的心理前提。后来影响到刘勰的《文心雕龙》便是“陶均文思,贵在虚静”的理论。应当如何评价这些充满原始活力的思维学说呢?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我们也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少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4](P120—121)黑格尔从唯理论出发,忽视《周易》中蕴含的思维活力与巨大的精神张力。实际上神感论在保留人类精神的自由与活力方面,是唯理论所远远不及的。唯理论对于感性的过分轻视势必导致人类精神活力的衰退。因而西方自从19世纪末理性主义思潮消退之后,哲学家与思想家开始重新关注人类早期的原始思维问题,力图从中挖取有意义的东西。卡西尔在他的名著《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呼吁:“除了纯粹的认识功能以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去理解语言思维的功能、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功能,以及艺术直观的功能。”[5](P79)这些话语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周易》中“神感说”的精神意蕴。
《周易》将重神的观念人格化,具有了浓郁的审美自由的色彩。《周易》中《易传》的作者认为,《周易》是圣人观物取象以通神的结晶。《周易·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圣人智慧的结晶,而圣人本身则是这种智慧的人格化。《周易·系辞上传》:“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易传》认为圣人是《周易》中精神境界的体现。人们将那种伟大超凡的人物称为“圣人”,将艺术作品中的上品称为“圣品”、“神品”。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为“书圣”;唐代画家吴道子被称作为“画圣”。唐代书论家张怀最早将书法艺术分为“神”、“妙”、“能”三品,宋代画论家黄休复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又以“逸”品置于三品之上,表现了新的美学观念。
二
《周易》中的“神感说”中蕴含着丰富的思维方式,对于文艺理论在内的思想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西汉扬雄《法言》中重神的文艺思想显然受到它的影响。扬雄在《法言·序》中,提出自己写作《法言》中章节安排的缘由:“芒芒天道,昔在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神心惚恍,经纬万方,事系诸道、德、仁、义、礼,撰《问神》。”[6](P569)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知扬雄是将天道与神心相结合。在他看来,天道茫茫,幽微难测,不可以常理预见,而只能以神心来感应。以天道为本,以神心为用,是扬雄哲学思想的基本路数,推而广之,也是后来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的基本思路。神心是沟通天道与人事的桥梁。惟其如此,它在表现上就是一种灵感状态,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自由无待的,体认了这种精神境界的人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庄子所说的逍遥游境界,或者说是这二者的完美融合。在《问神》中,扬雄云:“或问‘神’。曰:‘心。’曰:‘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敢问潜心于圣。’曰:‘昔乎,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神在所潜而已矣。’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6](P137)扬雄认为所谓“神”是一种灵感性质的心智,是天地之心在人身上的转化与体现。扬雄所说的神虽然不同于古希腊柏拉图所说的神灵凭附,它不是一种神祗,而是宇宙精神在人身上的显现,是宇宙与吾心的映合,实际上是呼唤文明社会中人们被扼杀的灵感,激活人类自身与宇宙同在的精神张力。在这种多少带有几分原始神秘意味的身心一体的世界中,人们很容易将它与审美的激情与创造相融合。这就是从神感到文艺理论中的神思说为何一脉相承的原委。然而诚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所言,两汉的思想文化界由于被天人感应论所覆盖,对于《周易》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大多被所谓象数之学所笼罩,《易传》中的“神感说”说无法与文艺理论进一步相融合,更多地受到迷信观念的左右。这种状况,一直到了魏晋时代才随着思想的解放而有所改观。
《易传》中的“神感说”,经过魏晋时代王弼与韩康伯等玄学家的重新诠释,其中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蕴涵得到阐扬,成为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与日渐兴起的佛教思想相融合。佛教将《周易》中“神”的概念朝着实体化的方向发展,所谓实体化,也就是将“神”演变为超离现实世界,独立无待的精神,与人的肉身存在没有太多关系。由于精神的超然无际,感通万物,不生不灭,人类的精神其作用也就顺理成章具备了神而化之、沉冥玄照的功能。东晋佛学对《周易》中的“神感说”朝着宗教精神方面作了发挥。《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7](P132)据《世说新语》注引《东方朔传》所云,“铜山西崩,灵钟东应”,系指东方朔应答汉武帝时“以阴阳气类言之”来解释的一种感应现象。支道林显然对于两汉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是不赞成的,他解释《周易》的感应论是从精神感应的方面去发挥的,表现了魏晋新的哲学精神。当时玄学家与佛学家对于《易传》的神感说主要从精神的感通与神妙功能去说的。他们认为人的精神思维中具有一种超验的、不可知的功能,能够凭借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第六感官”式的直观去把握对象,与对象为一,体现出至神至妙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恰好与文艺创作与感受中的灵感现象相契合。因此,在六朝宗炳与刘勰等人的画论与文论中,得到重视与阐扬,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当时调和《易传》与佛教重神说思想关系的人物,首先是一些玄佛兼通的人物,如支道林、慧远等人。支道林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提出:“夫至人也,览通群妙,凝神玄冥,感通无方。建同德以接化,设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滞,演成规以启源。”“夫体道尽神者,不可诘之以言教,游虚蹈无者,不可求之于形器。是以至人一物,遂通而已。”[8](P60—61)支道林以《周易》的“神感说”去解释佛学,认为佛学中之精神亦体现在神秘的感通作用之上。
刘勰在他们的基础之上,踵事增华,有所创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说”,毫无疑问与兼融《易传》的“神感说”与佛教的精神论的方法相联系。刘勰在《原道》中谈到文学的本原时提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9](P2)刘勰认为文学来自于道心的彰显,而道心即神理,也就是精神实体。他力图融合《周易》“神感说”与佛教精神说的关系,认为文学是表现精神意蕴的最好的载体,因为在人的审美精神世界中,天地之心尽显其中。最幽微莫测的东西在文学活动中得到了激活与表现,也是从事人文教育的要径。故而他在《原道》最后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元圣,炳耀仁孝。”[9](P3)刘勰用《周易》来说明文学的本原问题,说明他是深契于文学的精神价值的。然而刘勰更重视用佛学的的精神论来看待文学创作的精神蕴涵问题。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胸襟,也体现在兼融《易传》“神感说”与佛教重神说的关系上面。刘勰的精神世界同他所信守的佛教精神直接相关,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佛学代表作《灭惑论》中可以见出。刘勰《灭惑论》曾比较佛法与道教的优劣:“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暗者恋其必终,诳以仙术,极于饵药。慧业始于观禅,禅练真识,故精妙泥洹可冀。药驻伪器,故精思而翻腾无期。若乃弃妙宝藏,遗智养身,据理寻之,其伪可知。假使形翻无际神暗,鸢飞戾天,宁免为乌?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学死之谈,岂析理哉?”[8](P323)这段话对于佛道境界的高低作了态度鲜明的褒贬,体现出刘勰行文时一贯的辞气严正的风格特点。在他看来,惟有精神是不生不灭,可以达到最高的人生胜景与智慧,它可以超越形质,远游天地。刘勰嘲笑世人常常为生死等肉体问题所困惑,看不到修练精神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这是甚为可惜的。刘勰的这段话很显然受到他的老师僧佑的思想影响。僧佑在《弘明集后序》中说:“论云:夫二谛差别,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观。俗教封滞,执一国以限心。心限一国,则耳目之外皆凝。等观三界,则神化之理常照。执凝以迷照,群生所以永沦者也。详检俗教,并宪章五经,所尊惟天,所法惟圣,然莫测天形,莫窥圣心。虽敬而信之,犹蒙蒙弗了。况乃佛尊于天,法妙于圣。化出域中,理绝系表。”[8](P292)僧佑从真谛、俗谛之区别论述了佛教精神的伟大,其特征是超越世俗、等观三界,而那些俗教执迷于一隅,导致精神永堕地狱,心有所限,则耳目塞滞,而等观三界,则神理常照。佛教所说的“照”,是指精神的作用,它摆脱了世俗的阻碍,故能圆照无偏。刘勰从他的老师那里继承了重神之说,以张扬文学精神,排击当时道教对于佛教的诘难。刘勰从宇宙间惟神为重的信仰出发,对待文学问题是从这一高度去立论的。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自序其心思:“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9](P725)这一大段话在赞扬孔子的话之前,可以说明刘勰是从很深的人生意义与人文关怀的高度去彰显文学界意义的,这同他在《原道》从天地人三才的高度去说明文学产生一样。“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这几句话同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写作《灭惑论》时大力阐扬精神作用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刘勰的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中,精神的意蕴汲取了《周易》的思想与佛教的思想,二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有时候简直很难判然相剖。关于此中之关系,值得另作深入的讨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最后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心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明显地说明了作者是融合了《周易》的“神感说”与佛教的重神说,用来统率传统的比兴论与声律论。在刘勰看来,文学创作最根本的乃是神用象通,心以理应的问题,即用精神感通世界,以心灵去融合神理的运思过程。比兴这些在先秦两汉诗学中重要的概念,在神思中乃是一种手法。《文心雕龙·神思》开章云:“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9](P493)文章一开始借用《庄子·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说明神思是一种身在此而心在彼的想象超升。不过刘勰之所以用神思,显然与他的受《周易》与佛学重神思想感情相关。他的神思并不是一般的想象,而是更接近神感的灵感活动。这就是强调凝神寂照的作用,是一种内游的功夫。“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这些关键词都说明他的神思与《灭惑论》中所说的“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有着直接的关系。“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两句话,说明精神在想象中的畅游无碍,是刘勰“神思说”的精髓。刘勰认为,思理最妙之处乃在于发挥精神的作用,与物界相游。这种用冥思去激活心理功能的思想,也是佛学的一个重要思想。东晋高僧慧远在《念佛三昧诗集序》中宣扬:“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6](P230)他认为精神智慧来自于神秘的凝想,这种神秘的凝想乃是精神发挥的关键所在,慧远强调“想寂”是鉴明内照,即内心冥感的功夫,精神的至妙正在于此,“鉴明则内照交映而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慧远赞美天下之至妙在于这种神思内照之中,是以心照物、内外相感的过程。当然,我们说刘勰采用了《周易》与佛学的精神之说来重新解释文学的想象活动,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文心雕龙》毕竟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它对于文学创作的现象与特殊性也是充分考虑到的,并没有先入为主地用既定的理论范式去削足适履。刘勰对于文学的情感与神思的关系有着很好的论述:“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9](P493—494)可见刘勰对于文学理论固有的特性是深有体会的。
从《文心雕龙·神思》自身的理论发展逻辑来说,直接受到西晋陆机《文赋》的影响,这一点是学界所基本认同的。《文赋》所探讨的问题集中在“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两个方面。前者是如何描写对象的问题,后者则是如何将构思中形成的意象传达出来的问题。陆机《文赋》的主旨明显地体现出太康文学的特点,当时文风注重的是意物相称,文以逮意,对于主体精神的弘扬则相对较弱。刘勰的“神思说”则提出“意授于思,言授于意”的公式,呈现出“思”——“意”——“言”的次序,陆机《文赋》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则显然是“意”——“言”——“物”的公式,相对而言,刘勰强调了“思”的功能。刘勰的“神思说”并非忽视外界事物对于创作缘起的作用,为此他专门写有《物色》一篇,讨论外物与人的感应作用。但是刘勰更重视精神的能动作用,主张“意”必须受“思”的统率,“思”只有在“神”的支配下才能发挥其神妙的功能。为此刘勰提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神理为妙,神与物游”,从而张扬了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刘勰的“神思说”与陆机相比,更强调文学创作是一种幽缈难识的精神活动,变化无端,因而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
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9](P495)这一观点,显然是建立在将文学创作视为心灵活动的观念之上的,是对于所谓“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的具体诠释。在他看来,“文心”其实乃是精神的运用,深契于文心的人,必定关注精神对于文学创作的潜在作用。刘勰这段话用了庄子论精神之道的话来说明文学精神的幽妙不可言说,是充满《周易》中所“神无体而易无方”的精神活动。总之,以刘勰为代表作家的“神思说”,受到《周易》的“神感说”与佛教的重神说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由此可见,深入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理路与精神价值,搞清楚其中的微妙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更为重要,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课题。
标签:易经论文; 易传论文; 文心雕龙·神思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文化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读书论文; 刘勰论文; 原道论文; 国学论文; 佛学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