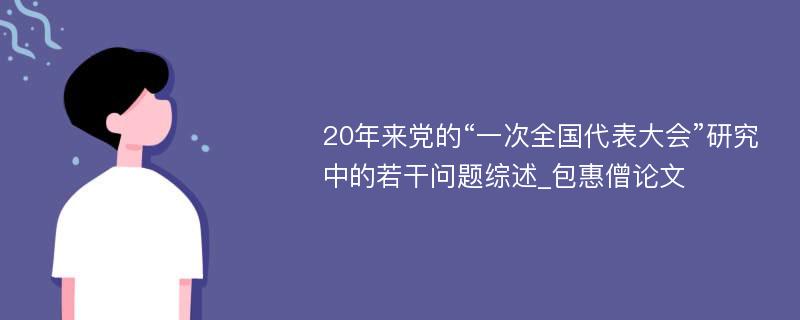
近二十年来中共“一大”研究若干问题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大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中共论文,近二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近二十年来党史工作者就“一大”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现将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关于“一大”召开日期及党的诞生纪念日问题
对于“一大”何时召开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
(一)“一大”于7月23日召开。这一观点主要由邵维正教授提出,其依据有三点:一是基于对“一大”代表行踪的分析,根据大量材料考证,在所有与会的13人中,7月1日到上海的代表只有3人,余者均是7月14日以后至7月下旬之间到达。“一大”是全体代表到齐后才召开的,这说明“一大”在7月下旬召开的可能性最大。二是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记载,一大于7月23日开幕。三是借助“一大”代表的回忆,“一大”在上海开了6天,中间休会两天起草文件,合计8天。根据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美琴被杀案,查上海《新闻报》、《申报》,此案发生于7月31日,由此可推知最后一次会议为7月30日,从30日起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1)。)
(二)“一大”于7月24日召开。提出这一观点学者的依据有二点,一是依据陈公博在“一大”期间的行程。陈公博于7月23日乘英国邮轮到达上海,由于他要安排食宿以及向张国焘、李达汇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与陈独秀的情况,因此,从日程安排上看他不可能于7月23日当天参加大会,根据材料“一大”第一次会议是全体代表参加的,由此认为“一大”的召开日期为7月24日。二是依据“一大”会议日程的合理安排。通过对一些史料的考证,从对会议进程即汇报交流阶段、体会阶段、讨论阶段的时间分配,推断出“一大”于7月24日召开。(注:《“一大”开幕日期再考证》,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6);《“一大”7月24日开幕补证》,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7)。)
既然党的“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怎么把7月1日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呢?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于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的报告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6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通知,决定7月1日至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建立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七一”采取多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这是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指示。从此,7月1日就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确定下来,因而党的诞生纪念日并非“一大”召开日期。(注:《党的诞生纪念日与“一大”的召开日期》,载《红旗》,1981(3)。)
二、关于“一大”闭幕时间问题
“一大”于何日闭幕,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存有较大分歧,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7月31日闭幕。此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几位一大代表的回忆。1971年董必武回忆,会议中断后第2天(7月31日),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1979年刘仁静回忆出事后第2天(7月31日),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1953年包惠僧回忆,出事当天晚(7月30),他曾与李达、张国焘、周佛海等人商议决定明天(即7月31日)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们到了火车站……,约十时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注:《中共一大研究综述》,载《益阳师专学报》,1991(2)。)由此得出“一大”闭幕于7月31日。
(二)8月1日闭幕。此观点的主要依据也是几位“一大”与会者的回忆。董必武1929年回忆,会议中断后的次日(即7月31日),因商讨更改会址和布置有关事情,没有开会,再隔一日(8月1日),始赴南湖继续开会,大会闭幕。张国焘、陈公博的回忆也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还对7月31日闭幕说进行商榷,指出从7月30日会议结束的时间,代表居住分散的状况,7月31日几位代表的行踪等因素看,7月31日举行闭幕会议是不可能的。(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举行于八月一日考》,载《绍兴师专学报》,1984(2)。)
(三)8月2日闭幕。此观点的依据有二点,一是根据“一大”的筹备组织者,“一大”上海代表之一的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回忆。她回忆说7月30日会议因法国巡捕干扰而中断,7月31日李汉俊、李达、张国焘碰头后决定8月2日到嘉兴南湖开会,此事由王会悟具体安排,作为当事人王会悟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二是从当时党的机关刊物所登载的文章来看,“一大”的闭幕日期应8月2日。陈公博在《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说,他在“一大”会议中断后的第二天(7月31日),来到李达住处,李达告诉他“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他遂于7月31日夜乘车赴杭州。由此可知陈公博在7月31日尚未接到何时复会的通知,因而大会不可能于8月1日闭幕。他在文中还说,他在杭州玩了两三天回到上海后,周佛海告诉他“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开过,会议至此结束”。由此可推知“一大”闭幕日期不可能早于8月1日,也不迟于8月3日,而是8月2日。(注:《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是八月二日》,载《教学与研究》,1986(3)。)
(四)8月5日闭幕。此观点的依据有四点,第一,原始文字资料明确记载着“一大”闭幕日期是8月5日。前苏联《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上公布了《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信件》。其中明确写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斯穆尔斯基的信件写于1921年11月3日,距“一大”闭幕仅仅66天,是关于“一大”闭幕日期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可信的。第二,达林回忆“一大”会期为1921年7月到8月,至少说明会议是8月闭幕的,从而印证了斯穆尔斯基信件的可靠性。第三,陈公博的“一大”会期两周说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一大”于8月5日闭幕。陈公博1924年回忆说“一大”持续了两周,如果按准确开幕时间7月23日算起,持续两周,正好是8月5日闭幕。第四,前苏联学者认为我党“一大”于8月5日闭幕,前苏联《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曾发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注:《党的“一大”闭幕日期考》,载《近代史研究》,1987(2)。)
此外苏东海根据“一大”期间嘉兴南湖气象资料分析出“一大”的闭幕日期应为8月5日。他指出:根据1921年8月8日《申报》地方通讯专栏所载,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遭狂风巨灾,南湖游船吹覆四五艘,溺毙游客3人,狂风持续1小时许。另年1921年8月4日《申报》本埠新闻栏载,此次风灾对嘉兴车站破坏亦很厉害,直至3日晚仍未恢复正常。此由可认为:一、“一大”代表回忆中并未提及风灾,可见会议进行时未遇风灾,因此,8月1日闭幕说不能成立。二、8月2日风灾刚过,正在善后,王会悟租船不可能不闻此事,能否租到船亦成问题,风灾过后满目灾情,与会者的回忆皆未提及此事,8月2日闭幕说也难成立,因此8月5日闭幕之说是可信时。(注:《中共“一大”闭幕日期外证一则》,载《党史研究资料》,1986(10)。)
三、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
包惠僧出席了“一大”,这一点学术界已无争议,至于他是否为会议正式代表,尚存分歧,这一分歧也涉及了“一大”正式代表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包惠僧虽然出席了“一大”,但却不是会议正式代表。其主要依据有两点,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有两名代表。”包惠僧不是湖北代表(湖北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广州(陈公博)、日本(周佛海)各有一名代表参加,这样就排除了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第二,“一大”与会者的回忆。李达在1957年3月18日《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信》中指出:“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会议的代表。”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大”代表是12人,他列举了全体代表的名单,其中并无包惠僧。刘仁静在回忆“一大”的情况时说:“第一次党代会人数是12人,包惠僧不是代表。”(注:《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考辨》,载《争鸣》,1982(3)。)
第二种观点认为包惠僧是“一大”正式代表。持此观点的学者也引用了一些“一大”代表的回忆来证明包惠僧是“一大”代表。1936年陈潭秋回忆说:“……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国共分裂后投降了国民党……”。1929年董必武在给何叔衡的信中写道:“广州代表陈公博(早已投降)包惠僧(1927年脱党)……”,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在回忆中都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其次,坚持包惠僧为“一大”代表的学者指出,不能因为包惠僧不是广东代表也不是湖北代表而否认他“一大”代表的资格,因为在党的筹建以及初建时期,党的组织并不健全,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可能都有完备的手续,从包惠僧参加“一大”前在党内的身份(1920年6月筹建湖北共产党临时支部并任支部书记,1921年1月到上海参加临时中央工作)以及在“一大”上的表现(在“一大”讨论会中积极发言,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来看,包惠僧不仅具备了参加“一大”的资格,也起到了正式代表的作用,因此包惠僧是“一大”正式代表。(注:《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考辨》,载《争鸣》,1982(3)。)
四、关于“三月代表会议”问题
对于“一大”前是否召开过“三月会议”,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一大”前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这是一次清除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会议,是一次制定党的目标、原则和策略的会议,从思想、政治、组织上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作了准备。“三月代表会议”存在的依据是张太雷在1921年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原稿题为《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这一报告明确地提出1921年3月党召开了代表会议,同时他们还引用了董必武与瞿秋白的回忆来旁证“三月代表会议”的存在。(注:《中共“一大”前曾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4)。)
第二观点认为“一大”前没有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张太雷在1921年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有关表述,并非指中共在1921年3月已召开过代表会议,而是指他个人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一次代表会议,以便解决共产主义者还未形成统一组织,还与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共事而产生的不利于共产主义运动开展的状态。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有必要在此时召开一次代表会议与实际上召开了会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他们还指出,在1921年3、4月间中共正在积极筹备“一大”,不可能抽出时间召开会议。(注:《“一大”前中共没有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4)。)
第三种观点认为“三月代表会议”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一大”的筹备会议,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次改组会议,涉及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张太雷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身份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不过是苏联方面的临时安排,因此张太雷的报告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为主要背景。张太雷在报告中列举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与“一大”前夕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实际地点不符,而与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点正相吻合。同时大量资料述及1921年3月前后上海地区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激烈斗争,证明了张太雷所云“三月代表会议”的主题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会,而非中共“一大”的筹备会议。(注:《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问题的辨证》,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4)。)
五、关于共产国际与“一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与“一大”召开前后,共产国际起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
首先,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予了正确的理论指导。1920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着重讨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要求东方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解决本国的问题。大会制定的纲领实际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解决了建党最重要的制订党纲和使党建立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问题。
其次,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一大”的召开。共产国际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派代表来华,广泛接触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干部,建立共产党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宣告成立。
最后,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明确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从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民主革命纲领。
在充分肯定共产国际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帮助和作用只是外部条件,只能加速或延缓党的创建过程,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也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的必然定律。(注:《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作用》,载《江西大学学报》,1983(4)。)
六、关于党纲研究问题
目前还没有找到“一大”上通过的中共党纲的中文本,能够看到的只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一大”党纲的理论渊源于《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以及俄共党纲,因为“一大”党纲中的“党的名称”、“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入党条件”与上述文件及纲领中的规定有很大相似之处。(注:《中共一大党纲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5)。)在“一大”上,对党纲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党在当前的工作是以研究教育为主还是以革命运动为主。李汉俊、李达、陈公博等代表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中国尚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刘仁静、张国焘则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贡献,很明显党纲肯定了后者的意见。(2)中共是否需要联合其他政党。李汉俊认为中共应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而包惠僧则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党纲对联合其他政党采取了否定态度。(3)党员可不可以在政府里做官。一种意见认为党员应参加国会和政府,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采取共同行动。另一种意见则反对党员参加政府和国会,认为党员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经过讨论,党纲中规定: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和国会委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注:《中共一大党纲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5)。)
“一大”党纲中有两项组织规章没有详细订立,一是地方委员会的章程,一是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定。这两项规章只是明确了组成人员的设置,至于产生的办法,管辖的范围及权限,每届的任期都没有提及。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党纲作了补充,完成了这两项任务。
由此可见,在理论上“一大”党纲是以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性质很明确,起点很高。在实践中,“一大”党纲的制定经历了长期的摸索,是在集中全国各地以及国外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后形成的。它的内容既有中国特色,又与近代中国其他政党的纲领有本质的区别。(注:《中共一大党纲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5)。)
七、相关问题研究
(一)会址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只把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和南湖游船看作“一大”会址。近年来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一大”在上海举行了8天,除最后一次会议指明在李书城家举行外,其余几次会议均在博文女校举行,其依据是陈谭秋与张国焘的回忆,因此博文女校也应是“一大”会址的一部分。(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若干史实新证》,载《武陵学刊》,1997(5)。)
(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历史作用问题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最早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一大”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北京、武汉、济南、广州、长沙远至于国外的日本、欧洲等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下实现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担负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翻译、出版、发行了大量的书刊,对于提高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认识水平,统一建党思想,加强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系,都起了重要作用。三是以《新青年》为阵地,进行了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提高了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四是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外语学社,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输送干部。五是积极筹备,为“一大”召开做了充分的组织工作、文件准备工作和物质准备工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注:《纪念建党七十九周年全国党史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5)。)
(三)“南陈北李”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
1、对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由于公务繁忙无法出席大会,其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的回忆。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广东做教育厅长。”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注:《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载《齐鲁学刊》,1991(4)。)
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出席“一大”是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现象有意见。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应该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成立大会。然而马林并未这样做,而是在没有征得陈独秀同意情况下召开“一大”,出于此种原因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注:《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载《齐鲁学刊》,1991(4)。)
2、对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1921年6、7月间李大钊要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故未能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出席“一大”。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张国焘、陈公博等人,张国焘回忆说:“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注:《李大钊未曾出席“一大”原因考》,载《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1(2)。)
第三种观点认为李大钊“一大”期间正在北京领导一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因而无法出席“一大”。“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无理断绝支付教育经费和教员薪金,使北京的大中学学校教育陷于无法维持教员生活的地步。为抗议这一无理决定,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联合罢教,李大钊积极投身于这一斗争,并成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经过长达4个月的斗争,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发还拖欠的教员薪金。由于领导这一斗争,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注:《李大钊未曾出席“一大”原因考》,载《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1(2)。)
标签:包惠僧论文; 陈公博论文; 陈独秀论文; 中共一大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张国焘论文; 申报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