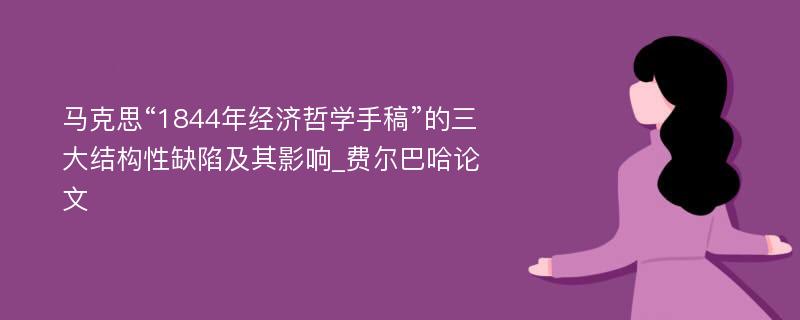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三处结构性断裂及其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手稿论文,结构性论文,三处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 8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1)10-0008-0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自1927年首次问世以来,关于它的研究文献早已是汗牛充栋,但是根据笔者的浅见,如果从叙事学的角度来划分,也不过三种模式:平面叙事、后设叙事和发生学叙事。平面叙事是研究者直接面对文本,厘清本文篇章构成并辨析文思理路与涵义,这方面的文献俯拾皆是,著名的有尼·伊·拉宾的“《1844年手稿》对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和哲学论证”(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亚·沙夫的“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等等;后设叙事指研究者从马克思成熟期著作反注《手稿》中的思想并对文本话语重新进行取舍和编结,以便使前后期思想保持一致,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有卢卡奇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简论”(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刘永佶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方法论》(注:刘永佶:《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方法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尤见第175页、第186页。),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注: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以下。)等等;发生学叙事通过揭示马克思手稿概念的意义转向的踪迹和思路的断裂,“移情”式地追溯马克思理论探索的艰辛历程,这方面的文献所见不多,像马尔库塞的“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和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注: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源起性语境”的口号并明确反对“用后来发表的论著来简单地评判手稿的非科学惯性思路”。(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就属此类。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有些作品不止一种叙事模式,但只要我们细加考究,一定会发现其中总有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每一种叙事模式都提供一种解释学的视域,马克思使用的同一个范畴、同一个表述在不同的视域里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解释学景观。举例来说,下面这一问题——在《手稿》的最后马克思为什么突然转向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经过每一种叙事语境的多重折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截然相异的答案。平面叙事者简单直观地罗列“事实”、平铺直叙地逐一注解,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提出这一问题;后设叙事者常常给我们提供一些貌似正确的大道理:埃·博蒂热利就认为,马克思已经“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和“唯物主义一边”,已“成为真正战胜黑格尔哲学的人”,为了“把对黑格尔思想的分析的成果固定下来”,“理所当然”要对黑格尔进行彻底的批判(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国内有些学者也认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是为了“从黑格尔哲学中拯救出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变为唯物主义哲学”(注: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发生学叙事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景观?据笔者陋见,无论国外国内,从这一思路出发的研究文献极少(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但只有这种叙事模式才能使我们有机会贴近马克思的真实思路并有可能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是如何“在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本文就是这样一种尝试,抛砖以期引玉。
一
断裂是意味深长的休止符。马克思《手稿》中先后出现了三次这样的休止符。
断裂Ⅰ:在[第一手稿]的结尾有一处显而易见的中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马克思在考察了非工人同工人的三方面关系之后写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可是他突然打住,没有了下文。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写在第27页上。根据张一兵先生的文献考证(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这一页上只有两行文字,后面留下的是9页半的空白!很明显,这里的中断并非手稿的遗失所致。我们只能这样解释:马克思本来打算继续往下分析并且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但这种分析无法深入下去!我们只要认真揣摩一下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讨论非工人同工人的关系的“第三”个方面时(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已类似于同义反复了。我们知道,任何还原和分析,到了同义反复这一步,已是走到尽头。
断裂Ⅱ:[第二手稿]在第43页“敌对性的相互对立”处戛然而止(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这里会不会发生手稿遗失呢?第二手稿共有43页,可保持下来的只有4页,遗失了39页。但从马克思所标的罗马数字页码来看,遗失的应是前面的39页(从第Ⅰ页到第ⅩⅩⅩⅨ页)。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此处的话语逻辑,以资进一步的佐证: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统一、对立、自身对立三个方面探讨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接下来准备分析劳动和资本在自身中是如何“敌对性”地彼此对立的,也就是说,在[第三]项中考察资本自身与利息之间以及劳动自身与工资之间的敌对性关系。让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考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资本自身与利息的关系纯粹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的事情,而劳动自身与工资的敌对关系又让我们回到了[第二]项,这实际上是在重复第一手稿结属处的分析,即回到断裂Ⅰ。这样的辩证分析不仅是同义反复,甚至已经变成一场概念的游戏!按照这条思路走下去是不会产生任何新的理论收获的。因此,从行文的内在逻辑看,马克思是无法接着往下说了——实际上,从马克思后来的任何文本中我们都没有看到由此处的未尽分析所产生的新的关于劳动自身与工资之间关系的洞见和成果。
断裂Ⅲ:这是一个隐性裂口。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给自己提出了“两个任务”(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第一个任务在“补入(1)”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非工人同外化劳动的关系,——正如在“断裂1”中所看到的,这一思路受阻并被迫中断;2)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第二手稿]以及[第三手稿]中的[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小节和[需要、生产和分工]小节对此作了探讨,但在获得一些成果后中断(参见“断裂2”的说明);3)真正人的财产是什么,——[第三手稿]中的[共产主义]小节对此作了一些初步的回答。
第二个任务是“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综观三个手稿,这第二个任务只见提出不见回答(注:虽然[第二手稿]遗失很多页码,但据现有资料来看,这一手稿所讨论的主要是“私有财产的关系”,这一问题仍属于“第一个任务”。)。我想,由于第一个任务中的三分之二还没有完成,马克思当然无法写下“补入(2)”这几个字。
实际上,除了上述三处中断之外,还有几个隐性裂口。因无关本文宏旨,故从略。
二
任何一个文本,如果发生了逻辑上的中断,不外乎有三种原因:部分文本丢失;作者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或不愿继续;作者思路阻滞。马克思的《手稿》虽遗失很多页码,但都不在上述中断之处;上述三处中断所涉及的都是马克思当时思考中的焦点问题,马克思轻易绝不会放弃他的“进一步考察”。因此,我以为,马克思行文到这三处时思路的中断属于被动性停滞。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思想家,马克思明确地觉察到自己运思的困境。马克思并不惧怕这种困境,他肯定意识到在自己身上徘徊着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两个巨大阴影,招之即来,挥之不去。他批判时讲着费尔巴哈的话语,他思考时遵循着黑格尔的逻辑。他同时也知道运思困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因为理论运思中的任何困难都像一束阳光照出费尔巴哈或黑格尔理论的隐蔽的缺陷。异化理论是一个令马克思自己也充满“喜悦之情”(注: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的思想创新,他自信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然而事实上呢?当他运用“这些论述”去考察非工人同工人的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需要、生产和分工等等这些理论前件时,他的“喜悦”便变成不能深入下去(“进一步”)的痛苦。马克思是敏锐的,他立即(注:根据张一兵先生的“第三笔记本原初文本结构示意图”(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可知,第1-Ⅺ页所谈的内容或者是补入第二笔记本,或者是与第二笔记本属于同一主题,也就是上迷的“第一个任务”;从Ⅺ页起,马克思开始讨论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如果忽略与[第二手稿]相关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第三手稿]的一开始便“立即”展开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反思。)展开对自己身上的阴影——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反思,他断定问题多半出在黑格尔身上,但随着反思和批判的深入,他看到了他意料之外的景观。
首先我们来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请注意它属于[第三手稿]的结尾部分)以及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专门谈到费尔巴哈并列举了他的“伟大功绩”。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极为有限:他含蓄地批评了费尔巴哈误解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理论,没有能够在扬弃它的神秘性之后抽绎出它的积极的、批判性的方面,把否定理解为运动、活动和过程。在马克思的显意识里,这是他与费尔巴哈的唯一区别,所以他称自己是“费尔巴哈主义者”,我以为并不过份。
下面我们来看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节中集中精力专门对付黑格尔:1.指出黑格尔《现象学》的“双重错误”以及它的“伟大之处”;2.批判性地逐项反思《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3.努力寻找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积极因素。这一节的内容大致如此,但有两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追问:马克思为什么要在[第三手稿]一开始就展开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哲学内容庞杂,为什么偏偏选中上述三个方面?如前所述,平面叙事无力提出这些问题,后设叙事则是先把此时的马克思提升至成熟期的水平,然后宣称马克思自觉地(先知先觉地)批判黑格尔。这是一种典型的把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抹平后作一种同质的、反历史的叙述的结果,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证明马克思的天才和伟大。现在我们把问题放在发生学描述的视域中,问题的答案会呈现出崭新的可能性。
三
历来的《手稿》研究者只是一味地高度评价[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节,虽然,有的学者目前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注:例如,张一兵先生曾问道:“马克思为什么在《1844年手稿》的最后会突然想到批判黑格尔?”(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但罕有人从发生学叙事的角度探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话语内容,并联系《手稿》的深层逻辑机制加以阐发以最终揭示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关于黑格尔的这一小节的主要内容。第一,对黑格尔的《现象学》“双重错误”的揭示以及对《现象学》的“伟大之处”的赞扬和扬弃,并不是本节的要点和“本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页。),毋宁说,马克思在此处仍然在重复他此前的思想;第二,马克思接下来逐项考察了《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他考察了哪些内容呢?马克思从八个方面“全面”总结了《现象学》对克服意识对象所持的观点和思路。沿着这个视角,我们立即发现,原来马克思真正关心的是黑格尔如何描述“克服意识的对象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页。)、“意识的对象的克服”与马克思此时正殚精竭虑的“异化劳动”的扬弃在内在逻辑运演上何其相似乃尔!第三,马克思明确提出,“要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考察一下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页。)。在马克思的考察中我们依然能碰到一些重复的话语,但我们也遭遇到马克思在黑格尔批判中的新发现:“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的必然结果;……从而达到了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了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7页。)。马克思把“特定概念”、“固定的思维形式”和“自然界”视为黑格尔逻辑学中积极东西的关键概念,这与“异化这个规定”有关系?为什么马克思不惜笔墨反复谈到“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对理解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至关重要。然而查遍《手稿》研究文献,大都对此避而不谈,少数文献认为它表明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批判黑格尔的异化观点及其思辨唯心主义基础(注:参见:N·C·纳尔斯基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47页。)。
在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有一点需要澄清,马克思绝不是在对黑格尔进行学术研究,以便把学术成果“向‘学术’界吐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7-248页。)。他的研究目标只在于“自己弄清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8页。)、“便于理解和论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页。)。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此处的反复陈辞与自己正在深思的问题密切相关。他要弄清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四
断裂Ⅰ、Ⅱ和Ⅲ所标志的思路阻塞使刚刚获得的“喜悦之情”烟消云散,他陷入了沉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一定出在黑格尔身上!马克思带着挑剔的目光重新审阅黑格尔《现象学》的最后一章:“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他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他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但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不从属于他的本质并且凌驾于其上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页。)是的,只是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换成“人”,一切都是“十分自然”而合理的。那么症结何在呢?症结恰恰就在这里!把“自我意识”换成有生命的存在物、换成“人”并没有摆脱思辨唯心主义!自我意识所设定的物性根本不具有现实性和独立性,这一点很好理解,但如果你据此反向推理,认为设定物性并使之具有现实性和独立性的是人、是主体,那你就错了,而且比黑格尔错得更远!这种设定不是主体,而是主体性!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说白了,人、主体的一切活动并不是一种从自己出发的“纯粹的活动”,它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具有客观性、对象性和被动性。
人和主体是异化理论的骨骼,既然人和主体的内涵已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那就必须重新审视异化理论。我们发现,这种审视集中体现在“感性”这一范畴上。感性、感觉既是费尔巴哈“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的基石,也是异化之所以为异化的真正的参照系(注:马尔库塞也持同样的观点:“‘感性’成了创立理论的中心”。(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经过批判性的思考,“感性”范畴不知不觉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辩证地看,“感性”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主体性和客体性。此处的主体性指人的主动的活动、人对人的产品的感性的拥有,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客体性即被动性和受动性,是人作为自然物受制于自己的物质需要的方面。此前马克思虽然也提到人的受动性,但主要是从主体性角度来讨论“感性”。他认为,人同世界的一切的感性方面都应该直接地、无障碍地、现实地得到,否则就是不人道的、异化的。他在[共产主义]一节中还特别从主体方面谈到了人的感觉性的事实和发展,这一理论视角为异化劳动学说、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关系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背景。但由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现象学》时有了新的决定性的发现,这时他开始转而关注感性的受动性方面。他虽然也谈到感性的主体性(天赋、才能和欲望),但主体性和客体性在他的思想中的比重对比已经发生了颠倒,他甚至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但这时马克思是不是回到了费尔巴哈的立场?乍一看,似乎是这样。费尔巴哈在1842年就已指出,“一种哲学,如果不包含被动的原则……就是一种绝对片面的哲学。”(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0页。)马克思高出费尔巴哈的地方在于他从黑尔格辩证法中提炼出来的否定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把历史看作一条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长河。将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应用于从主体出发的感性,在[共产主义]一节的末尾便得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必然的环节”;将这种辩证法应用于从客体性和受到性出发的感性,一种新的景观便展现出来:费尔巴哈认为“直观提供出与存在直接同一的实体”(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马克思对此有更为深刻的洞见:“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就是说,即使在直观上,人与自然界也不是直接同一的“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7页。)——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实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进展!马克思运用否定的辩证法,立即得出新的结论:“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直到这一小段结束时马克思对这一新的发现还念念不忘:“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回过来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感性”范畴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前后的转变是不是他自觉地完成的呢?我认为,这种转变是马克思自觉探索的不自觉的结果。马克思挖掘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受动性、受制约性之后,迅速地滑向他前面的惯性思路中去:这一切(不管是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事物,还是作为肉体的人本身)其实都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只是在进一步讨论非存在物(Unwesen)时才重新确认了受动性的地位和意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与其说是在批判黑格尔,不如说是在与黑格尔进行对话,诚如马克思所言,目的在于“理解和论证”。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就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对黑格尔的“自然界”那么感兴趣了。马克思在此当然不是要显示一下唯物主义(甚至辩证唯物主义!)的高明之处,他要通过批判性的对话解决自己的困惑:既然人在内外两个方面都是受动的,而自然界与人的需要即使在直观上也并不天然地一致,那么人是如何从自然界中超拔出来呢?人的历史是如何展开的?关于自然界,黑格尔有许多抽象的议论,有的极为荒谬。马克思在对黑格尔作出层层剥离之后,发现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概念——“外在性”:自然界的外在性意味着“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页。)。自然界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要正是自然界的缺陷!马克思的困惑与黑格尔的论述在此产生共振!黑格尔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呢?马克思不惜工夫抄下了黑格尔的“冗长”表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181页。)。马克思终于从中发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在概念、观念、精神中自然界扬弃自身。这一发现的意义要到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会向我们清晰地显现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前后,“感性”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给马克思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和思考的出发点。马尔库塞对此也似有所悟(尽管他给出的理由是错误的):“也许正是在感性(作为对象化)这个概念上……马克思完成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决定性转变。”(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319页。)
“感性”内涵的变化为马克思开创新的理论道路提供了既不同于黑格尔又区别于费尔巴哈的可能性,它的效应很快就开始发挥了。没有对人的对象性和感性的确认,就不会有《神圣家族》中人的“实物本质”的提出,而“实物本质”,——按列宁的理解,离生产关系只有一步之遥;没有对精神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反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不可能提出感性的“能动”性问题,而能动性对“实践”观的建构是极为关键的;没有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受动性的强调,就不会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的肯定,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的起点!承认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只要想一想他在《手稿》中的抗议——当一个对象仅仅作为“吃、喝、穿、住等等”而对我们存在时就是一种愚蠢和片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我们就会惊叹于他在理论上又走了多远!
当然,本文并不想无限地抬高“感性”内涵的转变在马克思“第二次转变”中的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马克思“第二次转变”的完成是他亲自参加革命实践、独立思考、扬弃资产阶级文化成果特别是经济学成果等等方面立体作用的产物。本文想强调的是,马克思对“感性”问题的思考正是这个“立体作用”的一个重要层面,尽管它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但发生学叙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使之敞亮的窗口。
这个窗口呈现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全知全能、先知先觉的马克思,而是一个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在黑暗中不懈地进行理论探索的马克思。他勇敢地面对理论中的断裂和困境,从几无道路的绝境中开辟出一条前无古人的蹊径,尽管这条蹊径此时还为丛林所覆盖、被迷雾所笼罩。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经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哲学家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