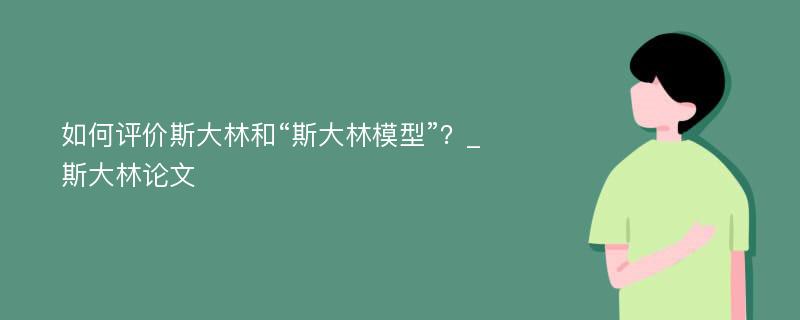
怎样评价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评价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
最近,我从《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卷首读到一篇文章《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署名高放,见复印件)。我反复看了几遍,照此文作者说来,斯大林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过程中,只有错误,甚至罪行,没有功绩,遑论建树。我总觉得这样评价历史,特别是评价旷古没有先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似欠公允。这不仅是对于斯大林个人的评价问题,而且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遭遇挫折的功过是非与历史认识问题。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此类言论当前多如牛毛,对于像我这样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其影响不容低估。我对你们有一个恳切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吁请在这方面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写点专题文章,为我们释疑解惑。如蒙俯允,当不胜感激。
专此谨致
崇高的敬礼!
晚辈 欧阳凡
复信
欧阳凡同志:
《中华魂》编辑部转我的来信及附件均已读悉,我想就着你所提的话题,着重谈谈怎样评价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问题。
诚如来信所说,近来,有关斯大林问题的讨论又热闹起来。在俄罗斯,不仅学术界在讨论斯大林的功过是非,而且连总统、总理也参加了进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议论纷纷。应该说,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有关斯大林问题的议论就没有停息过。斯大林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了,至今仍成为政治界、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俄罗斯人关心它,自不用说了,中国某些人热心议论这个问题,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突然对外国问题感兴趣了,而是因为: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从背后的深层次的缘由来说,直接关系到我们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他们想通过彻底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缘由,有的人是公开说出来了,有的则不肯说出来,但实质就是如此。所以,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政治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他只是提出了一些设想,初步进行了一些实践。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久,他就病重不能视事,并于1924年去世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和实施的。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把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下来。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尽管苏联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仍沿袭了斯大林创立的模式,即1936年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与斯大林分不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国家基本上照搬了斯大林创立的模式。我国解放初期,在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情况下,主要也是学习苏联的经验。1956年毛泽东指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发端的。但他仍坚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仍与斯大林创立的模式是一致的。所以,对斯大林以及他创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不仅关系到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非对错的判断,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重大的政治问题。
正因为如何评价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关系到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马克思主义灵还是不灵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原则是非,所以,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以及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两次大规模的反斯大林浪潮
斯大林去世以后,在苏联国内以及国际范围内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反斯大林浪潮。1956年,斯大林刚刚去世不久,赫鲁晓夫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抛出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从“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尺”。过去,赫鲁晓夫曾经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 “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亲”,过了十多年时间,还是同一个赫鲁晓夫,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 “伊凡雷帝式的暴君”、 “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一切恶毒、污秽的语言都倾泻到斯大林的头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是众所周知的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诬蔑和攻击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波匈事件,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三分之一的党员退党。一时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在戈尔巴乔夫的带领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大反斯大林的恶浪。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内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与社会上的所谓“民主派”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把攻击斯大林作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他们不仅把对斯大林个人的攻击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无中生有的彻头彻尾的造谣手段都使出来了,例如说斯大林是沙俄的特务之类,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了赫鲁晓夫衣钵、自命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宣布:“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失败。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并由此提出应该“彻底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戈尔巴乔夫之流要求“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划清界限”,进而把建立与“斯大林模式”相对立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即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与赫鲁晓夫相比较,戈尔巴乔夫终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斯大林的恶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其后果也更为严重。正是在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口号下,苏联和东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迅速遭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犹如雪崩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被推翻。
对于国内外出现反斯大林的浪潮。斯大林本人早就有所预见,他在1934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历史的风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
当反斯大林的浪潮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一阵把扔在斯大林坟头上的垃圾刮走的清新之风,开始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刮起,而且有越刮越大的趋势。
到了21世纪初,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果显现出来了:经济持续下滑、人民生活下降、政局动荡不安、社会治安恶化。随着国力的衰落,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原来使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超级大国沦落为被西方瞧不起的二等,甚至三等国家,这是俄罗斯人民难以容忍的。俄罗斯人民开始反思了。正如资深政论家齐普科教授在《我们怎样认识斯大林》一文中指出的,“今天俄罗斯……试图重新评价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做法,遭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广大人民的反对。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指出:“从1987年至2000年13年来,俄罗斯历史科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历史科学的很多方面被破坏了,被颠倒了。”许多人要求重新评价历史,恢复被颠倒的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相。2002年什·姆·蒙恰耶夫和弗·姆·乌斯季诺夫在其撰写的《苏维埃国家史》中写道:“历经了多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今天终于合乎规律地在千百万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不能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于是,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热潮。形成这股热潮,并不是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连续出现的纪念日”多(有关的纪念日年年都有或者隔几年就有),也不是因为“人们的记忆往往是记住好的,忘记坏的”,“人们的习俗也往往是对逝者多说好话,少说坏话”(过去一、二十年间有的人恰恰是忘记“好的”、只记得“坏的”,对逝者没有“多说好话”,尽说“坏话”),而是因为严酷的历史事实教育了广大人民:不能忘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能听任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摆布。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面貌,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呼声。俄罗斯教育部决定按照1945年原样再版发行斯大林亲自修改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指定作为高等院校历史教学用书,同时封杀某些肆意歪曲苏联历史的书籍,就是一个典型表现。
然而如何对待斯大林问题,国际国内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评价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一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完全否定斯大林、 “斯大林模式”,甚至认为否定得越彻底越好。遗憾的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后一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占上风。在学术界, “斯大林”、“斯大林模式”成了一个贬义词,只要是斯大林说的话、做的事,都是错的,无须论证,也许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党对斯大林问题的基本观点
谈到斯大林问题,我们不能不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斯大林问题的基本观点。大家知道,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抛出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报告不仅震动了苏联人民,而且震动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队伍涣散,而帝国主义势力乘机兴风作浪,发动凶猛的进攻。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毛泽东主持下,撰写了两篇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全面阐述了我们党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顺便说一下,过了40年,在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的形势下,我们党重申《一论》、《再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指出:历史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
《一论》、 《再论》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错误,指出: “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的确,斯大林的错误给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社会主义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时,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功绩和错误。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他的错误和他的功绩相比,只属于第二位的地位。毛泽东明确指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一论》、 《再论》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斯大林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同意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的账上,也不同意说都是斯大林个性粗暴造成的。
随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深入,1963年9月,我们党又写了一篇专门评论斯大林一生功过是非的文章: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篇文章坚持《一论》、 《再论》的基本观点,逐点批驳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据参与撰写这篇文章的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二评》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多,而且文章开头的这样一段话是他亲自写的:“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定论。”(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第646页)现在看来,不仅20世纪,而且进入21世纪,仍然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分歧更大了。
吴冷西对《二评》有一个中肯的评价: “《二评》真凭实据,把赫鲁晓夫驳得淋漓尽致,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第650页)我们在讨论斯大林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这篇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政论佳作。”
《二评》在尖锐地批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态度的同时,对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基本评价。《二评》在回顾列宁逝世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之后,得出结论: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确定并贯彻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基本上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了巨大的援助。这些功绩,不容抹杀。
斯大林作为一个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家,在他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确实犯过一些错误。《二评》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分析,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这些错误,既有社会历史根源,也有思想认识根源。《二评》指出,“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重要的不是罗列这些错误,而是应该科学地分析其原因,从中吸取历史教训,引以为戒,以免重犯或者少犯错误。
《二评》对斯大林的一生作出了总的评价,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一生功过得失得出的结论。
现在,《两论》发表已经50多年了,离开《二评》的发表也已经40多年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深化,我们需要对斯大林的功过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但贯穿《两论》、 《二评》分析斯大林问题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基本结论,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仍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斯大林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分析斯大林问题的几个方法论原则
我们认为,在分析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问题时,必须把握以下方法论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列宁全集》第1卷第181页)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而是对实际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我们评价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必须把握斯大林一生的言论和行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详细占有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决不能为了某种既定结论的需要,剪裁材料,甚至随意地捏造材料。
敌对势力攻击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经常采取的就是这种手法。这一点,在肃反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了。为了煽动群众反对苏维埃政权,敌对势力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随意夸大被镇压的人数,渲染恐怖气氛。这种手法在政治动乱中屡见不鲜。他们对肃反扩大化冤死的人数是一变再变,每变一次数目就激增一次。从200多万到2000多万,再到4000多万,迄今为止最高数字出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书中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4500万到5000万人(有时又说有6000万人)。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谎言捡了起来,叫做“五千万冤魂”。这个码加得也太离谱了,因为在30年代初,苏联人口才1.6亿,怎么能杀了5000万人呢?
究竟30年代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可以从苏联肃反遭到镇压的总人数中得到一点概念。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在1921年至1954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判处25年以下劳改和监禁的2,369,220人,判处流放和驱逐出境的765,180人。(《参考资料》,1992年1月27日)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应得,多少是错判的,该报告没有分析。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缅采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进行复查,最后确定,从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为3,853,90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827,995人。(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班子里》,第5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想来,雅科夫列夫是不会有意缩小这一数字的。
我们并不否认苏联在肃反运动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应该总结他们的教训。但是故意捏造材料来否定苏联的政治制度,这种手法是错误的,甚至是可耻的。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国内仍有一些学者不从实际出发,不仔细考证资料,随意引用一些资料,肆意夸大肃反遭到镇压的人数,渲染恐怖气氛,进而否定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如果不是学术上的粗漏,那就是别有用心。
——全面分析,既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分清主流、支流。
为了正确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不能援引一些具体材料(更不用说捏造的材料了)就做出结论,而必须把握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事实。列宁曾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事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有一个方法,即看他接任时国家是什么状况,而他离任时国家又是什么状况。在斯大林接任苏共主要领导人时,苏联是一个极其落后的、遭受外国欺凌的国家,到他逝世时,苏联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令帝国主义畏惧的超级大国。根据这一事实,就足以对斯大林及其“模式”做出基本评价。
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带着偏见去观察,事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寻找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而对不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视而不见。列宁曾经说过: “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列举点事例并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要全面地考察,把反映事物本质的基础性综合材料作为判断的根据。例如,经常有人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把它作为否定“斯大林模式”的依据。其实,如果全面地考察苏联经济,应当说两句话: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存在很多问题。简单地说“没有搞好”,并不符合实际。1913年苏联疆域内的工业总产值只占美国的6.9%,到1985年已达到美国的80%,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且苏联是在其国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环境下取得这一成就的。我们不否认苏联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诸如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粗放式经营,经济效益不高;产品花色品种少,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等等。应该总结其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些问题相对于经济成就来说,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不能抓住这些问题就得出苏联经济没有搞好这种结论。如果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历史地分析,即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
这就是说,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例如,有人谴责计划经济体制,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断言苏联就是因为搞了计划经济才垮台的。然而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用不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定。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于是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
苏联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些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月革命的普遍道路,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另一类制度是具体制度,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些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苏联人民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类制度是在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这些具体制度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条件下是对的,但不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去;更多的情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却必须进行改革。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苏联模式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它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只要搞社会主义,就应该坚持,抛弃了就不叫社会主义了;有关具体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则是有对有错,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对于具体的体制和机制,我们不能照搬,而应该把它作为借鉴,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做的。
顺便说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在基本制度层面上,两者是一致的,都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都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搞的都是社会主义;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面上,由于两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不同,两者显然有很大区别,因而形成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层面上,“斯大林模式”的确存在很多弊病,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把“斯大林模式”视为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现实。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建立起来的。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结合苏联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索。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人进行嘲笑、谴责乃至攻击,这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必须看到,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从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 “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等,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试问,在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一无成就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总结这一教训,我们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轻言“失败”,不要轻易否定。
我的信就写到这里,但愿对你思考这个问题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顺致
同志的敬礼!
你未曾谋面的老年朋友
辛程
标签:斯大林论文; 赫鲁晓夫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