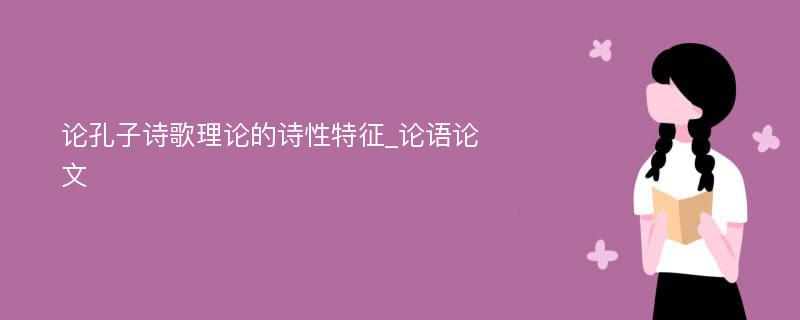
《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特色论文,诗论论文,论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博简《孔子诗论》(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著作。这些特色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它之前,人们普遍采用断章取义的方法说《诗》。《孔子诗论》在说《诗》方法上筚簬褴褛,勇于探索,虽然方法尚未成熟,但实现了全面的开拓与创新。作者高举孔子旗帜,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诗》学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尤其是作者吸取思孟学派的性情学说,给《诗》学论著注入了丰富的哲学内涵,打下了清晰的时代烙印。它论诗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不像汉儒那样以史说诗。由于这些因素,《孔子诗论》既不同于此前的说《诗》材料,也与汉以后的《诗》学著作有明显的区别。
一、处于过渡形态的说《诗》方法
先秦人士说《诗》大抵采用断章取义方法,说《诗》者往往根据自己需要,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所取的意义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定,听者也要根据特定的情境去感悟。人们把《诗》看成“义之府”(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大夫赵衰之语。)亦即一个思想库,熟读《诗三百》,就可以随时在政治外交场合从这个思想库里取来诗句,作为传达某种志意的媒介和工具,也可以在游说、著述时引《诗》作为论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严格地说,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学研究,因为它还没有将《诗》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充其量只能是前《诗》学状态。
《孔子诗论》在说《诗》方法上实现了根本转变,它第一次将《诗》作为独立的专门研究对象,不是借《诗》来说明政治、外交、礼义和学术观点,不再把《诗》看作传达志意的媒介或工具。以《孔子诗论》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但《孔子诗论》毕竟处于草创阶段,在说《诗》方法上并没有达到成熟水平,而是呈现出一种过渡形态:一方面它抛弃了此前断章取义的说《诗》方法,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形成统一的稳定的说《诗》方式。在29简1006字的竹书中,作者采用了多种论诗形式:或作题解式的评论,或以一字提炼作品主题,或借孔子之口发表对作品的主观评价,或综括四类诗大旨,或概括诗歌性质。多形式的运用,使这部竹书看起来颇似后代的杂感或随笔。
直接概括诗旨并加以发挥,这是《孔子诗论》中最值得注意的论《诗》方式,因为它已经接近汉代的《诗序》。如第八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第九简:“《天保》,其得禄蔑疆矣!赞寡德故也。”这些诗旨概括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堪称《诗序》的雏形。其它像《清庙》、《十月》、《小旻》、《祈父》、《黄鸟》、《菁菁者莪》、《关雎》、《甘棠》、《葛覃》、《将仲子》、《木瓜》、《将大车》、《鹿鸣》、《有兔》、《蓼莪》、《隰有苌楚》、《蟋蟀》、《墙有茨》等作品,《孔子诗论》中都有简要的主题概括。
《孔子诗论》有时用一个字来概括某一首作品主题,如第十简:“《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动而皆贤于其初者也。”作者一口气点了7篇作品,都是用一个字概括诗旨,而这个字下得很准。如《邶风·绿衣》是诗人抒发对亡妻(或出妻?)的思念之情,他穿上故人亲手为他缝制的绿衣黄裳,不禁睹物思人,悲从中来。《孔子诗论》用一个“思”来概括诗旨,尤为贴切。其它像“《邶·柏舟》,闷。”“《谷风》,忑”(第二十六简),也都是用一个字对诗旨进行概括。
《孔子诗论》有时借孔子之口,发表“吾”对作品的看法。如第二十一简:“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第二十二简:“《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变,以御乱’,吾喜之。《鸤鸠》曰:‘其义一氏,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这是通过“吾”对作品的态度而间接地点明诗旨。如《鸤鸠》,“吾’之所以“信”诗中的淑人君子,就因为他“其义(仪)一氏(兮),心如结也”。《鸤鸠》歌颂贞一的主旨就是通过“吾信之”而体现的。
《孔子诗论》第一次对《诗经》中《邦风(国风)》、《少夏(小雅)》、《大夏(大雅)》、《讼(颂)》的大旨作了概括。第三简说:“《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这是说《邦风》包容了各种事物,从风诗中可以普遍地观察民情风俗,风诗的语言富有文采,乐声非常动听。同简论述了《少·夏》的题旨:“多言难而悁怼者也,衰矣少矣。”这是说《少夏》多歌咏人生苦难,抒发诗人的怨愤情绪,反映政治衰败,叹息为政者少德。“难而悁怼”是对诗人而言,“衰”和“少”则是指时政。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正因为王道衰败统治者少德,所以诗人才遭受种种人生苦难并因此怨刺上政。《孔子诗论》对《大雅》的总体评价是:“《大夏》,盛德也。”(第三简)意谓《大夏》的主题是歌颂王公大人的盛德。《孔子诗论》第二简概括了《颂》的主题:“《讼》,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篪,其思深而远,至矣。”第五简又说:“又成功者何如?曰:《讼》是也。”综括这两简的意思,是说《颂》歌颂文武平成天下之德,它们多出于文武后人之手,多写成功者的业绩。《颂》的音乐安和缓慢,其乐曲多用壎篪相和。歌颂王德是《大雅》和《颂》的共同主题,所不同的是《大雅》歌颂的是王公大人施德政于民的这一面,而《颂》则是商周王后人祭祀祖宗神的郊庙歌辞,它一方面歌颂祖宗神的盛德,另一方面又要将王朝在现实政治中的成功告诉给祖宗神。
《孔子诗论》论述了诗歌性质,第一简说:“诗无离志,乐无离情,文无离言。”这是说诗离不开志意,乐离不开情感,文离不开语言。
《孔子诗论》虽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稳固的说《诗》方法,但它的大胆开拓却具有开启意义。《诗论》中的解题文字和对诗歌性质的概括,是汉代《诗序》的先声。《孔子诗论》对四类诗大旨的概括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表明作者开始从总体上把握《诗三百》,《孔子诗论》事实上已经勾勒了中国第一个《诗》学体系的雏形。汉初《鲁诗》就是在吸取《孔子诗论》观点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提出以四类诗始篇题旨来概括该类诗的主题,即以《关雎》的主题概括《国风》的主题,以《鹿鸣》的主题概括《小雅》的主题,以《文王》的主题概括《大雅》的主题,以《清庙》的主题概括《颂》诗的主题,由此而形成著名的“四始说”。(注:《鲁诗》的“四始说”见于《史记·孔子世家》。由于《鲁诗》亡佚,后人多不了解“四始说”的内涵。拙作《论四始》(载台北《孔孟月刊》第三十九卷第五期)有全面的阐述。)后来《毛诗》更在《鲁诗》“四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构建了一个始于《关雎》的《诗》学体系。
二、高举孔子大旗
高举孔子旗帜,继承孔子《诗》学思想,是《孔子诗论》又一个显著特色。
《孔子诗论》中五次出现“孔子曰”,这是整理者马承源先生将其命名为《孔子诗论》的根本理由。但这部竹书不一定是孔子本人所作。李学勤先生指出:“《诗论》非出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他认为《诗论》的作者是子夏。(注: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收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4页。)江林昌先生亦持同样的观点。(注:江林昌《上博竹简〈孔子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第4-15页。)郑杰文先生将《孔子诗论》与先秦其它古籍的引《诗》资料作了比较,证明《孔子诗论》的作者不是孔子。(注:郑杰文《上博筒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第4-13页。)联系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典籍来看,《易传》、《孝经》、《礼记》、《大戴礼记》中都有不少“子曰”“夫子曰”“孔子曰”,可见运用“子曰”发表学术观点,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著述乐于使用的一种常见形式。这些“子曰”,有些是孔门弟子和再传弟子辗转相传的孔子言论,但更多的是儒家后学借孔子之口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这用庄子学派的术语来说,就是“重言”,亦即借重之言,目的在于加重论述的份量,扩大学术影响。用今天的术语说,就是要借孔子之名来谋求话语权。不仅儒家如此,就是在战国诸子百家著作中,也普遍存在后学以宗师名义发表学术观点的现象。在战国时代,只要你归于某一学派的旗帜之下,你就有责任和义务按照宗师思想和文风,去宣传、演绎、发展宗师的学说,而门人、弟子、后学在从事著述的时候,一般不会留下自己的名字,有资格署名的只有宗师——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风气。《孔子诗论》的作者是一位儒家后学,他当然要遵循时代的游戏规则。
《孔子诗论》并没有停留在借用孔子名义之上,将《论语》与《孔子诗论》对读就可以发现,《孔子诗论》吸纳了孔子关于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礼乐教化思想在上古时代就已经萌芽,西周以“文”著称,礼乐教化是西周重要的治国方略。孔子以继承西周礼乐文化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宣传诗乐教化思想。《论语,阳货》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是儒家以诗乐教化方法治民的最早记载,子游此举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教弟子学《诗》,是孔子讲学中的重要内容,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启示弟子,应该在学《诗》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伦理道德水平,培养合于礼义规范的人格品质。他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注:《论语·泰伯》。),“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注:《论语·阳货》。),他与子夏、子贡之徒论《诗》,以及南容三复白圭,他便将自己的侄女嫁给南容的故事(注:《论语·先进》。),都具体生动地体现了诗乐教化的精神。《孔子诗论》的著述宗旨就是要贯彻教化精神,从具体作品阐释中揭示《诗》的教化价值,为儒家心向往之的礼乐教化夯实基础。对此下文还要讨论。
孔子兴观群怨思想也被《孔子诗论》所吸收。兴是“感发志意”(注:《论语正义》,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第375页。)。像《论语·八佾》载子夏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悟出礼仪形式是在仁义伦理情感之后,就是感发志意的典型例子。《孔子诗论》中没有“兴”字,但这不等于它没有“兴”的思想。竹书往往征引《诗三百》篇名和篇中名句加以评价。例如:“‘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也。”(第六简)这是一种感兴式的评点,它是受孔子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观点的影响。说得更明确一些,它是孔子关于“兴”的思想的一种实践,就是将孔子“《诗》可以兴”的思想落实到论《诗》之中。之所以征引《诗》中的名句,是因为这些名句特别能够打动《孔子诗论》作者的心灵,能够激发作者的联想、想象、理解、同情,由此产生政治、伦理或艺术等方面的感兴。孔子关于《诗》“可以观”的思想也被《孔子诗论》所接受,第二简说从《邦风》中可以“溥观人俗”,就是说从风诗中可以普遍地观察民情风俗。孔子所说的“群”,是指群体交流学《诗》心得,共同提高思想素养。《孔子诗论》第四简说:“贱民而逸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已。民之有罴惓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贱民”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生活贫困、劳作疲倦、上下不和各方面的困扰,他们是如何从激愤、轻薄、妒忌的心态而走向平和,如何做到身“贱”而心“逸”?如何达到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水平?《邦风》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因此,《邦风》是对“贱民”群体进行教化的理想教材。孔子的怨诗思想也被《孔子诗论》所接受。作者认为《少夏(小雅)》就是歌咏人生苦难,抒发诗人的怨愤情绪。在评论《十月》、《小弁》、《巧言》、《祈父》、《节南山》、《雨无正》、《邶风·柏舟》、《北风》等诗作时,作者继续阐发了怨刺思想。
当然,以作者锐意创新的理论品格,他不可能亦步亦趋地祖述《论语》。例如,孔子受时代风气影响而教弟子学《诗》以出使应对,由于战国已无赋《诗》言志之风,所以《孔于诗论》中没有出使应对的内容。孔子论《诗》还无法避免断章取义的时代局限,而《孔子诗论》则直探诗旨。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
三、显著的时代特色
《孔子诗论》吸收战国中后期思孟学派的性情理论,高扬诗歌性情的价值,突出圣人之性的意义,主张以礼义规范性情,带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性”字在中国出现甚早,《尚书·召诰》有“节性”之说,《诗经·大雅·卷阿》中有“俾尔弥尔性”的诗句,这些“性”都是指生命中所蕴藏的欲望,并无多少哲学内涵。从《论语》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很少谈性,《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阳货》载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论语》所载孔子讨论性的唯一材料,从这条语录推测,孔子认为人性在出生之初彼此相近,但是后来人们的习染环境相距太远。孔子关注的是“仁”和“礼”,他以毕生的精力来培养社会成员的仁心,以重建理想的礼制秩序。至战国中期,随着诸子百家探讨平治天下理论的深入,从人性角度切入来研究如何治人,就成为时代的学术热点。儒家关注的焦点是人性教化,《礼记·中庸》、《大学》、《乐记》、《荆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孟子》等典籍对此都有深入的探讨(当然各家观点并不完全相同)。《孔子诗论》就是受到这一股哲学思潮的影响。此次与《孔子诗论》一同面世的还有一部竹书《性情论》,内容与《荆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略有出入。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诗论》“涉及性、情、德、命之说,可与同出《性情论》(郭店简《性自命出》)等相联系”(注: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收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孔子诗论》吸收《性情论》崇尚真性情的思想,高扬《诗三百》中性情的价值,伸张“民性”的合理性。《性情论》认为由性情出于天命,因而提出“君子美其情”的命题。《孔子诗论》接过性情的旗帜,作为论《诗》的理论武器。第一简所说的“诗无离志,乐无离情,文无离言”,从字面上看这些提法与《尚书·尧典》“诗言志”之说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联系全书就可以知道,作者是以抒情言志作为全书的立论前提,为下文肯定诗歌性情确立依据。在具体讨论作品的时候,作者反复指出,这是出于诗人的性情,是“民性固然”。如第十六简:“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第二十简:“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第二十四简:“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在29支竹简中,就先后三次出现“民性固然”,这绝不是作者由于疏忽而造成语意重复,而是有意识地张扬性情。作者所说的“民性”,就是《性情论》所说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性”。作者所说的“固然”,是说这些性情出自人们生命的本原,它天生就应该是这样!
《孔子诗论》还吸纳了《中庸》“诚”的思想,突出了圣人之性的意义。《孔子诗论》第七简:“‘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已,得乎?此命也。’”“怀尔明德”语出《大雅·皇矣》,“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出自《大雅·大明》。歌颂文王之德,赞美文王受命,这些都是西周初年就有的观念,《孔子诗论》的新意在于用“诚”作为文王之德(即圣人之性)的内涵。“诚”的概念见于《礼记·中庸》(注:《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思作《中庸》。”《孔子诗论》作于战国中后期,它的作者完全可以读到《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注:《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46页。)文王的“明德”是出于天性,是属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那种性,此种性就叫“诚”。《中庸》又说:“大德者必受命。”既然上天赋予文王以明德,那么按照“大德者必受命”这一原则,文王命中注定要受命为王,即使他不想干,也是逃不脱的。
《孔子诗论》与《性情论》一样,最后的旨归是人性教化。《性情论》所要解决的是“心亡正志”问题。作者认为,天命赋予人性,而性有赖于心,心又没有预定的方向,它要等待“物”“悦”“习”等因素的诱导才能“取之”,因此教化至关重要。第四简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有了“教”,“心”就有了“正志”,就有了正确的伦理方向。《孔子诗论》就是运用这一教化思想论《诗》。作者虽然充分肯定诗歌表现性情的合理性,但他同时又认为诗乐所表现的性情不能没有规范,而必须将诗乐的性情纳入礼义轨道。以作者评《关雎》为例:《孔子诗论》第十简:“《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一简:“《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第十二简:“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第十四简:“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总括这几简的意思,是说《关雎》男主人公从开始“寤寐求之”“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到后来欲以琴瑟钟鼓之礼迎娶淑女,心性从情爱“改”到礼仪之上,这就是将性爱纳入礼义的轨道。用《毛诗序》的话说,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孔子诗论》就是通过这些具体诗作的评价,来贯彻人性教化的思想精神。思孟学派的性情理论给《孔子诗论》注入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是此前和此后《诗》学著作中所没有的,它只能出现在战国中晚期。
四、尚未以史论《诗》
将《孔子诗论》与汉代四家诗对读就可以发现,它论《诗》是从作品内容出发,而不像汉儒那样以史论《诗》。
由于《诗三百》时代人们的著作权意识尚未觉醒(注:有人说《诗经》是“集体歌唱的时代”,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每一首诗都会有它的第一作者,不可能是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因此绝大多数作品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注:《诗三百》自言作者的仅有“吉甫”“寺人孟子”。《左传》中有卫人为庄姜赋《硕人》、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为高克赋《清人》、秦人为子车氏赋《黄鸟》几条记载。)对这些无名之作很难准确指出它的作者和具体创作背景。《孔子诗论》所提及的历史人物仅有后稷、文王、召公三人,而这三人分别是《大雅·生民》、《文王》、《召南·甘棠》诗中点明了的。此外《孔子诗论》中再没有以史论《诗》的内容。与此相比,汉代四家诗特别是《毛诗》总是将作品与某王、某公侯、某后妃、某大夫联系起来,那种言之凿凿的肯定语气,似乎让人不容置疑。(注:本文所征引的汉初三家诗材料,出于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毛诗》材料出于《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例如《周南·关雎》,《孔子诗论》仅说“《关雎》以色喻于礼”,而《鲁诗》则说它是讽刺周康王好色晏朝。《韩诗》说《关雎》正容仪以刺时。《毛诗》则说《关雎》是歌颂“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的后妃之德。又如《鄘风·墙有茨》,《孔子诗论》第二十八简说:“慎密而不知言。”三家诗一致认为是刺卫宣公,《毛诗》则说:“《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庶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又如《邶风·柏舟》,《孔子诗论》仅用一个“闷”宇概括它的主题,《鲁诗》说它是卫宣公夫人明志之作,《毛诗》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又如《邶风·燕燕》:《孔子诗论》第十六简说:“《燕燕》之思,以其笃也。”《鲁诗》认为《燕燕》是卫姑定姜送媳妇归宁之作,《齐诗》不仅说《燕燕》的作者是定姜,而且增加了卫献公无礼的情节,《毛诗》则说是卫庄姜送归妾。再如《小雅·小弁》,《孔子诗论》第八简仅说它“言谗人之害”,而《鲁诗》《齐诗》都说它是尹吉甫之子伯奇受后母谗毁所作,《毛诗》则说:“刺幽王也,太子之博作焉。”《小雅·祈父》,《孔子诗论》第九简说:“《祈父》之责,亦有以也。”《毛诗》说:“《祈父》,刺宣王也。”其它如《小雅·大田》、《谷风》、《蓼莪》、《黄鸟》、《巧言》、《邶风·绿衣》、《北风》、《鄘风·柏舟》、《卫风·木瓜》、《王风·兔爰》、《郑风·将仲子》、《齐风·猗嗟》、《唐风·蟋蟀》、《有杕之杜》、《陈风·宛丘》等作品,《毛诗》都为它们找到了具体的历史背景。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考察,四家诗以史论《诗》是受到孟子的启发。《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将《诗三百》看作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这就给《诗》确立了一个创作背景。孟子还强调要知人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注:《孟子正义》,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第337页。)这个说法也促使后人重视诗作的历史背景。汉儒就是在孟子确立的思想框架之下,为《诗三百》许多作品找到了具体背景,而且越到后来说得越具体,《毛诗》后出,在以史说《诗》方面最为详尽。《孔子诗论》的作者虽受思孟学派影响,但从他尚未以史论《诗》来看,他或者没有看到孟子这一番言论,或者是看到了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因为一种思想从提出到最后付诸实践,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从《孔子诗论》来看,战国中期还没有形成以史论《诗》的格局,当时的儒家学者在治《诗》的时候,能够从作品实际出发,保持比较严谨的学风,不强行为作品指定作者或安上背景,像《汉书·艺文志》所批评的“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的情形,在战国时期还没有发生。所谓某诗为某王、某妃、某大夫所作,大多出于汉儒的创造。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孔子诗论》有它独特的学术个性,有它自己的理论品格。它吸收了前人的和当代的思想营养,但它的创新成就更引人注目,它在中国《诗》学史写下了许多“第一”。汉代《诗》学的格局,在这部杂感式的竹书中已初见端倪。它继承前人,又不蹈袭前人;它开启后代,又异于后学。惟其特色鲜明,《孔子诗论》才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价值。
标签:论语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孔子论文; 战国论文; 大雅论文; 孟子论文; 文王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中庸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