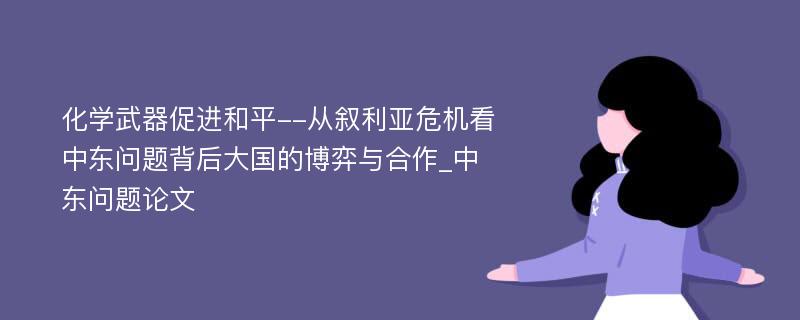
化武换和平——从叙利亚危机看中东问题背后的大国博弈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叙利亚论文,化武论文,大国论文,和平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局势就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随着叙利亚接受俄罗斯的提议,申请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战争的乌云似乎暂时离叙利亚而去,中东的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缓和。回顾一个月来叙利亚危机的发展历程,既可以从中透视出中东地区格局演进的一些趋势,也再次证明国际合作和政治谈判才是解决叙利亚问题和中东问题的正道。
一、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和性质
不管是从冲突的烈度抑或频度来看,还是从危机的数量抑或蔓延的范围来看,中东地区一直都是热点问题集中爆发的地区。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中东地区带来持久和平,相反后冷战时期几场重大的干预战争均发生在本地区,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西方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基本十年一周期。中东地区的冲突和动荡既有地区自身的原因,也与国际体系的转型密切相关。与其他次地区体系不同的是,中东地区体系的独特性在于其对国际体系的高度依赖,其格局变化的逻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的博弈和互动。[1]同时,当前的中东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国际体系转型和地区格局重组同时发生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增加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2011年初始于突尼斯的中东大变局既是这种格局转换的一种后果和反映,又对地区和国际格局的演进施加了强大的反作用力。
从爆发开始,中东大变局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场变局仅仅是中东地区国家和社会历史性变革长周期的一个开始。该地区人民长期期待的变革的确已经发生,但是变革本身并不是目的,单凭变革并不足以解决本地区面临的各种问题,相反新的变化给地区局势带来了更多的动荡和冲突,最大的变化是不可预测性和脆弱性因素的增加。这种新的战略不确定性既有外部的原因,又有内部的原因。外部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日益推进的今天,中东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实际上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相应地中东在各大国外交地位中的排序也有所下降。此外,当前国际体系中总体实力对比东升西降和权势转移的趋势也动态反映到了本地区,一种新的大国互动的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内部的原因在于,中东地区的均势正在重组的过程中,传统的力量对比和实力格局已经不适应新的局势的发展,新的地缘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从国际体系层面还是从地区体系层面,中东地区格局都表现出新老格局并存、新老矛盾交织的特点,这在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从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中可以透视出新老格局交替的影响。一方面,冷战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西方舆论倾向于把俄罗斯维护叙利亚政府的立场解读为维护其在中东冷战盟友的努力,特别是渲染叙利亚拥有俄罗斯在中东最后一个军事基地这一事实,把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立描述为新冷战。由此可见,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当前国际格局中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对中东格局的影响也不断显现,在叙利亚问题的出路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存在明显的分歧。
其次,叙利亚危机也反映出中东地区力量对比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中东变局使阿拉伯力量和非阿拉伯力量的对比进一步朝着非阿拉伯力量方向倾斜。埃及国内政局的动荡削弱了阿拉伯世界一支重要的领导力量,中东变局的连锁反应使许多阿拉伯国家忙于内顾而无暇在外交事务中投入更多精力,这为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在中东事务中扩大影响打开了机会之窗。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对立和分裂在加剧,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改革力量和保守力量的冲突在加大,而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在热点问题上,这在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上表现得很突出。
最后,叙利亚危机背后折射出宗教和世俗新老力量的相互交织。在新的中东变局中,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间的争夺,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围绕权力和利益,宗教和世俗、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常人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交叉结盟组成“权宜联盟”的情况。例如叙利亚一直是阿拉伯世界内部世俗主义政权的代表,但是却得到了被认为是政教合一的伊朗的支持,伊朗的立场背后无疑有国家利益对宗教的平衡考虑,而叙利亚反对派内部派别林立,既有伊斯兰主义分子,又有亲西方的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子,他们背后的外部支持力量也各有不同,只是在推翻阿萨德政权这个共同的目标下暂时走到一起。
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困境
在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中,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影响未来局势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变量。但是相比十年前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的坚决,奥巴马政府在是否对叙利亚动武的问题上显得有些首鼠两端,不管是奥巴马总统本人还是其外交团队前后发出的信号,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奥巴马甚至一反常态地将此问题提交美国国会讨论,表明了奥巴马总统在动武问题上的不自信和进退失据。
首先,在叙利亚问题大动干戈与美国目前的中东战略目标相悖。在伊拉克战争十年之后,在美国2014年即将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背景下,美国当前中东战略的基本方针是相对收缩,目标是总体可控,具体途径是最小主义,即以最小的代价维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防止过度介入而浪费美国的“财富和生命”,防止中东出现大的动乱而干扰和破坏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美国目前在中东正面临严重的能力和意愿赤字,由此带来两个后果。后果之一是由于能力和意愿的不足,美国在中东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尽管美国试图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但是由于缺乏实际的资源投入,其目标和实际行动能力之间的差距在加大。此外,与克林顿时期提出的“东遏两伊,西促和谈”战略、小布什时期提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相比,奥巴马总统的中东战略缺乏总览全局的主题和具体实施的路线图。此次叙利亚化武危机事发突然,尽管美国军事打击的预案很充分,但是明显缺乏连贯的政治配套战略。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是,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军事行动往往会反噬自身,带来更多不可测的风险。后果之二是尽管明知自身能力和意愿在下降,美国还是情不自禁地要在中东问题上出头,导致舆论和行动的脱节。与舆论上的高调表态相对应的却是行动上的谨慎和小心,这反而损害了美国政策的可信度。
其次,在对叙利亚动武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始终面临着军事行动的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如果说动武的目的是威慑性的,是为了给叙利亚政府施加更多压力,迫使叙利亚政府作出更多让步,那么保持军事行动“引而不发”可能比实际实施军事打击更加有效。如果说动武的目的是惩罚性的,且不说法理上是否有充分的理由,有限军事行动的惩罚效果并不会太好,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平民伤亡。如果说动武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美国的威望,因为叙利亚跨过了奥巴马设定的红线,那么时间拖得越久,效果越差。如果说动武的目的是迫使叙利亚政府放弃化学武器,那么谈判无疑是最佳选择,而实际上俄罗斯的方案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如果说动武是为了实现叙利亚政权的更迭,那么唯有大打,而这是奥巴马最没有把握的,因为一旦大打,美国将面临军事行动易发难收、投鼠忌器的困境。
美军事行动有效性不足的后果有三。一是将严重干扰美国在中东甚至全球战略的实施。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美国中东战略将更加突出重点而不是全面投入。在美国看来,伊朗而不是叙利亚是美国未来在中东地区的头号威胁,解决伊朗核问题是第一要务,但是一旦在叙利亚大打,不仅会转移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打下来的结果可能会像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那样,反而使伊朗从中大大获益。二是因为可能引发不可控的全面危机。叙利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东矛盾的一个集合点,有太多的外部势力陷在其中,太多的利益牵涉其中,一旦局势失控,叙利亚问题有极大可能升级为泛地区危机,从而严重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三是美国不想再背上下一个伊拉克包袱,在战后重建的问题上,美国过去在中东做得并不成功,现在则更缺乏相应的物力和财力支持。
最后,在对叙利亚动武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还受到内部意见分化的很大牵制。
第一,美国的盟友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在美国的大西洋伙伴内部,尽管英国和法国表现得非常积极,也得到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响应,但是总体而言,在欧盟和北约内部还是存在不一致意见,许多国家不赞成甚至反对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单边动武。即使是一直坚定站在美国一边的英国和法国,国内的意见也并不统一,英国国会8月29日投票否决了首相卡梅伦对叙利亚动武的提案。在美国的中东盟友内部,意见也有分歧,虽然阿盟国家外长会议敦促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化武事件采取应对措施,但与会国家并未一致同意美国军事干预的做法,部分阿盟国家反对外国介入叙利亚局势。在叙利亚的周边国家中,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都呼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这次危机。
第二,尽管西方舆论上似乎喊打声一片,但美国政府内部分歧严重,普通民众和学术精英之间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民众似乎已经厌倦于过多的对外用兵,民意调查的结果一般都倾向于反对动武。但是在政府内部和学界,支持动武的强硬派观点则颇有市场,甚至一些学者鼓吹不仅要小打,更要大打,美国需要调整战略决策,以叙利亚为契机纠正过去不干预政策的错误。[2]美国的政要和学者还不断从美国的价值观角度为对叙动武辩护,国务卿克里在8月30日的讲话中高调声称,叙利亚问题也深刻影响到美国的自我认同,因为美国就是美国,“一直努力尊重那些规划我们的生活和理想的普世价值”。[3]克里的讲话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响应和赞许,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高尔斯顿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问道,美国因为错误的原因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会阻止美国即使有了正义的理由也不在叙利亚采取行动吗?[4]反战的舆论和支持大打的舆论同时存在,使奥巴马不得不在左右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三、国际合作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必由之路
在各方特别是俄罗斯的努力下,目前叙利亚危机暂时得到了缓和,又重新回到了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解决的轨道上。俄罗斯之所以能成功地斡旋这场危机,除了其高超的外交谋略以及在中东地区长期积累下来的人脉和历史影响力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俄罗斯抓住了有关各方厌战愿和的心理,照顾到了各方的利益关切,为危机当事方提供了缓和和退出的台阶,这对未来国际合作解决中东其他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中东的许多危机从表面看是地区性危机,实际上是国际体系层面的危机和问题在中东地区层面上的投射,背后反映的是深刻的大国博弈和斗争。阿拉伯变局发生之后,原有的地区地缘平衡被打破,各大国和地区力量都还处于重新适应新的地区格局的过程中。不管未来叙利亚危机走向何处,至少从过去一个月各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互动特别是美俄互动的结果来看,各方都不愿意看到中东危机失控,在维护中东稳定和安全的问题上大国的利益是一致的。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中东危机不仅是可能的,可行的,也是各方所期待和赞许的,政治谈判仍然是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最佳出路。
首先,仅过去十年中东地区的历史经验就已一再证明,军事干预和战争手段的效用不仅有局限性,而且是把双刃剑,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都已经证明了这点。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的,“我们要想想,在过去十年里,世界各个地区已有多少次武装冲突与美国有关了?这些冲突最终又有哪一次解决了问题?”[5]应该说,从奥巴马政府此次在叙利亚动武问题上的进退两难可以看出,伊拉克结束十年以来,美国对外干预和用武的顶峰已经过去。一方面,随着美国在中东的收缩,美国在中东动武越来越力不从心,也越来越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动武问题上并不是没有过反思,正如奥巴马9月10日就叙利亚问题对全国发表讲话时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再次使用武力推翻另一个独裁者,我们已经从伊拉克那里吸取了教训,如果我们那么做的话,我们将为此后发生的一切买单。”[6]
其次,随着国际格局和中东格局的变化,美国和西方在中东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新兴大国和地区大国的话语权不断上升,中东格局中权力和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政治解决方案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赢得国际社会的共识,其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各方利益汇聚点上的妥协。在本次叙利亚化武危机之中,俄罗斯的提议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它准确地把握了有关各方的心理,满足了各方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对奥巴马政府来说,首要的考虑是防止因为军事干预陷入战争的无底洞,俄罗斯的方案将矛盾聚焦在禁止化学武器的使用上,减轻了奥巴马政府在动武问题上进行战略决策的压力,也给了美国保全面子的台阶。对于叙利亚政府来说,当前的头号大事是政权的生存,与此相比,放弃化武并不是核心利益,俄罗斯的方案满足了叙利亚化武换和平的需要。对于国际社会甚至包括那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地区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避免叙利亚危机升级为地区危机,保持中东地区的总体稳定,而俄罗斯的方案为回到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轨道铺平了道路。
叙利亚危机和其他中东热点问题一样,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中东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方案,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包揽一切。只有顺应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坚持外交解决的政治原则,付出更多的智慧和耐心,才能为中东和平带来真正的曙光。
标签:中东问题论文; 奥巴马论文; 叙利亚危机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中东论文; 博弈论文; 叙利亚政府军论文; 伊拉克战争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