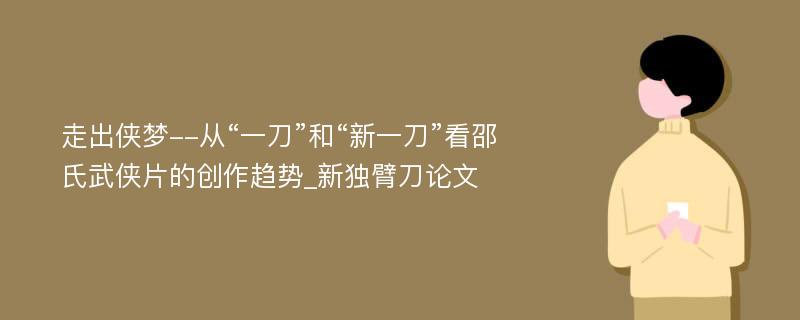
走出“侠客梦”——从《独臂刀》、《新独臂刀》看邵氏武侠片的创作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侠片论文,独臂刀论文,侠客论文,邵氏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之所以选择两部“独臂刀”进行分析并以此探讨邵氏武侠片的创作走向,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因为1967年出品的《独臂刀》以突破百万元的影片收入创造了香港电影票房的新纪录,其巨大的商业效益必然会影响其后的武侠电影创作,并由此形成一种具有特定风格的类型片潮流,如同1920年代的《火烧红莲寺》带来的一大批“火烧片”一样——当然《独臂刀》带来的并不是一大批“独臂片”。其次是因为两部“独臂刀”都出自张彻之手,在同一导演所拍摄的同类题材、类似故事的影片中应该最能看出其创作的特点及其风格的发展、变化。最后,则是因为张彻既长期在“邵氏”拍片又是香港武侠电影的一代宗师,他的创作特点和风格无疑不只是属于个人的,同时也是属于邵氏的和香港的,能够代表邵氏乃至整个香港武侠电影创作的一种走向。因此分析《独臂刀》和《新独臂刀》(1971)对于探讨邵氏乃至整个香港武侠电影的创作走向是非常必要的;而探讨邵氏和香港武侠电影的创作走向对于深刻揭示武侠电影的发展规律、准确判断张彻和“邵氏”武侠电影在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又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早出现于1920年代的武侠片是中国电影的特有类型,它的诞生与中国传统的“侠义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而“侠义文化”的兴起和广泛流传又源于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这种“侠义文化”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从唐、宋传奇到明、清及其以后的话本、戏曲、章回小说——中就有充分的表现:“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见多少关于侠客义士的事迹,‘抑强扶弱’、‘轻诺好义’,那一种慷慨激昂、叱咤风云的气概,实在令人倾倒,尤其是能引起压迫下弱小者的同情。本来在这魅厉横行,肖小潜迹的万恶社会中,所谓‘公理正义’‘民法国律’者,早已被强权者摧残殆尽了!弱小者除了俯首听命,敢怒而不敢言外,还能向谁去伸诉呢!惟有侠士一出,除暴安良,为弱小者张目,为冤屈者鸣不平,为人之所不敢为,为人之所不能为。所以武侠是弱小者的保障者,是强暴者的惩戒者,其能裨益于社会人心,实非妄言啊!而文人的加以表扬,戏剧加以宣传,也实在有很大的理由在也!”[1] 由邵邨人、高梨痕编剧,邵醉翁导演,天一影片公司1925年出品的我国第一部武侠片《女侠李飞飞》所塑造的也是一个能除暴安良的侠者,影片中的女侠李飞飞像所有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一样寄托着人们的理想,表达了人们的期待:“吁,世路崎岖,人心险恶,安得千百李飞飞,一一平除之耶。”(《天一影片公司特刊》)实际上,所有中国早期的武侠片和1950年代香港流行的粤语黄飞鸿电影所表现的都与《女侠李飞飞》及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如出一辙,基本上没有超越“抑强扶弱”、“轻诺好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范畴。
虽然香港邵氏(兄弟)公司与中国最早拍摄武侠片的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独臂刀》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武侠片,但它却与《女侠李飞飞》等此前所有的武侠片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恰恰表现在对《女侠李飞飞》从传统武侠文学、戏剧作品中所继承,由《火烧红莲寺》等一大批武侠片所肯定,并在香港的一系列黄飞鸿电影中所一以贯之的“抑强扶弱”、“轻诺好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武侠主题的突破,其内容和意识形态的表达有所创新,也更为深刻和复杂。
影片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结构也比较简洁:方刚本是“金刀大侠”齐如峰的仆人方成的儿子,在方成为主人而死之后,方刚成为了齐如峰的义子和徒弟。尽管身份发生了变化,齐如峰本人也信守对方成临死时的承诺,待方刚不薄,但齐如峰的女儿齐佩却对方刚极不友好,经常与两位分别出身于富豪人家和武侠世家的师兄一起欺负方刚,后来竟然在一次冲突中一刀将方刚的右臂砍了下来——由此开始了“独臂”的传奇。方刚失去右臂后独自离去,途中晕倒被村姑小蛮所救,伤好后与小蛮一起过着普通的乡下生活。这时几年前被齐如峰打败的长臂神魔发明了专门克制齐家刀法的“金刀锁”,上门寻仇。方刚知道后,不顾小蛮的极力劝阻,毅然返回师门增援。当齐门众弟子纷纷丧命于“金刀锁”,齐如峰也被长臂神魔打败,齐家面临灭门之灾的关键时刻,方刚及时赶到,用一把“金刀锁”无法克制的短刀和一套自练的独臂刀法狂胜长臂神魔,救了齐门众人的性命。
从影片的故事情节来看,传统武侠小说和电影所强调的“抑强扶弱”、“轻诺好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等内容似乎被淡化甚至被消解了,尽管在“序幕”中通过寻仇者与齐如峰的对话我们能够隐约地知道齐如峰爱管江湖“闲事”,阻碍了一些黑道的作恶,但影片重点叙述的并不是齐如峰的“行侠仗义”,而是方刚被齐佩变成“独臂”后不仅没有记仇反而用“独臂刀”先从“笑面二郎”郑二爷家里解救了被困的齐佩,最后又救了齐如峰全家的故事。当然,在这个故事中方刚表现的也是一种“侠义”之心——正是因为这种“侠义”之心的表现,该片才仍然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武侠片。只是,影片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侠义”的表现上。
影片中的小蛮是个令人饶有兴味的形象。这个乡下姑娘在影片的情节结构和思想表达上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不仅救了方刚的性命,也将她父亲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半本短刀刀谱交给了方刚,使他得以练成独特的“独臂刀法”,最后战胜长臂神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通过刀谱间接传授了方刚武功的青年女子虽然也是武林人士之后,但却在亲眼看见父亲惨死之后早已对“武林”、“江湖”有了与其父辈截然相反的看法。她对方刚说:“我妈妈告诉我,宁愿嫁给一个种田的乡下小子,两人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千万不要喜欢那些江湖子弟,他们为了什么师门名誉,就连性命都不顾!这种人逞英雄,争面子,看上去有义气,有血性,堂堂的男儿,最容易迷惑女子,喜欢上他们。妈叫我千万不要上当!”这一段表白既是小蛮妈妈的观点,也是小蛮自己的观点——为此她妈妈烧掉了半部刀谱(留下的只是半部左手辅助刀法),母女二人远走他乡,远离武林、江湖,隐居乡间,过着简朴而平静的田园生活;也为此,小蛮将半部刀法交给方刚只是让他用来自卫、防身,极力劝阻他重返江湖争斗。当然,上述表白无疑还可以看作是编导的想法或他们想要通过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小蛮这个角色的塑造除了推动情节发展本身外也是出于创作者反思武林、批判江湖争斗的思想表达的需要。显然正是因为这样的反思和批判,所以影片有意不去强调齐如峰的“行侠仗义”,相反还突出了其女儿齐佩的娇纵、蛮横,和其手下某些弟子的狂妄自大。
与此相同,影片的“正”、“反”人物的确定也似乎淡化了传统的社会道德原则,如将长臂神魔作为反面角色来塑造便没有过多地考虑他的“正义”或“非正义”性,而只是因为其“逞英雄”、“记仇”的性格和“斗输赢”的行为:这个作为“反面人物”的神秘“恶魔”仅仅因为13年前与齐如峰决斗时输了一刀,为了报这所谓的“一刀之仇”,便处心积虑,发明“金刀锁”,训练徒弟,杀了许多齐家弟子,最后打到了齐府上,要将对手斩尽杀绝。而方刚作为正面形象,则是因为他不记断臂之仇,以德报怨!他返回师门迎战长臂神魔并不是为了维护师门名誉,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救人,当然更不是重返江湖争斗,而是要阻止江湖争斗,以武力消解武力,所以在杀了长臂神魔以后,他对齐如峰说:“师傅,弟子已经是一个残废之人,早已厌倦了江湖的争强好斗。今天报了师恩,从此远走天涯,做一个种田的农夫了!”在他走后,号称“金刀大侠”的齐如峰也折断了金刀——这实际上也是影片反思武林、批判江湖争斗思想的进一步表达。
由此可见,《独臂刀》虽然还是一部武侠片,但显然已经不再是表现“抑强扶弱”、“轻诺好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武侠片了,它以对武林的反思或对江湖争斗的批判超越了传统武侠片,开创了武侠电影的一个新的思想领域;而且,这种思想可能更具有现代性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因为“侠客梦”原本是法制不健全时代人们继“好皇帝梦”、“清官梦”之后的最后一个“中国梦”,不可否认,它确实给了中国老百姓许多期待和精神安慰,这也是武侠小说、戏剧和电影一直以来深受人们欢迎和喜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是,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步伐似乎要将人们从这样的“中国梦”中唤醒过来——毕竟将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的传统“人制”时代总要过去,现代化的“法制”时代终将到来。如果说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滩上还没能迅速发生效应,在制度和精神方面都还没有“旧貌换新颜”,以致海派武侠电影依旧在轰轰烈烈演绎着“千古侠客中国梦”,人们也一时还无法从“梦”中醒来;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随着法制社会的逐渐建立,传统的“侠客梦”早已不再令人流连。更有甚者,当法制进一步完善后,传统的“江湖”、“侠客”在成为一种制度之外的“多余社区”和“多余人”的情况之下,有的便可能会逐渐演变成一种对抗法律的力量(如黑帮、打手),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引起公民的不安与反感,也因此,传统的武侠电影就失去了现实的“土壤”:在《独臂刀》之前香港武侠电影的逐渐式微便是一种突出的征兆。
如同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大老板邵醉翁先生最早拍摄中国武侠电影一样,香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继任老板邵逸夫先生也最早认识或敏锐地感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武侠电影的审美心理和需求的变化,所以“他从南洋回到香港主持邵氏兄弟公司的制片业务之初,就一直想拍摄一种新的武侠片,希望能有美国西部牛仔片那样激烈、逼真的打斗,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武术招式,好好设计动作,一定要超过粤语武侠片黄飞鸿电影”,从而创造一个“彩色(国语)武侠世纪”。[2] 显然,在邵逸夫先生的设想中,这种“新的武侠片”有两个参照系:“美国西部牛仔片”和“粤语武侠片黄飞鸿电影”,也即模仿“美国西部牛仔片”,超越“粤语武侠片黄飞鸿电影”。当然,这种“模仿”和“超越”可能首先是影像风格上的——张彻和胡金铨当时学习、研究美国西部片时便特别注意到了其镜头的数量之多和由此带来的影片节奏之快,并通过对比,发现华语片的镜头数量太少,节奏缓慢,认为这是华语片不能适应和吸引当代观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3]——但一当将眼光投向了西方电影,便自然改变了此前中国武侠电影单一的传统文化模式,从而势必带来从形式到内容的一系列变化——美国西部片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文明与野蛮或代表法制的警长与危害一方的江湖匪帮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尽管张彻他们遵照邵逸夫先生的指示认真研究了美国西部片的镜头、画面和节奏,并拍摄了“力求画面的质感和真实感,摆脱传统武侠片的花拳绣腿及程式化之弊端”的“被认为是新的‘武侠世纪’的真正的开山之作”的《虎侠歼仇》(1964),但此片并“没能使观众认可和欢迎”,随后的《江湖奇侠》(1965,张彻编剧、由邵氏派往日本学习归来的徐增宏导演)、《边城之侠》(1966)、《断肠剑》(1967)也是如此,直到《独臂刀》问世才一举成功,而《独臂刀》中的武打动作、镜头、场面其实并不是非常真实、精彩:人工搭景、招式简单、动作仍然比较慢——可见其百万票房主要并不是来自武打本身,而是来自影片对传统武侠电影主题的突破,或对江湖、仇恨、争斗、争霸的反思和批判,而这正是法制社会中的当代观众对武侠电影的一种新的现实和审美需求。
正因为体现了当代观众对武侠电影的新的现实和审美需求,所以反思江湖争斗、反仇恨、反争霸的思想在《新独臂刀》中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新独臂刀》中的雷力之所以成为独臂都是因为江湖中人的好强和争强:一方面是雷力自己断臂前趾高气扬,影片一开始,雷力骑马举刀一路杀来,无人能挡,所向披靡;另一方面则是龙异之“龙大侠”见雷力刀法了得,生怕他日后胜过自己,为了自己能够永远称霸武林,他故意激起雷力与自己决斗,并以“自断一臂”作为输者向赢者所付的代价,最后雷力被打败,只好自断右臂,“龙大侠”因而得以保住其霸主的地位。像《独臂刀》一样,《新独臂刀》中虽然也有“主持正义”的内容,如封俊杰追查虎威山庄陈震南劫镖案,但这唯一的主持正义者最后却惨败在龙异之的手中,并惨死在陈震南的刀下——“正义”实际上无法得到“主持”,或者无人能够凭借个人的力量“主持”!这充分表现了法制社会中人们对侠客“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怀疑,传统的武侠电影主题因而也失去了原有的效应。同时期张彻的另一部现代题材的武打片(已经不再有“侠”,所以不再是武侠片了——一字之差充分显示了张彻或邵氏乃至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或转型)《拳击》(1971)便干脆将传统主题完全“悬置”了起来,表现兄弟二人与江湖黑帮的斗争,并最后让警察将黑帮头目绳之以法。由于既除不了“暴”,也主持不了“正义”,而且封俊杰很快就死去了,所以《新独臂刀》着重叙述的显然并不是侠客的“除暴安良、主持正义”,而是武林争斗、争霸和反争斗、反争霸的故事。围绕这一主题,影片有三重表达:一是雷力的“断臂”,二是封俊杰的“断身”(他不愿断臂,结果被陈震南拦腰砍成两段),三是龙异之的“断命”(最后被雷力所杀),三重表达都以人物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共同指向了对江湖“争斗”、“争霸”的有力否定!
实际上,雷力在断臂后自己也开始反思,他的整个性格都为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桀骜不驯、趾高气扬变成稳重宁静、小心谨慎,并能忍辱负重,甚至忍气吞声,连似乎与他有某种情爱关系的芭蕉姑娘对他处处受欺凌都看不下去,特地请做铁匠的父亲为他打了一把好刀,并说“死在别人的刀下也比被别人踩在地下要好得多”,但他不愿意接受和使用这把刀,与以前完全判若两人,本来不愿意为雷力打刀的巴铁匠所说的“‘强中更有强中手’,人不能强出头”的话可能道出了他此时的人生态度。饶有兴味的是,影片特别表现了封俊杰对雷力现状的羡慕,他羡慕雷力能够改变自己,放下武事,希望自己也能像雷力那样,并说等赴了虎威山庄的约后就和雷力一起到太湖边务农去。这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江湖争斗的厌倦。但现实中的他在遭到挫折之前还无法回头,甚至在同样被龙异之打败后宁愿死也不愿意自断右臂。他宛如以前的雷力,也是试图凭借个人力量拯救世界的传统侠客。他和雷力其实是编导同一个主题的两种反向表达:雷力以改变性格对江湖的争强好胜进行了正面反思,而封俊杰则从反面以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个人武力对于维护社会公正的无济于事。作为同一主题的进一步开掘的是龙异之,这个影片故事中的“反面角色”虽然比《独臂刀》中的长臂神魔善于伪装,更诡计多端,但同样都是为了争霸而不择手段、而陷于不义,最后丢掉了性命!他专门对付新出道的高手,将他们扼杀在武功强于他之前,以便自己能够永保武林霸主的地位。这样的人物后来成了香港新武侠/武打电影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人物,他们都是因武功而争霸、因争霸而变坏。如果说雷力和封俊杰只是证明了传统侠客使命的难以完成,那么龙异之(以及长臂神魔)们则将“武功”与“争霸”、“作恶”、“危害社会”联系了起来,在侠义之士缺席,或侠客使命无法完成的情况下,这些由于恃强争霸而作恶的武林高手们便彻底颠覆了武侠电影“抑强扶弱”、“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主题,让观众看到了江湖的险恶和武林的反面,从而走出了应已成为历史的“侠客梦”——虚幻而充满着无奈的最后一个“中国梦”。
传统的“侠”、“义”消解之后,武林争霸被否定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情”:在《独臂刀》中是爱情和师徒之情,而在《新独臂刀》以及《拳击》中则是友情和兄弟之情。方刚杀长臂神魔并不是因为“仗义”,而是为了报答师傅的恩情;雷力最后奋起与龙异之一搏,也不是作为侠客出来“主持正义”,而是出于他与封俊杰的兄弟之情;《拳击》更是用这种“兄弟之情”结构剧情,并贯穿影片的始终。“情”之现代性并不是说这些“情”只有现代才有,而是说在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中,正在逐渐淡化的“情”却是人们最迫切的需要!“情”当然同时也是对“无情”争斗的有效抑制,而所谓无情争斗又显然并不只是存在于古代、江湖之上或武林之中,在观众所处的现实生活里也比比皆是,因而更令人们反感,同时更让人们渴望有“情”——爱情、亲情和友情。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现实中人们所渴望的“情”的表达,新武侠/武打片才又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
武侠片创作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在20年代末达到了一个高潮,30年代以后逐渐消沉下来,1949年以后,在大陆完全消失,只在香港得以延续,八九十年代以后大陆才又通过合作的方式和借鉴香港武侠/武打片的创作模式逐渐恢复武侠/武打片的创作。由此可见,在中国武侠/武打电影发展史上,香港的武侠/武打片创作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其中,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延续问题,还涉及到创作的现代转型和在转型中的进一步发展。根据上文的分析、论述,我们不难看到,“邵氏兄弟”不仅在上海的“天一”时代创作了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片《女侠李飞飞》,成为中国武侠电影的源头;而且,在1960—1970年代又以《独臂刀》和《新独臂刀》(以及同时期的《拳击》)顺利地完成了武侠/武打电影的现代转型:走出传统、虚幻的“侠客梦”,走向了现代、理性的现实人生。因此,如果说在中国武侠/武打电影发展史上,香港的武侠/武打片创作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这种承上启下性首先表现在《独臂刀》和《新独臂刀》中。我们完全可以说,《独臂刀》和《新独臂刀》所显示的不只是张彻,也不只是“邵氏”,甚至不只是香港,而是整个中国武侠电影的创作走向,代表着中国武侠电影创作的一种方向。事实上,香港和中国武侠/武打电影就是顺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到今天的。
标签:新独臂刀论文; 侠客论文; 邵姓论文; 女侠李飞飞论文; 拳击论文; 武侠论文; 武侠片论文; 邵氏电影论文; 武打片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古装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