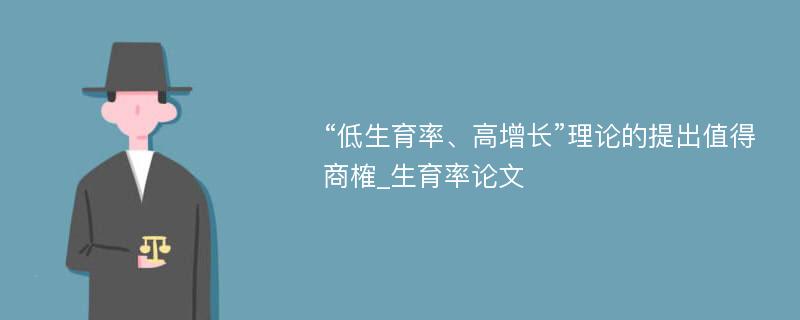
“低生育率高增长量”论的提法值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提法论文,高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低出生率高增长量”、“低生育率高增长量”、“低增长率高增长量”之类的“低率高量”论述与论点,频频出现在学术刊物、报纸、讲话、报告及宣传材料中,认同者居多。然而,此论一提出作者就持否定观点,认为这是因人口统计学基本概念混淆所酿成的一种似是而非论,并在相关场合多次阐明了此论提法的不妥。
坦诚地讲,此论之误本应属人口统计学的基本常识性问题。因此,一直无意打算花费时间与笔墨做专门论述。鉴于不少同志时至今日还未搞清楚此论的正确与否,建议我对此论能做一专题论述,于是写成此文,以飨各层读者。
一、“低率高量”提出的背景
以今天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来看,中国人口形势严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恐怕无人对此有疑义。
自70年代中国城乡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以来,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急剧降至1980年的2.28。表征妇女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总和生育率,根据多种调查资料计算,都表明其整个80年代的平均值不会低于1980年的水平。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值,虽然较80年代有所下降,但是降幅也是有限的。
近10多年来,一讲中国人口形势,必谈“严峻”二字。“严峻”二字习惯地成了表述中国人口形势的专用语。尤其是在统计结果显示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生育水平值之后,“严峻”便成了人口控制任务仍十分艰巨的强调词。
全国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因80年代初期之后的早婚比例上升、晚婚比例下降,以及生育水平的回升,而提前于1986年到来。较之预期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起始年早了一年多。
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中国妇女的峰值生育年龄段为25~29岁,即形成了中期生育型控制模式。这是70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获得初步成效的体现。1980年之后,受生育政策急转弯式的紧缩影响,峰值生育年龄段急剧前移。1983年移至20~24岁,即生育模式反弹为早期生育型控制模式。
这种生育模式的反弹,无疑将酿成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与生育水平下降难度的增大。根据陆续进入婚育年龄的全国妇女年龄构成变动推算, 中国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将要持续10 多年, 高峰期的峰顶约在1992年左右。然而,令人吃惊与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次出生高峰期间,从1988年起就未见高峰,尤其是在出生峰顶年份更是如此。因为统计调查的出生率非但未见客观上本应出现的回升现象,反而呈急剧下降。全国的人口出生率1987年为24.09‰,1992年为18.14‰,5年间下降了5个多千分点。人们不禁要问:出生高峰期间无高峰,是人口学者对客观人口增长趋势认识水平太低,竟连出生高峰都测不准呢?还是统计“水分”屡创新高,掩盖了真实的出生率回升呢?
倘若没有“水分”,果真统计数字所反映的就是事实,这无疑将成为奇迹之奇迹。然而,客观上“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历年自然增长率(出生率)都普遍过于偏低”,“根本不存在稳中有降的客观可能性”[1]。
若从计划生育日常统计来看,除少数不在出生高峰期或不久退出出生高峰期的几个直辖市和个别省外,绝大多数省份的人口出生率,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种出生率下降就更甚。有的在其出生峰顶年份出生率仅略高于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低到甚至连统计部门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地步。
从统计数据普遍反映出的这种一发而不可收的出生率下降趋势,令人不禁疑惑中国人口是否是恰处在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
计划生育统计中的“水分”之大,不仅夸大了计划生育的实际人工控制能力,同时也使今后的工作务实增加了困难。
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相对于计划生育统计中的“水分”虽然要少些,但也与客观实际相差甚远。众所周知,一些被调查对象不如实申报,其调查的“水分”逐年在加大,早已不再是新闻。抽样调查的准确性,离不开被调查对象如实申报这个基础。否则,就无所谓准确而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80年代初期之后的历年人口变动抽样结果,及其之后多次调整的数据分析,可以说其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准确性是一年不如一年。这并不能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方法与技术不先进,而是人为的干扰因素如瞒报、漏报在增大。尤其是受当地行政方面的干扰,使其调查质量每况愈下。因此,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也务必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万万不可将错就错。这决不是否定成绩,而是否定本应该否定的东西,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
正确地评估生育率变动,并非是无规律可循,也并非是“水分”就可以掩盖得住的。在生育模式变动不大的条件下,受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生育率变动方向与大小是客观的。那种以无法改变的年龄结构变动影响,来说明人口形势严峻是不可取的。真正的严峻莫过于是对那些通过主观努力可以加以改变的,却不认识或缺乏认识,或有认识也没集中力量去抓,而是对那些近期很难有所作为的硬去强办。
面对高峰期间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出生率大幅下降,“严峻”二字的确显得苍白无力。于是有关“严峻”的“低生育率高增长量”论就恰逢其时应运而生了。
强有力的行政控制手段,可以导致人口出生率呈现暂时很低的人口现象,但回升却是不可避免的。须知在生育水平已经较低的出生高峰期间,在生育水平下降有限、出生问题变动不大的条件下,由于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比例上升与居高不下,根本不可能出现连续10多年的出生率下降。因此,只能从统计“水分”过大来找原因并加以认识。
如果误信统计“水分”过大的数字,并以此来认识人口形势、评估与指导工作,必然导致盲目乐观,失去对客观实际人口控制能力应有的认识,也就侈谈正确有效地指导工作。
所谓“低率高量”之诸论,其核心是肯定“低率”是事实,否定统计中的“水分”大。“高增长量”虽说是用来强调人口形势严峻,但须知这种所谓的“严峻”是客观的,也是无法改变的。为此,剖析“低率高量”论,对正确认识人口形势、正确认识计划生育工作与人口控制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低率高量”论剖析
1994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第1期刊发了《论70年代至90 年代中国生育变迁》一文。论文指出:“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当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降到接近更替水平时,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每年的出生婴儿数和人口增长量,却高居于生育率急剧下降前期即7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当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高达4.5以上。所以可以说, 中国今天面临的不是一个生育率太高的问题,而恰恰是‘低生育率和高增长量’并存的问题,这正是中国目前的生育态势与70年代相区别的最根本的特征”[2] 。
1999年,《人口研究》第3 期刊发了《对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文。该文指出:“我国人口发展将长期处于低增长率和高增长量的态势”[3]。
如果我们把观察生育率与出生量、增长量的时间移到五六十年代,就会清晰地发现,那时的总和生育率都在6以上, 其历年的出生量与增长量较趋近于更替生育水平值的80年代要低得多。相对来说,这是否可以称为,“高出生率与低增长量”并存呢?显然,如果这一论点成立,对于同一问题,从不同的时期看,然后加以比较,就会得出迥异的结论。可见,此论是站不住脚的。
人口统计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死亡率相对稳定或变化很小的情况下,出生量与自然增长量,是与人口基数及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年龄构成变动紧密相关的指标。脱离相应的人口基数前提,仅仅以出生率及生育率变动来进行出生量与自然增长量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为了使同期内相同或不同的人口,以及同一人口在不同时期的出生量与自然增长量具有粗略的可比性,在人口统计学中才设置了相对指标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
在通常情况下,由于总和生育率具有出生速度“信号”的指标特点,死亡率相对稳定条件下,高总和生育率总是与高自然增长率相伴,低总和生育率总是与低自然增长率相伴。
无论是高生育率还是低生育率,其指标的获取都是来自相应的人口。其出生量的大小或高低,都是相应于生育率的大小或高低而言的。高生育率必与高增长量对应,低生育率必与低增长量对应。诸如:
出生人数=年均人口数×出生率
自然增长数=年均人口数×自然增长率公式清楚地表明:出生量与自然增长量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的高低。“量与率”是相应于其人口规模,分别以绝对数和相对数来表达的同一人口现象,其间是等号关系,不是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关系。
可见,那种“低生育率与高增长量并存”、“低增长率和高增长量并存”之类的论点是不妥的。将中国目前的生育态势,定论为低生育率与高增长量并存,并揭示为与70年代相区别的最根本的特征,无疑是一种似是而非论。正因为该论具有似是而非,也才更易于酿成大面积认识上的误导。
1994年,《中国人口科学》第5 期刊发了题为《跨世纪时期中国人口的新特点》一文。该作者虽然未加出处,但显然是全盘地接受了《论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生育变迁》一文的相关论点。非但如此,还将此论抬高到跨世纪时期中国人口新特点的高度。须指出的是:该文从四个方面以专题来论述这一似是而非论,的确是首次。
该文专题论述的四个方面分别是:
一称:“低增长率高增长量,本身就是对立统一”;
二称:“增长率和增长量之间,生育率和生育量之间显得很不协调,形成了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尴尬局面”;
三称:“高增长量的局面很难有很大改变。整个跨世纪时期,国家和社会仍需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应付新出生的人口,仅此一点,也不容将人口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不能只看重低增长率或低生育率而忽视了绝对量,否则很容易为表面的成绩所陶醉,忽视了新人口特点所揭示的特殊矛盾,而重蹈历史覆辙”;
四称:“低增长率的直接原因是低生育率,而生育率越低人们对生育质量的选择越强烈。在这种生育心理的驱动下,人们很自然地将质量选择的砝码偏向于男孩一头。应该承认,在优生优育尚未成为社会普遍行为的情况下,多数人的生育质量观倾向于男孩偏好,是可以理解的”。[4]
人口统计的常识告诉我们,此处的“率”与“量”,一个是相对同期人口规模而言的相对量,一个是相对同期人口规模而言的绝对量。“率”是以相对的绝对量计算获取的。如自然增长率是以同期自然增长量与其相应人口规模均数之比获得。在认定该“率”为低增长率的同时,实际上也就认定了该“量”为低增长量。因为该增长率与增长量只不过是对同期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的不同表述而已。两者之间是等同的、统一的,也是一致的、无差异的。根本不存在对立统一的问题。这个道理与人们在银行储蓄所存款获取利息颇为一样。低利率获低利息,高利率获高利息。
假定甲乙二人于1999年1月1日分别在某银行储蓄所定期存款一年,若定期一年的人民币存款利率低至2.50%,甲存入人民币10000元, 乙存入人民币100元。2000年1月1日,甲将获利息250元,乙将获利息2.5元。若不顾及甲乙二人存款的基数,即不顾及甲乙二人存款的绝对数额差异,能否将甲获利息是乙的100倍说成是低率高息呢?
如果把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换成生育率,同样的问题仍会发生,只不过生育率的提法不那么直观,往往不易为人们所分辨而已。
假定1994年时中国的人口规模年均数为12.2 亿, 年出生婴儿数为1220万,年死亡人数为732万,那么,年自然增长人口为488万。其相应的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则分别为10.0‰、6.0‰和4.0‰。我国人口规模为世界各国之最是由来已久的客观事实。近30年来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也未低过20%。每一个千分点的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所对应的出生量、死亡量、自然增长量相对来说,都是相当可观的。人口基数越大,该率的每个千分点所表征的绝对值也越大。人口统计中的每一个具体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都是相对应于自身人口规模而言的,而非是相对应的自身人口规模之外的率。正是因为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异,使得以绝对数来进行出生、死亡、自然增长的比较才不具可比性,才采用了相对数——率。这就是说,因人口规模的差异,其出生、死亡与自然增长的升降变动与比较,只能用其率而不能用其量来进行。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不少学者将有可比性的与无可比性的“率”与“量”混为一谈,提出了“低率高量”论。从学术上讲,这是概念混淆。
如果从低出生率10.0‰与低自然增长率4.0 ‰误引出其相对应的出生量与自然增长量是高量,来企图说明人口形势严峻的内涵,那么,同样也可以从低死亡率误引出其相应的死亡量是高量,但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假定此间一个人口小省的人口规模年均为446万人, 其年出生人口为17.84万人,则出生率高达40.0‰; 同期的一个人口大省年均人口规模为10722万人、年出生人口为107.22万人,其出生率则低为10.0‰。 就出生率而言,人口小省是人口大省的4.0倍,但就出生绝对量而言, 人口小省仅及人口大省的16.6%。相对人口大省,能否说人口小省的人口特点是,高出生率与低出生量并存?相对人口小省,能否说人口大省的人口特点是,低出生率与高出生量并存?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口统计学中有关相对量与绝对量的应用原则就被歪曲。这样与之雷同的人口分析或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比较与评估,就都可以人为地取其所好,无规则地加以判定。
近些年来,在人口学研究领域,由于缺乏学术评论,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论因得不到及时的澄清而蔓延。这不仅戕害人口科学的健康发展,也使学术上的混浊不清而误导实践。
本文之所以要解剖“低率高量”论,还在于此论对实际工作已产生了误导。在一个有百万人口的大县甲,年末统计的出生人数为8800人,出生率低至不足8.0‰,而调查发现其“水分”很大。与此同时, 有一个人口规模为20万人的小县乙,年出生人口为4200人,出生率为21.0‰。甲县领导说:“我们是低出生率、高出生量,符合当前人口发展的特征,因而不存在统计水分问题。既然是高出生量,出生人口该统计的都统计了,怎么会有水分(瞒漏报)问题呢?乙县统计的出生人口还不及我们的一半,他们才会出现统计水分问题。”乙县领导则说:“别老盯住我们的高出生率,如果从人口出生量看,与甲县相比,我们是低出生量,不足甲县出生量的1/2,因此我们的人口控制工作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真实例子的抽象,说明这种高率低量或低率高量的似是而非论确实在戕害人们的科学思维,造成了对计划生育工作和判别标准的误导。
有人说外国人也讲“低率高量”。须指出的是,对与错不是以外国人说的还是中国人说的来判别。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其判别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反映客观本质属性的科学。
所谓“低率”与“高量”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立论,之所以错,就在于它混淆了人口统计学中相对量与绝对量的概念。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导致了将相对量指标与绝对量指标对立起来。应该明确的是“率”与“量”都是相对同一人口规模而言的“率”与“量”。抛开同期同一人口规模,来进行“率”与“量”的比较,实际上是将根本无可比性的指标错误地做了比较。其结论怎么可能不错呢?
所谓“对立”,实际上是把原本为一码事的误为是两码事。
所谓“统一”,应该是“低率”与“低量”的统一。然而,立论的自相矛盾,将一码事曲解成两码事,最后只能强冠以“统一”。应该说,在此问题上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问题。
若生育率指的是总和生育率,应该指出的是:总和生育率是一表征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指标,虽称作“率”但具有“综合性”指标特征,有明显的“速度”信号特点。通常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呈正相关。由此可知,在死亡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增率”与“增量”之间,“生育率”与“生育量”之间,都根本不存在不协调的关系。
所谓“尴尬局面”,是因立论的错误,混淆了人口统计学相关指标概念所酿成的自相矛盾局面。指标与指标间以及指标所反映的人口现象,怎么会有尴尬局面产生呢?指标间怎么变动才算不尴尬呢?
“高增量”是相对自身人口规模而言的概念。否则,就很难判定该增量是高还是低。如果中国人口的增量不是以中国的人口规模而论,那么,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的增量相对其他各国而言,就无所谓低增量之说。因为受人口惯性的作用,即使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已降至更替水平,其人口的增长也还要持续数十年。
可见,判定一个人口的增量是“高增量”还是“低增量”,应该根据该人口的“增率”是“高增长率”还是“低增长率”。因为一个人口的高增长率必有其相应的高增长量,而一个人口的低增长率必有其相应的低增长量。把中国人口低增长率对应的低增长量误认为高增长量,进而“创造”出“低增长率高增长量”之“说”,又怎么能正确地分析新时期人口特点与揭示出什么特殊矛盾呢?
承认中国近期与未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低率,也就无所谓高增长量,中国在跨世纪时期也就不存在“高增长的局面很难有很大改变”的问题。高增长率已成历史,当然,高增长量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中国因实行计划生育使得其生育水平急剧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大大放慢。如果主要不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因,现时的中国人口规模就有可能超过16亿。中国人口少增近3亿左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标签:生育率论文; 自然增长率论文; 出生率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人口增长率论文; 生育年龄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总和生育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