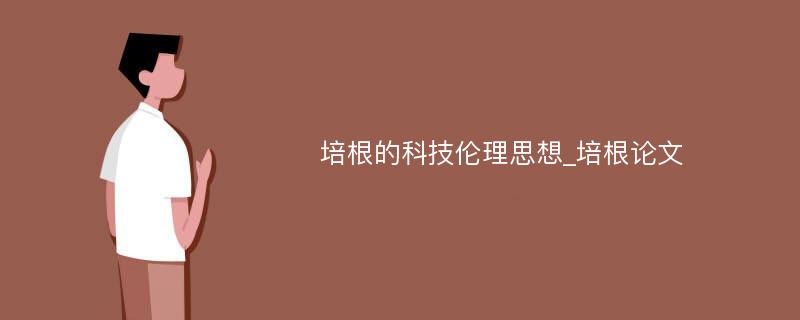
培根的科技伦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培根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近代英国杰出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被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上,他是科技乐观主义、科技决定论的先驱,充分肯定了科技的社会作用和道德功能,力图为伦理道德提供科学依据,并以此抨击经院哲学与宗教道德,从而在科技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经院哲学和宗教迷信不能给人幸福
培根的科技伦理思想是从反对经院哲学、宗教迷信和尊重科学技术出发的。在中世纪,基督教崇神贬人,反对研究自然、学习科学,要求人们禁欲赎罪,以求天国之乐,万世之福。培根虽然口头上对基督教表示出相当的虔诚态度,甚至说来世的幸福是最高的幸福,但实际上他关心的却是现世幸福。因此,他抨击迷信而肯定无神论,认为无神论“顺情合理,敬畏国法,爱惜令名,崇尚道德”;“既令不顾来世,犹使其谨慎自守”,故“从不危害各国”;而迷信则会解除此等美德,“使许多国家陷于混乱”。造成迷信的原因,“如绚烂夺目的礼节仪式,如过度伪善的外表圣洁,如对教会中不胜其烦的圣传之过分尊崇;如教士为满足野心与贪心所设置之种种诡计”,而经院学者则“虚构不少难以捉摸、曲折奥妙之公理与定理,以便文饰教会之措施”。(转引自周辅成《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577页。)
培根指出,宗教神学使人脱离自然,阻碍人类认识的发展,它象献身上帝的修女一样不能生育,使人厌恶。而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即精神与宇宙相结合,却可以使人类“产生一些发明,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类的贫困和灾难。”因此,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的响亮口号,认为利用科学知识和技艺,人就可以驾驭自然,利用自然,使之成为幸福的源泉和文明的基础。他说:“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就在于“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他以光比喻科学,“火使我们能够行路,能够读书,能够钻研方术,能够互相辨认,其功用固然是无限的,可是人们之见到光,这一点本身却比它那一切功用更为卓越和更为美好。同样,我们对事物进行思辨这件事本身,也是比各种发明的一切果实都更有价值。”(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 页)培根强调“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的合二为一”,认为人类的许多有价值的发明就是从这种结合中产生的。“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航行方面,第三种是在战争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的发现了。”(《新工具》第103 页)而人类就是受惠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发明的。
二、科学技术有重要的道德价值
培根认为科学技术包含着造福人类的力量,因而具有道德价值,而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的专家则是品德高尚的人,应该予以褒扬。他说:“我认为善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这也就是希腊人所谓‘仁’或者‘人道精神’,但意义还要深”;在他看来,“利人的品德”就是善,“这是人类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最伟大的一种”(《培根论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由此出发,培根进一步指出, 凡是“能够把实践导向对于人类最为有用的对象,或者能够使动作少用工具,或是能够节省质料和供应,那就应当认为是宝贵的事例”,也就是“统称为嘉惠的或仁慈的事例。”(《新工具》第239 页)科学家和发明家就是这种给人类带来利益的人。他说:“在所有能给予人类利益当中,我觉得没有比得上发现新技艺、天赋和商品来改善人生那样重大了。因为我看出在原始时代,粗鲁人民中发明者和发现者被尊为圣,被列为神。”在这里,培根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作为评价圣贤即科技道德理想人格的根据与标准,这在当时封建神学思想浓厚的条件下是很不寻常的,是要有理论勇气的。
培根指出,历代之所以“对于发明家酬以神圣的尊荣,而对于功在国家的人们(如城国和帝国的创建者、立法者,拯救国家于长期祸患的人、铲除暴君者以及此类等人)则至高不过谥以英雄的尊号”,因为把二者加以比较,一是“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及于个别地方;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千秋;此外,国政方面的改革罕能不经暴力与混乱而告实现,而发现则本身便带有福祉,其嘉惠人类也不会对任何人引起伤害与痛苦。”二是在发明者所提供的成果中,包含着更高,更普遍的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它“在自然界中燃起一道光芒——这道光芒在升起时就应该接触并照亮界限着我们现有知识范围的所有边缘地域;并这样越散布越广,不久就应该揭开并使人看出世界上一切最隐蔽最秘密的东西——这个人(我以为)就会真正是人类的恩主——把人类统治推及于全宇宙的传播者、自由的战士、贫困的征服者和抑制者。”培根把技术发明家称为人类的恩主、贫困的征服者,赞誉他们的功德永垂,这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思想家如此褒扬过,而在他之后,这样的推崇也并不多见。
培根还把科学技术的进步,视作实现新的社会生活乃至包括道德在内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杠杆和起点,他指出:在欧洲最文明的地区和新印度落后地方的人类生活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无关于土壤,无关于气候,也无关于人种,只在于方术。”(《新工具》,第103 页)培根在他未完成的著作《新大西岛》中,描写了他所憧憬的人类理想社会与人类未来的“黄金时代”:到那时,社会将由掌握了高度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所管理,人人都能学习与利用科学技术为社会造福,所以物质生活富裕,精神文明不断提高。他指出,通过教育和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人类能逐步进入这个美好的时代。
培根也预计到科学技术被错误地运用会造成的不良后果。但他认为,这不能成为否定科学技术道德功能的理由:“若有人以方术和科学会被滥用到邪恶、奢侈等等的目的为理由来加以反对,请人们也不要为这种说法所动。因为若是那样说,则是对人世一切美德如智慧、勇气、力量、美丽、财富、光本身以及其他也莫不可同样加以反对了。”他认为,科学技术如何运用问题,“自有健全的理性和真正的宗教来加以管理。”(《新工具》第104页)
三、为伦理道德寻求科学的依据
培根的伦理思想,是以具体的知识为依据的。他认为,每个事物都包含着整体的善和整体组成部分的善两重善性。两者相比,整体的善程度较高,价值较大。他用自然科学中物体的吸引力、向心力来说明物体的善性。如“铁在受了小的吸力时,就趋向于磁石;可是铁如果超出某种数量,它就抛弃对于磁石的爱力,仿佛一个忠贞爱国者一样向着地球移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551 页)但地球又被宇宙更大的天体所吸引,所以地球上的物体或水又有脱离地心引力而趋向宇宙天体。这似乎又是“为了尽它们对宇宙的职责,而抛弃了它们对地球的职责。”(同上书,第551页)这说明, 力小者必然被力大者吸引而趋向大者,故部分的善必然趋向于整体的善。“善德的这种双重性,和其轻重高低,更铭刻在人身上,如果他不是堕落的话。”据此,培根认为公共的善或一般的善高于私人的善或特殊的善,具有更高的价值,因而“力守对公家的职责,比维持生命的存在,更其珍贵得多。”(同上书,第554页)维护公共利益、人类利益,这是善的根本, 故“我们在谋求公益时,纵然达不到良善有德的目标,那也比任意动用自己财产,为自己求得一切想欲罗致的事物,要幸福的多。……存心忠良,不论成败,总可使人永享珍馐,有甚于一切可以称心如意的丰光美景。(同上书,第554页)他之所以推崇科学家、发明家, 就是因为他们能给社会带来公共利益。
培根还采用与动、植物的一些特性相类比的方法,描述人的道德心态和品质。他说:一个人对他人的苦难若“表示慈悲,那就表示他的心田像一棵高贵的树一样,划破自己树皮,流出芳香来。如果他容易饶恕赦免人的罪过,那就表示他的心苗种到高处,受不到侵犯,因而他不能被射中。”(同上书,第576页)他把“猜疑之心”比作蝙蝠; 把自私的报复比作蔓草,“是野性的产物”。认为自私自利者的所谓聪明,其实是一种老鼠、狐狸式的聪明,是“在即将吞噬落入口中的猎物时,却假装悲哀流泪鳄鱼式的聪明。”这种小聪明到头来终将成为“自己的牺牲品”(同上书,第64—65页)。培根又以人对自然物的态度,说明人的品性。他说:“向善的倾向可以说是人性所固有的。如果这种仁爱之心不施于人,也含施之于其他生物的。”如土耳其人对狗和鸟等动物就很仁慈;有个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由于戏弄一只鸟,“险些被当地人用石块击死”(《培根伦人生》第6页)。
培根把伦理道德与自然界的无生物与有生物联系起来,把对动物的态度纳入道德领域,固然还不能给伦理道德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不能揭示道德心理的本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使伦理学摆脱建立在对上帝信仰基础上的神秘主义,达到其“求教于自然”的目的,这对于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四、追求科学真理是人性中的最高品德
培根赞美真理而厌恶谬误,他把科学真理比作“平凡的日光”、“纯洁的明珠”,指出:“要追求真理,要信赖真理,这是人性中的最高品德。”也是人生的最高幸福,道德的最高价值。并引用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话说:“站在高岸上遥看颠簸于大海中的行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登于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后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障、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培根进而认为,一个人如果达到真理高峰而“不自满”,“心中充满对人类的博爱”,“永远围绕着真理的枢轴而转动,那么他虽在人间也就等于生活在天堂中了。”(《培根论人生》第2—3页)
培根把科学真理分为“理论的真理”与“实践的真理”两种。前者指对真理价值的正确认识,后者指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具有探索的欲望,怀疑的耐心,沉思的嗜好,断言的谨慎,重新考虑的果断,整理的仔细,……不损害新的东西,也不赞美旧的东西,并且痛恨一切欺诈”(同上书,第1页),而“光明正大”地去追求、去探索。 他指出:“探索真理是艰苦的”,应该以勇士的气魄,开拓的精神,去顽强地克服它,而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说:“自己完全是一个开荒者,既无他人的轨辙可循,也未得到任何人参加商讨”(培根《新工具》,第87页),国务又很繁忙,健康亦不很好,但还是走上了这条真路,决心用各种办法来做一番尝试。“我不能象那个孩子为追逐金苹果而跑上了岔道,我是要在这竞赛中倾一切赌注来博取方术对自然的胜利;我也不能犯急性病去刈割那尚未吐开的小草或谷穗,而是要等到适当的季节来得一场好收获。”(同上书,第91页)培根准备撰写一部论述科学知识原理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伟大的复兴》,此书由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近代科学的分类、解释自然的原则、经验材料的收集与实验、归纳法、全新科学的全新哲学等各部分构成,目的在于替人类把科学的基础打得更坚固些,把科学的界限推得更宽广些。这当然是宏大而艰巨的任务。培根虽然意识到这个计划在有生之年是难以完成的,但仍然认为,只要鞠躬尽力于中介性的工作,为后世播下一些较纯的真理的种籽,自己就尽到了开创这伟大事业的责任,就足够了。事实也是如此,他只完成了其中的两部分即《学术的促进》和《新工具》。不过,他献身科学的精神还是令人钦佩的,他最后也是因为在雪地里做科学实验——把雪塞入鸡肚以试验其防腐效果——受寒得病而去世的。
五、求知是品德修养的基本途径
培根认为“天性好比种子,它既能长成香花,也可能长成毒草,所以人应当时时检查, 以培养前者而拔除后者。 ”(《培根论人生》第22页)由“天性种子”论与知识就是力量出发,他提出了包括科学家、发明家在内的人的品德修养理论。在培根看来,人的天性种子所以会萌生出“香花”或“毒草”,是因为它内部存在趋善和向恶这两种对立的因素,依据条件的不同,或者形成仁爱、利人、爱人的德性,或者形成虚荣、急躁、固执、不逊乃至嫉妒和祸害的恶行。他重视培育善的根苗,更强调克除恶的倾向,认为“人们应当奉行社会职责,凡最能抵御一切艰难困苦的,才是身体的最好健康;同样,凡能抵御最大诱惑和干拢的,才是心灵的最好健康。”(周辅成《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554页)其办法主要是求知学习:“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 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这里讲的“知”,包括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范围很广。他说:“读书使人的头脑充实,讨论使人明辨是非,作笔记则能使知识精确。”“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辨。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同上书,第13—14页)
求知所以能提高人的品质,是因为读书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改造自身的过程。一方面,坚持读书的人一般都有正确的态度与纯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培根指出:“一个人既然立定诚实善良的目标,又能坚定有恒,忠于那些目的,那末,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将同时把自己陶冶得契合于一切德性。”(《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572 页)当然出于自欺欺人的“装璜门面”或“吹嘘炫耀”而去读书,既不能持久,也不会真正有收获。另外,“狡诈者轻鄙学问”,谬误能迎合人的恶劣的天性,不读书又冒充博学多知的人,必定十分狡黠。无知而又不求知的人往往是与无德相关联的。另一方面,“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如学习教学,可以使思维不集中的人集中;“强迫自己遵守固定时间”去学习最不喜欢的学科,可以培养毅力;“阅读历史、格言或观察自然”,有助于“克服嫉妒、暴躁以至埋在心里的怒火,积郁不解的思考,无节制的狂欢,内心的隐痛”,而“保持一种怀有希望、愉快、明朗、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总之,“种种头脑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治疗。”(《培根论人生》第14、22、18页)还应该指出,培根的“知”,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来自实际的,因而求知不光是读书,还包括“实习尝试”以检验修正知识本身的“真伪”,通过“实验”以“改进知识本身”。这个检验真伪与修正改进的过程,也是锤炼人们热爱真理的道德品质的过程。总之,知识对道德修养有重要价值,是道德的前提、基础,真理是致善之道,是人自我完善的手段。
培根认为,提高人的品德的具体途径与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风俗习惯尤其值得重视。因为“人的思考取决于动机,语言取决于学问和知识,而他们的行动,则多半取决于习惯。”(同上书,第12—13 、23页)在诸多习惯中,“一种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在这方面,他吸取了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道德教育的思想;有人问毕应如何教育子女,答曰:“让他在一个具有良好法制的社会中作一个好公民。”对此,培根发挥说:“如果有一个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养好的社会公民的。”(同上书,第25页)科学家是不能脱离社会的,科学家良好品德的培养,决不是仅仅求知所能解决的,也需要一个好的集体环境,社会环境的熏陶。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培根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他主张“二重真理论”,认为科学真理与神学真理应当互不干涉,这种说法固然有使科学摆脱宗教监督,争得独立地位的积极作用,但也反映了他与神学妥协的思想;他虽然研究了大量的自然现象,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对当时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不多,如其天文学理论是过时的,对杠杆率、物体加速度、血液循环近于无知,对吉尔伯特的磁石论的评价也有失公允,等等。当然,这并不影响培根在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他继承与发挥了毕达哥拉斯关于知识“最有力量”和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道德价值,重视科学实验、归纳逻辑的作用;重视职业道德和科学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心理对伦理道德的影响;他在1627年提出的关于成立“智者之家”的建议,促成了英国在1662年正式成立皇家学会。这表明,培根比同时代的伦理思想家和科学家、技术专家在总体上要高出一头,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更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