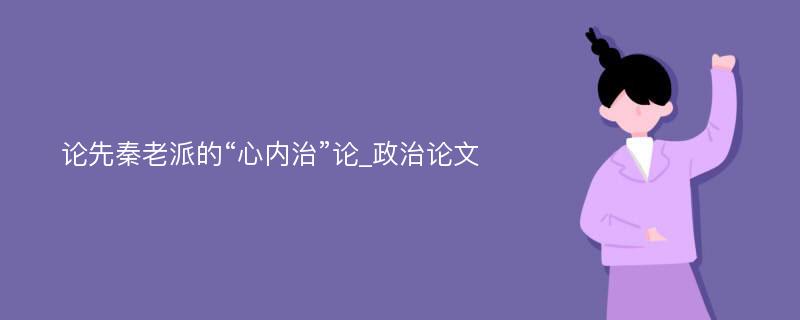
論先秦黃老之學“內聖治心”理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內聖治心论文,理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黃老之學是君人南面之術,其基本思路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將天道理論落實在現實治國操作中。與此同時,黃老之學指導君主通過“治心”——强身健體、净化心靈、體悟天道來使人君的身心也接近天道,符合天道。這種雙重修養,可以借用《莊子》中的“內聖外王”一語概括。修身治心,從而接近聖王,從而達到更高層次的“外王”。以天道爲標準的內聖與外王已成爲黃老之學政治理論中重要的一項內容,突出體現了黃老之學的君人南面理論內外兼修的追求。先秦黃老文獻中,無論是馬王堆《黃帝四經》①、《管子》四篇,還是《莊子》部份篇章,都對黃老之學內聖外王有精闢論述。本文重點關注黃老之學內聖治心理論的發展,間或涉及其外王理論。 內聖治心之道並非黃老之學所創。一直以來,“內聖外王”一語也被認爲是儒家思想範疇,因此學界總體傾向于結合儒家典籍及思想來討論“內聖外王”,而少有擴展其範圍至黃老之學的。雖曾有學者撰文論《莊子》及《老子》同內聖外王之關係②,但乃是就廣義道家而言,未嘗涉及到黃老之學的內容。 但“內聖”與“外王”確是黃老之學君人南面之術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其中的“內聖”部份,同儒家所講求的“仁”、“禮”等內容大有區別。黃老之學所主張的“內聖”,同其本身所主張的天道理論,推天事人的思路分不開,又提出了新的概念加以闡述,充分體現出獨特而實用的黃老道家學派特色。從“天道”出發最終落實到“法天而治”——兼顧治國與治心,治內與治外兩個方面。 一、“內聖外王”理論的出現 “內聖外王”一語在文獻中的出現雖然晚至戰國中後期,但古代聖賢修身爲政的傳統並不是新鮮事物。很早以來,人們便要求君主具備聖人之至德,並施之于外,是爲王者之善政。因此《莊子·天下》感嘆道:“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③這是對戰國社會現狀的一種無奈的評價。 考察“內聖外王”的淵源,可以從西周時期重要的概念“德”的字形發展來看。在甲骨文中,“德”字無“心”,西周金文則添加“心”部。這使得“德”之概念在周代有了內心修養之含義。西周“以德配天”的提出實際上同“內聖外王”有關。“德”在西周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概念。“德”强調統治者的政行懿德,有德的人纔配接受天命。“德”的概念在金文也很常見,“敬德”“恭德”“正德”“秉德”“懿德”“哲德”“孔德”“安德”“烈德”“介德”“明德”“元德”“首德”等用語都出現過。毛公鼎銘文有:“丕顯文武,皇天弘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可見,“德”政思想貫穿整個西周時代,其核心的含義是祖先與周天子的宏偉德業和美好德行。由于“德”政思想將人君所掌握的權力附以天然的道德優勢,因此人君要以先祖之德爲楷模,“以德配天”,方能保有上天所賜的權利,進而保有國家。“德”也就成爲西周時期人君修身治心的主要內容。在這個時期的文獻中雖然没有“內聖外王”的提法,但“內聖外王”的本質已經體現在“敬德”“保德”等思想中。 春秋時期,“修身”“治心”等術語已經出現,也廣泛被爲政治家所倡導,《論語》《左傳》《國語》等文獻皆有相當多的記載。而“修身”“治心”等內容也從抽象的“德”概念中抽離出來,修德的要求顯得更加具體。 此時期內,修德治心同“禮”關係密切,“禮,國之幹也”。政權得以穩定,國祚得以綿延,其根本在于維持“禮”,這一點成爲政治家們的共識。守禮亦是統治階層成員應盡的義務,禮是維持社會關係的準則,因此禮的起點,在于個人之修身。禮,可以細化至言動視聽,言動視聽合于禮,則無邪僻之事。“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④,《論語》記録孔子言論: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⑤ 無論是戒色、戒鬥或戒得,都屬于以禮來約束內心,提高個人的內在修養,這是孔子所謂“君子”的內涵之一,一國之君更應如此。廣而言之,以禮調整血氣,規範行爲,修身治心,是國運昌盛、理想平穩的根本所在。 正因如此,政治家們對人君感受聲色的耳、目、心、口等器官都做了種種要求,認爲耳目心口都要應經過禮儀的薰陶纔能達到理想狀態,否則便與蠻夷無二。《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富辰語:“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狄皆則之,四奸具矣。”⑥《國語·周語中》也載周襄王語云:“夫戎、狄,冒没輕諂,貪而不讓。其四氣不治,若禽獸焉。”⑦此處的“四氣”即指人的血氣與精神狀態,與上文所謂聾、昧、頑、囂屬于一種類型。若統治階層缺乏身心修養,便無法實現禮樂社會。 在身心修養中,養心治心最爲重要,晏子曾說:“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又說:“心平,德和。”⑧耳目口的感覺,皆要合于禮而爲養心服務,而“心平”纔能達到“成政”的目的。所以古人對味、音、色等給人以享樂的事物以諸多限制,《國語》載單穆公言論: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名。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明,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⑨ 人君從耳、目、口入手,每一舉一動能够符合“禮”的標準不逾矩,以求達到氣血平順的效果,最終“思慮純固”,纔能保證國體平穩安康。因此,人君不合禮的享樂要被臣下規諫,以防有礙政治。如《左傳》昭公九年載晋荀盈到齊國迎接齊女,歸來時死在戲陽,尚未下葬。當此時,晋文侯設宴飲酒,膳宰屠蒯認爲不合禮儀,因此進諫說:“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⑩屠蒯認爲,口味用來讓氣血流通,氣血用來充實意志,意志用來確定語言,語言用來發布命令。停棺未葬之時,不該進行宴樂,晋平侯此舉無疑是失當的,表面上滿足了口腹之欲,實際上以破壞了國家政令的和順。晋侯最後接納了屠蒯的進諫,說明他也認識到由耳目之欲而影響到君主之“令”的嚴重性。 以上文獻皆說明,從西周到春秋,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人的身心狀態,同德政之間有著异乎尋常的關係,尤其是人的行爲是否符合“禮”,對于治國是非常重要的。合禮,則耳目口鼻等皆能和諧順暢,人君血氣平順,聚而不逸,智慮清明,也能够在政治方面做出正確决策,保證國家的平安。政治家們强調修身養心,其目的不在于長生久視,而是落實在“政治”用途上。而這同黃老之學的學術品格亦有契合之處。這些從西周到春秋的治身之論雖尚未涉及黃老之學所提出的“形神觀”,但從“耳目口”到”心”的邏輯順序已基本完整,爲形神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統治者身心狀態同政治狀態的協調一致已成爲共識,有識之士已開始將這一理論貫徹在政治實踐中。 至諸子學派興起,百家之學都提出類似主張,因爲諸子學本身確如司馬談所言“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廣義而言,“外王”是諸子的共同目標。但完成這個目標的方法卻各异,這其中便包含以不同方式完成“內聖”的個人修善。换言之,以修身進而治心的過程成就個人,以此過程擴大而成就天下,這幾個階段在先秦每一學派中或明或暗都有所體現。具體到黃老之學也是這樣,諸多黃老文獻都涉及到“形神二元”的觀念,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形神”觀念也即討論形體、精神之間的辯證關係,如《管子·內業》中所謂:“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12)這是黃老之學在形神觀念上的典型代表。正是在這種認識基礎上,黃老之學進一步討論內聖之修身與治心的關係,具體指出血氣運行對精神狀態的影響,精神狀態對精氣灌注的影響,以及如何虛空內心,使人君達至“神明”的理想狀態。 二、《黃帝四經》:“天道”統攝、“內聖”修心 黃老之學的內聖治心理論,以其“道論”爲基礎。黃老學者認爲,“道”爲天地萬物的總根源,人君必須通過修身、養心、節欲,纔能使得人君的身體做好準備,最後引“道”或“精氣”進駐人心,從而獲得治國的思路與智慧。因此修養本身實乃人君得“道”的途徑之一。這在戰國及秦漢之際的《黃帝四經》、《管子》四篇及《莊子》等相關篇章中均有表現。 先從《黃帝四經》來看。《四經》的作者顯然對春秋時期所流行的修身理論非常熟悉,在《四經》中有很多此類文字,闡述氣血調整以及對人身的影響,進而對政治的影響。可見《四經》作者是接受、繼承這種傳統觀念的。如在《十大經》中,假托黃帝戰蚩尤的故事所重申的道理: 黃帝問閹冉曰:吾欲布施五正,焉止焉始?對曰: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後及外人。外內交絞,乃止于事之所成。黃帝曰:吾既正既靜,吾國家愈不定。若何?對曰:後中實而外正,何患不定?左執規,右執矩,何患天下?男女畢同,何患于國?五正既布,以司五明。左右執規,以待逆兵。(13) 黃帝輔臣閹冉提出,好的政治要從完善君主自身開始,“中正有度”即指人君完善自身。但黃帝疑惑爲何在“正”“靜”之後,政治仍没有取得相應的效果。“既正既靜”表示自身端正,寧静寡欲。因此閹冉再次規勸說只要“中實”而“外正”,也即內心平實安定,行爲端正,讓身體和心靈回復到“正”“靜”的狀態,使得自己的行爲毫無偏頗,必然能够“五正既布,以司五明”,討伐“逆兵”蚩尤也將取得勝利。 《黃帝四經》中黃帝的形象,是以黃老道家“無爲而無不爲”政治追求爲旨歸,因此黃帝所秉承的是一套法天事人的無爲之術,在政治上亦以“不争”爲“大争”。《五正》中描述黃帝爲取得政治上的成功,意欲“自知”,也即充分認識自己、克制自己。閹冉要求先“深伏于淵,以求內刑”,藏匿身形以求自我完善,之後纔能有效控制思想上的“争欲”,最後達到成功的人君的境界。他說:“怒者血氣也,争者外脂膚也。怒若不發浸廪是爲癰疽。後能去四者,枯骨何能争矣。”(14)在黃老之學看來,“怒”“争”雖皆是人之常情,但皆爲政治上的下策,不有意克制則會引發嚴重後果——身體上的癰疽,政治上的失敗。因此,聖人從身如枯骨做起,心静如水,淡泊自持,方能成就大業。因此黃帝果然“辭其國大夫,上于博望之山,談臥三年以自求也”。(15) 類似的理論在《經法·大分》中也有提出。《大分》篇將成功的君主稱之爲“知王術”者,“知王術者,驅騁馳獵而不禽荒,飲食喜樂而不湎康,玩好嬛好而好而不惑心,俱與天下用兵,費少而有功,戰勝而令行”。(16)在君王的生活中,田獵、宴飲、珍寶、女色皆爲常見事物,也是耗費精力之事,只有聖明君主纔能抵抗這些物質的誘惑,減少對心力之牽扯。 實際上,這種將人君的身體狀態和執政水準簡單聯繫的思路並非《黃帝四經》最典型的內聖治心之法,《黃帝四經》中對治心有更深入、豐富的討論。特別是對人的感知能力,黃老之學提出很高的要求。這已經約略涉及到黃老之學的“形神”觀念。 《黃帝四經》在很多篇章中提到聖人所必須具備的精微敏銳的感知,這既同春秋社會大家普遍認可的調整血氣、修身治心內聖模式有關,又是在此基礎上的發展。其突出之處,在于將耳目的能力也即人的認識基礎無限放大、提高。《道原》: 故唯聖人能察無形,能聽無聲。知虛之實,後能大虛。乃通天地之精,迥同而無間,周襲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謂能精。明者固能察極,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謂察稽知極。聖王用此,天下服。無好無惡,上用察極而民不迷惑。上虛下靜而道得其正。信能無欲,可爲民命;信能無事,則萬物周便。(17) 文中所謂的“察無形”“聽無聲”,實際是指用感知來“得道”,這種狀態可以稱之爲“精”。《黃帝四經》認爲人君需要認知人們所不能認知的東西,把握人們所不能把握的細節,這可以稱爲察知一切事物的至極。在這裏,人君需具有極强的感知力,達到“精”的狀態,纔能够“天下服”。正如《道法》所言,“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靜,至靜者聖。無私者智,至智者爲天下稽”。(18)可見在認知能力方面,黃老之學對人君的要求是具有超越性的。黃老之學已經不是在普通的口鼻耳目方面提出某種修養的方式,而是將整個修身養心上升至“道”的層次,耳目口鼻之“形”的虛空和敏銳,直接影響到精神狀態之“神”的得道與否。《經法·名理》: 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處于度之內而見于度之外者也。處于度之內者,不言而信;見于度之外者,言而不可易也。處于度之內者,靜而不可移也;見于度之外者,動而不可化也。靜而不移,動而不化,故曰神。神明者,見知之稽也。(19) 這一段明確闡述道,神明是人君“見知之稽”,也就是說,人君所具備的施政智慧,其來源在于神明。而此“神明”,又是源自“道”的,只有按照“道”的運轉規律和要求來修身、處世,纔能而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干擾,保持理性的判斷力。這段話是講爲人君基本之道,是黃老之學提出的治心要求。 爲此,在《黃帝四經》中,人君的治心至少從幾個方面提出了要求。比如要做到“貴柔守雌”,人君以靜、柔爲德,纔能够符合“道”的本性。《十大經·雌雄節》提出,“夫雄節而數得,是胃(謂)積英(殃)。凶憂重至,幾于死亡。雌節而數亡,是胃(謂)積德”(20),這同《經法·名理》的“虛静正聽”,“以剛爲柔者栝(活),以柔爲剛者伐。重柔者吉,重剛者滅”是一致的。(21)“虛静”“柔弱”是人君必備的心術修養。再如人君要“節儉省欲”,《經法·道法》認爲“道”的本性是“無執”“無處”“無爲”“無私”,貪私多欲與虛靜無爲的“道”背道而馳。再如人君必須言行相符,若言而無信則損傷大智,《經法·名理》提出,“若(諾)者,言之符也,已者言之絕也。己若(諾)不信,則知(智)大惑矣。已若(諾)必信,則處于度之內也”。(22)這些實際的做法雖然同春秋之際的政治家類似,但黃老之學的特殊之處在于,將這些修身治心的要求納入“天道”範疇,人君的一切修養有了超越的含義,黃老之學修身養心的特徵也就此體現。 三、《管子》四篇:形神兼備、內静外敬 人君的內聖治心理論在《管子》的《心術》(上、下)、《白心》及《內業》篇中得到相當充分的闡釋和發展。如果說《黃帝四經》的貢獻在于將修身治心統攝在天道之下,則《管子》四篇則在其中與“體道”的認知能力方面做了更精深的探索闡述,形成系統的黃老之學形神觀。由于“道”的超越不可感知,治心也即體道特別要通過修養的功夫,而非普通感官知覺的觀察。《管子·內業》: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因此,《管子》治心功夫扼要地說,可以概括爲“內靜外敬”。內靜外敬,一爲“虛欲去智”(23),一爲“正形飾德”。(24)透過這種形神兼修的功夫,人君纔可“體道”。實際上,爲了說明“道”灌注人心的過程,《管子》四篇還特意提出一個重要概念“精”來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論述。 “精”在《管子》四篇中有雙重含義:一是指赋予萬事萬物生命的“精氣”,擁有生命或靈性的物體便擁有“精氣”。如“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不和不生”。(25)在這層含義上,“精”是生命力的代名詞。第二層含義,是一種理想人格的精神狀態和道德水準。人君必須利用“心術”,修煉“內業”,力求“白心”,也即在“形”的方面完成必須的修養過程,纔能得到“精”,從而在“神”的方面完成修身治心的最高目標。 因此,《管子》四篇的治心理論,實爲通過收心斂性,使心靈達到虛靜、無爲的狀態,讓“精”更多進駐于心,藉助精氣的作用,從而使身心達到更高層次的修養,體悟“天道”的規律。“精”進駐人身是一系列的過程,《管子》四篇也提出了不同層次的要求。 《管子》四篇首先闡明了物質生活和情緒狀態等低層次之“形”對人的影響。《內業》多次講到“嚴容畏敬,精將自定”,“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26)作者主張調和人之體氣,透過端正體貌、言行、使得人欲望減少,耳目、四體、血氣等外在之“形”符合規矩,從而達到心神空虛之境界的。《內業》: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冱。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饑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饑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于四末。(27) 形神相互影響甚大,飲食、氣血這種形體上的變化會阻礙“精”的進駐。因此《管子》四篇在“形”的層面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靜之”。 正如《內業》所說:“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28)心中去欲內靜,外表自然泰然方正。無論“四體”或“九竅”,外在之“形”皆需“正靜”,只有如此,纔有可能“體道”,而具備成爲“聖人”的可能。 有了對外在之形的要求,《管子》四篇進而對“神”也即人的精神狀態加以關注。“神”涉及到各類感覺器官,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心”。《管子》四篇强調人君必須虛心净舍,纔能等待“精”氣充盈,完成“體道”之舉。 對于心,《管子》强調“虛”和“靜”。“虛”指去除欲望,擺脫成見,“靜”則是保持情緒上的平静。欲望、成見和情緒波動,都有可能導致不正當的喜怒哀樂之感,這些不正當的情感,是需要嚴格禁止的。 因此,《心術下》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29)《內業》又强調:“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30)人心天然就是“精舍”,如不爲外物所擾亂,自然“自充自盈,自生自成”,會有精氣進入。但當各種嗜欲引起的不正當情感充斥在“精舍”之中,自然無法攝精體道。《內業》: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毛泄,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31) 心裏有憂悲喜怒等過度的情緒,“道”也即“精”就無地可容。如能够去掉這些不正當的情感,心就能重新成爲“精舍”。因此說“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32)《內業》同時提出了做到“虛靜”和“無欲”的具體要求: 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征不醜。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33) 虛靜平實的心境,不同于毫無情感。《管子》認爲“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34),適度、正當的情感是可以存在的。只是當這些情感“失度”,纔要對它采取措施:節制“耳、目、口、鼻、心”五種情欲,除去“喜、怒”兩種凶事,平和中正、虛靜平實就可以占據胸懷了。“正”“靜”之後方能“定”,做到去欲内靜之後,身體器官和精神狀態都可以得到提升,能够四肢堅固,耳目聰明,則整個身心成爲可以吸引、容納“精”的容器。 至此,《管子》對內靜外敬、形神兼顧的辯證關係做了非常系統的論述,人君外在的一切都爲精氣的進駐做好了準備,外在的修養功夫做到了,內在的修養纔能得以提升。對于精氣的進駐,《心術上》也有詳實的闡釋: 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35)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36) 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37) 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于四極。(38) 治心至于虛空境地,引來精氣,留駐人體,“形神”俱能達到更高的層次。《管子·內業》又說“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無他圖”。(39)《內業》篇又强調“一意摶心”,精氣進駐後,精神要專注于內而不馳逐于外。完成了精氣進駐的人君,因此也具有了與世俗不同的宏大人格氣象,《內業》: 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40) 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人君在人格修養上同“天道”完全協調一致。這種狀態,《管子》也稱爲“全心”: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全心在中,不可蔽匿,知于形容,見于膚色。(41) 作爲君人南面術一部份,《管子》的“治心”突出體現了道家道法自然,虛静、無爲的本色。《白心》: 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周視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42) 這一段論述非常符合黃老之學的內聖外王的思路,人君必須要從對宇宙萬物的普遍觀察中,“周視六合,以考內身”,瞭解自身實際,驗證自身形態。天道與修身完全是一致的,只有這樣纔能體證大道之理,最後將對身心的修養落實到政治實踐中。 以上簡要分析了《管子》四篇的內聖治心理論。但《管子》的論述並没有結束,內聖進而外王,從修身來檢視治術,反過來,《管子》四篇又從另一個方向考察,由“治術”印證“治心”的重要,由治人事來說明治心的關鍵之處,這實際上還是在强調內聖的最終目的在于外王。黃老之學“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特徵,充分貫徹在《管子》四篇的心治理論中。而《管子》四篇的這種反向推論,也充分突顯了其黃老的學術品格。《心術上》曰: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43) 心之于人體相當于人君之于國家,九竅則類似百官。黃老在政治理論上主張人君無爲而治,下官各司其職,修身治心同樣如此。心要“無爲而制竅”,要能够使“官得守其分”。但不涉足“視聽之事”僅僅是“無爲”的一個方面。《管子》四篇還要求“心“去除情欲,去除私欲。無論是情欲還是私欲都會使得“心”無法發揮最高統治功能,使其背離道德標準。人君也是這樣,若處在私欲蒙蔽下,會因個人己見而無法洞悉事物的真相,在私心指導下,必然做出滿足個人利益之舉,最終會落得“上離其道,下失其事”的結果。 因此,作者從正反兩面論證了“內聖”和“外王”的辯證關係。“無爲”的治術,要建立在去除私欲的修養之上,去除私欲,進而達到無欲,無欲進而達到內心空明虛靜,內心空明的人君纔能洞悉治國的最高原理“天道”。此時的“無爲”,終于由身心修養轉化爲外治,從精神上的明道、識道,落實爲循理用道的政治措施。因此可以說,“無爲”不但是政治作爲,更是人君內心修養、得道的具體展現。不修練心術必然無法“無爲而制竅”。這也是《管子》黃老之學著力闡發心治,要求人君修煉內業以求白心的目標所在。 四、《莊子》黃老諸篇:“虛靜”養德 《莊子》外雜篇所包含的黃老篇目,主要集中在《天道》《在宥》《天地》《天運》《刻意》《繕性》等六篇中。《天道》諸篇並無《管子》那樣專門論述治心理論的篇章,但對治心的理論依然有涉及。得道之人注重修養內心,而天地之道是修養內心的重要準則,這是《天道》諸篇的基本認識。《天道》諸篇論述治心,也以“虛靜”“無爲”爲最高追求。《天道》: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44) 修煉者心境虛靜無爲,便可同天地之道保持一致。“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45)“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46)從天地人同源同構的起點出發,天地的清静無爲很容易成爲修煉者效仿的對象。《在宥》記載黃帝向廣成子求索長生久視,廣成子提出:“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47)云將向鴻蒙請教治道,鴻蒙要求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48)这些都體現了虛靜無爲的準則。 《天道》諸篇同樣是出于治心與治國的密切關係而提出修身養性的做法。《天道》認爲: 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49) “聖人”即指人君,“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人君從內心發出的一舉一動,無不關乎天下萬物,人君必精于治心的原因即在于此。《天地》中借孔子之口說:“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50)形神皆“全”,纔能成爲“聖人之道”。《天地》描述“王德”: 夫王德之人,素逝世耻通于事,立于本原,而知通于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采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51) 內心的修養,能够通過其形體外在表現出來,因此“其心之出,有物采之”。而“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又說明內心與外在的修養,皆以“道”和“德”爲準則。如此,纔能達到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萬物從之的效果。 “內聖外王”在文獻中的提出雖然晚至《莊子·天下》篇,但其精神實質出現得非常之早。西周時期的“保德”、“明德”,將周天子掌管國家的權力同祖先和天子本人的宏偉德業及美好德行相聯繫,認爲人君缺乏“德”便失去權力的有效性,這可以理解爲最原始的“內聖外王”思路。 春秋至戰國時期,“德”之概念日益具體化,“修身”“治心”等內容已經逐漸從中抽離出來,作爲對人君的具體要求而提出。這一時期修德治心同“禮”關係密切。人君的舉動不逾禮,方能在身體上達至氣血平順,思慮純固,從而政治方面做出正確决策,保證國體安康。 黃老之學是先秦諸子學術的一支,同樣有符合自己學術品格的“內聖外王”理論。黃老之學重在“推天道以明人事”,對人君的修養要求則重在“體道”。因此《黃帝四經》中的“內聖”理論,不僅承襲了春秋時期調整氣血以對人身產生積極影響,進而利于政治的傳統,同時特別在“天道”統攝下,從“形”“神”二元角度對內聖治心做出闡述。人君要在耳目口鼻等具體之“形”的層次上做到虛空和敏銳,方能至“精”,方能體“道”,方能以“道”修身、處世,方能而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干擾,在施政時保持理性的判斷力。 如果說《黃帝四經》已經體現出黃老之學形神分論“內聖外王”思路,那麼在《管子》四篇中,作者已經對“內聖治心”做了精深的思考,並且形成了體系。《管子》四篇專門討論“內聖治心”,提出“體道”的過程,是“精”進駐人心的過程。人君通過收斂外在形體,使心靈達到虛靜無爲的狀態,纔能讓“精”更多進駐于心,藉助精氣的作用,體悟“天道”。“心”爲“精舍”,要去欲內静方得引精。因此《管子》四篇從形神兩方面做出要求,對外要“正形飾德”,對內要“虛欲去智”,“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静,心不治”。(52)如此,人君纔能在人格修養上同“天道”完全協調一致,達到“全心”的境界。這種攝取精氣體道的內聖理論,在黃老之學內聖心治理論中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不但超越了春秋時期僅從外在形體修養談論治術的思路,同時也對《黃帝四經》較爲簡單的“形神分論”內聖治心進行了極大的豐富,黃老之學的形神二元論在《管子》四篇中體現得非常鮮明。可以說,《管子》四篇的“內靜外敬”治心思路是黃老之學對先秦“內聖外王”理論的一大貢獻。 《莊子》一書的學術傾向較爲複雜,在其外雜篇中包含有黃老之學的思想,但尚未自成系統。因此,在《莊子·天道》諸篇的內聖治心理論,整體體現出道家黃老之學無爲而治的學術旨歸,主張“虛”“靜”以養德,德全則爲“聖人”。 由此我們大體能够看出先秦黃老之學內聖治心理論的發展脉絡,其理論基礎仍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內聖”的目的是“外王”,“內聖”的途徑是“體道”,“體道”則需身體的靜、定、少欲,內心的虛、空、無情。這種內聖,既不同于原始道家注重長生久視的養生之道,也不同于儒家《詩》《書》教化的修養方式,是獨屬于黃老之學的內聖外王之道。 ①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是否《漢書·藝文志》載録的《黃帝四經》尚無統一定論,本文爲簡省,暫且將其稱之爲《黃帝四經》。 ②蕭漢明:《論莊子的內聖外王之道》,《武漢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陳球柏:《內聖外王之道:〈郭簡·老子〉的主題》,《哲學研究》2004年第1期。 ③王先謙撰:《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88頁。 ④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顏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7頁。 ⑤《論語注疏·季氏》,第258頁。 ⑥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僖公二十四年》,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25頁。 ⑦徐元誥撰:《國語集解·周語中》,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8頁。 ⑧《春秋左傳注·昭公二十年》,第1420頁。 ⑨《國語集解·周語下》,第109頁。 ⑩《春秋左傳注》,第1312頁。 (11)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485頁。 (12)黎翔鳳撰:《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945頁。 (13)《馬王堆帛書》(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5頁。 (14)《馬王堆帛書》(一),第65頁。 (15)同上,第65頁。 (16)同上,第49頁。 (17)同上,第87頁。 (18)同上,第43頁。 (19)同上,第58頁。 (20)《馬王堆帛書》(一),第70頁。 (21)同上,第43頁。 (22)同上,第58頁。 (23)《管子·心術上》云:“虛其欲,神將入舍。”《管子校注》,第759頁。 (24)《管子·心術下》云:“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管子校注》,第778頁。 (25)《管子校注》,第945頁。 (26)同上,第943頁。 (27)《管子校注》,第947~948頁。 (28)同上,第939頁。 (29)同上,第778頁。 (30)同上,第931頁。 (31)同上,第950頁。 (32)同上,第937頁。 (33)同上,第945頁。 (34)同上,第937頁。 (35)同上,第759頁。 (36)《管子校注》,第767頁。 (37)同上,第764頁。 (38)同上,第778頁。 (39)同上,第938頁。 (40)同上,第948頁。 (41)同上,第939頁。 (42)同上,第811頁。 (43)同上,第767頁。 (44)《莊子集解》,第113頁。 (45)同上。 (46)同上。 (47)同上,第94頁。 (48)同上,第95頁。 (49)同上,第114頁。 (50)同上,第107頁。 (51)同上,第101頁。 (52)《管子校注》,第9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