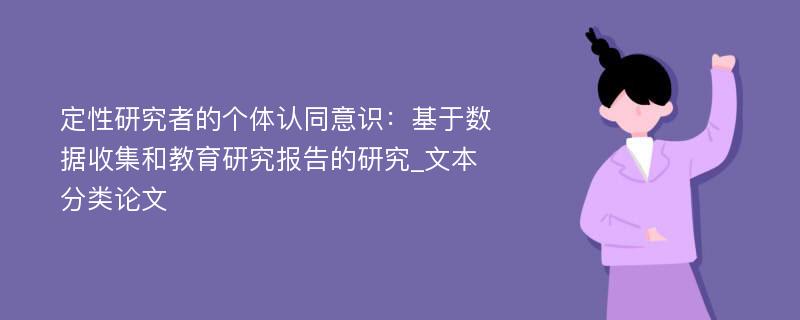
质性研究者个人身份的自觉——基于资料收集与教育质性研究报告撰写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者论文,研究报告论文,自觉论文,身份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人身份问题的提出
质性研究讲求实地研究资料的收集,要求研究者亲身体验研究地的日常生活。在教育质性研究中,研究者资料收集的常用手段集中在访谈、观察以及实物收集等。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预设性极强的过程:研究者事先准备好访谈提纲和观察量表,然后进行材料收集;而研究对象则按照要求呈现材料和行动。如果我们承认这个过程确实存在诸如“结构化”、“预设”等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研究者运用诸多手段收集资料的过程,其实就执行了一个个人意志与选择的过程。而后研究者才对这些材料进行编码、予以分析,并引出研究结论,撰写研究文本。这个编码、分析与引出研究报告的过程,同样是研究者个人选择与鉴别的过程,是研究者个人身份参与的过程。如果这样,那研究者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情景:所谓材料的收集抑或是研究文本的撰写,其实都是在研究的高度参与和控制下完成的,质性研究乃是一个“个人化”的研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提出个人身份自觉的概念。
所谓身份的自觉,是指研究者自我的身份意识,即对自我身份之于教育质性研究过程影响的体认以及自我重构的意识与觉察。教育质性研究乃是“一个带着丰富身体和生命经验的研究者在研究活动过程当中从事观察与体验同样带着丰富身体和生活经验的生活世界,作者之间是一个不断相互反身(mutually reflexive)和诠释(mutually hermeneutic)的过程”。①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走向身份的自觉,保持对研究者个人身份的敏感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分析质性研究者的个人身份问题,是把身份理论、伦理学理论以及质性研究理论运用于研究实践的尝试。这对于提高质性研究规范、摆脱实践的伦理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次,对于研究者本身而言,身份的自觉让其自身更加地明了。正如黄剑波所言:“我认为这种身份自觉其实关系到我们对于研究本身的意义的把握。就我看来,我们之所以对某一社会现象或宗教进行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和认识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对自我的认识过程……。”②
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一)制造同意的取向
一般而言,访谈成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直接交流的最主要形式,而观察则在另一个侧面支持和验证访谈的真实性,长期的、深入的实地生活和体验过程使研究具有合法性,由此带来了过程与结论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质疑的恰恰是这种客观性——即材料收集过程中其实隐含的“表演性”和“制造同意”的可能性。
访谈被认为是平等的。访谈者依据设计好的访谈提纲提出问题,访谈对象按照问题提供真实的信息。实地的观察也处于类似的状态,研究者按照设计好的观察指标与量表,运用参与式与非参与式的形式观察研究对象,并依据时间、关键事件或者其他分类的形式记录所观察的行为。可以说,无论是访谈还是观察,研究双方都是处在一个平等交流的互动环境之中的。但事实上,这种平等在后现代视域下并不能得到承认,后现代学者强调这个过程乃是一个创造“标准现代主体”的过程。即由于访谈、观察都是结构性很强的预设,被访谈者在“参与”、“互动”的形式下其实不得不忍受“规范性”、“约束性”和“远离日常经验”而带来的“伤害”。而在女性主义看来,这种互动不过是研究者引导研究对象“表演”的过程,是引导研究对象与主流文化模式吻合的过程,而一旦研究对象存在“反抗”,研究者的强势文化与文化暗示便会出现,并在访谈与观察的结构性中得到部分的呈现。这其实就好似一个“共谋”意图与“同意”的“制造”。保罗·拉比诺就曾指出这种在田野作业中“制造同意”的知识生产方式:“事实(fact)是被制造出来的——这个词语来自拉丁语factum,是制作、制造的意思——我们所阐释的事实是被制作,并且被重新制造。”③
(二)实地记录
在研究过程受到强烈批判之后,再讨论研究者在实地研究中所作出的实地记录,似乎有些牵强和多余。过程既然是“制造同意”的过程,那么实地记录必然也是“制造同意”的记录而已。在这里,我们并不需要持有这样坚决否定的态度,而明智的做法在于承认实地研究中个人的高度渗入,并予以分析和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在后现代思潮盛行的时代,质性研究依然不减魅力的原因所在。研究者没有必要因为“自我”成为实地记录中的一部分而焦虑。
实地记录作为一种研究手段与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实地生活的现实场景,为研究者的后期写作提供了最根本的材料。实地记录具有连接和唤起的功能,连接实地研究中碎片化的记录,唤起研究者内心曾有的感悟和记忆。其实,在研究者看来,实地记录其实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是精心写作、编排和润泽的过程。在写作的形式上,它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形式,比如,日记体或者是自传体。虽有文学的形式,并且只能通过文学的形式,但是在时间、情节与事件上,实地记录与文学作品相距甚远。在实地记录中,研究者不仅仅记录研究对象,也记录自我的亲历和感受,是有价值的文献。
在肯定实地记录情节的真实性的同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实地记录的个性化和私人性。质性研究是带有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研究,实地记录在含有集体研究信息的同时,还是一个极度个性化和私人化的记录。实地记录当中有研究事件的记录,也有个人反思的故事,当然也会有一些晦涩模糊的个人化语言以及情感宣泄的话语。作为实地研究的资料,它是有价值的,它不仅是研究者实地活动的记录载体,也是研究者反思的载体,还是研究者情感排遣的基本途径。而更重要的是,它及时记录了研究者一闪而过的“幽灵”,渗入了研究者的个人理解而成为研究的重要资源。实地记录是质性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活性元素,并作为一种互文性联系而最终展现质性研究的魅力和价值。
(三)回忆实地
依据实地记录回忆实地研究同样是一种资料整理和分析的手段和过程。如果说实地记录真实地再现了研究现场的话,那么回忆则把这些场景进行了个人化的处理,并最终形成一种整体的记忆储存于研究者的脑海,继而又自觉地隐射到研究文本的撰写之中。回忆实地其实也是一个个人高度参与的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个感性实地研究者来说来说。对于感性研究者而言,研究过程是一个浪漫的过程。阿曼达·科菲下面这段话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把自己的实地研究过程当做是一场浪漫的邂逅,一段难忘的爱恋。
我们的恋爱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我们不期而遇,并马上意识到我们的相遇另有意味……是吸引力,不,是好奇。我对我见到的既好奇又谨慎,既渴望交往,又害怕陷得太深……我注视着你,观察着你……有时,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很特别,又愉快又激动,我共同感受新事物……我们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之间会有暴风雨,但我们确实有发生争执的时候……和你在一起我感到愉快、兴奋、紧张、开心、值得……最后,我们都意识到,我们必须结束了,……我们之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太多的喜爱,太多的分享和太多的失落,但我们之间没有恨……
阿曼达·科菲把一段质性研究的过程比拟成为一场感情由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其中渗入的个人取向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实地研究的真实事件构成了研究者回忆的基础,但记忆也同样与研究者的情感体验等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记忆是实地研究的情感性与经验性的呈现。
三、文本的撰写
(一)文本与现实
关于文本与现实的讨论,其实就是承认了文本写作中可能存在的与现实之间的交互问题。文本的写作,其实是一个挑选、收集、初步写作与加工润色的过程。在质性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不断透过概念与符号系统来记录与理解实地,最终形成文本。事实是,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质性研究文本的写作都难以避免陷入多种关系的雷区。陈向明就明确提出过“写作是思考,写作是对现实的建构,写作是权力和特权”等命题。这些命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所谓的中立、客观而全然的掌握与描述实地所形成的文本并不是唯一的真实。文本其实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建构和表征,不能也无法等同于社会现实。这就牵涉到研究者对所谓的“现实”和“虚构”的认识问题。
不言而喻,质性研究是承认社会现象的价值性,也承认研究者的个人的涉入,并承认研究者个人因素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的重点就在于如何看待这种“建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建构”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虚假?“虚假”是假想、捏造和篡改,是毫无根据的情节间的联系。而建构强调的是反映对象的可变动、暂时性与能动的特征。建构本身就意味着质性研究者承认了自己的文本只是某个历史场景的产物,它适合于解释和理解当下的研究对象在实地中某时某地的活动,当然这些是建立在研究者个人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文本的建构性质也提醒每位研究者:文本的写作,无非是一种把个人嵌入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与社会情境中而获得的个人理解,它的意义是可变动的、可挑战的、可否定的。第二,文本“建构”的合理性在哪里?这个问题和质性研究的特征联系在了一起。质性研究是一种人文性极强的研究,它所追求的所谓的真实和想象,与自然科学的真实与客观有着天壤之别。自然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其真实性与客观性,而人文科学的魅力在于其理解力与想象力。有一位研究者这样说:
人的生命是极其多彩的,无数的具体事件构成了每个人独特的生命历程。对于韩雪,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性,她的生活史对研究者来说永远也无法穷尽。基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有意识地引导其讲述与专业发展有关的内容……在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并标记对研究目的有意义的主题,然后书写韩雪的生命历程。文件资料是研究的重要的参照依据……但在研究韩雪生命历程资料的衔接和补缺上,有很多的帮本研究所搜集的资料,大略有以下几类:记事本、证书、参编书目、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记录、行政文件、网络日志、纪念册……(宋大伟,2006:8-9)
可见,在质性研究中资料的收集及使用,都依据研究者的需要进行,有着一定的建构框架,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解力。
如果说以上两点关于文本建构的合理性辩证还停留在质性研究特征之上的话,那么第三点理解则直接指向了文本本身。正因为文本的建构与虚构的特性,所以文本才有了想象与表达的空间。以下面一段教育叙事作品的描述为例:
在陶川的博客世界中,我已经习惯了沉浸在她的文字中,或读或想,或喜或悲……她的篇篇美文化成袅袅音符轻舞飞扬,而思悟,如一点一滴,不舍其小,汇成汪洋,惠泽每一颗渴望进取的心。……这不停的积累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陶川丰富明敏的成长轨迹……而博客也留下了她在岁月征程中的足迹。……当我读着那些充满生命与活力的故事时,我感受到属于陶川的快乐,我的心灵再一次地受到洗礼……(叶莉洁,2007:56)
文本的建构不是凭空捏造之举抑或是无病呻吟的作秀,文本的写作基于最真实的生活情节,基于最朴实的个人情感,而作者想象力的发挥也不是天马行空的作为,其中的个人真挚情感与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基于真实的材料而建构,由此带来的想象则是研究者基于对现场感知以及专业知识的自我心灵的飞翔。
(二)文本与自我
由于文本的建构性,使研究者在其中的出现成为合理。研究者完全可以说:这是“我”写的。“这是我写的”这一表达其实就暗含了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首先,“我”的身份得到了承认。在教育研究中,“我”一般是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而存在的,必须在研究报告中隐身或者消失。而“我”一旦出现,其实就挑战了科学研究的权威。事实上,我们需要呼唤质性研究者在文本中现身,“现身”乃是研究的必然。
很多情况下,我像是一个不能很好表达自我的小孩儿,在既有理论和我自己的解释前惘然选择着表达方式及内容。我承认在既有理论面前,我有些怯于说出我自己的语言,唯恐前言不遮后语,或是一味自我感觉良好。很多时候以一读二改三删的形式把我自己的话隐藏起来。或许这是一种缺乏话语权利的病症表现。但很多时候我还是舍不得将我的所思所想改头换面,我自己的思想是我研究过程基于事实的思维闪动的轨点,没有它们,也就没有我的质的研究的存在,我会彻底成为失语者。(唐芬芬,2002)
质性研究主张研究者在研究文本中“现身”而不是“裸身”。台湾学者蔡敏玲曾提及“裸身”,意指研究者身份的过度膨胀而给质性研究和叙事写作带来的困境:“研究者对自我的叙说,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如果这些关于自身种种的叙说和报告中的其他叙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读来就像是作者突然跳了出来,专注地观看着自己,似乎忘了要做的事,搁置了要说的故事。”④
其次,“我”只是历史时空和研究情境中的我。质性研究文本向来都有两种身份,“小说的身份”和“文献的身份”。之所以存在两种身份,其原因就在于文本写作中的“我”与“情节”之间的互动关系。叙事作品有主人公、有场地、有故事情节,这三个要素是存在于历史时空和具体情境之中。至于文献身份,主要是基于三要素的真实性而言。无论是作为小说身份抑或是文献身份,研究者个人都是处于历史时空和研究情景之中的,这是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必然联系。
第三,文本写作之于“我”。文本对于研究者意味着什么?在文本写作中,研究者的个人情感投入其中,“我”的写作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生命经历的诉说,是一种对于自我生命的印证。如果这个“实地——个人——自我”的完整的过程就是文本写作的全部过程的话,那“我”更愿意把这个写作的过程看成是回忆一起走过的日子的过程。
四、走向书写的自觉
在文本写作中,研究者应该形成自觉:文本写作从来都不能脱离研究者的个人因素而独立产生;文本写作从来都不应该只是单一的形式;文本写作不应该被科学话语禁锢。这里不得不提到“修辞学的再发现”。阿曼达·科菲认为,启蒙运动让修辞学与科学相区分了,一边是科学、逻辑、推理、方法和证据的学问,另一边是说服、观点和修辞的学问。区分的结果之一是,修辞学一直被排挤在合法学术的边缘。⑤随着修辞学的再发现,不同文本写作方式也冲击着原有的认识,写作方式与客观性之间的冲突也受到了质疑。有学者明确提出:对已有的真实经历的修辞学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叙事的质量,而不是降低了其真实性。当前,在教育领域,已经有了很多不同于传统学术研究的书写范式和修辞学取向的作品,如耿娟娟、刘云杉、鞠玉翠、唐芬芬等对教育现场的描述。质性研究作品的写作需要研究者的自觉,不管是真实的原则抑或是情感的投入。
这还必须提及书写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果把书写看做是知识的生产的话,那么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书写就蕴含了一种知识的伦理,质性研究者的书写过程也应该关照此种伦理关系。知识的伦理指知识的生产、知识的地位与变迁而构成知识的伦理关系。质性研究强调将作为探究主体的经验、用意与主张展现出来,将研究对象的地方性知识挖掘出来,把情境互动与意义生成作为是质性研究的基本进路,力图反映人类认识的多样性,这是走向书写自觉的重要过程。
注释:
①周平.诸法皆空:质性研究与知识想象[EB/OL].http://www.docin.com/p-4132210.html
②黄剑波.身份自觉:经验性宗教研究的田野工作反思[J].广西民族研究,2008(11)
③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3.
④蔡敏玲.教育质性研究报告的书写:我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认真与想象[EB/OL].http://www.dabuluo.com/xxdj/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05
⑤阿曼达·科菲.人种学研究者剖析:实地研究与研究者身份[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