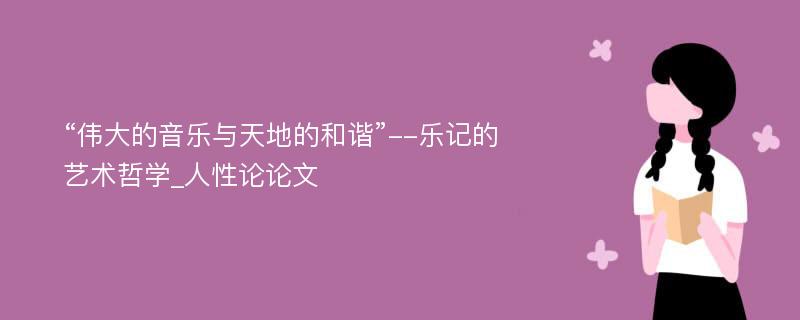
“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大乐论文,同和论文,艺术论文,天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乐记》的出现,是儒家艺术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的艺术理论专著。孔孟论乐只涉及乐的教化作用,强调乐的道德意义而对乐本身却不甚了了,诸如乐何以产生,乐的形式创作和基本性质,可以说都未涉及。荀子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论述,尤其对乐的根源和本质的论述是对孔孟礼乐思想的重大突破,但对其他方面的认识仍然比较笼统。《乐记》继承了荀子的基本观点,对乐的根源、本质以及形式创造、审美特征、礼乐关系等都作了具体、深入的论述,极大地发展和完善了儒家的艺术思想,对儒家艺术哲学的构建作出卓越的贡献。
一、人性论与乐的本源
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从孟子性善说开始,经过荀子性恶论的反驳,至《乐记》则加以折衷、综合,使人性论思想得以逐步发展和完善。这正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有人认为,《乐记》的人性论思想完全接受了荀子性恶论的观点(注: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页。)。这一看法是值得斟酌的。《乐记》的人性论思想受到荀子性恶说的影响,当无问题。甚至还可以说,《乐记》从荀子性恶论中汲取了一系列观点,乃至直接重复荀子的说法。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乐记》也从孟子的性善说中汲取营养,甚至也汲取了庄子的某些看法,经过扬弃、综合,而建立了自己的人性论,纠正了荀子人性论上的自相矛盾之处,避免了孟、荀的极端之论,使儒家的人性论更加稳妥,内容也更加丰富。
首先,《乐记》用“静”与“动”两个概念,把“性”与“情”、“欲”区别开来,认为性是静的,即潜在的存在,无所谓善恶,实际上认为性是善的(详下)。性受到外物的刺激便由静而变为动,性动则为情和欲,只有这时才有可能成为恶。这与荀子把性、欲、情浑称为恶,显然是不同的。《乐本》篇云: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乐记》认为,人性是天生的,这与孟、荀的看法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乐记》没有说是善或是恶,而是说它是“静”的。“静”是什么意思?就是未受外物摇动时的一种自足而平静的状态。有人认为,《乐记》中“静”也是从荀子那里接受过来的,因为荀子也用过“天静”这一概念。“人何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注:《荀子·解蔽》。)很显然,荀子的“静”,在这里说是知的根源——心——的一种状态,而没有和性联系起来。本文赞成另一种说法:“以‘静’来解释‘性’的观念,是起源于道家的庄子。庄子认为‘夫虚静怡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篇)‘静是万物之本,自然也是人性之根本。庄子认为‘静’对人而言,就是‘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天道》篇)所以用‘清净无为’为本心,来解释人性的根本,这原是道家的说法,可见《乐记》的‘人性论’乃受庄子思想之影响。”(注:林安宏:《儒家礼乐之道德思想》,天津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这一说法是有说服力的,也是有历史根据的。战国末期至秦汉时代,先秦诸子思想已从对立、争辨而走向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因而出现了杂家之作《吕氏春秋》,以道家为主又明显汲取儒家思想的《淮南子》,以儒家为主又明显汲取道家思想的《乐记》正是儒道互渗互补又一结晶。甚至可以说,荀子的“虚壹而静”很可能是接受庄子思想影响的结果。
其次,《乐记》的人性论的形成,一方面受到荀子性恶说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对情欲的分析;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孟子性善说的某些观点,突出地表现在对心的看法。先看《乐记》对情欲的分析: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失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脇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注:《乐记·乐本》。)
以上所列举的乱事恶行,都是以末受限制的情欲为根源,都是性恶(情欲)的缘故,因此情欲与天理是根本对立的。这明显是对荀子性恶论的发挥。但性、情、欲三者荀子并未加以严格区分,因而也都是恶的根源。《乐记》与荀子不同用“静”与“动”把性与情、欲区别开来,只认为情、欲是恶的根源,是性感于物而动的结果,而性本身如何,《乐记》没有明确其或善或恶的性质,这是“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论断的情形。但《乐记·乐象》又云:“德,性之端也。”德是性表现,德是善的,因此可以推论性是善的,这与孟子的看法相近。此外,荀子认为,心是理智的根源,强调“心知”的方面。由心而知礼乐,使情、欲不成祸乱。孟子认为,心是道德、情感的根源,心的用法,有时是指道德情感本体,有时就是道德情感本身,“恻忍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里的心显然不是本体,而是道德情感表现。《乐记》中的“心”,多近于孟子,不同于荀子。如“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单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注:《乐记·乐本》。)“这里的“心”都是指“情”,既不是指“性”,也不是本体的“心”。《乐记》中凡与“动”、“感”连用之“心”,都不是指作为本体的“心”,而是指作为情感表现的“心”。作为本体的“心”是“静”的,此“心”可释为“性”;性是尚未动之心,是与外绝离的心。
要而言之,《乐记》认为,心静则为性,心动则为情欲。心为什么有动、静之别呢?根本原因在于,心是否与外物接触,是否受外物的刺激和诱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就是说,乐的产生不是来自人心一个方面,还必须有心外之物的发动,只有人心一方面仍是静的(性),唯有与外物接触才动感起来(情)。所以乐的产生不是单向度的,不是心自生的,而是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相交融相感应的结果。《乐记》最为全面地回答了艺术的根源。一方面,艺术是人的心灵表现,另一方面,这种心灵表现又不是凭空而起,而是受外刺激的结果;心与物相比,物更为根本。《乐记》的艺术根源论,不仅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而且是正确的,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二、乐的表现形式与审美特征
与乐的根源紧密相关的是乐的表现形式。《乐记》反复说“凡音者生于人心也”。但人心还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源”是“物”而不是“心”,是客观存在。是以感性世界为根源,以感性形式为表现。《乐本》开篇即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一个“动”字,一个“形”字,把乐的感性直观这一审美特征凸显出来。同是人的心理活动,知、意、情却明显的不同。情是“感”、“动”的,最能体现人的生命活动特点。艺术审美属于情感领域,其表现形式不是抽象的概念及其逻辑关系,也不同于道德行为。它是超越功利超越实在的一种实践活动。它不靠概念,不靠公式而靠“形”即由声音、表象、装饰及人体动作等所构成的具体形象、画面、场景来表现一种情感态度和意义。卡西尔说:“它(指艺术)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注:卡西尔:《人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艺术的创作心理因物而激发(情感),借感性形式而外化(形象),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感性活动,一种直接观照。它是一种形式创造,即精神创造实践活动,不同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从欣赏主体方面说,欣赏艺术是一种形式感,用席勒的话说是“形式冲动”,超越物质欲望之上,属于精神领域。
对于艺术创造活动过程,《乐本》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声”、“音”、“乐”三个概念,既紧密相联又处于不同的层次。三个层面又表现为两种区别。第一,声与音的区别,表明自然与人工、质料与形式美的区别。感于物而形子声的“声”包括人的声和器物的声,是人的情感的自然表现。自然的声不同于悦耳的音乐,一般的情感也不同于艺术的情感,它们只是构成艺术的“质料”。声有强弱高低长短的不同,是情感变动不居的表现。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对不同的声加以取舍、重构和美化,即《乐记》所说的“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以及“声成文”的过程,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造型”(马克思语),变自然之声为有节奏有韵律之声,如《乐象》所说的“文采节奏,声之饰也”。从而才成为“音”。这里的“音”,释为音乐或形式美或美的形式,都能讲得能。第二,音与乐的区别,是音乐与戏剧表演的区别。声与音的区别是自然与艺术的区别,音与乐的区别是艺术之间的区别。这后一个区别,也包括形式与艺术的区别。因为纯粹的音乐和形式美,都是由极为抽象的形式构成的,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社会内容,其意义是朦胧的,因而在《乐记》作者看来“音”与既有歌诗,又有乐器演奏和舞蹈表演的“乐”是很不相同的。《乐象》云:“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内容含量以及教化效果上看,乐都是音无与伦比的。乐是一种综合体艺术,也是中国的元艺术。
《乐记》关于声、音、乐的区分,不仅概述了艺术创作过程,同时也说明了艺术的文化意义。《乐记》认为,音与乐是人类独创的一种文化形式,对音、乐的性质认识和把握如何,是区分有无人性的人性高低的重要标志。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注:《乐记·乐本》。)。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没有涉及“感于物”的方面。因为这段话主要不是谈艺术创造,而是谈艺术鉴赏。艺术鉴赏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动物是不知音的。“知音”是人性的表现,只知声而不知音是一种自然本能反应,人和动物在这里没有区别。但是从艺术创作的欣赏上说,知声又是最基本要求,只有知声,才能知音,才能进入艺术境界。《乐记》把人的生理本能看作艺术最起码的条件,生理本能和心理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很强调“审声”的基础工作。只有“审声”,才能“审音”、“审乐”。当然,“能乐”惟有君子,众庶是达不到的,这有《乐者》作者的政治偏见。如果去掉这种政治偏见,认为艺术创作是少数人的专门才能,而非众庶之能事,这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乐记》的一个可贵之处,是非常重视美感形式和形式美的创造,对美感形式是形式美的性质、功能和文化意义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形式美和美感形式,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僵死的,而是可感的,有意味的。这是因为:“艺术家不仅必须感受事物的‘内在的意义’和它们的道德生命,他还必须给他的感情以外形。艺术想象最高最独特的力量表现在这后一种活动中。外形化意味着不只是体现在看得见或摸得着的某种特殊的物质媒介如粘土、青铜、大理石中,而是体现在激发美感的形式中:韵律、色调、线条和布局以及具有立体感的造型。在艺术品中,正是这些形式的结构、平衡和秩序感染了我们。”(注:卡西尔:《人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艺术家“还必须给他的感情以外形”,卡西尔所强调的“这后一种活动”,也是《乐记》所反复强调的。然而,这一点又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原因是《乐记》把艺术形式变成了礼的附丽物,变成道德政治的工具,从而取消了艺术的独立地位。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为什么不从另一方面想想,《乐记》也把伦理政治艺术形式化了,把礼仪变成了形式美。“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铁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注:《乐记·乐化》。)“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乾,礼乐之谓也。”(注:《乐记·乐论》。)为治国安民和友爱邻邦和提倡礼乐教化,尽可能避免征战杀伐,这反映了人类的美好愿望与理想,而这正是通过艺术形式创造,通过对形式美的充分运用而实现的。《乐言》篇云: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群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这些都在说明,多样性的感性形式,正是人的丰富情感的外在表现;而不同的感性形式,则影响着人们产生不同的情绪,所以形式创造关系民心,不可不慎重对待。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机械地理解“内容决定形式”、“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等结论,似乎觉得记住这些“公式”,艺术创作与欣赏便不成问题,因而对于形式、技巧问题,反而可以不闻不问了。这是十分有害的。从《乐记》对艺术形式的重视和精炼的论述,应该得到启示。西方近代,从康德以来许多美学家也非常重视艺术形式问题,认为这是把握艺术根本特征和特殊规律的关键所在。这本是真知灼见,反而经常被“唯物主义”当作错误进行批判,在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因此有必要重伸一下关于艺术形式的美学观点:“如果艺术是享受的话,它不是对事物的享受,而是对形式的享受。喜爱形式是完全不同于喜爱事物和感性印象的。形式不可能只是被印到我们的心灵上,我们必须创造它们才能感受它们的美。……一个伟大的画家或音乐家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他对色彩或声音的敏感性,而在于他从这种静态的材料引发出动态的有生命的形式的力量。”(注:卡西尔:《人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三、乐的功能及礼乐关系
《乐记》认为乐的功能是巨大的,涉及的方面很广。从个体的情感宣泄到人格修养,从社会秩序的维护到政治伦理关系的协调,以及“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注:《乐记·乐论》。),处处都少不了乐。《乐记》对乐的功能的论述大都是在礼乐异同的比较中阐述的。“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注:《乐记·乐礼》。)“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注:《乐记·乐论》。)这就告诉人们,乐的功能虽是巨大的,但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条件的,在一定范围之内才有它的用武之地。具体地说,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礼乐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并且先王的礼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因时因地而制宜。这些都是正确认识乐的功能的理论前提。
首先,乐与人的身心健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古代的乐是音乐、诗歌、舞蹈浑一的综合体艺术。对乐的欣赏活动不仅要用“心”去“思”,去体验,而且还要用身体器官去表演,去参与。“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注:《乐记·乐论》。)这都是具有音乐节奏的舞蹈动作,形式上是一种美。不仅符合礼义规范,也健体强身。儒家从荀子开始,对于乐教的功能是生理与心理并重,强身与治心统一。《乐记》继承了荀子这一观点,认为:“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此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使耳目口鼻心知反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注:《乐记·乐象》。)可见,中国古代的礼乐教化是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礼乐教化只是道德政治教育。当然,道德政治是礼乐的主要内容和根本目的,但《乐记》认为,主要内容不是孤立存在的,根本目的的实现是与人的“耳目口鼻心知反体”顺正和血气顺畅是一致的。人心不顺,怨声载道,想用礼乐教化达到政治目的,那是不可能的。
所谓“反情以和其志”,即是指受外物刺激而动的情欲,经过乐的美感的熏陶、净化,又超越了实在物的诱惑而返归于平静(性),同时由于行为受到礼仪的规范调节,便和众人取得和谐一致,也就是“比类以成其行”之谓。经过这样的反复训练,潜移默化,便可使流动不居的情感形成为一种稳定而高尚的情操,使人养成为一种文明的习惯。这样,一切奸邪惰慢之气不会沾身。身心健康,血气顺畅,德行高雅,符合礼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注:《乐记·乐象》。)
在儒家的心目中,完美理想的人格是“圣人”,能达到“圣”的太少了。孟子甚至说五百年才能出一个圣人。比圣人次一等的,是君子。君子是人群中的模范人物,经过文化修养很多人都可成为君子。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论语·雍也》。)所谓:“文质彬彬”,就是天生资质和文化修养、内在精神实质和外在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统一。而文化修养的根本内容是礼乐。所以《乐记》说:“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化》篇云:
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
“易直子谅”是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意思,通过乐的感染、陶冶所达到的高尚品质。有了易直子谅之心必然产生安乐,“乐得反则安”,即达到心理平衡,心理平衡保持长久,便可返归天真本性而有精神。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反情以和其志”的过程。
其次,乐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是从个体开始的,因个体是构成社会群体的细胞,其素质的高低决定社会群体的凝聚力的大小和文明与否。如果个体保持一种和乐心理,人心自然也就向善,那么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群体和谐一致的目的也就水到渠成了。《乐情》篇说:“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乐记》接受荀子的观点,认为乐的实质是乐(lè)。这是从个体的心理需要角度而言,人人皆如此。但乐什么,乐到什么程度,个体的素质和文化修养的不同,却又大有区别。君子有君子之乐(乐道),小人有小人之乐(乐欲)。前者是高尚的精神之乐,是真正的自由之乐;后者是低级的官能之乐,是自私的、短暂的,必先乐而后苦,因为欲望无穷而能满足者极其有限。因此应该培养一种正确的快乐观,那就是:“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玄,乐终而德尊,君子的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注:《乐记·乐象》。)而圣人之乐又不同,不是“独乐其志”,即已超越个体心理之乐,以天下大化而乐。
第三,乐的功能,在其与礼的关系中更显得突出。乐与礼的关系问题,荀子已经提出来了,并进行了初步地论述,认为“乐合同,礼别异”。《乐记》充分发挥了这一基本看法,对于乐与礼的区别及其各自的性能、特点,进行较为细致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密切联系和统一目的进行论述。《乐记》的《乐论》篇以及《乐礼》、《乐施》、《乐象》、《乐情》、《乐化》诸篇,在论乐的功能时,大都是礼乐对举的。
乐与礼的性能是不同的,但却是互补的,即乐与礼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用不同方法对个体与社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但共同的目的又使它们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具体地说,一是既通过乐激发情欲,使人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并且“乐其所自生”,又要通过礼节制情欲,使之不放任自流,“反其所自始”。这就是“乐主其盈”、“礼主其减”之谓。一味地“减”而不“盈”,就要停顿,最终失去生命力;一味地“盈”而不“减”,就要“淫”,就要“放”,最终导致祸乱。“减”而能“进”,靠乐“盈”为动力;“盈”而能“返”靠礼“减”为导引,在这里礼乐相济,相反相成。二是从“内”、“外”的关系讲乐与礼的作用:乐是人的内在情感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不同于一般的情感表现,是通过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对情感有陶冶、净化的作用,这即是“乐由中出”、乐“动于内”的含义。而礼则是外在于人(个体)的反映形式,它是社会公理的表现,它的作用是从外部规范、引导人的行为,使之符合礼义,这即是“礼自外作”、礼“动于外”的含义。礼自外作也不是简单地强制,而是通过美感的形式使礼变成人们愿意接受的东西,从而启发人的自觉,甚至把社会公理通过美感教育而变成人的内在需求。这种内外结合,方圆兼施,目的是使人们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或者诱导人们向着君子的目标不断地努力。三是“乐统同,礼别异”。即是通过乐的美感教育把人们情感联系起来,使之亲和,目标一致,具有凝聚力。但一个社会群体只有乐作联系的纽带还不成,还必通过礼把人伦社会关系区别开来,使尊卑贵贱有序,长幼亲疏有差,使人们都能安分守己,社会才能成立。乐统同的结果是和谐,礼别异的结果是恭敬,既恭敬又和谐,才是社会人伦关系的最佳状态。四是通过礼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乐记》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通过礼乐便可把人与自然谐调起来。
《乐记》继承了孔孟荀的礼乐观点,非常看重礼乐的社会功能。但孔孟荀有些夸大礼乐的社会作用。因为他们就礼乐而论礼乐,没有把礼乐放在社会系统中考察它的地位和作用,修齐治平,似乎有了礼乐教化,就有了一切。尤其礼乐作为制度的层面崩坏以后,仍作如是说,就显得不符合实际。《乐记》与孔孟荀不同:一方面,礼乐真正发挥教化作用是在“功成”、“治定”的前提下,而不是无条件的;二是把礼乐的功能与刑政的功能既区别又而统一起来。《乐本》篇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五道备矣。”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乐记》用一种新的眼光重估礼乐的价值,对礼乐功能的论述更显得具体、实际。
四、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和”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和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和也是儒家哲学和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一种理想的境界。不过,和的内容,即使是在儒家那里也是不断地变化、充实、发展着。孔子孟子的和主要是指个体与社会、情感与道德的和谐一致。至荀子有了较大地发展、变化,除了个体与社会这一基本关系的和谐一致外,还包含生理与心理、伦理,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一致,并且提出艺术审美中的天人合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以礼乐配天地,建立初步的天人同构关系。但是由于他在哲学上持天人相分的观点,因此在他整个思想体系中,天人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矛盾。《乐记》接受了《易传》中的天地阴阳观念,舍弃荀子天人相分之论,从而在艺术哲学上建立了“天人合一”的理论。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反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注:《乐记·乐论》。)
这实际是在说,宇宙万物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整体当然包含了“天人合一”,礼乐则是沟通“天人合一”的桥梁。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注:《乐记·乐论》。)
这说明礼乐的制作,要按照天地运行、四时变化的规律,不可违背天地万物和谐有序的成规。礼乐本属社会现象,是适应社会运动和人群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但在《乐记》看来,社会也是天地中的一部分,自然要服从天地运动的客观规律。因此礼乐的制作也必须服从这一根本的客观规律,“过制则乱,过作则暴”,即不按天地自然规律而制作的礼乐,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暴乱。“故圣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注:《乐记·乐礼》。)《乐记》认为,“天人合一”决不仅仅是人的主观愿望,而是一种客观规定,即天地与社会同构,人与天地万物相感应。
“天人合一”是以什么为中介呢?是气。气分阴阳,阴阳相摩,万物而生。“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礼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注:《乐记·乐论》。)这些说法自然包含不少神秘成分。但《乐记》反复强调社会的运动、发展,人类的所作所为,都必须服从天地自然的总规律,“过制则乱,过作则暴”,不失为真知灼见。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人类破坏自然,自然正在惩罚人类的破坏行为,面对这一事实,再品味一下《乐记》的这些话语,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我们的祖先是有何等的远见卓识!当然,《乐记》对“天人合一”的认识是朴素直观的,是用一种描述的方法加以比附、联想和想象,甚至是主观上的想当然,并非对天人关系的本质认识和科学把握,而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