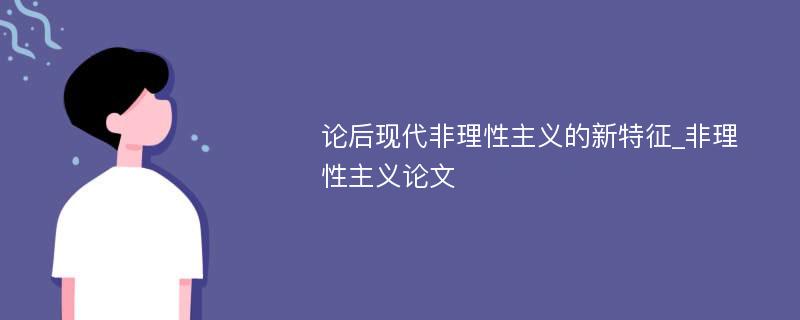
论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新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理性主义论文,后现代论文,新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西方后现代哲学在非理性主义发展上表现出的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1)以功能的非理性取代实体的非理性,即不再寻求那种形而上学的不变基础或架构,只诉诸于永恒的消解;(2)以解构的非理性取代建构的非理性,即在摧毁了理性概念之后不再建立一个非理性概念,而是放弃建构任何中心概念的企图;(3)以有意识的非理性状态取代退回到无意识状态的非理性,即力图保持理性自身的不断消解,而不是诉诸于理智不能穿透的非理性本质。
自叔本华以来,非理性主义在形态上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发展。但20世纪上半叶之前,非理性学说仍有一些共同特点:用一种非理智的或理智不能理解的在场实体取代理智的或理智可以理解的存在;用非理性的中心概念的建构取代理性概念的建构;以对无意识本质状态的发展取代意识的中心位置。20世纪下半叶后,非理性主义在发展中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如不再寻求任何在场的实体,不再进行新中心概念的建构,同时不再诉诸于无意识或超理智概念,而是力求让理性在操作过程中自我解构。本文的任务,就是对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及其与原有理论的关系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以功能的非理性取代实体的非理性
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都在致力于寻找一个不变的存在、本质或基础,无论这种东西是精神的或物质的实体,还是先验的形式或结构。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都起来反抗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基础,可他们仍然是以柏拉图的逻辑来对抗柏拉图,他们的工作无非是在柏拉图“理念”的位置上换了“意志”、“权力”、“生命”和“力比多”,等等,用种种盲目的和理智无法穿透的存在取代了自明的和可以理解的存在。即使反本体论的哲学家,如罗素、弗雷格、石里克和胡塞尔等人,也以“逻辑”、“意义”、“结构”或“形式”填补了原来由上帝、理念、物质所占据的位置;实际上,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复活着柏拉图和康德的先验认识模式,从而用认识的基础来反观存在的世界。这种用认识论的先验基础代替本体论的存在基础的尝试,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因此,怀特海才认为,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脚注而已。
20世纪下半叶,所谓后现代派试图提出一种话语,以使理论永远脱离作为本体的存在和作为认识前提的先验结构,放弃对确定性、一元基础和严格性的寻求,也放弃使自身成为真理的新的尺度的企图。在后现代派看来,不仅世界的本质不是理性的或可以理性地加以解释的,而且非理性的意志、生命、性欲、无意识,也未必是世界的本原或人的本质。人或许没有本质,因此人应以无本质为本质;也不存在什么中心,因此世界的中心就无中心;没有什么目的,因此人和世界的目的就是无目的。一切都在自我消解,一切都在过渡之中。一切都行,一切都不能永远行。新非理性主义既消解着理性范畴的逻各斯中心结构,也消解着非理性本质的在场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更为彻底的非理性主义,它认定非理性本质的在场无非是理性构造的结果,是理论家的自欺与欺人。新非理性主义不讲在场,只讲对在场的消解:既消解理性设计的理性,也消解理性构造的非理性。如果说老非理性主义表现为实体或本质的非理性,那么新一辈则表现为功能的非理性,他们不再追求一个形而上学的不变架构,而是处处破坏、颠覆或摧毁。老非理性主义者有一个出发点,有一个主体驻足的家园;新一辈则放弃家园,四处流浪。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因而处处是他们的栖身处,他们对每一逗留处都毫不留恋,反而要拆毁,使之不再成其为安身立命之地。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对哲学放弃本体论承诺起了很大作用。维特根斯坦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挥之不去,就在于人类语言总是暗示有一个实体存在,即使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家也想象有一个客观意义与语句对立。他写道“凡是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实体存在而又没有的地方:我们就想说,有个精神存在。”①比如,他本人在早期就主张:语句命题反映的是事物的逻辑关系。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与现实、语句与意义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语言中的一般名词也不反映共同的逻辑本质或客观意义,一般名词只表述一种“家族类似”(family resemblances),如同家庭成员之间在身体、相貌、性格、步态等方面交错出现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并不是家庭所有成员的共同性。由于不存在语言的共同逻辑本质,语言也就没有先天的意义,语言的意义就在于运用它时的用法。由于语言的用法多种多样,它的意义也就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不能认为“坏蛋”一词有先天一致的意义,在人们用这个词骂杀人越货的歹徒和一个姑娘娇声地说自己的情郎为“坏蛋”之间,有天壤之别。这样,语言问题就不再是对客观意义的发现,而是运用语言的博弈或游戏活动本身。
对于德里达来说,中心结构由于内在矛盾必然自我解构。中心之所以为中心,就在于它的主宰性,这要求它不受结构因素的支配,为此它要在结构之外,因为结构内的东西必然受结构因素的制约;可在结构之外,它又不成其为中心。“所以,围绕中心结构这一概念,其实只是建立在某个根本基础之上的自由嬉戏的概念”②。而且,西方哲学演变的全部历史,“就必须被认为是一系列中心对中心的置换,仿佛是一条由逐次确定的中心串联而成的链锁。中心依次有规律地取得不同的形式和称谓。形而上学的历史,与整个西方历史一样,成为由这些隐喻和换喻构成的历史。其根本策源地……就是把存在(bbeing)确定为全部意义上的此在(presence)。我们完全可以说明,所有与本质、原则、或与中心有关的命名总是标明了一种此在的恒量——理念,元始,终结,势能,实在(本质,存在,实质,主体),真实,超验性,知觉,或良知,上帝,人,等等。”③
既然看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置换的嬉戏性质,我们就不应再梦想去破译一种不受自由嬉戏和符号系统制约的真实或本原,而是不再去追寻本原,我们不应限制而应肯定自由嬉戏。显然,德里达取代中心位置的不再是一种在场的存在,而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是要固定什么,而是使一切处于流动和嬉戏状态,不是要求同一,而是强化差异。容忍差异,就是避免垄断真理。“这种原则不仅迫使我们不要赋予某一实体……以特权”,而排斥另外的实体,而且还要求我们将这种过程“看作差异的形式游戏”。这是一种踪迹的游戏。“在要素中或系统之内,没有任何纯粹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之踪迹遍布各处。”这就产生了可称之为历史性的问题:“延异”(differance)就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④这就是说,差异先于同一,间隔先于联系。因此,哲学的真正任务应该是保持差异,而不是寻求同一或固定中心。
这种容忍差异,不寻求统一性真理源泉的思想,也为费伊阿本德所主张。他认为,科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因为它宣称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或唯一来源。“当然,科学向来被认为站在反对权威主义和迷信的最前沿。我们日益增长的对抗宗教信仰的理智自由,得益于科学;我们人类从古老而刻板的思想下解放出来,也得益于科学。”可是,一旦击败了所有对手,科学就成了现代社会的上帝。于是,科学就从一种解放思想的力量变成了一种限制思想的力量。由此可知:“科学或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中并不内在地有本质上产生解放的力量,意识形态可以退化并成为愚蠢的宗教。”⑤这就是说,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在现实中只表现为统治与束缚力量的改朝换代,从这种王朝更换解放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方法,采取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和多元论,其口号就是:“什么都行!”巫术与科学、神灵与自然、理性与非理性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所以,不应使其中任何一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罗蒂的主要工作,是颠覆自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及其逻辑基础。他认为认识论哲学之所以走到了“穷途末路”,就在于“对知识论的欲望就是对限制的愿望——发现人们可以坚守的基础、人们不能脱离其外的框架、人们无法不接受的对象,以及人们不可能反对的表象的欲望。”⑥罗蒂的观点是,除了历史形成的社会约定之外,知识并无终极的基础。这种约定不仅支配着文学艺术和宗教神话,也同样支配着自然科学。认识论之镜对绝对客观性的寻求,结果都只能是一场康德式的梦幻。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虽然相互取代,但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人必须用自己的镜式本质准确地映现周围世界。如果撒除这种基础认识论,往往使人们感到留下了须予填充的真空。因此,就出现了各种“梦幻”的相互批评和不停地置换。为了结束这种梦幻,必须用无镜的哲学取代有镜的哲学,用教化哲学取代系统哲学。罗蒂指出:“把教化哲学看作对智慧的爱的一种方式,就是把它作为企图防止谈话蜕变为探究、蜕化为观点的交换。教化哲学家决不能终止哲学,但他们可以有助于防止它获取牢靠的科学大道。”⑦可见,罗蒂的“后哲学”除了保证无人能固守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思想方式之外,它并没有设定一种新的镜式本质。他强调,我们不应企图获得一种接替认识论的学科,而勿宁使自己摆脱哲学应当发现永恒的研究架构和纲领式方法的企图。有趣的是,罗蒂并不认为自己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新实用主义者并不具有一种真理论,所以也就没有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论。作为协同论的拥护者,罗蒂对人类合作研究价值的论述,只具有一种伦理的基础,而不具有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
从上述几位代表人物的学说,足以看出非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特征:消解了任何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实体;既瓦解了作为万事万物基础的本体性存在,也拆解了作为认识形式或结构的意识主体。后现代派不希冀任何固定的家园:既不象海德格尔那样寻找失去的故园,也不象宗教徒那样准备迎接未来的天堂。正象B·G·张所说的,这是“流浪汉的思维”⑧。思想上的流浪汉必须流浪,因为他以流浪为目的。流浪者以四海为家而永远不在家,对他而言,家是窒息生命的枷锁,是凡夫俗子自我限制的借口。这类思想寻求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以便徜徉在一片没有地界的莽原之中,从此思想不必再作茧自缚,它将面对无限开放的空间。
显然,所谓后现代派不是因其所信的对象,而是因其拒绝对任何特定对象有信念而体现出非理性特征。由于不设定在场的非理性存在,他们中有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非理性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是以功能的非理性取代了实体的非理性,这种功能表现为对理智的任何相对稳固的性质与形式的完全而持续不断地否定。他们不追求单纯的在场,或在其自身中并属于自身的被给定的某物,而是保持不在场及不可公度的差异。他们不是追寻本原,而是对本原的放弃。对他们来说,非决定的状态比确定的真理更有价值。他们肯定认识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嬉戏,并通过游戏过程揭示世界的无限复杂和神秘以及理智的有限和虚无。
后现代派达到目的了吗?就中心概念而言,一方面他们使中心消解或空缺,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中心。虽然他们消解了实体性中心,但却需要一种功能性中心。德里达承认:“我从未说过不存在中心,没有说过我们可以不要中心。我相信中心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实在,只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⑨可见,后现代派不是无信念,而是以无信念为信念;不是无基础,而是以无基础为基础;不是无限制,而是以无限制为限制。不对任何信念持确定的态度,这本身就转变为一种确定的态度;要求无任何限制,这本身也转变为一种限制——不是自由地消解限制,而是必须消解限制,这必须就是强制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后现代派并不能完成超越柏拉图主义的任务,它不过是翻转过来的柏拉图主义。绝对的否定必然是对否定的肯定。正象美国学者马什所批评的,“如果肯定、同一和在场没有否定、差别和不在场就不可思考,那么反之亦然。没有不在场的在场和没有在场的不在场一样不可思议。”⑩后现代主义驱赶着所有的在场,因此它必须使不在场永远在场。这样,在场的实体的非理性主义就转变为一种保证不在场永远在场的功能的非理性主义。
二、以解构的非理性取代建构的非理性
由于后现代派拒绝填补中心消解后出现的空缺,美国学者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存在的状况所依赖的前提是某种根本的断裂或中断”(11)。
老非理性主义者也讲破坏和断裂,但他们一般在破坏之后有自己的建设,在割断旧联系之后试图沟通新联系。新非理性主义只讲摧毁,不讲构建,因此呈现某种“根本的断裂”。弗洛伊德打碎了人的理智性主体,使之变成了一种由无意识性欲能量驱使的假象。但他毕竟在理智的废墟上建立了无意识的“力比多”,当作解释活动的基础。尼采把自启蒙时代以来就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上帝送上了断头台,从而摧毁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最终基础,使形而上学的大厦摇摇欲坠。不过,他仍有肯定的成分:既用“权力意志”来说明破坏力量的源泉,也设立了一个“超人”作为人未来的希望。弗洛伊德通过还原而肯定,尼采依靠超越而建立。然而,后现代派既不想通过还原找一个新立足点,也不想通过理想化寻觅一种未来的目标。他们只管破坏,不思建设,只要解构,不图构建。他们象漂泊的武装游牧部落,一路劫掠和破坏,却从不想在攻克的城池中安营扎寨。
后现代派不仅要摧毁理性主义的建构,也要摧毁非理性的建构。在它看来,非理性的建构无非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在旧形而上学基础上提出的新问题。无论“意志”还是“无意识”,都是人类理智的幻想物。无论逻辑实证主义超越有限理智的逻辑形式,还是结构主义先于人类理智的结构,事实上仍是由人类理智用形而上学的魔杖象魔术一样变出来的。非理性的建构,无论多么神秘莫测,都是披着非理性伪装的人类理性,它虽肯定了世界本质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但无法摆脱人类理智和形而上学的幻想性质。在旧形而上学基础上提出新问题,利用理性工具进行非理性建构,这并非难事。因此,许多新体系相继提出,许多新架构相继问世,但都不能克服形而上学。尼采和海德格尔都主张克服形而上学,可他们仍摆脱不掉在场的形而上学。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如何摆脱理性操作的陷阱。
为了最终摆脱形而上学的阴影,后现代派思考如何摆脱理性操作所带来的悖论。人们不能不用理性方法进行理性批判,因为批判就包括使用证明、论据和概念,如果不采用这些手段,人们只能缄默其口了。可是,如果使用理性方式批判理性,就必然陷于自我矛盾之中:在批判中必须预先假定在论断中要否定的理性的有效性。为了走出困境,后现代派采取的策略是:只进行操作,不做任何论断;不进行建构,让理性在操作过程中自我解构,即让理性在自我批判中充分展示其破坏性、游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公度的差异性。
为了让理性在操作中自我摧毁,德里达“假定一种‘双重表示’(doulbe register):它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同时又强调在科学的有效活动中有助于使它摆脱从其开端处就影响它的定义和活动的形而上学桎梏的任何东西。”(12)对德里达来说,唯有“延异”在策略上最适合于思考,因为它仅表现为否定。“它不是在场的存在,无论是多么出众的,独一无二的,根本的,或超验的。它一无管辖,一无统制,不在任何地方实施权威。……不仅没有任何‘延异’的王国,而且‘延异’煽动对每个王国的颠覆。这使它明显地产生威胁,并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欲求着王国,欲求着王国在过去或未来的出现的一切事物担惊受怕。”(13)由此,德里达自己认为,“开始认识到,不仅我真地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而且对作为的逗留而已经达到的地方也知之甚少。”(14)
由于不希冀任何王国,就须考虑这样一个“未听到的”思想或无声的追踪:存在的历史只是“差异”的一个时期,甚至现在可以不再称之为“时期”。于是“延异”是比本体论的差异或存在的真理“更古老”。在这里,不再是尼采谋害上帝时的悲壮,而是嘲讽一切严肃性的游戏。“这是不再从属于存在视界的印迹的游戏,但它的游戏转达与包括了存在的意义:印迹的游戏,或‘延异’,它没有任何意义和不存在。它不从属,没有任何支持,也没有任何深度,这一无底的棋盘,存在就在其上被推入游戏。”(15)德里达显然复活了赫拉克利特的逻辑:一就是多,同就是异。印迹始终在变化和迁延着,永远不是展现中的自身。
为了结束在场形而上学的强制性构建,德里达甚至不把“延异”视为一个名称。它“作为一个名称,依然是形而上学的”。用名称代表不在场的在场者,它就代替了在场者的位置。当名称用在场与在场者的差异表示“延异”的规定性,甚或用存在与存在物的差异表示这种规定性时,它就留在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差异之中。因此,“甚至没有‘延异’的名称,它不是一个名称,不是一个纯粹的命名单位”;命名就是对延异的暴政。这种不可命名不是那种传统的无可名状,如“上帝”或“绝对”,而是“造成可能命名效应的游戏”,是“名称的置换链”。延异就是“在一个变化的和推延的置换链中不停地自我移位。”在置换中,“延异”的名字效应本身就陷入网络之中,“被消除掉,被重新写录,正象假的上场和假的下场仍然是游戏的组成部分,是系统的一个功能。”(16)
显然,德里达试图不再重复那种要求:假的下场,真的上场;用真的在场取代假的在场。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游戏,不必再问真假问题,因为延异已消解了这个问题。在这点上,德里达比维特根斯坦更具破坏力,当维特根斯坦说意义不过是语言游戏时,他仍要人们遵守游戏规则。可德里达认为,游戏虽有规则,但规则既不主宰游戏,也不控制游戏。“现在,游戏的规则已被游戏本身替代,我们必须找到一样不是规则这个词的东西。”(17)有人问德里达,他对他的学说将走向何方是否有所把握。他回答说:“我正试图把自己置于某一个点上,以便让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正在朝哪里走。”(18)可见,德里达的学说正象他自己说的,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怪胎。”因为它既没有肯定的基础,也没指明自己的方向,甚至不承认有一个名称。它既不知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它劫掠四方,到处摧毁,而自己却似乎“无形无状,无声无息”,令人难以反击。
如果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对欧洲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的反抗,那么罗蒂的教化哲学则是对英美先验认识论传统的背叛。正象德里达破坏了在场的本体论建构,罗蒂拆解了先验的认识形式,打碎了反映世界的认识之镜。罗蒂要求一种“没有建设的教化”,“因为教化的话语被设定为反常的,它通过奇异的力量使我们摆脱旧我,帮助我们成为新的存在。”(19)讲正常话语的系统哲学家不忘营建,并提供着论证,他们想将自己的主题安置在可靠的科学大道上。教化哲学家则是破坏性的,并提供讥讽、嘲弄和警句。“伟大的系统哲学家,就象伟大的科学家,为永恒而建设。伟大的教化哲学家,为他们自己的一代而破坏。”(20)教化哲学家拒绝把自己装扮成发现了任何客观真理,他们“在避免对有观点这点有一个观点的同时,不得不摧毁有一个观点这个概念本身。”所以,他们“在这个元层次(meta-level)上是反常的。”(21)
在罗蒂看来,思想的模式化和文化的冻结,或许就是人类的非人化。正确的态度应是维持谈话继续进行,而不是最终发现客观真理。把哲学的目的看作真理,就是把人看作客体而非主体。不过,罗蒂的否定性似乎比德里达要收敛些,因为他肯定了某种目标:无限地追求真理,要比固守真理更重要。为了无限追求真理,我们既不能停留在真理的任何现存形式上,也不能幻想最终的全部真理。“全部真理”的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真正的智慧应是维持谈话持续不断的能力,因此应把人看作新描述的产生者,而不是希望能去准确描述的真理发现者。
作为实用主义的后裔,罗蒂有更多行为主义的特点。他认为,实际活动的非秩序性比理论上的解构论证更有价值。例如,过去二百年资本主义的历史,比人们阅读德里达的著作可能推想到的,远远更富于流动性、闲谈性和游戏性。现实活动时刻都粉碎着严密真理的迷梦。既然理论并非真理性描述,罗蒂认为,理论就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因此,他告诫理论家:“知识分子应当停止对社会的各项制度采取激进的批判态度。他们不应再拒绝现实。”(22)一个理论上的破坏者,却对现实抱温情态度。这或许令人惊奇,可恰恰说明了罗蒂“破坏性”理论的消极性质:正象皮浪的宗旨,既然我们无法获得真理,那么就让我们对现实抱无所谓的态度吧!既然手中没有干预现实的可靠理论,那么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德里达和罗蒂等人真地摧毁了理性,彻底摆脱了形而上学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他们并未摆脱用理性方法进行理性批判的悖论。尽管他们未用理性设立任何在场的非理性存在,从而避免了非理性对理性的依赖。然而,他们让理性自我消解的策略,仍停留在这个悖论之中:论证理性自我消除的能力也就承认了理性的有效性;要么承认理性的有效性,要么放弃让理性自我消解的企图。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正如马什指出的,“后现代理性批判能够摆脱理性基础之前就破坏了它的基础。”(23)
其次,破坏、解构、反独断、批判和怀疑等因素,并不必然属于非理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为理性所具备。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理性一直强调怀疑和批判精神,康德之后,理性也包含了反独断论的成分。可见,后现代派并未消除了理性,而是用理性的否定性对抗其肯定性,用理性的灵活性对抗其确定性,用理性的怀疑精神对抗其系统性。严格说来,争论并非发生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而是发生在理性的两种不同功能之间。德里达和罗蒂等人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理性的两个辩证方面,然后夸张地使它们成为势不两立的对手。
第三,后现代派所讲的理论摧毁性也是虚假的,他们与其说让人们从“真理”的有限形式中解放出来,倒不如说让人对所有理论采取消极态度:既然无法获得严格的真理,就应对所有理论抱漠然无动于衷态度,更不要做真假判断;既然任何克服形而上学的努力都必定不战自败,那就让我们“终止所有克服形而上学活动,听其自然发展。”(24)他们认为,“僵化性和僵化过程从来都是由明晰造成的”,所以人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应有一种较为“谦卑、质朴和传统的想法”,似乎在一种混沌模糊的状态下才能保持灵活性和创造力。可见,后现代派与其说是颠覆一切理论,不如说是不伤皮毛地保留所有理论。自诩“颠覆者”的德里达就承认:“我对于我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破坏性意义这一点则是相当明确的。我时不时地用了解构这个字眼,但它与破坏毫无关系。换句话说,它只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隐含的意义,注意我们所用语言中的历史积淀现象……这不是破坏。”(25)显然,后现代派的解构无非提醒人们游戏地对待所有理论,不要相信任何理论的真理性。它并未驳倒任何理论,而是让各种理论原封不动地存档;它不对理论进行判断,因为它主张没有判断真假优劣的标准。这样的哲学,显然不能摧毁传统悠久的形而上学。
最后,后现代哲学即使有某种批判力,那也只表现在理论层面上,并不能触及现实。它确实击中了知识分子幽于理论,作茧自缚的弱点,并要求知识分子自我启蒙。但是,后现代派幻想,只要宣布一切理论都是游戏性的,就可把人们从各种束缚下解放出来。这实际是用理论的批判取消现实的批判。口口声声讲反常话语的罗蒂,却要求知识分子对社会传统和现实持温情和恭顺的态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理论协调,而不是现实批判。马克思呼吁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罗蒂却告诉人们:由于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人与其说应改造世界,不如说应适应世界。就对现实的态度而言,罗蒂显然是消极的或保守的。正因如此,罗蒂称传统的系统哲学是“革命的”,而他倡导的教化哲学则是“反动的”(26)。
总之,后现代派企图让理性自身消解,使其陷于解构、游戏和不可公度的差异中,从而呈现非理性的特征。然而,由于他们把理性的肯定与否定、建设与破坏、信念与批判功能形而上学的割裂并对立起来,所以,他们所揭露的并不是理性的游戏性和荒谬性,而是理性被割裂后的游戏性和荒谬性。
三、以有意识的非理性状态取代退回到无意识状态的非理性
说后现代非理性主义以有意识的非理性状态取代退回到无意识状态的非理性,并不意味老非理性主义者是无意识中不自觉地落入非理性主义的。实际上,新老非理性主义者都自觉地、有意识地引出非理性的结论。但二者自觉追求的最后目标不同:后现代派企望一种清醒的非理性状态,即有意识让过程处于不断解构和流变中,使理性本身呈现游戏性和非理性特征;老非理性主义者力图发现一种人不能认识、不能论证、不能理解的非理性本质。
老非理性主义者试图发现某种本真的、不可分析的非理智存在,以取代理性的中心位置。后现代派认为,这种非理智存在无非是理性包装起来的虚无。就其内容而言,它是无;就其有个名称并力图有所指而言,它是理性的想象物。萨特的“存在”概念就是典型。罗蒂肯定了萨特哲学的教化性质,认为萨特发现了存在的虚无性而帮助我们理解视觉譬喻何以永远倾向于超越自己。但给虚无一个名称,就为人类研究提供了最终公度性词语。由此,人们就能把人这种描述着的主体看作一种被描述的客体,就是认为一切可能的描述,都可借助单一词汇被公度化。从而把哲学的任务从保持谈话的持续不断,转向对建设性真理的发现,并由此导致僵化。因为“存在先于本质”在否下人有共同本质的时候也承认了人有共同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存在”本身。罗蒂就此指出,“说‘我们的本质是没有本质’,并未从柏拉图主义逃脱出来,只要我们随之把这一见解当作发现关于人类其它真理的建设性和系统性尝试的基础的话。”(27)这就是说,只要设立公度性词语,就无法摆脱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由于“意志”、“生命”、“先验结构”和无本质的“存在”等词语都是理性符号,因此老非理性主义者仍把一只脚留在理性范畴之内。如果非理性的东西是超越人的理智的,为什么理智能发现这种超越理智的存在。可见,老非理性主义是披着非理性伪装的理性主义,是非理性的理性。
正是为避免这种一般名称的窘况,维特根斯坦才认为,“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28)一个字词有多种不同的用法,因而根本不存在与一般名词对应的共同的客观意义或本质。他力求排除严格对应的指称关系,而使这个关系模糊化或具有游戏的性质。“游戏”的概念就是“界线模糊的概念”(29)。尽管游戏需要规则,但规则本身并非永恒的。因为“我们一边玩,一边制定规则,而且也有我们一边玩,一边修改规则的情况。”(30)可见,维特根斯坦力图使人保持一种清醒状态,以时刻意识到语言的游戏性质。
德里达进一步强化了游戏性,他不仅把游戏规则说成是游戏的一部分,而且把游戏看成无底棋盘上的自由嬉戏。他不仅使一切话语都变为印迹的游戏,而且拒绝为这种游戏命名。他不想找一种无意识的在场者,以在其上放弃思考或游戏。他追求使自由嬉戏永不停止的东西:“一系列最终没有所指(signifies)的能指,而且除了从这一空缺起步否则无法变成能指的能指。”(31)德里达试图自觉保持一种清醒的游戏状态,而不诉诸可以放弃理智、放弃游戏的非理性在场者。他让理性处于某种持续自嘲的状态,似乎只有如此,才会呈现真正的非理性性质。所有在场的非理性概念,不过是假装失去理智的理性符号而已。
如果说后现代派是一种理性的非理性,那么老非理性主义则是非理性的理性。理性的非理性是利用理性自身的解构分析消解一切暂时的在场性理性设计,包括理性设计的非理性存在,使理性处于永恒的操作状态,永远不能获得肯定的结论。非理性的理性是设立了某种在场的非理性,而这种非理性无非是理性的设计。一旦设计出在场的非理性,非理性主义者就可宣布发现了终极真理,并大致结束研究活动。研究的理智就可蛰伏在非理性的在场形式中休息,并因宣布了非理性存在的不可理解性而对放弃研究活动感到心安理得。
后现代派在非理性上的自觉与清醒状态,一方面揭示了老非理性主义者的虚假性和不彻底性,即他们停留在理性为人们所划定的界限之外,面对理性设计的非理性在场者自动放弃游戏或批判,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进人们不断探索的精神,这种状态把理智不断推向新边疆,不让其在熟悉的现存形式下耗尽研究的热情。这些是后现代哲的积极因素。但是,这种理论夸大了理性的怀疑精神,抛弃了理性固有的严谨和尊重知识的内容。它只放火烧荒,却不事耕耘和收获。这与其是维持研究活动永不停止,不如说是放弃研究活动的深化。因为只有在现有知识基础上,人们才能达到更高一级的认识。如果没有任何相对稳定的主题,即使能保持谈话持续不断,那么谈话也是毫无意义的闲聊,这与真正的研究精神相去甚远。后现代派不愿象他们的先辈一样返回到“无意识”的子宫中寻求安息,这似乎是积极的,但他们的理论仍具有很多消极的性质。
首先,后现代派的清醒是无方向感的清醒,他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应去何处。就象失去记忆而又在密林深处迷了路的人,不知如何走才能获救。他与其说在研究,不如说在挣扎,挣扎着不使自己昏昏欲睡的双眼闭上,害怕一旦入睡就再也醒不过来。这与其是清醒,不如说是茫然无措。这是自愿保持糊涂的清醒。德里达曾说自己象尼采一样带着欢快的舞步肯定游戏,走出失落的思想故园。可他与尼采是有区别的,尼采的目标在未来,而德里达却以无目标为目标。
其次,这种清醒是无意义的清醒,因为它只知嬉戏,不求真理,也不在众多理论中做选择,甚至不想回答哪种游戏更有价值。尽管后理代派说:“我们应该追求新奇但却不能变成梦游者。”(32)可是,象德里达那样在无底的棋盘上玩游戏,不守任何规则,那与梦游者有何区别?
最后,这种清醒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偏执,它割裂了人们相互理解的纽带。如果为了追求新奇而不承认任何成规定论,那么任何游戏也无法进行下去。假若两人下棋,无有规则,甲有甲的走法,乙有乙的下法,那怎么能够玩下去呢?
当然,后现代派正是基于这种无方向、无意义和对差异的偏执,而有意识地呈现非理性特征的。它也因此有了某种方向和意义。
注释:
①(28)(29)(30)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31、48、55页。
②③⑨(17)(18)(25)(31)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载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4—135、154、150—151、150、153、151页。
④(12)《符号学和文字学——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与J·克里斯特娃的会谈》,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1期。
⑤Psul Feyerabend,"How to Defend Society Against Science,"inJohn Perry & M·Bratman ed.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New York/Oxford:Oxford Llniversity Press,1993),P.287.
⑥⑦(19)(20)(21)(27)R.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e,1980)P.315,372,360,369,371/370,369,378.
⑧B·G·张:《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与德里达的解构学》,载《哲学译丛》1990年第3期。
⑩(23)J·马什:《后现代主义对理性批判的悖论》,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11)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载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第331页。
(13)(15)(16)德里达:《延异》,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
(14)Derrida,"The time of a thesis:punctuations,"in Alan Montefiore ed.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49.
(22)《罗蒂谈当代西方哲学》,载《哲学动态》1992年第8期。
(24)罗蒂:《战胜传统:海德格尔和杜威》,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
(32)乔纳森·阿拉克:《后现代主义、政治,以及纽约才子们的绝境》,载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第309页。
标签:非理性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德里达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自我中心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自我认识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