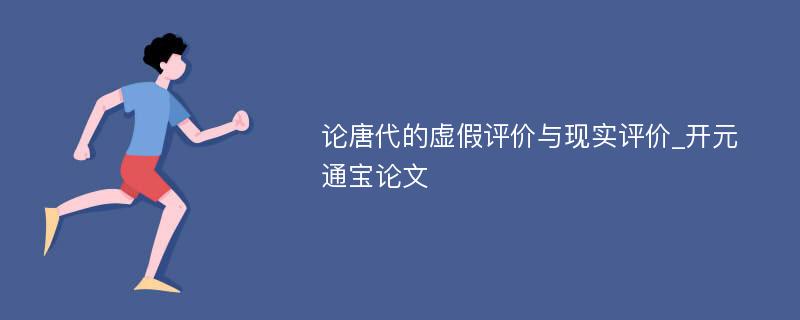
论唐代的虚估与实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虚、实估是唐代财政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与核心问题,涉及唐中后期财政制度的方方面面。但专论虚、实估的文章,仅有刘淑珍先生的《中晚唐之估法》(注:载《史学集刊》1950年第6期。)(以下简称刘文)一篇而已;此外,李锦绣先生的《唐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注: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也对此多有涉及。以上二文引证虽详,但因不得要领,对虚、实估误会颇深。其他论及唐代财政制度各种著作中,虽然都有对虚、实估的说明,但为其复杂性所困扰,一般不作深入研究,多采用刘文之说。笔者不揣浅陋,今试就此疑难问题作一正确说明。
一、虚、实估之由来
刘文、李文都将实估当作市场的实际物价,将虚估看作是政府制定的不切实际的高物价,并认为虚估是政府为改变两税法下民众负担过重而采取的措施(详见二文)。这一论断的前提是所谓两税法造成了物价的不断下降。而两税法是否造成了物价的不断下降,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以此作为前提条件的结论自然难以服人。退一步说,既便是承认两税法的确造成了物价的不断下降,其推断也不能成立。其一,如果说虚估只是为减轻两税法下民众赋税负担而设置的高物价,那么,虚估就应该只存在于两税征收之中,而不应该再出现在其他领域中。但事实上,在唐中后期,虚估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出现于两税征收中,而且政府的各项收入与支出,包括盐铁酒茶各税、官俸、军费、和籴、和市、和雇等等,都有虚估的存在。其二,唐后期的盐价一直在持续上扬(详本文末节),如果说虚估价是针对物价下落的措施,那粜盐和榷盐中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出现虚估,实际上却恰恰相反,盐铁收支中,虚估出现的频率极高。其三,如果说虚估是政府出台的不合实际的高物价,那么,始行两税时匹绢3300-4000文的估价到底是虚估还是实估呢?按刘文、李文的观点,只能理解为实估。因为,若这是虚估,那它在两税始行时就已有之,二位先生所谓虚估是两税实行之后由于物价持续跌落才出现的论点,便不攻自破。若将它释为实估,但唐前期匹绢的估价一般在200文上下(详后),同为市场价,前后期的差价为什么会高达16-20倍呢?显然无法解释。这足以说明,虚估的产生与物价的涨落并无关系,其含义也并非是指政府制定的不切实际的高物价。
要理解虚、实估,首先要了解虚、实钱,前者即由此而来。虚钱、实钱同样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疑难问题,包括李文在内的各种涉及唐代货币的论著,都将是否足值作为区分虚、实钱的标准,将“开元通宝”钱当作实钱,将以“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为代表的当十、当五十等不足值的大钱当成虚钱。(注:李文认为唐前、后期虚、实钱的概念不同,前期之实钱系指开元通宝钱,虚线是指乾元大钱,后期的虚、实钱源自于虚、实估,是指具有两种估价的绢帛。)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如果说虚钱是指乾元大钱,那么,随着大钱的消失,虚钱也应消声匿迹。但是,乾元大钱在发行5年后,即告消失,《通典·食货典·钱币门》中说:“人间无复有乾元、重棱(轮)二钱者,盖并铸为器物矣。”而虚、实钱在唐后期的史籍中不仅不绝于册,出现的频率反倒远远高于唐前期。可见,虚钱根本不是指大钱。关于虚、实钱的概念及影响,笔者曾专文进行过说明。(注:参见拙文:《略论唐朝的虚钱与实钱》,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为避免重复,这里只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所谓虚、实钱是以计值方式而言,是指同一种钱币本身具有的两种不同的计值方式。众所周知,唐代一直以开元通宝钱为主要货币,但除了官铸的开元通宝钱(好钱)以外,尚有大量的私铸开元通宝钱(恶钱)。好、恶两种钱币的含铜量、重量等相差较大,当它们在市场上共同流通时,按照金属货币使用价值决定其交换价值的原理,好钱在交易时必然被加抬使用,即好钱一文当恶钱若干文使用。《旧唐书》卷48《食货上》中说;“府县不许好者加价回博”,说明好钱在流通中确实被加抬使用,只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而已。这样,作为好钱的开元通宝钱便有了两种不同的计值方式:一种是原面值所规定的一文实价,即实钱;一种是用来对付恶钱的超面值虚抬价,即虚钱。好钱虚抬的倍数,并不固定,视流通领域内恶钱的质量而定。如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约741-742),“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注:《新唐书》卷54《食货四》。)是好钱加抬七、八倍。至宪宗元和六年(811),“计成盐价,钱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总约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疑为二)千七百一十二万七千一百贯。”(注:《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是好钱加抬4倍左右。
好钱在流通中被加抬,是私铸币泛滥的结果。中国历史上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有私铸币泛滥的现象,大概民间交易中也都存在虚、实钱的问题。但好钱加抬,在其他时期,从来没有得到过官方认可。唐朝的好钱虚抬却得到官府认同,合法化了。促使虚钱合法化的因素是官铸大钱的发行。大钱早在高宗乾封元年(666)就已出现,至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稍重于开元钱,却一当开元通宝十;次年,又发行重轮乾元钱,约比开元钱重三倍,却一当开元通宝钱五十。大钱的发行,不仅造成货币贬值、物价腾踊;而且其与当时的主要货币开元通宝之间的比价严重失调,造成极度的交易混乱。因开元钱作价太低,于是,民间“乃抬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重轮)乾元钱一当三十。缘人厌钱价不定,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注:《旧唐书》卷48《食货上》。)由此可知,虚钱是指民间抬价后的开元钱,与之相对,实钱自然是指开元钱的原定面值。民间加抬开元钱、减降重轮钱的做法,符合金属货币其使用价值决定其交换价值这一基本定律。因为开元通宝钱大小成色基本同于乾元重宝钱,后者既然能一当十,那么开元通宝也自然应该加抬10倍使用,而重轮钱的大小成色约值开元钱3倍,当然应降至30流通。
正是因为民间加抬开元钱的做法符合货币流通规律,而且也纠正了因政府发行大钱造成的货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脱节的弊病,所以,政府改变了原先不许好钱“加价回博”的态度,转而允许开元钱加抬流通。肃宗“上元元年(760)六月七日诏:‘其重稜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钱,宜一钱十支行用;乾元当十钱,宜依前行用’……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诏:‘应典贴庄宅、店铺、田地、硙碾等,先为实钱典帖者,令还以实钱价;先以虚钱典贴者,令以虚钱赎。其余交关,并依前用当十钱。’由是钱有虚实之称。”(注:《唐会要》卷89《泉货》。)诏文认可了民间业已存在的虚钱交易,允许同时存在虚钱买卖和实钱买卖两种交易方式。这说明虚钱交易在上元年间因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而得以合法化。
钱既分虚、实,货物自然也有虚、实两价。如一斗粟,实钱5文,虚钱则可能需要50文。虚、实估也由此而起,以实钱估价物品称为实估,以虚钱估价物品称为虚估。实估因为是以实钱估价,相对稳定,比如绢帛的实估价,除去受战乱影响的时期,基本保持着匹绢200文的价格。而虚估则是频繁变化的,因为,虚、实估既然源自于虚、实钱,虚、实钱之间的差价自然就是虚、实估之间的差价,而虚钱与实钱的差价,并不固定,实钱加抬成虚钱的倍数,视流通领域内恶钱的质量而定,从4倍到20倍不等,所以,同为虚估,但各时期的虚估价并不相同。仍以绢价为例,唐后期匹绢的虚估价从800-10000文不等,差距极大。
虚、实估既然由虚、实钱而来,那么,只要虚、实钱存在,虚、实估自然也难以消除。从唐后期的史籍记载看,私铸恶钱始终泛滥成灾,虚、实钱也得以长期存在,人们已习惯用虚钱作为计值方式。同时,政府的财政收支也多以虚钱记算。因此,源于虚、实钱的虚、实估自然也就长期存在。
总而言之,虚、实估系由虚、实钱而来;其中,实估是相对稳定的,而虚估却是变化不定的;自虚估随虚钱在肃宗上元年间合法化以来,唐后期政府的财政收支基本上以虚估价计算。此三点是理解唐代虚、实估的关键所在。
二、虚、实估与其他估法的区别
唐之估法,错综复杂,凡事关物与物或钱与物之间的折变计算,都称之为估法,故史籍中估法之名称也杂乱繁多,常见的有三估、折估(纳)、折变、平估、加(增)估,降估、实估、虚估、省估、元估、时估、月估等等。以上各种估法,依其性质,大约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类是有关物与物之间折算变纳的估法,主要包括三估、折估(纳)和折变。三估又称三等估,唐初已有。唐初,赋役制度沿袭了隋朝的租庸调制,其中,租纳粟、米,庸调纳绢、布、麻等物,所税皆为实物。而物有精粗之分,于是政府收税时,对百姓所纳实物,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这就是史籍中所谓的“三等估”(即上估、中估、下估)。按政府之惯例,民间税物的质量需达中等水平,对于达不到要求的下等物,要另征质量间折损之差价,即折估钱,又称折纳钱。折估钱本该是对破损滥恶的税物加收的折损差价,但地方官奸诈贪婪,百姓所税物品无论质量如何,照例征收折估钱,以中饱私囊,遂成税外之税。为减轻民众负担,唐玄宗曾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下诏禁止征收折估钱。(注:参见《唐会要》卷83《租税上》。)但征收折估钱是地方官获取非法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仅凭一纸空文是难以杜绝的。实行两税制后,两税虽以钱定税,但征收时一般折征实物,故滥收折估钱的现象仍然存在。如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官府收税时,仍“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注:《新唐书》卷52《食货二》。)租庸调制下,与折估相类似还有折变制度,是指政府处于各种需要,将原本纳粮的田租折征绢帛或将原本纳绢布的庸调折征米粟。因为折变涉及到米粟和绢布之间的比价折算,故也属估法的范围。有些学者认为虚、实估起源于折估与折变制度,其实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因为虚、实估是对同一物品的虚、实两种不同的估价,与作为税物等级间差价的折估和绢布与米粟互换征收的折变,性质迥然不同,不应该存在因果关系。
第二类是官府调节物价或优恤平民的物估,包括平估、加(增)估、降估等。平估即是市场的实际物估价格,加(增)估和降估都是针对平估而言的,分别指高于和低于平估的物估法。设立加(增)估和降估的目的,最初是常平的需要,政府为优恤平民并保持物价平衡,物贱加估而收,物贵则降估而出,两唐书《食货志》中不乏此方面的记载。以后加估又推广于和市、和买与和籴之中,唐代设有宫市,专职负责宫廷之物资采购,谓之和市或和买。官府购物,向来强取贱买,成为害民的一大弊政。为防止官吏巧取豪夺,政府规定,和市、和买,须依市价;同时为优恤平民,允许和市、和买所购物品的价格略高于市价,即可以加估购物,加估因此而有了加饶和优饶的别称。和籴是指为军国之需而购粮于民间,一般也多加估购粮。两税法实行后,加估又渗入税法之中。两税之税额以省估计算,而民众折钱纳物却以时估计算。因唐后期的时估价皆低于省估价,为减轻民众负担,弥补时估与省估之间的差价,政府决定,在百姓依时估价折纳物品时,要在时估价的基础上加(优)饶若干,以缩小时估和省估间的差距。刘文、李文都把加(增)估理解为虚估之一种,这种解释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加、增与虚,不仅其字面含义截然不同;而且从出现的时间上看,互相之间也并无联系,虚估产生于中唐以后,刘文、李文也持此观点,而加估和降估早在唐初就已出现,将加估与虚估等同起来,纯属误解。
第三类是分别以实钱和虚钱估价物品的物估法,即实估与虚估;其中虚估又分为省估、元估、时估、月估等数种。如前所言,实钱加抬为虚钱的倍数是变化不定的,那么,各个时期的虚估价自然也并不相同,史籍中所谓的省估、元估、时估、月估等,实际上就是各个时期不同的虚估价。具体来说,省估和元估是德宗建中年间(780-783)的虚估价。建中元年(780),政府始行两税法,将代宗大历十四年(779)赋役各项所得的米粟、布帛等实物,以当时之虚估价折成钱额,作为赋税征收之总额,因为建中年间的虚估价是中央都省用来确定两税总额的物估价格,故称省估。然而,虚估价是经常变动的,建中以后的虚估价肯定不同于建中年间的虚估价,那么,根据建中年间的虚估价确定的两税总额就应根据新的虚估价相应作出调整。但两税法下,无论以后的虚估价如何变动,用建中元年的虚估价确定的两税总额却始终不变。如此,两税收支关系中,便同时存在两种虚估价:即定两税税额时中央都省所用的虚估价(省估)和以后不断变动的虚估价,为区别之,人们便将前者称为元(原)估,将后者称为时估。月估,是指市司按月统计的市场物价指数,目的在于让中央政府掌握市场行情,以便调控物价。(注:参见《资治通鉴》卷234“贞元八年八月条”胡三省注。)月估之称,始见于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此时政府的财政收支都以虚估计算,市司每月上报的物价应该是用虚估价来计算的,因此,月估实际上就是时估之他称,也属虚估的范围。
省估与时估虽同为虚估,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时估一般低于省估,故研究者极易把时估理解为实估。《元稹集》卷38所载“为河南百姓诉车状”,更加深了这一误会:“〔元和十四年(819)〕,河南府应供行营般粮草等车,准敕粮料使牒共雇四千三十五乘,每乘每里脚钱三十五文,约计从东都至行营所八百余里,钱二十八千,共给盐利虚估匹段。绢一匹,约估四千以上,时估七百文;绸一匹,约估五千,时估八百文。约计二十八千,得绸绢共六匹,折当实钱四千五百以来”。从状文中看,官府应按匹绢700文的时估价,付给每乘车共计价值28000的绢帛,实际上却按4000的约估价付值。刘文和李文都引用了此诉状资料,认为状文中的约估即是虚估,时估是指实估。说约估是虚估,当然是正确的;但状文中的时估实际上也是虚估,确切地说,是元稹时低于约估的虚估。理由有二:首先建中以后,官方收支例用虚估核算,《新唐书》卷52《食货二》上说:“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从史籍中看,官俸,军费皆以虚估计算,直至会昌六年(846),政府虽已毁佛像、铜钟而大量铸钱,官俸中尚有一半为虚估匹段。(注:参见《唐会要》卷89《泉货》。)而和雇、和市,和籴等,向来具有半强制性质,是变相的赋役,官府又怎么可能善良到对官俸和军费以虚估计折而独对和雇以实估价付值呢?所以时估只能是虚估。其次,从状文中提到的雇价上看,官府应给与所雇运粮车每乘每里35文的报酬,考虑到有返回路程,每乘往返平均每里为17.5文,以每乘日行40里计,日酬当为700文,每乘按三牛一车一人计算,平均所得日酬为140文。若把这140文当作实钱看待,恐怕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唐前期的租庸调制下,纳庸代役的标准是每日折绢三尺,政府和雇,雇价也是日绢三尺,(注:参见《新唐书》卷51《食货一》,卷46《百官志》。)唐代四丈为匹,以匹绢实钱200文折算,三尺绢仅当实钱15文左右。两相对比,可知状文中每乘每里35文共计28000文的报酬无疑是指虚钱。明白了这一点,若再把约估当成虚枯、把时估看作实估,就无法解释元稹为什么还要替民众诉冤了。因为,既然雇价是以虚钱计算的,而约估就是虚估,官方现以约估匹段付给雇费,自然是合情合理的,民众还有何冤要诉呢?百姓现要求以时估付值,而时估就是实估,等于民众要求政府用实估付给他们按虚估计值的雇价,岂不是成了民众在无理取闹吗?由此可见,状文中的约估与时估都是虚估。另外,元稹文中提到,以约估价所得的六匹绸绢,若按绸绢七、八百文的时估计算,仅“折当实钱四千五百文”,他将时估和实钱联系起来,极易使人把时估误会为实估。但匹绢七、八百文的时估远高于唐前期200文的实估,时估不可能是实估。依笔者看来,“折当实钱”或是“实折当钱”之误。
顺便指出,从元稹状文的内容看,刘文、李文中关于虚估的基本立论难以成立。她们都坚持虚估是两税法实行后由于物价持续下跌才出现的,言外之意是说始行两税制时并没有虚估。而状文中匹绢4000被她们称为虚估的约估,恰好正是建中初年行两税时的物估价格,元和十三年(818),李翱的奏疏是绝好的证明材料:“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今税额如故,而绢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不过八百。”(注:《全唐文》卷634“疏改税法”条。)又如何能说始行两税时没有虚估呢?
三、虚、实估与唐代绢价的变动
唐朝以铜钱和绢帛共为货币,所以,虚、实估自产生以后,首先涉及到铜钱与绢帛的比价问题。绢帛因为铜钱的虚、实两价也有了虚、实两估。唐前期,虚、实估尚未合法化,故官方物估不用虚估价,绢价当然较低。自肃宗始,政府收支多用虚估,绢帛也常用虚估价,因而唐后期之绢帛价格比之唐前期,上涨了许多。唐前期的绢帛一般为200文一匹,(注:如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据全汉升先生考证为210文左右;参见其著《唐代物价的变动》一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又《新唐书》卷42《食货二》:玄宗天宝年间(742-756),“绢一匹钱二百”。)至肃宗乾元、上元年间(760-762),一匹绢曾高达10000文;(注:参见全汉升:《唐代物价的变动》一文。)至代宗大历末年及德宗建中初年(778-781),一匹绢为3300-4000文;(注:《新唐书》卷42《食货二》:“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匹”;又《全唐文》卷634“疏改税法”条:“初定两税……绢一匹为钱四千”。)德宗贞元四年(788),绢价为1600文;(注:《新唐书》卷42《食货二》:“贞元四年……一匹为钱一千六百。”)此后,绢价一般固定在800-1000文左右。(注:《全唐文》卷634李翱《进士策问二道》:元和五年(810)“绢一匹值不出八百”;开成三年(838),据全汉开先生考证为1000文左右,参见其著《唐代物价的变动》。)唐代绢价之变动主要在于估法的不同。前期每匹200文的价格,是实估价;自肃宗时虚、实钱和虚、实估合法化后,物估一般用虚估,绢价皆为虚估价。那么,既然唐后期的绢价都是虚估价,为什么价格仍不一致且相差悬殊呢?这就涉及到虚估的计算方法问题。
如前所述,虚、实估起源于虚、实钱,虚、实钱之间的差价就是虚、实估之间的差价。而实钱加抬为虚钱,其加抬的倍数并不固定,视流通领域内恶钱的质量而定。唐后期,私铸币、大钱等恶钱的质量不一,虚、实钱之间的差价也各不相同,因此,虽同为虚估价,却仍然在价格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地说,肃宗时匹绢折合万钱,是因为当时朝廷发行了当五十的重轮乾元钱,史思明占据洛阳后又发行过当百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这两种一当开元通宝百的大钱,仅比开元钱约重5倍,开元钱加抬便为20倍,万文的虚估价折合实估价,不过500文。若以重轮钱推算,其钱约比开元钱重3倍,开元钱便加抬17倍,万文的虚估价折当实估价,也只不过是580余文。当然,500文或580文的绢价,仍比唐前期上涨了二、三倍,这是因为当时时局动荡、物品奇缺之故。德宗建中初,绢1匹折钱3300文,其原因是当时赵赞铸当十钱,其钱之重量历来说法不一,按常识判断,应与乾封、乾元当十钱相当,重量大小近似于开元通宝钱。那么,开元钱虚抬当为10倍,3300文的虚估价折合为实估价,应为330文左右。此时之唐代社会还没有从安史之乱中恢复过来。德宗贞元时,匹绢折当铜钱1600文,是因为当时铅锡钱极多,铅锡钱又称偏炉钱,它与好钱的比价,按前引之《新唐书》卷54《食货四》的记载,官炉好钱“一当偏炉钱七八”,开元钱应虚抬七、八倍,1600文的虚估价折成实估价,当为200文左右。与唐前期基本持平。宪宗、文宗时的绢价变动较小,固定在800-1000文上下,此时的虚、实钱差价,按前引《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的记载,是“总约四倍加抬”,那么,开元钱应加抬4倍,500-1000文的虚估价折成实估价,为200-250文,也与唐前期的价格相差不多。由此可见,唐代之绢价,从实估价上看,除了受动乱影响的时期外,前、后期的价格基本保持一致,绢帛价格在“文”数上的巨大差别,是估法的不同造成的。
四、虚、实估与赋役征收
唐前期的租庸调制,虽皆征收实物,但米粟与绢布之间往往互相折变征纳;两税法下,更是以钱额定税,交纳时又要折成实物。两种赋税制度都涉及到物与物或钱与物之间的折算估价问题,也即都要涉及到估法。但唐前期,政府并没有认可虚、实钱的合法性,虚、实估还没有渗入到税法中,只有所谓的三等估。自760年始,政府正式承认了虚、实钱,虚、实估方与赋役征收联系起来,榷盐税中已经出现了虚估(详后)。但此时盐税尚不重要,政府的主要收入是户、地二税。户税按户等纳钱,地税则按亩纳粮,钱与物之间的折变较少,这和两税法下户、地税以钱定税额实际征收时又折征实物的做法有所不同,虚、实估在赋役征收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虚、实估与赋役征收密切相关,当是在两税法推行以后。两税法规定以钱额定税,即先将大历十四年(779)年赋税所入实物以当时之物价折成钱数,以此作为全国应征之赋税总额分摊至各地,实际征收时再依钱额折收实物。因此,两税的征收实际上是双重折算的过程——先将实物税额折成钱数再将钱数折成实物。因为物品有虚、实两种估价,折算过程中依据虚价还是依据实价就当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史籍记载来看,政府在将实物税额折成钱额时,依据的是当时一匹绢高达3300-4000文的虚估价。而地方官在将钱额折征实物的过程中,却以实估价来折算实物,民众的负担便成倍增长。《旧唐书》卷148《裴垍传》:“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流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而唐后期虚、实估之间的差价,至少在4倍左右,民众赋役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官吏降虚就实的做法,在后期较为普遍,各地“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注:《册府元龟·邦计部·赋税门》。)朝廷不得已屡下诏旨,明令禁止。元和四年(809),宪宗敕令停止实估,认为“征剥实钱,即是重伤百姓”;(注:《全唐文》卷61“停实估敕”。)宣宗大中四年(850)又敕:“近闻近日内或有于虚估匹段数内征实估物……并不尽依敕条,宜委长吏,切加遵守,如有违越,必议科绳。”(注:《唐会要》卷84《租税下》。)
官吏在赋役征收中,以实估替代虚估,民众自然不堪忍受。那么,如果官吏在将钱额折征实物的过程中依据虚估价进行折算,民众的负担是否就不会加重了呢?也不一定。
虚估有元(省)估和时估之分,两税总额是依元估核算的,在向民众折征实物过程中,若依据时估向民众折征实物,时估虽然也是虚估,但民众的负担仍然要加重。因为,省(元)估价要远远高于时估价。省估或元估是指大历末、建中初的虚估价,当时唐朝的物价正值高峰,匹绢的虚估价高达3300-4000文,省(元)估事实上是一种偏高的虚估价。其后,随着用钱的好转及社会经济的恢复,虚估价自然要回落,如前文所列,德宗贞元时匹绢的虚估价为1600文,宪宗元和时为800文,这些下降的虚估价,称作时估。尽管时估持续走低,政府仍维持元估所定的税额,征收时却不依元估价而以时估价折收实物,民众的赋税负担当然要成倍增长。对此,陆贽斥之为“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认为应“比类当今时价(估),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陆贽从优恤百姓的角度出发,认为两税税额应以时估而非以省估确定,但正如反对派所言:“自定两税以来,恒使计钱纳物,物价渐贱,所纳渐多;出给之时,又增虚估,广求羡利,以赡库钱。岁计月支,犹患不足。”(注:以上引文均见《全唐文》卷465,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所以,“贽言虽切,以谵逐,事无施行者。”(注:《新唐书》卷52《食货二》。)
在元估与时估的差价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为稳定小农,保护税源,政府遂在征税时,对百姓给予一定的优惠,即在时估的基础上加估若干,如“依本县时价……每匹加饶二百文”、(注:《唐会要》卷83《租税上》。)“仍于时估外每贯加饶三五百文”(注:《唐会要》卷84《租税下》。)等,以缩小时估与元估间的差距。《全唐文》卷634所载元和十三年(818)李翱“疏改税法”’就较为明确地说明了省估、时估、加估三者之间的关系:“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绢帛日贱……绢一匹不过八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假令官杂虚(疑为加)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
在两税税额依据元估的前提下,由于时估的回落,同样是纳税10000文,建中初折绢才二匹半,而至元和十三年时,需折绢12匹,就是在时估的基础上加估若干,仍需纳绢8匹,比起建中时,税加3倍有余。正是因为唐后期时估与元佑的差价较大,有限的加估,难以达到减负的作用;而且,在时估基础上增估若干的做法,使得估法混乱,事实上只是给地方官营私舞弊创造了条件,朝廷对民众的加估优惠是否能够落到实处,完全取决于地方官之道德品质。于是,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朝廷决定“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绸,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唯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注:《新唐书》卷52《食货二》。)如果这次税制改革,确实做到定税、收税都依布帛而不依钱数计折,那么,两税中的虚,实估从此应当消失。
两税之外的盐、酒、茶税中,也有虚、实估的存在。榷盐,一般认为是始于肃宗乾元元年(760),“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引文中所谓“时价百钱”即是政府之榷盐税,但非实钱,时价百钱是虚钱百钱之意。此年,因第五琦发行乾元重宝钱,开元通宝钱遂虚抬10倍,时价百钱仅当实钱10文而已,榷率相当于原来的盐价。可见,榷盐、粜盐从一开始,就是以虚估计算的。德宗建中年间,“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注:以上引文均见《新唐书》卷54《食货四》。)这里所记的盐价也应都是虚估价。在唐后期,盐价一般都用虚估价,但盐利收入的计算,却虚、实估交替并用。如《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所载:“元和三年(808)粜盐,都收价钱七百二十七万八千一百六十贯,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二千七百八十一万五千八百七贯。(注:原文为17815807,实误;《唐会要》卷87作2780余万贯,今据《唐会要》改。)贞元二年(786)收粜盐虚钱六百五十九万六千贯;永贞元年(805)收粜盐虚钱七百五十三万一百贯;元和元年(806)收粜盐虚钱一千一百二十八万贯;二年(807)收粜盐虚钱一千三百五万七千三百贯。”此段记载中各年的盐税收入,相差极大,元和三年盐税收入的虚估价比前二年高出1400余万以上,更令人费解的是,元和三年盐税收入的实估价竟然高于贞元二年的虚估价收入。若将比较的时间范围再扩大一些,差距就更为明显。《新唐书》卷54《食货四》上说,大历末(779),经过刘晏的改革,盐税收入由原来的40万缗增至“六百余万缗”,这600余万应是虚估数。因为元和三年盐利实估收入700余万,是李巽任盐铁使后出现的奇迹,新、旧书的《食货志》都说700余万的收入,3倍于刘晏时,那么,刘晏时的600余万只能是虚估数。700余万的实估收入,比刘晏时的虚估收入还高出120余万。李巽卒于元和四年(809),其后的盐税收入,“元和五年(810)……盐利钱六百九十八万贯,比量改法以前旧盐利时价四倍虚估,即此钱为一(应为二)千七百四十余万贯”;元和七年(812),盐利共“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注:《旧唐书》卷49《食货下》。)比之元和三年,略有下降。但元和以后的盐税收入却大幅下降,如大中七年(853),盐利收入为278万余缗。(注:《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七年”条。)此数当为实估价,却比元和三年降低了3倍多。唐后期盐利收入上的巨大差异,向来是令治唐史者头痛不已的问题,今依据《新唐书》卷54《食货四》和《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的相关记载,试从虚、实估的角度作一说明。
唐代榷盐,盐户制盐,官府收购,再粜于商。然商人从官府籴盐,不用钱而多用绢帛,官府计榷税收入不计绢而计钱额,故绢价愈高则榷盐收入愈低。唐后期的绢价,虽在钱文上有较大的差异,但如前所述,若除去虚、实估的影响,则只有肃宗、代宗及德宗初的绢价高于正常年份。唐榷盐始于肃宗,绢价奇贵,加之榷率远低于以后,其收入仅40万贯而已。代宗时绢价有所下跌,加之刘晏整顿盐法,严禁私制私贩,规定商人以绢代盐价者,每贯加钱200文,故榷盐收入上升至600万贯。建中以后,政府大幅度提高榷盐税,斗增200,且绢价日益回落,从贞元开始,绢帛的实估价,已与唐前期的绢价基本持平,按当时财政收支的惯例,盐税收入的绢帛以省估计算,粜盐时商人所纳绢帛却以时估计值。因时估远低于省估,按照常理,以省估核算的榷盐收入应大幅度提高,但刘晏被贬,盐法日坏,私盐不绝,“官收不能过半”,故贞元二年盐利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贞元后期至永贞元年(798-805),李錡任盐铁使,杜绝私盐,盐税收入比贞元时增加百万左右。但李錡用盐利收入重贿权臣,“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耗屈”。所以,750万的盐利是打了折扣的,应收数当远高于此。元和初(806-808),李巽任盐铁使,改革旧弊,收入悉归国库,李巽又将原属盐铁使及地方煮盐之利与度支粜盐之利,合并计算,“以盐利皆归度支”,于是当年的盐税急剧膨胀至2700余万。李巽在上报收入时,专门声明“非实数也,今请以其数除为煮盐之外,付度支收其数。”所以,此年的盐利收入与往年有别,是煮盐与榷盐的收入合并而得,学者怀疑其真实性,并非没有道理。但若以为2700万是虚估,刘晏时的600万是实估,从而认为史籍中所谓李巽时的盐利3倍于刘晏时之记载并不可信,(注:张泽咸著:《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8页。)那就不对了。其实,唐代的榷盐,一开始就用虚估法,元和三年以来,唐代的盐利才开始以实估核计。唐代的盐利,如仅计榷盐收入,以元和二年之数为最;若榷盐与煮盐相加,以元和三年之数最高。其后,煮盐收入,例归度支,故元和五年、七年的盐利收入与元和三年相近。穆宗至武宗朝的盐利收入,不见史载,考虑到唐后期地方割据愈演愈烈,盐利收入自然连年下降。至大中七年,盐利降至278万,此数也是榷盐与煮盐之利累加而得。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的记载,大中年间的榷盐收入只有121.5万余贯,270余万的盐利中自然应包括煮盐之利。
茶税的征收始于德宗贞元九年(793),当年的收入为40万贯,(注:参见《旧唐书》卷13《德宗纪》。)穆宗长庆间(821-841);“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但税茶之总收入不见记载。“大中初(847),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注:《新唐书》卷54《食货四》。)收入应在80万贯左右。酒税之设,据考证,始于代宗广德二年(764),德宗建中三年(782),方行榷酤之法。(注:参见《唐五代赋役史草》,第208页。)从《新唐书·食货四》的记载看,榷率为“斗钱百五十”,大和八年(834),收入“为钱百五十六十万余缗”。《资冶通鉴》卷249“大中七年”条载,当年榷酤收入为82万贯。以上钱额,史籍虽未注明是实估价还是虚估价,但似可比照盐利,以元和三年(808)为界,在此之前的为虚估,之后为实估。至于税收数额上的差异,其原因应大体上与盐利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