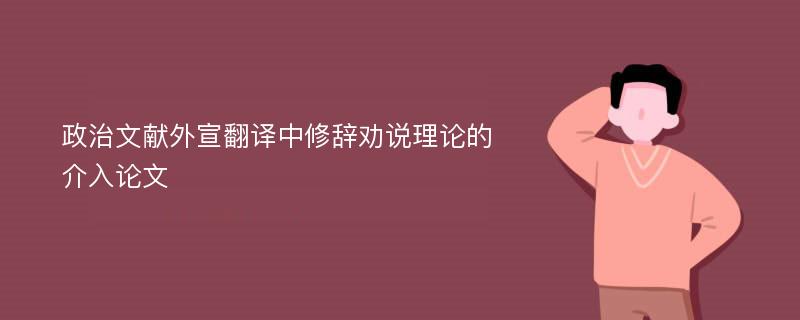
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中修辞劝说理论的介入
张添羽 宇文刚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山西太原030001)
摘 要: 为了从不同理论视角去探究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依据修辞学劝说理论着重分析修辞劝说理论介入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的理论依据以及有效实现途径。研究指出,修辞劝说理论中的修辞诉诸三模式、以受众为关注点、以“劝说”和“认可”为修辞目标等理论观点与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的目标有诸多契合点,这为今后进一步运用修辞劝说理论探索新的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策略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修辞劝说;修辞诉诸;政治文献;外宣翻译
在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中,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作为外宣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一直以来受到各方高度重视。近年来,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研究者尝试从各个理论视角切入,如: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功能对等理论等。当前研究大都围绕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中遵循和采用了何种翻译策略和原则,及如何提高译文文本质量展开,成果多聚焦于共性研究,而对其隶属于外宣工作范畴这一属性还缺乏足够关注。事实上,政治文献外宣翻译具有跨学科性,这一特性促使我们可以尝试借鉴修辞学理论体系,通过对其核心概念及理论观点的分析,去探究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对于翻译学当中提高交际与传播实效能提供何种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也能够进一步丰富翻译学研究的理论视角。
一、修辞劝说理论
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就是对“劝说方式”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视为在解决所有问题时探寻劝服方式的能力。针对“劝说”获取成功的方式,他提出了“品格诉诸、情感诉诸、理性诉诸三种基本的劝说模式”[1]。
(一)修辞诉诸三模式
1.诉诸修辞者品格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修辞者品格在修辞中的“说服功能”时认为,语言行为发出者总是试图借助“品格诉诸”来获取语言行为接受者的信任进而说服他们。一般而言,较之于其他语言行为发出者,语言行为接受者更愿意信任公允之人,特别是那些尚存争议以及认知模糊的话题中,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对那些具有优秀品格的语言行为发出者产生信任感。人们对语言行为发出者的所有信任感大都来自话语行为本身。品格对于成功说服而言,可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上述分析来看,亚里士多德在其理论体系当中着重强调语言行为发出者可以通过话语行为本身来凝塑自我形象,以期建构某种促使他人信任的修辞人格。因而,语言行为发出者需要借助修辞手段促使语言行为接受者产生某种心理和认知,“这一结果必然会对话语行为发出者所期待的目标——说服,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2]57。
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行为发出者要赢得语言行为接受者的信任,构建可信的修辞品格必须具备三种特质:美德、善意和理智。正是因为语言行为接受者信任具有这些良好品行的人,语言行为发出者在其语言表述行为过程中,必须竭力展示自身良好的道德、善意或是理性的形象,才能得以塑造出杰出的修辞人格,从而有效地实现“劝说”的目的。
2.诉诸受众情感
“修辞行为与政治文献外宣翻译均为一种语言交际行为,实现有效沟通是二者共同的目标,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语言交际行为,其实质即是交流和传播。”[6]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又是为了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一个国家,推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政治文献外译可以促使他国的译文读者受众增进对一个国家政治环境、政治理念、国家治理体系等方面的了解和认同,一定程度上消除他们对政治文献源语国的误解和偏见,营造一个有利于该国在世界范围内全方位谋求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可见,外宣翻译范畴之内的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一环,其实质仍旧是以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去推进的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的译者能否通过自己的译文文本成功营造出感染他国译文读者受众的特定情境,能否成功获得他们情感及内心的某种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的终极目的能否得以如愿达成。
在国家外宣与传播体系当中,政治文献外译一向都将提高译文读者受众意识作为其有效提高翻译效果的核心手段。黄有义曾就外宣翻译谈到,外宣翻译应以受众作为依归,始终将目标语译文读者作为翻译过程的关注核心,重视外宣翻译的交际功能,应尽量遵循“外宣三贴近”原则[9]。在此基础之上,袁晓宁进一步指出,外宣翻译要尽量使目标语在语篇和句法结构、语言表述方式以及语体风格等方面尽量贴近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将目标语作为最终归宿[10]。这一翻译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凸显了目标语译文受众的核心地位。此外,赵启正也曾提出:“外宣翻译应将受众需求与期待与外宣目标相结合,通过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和语言表述传达中国信息,讲述中国故事。”[11]由此可见,外宣翻译范畴下的政治文献翻译译文在受众身上所产生的预期影响充分体现了其翻译的预设效果是否顺利得以达成。总之,得到目标语受众群体的“认同”是实现对外宣传目标的根本所在。
3.诉诸论证理性
亚里士多德对话语行为受众的性格特质所采取的系统分析及描述,使得语言行为发出者在“劝说”过程中可以根据各群体的不同特点,采用截然不同的“劝说”策略,以达到其想要的“劝说”效果。诉诸受众情感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为其后的各领域学科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借鉴和参考。
效益分析:试验1早熟品种KX9384 1穴2株不覆膜种植,增产15.79%,增收3 475.2元/hm2。试验2晚熟品种覆膜与早熟品种不覆膜4∶4间种,减膜50%,增产15.12%,增收2 978.64元/hm2。
塑造修辞人格、赢得受众对于言说者的信任、调动受众情感固然易使受众进入“接受劝说”的状态,但劝服受众终究只能借助于言说者辩明事理、对事实加以阐述和证明才能使这一过程得以顺利实现[4]58。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事件本身所蕴含的“说服理性”来证实其表述的内容真实或者内容明显倾向于属实的事实,“劝说”就能得以实现。他使用“logos”一词来表述话语自身当中所包含的语言逻辑,认为修辞劝说的途径无外乎就是“修辞论证”与“修辞例证”。亚里士多德在阐发修辞过程中应该如何驾驭此两种手段时认为,“例证法”在话语行为发出过程当中的“劝说”功效尽管十分显著,然而较之于“修辞论证”,它并不太容易获得受众的积极响应。修辞论证和修辞例证在施加于受众的逻辑以及推理行为时,完全可以有效地将此两种手段配合使用,使它们最大化地发挥出彼此在“劝说功效”上的优越性。同时,还可以结合其他诉诸手段——受众情感、构筑可信的修辞人格等方式获取受众对言说内容的接受与认同感。
(二)受众—修辞劝说理论的核心因素
修辞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对于受众的研究置于其学科的核心地位。亚里士多德将“受众信念”作为修辞诉诸的重要基础,认为言说者只有使自己的言说过程符合受众的价值期待才能顺利说服受众。语言行为发出者务必要去探究如何才能使自己运用的语言能够条理清晰地论证观点,令话语受众产生信任感与认同感,与此同时还必须极力展现出语言行为发出者所拥有的某种性格特质,明白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使语言行为受众产生某种特定的心境。也即是说,语言行为发出者必须充分关注受众的信仰、价值观、社会地位等因素,修辞者要想使受众成功得以被劝说就必须架设起与受众之间的关联,用受众熟悉和认同的语言方式述说,修辞者的首要目标就是构建与受众的共同立场。修辞学家Perelman在《The New Rhetoric: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一书当中,着重论述了受众的重要性。他认为,论说者必须不断贴近和适应受众才能使言说效果达到最佳。即便是在独自构思阶段,论说者也须将自己设想成受众,确保能够获得他们心理上的赞同与合作。
(三)“劝说”与“认同”——修辞劝说的核心概念
修辞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言说的艺术”,亦是一种“劝说的艺术”。为了实现成功劝说目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格诉诸、情感诉诸和理性诉诸三种修辞劝说模式。运用这些模式可以使言说具有说服力。在修辞学研究中,伯克提出的“认同”概念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人们通过各种不同的特质来构筑自我,当自身的这一特质与他人发生联系时,我们便与他们分享共同的本质。伯克用“认同”这一概念来表述事物之间的“同质性”,“他将‘劝说’看作是‘同质性’或‘认同’,认为能否获取语言受众的认同感直接决定了修辞行为最终能否获取成功——‘劝说’是由‘认同’最终引发的结果”[5]59。只有当我们使用他者的语言方式,在言辞、姿态、形象等方面与受众相一致时,我们才能得已将他劝服。“认同”本质上是实现修辞目的的一种手段。当言说者与受众彼此之间确立了某种“认同”时,劝说的预期目标便达到了。
二、政治文献外译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的理据
政治文献外译是外宣翻译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外宣翻译虽以“劝说”和“沟通”为目标的修辞性话语行为分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但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众多方面存在共性关系。政治文献外宣翻译是国家对外宣传中的一种翻译实践行为,其本质也是一种修辞行为。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契合性十分显著。
(一)话语修辞与政治文献外宣翻译均以“沟通”为最终目标
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诉诸即是为了激发受众情感,使受众萌生同情、唤起受众的注意力并接纳语言行为发出者的观点,而采取相应行动的修辞手段[3]。语言行为发出者需要善于体察语言行为接受者的心理,通过激发语言行为受众的情感促使他们产生某种认同。如若想要有效操纵情感诉诸修辞手段,就必须对产生情感的心理状态、激发这种情感的动因以及情感的宣泄对象等进行仔细的探究。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将各种话语行为受众进行细致的划分,对各个受众群体的品性特质加以阐述,进一步去探究通过何种途径与方式可有效激发话语受众的情感。
其次,修辞行为与政治文献外宣就动机来讲,他们之间很大程度上具有“同一性”,两者在动机上显然都隐含有一定的“劝说性”。“西方修辞学历来都将修辞视作一种‘说服的艺术’,它是一种借助于象征手段对他者的情感、思维以及看法施予某种影响的实践性行为。”[2]2当代修辞研究学者伯克将修辞界定为一门“认同艺术”,“他认为现代修辞的目的主要是‘劝说’和‘沟通’”[7]。我国传播学学者则认为:“传播效果就是指受众主体自身因内隐有说服性动因的传播性行为所引发的其心理、看法及行为当中的变化。”[8]由此可见,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作为一种传播话语,其劝说属性是十分显著的。修辞学研究当中的“劝说动因”“有效沟通”等理论观点与政治文献外译目标两者间的契合点,为在政治文献外译中引入这一理论视角提供了充分的理据。
由于其定位于中高端消费,且配送范围只有3千米,所以盒马鲜生在选址上面临着比一般商超更高的要求。这样看来,盒马鲜生试图通过门店与仓储合一的模式降低成本,实则是走到了事情的反面。
(二)修辞劝说理论与政治文献外译均突出受众的核心地位
综上所述,在建筑给排水工程管道安装过程中,应加强对工程项目的规划和设计,按照既定的施工流程,科学合理地安装给水和排水管道。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施工单位应予以重视,以便能够及时地进行补救。另外,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施工单位应对管道材料和施工设备的质量等进行严格把控,同时还应加强一线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以增进其对管道安装工艺要点的理解,提升其实际操作水平。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以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为例 刘小晴,等 5—96
西方修辞学自产生之日起,一向十分重视对于受众群体的研究,不论是古典修辞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还是之后兴起的新修辞学都一直将“受众”作为修辞学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新修辞学学者Perelman认为,所有的论说行为均应适应受众,要以受众所接受的方式展开和推进论说行为。当代修辞学家伯克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后所提出的“认同”理论认为,“认同”的最终结果与目的是为了“说服”,话语行为发出者的表述方式无法获取受众的充分认同,其结果就必然无法说服受众[5]41。
英语是一种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帮助学生建立自信,扫除心理障碍。合理的教学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进教学方法。教师在英语教学中的角色始终是引领者和领路人,是英语学习方面的教练。教师要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让学生充当教学活动的主角,而不是把学生当成灌输知识的容器,这只能让学生被动的学习。
综上,修辞学与政治文献外宣翻译在“有效沟通”上均将“受众”作为其主要关注点及出发点,并在这一内容上形成了深刻共识。因此,政治文献外宣翻译实践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参考修辞学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成果尝试探究新的跨学科翻译策略。
三、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中修辞劝说理论介入的有效途径
(一)政治文献外译过程中修辞诉诸三模式的介入
政治文献外译从本质上来看,是译者接受原著作者和翻译发起人委托与国外受众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与交际互动的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成功说服受众——国外受众接受并认同政治文献中所述观点,正是政治文献外宣翻译力求达到的宣传效果。译者要主动提升自身的修辞意识,运用多样化的“说服”手段去描述和构思译本话语,才能有效地实现文献翻译的外宣效果。译者须善于利用有效的诉诸手段,特别是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劝说效果来进行译文话语构建,才能顺利实现外宣翻译的预期目的。
中国十多年来的研发投入增速(20%)、投入总量(世界第2)和投入强度(翻了一番)都十分引人注目,且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两大特点决定了研发投入总量仍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一是中国的研发强度只有2.12%(2017年),与很多创新型国家(地区)2.5%以上的水平差距较大,在GDP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研发投入总量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二是中国约75%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这一比例超过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地区)。鉴于企业天然的逐利性,在企业研发投入占主体、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还较低(不到2.8%)的情况下,中国研发投入增长的动能十分强劲。[2]
其次,修辞情感诉诸在政治文献外宣翻译当中也能够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善于运用情感诉诸手段可以有效地拉近政治文献译文译入语受众与源语国之间的心理距离,消除受众对源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固有偏见及隔阂,进而转化为他们内心对于该国政治文化的某种认同感。此外,修辞者——政治文献外宣译者,还应极力展现原文作者的理智、美德和善意等人格魅力,从而向译入语受众投射出一种与人为善的形象。
修辞学理论中的情感诉诸、人格诉诸和修辞理性,三者是最能有效感染受众的三种模式。“修辞理性作为实现劝说过程的核心手段,能够以某种形式、推理模式以及惯例去打动受众并使之信服。”[5]59修辞理性诉诸要求政治文献外宣译文在构建过程当中要极力展现出文本内部良好的连贯性及逻辑性。译者要极力使文献译本的语言表述过程、语言逻辑关系、感染模式等因素能够契合他国译文读者对译入语译本的阅读认知期待以及对译本话语逻辑的期待。如据中国外文局阿拉伯语译者王复在与其他译者讨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党校姓党”一词的翻译上,有的译者主张将其翻译为党校必须要绝对跟着党中央,没有必要将“姓”一词直译出来;有的译者则认为,中国人提到“姓”时,是在说明一种绝对的从属关系,就如一个人说到自己姓张,就是在表达自己的身份在根本上是从属于“张姓家族”。中方译者在与外方译者充分讨论后将这一说法最终翻译为“党校的姓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并在后面附上了注释,这样的翻译方式既忠实了原文,同时也使得译文能够充分体现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其讲话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自身的话语风格。另一方面,这样的译本其语言表述、语言逻辑关系、感染模式等几方面都契合他国译文读者对译入语译本的认知期待以及对译本话语逻辑的期待。
不同语种当中对于政治文献中同一措辞的处理也能够体现出译者对于译入语受众的关注。例如,在翻译“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的“惊天地、泣鬼神”这一语汇时,在不同语种译者的翻译方式上能够看出一些微妙的差异性。英语将这一说法译为“earthshaking”,日语则将其译为“天地を驚かせ、鬼神をむせび泣かせる”。英语把它翻译为“撼动天地的”,日语则是采取了相对直译的方式。这一不同的处理方式,反映出译者充分观照了不同民族文化当中受众对于“鬼神”在认知上的差异性,充分运用修辞手段诉诸受众情感而做出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超越美学反对单一理性,注重情感的培养与生成。康德将人的心理机能划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美学属于情感判断领域,康德此举与其说奠定了美学学科地位,不如说强调了哲学中的情感研究,承认了非理性存在的合理性。后来叔本华、尼采等人正是在非理性的基础上陆续发展了意志学说。20世纪以来,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思潮等学派轮番打击单一理性,彻底摧毁了古典时期的理性骄傲。虽然这种非理性的扩张远远超出情感的培养,但情感在生存中的地位借着非理性思潮的崛起也上升不少。
(二)以受众为中心,提高政治文献外宣译文的可接受度
政治文献外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译入语国家受众进行“说服”的过程,因此可以认为,文献译文文本能否最终得以有效感化和影响译入语读者,是衡量译文翻译是否成功的核心准则。目前,聚焦“受众因素”在文献外译当中已达成普遍共识。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去发现将这一认识转化为翻译策略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故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受众中心”这一修辞学策略,去达成政治文献外译在翻译初始阶段预设的译介效果。
“修辞行为在修辞学当中被视作是一个‘双向互动、立体建构’的多维度结构,是修辞者与接受者两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在多维度层面的展开。”[12]政治文献外译活动中,主体是译者与受众两者,翻译行为实质上就这两者之间的交际与互动,这一过程当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始终围绕“受众”。
修辞学理论在讨论修辞行为中的“互动关系”时提出的“预设”和“言说策略”,完全可以为政治文献外译过程中译介策略的选择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借鉴。双向交流当中的“预设”可以将其界定为三个类别:经验预设、角色预设以及价值预设。遵循这一理论观点也能够为政治文献外译提供一种可操作的运作模式,即:译者在进行文本翻译时,可提前对未来译入语译本读者的价值观、情感认知、生活体验及其身份进行一定的预设,并随之对译者自身的翻译策略、修辞技巧、诗学手段等做出相应调整,有效地构建译本话语体系,进而顺利地实现译者与读者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提到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两个典故,译者充分考虑到译本读者的价值观和情感认知,并没有将中国的传统诗词照搬过来或者进行直译,而是通过意译的翻译形式,将两个典故分别译为“治理一个大的国家需要非常细致,就如同你在烹饪一条小鱼”以及“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小官,但我们的心总是和老百姓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翻译形式,有效地通过译者自身的翻译策略和修辞技巧对译本进行了调整,从而使国外读者受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文献当中所表达出的原作者的思想内涵。
有一年,父亲因为手术后养病,大一放暑假的我第一次扛起铁锹,穿上父亲的雨靴去浇水。从没有打过拦水坝的我站在水中,一次次放土方,可土方一次次被水冲走,最终还是在母亲的帮助下才打好了坝。我精疲力尽地坐在渠沿上,看着被泥水灌湿了的双腿,深深体会到了父亲浇水的不易。
此外,译者在译前还需能够提前对译本读者进行充分的角色预设,尽可能准确定位未来译本读者群,这是提高政治文献译者受众意识的必然要求。文献译本源语国与译入语国家之间,在地理、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方面必然存在诸多差异,完全直译源语国政治文献的语言表述的“异化”翻译方式,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源语国受众与译入语受众之间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阿拉伯语的翻译过程中,外方专家建议将“大国外交”中的“大国”翻译为“大的力量”。他认为,在阿拉伯世界当中,“大的国家”首先会被认为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较大,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国家都符合这个标准,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的沙特等国家。但是“大国外交”中的“大国”是指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些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而并非单单指国土面积。但中方译者则认为,20世纪的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曾经被译为“大的力量”,如果将“大国”的概念翻译为“大的力量”,可能会导致阿拉伯世界的读者把中国和当年的“超级大国”混淆起来。又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卷当中都曾出现过“民主党派”的说法,中方译者直接将其翻译为“民主的党派”,但是很多外方专家则不认可这样的译法。他们认为,这样的译法会直接导致国外的读者受众产生一种误解——“难道中国现有的党派不够民主吗?”因此,为了有效地消除源语国与译入语国家读者受众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上的障碍,中方译者接受了外方专家的建议。
因此,政治文献外译的译者不论是在译前还是译中都应时刻保持“以受众为中心”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在预设译本受众价值观、情感认知及身份及生活体验的基础之上,依据两国受众之间的差异做出一定策略调整后有效构建译文话语体系,使译本话语与受众在各个层面实现有效对接,最终顺利实现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的预期效果。
四、结语
本文从修辞劝说理论出发,阐述了修辞者品格、受众情感、论证理性三个诉诸原则,受众以及“劝说与认同”三个核心概念。据此,进一步从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的本质属性、特征以及追求的翻译目标及其与修辞劝说理论的契合点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修辞劝说理论介入政治文献外宣翻译并为其提供理论参考的可能性和相关理据。本文从新的理论视角展开的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研究,为今后进一步从多维度、多角度探究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策略以及提高文献译本交际效果提供了一些参考。此外,本研究在修辞劝说理论介入文献外宣翻译的可行性和理据,以及对今后政治文献翻译策略和构建译文话语体系能够提出何种具体建议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的完善与充实。
参考文献:
[1]ARISTOTLE,GEORGEAK.On Rhetoric:ATheory of Civil Discours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28.
[2]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HERRICK,JAMESA.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An Introduction[M].Boston:Allyn and Bacon,2004:83.
[4]刘亚猛.西方修辞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5]袁卓喜.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6]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30.
[7]温科学.中西比较修辞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14.
[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8.
[9]黄有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7-28.
[10]袁晓宁.以目的语为依归的外宣英译特质:以《南京采风》翻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0(2):61-64.
[11]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4.
[12]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
On intervention of rhetorical persuading theory in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ocuments
Zhang Tianyu;Yuwen Gang
(Business Colleg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hetorical persuading theory,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 reference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rhetorical persuading theory in foreign publicity of political documents and its realization channels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ocuments from various aspects,points out the conjunction between the rhetorical theories including the three-model of rhetorical appeals,the receiver-focused and rhetorical aims of persuasion and recognition,so as to lay the theoretic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political document publicity translation by adopting the rhetorical persuading theory.
Key words: rhetorical persuading;rhetorical appeal;political documents;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55X(2019)04-0056-06
DOI: 10.16595∕j.1671-055X.2019.04.011
收稿日期: 2019-03-19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背景下新建本科高校应用型转型路径研究”(GH18172);2018年度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深化山西高校与法国大学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的创新策略研究”(2018041042-3)。
第一作者简介: 张添羽(1979- ),男,山西晋中人,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邹璇)
标签:修辞劝说论文; 修辞诉诸论文; 政治文献论文; 外宣翻译论文;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