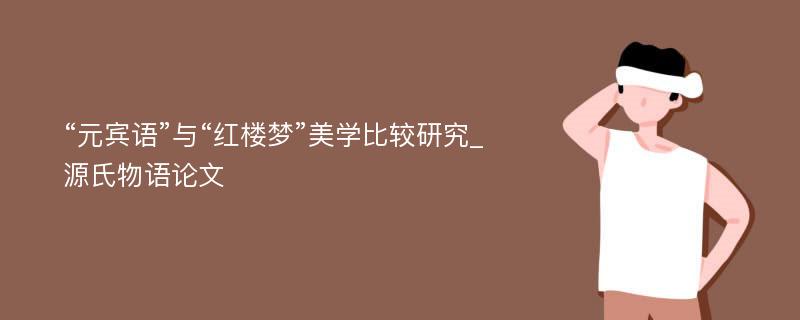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氏物语论文,红楼梦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与日本著名古典小说《源氏物语》同为现实主义杰作。本文从四个方面比较了它们的异同——两部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价值的总体比较,两位作家曹雪芹与紫式部的出身、经历和思想认识高度、深度之异同及其对作品影响的比较,两位男主人公贾宝玉与光源氏的比较以及两位女性宝钗与紫姬的比较。在着眼“同”的同时,也论析了《红》对《源》的超越。
【关键词】弃恶求善 殊途同归 缠绵哀婉 双璧争辉 清新恬淡 雍容华贵 典范哀歌
伟大的作家从来都是他所属时代的产儿,伟大的作品历来都是它所属时代的一面镜子。
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正是两位伟大作家的两部伟大作品。《红楼梦》(以下简称《红》)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扛鼎之作;《源氏物语》(以下简称《源》)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作。尽管它们时隔七百余年,诞生于两个国度,但它们都是富有深刻内涵和悲剧性主题的鸿篇巨制,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在以何种方式弃恶求善上呈现出分道扬镳的趋势,紫式部呼唤着过去,曹雪芹指向了未来。然而,共同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一道谱写了一曲缠绵哀婉的封建主义的挽歌。这正是千百年来《源》、《红》雄踞于艺术之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些微道理。
一、《源》、《红》媲美,双璧争辉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史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精品,代表着东方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
《源》不仅是日本文学的典范,也是世界第一部完备的章回小说。这部长达54卷、近百万字的长篇物语(“物语”是日本文学的一种体裁,主要指平安朝到室町时代所产生的传奇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问世于11世纪。作者以史实为基础,艺术地虚构了以日本藤原道长执政下平安王朝时期为时代背景,描写了源氏家族荣华、失意、隆盛、式微的历史,纵跨70年的时空。《红》不仅是中国文坛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部长达百二十回、洋洋百万余言的现实主义杰作诞生于18世纪,以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执政时期为时代背景,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飞跃100多年红尘。
《源》是日本著名女作家紫式部呕心沥血的杰作,《红》是中国文学大师曹雪芹“十年辛苦”的结晶。它们分别把本国的古典文学推到辉煌的顶峰,并给后人留下对于人生的思考,从而激发了后世永盛不衰的探究热情。其中一个令人难解的艺术之谜是:这两部名著诞生于两个国度,相隔数百年,却何以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呢?尤其是对于社会悲剧的揭示上,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部巨著都是从一个家族的盛衰荣枯入手的。紫式部把笔端伸向了皇族,从人的精神史角度,描写了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平安时代,以降为臣籍的皇子光源氏及其后代薰君(薰君乃光源氏少妻三宫与青年贵族柏木的私生子)为中心,展示了一幅宫廷表面相安无事,实则外戚专权、皇权旁落的日渐衰败的画面;曹雪芹选择了一个“世代隆盛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的贾府,真实地描绘出表面是“康乾盛世”,实则沉滞、老朽、临近衰亡前“回光返照”式的征兆。这样的两大家族,是具备了极其深刻的典型性的,对它们内外关系、命运、遭际的揭示,不可能不触及整个社会的脉络神经,传达出时代的全频信息。
正是这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歌舞升平中预感到统治阶级将至灭顶之灾,以令人拍案叫绝的形象系列共同唱出了震荡乾坤的封建末世的哀歌。当我们读着、咀嚼着《源》、《红》这两部史诗性的艺术珍品,又何尝不象贾宝玉品尝“千红一窟之仙茗,万艳同杯之灵酒”[①]一样,感到清香甘洌,纯美异常,魂萦梦绕,回味无穷呢?当我们细心品味着、比较着两部“各有妙文,各有美景”[②]的艺术佳作,顿觉它们犹如一衣带水的双璧联珠,共同放射出“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③]的灼灼光彩,共同创造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美。
《源》与《红》的两位作者都认和生命缠绕难分的爱情为主线,创造出“六条院”和“大观园”这样两个不同国度的“女儿国”,通过对女儿国众多红颜薄命的女性的描写,演绎出种种令读者梦牵魂绕、悲红悼玉的警幻之曲。《红》在第5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曾以“千红一窟”之仙茗,“万艳同杯”之灵酒相款待。甲戊本对“千红一窟”侧批云:“隐哭字”;对“万艳同杯”侧批云:“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深得《红》创作之真谛的脂砚斋,道破谐音,点石成金,令读者如拨云雾,茅塞顿开。对照《源》、《红》两部奇书,无论是光源氏的12个妻妾,还是金陵12钗,众多女子悲惨的命运确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剧。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人格美是我们的感觉能领悟的世界中的最高的美。”[④]《源》和《红》集中表现了“女儿美,爱情美,人格美的毁灭”[⑤]。为女性悲剧的人生,为女性人格的独立,发出了最强烈、最深沉的呼唤,演绎出美的毁灭的悲剧。莱辛说过:“悲剧是一首引起怜悯的诗。”[⑥]这正是我们从中引起爱怜的审美心理特征的原因。在两位文坛巨匠的笔下,“女儿国”中的女性,人人都是窈窕淑女,个个都是阆苑仙葩。她们越美,那么,这种美的凋零、残落、消亡就越可悲,而越是在凋零、残落、消亡之后,这种对美的惋惜、追忆和向往,就越动人,越神妙。在这里,日本川端康成式的“悲即美”的命题和曹雪芹的“美即是悲”的命题便息息相通了。
无论是《源》还是《红》,在写社会悲剧时都避开了战火弥漫、饥殍遍野的荒年乱世,而落笔于“昌明隆盛之邦,花柳繁华之地”,都借爱情写社会。可以说,爱情描写是《源》、《红》中最精彩的篇章,离开了优美的爱情故事,也就失去了“双璧”的美学价值。不过,在对社会悲剧本质的剖析上,《红》比《源》更深刻、更广泛。《源》写的是一部贵族社会的“艳情史”,而《红》写的则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源》所描绘的社会画面狭窄,主要写宫庭贵族,围绕源氏一家生活起居,多写情人幽会,社会性较弱;《红》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广阔,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平民,围绕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集中写封建社会的全貌,多带社会性。因此,《红》比《源》更具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另外,日本的文化历史远逊于中国,紫式部生活的时代,日本文学初兴,仅受唐诗影响而已。而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古典文学积淀丰厚。因此,两部作品相较,《红》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平都远高于《源》,这是客观的,毫无疑义的。
《源》的主题是通过源、紫(光源氏和紫姬)的爱恋与婚姻去揭示贵族精神上的没落和崩溃;《红》的主题是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的剖析和批判。《源》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过程,而《红》所着力显现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在旧势力压迫下毁灭的过程。紫式部向读者描绘的是一幅纲常沦夷、道德败坏的传统大厦的坍塌图,比紫式部更进一步,曹雪芹不仅展示了传统的崩溃,更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震聋发聩的叛逆者、反抗者的悲歌。
《源》以清新恬淡的质朴美,《红》以雍容华贵的古典美,流传后世,形成文学史上著名的《源》学和《红》学。《源》、《红》媲美,双璧争辉,便构成了世界文坛上令读者赏心悦目、耐人寻味的综艺大观。
二、天涯沦落,病蚌成珠
艺术的永恒主题,便是追溯人类历史,冥想人类未来,反思人类存在。若非有特殊经历者则很难写出愤世嫉俗之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论述可谓精辟,一言以蔽之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⑦]二知道人说得更具体:“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一把辛酸泪也。”[⑧]作家心中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而才发愤著书,回忆人生荣枯消长,抒发对社会的盛衰兴亡之感,“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语)因此,作家不寻常的经历往往成为饱含血泪著书的真正动因。
《源》、《红》的两位作者同遭家道中衰之变,同尝个人丧偶之苦,同有晚景悲凉之感。这恐怕是他们的创作取得惊人成功的秘诀所在。
紫式部与曹雪芹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且和皇族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紫式部当过一条天皇的皇后彰子的女官,为她讲解《白氏文集》(白居易的诗文集《长庆集》)。多年的宫庭生活使得她对皇亲国戚的争权夺势、互相倾轧烂熟于心。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皇帝的侍读。康熙帝五次“南巡”中有四次都住在曹家。父辈曹顒、曹俯连任江宁织造要职,财势和权势使得曹家显赫一时,和最高统治者的关系非寻常人家可比。紫式部和曹氏对朝庭内幕的耳濡目染,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非常人能及的丰富的素材。
由于紫式部和曹雪芹都是“从旧垒中来”,对其中“情形看得较分明”(鲁迅语),对封建贵族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了解透彻,对贵族家庭由盛及衰的崩溃过程看得较为真切。这也决定了他们都有着较浓厚的贵族意识,同具对末世的敏感,他们的同情不同程度地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的”(恩格斯语)。因而,紫式部对贵族和贵族生活的描写充满赞美和欣赏,往往以俊美、多情来掩盖贵族的罪恶;而曹公则对封建世家含情脉脉,不断地向统治阶级敲着警钟,不停地唱着“补天”的挽歌。正如他的朋友敦敏在《赠芹圃》诗中所云:“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
紫式部与曹公经历的又一相似之处是“朝荣夕萎,中途逢变”,最后成为“身世浮沉,天涯沦落”的同命人。
紫式部出身中层贵族家庭,祖上三代都精通日本典籍和汉诗文。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的她,儿时便聪颖过人,从小随父学习汉诗。22岁嫁给比她大20岁的地方官藤原宣孝为妾(第四房妻子)。婚后生有一女,两年后丈夫不幸死去。矢志自守的紫式部抚养着女儿贤子,过了5年孤苦伶仃的孀居生活。29岁入宫为女官,侍奉中宫彰子。多年的宫庭生活,使她亲眼目睹了宫庭妇女的不幸遭遇,对她们悲惨的命运有深切的感受。《源氏物语》就是通过这种人生体验,在她寂寞寡居的生活中,写成前半部分,到宫中做女官后又完成后半部分的。
曹雪芹的出身不同于一般的达官显贵,而是作为汉人早年加入满族旗籍、始终倍受恩宠的百年望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贵族世家,由于受到康熙和雍正政权交替期间政治斗争的株连而招致抄家之祸。此时年仅13岁的曹雪芹便由钟鸣鼎食之家的贵公子一变而为罪囚的后代。再加上家门不幸,历经人生三悲——早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最后流落北京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窘生活。这种生活剧变使曹雪芹饱尝了人间冷暖,历尽了世态炎凉,这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真正缘起和契机。
由此看来,紫式部和曹雪芹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坎坷,都有一种“世事无常叹飘零”的感伤。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悲观主义、厌世主义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源》和《红》是两位作家历经人生失意后写成的巨著,是他们心怀郁结后吐出的珠玑。然而令世人遗憾的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两位伟大作家都未能将大作写完,便积劳成疾,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使得两部伟大作品竞是残缺的未竟之作。尽管后人将它们续完《源氏物语》据说为紫式部之女贤子所续;《红》由程伟元、高鹗所续),但续作又都逊于原作,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两个民族无法弥补的缺憾”。[⑨]
当然,我们在看到两位作者身世相似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他们出身经历的不同之处:
紫式部由于女子生活环境的局限,接触社会面狭窄,长期的闺阁、宫闱的生活限制了她的视野,故而书中反映出以爱情为重的女子心态和贵族格调;而曹雪芹则历经沧桑,生活环境由尊富到贫贱,反差极大,他有幸接触到平民百姓,加之他朴素的民主意识,书中融进平民思想,能透过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看清封建社会不可挽救的历史趋势。紫式部在书中无心补天,唯有身世的慨叹;曹雪芹受阶级时代的局限,留下“补天”未遂的遗憾。
作家出身经历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他们对生活的认识高度不同,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对社会批判的力度也不同。
两位作家都在竭力反映他们生活的时代及他们所熟悉的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尽管紫式部在书中一再声言“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曹公也一再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庭”,“虽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然而,他们的作品都如实地描绘了封建社会的全貌,成为反映贵族生活的全景图。
在紫式部的作品中,无论是左大臣掌权,还是右大臣得势,无论是入世还是出家,都改变不了“末世”的境况。在曹雪芹的笔下,无论元妃省亲还是宝玉中第,无论是“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王熙凤,还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的贾探春,都阻挡不住“盛席华筵终散场”的到来。所以他们都从本质上写出了贵族的骄奢淫逸,堕落糜烂,展现了人伦的丧落,光明的无望。无论是《源》中的光源氏、左马头、头中将们,还是《红》中的贾珍、贾琏、薛蟠们,他们都一样挥霍无度,坐吃山空,勾心斗角,安富尊荣,都一样的少廉寡耻,轻薄浮荡,偷鸡摸狗,营私舞弊。这样的“不肖子孙”何谈“补天”,只能加剧危机,成为家族和封建制度的掘墓人。两部作品还从历史的纵向上,写出了贵族子弟一代甚于一代的精神危机,显示出封建社会没落之必然。《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恶性延伸、代代相传、愈沉愈甚的下垂曲线,是一部贵族阶级的精神没落史。《红》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封建阶级一代不如一代的示意图。“文”字辈昏聩无能,于国衰家败束手无策,“玉”字辈更是沉溺酒色、声色犬马,同样是一部贵族家庭的衰亡史。
两位作家在揭示贵族社会后继无人的危机上也有其相似之处。他们都意识到,在以血缘、世袭为特征的封建制度中,权力的继承往往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王朝的最为敏感的焦点,有传宗接代者可能使家声大振,社稷平安。“无后”则为“不孝”之最,令人惶惶不可终日。两部巨著对贵族家族衰败原因的揭示,继承人问题是重要因素。但《红》比《源》更进一步,它不仅写出了浸透了贵族劣根性的垮掉的一代,而且也写出了以宝黛为代表的敢与封建正统势力相抗衡的崛起的一代。《红》比《源》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源》中所涉及的人物都封闭在狭隘的贵族世界里,书中的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桐壶帝,朱雀院,冷泉院,无一不被描写为多愁善感、无所作为、缺乏自主精神的感伤主义者。主人公光源氏和薰君也被塑造成颓废、放荡、意志薄弱、逆来顺受的贵公子,以此来揭示封建统治者及贵族阶级的奢华、淫逸、空虚和腐败。而《红》并没有局限在公子闺秀中,它写出了众多个紫式部不屑一顾的社会下层的“小人物”,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特别是对他们“一处不了又一处”的“作反”的描写,深刻反映出在社会底层挣扎了两千余年的奴隶在近代曙光到来之前,具有全新意义的觉醒和反抗,使读者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看到了封建社会摇摇欲坠的现实。《源》对贵族社会的披露往往是含蓄的、温情的,甚至带有欣赏、玩味的成分,而《红》对社会悲剧的成因看得更透,哀叹得更深,批判也更尖锐、更有力。
总之,由于紫式部与曹雪芹所处时代的差异,民族的差异,人生遭际与经历的差异以及审美理想的差异,使得《源》更多地表现了旧制度悲剧性的历史,《红》则更多地显示了封建社会旧传统旧制度的日渐衰亡。
三、源氏、宝玉,男角竞美
徜徉于《源》、《红》绚丽多姿的人物画廊中,数以百计的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无一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若从审美的角度比较一下两部作品的男女主人公,便可“借一斑以窥全豹”,看出两位作家审美理想的异同。
《源》中的光源氏和《红》中的贾宝玉都是作家着笔用色最多、感情倾注最深、浓墨重彩、精镂细雕的中心人物。他俩象一对“孪生兄弟”,都经历了混世、厌世和出世的过程,且在出身、追求和结局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光源氏和贾宝玉同出身于“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整日过着“富贵温柔、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且都是聪慧过人、品貌出众、能诗善文、惹人喜爱的“情痴情种”。他们都生得美貌超群,俊俏无比。源氏“光华照人”,“美艳绝世”,被誉为“光君”;贾宝玉同样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风流倜傥,“美玉无瑕”。两位作家在主人公塑造上所取得的共识,无非是为男主角在生活中充满粉腻脂浓、花娇月媚提供优越条件。
源氏和宝玉这两位公子哥,虽然生活在朱门绣户,但都不热衷于仕途经济。源氏一再表白“自己无心仕途”,宝玉更是蔑视富贵功名。尽管他们天天受着封建贵族思想的熏陶,仍旧“不思进取”,“逐客去向叹渺茫”,最终也没能象统治阶级所期待的那样走仕宦道路,做一个“济世治国”的能臣,相反却都成为“富贵不知乐业”的“败家子”。
源氏与宝玉都没有“男尊女卑”的念头,却有“惜香怜玉”的思想。源氏认为,“世间女子个个可爱”;宝玉也认为,“女儿是水做的”,“我见了女儿便清爽”,“山川日月之灵秀只钟于女儿”,“男人是泥做的,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
好色,荒淫是封建贵族追求享乐的一个重要方面,混迹闺阁、追逐女性是贵公子的劣根性。但宝玉对女性的倾慕与“泛爱”与光源氏对女性的追逐与占有,有着本质的不同。
光源氏追求的是性欲的满足,是腐化淫乱,是丑。他凭籍相貌俊美而深得闺中裙衩的爱慕,从十几岁起,便开始了偷香窃玉的放荡生活。上至与他的继母藤壶女御发生了乱伦关系,下至与出身微贱、地处偏远的明石姬私通,从十岁的幼女到六十岁的老妇无不染指,先后与12个女性发生恋情,无休止地宣泄他的淫欲,甚至荒唐到闯入弘徽殿,去和他政治上的仇敌弘徽女御的妹妹胧月夜私通,导致他被流放到僻远的须磨。这证明他精神上已堕落到连权力、地位、政治前途都视若儿戏的地步。
贾宝玉追求的是“情”,他重情胜欲,是美。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在姊妹中过一辈子。他爱黛玉、喜宝钗、亲晴雯、近金钏、续《南华经》、作《芙蓉诔》,都贯穿在一个“情”字中。就是这个“情”字,反映了贾宝玉对封建道德的背叛和对新生活的追求。尤其是在宝黛爱情中,就更鲜明地显示出这个“情”字在反叛旧道德中的力量和作用。
源氏对女性有情,但他用情不专,朝三暮四,逢场作戏;宝玉专爱黛玉,至情至深,痴情不改。源氏情场忏悔是假,玩弄女性是真;而宝玉是尊重女性,平等人道。可见,宝玉对女性的“泛爱”,是有其民主思想基础的。
两部书通过源氏和宝玉对女性的“泛爱”的描述,充分证明了在封建社会里总是存在这种畸型现象: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纵容色情淫欲,并从制度上给予法律保护,正如恩格斯所尖锐批评的那样,“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⑩];另一方面却又严禁真正的爱情,开口“万恶淫为首”,闭口“男女之大防”,爱情被当作淫乱,这正暴露了封建制度自身的腐朽。总之,贾府的不可克服的颓败危机,是在“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之盛中显露出来的,而光源氏的精神崩溃,并非是他时乖命蹇、退避须磨之日,而是在荣华绝顶、“毫无缺憾”之时到来的。他的堕落,标志着封建社会所期待的栋梁的朽烂;而贾宝玉则在预示内部坍塌危险的同时,显示了外部冲击的威胁,他的叛逆正是对封建社会这“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所难以承受的致命一击。
由于源氏和宝玉均遭爱侣早丧的苦痛,精神变得一蹶不振,终究未能逃脱“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循环,最后落了个遁入空门的结局。
源氏自最宠爱的夫人紫姬病逝后,精神颓废不堪,又一次感到“世间一切都可厌”,他贪恋女色的癖好也象朝露一样散得无影无踪,最后只身隐居嵯峨佛寺,悄逝而终。同样,贾宝玉自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林黛玉病逝后,“连个说知心话儿的人也没有了”,变得精神萎靡,疯疯癫癫,感到世事无常,荣枯无定,于是万念俱灰,终于脱离污浊的尘世,遁入了佛门。
两位作家世界观和审美观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笔下人物的不同,贾宝玉的思想林比光源氏具有一定进步性,是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超越”。源氏的“泛爱”是建立在“始乱终弃”的基础上的。他因女性的千娇百媚能满足他精神和肉体的贪欲,所以才热恋她们。他的泛爱之举,更多的是一种统治者对下层的恩赐,一种带有自我欣赏的表白,一种以柔清似水的方式显现出的占有欲;而贾宝玉的“泛爱”是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的,是以尊重对方的人格为前提的,更多地表现在对姐妹和丫环无微不至的体贴、关心和同情,宝黛爱情和源紫爱情之性质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源紫之恋是建立在非自由、不平等基础之上的。表面上似乎朝朝暮暮,卿卿我我,然而实质上却是一场悲剧。无论紫姬怎样独享专宠,但她仍是被框入等级格式的一个充塞物,是按贵族标准由源氏一手培养起来的,充其量不过是源氏意愿的对象化而已。他们展示给人们的“幸福”,更是充满封建霉腐气味的夫贵妻荣,是夫为妻纲的婚姻观的图解;而宝黛之恋,是建筑在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上的。他们之间的心心相印、生死相依的纯真爱情,显示出对封建主义人生道路的彻底背离,对新的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因而,宝黛之恋比源紫之恋更富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更具催人泪下的美感力量。性质不同的爱情,其结局必然迥异。源紫之恋为统治阶级所赞赏,引为美谈;宝黛之恋为封建势力所不容,遗恨千古。
总之,在紫式部和曹雪芹的笔下,他们的主人公光源氏和贾宝玉都是封建贵族圈里“善”的化身。在对待女子的态度上,前者“为了恋情,一生一世不得安宁”,后者“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酬不暇”。然而,表面的相似并不等于本质的相同和思想内涵的一致。光源氏的“善”使他向着封建规范越靠越近;贾宝玉的“善”则使他在叛离封建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正是两位同怀改变不合理现实的作家,在以何种方式弃恶求善上呈现出的分道扬镳趋势的证据所在。
四、紫姬、宝钗,女角比贤
以东方传统道德而论,紫姬和宝钗都堪称“贤淑女子”的楷模,“四德皆备”的典范,都是封建社会倍加推崇的“最可爱”、“最理想”的女性。她俩在才貌、品德和命运等方面亦有许多相似之处。
紫姬与宝钗在《源》、《红》两部书中同处于女主人公的位置(宝钗为仅次于黛玉的第二女主人公),且都以标准的淑女姿态出现。从外表看,二人均有一种符合封建要求的典雅美,既拥有令人倾倒的花容月貌,又不乏大家闺秀的淑仪美态。紫姬在书中被比作日本的“群芳之冠”——樱花;宝钗在书中被誉为“百花之首”——牡丹。在形貌和气质上皆可谓天姿国色。她们妩媚艳丽却无轻佻浅薄之相,典雅端庄又不存矫揉造作之态,俨然是一种大家风范。从才艺上看,紫姬和宝钗均备上品女子的才华禀赋和文化教养。紫姬琴棋书画,赋诗赠答,无所不能;宝钗品诗论画,针黹女红,无所不精。日本著名学者井上靖用一句话概括出了封建社会理想女性的标准:“用美貌或才华来侍奉宫廷和博取高级贵族宠爱是贵族妇女的唯一出路。”[(11)]紫姬和宝钗同被封建社会奉为“楷模”,其原因不仅因为她们在才貌上可博得封建家长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她们在思想性格上能博得封建家长的欢心。紫姬被作者塑造成“众善兼备的完人”,“不可多得的理想人物”;宝钗被作者描写成封建家长“喜爱不尽”的“品貌超群”的上品女子。前者把源氏放荡不羁所激起的怨恨深埋心底,“绝不形于色”;后者则为规劝“宝二爷”言行,苦口婆心,不遗余力。二人均以恬静稳重、温柔敦厚、谦恭宽容、忍耐顺从为主导性格,这是封建社会标准的女性的美德。她们同有高贵的血统,紫姬的姑母是皇上的宠妃,宝钗的母舅任九省统制;又同有殷富的家境做后盾。这样的身份、地位是其她姐妹无法与之相比的。但她们从不骄纵自己,怠慢他人,同有一种长者风度。紫姬谨言慎行,举止矜持;宝钗罕言寡语,安分随时。最终,紫姬成为源氏的正妻,宝钗也当上了宝二奶奶,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紫姬之淑”、“宝钗之贤”,确在伯仲之间,难分高下,她们都是用封建礼教的“模子”刻出来的“完美女性”。封建礼教是残酷无情的,其本质就是“吃人”。作为它的信奉者和追随者的紫姬和宝钗同样难逃罗网,最终都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
紫姬表面上看,似乎比源氏一族的其他女性“幸运”得多,不仅居于源氏正夫人之尊位,又深得源氏的宠爱,可这一时的“幸运”,片刻的“荣耀”,却是以无止境的痛苦和难言的辛酸为代价的。她必须按照封建道德的准则,无条件地容忍丈夫的恣肆淫荡,绝对保持对丈夫的贞操与忠诚。“寂寞伤心人不知,泪洗衣袖无干日”[(12)]才是她生活的真实写照。最后终因忧思抑郁,凄楚苦闷,悲痛难挨,年纪轻轻竟先于源氏诸妻妾而去。宝钗的命运似乎比紫姬好一些,她察颜观色,极有心计,含而不露,坐待时机。最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13)],当上了尊贵的宝二奶奶。但是宝钗虽赢得了宝玉的婚姻,却没有获得宝玉的爱情,最终难免被宝玉抛弃。心如死灰的宝钗,只得在孤灯下独守空房。从某种意义上说,紫姬与宝钗的结局较其她女性更为悲惨,因为她们都尽力做到那个社会为女人所规定的一切,而正是这些规定埋葬了她们的青春。
当然,由于两位作家不同的审美标准,紫姬与宝钗在性格和感情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纯真未泯,透过心灵的面纱可感到几缕情愫的颤动;后者则城府极深,揭开灵魂的帷幕几乎是一片冷寂的荒原。紫式部笔下的紫姬,性格比较单纯,缺乏个性,属“扁型人物”,多偏重于“善”的方面,作者以欣赏的态度美化她,对她寄于深切的爱怜与同情。作者写紫姬如何“仁义”,写她对源氏放肆的依红偎翠的浪子生活如何大度与宽容。紫姬始终以理压情,安受嗟食,达到了封建社会标准的“善”。对此,书中明显流露出赞美之情。紫式部的紧系于传统道德的“善”的理想,是靠恶的收敛、善的屈从来实现的,靠害人者的恩赐和被害者的克制来完成的。作者企望的平等,是靠不平等关系的稳定来维系的。而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则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圆型人物”。她表面上温柔宽厚,豁达开朗,实则感情虚假,笑里藏奸。作者把她塑造成一个“美丑兼备”、“贤愚并存”的活生生的人物,从而曲折地反映出对她褒贬相杂、毁誉参半的审美评价。宝钗在众小姐群中是一个忠实地奉守纲常的封建卫道士,但却没得到作家那样多的赞许,正如哈斯宝在评论《红楼梦》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时所说的那样:“……只有宝钗,乍看全好,再看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没有什么好……读她的话语,看她的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象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14)]薛宝钗这一复杂艺术典型的创造,正是曹雪芹用笔高于紫式部的绝妙之处。
通过《源》和《红》的美学比较研究和对它们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挖掘,我们看到了有典型意义的贵族之家的衰败的历史必然,并从一个家族的命运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性结局,看到了封建制度本身所蕴含着的走向坟墓的自我瓦解机制和它的瓦解过程,这无疑对清晰地认识封建制度的腐败和没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源氏物语》很晚才被介绍到中国,对于我国大多数人来说,《源》好象近年出土的“文物”,它的丰富而充实的内容更鲜为人知,因此,很有必要认真地分析它,研究它,比较它,介绍它,帮助读者认识它,了解它,进而承认有人称《源氏物语》为“日本的《红楼梦》”确有道理。鉴于篇幅所限,关于两部著作艺术美的比较,只能在《再探》中论证了。
注释:
①②③刘梦溪:《红楼梦艺境探奇》第29、98页。
④《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第9页。
⑤王蒙:《红楼启示录》,第147页。
⑥⑧《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第602页、571页。
⑦司马迁:《报任安书》。 见阴法鲁:《古文观止译注》第401页。
⑨《东方文学鉴赏》下卷,第79页。
⑩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2页。
(11)井上靖:《日本妇女史》第50页。
(12)《日本古诗一百卷》第45页。
(13)曹雪芹:《红楼梦》第997页。
(14)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38回批语。见《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上)第690页。
标签:源氏物语论文; 源氏论文; 光源氏论文; 曹雪芹论文; 贾宝玉论文; 紫式部论文; 日本源氏论文; 红楼梦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文学论文; 贵族气质论文; 读书论文; 四大名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