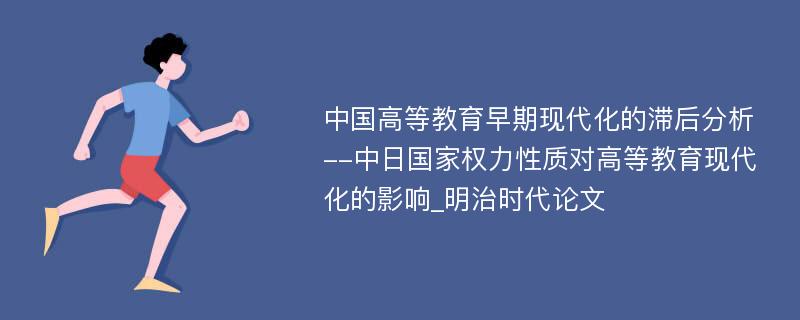
我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延误之原析——中日国家政权性质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政权论文,中日论文,性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两国同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封闭的国门被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炮舰所打开,两国都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的现代化取得成功,并最终脱亚入欧,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巨人。而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则几度成为被侵略和掠夺的主要对象,虽然今天的中国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日本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就社会现代化来说,我们已大大落后于日本!仅就高等教育而言,196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就达到了14.2%,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注:麻生诚等编著:《教育革新与教育规划》,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4年日文版,第110页。), 而我国今天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仅为9.07%(注:教育部编:《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教育事业和21世纪中国教育的展望》,1998年11月 24日,第2页。)。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个被延误了的历史过程。那么,这一延误的因素又是什么呢?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日本著名学者永井道雄在谈到日本的教育现代化时指出:理解日本的教育变化过程时,应该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1 )历史是按自己的规律发展的;(2)后进国家是要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的;(3)日本是具有非西洋文化传统的”(注:永井道雄著,王振宇、张葆春译:《现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毫无疑问, 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所决定的,教育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既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又受制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这是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本文仅从中日两国现代化早期的政权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延误的深层原因。
一
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往往比它与经济的关系更牢固、更密切。因为,农业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国家政权而不是市场,社会的自组织程度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进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是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虽然有剩余产品的交换,但这种交换只局限于地方性市场,国家权力是保证农业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现代工业社会则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取代了区域性的市场,社会生产的运作系统转向经济本身的自组织力量,市场成为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手段,社会也由政治力量起支配作用的政治社会转向受经济力量支配的经济社会,看不见的手成为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因此考察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的政权性质,对于该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所指的政权性质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强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的国家目标、政府主要官员的素质等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一般都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被迫启动的,而这种外部压力刺激的过程正是这些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过程,因此反殖民化的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必然相伴而生。国家作为民族主权的代表者,在实现国家统一、恢复民族主权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正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一个失去主权或国家长期分裂、内战连绵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对于非西洋的后发展国家来说,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严峻的外部世界的挑战,如果它要完成把现代化作为国家重建的任务,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通过威权政治来保持发展中的高度政治稳定,克服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的社会失序和危机,增强社会的内聚力,加强对分散的经济权势的宏观控制,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加强社会动员与促进社会整合,加速社会经济增长,从而为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提供基本的政治与经济环境。这种政权实现的关键又要有一批具有现代眼光的政治家和选择明智的现代化战略。但这种国家政权的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才能保证现代化事业既顺利进行又不至于变成现代化的阻力呢?为了使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以晚清的同治政府和日本的明治政府为重点进行比较,剖析国家政权性质与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我们强调国家政权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但显然不是说这种政治权力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推行现代化的大变革进程中可以无限地集中化和扩大化,以至滥用政治权力,违背教育的客观规律,以政治代替教育,最后必定导致教育现代化的失败甚至中断。
在比较现代化的研究中,人们常常把中国和日本当作比较的对象,的确,这两个儒家文明的东方国家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但它们又有着最大的不同,这就是在早期现代化国家中,日本是唯一取得成功最后脱亚入欧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非西方国家,而中国却走向了日渐衰微、边缘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半殖民社会。决定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何在,正是人们探讨的热点。其中,不少学者都对日本教育在促进国家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经济上几乎全部崩溃,但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却取得了超出想象的效果,经济的增长率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一批现代化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如罗斯托、舒尔兹等就把这一奇迹归结于日本教育在战前的高度发达为其积累了庞大的人力资本。人们大多倾心于日本教育对现代化的贡献,却很少有学者去探讨日本的教育本身又是如何成功实现现代化的。
当西方的炮舰打开中日两国的大门以后,两国都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现代化的运动,中国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开始了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目的;日本在“和魂洋才”的口号下开始了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两国的动员口号和目的都差不多,但结果却殊异。就教育而言,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和现代教育制度,而洋务运动期间除了办起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教育机构外,就没有什么现代教育的制度建树。这首先应归结于两国当时政权性质的根本差异。
二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都发生了政权的更迭,中国于1862年产生了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同治政府。这个政府是满清皇族内部矛盾激化导致的宫廷政变的产物,不具有任何革新和改良的性质,直到1908年她死去,控制满清中央政权达40多年。慈禧太后控制大权期间,主要依靠两种势力来维护其统治,一是以倭仁、李鸿藻、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守旧势力,另一部分是以奕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改革派。
顽固派是由一批昏庸守旧的大贵族、大官僚组成的政治集团。他们因循保守,冥顽不化,始终以天朝大国的姿态傲视一切,视洋人为蛮夷,把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把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学说当作异端邪说,并极力反对“以洋人为师”。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封建制度十全十美,是亘古不变的制度,圣贤经传是最好的学问。他们所要选拔的人才也就是那种熟读四书五经、深谙帖括小楷的儒生,对老百姓则不过是要求他们知晓儒家原则和臣民义务而已。因此,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和传统的儒家伦理成了他们维护传统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手段和工具,这种思想和政治态度,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生产力的停滞和小农经济的保守与落后。顽固派是当时中国势力最强大、政治上最反动的政治力量,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极力阻挠新式学堂的设立和西学、西艺的传播;在维新运动期间,则充当了扼杀维新力量的先锋。且慈禧太后依靠这一反动势力牵制洋务派,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一次次延误时机,只是在八国联军的彻底打击下,才稍有醒悟,开始对八股取士制度作些微的调整。由于形势所迫,最后才不得不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新式学制得以实行,并成立了专门管理教育的学部,这比日本晚了30多年!
洋务派由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地主实力派所组成,他们本质上来说与顽固派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维护传统封建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的基本力量。但他们在对待洋务的态度和对时局的看法上却与守旧派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主要特点是:传统儒学功底深厚,崇尚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的理论。热心西学,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除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赴日谈判并在战后又到欧洲作短暂的考察以外,其它则无人出洋考察过,也基本上无人对资本主义作过系统的研究。因此,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但他们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印象深刻,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不是制度不如人,而是技艺不如人。因此,他们反对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达求富自强的目的。他们所要培养的人才当然是具有“经世致用”的西方技艺又满脑子是儒家伦理纲常的“新式”人才。为此,他们在大量开设现代西式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同时,积极创办西式学堂,尤其是语言学堂、军事学堂和工业学堂,向西方国家和日本派遣留学生,但这些新式学堂彼此之间缺乏联系,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现代教育制度,而且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和买办性。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不仅规模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向保守势力作了妥协。洋务派中,除奕忻以外,其他几位都不过是地方大员而不是中央要员,这也从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作为。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西化,问题是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如何充分利用本国的文化资源使西方模式本土化,从而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是如果现代化启动时期的统治集团从根本上就反对西式的学问和制度,或者虽然部分主张西学、西艺,但仅停留于器物层面而在关键的制度问题上予以抵制,或者主张西学西艺的人本身对西方资本主义没有系统的研究抑或根本就茫然不知,那么现代化就根本不可能在这些传统人的手中实现。由于他们本身既没有受过现代西式教育也不懂现代西式教育为何物,那么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也就不可能最终在他们的手中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来说,由于当时的政权性质是传统的封建政权,政权的统治者又是一批极端守旧的封建官僚和部分根本不懂西方资本主义、仅仅热心洋务而为维护传统封建秩序的地主官僚。前者极力维护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使教育变成科举的附庸;后者虽然积极办理西式学堂,但他们从骨子里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从总体上优于西方的文化教育,只是在某些方面需要借鉴西学以补中学之不足,这样的认识水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扬弃封建旧教育体制,而只能是从眼前利益出发,办一些零星的新式学堂。但这种学堂在官学系统中毫无地位,宦途被人们描述得如此具有诱惑力,以致中国好似实际上也确实是一个出路唯有做官的社会,新式学堂当然也就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且自己又缺乏办理新式学堂的人才,只得依靠西洋人。鸦片战争后的整个晚清政府日趋衰败,对外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中央政权日渐旁落。罗兹曼指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19世纪的清廷统治者愈来愈无力去构思或立志去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更不用说去实践这样的变革了。象那种在四处碰壁的条件下为了应付危机而仓皇地进行防卫性小修小补的作法,实在谈不上搞什么现代化”(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而且“由于省级政府未能发挥其有效的沟通上下的作用,加上中央和基层社会之间失去了平衡,19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变革大多也跟着遭了殃。……随着旧官僚的那一套过分早熟的合理性日趋衰亡,从18世纪腐朽透顶的中央集权退到19世纪的地方主义,最后堕入20世纪的军阀主义,中国就演变为动辄为强暴的、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所左右的国家。”(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同时, 清政府长期实行低税率并让大部分地方财富保留在当地而不是送往国库,这也加剧了地方主义的繁衍滋生,其代价就是破坏民族的整合,中央政府既无力支付庞大的教育支出,也没有能力统筹全国的现代教育事业,在这样的条件下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也就无从谈起。
三
在中国的同治政府产生后不久,日本也产生了明治政府,但明治政府的产生却完全不同于同治政府。19世纪中叶,日本被迫开港后,幕府统治者在列强的威逼下,也同满清政府一样与入侵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从而引起举国的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失去政道,其罪实大”的政府必须退出舞台,否则,日本就不能得救。因此,一批中下级武士在“尊王攘夷”,即“王政复古,驱逐夷狄”的口号下开始了倒幕运动。运动开始时由于盲目地排外,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干涉。后来他们调整目标,认定:如果“继续进行这样的无把握的暴战,恐怕要有连续失败的后果,如果不迅速废除幕府而还政于朝廷,在谋求我国统一的同时,不破攘夷的谬见而执行开国的方针,则一定没有希望维持国家前途。”在这样的认识下,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幕府统治,于1868年建立了明治政权。因此,明治政府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谋求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产物,并一开始就确立了主动开放的国策,而中国理性地执行这一政策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事情,这比日本晚了100 多年!
明治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他不再是依赖封建领主支持的传统皇帝,而是在推翻幕府封建统治基础上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天皇。明治政府在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并收回了“版籍”,把原来的“四公六民”分成中交给大名的四成收归政府(注:参见Ruth Benedict:《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3页。),这与同治政权的封建性、地方势力的隆盛和中央财政的地方化趋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治政府成立时,天皇表示要“破以往之积习”、“求知识于世界”,这与慈禧太后时而盲目排外、时而卖国求荣的对外态度和因循守旧的本质又有天壤之别。再来考察明治时期的掌理朝政者,他们大都是中央要员且具有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比较确切的了解,其中很多人都出国留过学或亲自到西方国家进行过专门的考察。如井上馨、伊滕博文曾留学美国,林有礼、伊藤博文、大久保通利、井上毅、西村茂树等出仕时都只有20多到30 多岁, 年龄最大的岩仓具视也只有43岁。而且他们在改革的认识上基本一致,认为日本只有进行全盘性的改革才有出路,他们不仅各自具有运筹帷幄、笼罩全局的才略,而且能群策群力、相忍为国。本尼迪克特评价他们说:他们是“洞察形式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超过任何民族所曾尝试。”(注:参见Ruth Benedict:《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55页。)永井道雄在评价明治维新成功的政治因素时也高度评价他们说:“第一,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和果断地吸收外国文化的态度;第二,是他们有朴素的唯物史观;第三,是他们具有政治上的决断能力。”(注:永井道雄著,王振宇、张葆春译:《现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他们心目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而不是像同治政府的大员们那样,企图以和约换得永久的太平,和约过后依旧无动于衷。森岛通夫评价说:“从明治维新以来,有成就的政府的一贯目标就是要把日本建成一个有着头等军事能力和头等工业的强国,建成一个不会被欧洲先进国家和美国所打败的国家。”(注: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如森有礼就热心于教育改革, 醉心于西洋,甚至考虑要废除烦琐的日语改说英语,这并不意味着他想抛弃日本,恰恰相反他是出于对日本的爱。而且明治时期的领导人还善于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把握历史的发展方向,如福泽谕吉认为值得向西洋学习的东西很多,但归根到底决定彼此差距的乃是印刷术、电信、邮政制度和蒸汽机动能等,这些东西西洋有而日本却没有,推动历史前进的正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向西洋学习这些知识。他们认为既然实现产业革命和拥有符合产业革命的社会组织是西洋“先进”之所在,那么日本也就必须走这条道路。他们把经济上实现“殖产兴业”,军事上实现“独立自主”作为奋斗目标,并广泛开展现代教育,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为了适应这一目标的教育,一是要普及,二是要注重实用,现代意义上的普及教育却从来不是清廷的努力目标。1872年,以西方的教育制度为楷模,日本颁布了现代学制,并于前一年成立了管理教育的文部省。学制颁布后明治领导人在执行上采取强制的措施,并把官员的选拔与现代教育学历紧紧地联系起来。到1906年,其普通教育的入学率就达到了96%,1907年,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为6年,入学率达98%。在颁布学制的当年发表的《关于奖励学事的布告》中指出,“人人要立其身、治其产、兴其业,以此终生,别无他途,此乃修身、开智、增长才智也”,一开始就确立了教育的实用性。1879年颁布了《教育大旨》和《教育令》,接着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确立了政教一致的制度。此后,直到二次大战战败为止,日本的教育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知识分子的维新运动,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政策,教育和科学知识的获得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在全国推行强制性教育、建立配备有几所帝国大学的较高级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移植到日本,这是明治政府文化政策的几个主要目标”(注: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1885年,当第一届伊藤内阁成立时, 森有礼被任命为第一届文部大臣,森有礼在入阁后不到3个月即1886年 3月1日,颁布了帝国大学令,又一月后,颁布了师范学校令、中学令、小学令,使日本的小学、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及大学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可见森有礼之注重教育并力图构建系统化的现代教育制度,其继任者井上毅也非常注重教育的制度化和系统化。这又与洋务教育的非制度化和非系统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明治政府一开始就注重大学对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吸收,“学制”第38章中指出“大学是教授各种高深学问的专科学校”。1874年把设有法学、化学、工学、各科技艺学和矿山学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迅速扩大,于1877年合并为东京帝国大学。帝国大学以适应国家需要、传授学术技艺和研究学术上的深奥理论为目的,讲究实际学问,培养有用人才。森有礼说:“只有切实改革教育,培养人才。除此以外,别无它途。我所说的人才当然不能只空谈事物之道理或只重视品德,而不充实社会知识;也不能只会读书、写文章,而毫无实际能力。因为当今与外国竞争,这样的愚蠢之辈已不能满足国家之急需”(注:永井道雄著,王振宇、张葆春译:《现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这与科举制所选拔的人才不可相提并论!永井道雄指出:“只有依靠开明的行政领导和统治,才能形成学制改革以来日本教育的特色。”
除了以上提及的几位明治大员以外,天皇本身对教育就非常关心,他还经常深入学校,了解情况,天皇认为日本只有“改革旧制”才能“与列强并驾齐驱”。1871年他在向华族发表的敕谕中说:“要着眼于宇宙形势之变化,学习有用的技能,或者去外国留学进行实地学习,此乃最需要之事。”因此,明治时期为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向西方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即所谓“派遣卿”。1870年派出留学生115名,1871 年派出281名,1872年派出356名,以后逐渐增加。他们是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先驱,其中许多人成为日本现代教育的创始人。同时也高薪聘请外国学者到日本讲学,即所谓“用客卿”(注:参见朱永新、王智新主编:《日本的高等教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而慈禧最大的关注所在,只在于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权和她个人的权位,对“自强”、“求富”的事业,她所关心的也只是想阻止列强的进一步深入,从而采取的也是一种消极的防御观,更没有主动采取推动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任何努力。只是在八国联军之役后才开始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从而仿效日本开始了教育改革,颁布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式的学制。但第一批留美学生竟然未能完成学业就被顽固守旧分子召回国内,直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了留学热潮。两相对比,日本的教育现代化很快得以实现而中国却被远远抛在后面,其原因就一目了然了。森岛通夫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控制权一直紧紧地掌握在信奉官僚主义和从事农业的官员手中,而明治政府的核心则是由以前的武士阶级构成,他们尖锐的意识到了西方国家造成的军事威胁,因而,在日本就存在着一种想要学习和掌握能够给军事力量提供基础的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注: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这一结论是客观的。1918年日本有5所大学和104所高等学校与学院,到1928年时各上升到40所和184所,1945年则分别达到 48所和342所。即使在战争期间,明治的后继者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 他们也注重完善高等教育,特别是科技方面的高等教育。而20世纪的整个上半叶,中国却陷入了极度的政治衰败和社会混乱之中,并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整个现代化都被打断,高等教育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缓慢的发展。
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如此重要,以至它决定了一国现代化的最终成功与失败。著名政治现代化理论家亨廷顿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世界各国之间的最大差别不是他们的政府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败的历史时期。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近40年的时间里经历的恰恰是一个军阀混战、军人政治的时期,国家政权失落,社会失序。要克服这种动荡和衰败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政府,只有强大的政府才能有效地实施国力资源的开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权力象征的表达等主要功能(注: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页。)。对于现代化历程中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政府一直到1949年才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经成立,就全方位地恢复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整整100多年的国家与社会全面衰落和被动挨打的局面, 重新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正轨。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我们多快好省地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在短短的建国后17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建立起了一个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初步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建国初期,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要对旧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造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不可能的。
但这决不意味着专制与独裁也能保证国家和社会朝着现代化的目标健康发展。一旦国家政权被少数人用作满足私欲的机器而恣意滥用时,这样的政府就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难以估计的灾乱。当日本确立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以后,也就意味着它逐步走上了行政的独断专行,“集中”与“民主”两个制动阀中,只剩下了集中。“从那以后,教育以及一般文化做为一种制度,就成了政治性的东西,……由于承认了政治性的文化和政治性的教育,从而就同西洋传统的核心诀别了。”这就造就了明治时代教育的致命弱点,即“行政上统得过死和独断专横;缺少发扬民主自由的计划;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注:永井道雄著,王振宇、张葆春译:《现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4页。)其结果就是军国主义教育的盛行,最终导致其教育的低空飞行以致坠落。二战以后,通过民主化的改造,日本的教育得以获得新生,其发展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明治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并通过50—70年代的大发展,现在其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近50%,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中国“文革”期间的政治运作模式同样严重违背现代政治的基本准则,“四人帮”肆意践踏民主,从根本上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以权代法,大搞政治挂帅,把教育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致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整整中断10年之久,其负面影响却远远不只10年!1978年,当政治与法制、集中与民主的协调关系重新确立以后,一个强大政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正确作用又重新得以发挥,近20年来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辉煌成果就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性质对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作了最好的注解。
标签:明治时代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明治论文; 经济论文; 学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