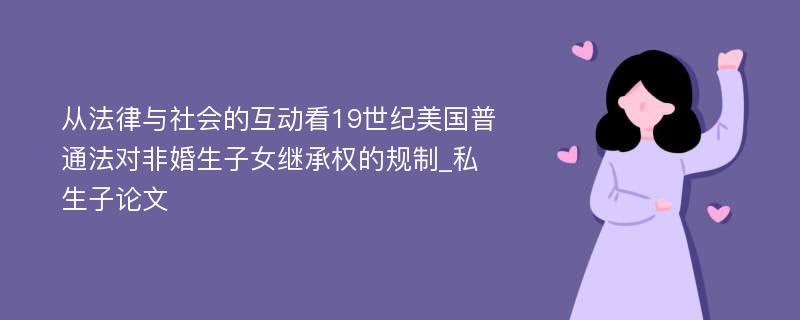
论19世纪美国普通法对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规制:以法律与社会互动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通法论文,继承权论文,互动论文,美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5]12-0097-07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15.12.018 法律与社会密不可分。这一观点为许多美国法学家所接受。劳伦斯·M.弗里德曼直截了当的指出“只要国家存在,就将有法律制度并同社会相始终……法律毕竟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①而在霍姆斯法官看来,法律虽然包含着原则与概念,但是“要使一个概括性(法律)原则有价值,你就必须给它一个载体;你必须说明,它可以被用怎样的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实际应用于一个真实的系统;你必须说明,它是如何逐渐呈现出来的,并且是以人们所体会到的融洽了所有具体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仅凭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不能单独明确的表明它的价值。最后,你还必须说明它与其他一些常常具有迥然不同的时代和起源的原则的历史关联,这样才能使它的命题恰当地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判断。”②法律的“载体”就是那个社会与历史所构筑的“真实的系统”。因之,法律并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③我们不妨依据这种理论,以美国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问题在19世纪的面貌为视角,展示法律与社会互动之下美国法律文化的一个侧面。 本文选择非婚生子女所代表的婚姻与家庭领域作为研究视角,在于家庭是基本的社会文化单元。它是个人发展的温床,是社会保障的来源之一,也是文化传播的机构。因此,家庭是从文化角度审视人类行为的恰当范畴。④而非婚生子女是婚姻家庭领域中一个非常态表现,宗教、伦理、法律、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纠缠其中,其中的纠葛也往往会触动人们的灵魂深处。美国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问题的历史沿革能为我们勾勒美国法律发展的一个侧面。 本文选择普通法作为另一个研究视角,则是因为普通法的灵活性,能够以法官造法的形式因地制宜的解决难题。“今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甚至坚持法律的一些制度定会发展,法律原则相对于时间和地域不是绝对的……无论法学家限制审判职能的纯机械理论是多么完美,司法造法的过程在所有的法律体制中总在进行而且会一直进行下去。”⑤普通法的“法律科学删去武断的法条,根据理性重塑法律原则,并调和矛盾……法官们通过在具体的案件检验法律原理、规则及标准的过程,观察的它们实际运作,并依据种种诉因缘由经过逐渐发现如何适用它们并借助它们以主持公道,创造实际上的法律。普通法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⑥正是基于普通法的这种特性,它对于社会的变化应对是及时的,从而使我们更容易理清美国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问题是如何在法律与社会的双重作用下逐渐演变的。 一、非婚生子女的称谓:19世纪美国普通法与文学作品间的映衬 正是由于非婚生育的敏感性,由之引发的悲欢离合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色彩,因而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并不少见的题材。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相伴发展的历史中,文学很大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非婚生子女的关注,也为反思这个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平台。时至今日,“我们不能简单的忽视非婚生子女这个现象,因为它具有一种被称之为‘半影(penumbra)’的特征(即非婚生子女问题处于合法与不合法的交汇之处,因为不仅非婚生子女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亦有将非婚生子女转为合法的婚生子女的措施)。让我们把形式主义的考量抛在一边,与保守主义自以为是的指责相反,没有什么比强有力的赋予非婚生子女合法地位这样的方式能够支撑起家庭和把自然的爱欲与实在的法律结合起来。如果法律意义上的孩子和自然意义上的孩子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个人与更为广阔的法律秩序以及情爱的关系将会缺乏一种核心的、基础性的协调。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即使探讨传统意义上的非婚生育问题似乎也会受到意识形态上的指摘。正是由于这种僵局,文学提供了一种思考这个问题的路径。在文学所虚构的情境中,读者们可以通过更多的释放同情与想象来体会这个问题的感情和精神上的复杂性;文学作品的情节并不把实际的法律规定添加到社会场景中,也不把虚构的解决方法上升到一种法律先例……但是,它却能极为有力的凝聚观点……西方文学中的重要部分,从《奥德赛》到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不仅试图解决非婚生子女这一在社会家庭生活中最为痛苦和难以化解的问题,也在持续地改变着人们对什么是家庭的理解”⑦。 作为西方文学的一份子,美国文学作品中亦不乏对非婚生子女问题的经典之作。美国作家霍桑的名著《红字》即是其中之一,透过其笔下主人公的境遇。我们能够一窥19世纪初叶美国社会对非婚生子女的普遍态度。当女主人公怀抱着自己的私生女走向接受审判和体罚的绞刑架时,“这个年轻女子——小婴儿的母亲……把那个缝制在她衣服上的标记遮掩住。但是,她很快明白过来,小婴儿就是她蒙羞的标记,用她来遮挡另一个标记是丑上加丑……在她的衣服的胸部,有一块细红布,布边装饰了精致的刺绣和金线交织的锦绣图案,红布上就是那个字母A”⑧。而A则是英文通奸-Adultery的首字母。而这仅仅是未婚母亲苦难的开始,在以后的七年中,“不管她走到哪里,不管哪里,肩负着不堪承受的痛苦负担,她也许希望找到安静,可这个红字总是抛下一道敬畏而可怕的令人厌恶的血红的光,团团把她围住”⑨。不仅未婚生子的妇女应该因为这种罪恶而受到惩罚,“那个与她一起作奸犯科的家伙……也应该站在绞刑架上,一起陪绑才是”⑩!由此可见,在美国历史的早期,未婚生子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丑事,在老百姓看来“论罪过应该是死刑”。而恰恰由于社会与宗教的双重压力,这个私生子的亲生父亲——受人尊敬的牧师,直至生命的尽头才有勇气当众承认了自己的“罪恶”。 总之,在美国社会早期,社会对非婚生子女的普遍看法是,“这些杂种就像妓女、小偷和乞丐一样,属于声名狼藉的一群人,为社会所唾弃,但社会又不得不忍受其存在”。(11)大众之所以能够忍受非婚生子女的存在,绝非出于宽宏之心,而是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无法禁绝。 美国社会对非婚生子女的这种敌视态度,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片新大陆的居民,起初大多是虔诚的清教徒。而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对于私生子的态度某一方面看来是严厉的。如摩西在《申命记》就意图把他们逐出信仰共同体:“私生子不可进入耶和华和会;它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12) 不仅在宗教上,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非婚生育也是人这个“天生的政治动物”所不应为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类为什么比蜂类或其他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原因也是明显的……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识……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13)。显然,家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结合,绝不仅仅是人类爱欲的自然结果。正是家庭把生育与性这两个源于人类繁衍生息的欲望,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受法律约束的制度。人类组成家庭,还远不仅是生育与性的欲望的实现,还源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一个国是由若干家组成的,每一家都包括一个家庭,所以讨论政治就应该从家庭开始。“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族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普的生活,自行结合而构成的。可是,要不是人民不共居一处并相互通婚,这样完善的结合就不可能达到。所以各城邦中共同的‘社会生活’——婚姻关系、氏族祠坛、宗教仪式、社会文化活动等一是常常可以见到的现象。”(14)因此,即使身为僭主也“绝对不能在色情方面对人有所伤害;他自己及其从属都应当避免伤害其治下任何人(无论其为童男或少女)的贞操的嫌疑,不让民间流传淫秽的蜚语”(15)。对于破坏家庭的非婚生行为,即成为阻止社会达至至善的一种恶,是应该禁绝的。 因此,非婚生子女不仅遭受信仰的排斥也为世俗的政治生活所不容,并最终映射到了法律层面。一个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对于非婚生子女的称呼,在很长时间内法律均是以侮辱性的私生子(bastard)一词来指代,而这个词还含有杂种的意思,其中歧视意味不言而喻,尽管创下诺曼征服辉煌的英王威廉以“私生子威廉”(William Bastard)而引以为傲。到17世纪早期,“非婚生子女(illegitimate)”成了私生子的同义词,并且在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和文学中一直沿用至今。(16)从词源上,非婚生子女来源于拉丁语中的illegitimus一词,即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非婚生就是指非因合法婚姻而出生。(17)我们不得不承认,非婚生子女的称谓中依然含有非法出生的韵味,但比“杂种”这种全然侮辱性的称呼总要进步得多。但在人们的意识中,即使是非婚生子女这种称谓依然是一个极富贬义的称呼,如果被人称作非婚生,绝对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许多州的普通法因此将这种做法认定为诽谤,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初叶还依然为普通法所接受。如1914年发生在田纳西州的Harris v.NashvilleTrust Co.一案中,法官如此裁决:“中伤他人的名声显然是违反了对他人应该承担的法定义务,提起侵权之诉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以书面形式作出这种错误行为,受害人当然可以以诽谤(libel)为由发起诉讼。书面称呼他人为非婚出生,这一行为即刻构成诽谤,且不需要有其他的损害来证明此类诽谤之成立。”(18) 对于非婚生子女的称呼问题,直到当代才有所缓和。美国各州中以纽约州的做法相对进步。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州不仅明文禁止使用“杂种”,甚至还禁止使用“非婚生子女”的字眼,将非婚生子女一概称之为“婚外子女”,从而最大限度上的取消了对这类人群在称谓上的歧视性。(19)此外,纽约州的出生证明上,也不能标明是否婚生或者是母亲的婚姻状况。而另一方面,孩子的父亲的名字如果未经其书面同意,也不得出现在出生证明中,只有通过这种父亲在出生证明中的缺位,才能直观的看到某人的非婚生身份。为了进一步掩盖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卫生署也不能出具某人完整出生信息的出生证明,其颁发的文件中只是记载了孩子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地点。原始的出生信息,只有经过法庭裁定才会出示,或是在孩子在21岁后经其要求可以查阅,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一方以及和出生信息有关的当事人的合法代理人的要求也可以查阅。(20) 但是,非婚生子女的称谓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如果过于关注使用什么术语来称呼非婚生子女,将会有这样一个风险:立法机关会认为只要宣布那些令人生厌的称谓是非法的,非婚生子女问题就解决了。(21)因此,我们需要从非婚生子女问题的实质进一步分析他们所面临的法律困境以及背后的社会因素。所以我们的切入点是继承权问题。 二、剥夺继承权:19世纪美国普通法处置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一般原则及其社会原因 在基督教中,非婚生子女要被剥夺信仰的精神权利,继承的物质权利也要被剥夺:《士师记》中,耶弗他是个有力气英勇的人,他是基列和妓女的私生子。“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22) 由于非婚生育为伦理与宗教所不容,法律对此问题也做出了回应:此种现象虽然无法根绝,但对于非婚生子女可以区别对待,那就是剥夺他们的继承权。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透过私生子爱德蒙的一大段独白,不仅道出了社会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更道出非婚生子女的无奈、愤懑以及对于合法身份的渴望: “大自然,你是我的女神,我愿意在你的法律之前俯首听命。为什么我要受世俗的排挤,让世人的歧视剥夺我的应享的权利……为什么他们要叫我私生子?为什么我比人家卑贱?我的壮健的体格、我的慷慨的精神、我的端正的容貌,哪一点比不上正经女人生下的儿子?为什么他们要给我加上庶出、贱种、私生子的恶名?难道在热烈兴奋的奸情里,得天地精华、父母元气而生下的孩子,倒不及拥着一个毫无欢趣的老婆,在半睡半醒之间制造出来的那一批蠢货?好,合法的爱德伽,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土地;我们的父亲喜欢他的私生子爱德蒙,正像他喜欢他的合法的嫡子一样。好听的名词,‘合法’!”(23) 莎士比亚的戏剧其实反映了英国普通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非婚生子女是没有继承权的。这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上的规定:非婚生子女被认定为“无亲之人”(filius nullius,son of none),他们自然无法从任何人即使是其生身父母那里取得法定继承权。因此,正如上文所述,在西方的传统中,私生子被定义成在合法婚姻之外出生的子女——是私通、通奸、蓄妾、乱伦、狎妓或其他性犯罪的产物,私生子既不是任何人的子女,又不是每一个人的子女,生来无姓无家,永远是怜悯与嘲弄的对象,既接受施舍又忍受虐待,还为浪漫文学与下流玩笑提供了素材。如果不能依法被准正和领养,生于罪恶和犯罪行为的私生子将终生带着耻辱的印记……很多世纪以来,私生子的法律地位都极端的暧昧不明,他们虽有权主张得到一定的抚养和帮张,但在法律上的权利却被严重剥夺,如关于继承和转让财产,担任高级教职、政治或军事职务,在法院起诉或作证的权利等等。(24) 从世界范围来看,非婚生子女所受到的歧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亲属关系的生理因素而言,道德和法律原则中所蕴含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应是一个男性,而这个男人在社会意义上承担了监护人和保护人的角色,是这个孩子和外界联系的男性纽带……概括而言,未婚母亲为法律所禁止,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是个‘杂种’。这绝不仅是欧洲或是基督教的偏见,而是在绝大多数从野蛮人时期算起的文化中就开始遵循的态度了。”(25)但是,普通法上对于取消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要求尤为严苛。 普通法法律人对非婚生问题的关注,更多地来自物质层面而不是道德层面。他们关心的是家庭财产的继承权,而不是孩子出生的纯洁性。他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可据以确定父母哪一方应该抚养年幼的子女,以及哪个孩子有权在赡养年老的父母后继承其财产……婚生子女有继承权,非婚生子有没有继承权。婚生子女必须照顾他们的父母,非婚生子女则没有这种义务。婚生与否的事实无法改变。(26)这种做法在以保守和传统著称的英国尤为明显。英格兰的普通法仅仅赋予婚生子女继承权,正如布莱克斯通所指出的那样:“非婚生子女能够获得的权利少之又少。因为被认定是无亲之人,他无权继承任何东西。”(27)这种普通法的规定直到1926年才有所改变。这一年,英格兰颁布的合法婚姻法(Illegitimacy Act of 1926)规定非婚生子女的父母如果嗣后合法结合的话,非婚生子女能够获得合法身份,随之可以获得继承权。(28)在美国建国之初,美国继承了英国普通法。美国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的《权利宣言》明确地宣布:“各殖民地居民享有英国普通法规定的权利”,“普通法规定的权利是我们固有的权利,是我们继承的遗产”(29)。因此,剥夺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顺理成章。但是,在美国,这样做不仅是一种对英国普通法的被动继承,更是在美国特有社会环境下的一种主动选择。 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上,发展出了符合自己特定环境的法律创新,所谓的普通法婚姻,即是一例。即使是美国的“兄长”英国也未曾用过这样的一种制度。它与市民或宗教仪式缔结的婚姻同样有效,它完全是非正式的,其本质是一份“口头合同”。也就是男女相互达成的各自认为是丈夫和其子并同居生活的这样一份协议。尽管这是“沿袭下来的做法”,却也不是必要的。普通法婚姻之所以确立,是因为它在社会环境中有更坚固的基础。在当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之外,农村的许多地方人口稀少。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普通人拥有房屋和农场。这些夫妇养育了成群的孩子。像宾夕法尼亚州那样严格的婚姻法就“不能适应社会的习惯和风俗”,首席大法官约翰·B.吉布森在1833年评述道:“如果呆板地执行这些法律,不过50年,该州出生的孩子,其绝大多数将是私生子。”(30) 美国在婚姻家庭领域,采取了和英国有所不同的法律调整手段,这源于美国的特殊环境。而将非婚生子女问题放置到这种环境考量,我们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在如此宽容的婚姻成立要件之下,如果某人依然非婚生育,很有可能是出于什么见不得光的理由。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于法于理,剥夺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在当时的背景下都是正当的。直到19世界来期,这一基本原则仍然为某些州的普通法所接受,如纽约州最高法院在1884年判决的Todd v Weber一案中,直截了当的指出:“普通法确实认为在婚前出生的孩子是‘无亲之子’(非婚生子女),而且他们不能享有继承权。”(31) 三、可以继承母亲的财产:改革思潮下19世纪美国普通法对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限制的松动 婚生子女的合法性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一方面来看,这种合法性给基于自然情爱的两性结合增添了法律保护的力量,而且孩子自出生之始就会享受文明社会带来的各种好处,这将会进一步稳固家庭关系;而消极的一方面是,合法性的另一面就是非法性带来的社会阴影,即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子女传统上都是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继承等方面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不仅如此,很多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子女都会遭受类似于《红字》中女主角那般的羞辱。人们也希望通过羞辱这种极端的社会情绪的释放作为一种威慑,阻止妇女未婚先孕从而把自己钉在社会的耻辱之柱上。显而易见,普通法对待非婚生子女的处理方式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其进行一定的革新是必要的。在美国十九世纪的大社会背景下,普通法自身对于非婚生子女没有继承权的这一一般性原则的使用逐渐出现了松动。 首先,在非婚生子女问题上,19世纪开始以来,非婚生子女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整个美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有了一个显著的下降。(32)同时,在整个社会氛围上,美国19世纪上半叶有两大特点:人为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奋斗不已;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去改革社会……改革之风越刮越劲,因为整个知识界似乎都赞成改革……改革坏的法律和环境,人类就能实现和平、繁荣和幸福。美国许多唯理主义者则依据英国思想家杰里米·本瑟姆(即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各种社会机构,看他们在为最多数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方面做得怎么样。(33) 美国法学家们也洞察到了这股思想潮流上的涌动和社会情势的变化。多年以来,随着非婚生子女问题在法律上的不断完善,针对其所发展出的法律体系逐渐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逻辑演进,它就不会依赖人间的爱恨来生长,婚生与非婚生成为一个干巴巴不带有任何感性色彩的词汇。但是,非婚生子问题与人的感情不可分割,而人类的感情本能更加看重与依赖精神上的慰藉而不是僵硬的法律规定。因此,对于非婚生子女问题,詹姆斯·肯特做出了如下论述:“普通法(对非婚生子女问题规制)的严格性在许多州出现了松动,这是考虑到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普通法应该让此种关系之间出现一种亲密的属性。”(34)这种思潮反映在美国普通法的一个结果就是,在非婚生子女方面,美国普通法部分放弃了英国传统做法中完全致非婚生子女利益于不顾的做法:美国各州部分废除了英国普通法上私生子不是任何人之子女,至少他们没有从母亲那儿获得“有继承权的血统”,其在母系方面没有继承权的原则。(35)对比1835年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审理的McCormick v.Cantrell一案与1840年美国最高法院所审理的Brower's Lessee v.Blougher(36)一案很能说明普通法态度的转变。 在McCormick v.Cantrell一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对是否给予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如果“为非婚生子女设定继承权,其效果就是非婚生子女通过分割其父亲的财产从作为其父亲合法继承人的婚生子女手中拿走了一部分财产权利”。此种做法就如同“如果允许人们把一个一时欢愉之下生出孩子(children of pleasure)领进家门,这个没人管的孩子就会被变成一个被合法的收养的孩子,于是,养父的一部分财产是要分给他们的,这样反而排斥了这个养父的亲生子女或是其他法律所保护的与养父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本应享有的继承权”(37)。最终法院效仿了普通法的一贯方针,肯定了婚生子女的继承权而维持了剥夺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这一合法的歧视性做法。 而最高法院在Brower's Lessee v.Blougher一案中,部分的缓和了普通法的这种严苛性。该案缘起于1825年马里兰州的议会出台的那部名为“非婚生子女法”(An act relating to Illegitimate Children)的法律。该法规定非婚生子女,如同婚内子女一样,享有继承其父母财产的权利以及相互之间继承的权利。而本案则涉及了父亲与女儿乱伦所生的子女是否享有继承权。反对这些子女继承其伦乱的母亲财产的律师以普通法为依据,激烈的反对马里兰州立法的规定,其陈述可以看做是对非婚生子女问题的传统观念在理念和法律上的一个总结: “我们的考察表明……所有的文明国家均……一致禁止因伦伦和通奸生子而造成的继承问题。马里兰州是否能够仅依靠一部法律就明显地做出了相反的规定,而这样的法律是马里兰州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样一部法律绝不构成马里兰州的民事法律,它也绝不会赢得人民的同意。而我们作为人民的一份子,也反对这部法律的观点。”(38)这一点可谓是反对意见的“群众基础”。而“依照普通法,非婚生子女是无所归属之人,因之也不会有法律承认的父亲”(39)。因为“在普通法看来,非婚生子女无权继承其父、其母或任何人的财产”(40)。所以“无论我们对本案中的非婚生子女有多么的同情,我们不得不透过严苛的普通法政策这一媒介来考虑我们的态度。这样,我们必须将抛弃这种同情,因为普通法是反对两性违法结合的……在解释所有类似于本案中所分析的法律规定时,必须严格遵循普通法的原则……而乱伦和乱伦结合后生子均是普通法所厌恶的”(41)。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塔尼则并未采纳这种看法,相反,他从子女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用简单但坚决的语言支持了非婚生子女可以继承母亲继承权的做法:“为父母的犯罪行为惩罚子女是不公正的。子女的权利与父母过错的大小完全无关”,尽管孩子的父母之间的乱伦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犯罪行为”。(42)塔尼大法官的判决掷地有声,它表明普通法也要考虑非婚生子女这一无辜的群体的利益,完全歧视性的排除他们的权利并不足取。遗憾的是,对于非婚生子女的敌视态度,在美国社会依然存在,他们与父亲之间的相互继承权(43)直到20世纪后期才得以普及。(44) 四、尾声:对美国当代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问题的折射 19世纪美国普通法处理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问题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伦理等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法院在作出判决时的取向。因此,当我们发现,20世纪以来非婚生子女面临着新的社会形势,我们对于法院如何应对应该不会感到惊奇,因为19世纪的做法已经是前车之鉴。 数据表明,美国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在10世纪中叶开始不断攀升。截至20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从3.8%提高到4.7%。(45)而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地区,该比例甚至达到了10%左右。如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10%的新生儿为非婚生。而1966年在芝加哥的14个区域所做的非婚生子女调查表明,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在27.9%至38.7%之间。(46)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国非婚生子女的出生数量巨大。从非婚生子女的构成来着,以2007年为例,全美儿童中有38%的人生于婚姻之外;所有白人儿童有25%,所有西班牙裔儿童有46%,非洲裔儿童有69%,都生于婚姻之外。贫穷和赤贫、落后的教育和医疗、青少年犯罪和逃学、刑事犯罪和被判刑罚等情形,在非婚生子女儿童中的比例大概是婚生儿童的三倍。(47)而在这样的数据背后,则是美国逐渐高涨的人权运动(48)所追求的受宪法保护的平等权利。因此,在人权运动达到高潮的196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Levy v.Louisiana(49)一案中,依据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明确赋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样的继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沿着19世纪以来普通法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处理非婚生子女问题的轨迹前行的结果。而这样的发展轨迹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理解美国普通法会如何处理在最新的社会背景下应对非婚生子女问题。 收稿日期:2015-10-20 注释: ①[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苏彦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3页。 ②[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学院的功用》,载《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刘思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2页。译文作者有改动。 ③James Willard Hurst,Justice Homles on Legal Histo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4,87.弗里德曼对此在其著作《美国法律史》的开篇也有类似论述“这部著作论述的是美国法律,然而,并未把美国法律作为独立王国,也未视作一套规范和概念,也不是作为法律家的领域,而是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未将它视为自足,没有把它看做历史的偶然事件,事物间是相互联系的,并由经济与社会所塑造。”[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苏彦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因此,在他看来,“整部美国法律史大概或多或少就是整部美国的生活史。”[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苏彦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3页。关于法律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还可参见弗里德曼的Law and Society Movement,Stanford Law Review,Vol.38,No.3(Feb.,1986),pp.763-780”[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苏彦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④Wen-Shing Tseng and Jing Hsu,Culture and Family:Problems and Therapy,New York·Sydney·London:The Haworth Press,1991,p.1. ⑤[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21页。 ⑥[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⑦Glenn Arbery,Why Bastard? Wherefore Base? Legitimacy,Nature,and the Family in Post-Renaissance Literature,2 Liberty Life & Fam.99(1995-1996),100-101. ⑧[美]霍桑:《红字》,苏福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⑨[美]霍桑:《红字》,苏福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⑩[美]霍桑:《红字》,苏福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11)Davis,Illegitimac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45 Am.J.SOCIOLOGY 215(1939). (12)《申命记23∶2》。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0页。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7页。 (16)[美]约翰·维特:《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钟瑞华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注释1。 (17)Shirley Forster Hartley,Illegitimacy,Berkely,Los Angeles,London:Unververisyt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4 (18)Harris v.NashvilleTrust Co.,128 Tenn.573,585(1914). (19)N.Y.GEN.CONSTR.LAw §59.NEB.REv.STAT.§13-115(1962) (20)Irwin W.Greenfield,Illegitimacy under New York Law,23 Brook.L.Rev.80(1956-1957).84. (21)Harry D.Krause,Illegitimacy:Law and Social Policy,New York:Bobbes-Merrill,1971,p.21. (22)《士师记11∶2》。 (23)[英]莎士比亚:《李尔王》,朱生豪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3页。 (24)[美]约翰·维特:《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钟瑞华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25)Bronislaw Malinowski,Parenthood,the basis of social Structure,in V.F.Calverton and S.D.Schmalhausen,The New Generation,New York:Macauley,p.130. (26)[美]约翰·维特《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钟瑞华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总体而言,普通法对所有私生子做同样的法律限制,其中最显著的是他们对任何人的财产都没有继承权,这点与大陆法有所不同,具体可参见Horace H.Robbins & Francis DeáK:Familial Property Rights of Illegitimate Children:A Comparative Study,30 Colum.L.Rev.308 1930。 (27)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England,4 Vols.(London,1765-69),1:447. (28)Section 1,16 & 17 Geo.5,ch.60(1926). (29)[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30)[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苏彦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 (31)Todd v Weber,95 N.Y.181,189(1884). (32)Daniel Scott Smith,The Long Circle in American Illegitimacy and Premarital Pregnancy,in Peter Laslett,Karla Oosterveen,Richard M.Smith,Bastardy and Its Comparative History: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llegitimacy and Marital Nonconformism in Britain,France,Germany,Sweden,North America,Jamaica and Japan,London:Edward Arnold,1980,p.372. (33)[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许季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75页。 (34)James Kent,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4 vols.New York:O.HALSTED,1826-1830,2:214. (35)[美]约翰·维特著:《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钟瑞华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36)作为美国联邦司法体系之最高审级的联邦最高法院,其主要的任务是对联邦法特别是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其所作出的判决是否能够被当做普通法来对待,似乎会构成一个关于普通法范畴的问题,对此美国学者斯托纳指出:“如果普通法司法体系的标志是重视先例规则、陪审团审理等等,那么联邦司法体系就有资格被称为普通法。简而言之,如果普通法司法体系的标志是重视先例规则、陪审团审理等等,那么联邦司法体系就有资格被称为普通法。”[美]小詹姆斯·R.斯托纳:《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因此,本文所论述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普通法。 (37)McCormick v.Cantrell,7 Yerg.615,623-624(1835). (38)Brewer's Lessee v.Blougher,39 U.S.178,186(1840). (39)Brewer's Lessee v.Blougher,39 U.S.178,198(1840). (40)Brewer's Lessee v.Blougher,39 U.S.178,196(1840). (41)Brewer's Lessee v.Blougher,39 U.S.178,194(1840). (42)Brewer's Lessee v.Blougher,39 U.S.178,199(1840). (43)美国曾经实施的黑奴制度这一历史问题也直接影响到了非婚生子女问题,因为美国的黑奴制度的一大棘手的遗留问题就是很多白人农场主和黑人女奴剩下的混血私生子。而在白人看来,黑肤色本身就是私生子的化身,甚至是对社会的一种污染。如在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中,主人乔·克里斯默斯一直深深怀疑自己的黑人血统,从而自我产生了一种疏离感。参见[美]福克纳:《八月之光》,蓝仁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在这种社会情绪之下,可以想象,那些犯下原罪的白人父亲们,几乎不会为了自己罪过的后果——私生子设法在法律上寻求公平待遇了,这显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继承权,特别是对于父亲的继承权。 (44)[美]约翰·维特:《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钟瑞华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45)Department of Heath,Education & Welfare,Illegitimacy and Its Implication on the 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 Programs,Washington:Bureau of Public Assistance,1960,p.5. (46)Champaign-Urbana News Gazette,Feb.14,1966,p.13. (47)[美]约翰·维特:《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钟瑞华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48)20世纪的民权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中一部分也来自于社会情绪的转变。在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中,主人公艾萨克·麦卡斯林在翻看自己祖父和父亲留下来的账簿时,对于自己祖辈在黑人身上所做的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他不仅产生了负罪感,也产生了要替祖辈赎罪的冲动。[美]福克纳:《去吧,摩西》,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235页。 (49)Levy v.Louisiana,391 U.S.68(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