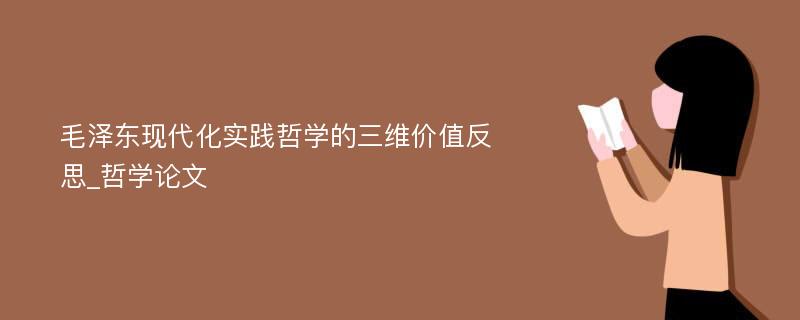
毛泽东现代化实践哲学的三维价值映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价值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中国现代化史,主要是“中国梦”的实践史,历来是各类“中国梦”的哲学思想相互激发的实践基础,因此也是理解包括毛泽东思想历史价值的基本坐标。但是,学术界对这种现代化哲学论争语境的关注,虽然已有少量成果,①但是总体上仍显单薄。②为此,笔者撷取中国现代化哲学的三种参照坐标,尝试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理论价值。 一、针对蒋介石“革命哲学”的唯心性、陈腐性,毛泽东为中国现代化提出了真正体现时代趋向和国情民心的实践哲学的实践致思、价值目标和方法理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第一个论战对象首推蒋介石的“革命哲学”,与蒋介石的现实斗争和哲学对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党外斗争发源地。 从历史背景和客观效果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第一个重大历史意义,无疑是系统地提出和科学地阐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实践哲学,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为中国现代化扫清前进道路的历史障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企图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和中国国内既定的政治架构,走资本主义和精英主义(依靠国内地主、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等政治力量)现代化道路,而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则主张动员农民、工人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内外压迫下风雨飘摇、危机四伏,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两类政治代表人物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他们之间的哲学论争和思想对峙,只是面对相同历史背景产生的不同实践哲学思路,思路不同是道路之争的逻辑基础和哲学呈现。 从思想目标和实践面向来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的学院派哲学家,他们围绕中国革命主导权的斗争实践展开,在思想深处也就是实践哲学之争。 卡尔·马克思主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毛泽东并非职业哲学家,他追随马克思的思想,把哲学只当作革命的“顶层思考”。蒋介石同样也没有学院哲学的背景和经历,他学习的专业是军事。从1908年加入同盟会,20多年以后,直到1932年蒋介石才开始系统演讲“革命哲学”④。只可惜,这种哲学充满了唯心、片面、陈腐的性质和成分。只是当丢失大陆统治权以后,蒋介石的哲学思考才有了较多冷静和实际的进步。⑤ 对于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革命领导权斗争,人们往往较多地关注其政治艺术和军事谋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哲学思想的价值合理性和思想历史高度才是具体政治军事活动的原点和基础。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起源、历程、形势、任务和前途,企图率先占领“中国革命”的理论制高点。毛泽东随后发表《两个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即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出来。”⑥中国命运的这两种思考和勾画,基于同样的中国革命现实,但是由于其实践性的真实性、彻底性不同,却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实践哲学系统,而各自主张的民心向背,奠定了斗争胜败的理论基础。 从价值目标和历史使命来看,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根本分野,在于如何理解和确立革命的价值目标或历史使命。 革命的根本问题首先是革命使命问题,就像毛泽东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⑦在实践哲学上,这可以说就是实践的价值目标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最低目标也如“中共二大”所说,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⑧。这样的最低革命纲领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并非绝对矛盾,在反帝反封建和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这个符合现代化历史趋势的共同点上,完全可以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集团没有这样的历史远见和开阔心胸。 蒋介石自认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正宗继承人,认为“总理创造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救星,是中国四万万同胞的救星”⑨。但是其具体行动方案,“第一期革命的对象是满清,革命的本质是民权革命”,“第二期革命的对象是军阀与帝国主义,革命的本质是民族革命”,“第三期革命的对象是中共匪党,革命的本质是社会斗争而兼民族与民权主义的革命”。⑩从1927年开始,他认为“北洋军阀是不配做我们的敌人的”,因为“军阀的军队是没有主义的”。(11)“因为立在主义上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他是破坏国民革命,阻碍三民主义实行的;我们要国民革命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12)他以“主义”名义“清党”,屠杀正在为革命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缺乏民主精神和包容智慧。 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斗争对象完全错误,后果十分严重,不只引发了国共之间长期的内战,葬送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更给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危害,错过了更早抵抗日本侵略的时机,拖延了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崛起的进程。 从认识路线和思维风格来看,蒋介石“革命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陈腐意识、庞杂折中,映现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和时代前瞻性质。 蒋介石关于国民革命实践的价值目标的认识,存在着根本的错误和深刻矛盾。他一方面认为中国革命的价值追求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自由幸福,另一方面又对日寇侵略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和生存疾苦置若罔闻,甚至基于迂腐的传统观念,认为国共两党的斗争“就是天理与人欲的斗争,换言之,亦就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的斗争”,继而又基于纯然唯心主义的思路,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归咎于“我们自己内部的散漫,不能团结御侮,以及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受了共匪的欺骗与麻醉”。(13)而且要看到,蒋介石对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任务和方式方法的理解,就其总体思路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各种旧学说汇总而成的唯心主义价值观、认识论基础上的。从他自己的各种论述看,他的哲学理念既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包括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同时包括各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孔孟儒学、宋明理学的学说,当然还包括欧美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观念。这些学说虽然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抱持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认识论。(14)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失败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实践哲学的胜利恰成鲜明对比。与蒋介石“革命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精英主义取向和形而上学相比,毛泽东实践哲学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时代观、价值观的基础上,是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人民生活实际的忠实反映,是站在资产阶级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前沿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思考,所以能够科学地回答和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和道路问题。 从方法理论和阶级基础来看,蒋介石的精英主义与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主义也恰成鲜明对比。 蒋介石“革命哲学”唯心主义性质还表现为它坚持精英主义、走上层路线,迷信欧美西方国家支持,迷信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以及文化正当性,迷信社会上层阶级如乡绅和资本家的支持,当然也包括国民党和他自己的坚强决心和顽强精神。由于秉持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和所处地主资本家的立场,在历史观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上,他不能站在社会被压迫人民的一边看问题,没有站到超越私有制社会局限性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蒋介石总是企图用他所谓高尚的精神、坚强的意志、果敢的牺牲要求他的部下和一般士兵、人民,也总是倾向于把失败归咎于这些芸芸众生不能理解他英明的决断。(15) 而毛泽东则相反,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愿意深入地了解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要求,他总是把革命实践胜利的原因归结为人民的支持,相应地总是把党和干部包括他自己的错误理解为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结果。所以,毛泽东对革命实践的最积极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降低革命的身段,让革命转变成真正的人民革命,从城市起义转变成农村包围城市,从单打独斗转变成民主统一战线,从简单对抗转变为阶段性的合作。于是,革命成为人民的革命,具有了无穷的力量源泉,貌似强大的国民党蒋介石相形之下必然霸王力穷、英雄末路。 从现代化认同和现代化实践的深度、彻底性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实践哲学也具有相对蒋介石而言的重要优越性。这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精准地抓住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问题,通过发动广大农村的农民和城市工人、市民、知识分子,通过启发他们对贫穷、落后、压迫、欺侮等的自觉抵抗,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普遍、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主体性革命,而人的利益、价值、自我的觉醒恰恰是现代化本身同有的历史要求。蒋介石同然也在概念上承认、期望国家富强和民主自由,但是他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目标并没有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广大农民、工人的切身利益之中,没有广泛动员和有效解放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真正体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也就难免期望落空。 二、从革命阵营内部的“因循派”,映现出毛泽东实践哲学通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而展现的实践性特质、创造性品格和辩证法优势 对于中国共产党内部来说,既然革命事业既符合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人民民主化的内在需要,也就是说革命实践的价值合理性毋庸置疑,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国共两党斗争力量形式复杂的情况下,寻找和选择科学的革命道路、方式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重大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败。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实践哲学的优越性不仅相对于蒋介石,更是相对于党内“因循派”,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国际权威、教条或狭隘经验上升成真理标准的思想倾向。 “因循派”还可以分为“原理论”和“经验论”两类,前者根据他们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否定立足中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创造性探索;后者根据他们习以为常的“中国国情”,否定对这种“中国国情”的积极改变。正是通过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因循派”的挑战和应战中,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实践性、创造性和科学性品质得到鲜明的映现和确证。 “原理论”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共产国际,包括“中国人民的朋友”(16)斯大林。有学者指出,对毛泽东“那主要依靠农民革命而不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起义的道路”,斯大林曾经质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吗?”他甚至“对心腹们说”,“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17)他们得到一个貌似有力的旁证,“直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还没有读过《资本论》”(18)。或许因此,毛泽东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从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确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甚至斯大林本人的某些干扰、误导,甚至打压。这种负面影响,更多地还是由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作为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以贯彻执行“国际指示”和“主义”、“原理”的名义实现的,由此导致毛泽东的探索性革命实践“长期受打击受排挤”。 “经验论”的情形貌似相反实则同样因循,只不过因循的不是“本本”,而是“国情”和“经验”。相对“原理论”,“经验论”初期的危害貌似只是个别少数情况,比如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都有过分强调根据国共力量对比现状,而向国民党方面妥协的问题,比如在红军建设中沿用旧军队官兵等级制和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单纯军事论观点等。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种由沿袭传统等级制度、封建文化和战争时期经验而建立起来的“计划体制”,以及在改革开放中难以突破既有利益格局和观念形态的“经验论”,却逐渐显示出顽强的、恶毒的生存能力。 “因循派”的共同特征,是依赖于现成既有的思想坐标,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地思考。正是在与党内这些形形色色的“因循派”的相互辩难中,在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富有实践特质和创造性品格的“实践论”认识路线,具体做法就是运用各种方法和途径主动、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来说,深入、系统、坚持不懈地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其中实现和体现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基本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功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而“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19)毛泽东绝不像蒋介石那样一味以三民主义、总理遗命、中华文化、人的精神等等名义,居高临下地宣布自己主张的正义性,指责敌对方面的邪恶、残暴和低劣,毛泽东总是根据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发现、确立和说明妨碍或促进正义、进步、革命的力量分布,同时还不断更新调查研究,根据事情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看法和策略。 毛泽东生长于普通的农民家庭,却仍然重视对中国农村情况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当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就与同学结伴“游学”,不带盘缠游历五个县域,实际了解中国社会实情。(20)毛泽东在1930年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里,开篇第一个标题就题名“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第二个标题题名“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第三个标题“反对本本主义”,第四个标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21) 调查研究是坚持和实行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具体工作手段,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实践始终注意坚持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哲学的“顶层思考”,从而把革命实践的理论探索和方略设想建立在坚实和充分的事实基础上,确保革命实践的科学性、人民性。调查研究使革命的理论和决策紧贴实践的实际,所以能够防止和反对“因循派”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而正因为紧贴实际,革命的理论和决策才能够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历史的规律占据创造的高度,具备创造性的品格。创造性其实就是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是根据现实、高于现实的辩证法精神的真正实现。 换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从世界和中国近现代的现代化历史发展线索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当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场符合“标准”的、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从多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来,这样纯而又纯的“革命”即使今天看来,甚至最近的将来看来,在中国也还谈不到条件完全符合。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在相当程度上,与其说是一场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如说是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形式或特殊道路。中国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实际上实现了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中国人民的普遍彻底的民主动员、中国文化传统的自我否定或自我扬弃,它是一场现代化运动。“因循派”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他们对书本、权威、主义的忠诚,也不是对某些实际情况的执着固守,而在于他们不能抓住这场革命相对现代化历史的切近性质和相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些个别经典革命论断的“非典型”辩证关系,而毛泽东的实践哲学的成功秘诀和历史价值,则恰恰由于其实事求是的理论作风、思想品格捕捉并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殊意义。 三、相对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问题,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既有探索性的思考,又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和自我悖反的深刻教训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思想继续发展,在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实践上继续探索,充实内容、创新理论。从现代化历史的一般趋势来看,这种理论对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工业化、人民民主化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但是毋庸讳言,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来说,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思想在探索中出现失误,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暴露出了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现代化历史趋势和时代精神的参照系来看,既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也有不无遗憾的道理。 毛泽东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情: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几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情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22)这个总结就其适合他本人情况这一点来说,真可谓是高屋建瓴、恰如其分。“两件事”前后相继、逻辑暗通,都没有最终完成。 第一件事是“祖国统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方面抗拒统一,一方面在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狭隘考虑,另一方面是哲学思想对立的结果。国民党仍然坚持蒋介石遗留下来的反共哲学,因此抵制“回归”;民进党更借由所谓民主、进步理念,妄图“台独”。如何超越党派之间相对狭隘的政治理念、利益立场,实现祖国统一,重振民族雄风,需要现代化坐标系的引入。 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那是一场遭到完全失败的“探索性试验”,因此在政治上也已经被彻底否定。但是,在哲学层面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决意发动和蜂拥响应却不能简单草率,现代化坐标系的引入同样十分重要。 就动机而言,“毛的根本目标,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去为自己真正地取得权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和资产阶级传统支配的新文化”(23)。这种动机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从积极的方面看,毛泽东对于他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抱有真诚的信念,急于消灭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再生土壤,希望用动员群众的办法防止社会的经济、权力等两极分化,防止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庸俗堕落的倾向,为此甚至不惜打破自己亲手建成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秩序。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种“革命”的价值目标本身几乎全然无视现代社会否定“前现代”社会的历史方向,一厢情愿地企图利用个人感召和政治强力,来对“人性”进行超越历史发展条件的“革命”,这无疑是脱离现代化历史背景、重蹈空想共产主义的老路。而策略性的利用个人崇拜,实现削弱或剥夺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的权力,(24)甚至不惜造成所谓“打倒一切,全面内战”(25)的局面,来强行推行个人理解的实践哲学理念或个人意志,则无疑又是唯意志主义哲学的表现。 从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蜂拥支持、盲目拥护的态度来看,说明“文化大革命”自有其深厚的社会土壤,几千年“前现代”社会的农耕经济和封建家国文化,个人崇拜、权力崇拜、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普遍价值坐标和心理惯性,缺乏民主、法治、理性地解决问题的文化传统、社会氛围、人民心性,即使是在化名为“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也难以掩盖其“前现代”的本质。而正是这种“前现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使得“造反”哲学、形式平等、无序民主、权威主义、个人崇拜、禁欲主义、意志主义等“前现代”的“革命化”表达甚嚣尘上,一时间蔚为绝对潮流。 由此看见,从通过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这两个目标来看,毛泽东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大举措,反映出他的实践哲学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规律的初衷下,同时包含着以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水平的思维方式,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的严重历史局限性。这也充分证明,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种政治手段强行建造道德孤岛、实现人间天国,是多么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 我们没有资格谴责伟人,也无意作消极的批判。谁都不能怀疑毛泽东实践哲学的良好初衷、探索成就和历史高度,毛泽东实践哲学追求革命理想的高尚情怀,无疑是众多庸人难以企及的,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感同身受的。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所指出的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避免自身腐化堕落和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迄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正在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主要危机因素。“前现代”的历史遗迹现在仍然严重存在,“前现代”的故事就不可能绝尘而去。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道德失范的矛盾日益加重,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和社会发展的矛盾积累不断加深,事情必须解决,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旧办法显然不行。 问题关键是解决如何把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化事业有机结合的问题,因为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先进、科学的革命历史实践,才能促进生产进步、政治公平、社会文明和民族复兴。企图靠唯心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实践建成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只可能是低于资本主义历史水平的“十分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26)。同时,资本主义无疑存在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世界上所有真正成功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都以不同的方式(西方用基督教伦理,东方用传统文化习惯)牵制和延缓资本主义原则的过度恣肆,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文明的历史意义本来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替代。所以,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历史特别长、濡染特别深的国家,通过现代化追赶资本主义的文明高度,通过新型现代化赶超资本主义,为把社会主义提升到更高的历史水平,既实现历史成为现代历史的质变,又实现扬弃资本主义的进步,这是当代“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党在新时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实际上就是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认真汲取毛泽东实践哲学的经验和教训,积极利用毛泽东实践哲学“遗产”的唯一正确选择。 注释: ①郭建宁:《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李佑新主编:《毛泽东研究》(2013年卷),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②杨明伟:《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价值的思维视角》,《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④(11)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534、257-258页。 ⑤⑨(12)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二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7-75、215、258-25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⑧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补编》(1919-192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154页。 ⑩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18页。 (13)(15)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八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8、29页。 (14)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八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遗嘱”。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17)(18)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6页。 (19)(2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9-112页。 (20)[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22)逄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0页。 (23)[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东方极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4)[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东方极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5页。 (25)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标签:哲学论文; 毛泽东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现代化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蒋介石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