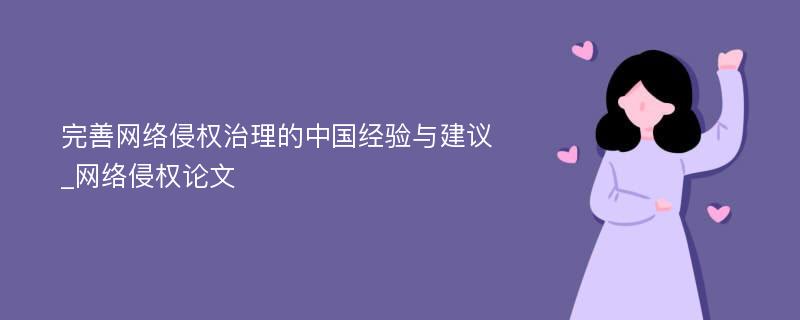
网络侵权治理的中国经验及完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验论文,建议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6-0206-11 长期以来,网络中侵权泛滥是困扰各国立法者的一个共同难题。对此,各国至今尚未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本文无意企图找到一种解决这一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本文意在总结我国20多年在解决网络侵权问题上作出的种种努力,并将之与他国的相关经验加以比较,以期探究我国网络侵权治理呈现出的一些规律,尤其是我国在网络侵权治理的制度设计背后蕴含的一些基本理念。在此基础上,尝试就中国网络侵权治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完善途径表达一隅之见。 一、网络侵权治理的两种模式 互联网的匿名性、无界性以及众多用户参与性等特点导致权利人直接向侵权用户主张权利的成本大大增加。在网络环境中,为了尽量维持如现实世界般对权利人利益的保障,有两种途径可以选择:一是降低权利人向网络用户主张权利的维权成本,通过制度设计尽量高效且低成本地找到侵权用户;二是放弃由权利人来对网络用户直接主张权利的思路,而是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来间接控制网络用户的行为。据此,各国对网络侵权治理的制度设计也呈现出两种风格迥异的制度模式,即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模式。前者是以追究网络用户责任为目标,进而消减网络中侵权现象的制度设计;后者则寄希望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网络中的侵权现象。 1.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 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指国家为应对网络侵权所采取的制度设计旨在为权利人联系上网络用户、确认网络用户真实身份、向网络用户提起诉讼、对网络用户实施不利法律后果等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和便利,使权利人能有机会高效且低成本地向网络用户主张权利。该模式的核心思路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使传统的权利人向直接侵权人主张权利的救济方式能够在网络环境中继续有效地运作,通过侵权的网络用户向权利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等方式来抑制网络中侵权现象的发生。 立法者采纳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的原因在于,实施了侵权行为的是上传了侵权内容的网络用户,故追究网络用户的侵权责任并让其承担其他一些不利后果是自然而然的结论,也是立法制度设计应实现的目标。正如有学者所言:“造成被侵权人损害的,全部原因在于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其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为百分之百,其过错程度亦为百分之百。”①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基于技术中立原则和“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等原理,其与侵权的发生无涉,故从最终意义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应就此向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当然,这并不排除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一定的义务来协助权利人,以便于权利人向网络用户追究责任。 从目前各国采取的应对网络侵权的措施看,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的具体制度表现如下: (1)实施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制有助于克服网络匿名性的特点,使权利人通过诉讼向侵权用户主张权利成为可能。韩国是世界上较为典型的实施了网络实名制的国家。自2002年以来,韩国便开始考虑推行网络实名制,并从部委网站开始做了一些尝试。2007年韩国通过了《信息通信网法》,正式实施网络实名制。从韩国实施网络实名制的立法初衷看,其意在通过实名制来对网络中的侵权人实施“威慑”,进而减少网络中侵权、犯罪的发生。正如韩国信息通讯部所说的:“利用匿名侵害人权的案件逐渐增加。互联网实名制是为了防止网名滥用、利用网络的匿名性进行恶意留言等弊端而实施的。”当然,实名制是把双刃剑,它在威慑侵权行为发生的同时,也对用户信息安全和言论自由等构成了潜在威胁。此外,韩国网络公司实施实名制而国外公司并不接受实名制导致韩国网络公司在商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以2011年韩国大型门户网站NATE和Nexon大规模泄露个人信息事件为诱因,韩国行政安全部在事件发生后表示,出于保护网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考虑,政府拟分阶段逐步取消网络实名制。②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12月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6条确立了我国将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制度选择。据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于2014年6月底前完成“出台并实施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但学界对此仍存在较大争议。 (2)法律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向权利人提供用户注册资料的义务。由于网络中侵权用户对外所展示的身份信息往往是不真实、不完整的,而真实、完整的信息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掌握和控制。③故为便于权利人对侵权用户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立法上可能会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向权利人提供用户注册资料的义务。比如,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第5条的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行为人在其网络的注册资料以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这一规则在电子商务类网站中尤其有效,因为基于财物交易的需要,此类网站中用户注册的资料多为真实、完整的信息。当然,与网络实名制一样,这一规则也存在侵害用户隐私等威胁,立法者对此规则也持谨慎态度。 (3)允许权利人以“网名”等为被告提起诉讼。为了避免权利人直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索取网络用户注册资料导致的侵犯网络用户隐私权等风险,江西省高级法院提出了允许权利人以“网名”为暂时被告,在提起诉讼后由法院调取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再确立真实被告的观点。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9条:“被侵权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不能提供被告真实身份的,法院应根据案件实际,告知其可以电子证据中标记的IP地址或者网络名称暂作为被告,并根据案件实际做如下处理:(一)被告是网络用户,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查被告在其网络的登记、注册资料;同时可以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网络安全监察部门调查该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二)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网络登记、注册资料或者公安机关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提供的信息,可以确定被告真实身份信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以相关信息载明的主体作为被告进行审理;无法确定被告真实身份信息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这是中国地方法院提出的一种试图兼顾权利人向网络用户追究责任和保护网络用户隐私的折中方式。该方式的具体实施效果如何则尚待时间检验。 (4)规定“三振出局”规则。三振出局规则是最近5年来权利人提出并积极呼吁立法者采纳的一种新的针对侵权用户的规则。各国立法对三振出局的规定不尽相同,根据欧洲数据保护监察组织(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的概括,三振出局规则可大致描述为:版权人通过系统监控技术来确认某IP地址的网络用户实施了侵权行为,并将该IP地址发送给网络服务提供者,由后者向该IP地址所对应的网络用户发送侵权警告。如果此种警告达到了一定次数,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将终止或一段时期内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④目前,立法上通过了三振出局法案的国家和地区有法国、⑤英国、⑥韩国、⑦新西兰⑧以及我国台湾地区⑨等。中国大陆立法中虽没有认可三振出局规则,但在一些地方性规范文件中则也出现了类似的相关指导意见,比如2011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发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指导意见(试行)》第5条规定:“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未经许可,多次实施上传他人作品的服务对象应当予以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当终止服务,并向版权行政执法部门举报。”总体来看,三振出局规则尽管没有帮助权利人从侵权用户处获得侵权的经济赔偿,但其可有效防止用户反复侵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利人对用户侵权行为的控制。 (5)通知通知制度。该制度是2000年下半年加拿大网络服务商协会、加拿大有线电视协会和加拿大录音行业协会自发设计的用于处理网络版权侵权的制度。⑩其具体运作过程是:加拿大录音行业协会如果发现其成员的版权受到侵害,就会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书面通知要清楚地列明投诉人和其利益,明确投诉事由(包括对侵权资料的描述),并提供资料的位置。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会向用户发出通知,提醒他们将资源用于非法目的是违反网络服务提供者政策的,建议他听取来自加拿大录音行业协会的信息,鼓励其与加拿大录音行业协会联系,以解决问题。随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会以回邮的形式告知投诉者,同时与加拿大录音行业协会确认已将投诉中的信息转告用户。如果用户不将有问题的内容移除,加拿大录音行业协会可以根据《版权法》向法院提出禁令或金钱赔偿。网络服务提供者需保存必要的数据以确定投诉中的人和事实,保存时间为6个月。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遵照执行以上要求,其会因为没有发送通知而受到最高额为5000加元的罚款,因为没有依法保存相关信息而受到最高额为10 000加元的罚款。(11)从通知通知制度的设计流程可看到,该制度的运作旨在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个中介,来实现权利人与网络用户间的沟通,为双方自行解决纠纷提供便利。网络服务提供者尽管会因其未提供相关便利而遭到处罚,但其承担的是行政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对权利人的损失承担相关民事责任。 (6)英国《数字经济法案》(Digital Economy Act 2010)所采纳的网络侵权治理方式。该法案所设计的制度方案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的立法设计。该法案的两大目标之一便是试图解决网络版权侵权问题。(12)为此,与之前英国的《电子商务管理办法》(Electronic Commerce Regulations 2002)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定性为传输通道(mere conduit)不同,《数字经济法案》希望网络服务提供者扮演起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协助权利人来治理网络中的侵权现象。总结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义务有:将从权利人处收到的版权侵权报告(copyright infringement report)通知相关网络用户,以匿名方式向版权人提供侵权用户名单(以便于权利人向法院申请调取这些用户的真实身份,进而使权利人提起诉讼成为可能)、根据政府(Secretary of State)的指令对反复侵权的网络用户采取降低网速乃至暂时断网的措施,等等。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履行这些义务,政府将对其处以罚金。(13)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法案》在解决网络侵权问题上采取的主要思路是准确记录并找到侵权用户,并对其进行处罚。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其角色在于协助这一目标的实现。(14) 由上述各国所采取的制度设计看到,不少国家都在尝试克服网络匿名性等给传统诉讼救济途径带来的困难,进而帮助权利人能够在网络环境中对其内容依然保有支配性的控制力。然而从制度实际推行的情况看,立法者所设计的追究网络用户责任的法律制度却遭到了许多批评和担忧。无论是上述的网络实名制,还是三振出局规则,抑或英国最新的《数字经济法案》,都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当然,批评并非针对立法者希望追究网络用户的责任,而是这一目标带来的对个人隐私安全、言论自由价值等的潜在威胁,以及实施这些制度将花费的高昂社会成本和取得的回报间的不成比例。从上述这些制度的运作效果看,既有成功的,亦有失败的。比如,韩国在推行网络实名制5年后,首尔大学的研究表明,韩国这5年来网络上的诽谤跟帖数量仅减少了不到2%,而韩国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15)这可能也成为韩国决定废除实名制的重要原因。与之不同,加拿大的通知通知制度则似乎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据加拿大录音行业协会主席Brian Robertson的介绍,有关各方的报告显示,网络服务提供者收到的大约80%投诉是通过这个制度解决的,他称之为“不容易的和平”。(16)尽管从理论角度来看,由网络用户向权利人承担侵权责任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但从目前各国的立法选择来看,完全采用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来治理网络侵权的国家似乎并不多,更多的国家选择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模式。 2.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模式 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模式,指通过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相关制度安排促使其积极采取措施以抑制网络中侵权的发生。至于是否追究网络用户的责任,则并非立法考虑的重点。之所以立法者会将规制重点放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上,而不是网络用户上,主要的原因在于,此种规制模式成本低而效率高。相较于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而言,此种模式一般不要求必须确认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网络服务提供者依权利人的要求对网络中的内容采取措施也不需要经过法院的确认,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经营的网站中的内容一般具有完全的控制力,故此种模式能够快速高效地对网络中的侵权现象做出反应。正如有学者所言:“网络服务提供者被视为连接上互联网的当然看门人,其毫无争议地处于过滤和制止互联网中非法和不良内容传播的最佳位置。”(17)就目前各国立法看,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网站中的内容承担严格责任。此种立法试图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科以严格的责任来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尽可能事先预防网络中侵权内容的出现。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曾体现于美国1995年发布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问题上,该白皮书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其用户有业务上的关系,他们或许也只有他们,能知道用户的身份和了解用户的行为,并进而阻止其非法活动。虽然网络服务提供者从其用户所获得的收益或许与其须负担的责任不相当,且任何措施均会增加其营运成本,但网络服务提供者相较于著作权人而言,对于防止及遏阻侵害仍是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对于同属无辜的两方,最好的策略是由网络服务提供者负起责任。”(18)据此,白皮书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地位类似于出版者(publisher)的地位,需就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严格责任。当然,白皮书中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所修正。 (2)不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科以任何侵权责任。此种立法设计与上述立法完全相反,但二者的制度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两种制度设计所认可的预设前提不同。采用不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科以任何责任的典型立法是美国的《正当通信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of 1996)。该法第230(c)条一般被解读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无需对他人在其网站发布的内容负责,即便其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未采取任何措施。(19)之所以立法者会作出此种立法设计,是因为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关于如何才能在不降低互联网产业商业效率的情况下促进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上的非法内容积极采取措施的辩论中,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的力量(market forces)是最佳的途径,即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会主动地采取过滤等措施来避免侵权的发生,其典型例子便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垃圾邮件的过滤。基于此,立法者应在法律上确保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对网站内容采取审查、过滤等控制措施时不会因此而被科以责任。(20)申言之,立法者认为市场的力量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较之法律责任能够更有效地避免网络中侵权的发生并促进产业的发展。《正当通信法》的这一治理网络侵权的路径引起了很多的争议,经过多年的实践,有学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并没有如当初所预期的那样承担起积极避免非法内容的角色。但也有学者认为,反对者低估了该制度带来的促进网络社区发展等正面价值,并高估了其对无辜者造成的伤害等负面效果。(21)这一制度将如何发展,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3)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做限制性规定。这是当前各国最广泛采纳的制度设计方案,如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欧盟的《电子商务指令》、日本的《特定电气通信提供者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及发信者信息揭示法》以及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等。其基本思路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科以严格责任将导致互联网企业在运营中承担过重的法律风险,且可能导致本国企业在与外国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完全的没有责任又将可能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滥用这一规则,损害其他无辜者的权益,故在一定条件下科以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或给予其责任豁免可能是更佳的选择。从具体制度看,其主要制度设计有二:一是通知移除制度,二是知道制度。根据各国法律环境的不同,通知移除制度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款,如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c)条的规定;另一类是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条款,如中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的规定。通知移除制度的目标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配合权利人的要求移除相关的涉嫌侵权内容,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移除相关内容,则可能需向权利人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22)知道制度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在美国随Grokster案发展出来的引诱侵权责任(Inducement liability),(23)即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利用侵权牟利的意图,则其将承担侵权责任;二是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若知道侵权内容存在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上述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模式的表现方式。总体来看,这三种方式都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解决网络侵权的关键主体,但在具体思路上又有所不同。严格责任多限于对涉及政治性、淫秽等内容的要求,且该方式也常被解读为抑制网络发展;完全放任常与自律、市场等相联系,且被视为保障了言论自由等价值;有限责任/免责往往被视为一种利益平衡的政策选择,似乎与自然正义等关联较少,因此随着利益各方、尤其是内容产业界和互联网产业界间力量的变化,此种有限责任/免责的制度安排也将随之作出调整。 3.两种模式的比较 治理网络侵权的这两种模式相同之处主要有四。其一,两者的制度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有效治理网络中的侵权现象。其二,无论哪种模式,都没有完全抛开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中介。即便是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其制度的设计和有效运作也有赖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诸多配合。正如有学者所说:“权利所有者、集体管理组织和政府将网络服务提供商视为在数字传播的瞬间链条中,能够控制使用者行为的最可行的聚点(point)。”(24)这或许是因为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来实现立法目的是成本低而效果佳的方式。其三,为了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积极配合国家或权利人的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未遵守这些要求时一般都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四,从两种模式的历史变迁看,都越来越强调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侵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两种模式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立法者重点关注的主体不同。前者将抑制网络侵权的重点放在网络用户身上,而后者则放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身上。这具体地表现在前者试图采取有效的制度措施来保障权利人顺利地向侵权的网络用户主张权利。而后者则认为,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等特点,确定和追究网络用户的法律责任成本较高,为此,立法者选择了控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来控制网络用户的方式,从而达到间接控制网络用户的目标。其二,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责任性质不同。在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中,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在于配合权利人向侵权用户主张权利,故其违反义务后承担的一般是行政责任,由国家机关给予其行政处罚。但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对权利人的权利侵害负责,此种侵权责任仍是由实施了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负责。而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模式中,由于立法者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权利人从侵权用户中获得救济,故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义务后往往需向权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需说明的是,这两种治理模式并非截然分割、非此即彼。一国所采取的网络侵权治理方式也并非只能二选一。事实上,由于目前各国对网络侵权的治理也基本处于探索阶段,所以这两种模式都可能被一国同时采纳和尝试,只不过不同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权利客体,或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从各国发展趋势来看,未来这两种模式可能会相互融合,即一国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同时采纳这两种模式。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既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又新增了三振出局规则。 之所以不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网络侵权治理模式,主要的影响因素有:(1)技术原因。如果一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则确定网络用户真实身份的成本可能也越大,其便不太会选择采用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为主要治理模式。(2)历史影响。一国传统的理论、制度能否在网络侵权产生初期有效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新问题也会影响该国后来的制度选择。最初的制度变通方式往往会影响之后的制度安排。因为一种均衡状态一旦开始建立,想再打破重建便比较困难,即便新的方案可能更为合理妥当。(3)价值选择。比如民众对言论自由、私法自治的重视程度会影响其对国家介入互联网管理的认同程度。(4)现实原因。尽管都是网络侵权,但各国所面对的网络侵权画面并不完全一样。比如我国民众知识产权保护观念较淡薄可能导致了我国网络中用户大规模侵权现象比国外更常见。而侵权的普遍程度也会反过来影响立法者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 二、中国网络侵权治理的特点 从目前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对网络侵权的治理方式属于较为典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模式。 1.我国网络侵权治理的具体表现 我国对网络侵权治理的制度设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责任构成上,以归责条款的方式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科以侵权责任。在民事领域,我国规范网络侵权的基本法律是《侵权责任法》,尤其是该法第36条的规定。依照该条后两款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权利人发送的侵权通知,或在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服务实施侵权行为后,若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可见,我国立法明确表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一定条件下需向权利人承担侵权责任。我国学界一般将该条件解读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后果的扩大存在过错。这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只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免责条款,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何种情况下需承担侵权责任未做明确表态的方式不同。 第二,在责任形态上,以连带责任的方式使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相关联。我国立法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规定为连带责任,学界一般将此连带责任的理论依据解释为二者构成共同侵权。此种制度设计与理论解读在国外并不多见。如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没有采取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设计方式。 第三,在实践运作中,我国几乎全面放弃了对网络用户责任的追究。尽管立法从未否定上传侵权内容的网络用户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法院、权利人抑或网络服务提供者,都未积极将直接实施了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纳入诉讼中。这可能与三方面原因有关:一是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这使得实践中权利人几乎只会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被告,因为在理论上其可从网络服务提供者处获得全部赔偿。二是我国立法者并没有设计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法院和当事人高效且低成本地获得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故难以将其纳入诉讼中。三是我国民众尊重知识产权等观念较浅薄,网络中大规模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法不责众”的思想未必正确,但若要对大规模的侵权用户都追究责任,无论在实践操作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较为困难。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立法是“以连带责任形式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立了独立负担的责任机制”,即“事实上的最终责任”。(25) 同时,立法也没有对侵权的网络用户科以断网、冻结用户等其他措施,比如三振出局等。因此,在我国网络侵权治理中,实施了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被全面放过。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网络用户才被追究法律责任,比如艳照门事件。而在美国,上传了侵权内容的网络用户被追究侵权责任并不罕见。事实上,对网络用户责任的追究也成为美国兴起copywrong和copyleft运动的原因之一。 第四,在责任承担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名重而实轻。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连带责任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是承担了较重的责任。比如王利明认为:“我们采取的连带责任,这个对网络经营者来说也是非常重的。”(26)杨立新也认为:“这(指连带责任)是给网络服务提供者苛加的一个较为严重的责任,对此,必须认识到。”(27)从立法规范意义而言,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确实较重。但从实践运作情况看,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责任却又不重。与理论界的通行观点不同,实践中权利人则普遍认为,我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赔偿金标准过低,根本无法有效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及时履行移除侵权内容等义务。理论与实务的这种相反观点折射出了我国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问题上名义责任重而实际承担的赔偿金轻的现实。 2.我国网络侵权治理的设计理念 在网络侵权治理模式上的具体制度表现反映出我国立法者在制度设计时存在以下一些设计理念。 第一,将不追究网络用户的责任作为制度设计潜在承认的现实。我国虽在立法和理论上都认同网络用户需对其侵权承担责任,但在制度设计和运作上却没有相关的安排来充分保障权利人对网络用户责任追究的实现。尽管我国立法中也存在个别有助于追究网络用户责任的制度安排,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权利人提供侵权用户的注册资料。但立法者对这一制度的贯彻实施其实尚处于犹豫之中。比如据立法资料显示,我国《民法(草案)·侵权责任法》第一次审议稿规定:“权利人要求提供通过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的注册资料,网站经营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该规定在第二次审议稿中即被删除。(28)据有学者介绍,删除是为了避免“带来侵犯网络用户隐私等风险,并可能破坏网络的匿名性”(29)。从司法实践看,法院在诉讼中其实并没有强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用户信息,也没有根据共同诉讼规则而要求权利人追加侵权用户为被告,相反,法院在诉讼中主要强调的是纠纷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权利人间解决。 第二,努力平衡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间的感受。由于几乎放弃了将网络用户纳入纠纷当事人中,故我国立法将制度设计的重点都放在了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关系的调整上。我国采取的是平衡二者的方式。一方面,在舆论和道德制高点上支持权利人的主张,但却并不给予权利人充分的赔偿。另一方面,在道德上谴责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用户的“帮助”行为,并就此在名义上科以重责(连带责任),但却在实际的赔偿金上放网络服务提供者一马,未让其承担较多的赔偿金。概言之,我国平衡双方利益和感受的方式是:对权利人采取的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安抚政策,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务实政策。 第三,重利益平衡而轻理论论证。不应否认的是,不仅在我国,包括在美国等国家,在网络侵权领域,立法者和司法机关所遵循的,更多的不是理论逻辑,而是利益平衡,尤其是内容产业界和网络产业界间利益的平衡。这突出地表现在对网络侵权的制度设计往往先于理论论证。包括通知移除制度在内的许多网络侵权治理规则都是先由相关产业界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率先提出,再由理论界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梳理和论证。理论界更多是在为产业界利益争斗所反映在法律文本上的结果做注解,而失去了引导产业界间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前瞻性。在我国学界,这一观念的典型表现是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取决于网络产业发展和权利人权益保护间的平衡。(30)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更多的似乎是一种利益平衡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正义要求或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规律。 第四,试图树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追究的道德正当性。在一些采用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的国家,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被认为并不负有向权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正当性基础。立法者希望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帮助权利人避免和减少网络中侵权现象的发生。权利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此予以配合与帮助并非理直气壮。这典型地体现在英国《数字经济法案》中权利人为取得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配合需承担由此给网络服务提供者增加的成本负担。 同样,美国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而产生了一股消解知识产权人道德制高点的运动,其典型表现是劳伦斯所倡导的知识共享运动(creative commons)和斯托曼所坚持的自由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而在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被视为侵权行为的帮助者和共同实施者,因此权利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承担的主张同时也包含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道德上的谴责。这是我国与他国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上所持的不同态度。之所以我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追究包含了道德正当性,潜在的观念支撑可能是,我国立法者其实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有能力审查网络上海量的信息。比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中颠覆国家政权等言论的预防做得就较为成功,故立法者有理由相信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他侵权内容也完全能够做到较好的审查和预防。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能做到,更易于被立法者认定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 第五,我国采用归责条款模式体现了立法者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问题上的封闭式处理方式。免责条款和归责条款的制度设计不仅与一国传统立法背景有关,也可能体现了一国在责任设计时的不同心态。前者体现了立法者的“不知”和谨慎,后者体现了立法者的“已知”(也可能是武断)和自信(也可能是自大)。对前者,立法者尚不知道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条件是什么,但他们需要给予网络服务提供者一个最低限度的预期,使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自己肯定不承担责任。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未满足该条件是否必然要承担责任,则留有空白,以观时变。后者的立法则画地为牢,在一定条件下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担责任。从逻辑严谨性角度而言,两种立法方式前者更优,因为在逻辑上,否定一个结论易,证成一个结论难。在新问题出现的初期,采用否定式立法,在研究较充分后,采用肯定式立法可能是更妥当的选择。 三、中国网络侵权治理的完善建议 从中国和他国治理网络侵权的经验看,中国对网络侵权的治理方式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出调整和完善。 第一,尝试逐渐将网络用户纳入侵权责任的追究对象中。之所以要将网络用户纳入责任主体中,是因为对用户责任的追究才能从根本上抑制侵权的发生。仅仅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而放任网络用户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用户继续上传侵权内容。目前制约我国立法者将网络用户纳入侵权责任主体的主要因素有:一是技术制约,我国尚未有足够高效且低成本的技术来实现对网络用户真实身份的确认。二是价值选择的制约,对网络用户身份的确认会引发社会对个人隐私安全、言论自由等价值被破坏的担忧。三是民众观念的制约,我国民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尚不高,网络用户大规模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对所有侵权用户大面积追究责任可能并非立法者所希望的。 可见,将网络用户纳入侵权责任主体中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事实上,我国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已经开始尝试对网络用户采取措施,比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9条允许权利人在提起诉讼时以IP地址或网络名称为被告。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发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指导意见(试行)》第5条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了类似“三振出局”的建议。我们需要积极总结这些措施的经验,并在理论上作出相应的回应。 第二,在当前我国仍以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为主的情况下,对其损害赔偿金的计算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而渐渐提高。 只有在制度设计上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放任侵权的损失大于因侵权获得的收益,才能有效地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积极地去减少自己网站侵权的发生。其实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司法机关采取的态度是优先保护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内容制造者的利益。但这种倾向性的保护很可能是阶段性的,随着互联网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天平可能会慢慢趋于平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的赔偿金也会逐渐加重。 第三,支持和鼓励技术保护措施的发展。我国目前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制度设计不利于鼓励发展确定侵权用户身份的制度和技术,也不利于鼓励发展事先预防侵权的制度和技术。我国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认定为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设计使得权利人不再关心侵权的网络用户本身,因为理论上网络服务提供者会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被“科以重责”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并不关心找到直接侵权的网络用户,因为其在法院判决中实际承担的损害赔偿金并不高,基本与其过错和原因力相当,而并非与权利人的损失相当。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制度设计和运作的结果是,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发现和追究真正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的责任。同理,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制度设计也不利于鼓励发展事先预防侵权的制度和技术,(31)但恰恰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救济,可能是网络侵权问题更为重要的解决之道。 第四,应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在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场合,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需向权利人承担侵权责任并非如国内学界所表现的那样理直气壮。事实上,不少国家并不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权利人所遭受的侵害负有责任,也并没有科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尽管从历史变迁看,毫无疑问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侵权治理中正在承担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有学者将此趋势概括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从过去的消极——被通知后采取措施(passive-reactive)发展为积极——主动采取预防措施(active-preventative)。(32)然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如何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才是问题的关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权利人承担侵权责任并非唯一途径。 第五,多了解和借鉴各国的网络侵权治理经验。目前国内学界对网络侵权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可谓“言必称美国”。无疑,美国的制度设计是我国需重点关注的,但我们同样也需要关注其他一些国家的制度安排。尤其是一些采用网络用户中心主义模式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了解他们如何设计制度并实现对网络用户的责任追究,对已经习惯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模式思维的我国可能会更有启发。 第六,网络环境中一些关键性网站将可能承担起更多的治理网络侵权的责任。在网络环境中,有一些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比如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域名解析服务提供者、网上支付服务提供者,等等。这些网站是网络用户进入其他网站,有效实现网上服务的重要辅助者,失去了这些关键性网站,网络服务的质量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在互联网中流传一句话:一个内容若无法被搜索引擎搜索到,那么这个内容在网络中便是不存在的。这表明了搜索引擎对于用户接触到网上内容的重要性。同样,一个无法被解析的域名,也难以被人们记忆和推广。正因为这些网站的重要性,它们在治理网络侵权方面可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2012年讨论的《阻止在线盗版法案》便采取了这一思路。我国有学者称其为垄断看门人所应承担的责任。(33) 从目前发展看,在美国由于互联网产业界强大的影响力,任何涉及网络侵权的新规则的通过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困难。2012年的《阻止在线盗版法案》因互联网产业界强大的压力而被无限期搁置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合理推测,在美国未来的趋势是,对网络侵权问题的解决将越来越依赖于呼吁行业自律、开发技术保护措施,同时辅之以在必要时司法判决发展出新规则(如Grokster案)。美国在立法层面对网络侵权作出调整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而这将倒逼内容产业界与互联网产业界间寻求相互合作。而在我国,并不存在立法上困难这个问题。从我国以归责条款的方式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认定为连带责任的规定来看,就网络侵权问题,我国在立法层面算得上是较为“激进”者,但我国在司法判决中又做得比较保守,尤其在赔偿金的计算方面。由于立法的稳定性,我国短期内修正立法的可能性较小。未来的重点在于如何从理论上解读该“激进”立法,使该制度的内涵变得缓和,并考虑如何将该立法内容融入传统侵权理论体系中。 ①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的理解与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②关于韩国实施实名制的情况,可参见詹小洪:《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兴与废》,《南风窗》2012年第5期。另见新华网的相关报道,如《国外互联网管理:实名制为韩国网络安全保驾护航》《韩国拟分阶段取消网络实名制以保护个人信息》等。 ③当然,有些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能未必掌握和控制,比如用户的注册密码如果是用密文(而非明文)方式保存,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也无法得知。 ④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Opinion of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on the Current Negotiations by the European Union of an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ACTA),22 February 2010,pp.3-4.http://www.edps.europa.eu/EDPSWEB/webdav/site/mySite/shared/Documents/Consultation/Opinions/2010/10-02-22_ACTA_EN.pdf,available on 2015-10-5. ⑤参见法国2009年《在网络上深化传播和保护创作法》(loi favorisant la diffusion et la protection de la création sur Internet,Loi HADOPI 1-Law further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Protection of Creation on the Internet)。 ⑥参见英国《数字经济法案》(Digital Economy Act 2010)。 ⑦参见韩国2009年《版权法》(Copyright law of South Korea)。 ⑧参见新西兰《2011版权修正案(侵权文件的共享)》(Copyright(Infringing File Sharing)Amendment Act 2011)。 ⑨参见我国台湾地区2009年《著作权法修正案》。 ⑩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国的DMCA已经通过,该法规定了通知移除制度。通知移除制度是加拿大最初版权改革中讨论最多,且最后加拿大遗产委员会也建议采纳的方法。但最终加拿大没有认可美国的这一制度,而自发设计了通知通知制度。可以合理推测,通知通知制度并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而是加拿大谨慎考虑后的结果。 (11)关于加拿大的通知通知制度参见谢利尔·哈密尔顿:《加拿大制造:确定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和版权侵权的独特方法》,载迈克尔·盖斯特主编:《为了公共利益:加拿大版权法的未来》,李静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01-219页。 (12)Sam De Silva and Faye Weedon,"The Digital Economy Act 2010:Past,Present and a Future ‘in limbo’," Comput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Review,No.17,2011,p.62. (13)See Digital Economy Act sections 3-16. (14)依《数字经济法案》第5条的规定,权利人若想取得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需事先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支付其为此所承担的成本,这更加体现出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对权利人而言是协助角色,而非必然的义务主体。 (15)詹小洪:《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兴与废》,《南风窗》2012年第5期。 (16)谢利尔·哈密尔顿:《加拿大制造:确定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和版权侵权的独特方法》,载迈克尔·盖斯特主编:《为了公共利益:加拿大版权法的未来》,李静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17)Lilian Edwards and Charlotte Waelde,Online Intermediaries and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p.17.http://www.wipo.int/meetings/en/2005/wipo_iis/presentations/doc/wipo_iis_05_ledwards_cwaelde.doc&sa=U&ei=GGF6UNP-FOrKmgW414GoDQ&ved=0CA0QFjAD&client=internal-uds-cse&usg=AFQjCNGyXIBpfB3_hhWPP3FGpyOHdfJ_xg,available on 2015-10-5. (18)Bruce A Lehman(Chair),"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Th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September 1995,p.117. (19)Blumenthal v.Drudge and AOL,992 F.Supp.44,24(D.D.C.1998). (20)Lilian Edwards and Charlotte Waelde,Online Intermediaries and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pp.17-22.http://www.wipo.int/meetings/en/2005/wipo_iis/presentations/doc/wipo_iis_05_ledwards_cwaelde.doc&sa=U&ei=GGF6UNP-FOrKmgW414GoDQ&ved=0CA0QFjAD&client=internal-uds-cse&usg=AFQjCNGyXIBpfB3_hhWPP3FGpyOHdfJ_xg,available on 2015-10-5. (21)H.Brian Holland,"In Defense of Online Intermediary Immunity:Facilitating Communities of Modified Exceptionalism," Ssm Electronic Journal,Vol.26,No.26,2007,pp.164-71. (22)在美国2012年讨论的《阻止在线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通知移除表现方式,即将过去DMCA中适用于具体侵权内容的通知移除制度扩展应用于整个网站,将侵权网站从搜索引擎、支付服务提供商、广告服务提供商中整个移除掉。但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强烈反对,该法案最终并没有得到通过。 (23)Metro-Goldwyn-Mayer Studious,Inc.v.Grokster,Ltd.,545 V.S.913(2005),F.3d 1154. (24)谢利尔·哈密尔顿:《加拿大制造:确定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和版权侵权的独特方法》,载迈克尔·盖斯特主编:《为了公共利益:加拿大版权法的未来》,李静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25)吴汉东:《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26)王利明、杨立新、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立法的新进展三人谈》,载王利明、韩大元主编:《在人大法学院听讲座》第3辑《侵权责任法专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27)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的理解与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此外,认为连带责任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责任较重的学者还包括张新宝、刘颖等,参见张新宝、任鸿雁:《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刘颖、黄琼:《论〈侵权责任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8)《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4、11页。 (29)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263页。 (30)参见陈锦川:《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认定的研究》,《知识产权》2011年第1期。 (31)比如国外一些公司已在使用和完善的指纹过滤技术、数字水印技术等。 (32)Jeremy de Beer and Christopher D.Clemmer,"Global Trends in Online Copyright Enforcement:A Non-Neutral Role For Network Intermediaries?" Jurimetrics,Vol.49,No.4,2009,p.35. (33)参见万柯:《网络等领域垄断看门人的替代责任》,《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其实,就商业而言,各网络公司都希望自己成为网络用户入口性的网站,但成为用户入口,也意味着可能需负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标签:网络侵权论文; 网络服务提供者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互联网侵权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