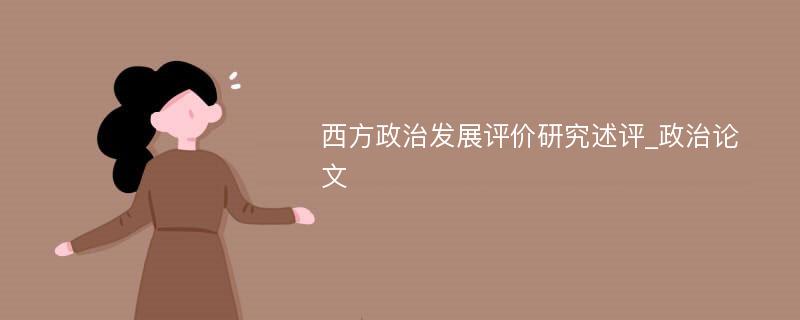
西方政治发展评估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自人类社会产生政治现象以来,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便成为贯穿其始终的主题之一。20世纪50~6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发展概念最早形成于西方政治学界。凭借战后庞大的研究投入和长久的学术积淀,西方政治学界从一开始就掌控着政治发展评估领域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然而,西方政治发展评估研究在概念解析、评估维度选取、指标测量等多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甚至是意识形态偏见,难以对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展开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估与测量。有关民主、人权、治理、清廉等政治发展,诸多领域的评估的话语权仍然被少数西方国家所垄断。相比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相应的话语权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因此,对战后西方政治发展评估研究展开必要的回顾、批判与反思,对于我们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科学、客观、全面地评估全球政治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围绕政治发展概念的相关研究与争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在政治发展的概念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统一、权威的认识。在政治发展的概念问题上,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鲁恂·派伊(Lucian W.Pye)所言,尽管“对于认识政治发展的性质的重要性有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在‘政治发展’这个词的运用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模糊”。①可以说,政治发展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西方政治发展评估研究必然会陷入更加错综复杂的格局。 关于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念,派伊在《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中列举了理解政治发展概念的十个方面:(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政治形态;(3)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5)政治发展是行政和法律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7)政治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迁;(9)政治发展是动员和权力;(10)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他归纳出了政治发展概念的三个最根本的主题:(1)它是关于平等的一般精神或态度;(2)它与政治体系的能力有关;(3)它与政治体系的分化和专业化密切相关。②与派伊相对庞杂的理解不同,阿尔蒙德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将政治发展定义为“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③ 在讨论政治发展概念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对另一个与政治发展密不可分的概念——政治现代化予以关注。从源头上看,“现代化”一词最初多被视为一个经济学概念。随着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这一概念开始日益渗透到政治学研究领域。与政治发展一样,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定义同样没有统一的标准。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认为,政治现代化涵盖了政治发展,“现代化是一个有意识地引导和控制社会中日益分化的角色和组织体系的社会结果的过程”,而传统性“是现代化研究(尤其是其政治方面)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④派伊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二者视为同一,“如果只简单地把政治发展归结为一种政治上的‘现代化’的话,就会碰到区分‘西方的’与‘现代的’之间异同的困难了”。⑤相比而言,亨廷顿倾向于将二者间的关系模糊化,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分析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秩序问题。不过,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仍然使用“政治现代化”一词来概括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并将政治现代化归纳了三个基本特征,即权威的合理化、政治结构与功能的专门化和广泛的政治参与。⑥ 实际上,无论是政治发展还是政治现代化,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虽然在体系化、实证化方面存在可取之处,但难以真正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例如,詹姆斯·柯尔曼(James Coleman)就认为:“从历史观点来看,政治发展指16世纪首先发生于西欧的社和经济现代化的变迁,及政治文化和结构同时发生的整体变迁,后随历史演进,这种变迁不平均亦不完整地传播到全世界。从类型学观点来看,政治发展是一种从假定的现代前期的‘传统’政体转变到后传统期的‘现代’政体的运动。”⑦甚至连阿尔蒙德也曾自信地表示,“我相信,我们能十分安全地使用像西方化这样的观点,只要我们注意易受经验研究影响的演绎过程。因为这只是帮助我们解释如何及为何政治发展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发展程度的一种重要资讯罢了”。⑧可见,即使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自身的观点,大多数西方学者仍难以摆脱“现代化=西方化”这一根深蒂固的理论偏见。 随着战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发展中国家关于政治发展概念的研究也在由初期的单纯引进转向不断地消化、反思与创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国内学者就已经开始摆脱“政治发展专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观念束缚。例如,王沪宁就认为,对于政治发展概念,应该从多维度的思路来理解,其中主要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维度。他认为,政治一体化、政治结构的分化、政府机构的高效化、政治民主化这四大特征是政治发展向较高层次迈进过程中对政治体系提出的必然要求。⑨又如,在对西方多达11种定义进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台湾学者陈鸿瑜指出,政治发展是“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度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⑩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全面、理性地看待政治发展,无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它也成为科学地评估政治发展进程的基本前提。 二、理论流变与发展阶段 从源头上看,西方政治发展评估与战后兴起的政治发展研究密切相关。伴随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衰起伏,西方政治发展评估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产生、发展、壮大到衰落的曲折嬗变过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不断瓦解,在欧美以外的广大地区,大批前殖民地纷纷摆脱殖民统治的束缚成为独立国家。与战后方兴未艾的“现代化”研究热潮相对应,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更多地呈现出对西式现代化模式的盲目乐观。持这种“正统现代化论”的学者大多认为:“早期实现了工业化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具有现代性;新独立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仍属传统国家,不具备现代性。传统国家经过发展和阵痛,逐步引进和采纳现代性的全部价值标准,摒弃并排除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从而过渡到现代社会,正如早期现代化国家在18、19世纪曾经经历过的那样。”(11) 但是,这一过于线性化的政治发展理论并没有被广大受援发展中国家中的政治实践所证实。恰恰相反,伴随着经济、技术援助而来的西方模式所带来的并非稳定与繁荣,而是一轮又一轮的政治社会动荡与经济衰退。面对这一理论困境,在重新思考传统—现代二元关系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所谓“修正”的现代化理论。(12)该理论主张,政治发展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简单线性关系,而是能够通过良性互动有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前述两种现代化理论不同,亨廷顿从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提出了以“秩序”与“权威”为核心的“强大政府论”。他指出,“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急剧的社会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系本身的承受能力。为了从根本上抑制国内政治动荡与衰朽,必须在这些国家树立起强大、稳定的政府权威。”(13) 随着世界很多地区包括欧美在内相继迎来战后空前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企图简单地依据某种现存的模式来划分社会类型是一种不可取的研究方法”。(14)在对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一批学者提出了“依附论”或“依附与低度开发论”(dependency and underdevelopment)。(15)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反题,持这一论点的学者主张,“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落后与低度开发,并非由于它们的前现代化即前资本主义结构,而是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所造成。这种经济体系形成的宗主国与卫星国秩序,是一种帝国主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16)当然,依附理论主张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权威的分析框架与基本结论,持此观点的学者之间在前提预设、研究方法、概念构建、思考逻辑和价值判断上都存在不小的分歧和争论。而在西方政治发展学界,学者们也开始从方法论、实证和意识形态挑战的角度反思与修正早先关于政治发展评估的相关认识与结论。(17)总体而言,战后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评估的认识越来越摆脱传统现代化观念的束缚,贴近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现实的趋势。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对西方本位主义的强调仍然是西式政治发展理论及其评估研究根深蒂固的所谓“道统”,这一点无疑严重阻碍了政治发展评估研究进一步创新的步伐。 三、评估标准、维度与指标体系 20世纪50~60年代,伴随政治发展理论的形成,西方关于政治发展评估的研究和探索也开始出现。实际上,关于政治发展评估与测量的研究与区域研究尤其是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入开展同样密不可分。关于这一发展趋势,亨廷顿曾指出:“60年代初,源于区域研究和源于行为革命的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结果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发展的问题上。(政治学者们)运用从行为革命吸取的概念和方法,而且相当自然,常常还试图把他们在首次研究一个国家时所发现的关系概括进多少与大多数国家有关的关系中去。”(18)可以说,行为主义革命不仅为发端于区域研究的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根基和新的理论分析模式,也为政治发展的评估与测量构建起坚实的学理性资源和提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契机。 在评估政治发展的评估目标、价值与标准方面,阿尔蒙德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一书中,他将世俗化、分化和能力作为评估政治发展最为重要的三大标准,三者分别对应于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结构的专业化程度以及相应的统合能力。(19)与之类似的是,派伊也总结了评判政治发展的三个得到广泛认同的主题,即关于平等的一般精神或态度、政治体系的能力、政治体系的分化和专业化程度。派伊认为,这三个向量正是政治发展过程的核心。(20)与此同时,在探讨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过程中,李普塞特较早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测量与分类。依据工业化、财富、教育、社会沟通等多个维度,他将欧洲以及母语为英语的28个国家划分为稳定民主、不稳定民主与独裁两类,将20个拉丁美洲国家划分为民主与不稳定独裁、独裁两类。(21)此外,菲利普·卡特莱特(Phillips Cutright)从测量政治发展的宏观角度出发,以1940-1960年间的77个主权国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些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的绩效进行赋值和加总,发展出一套用于衡量不同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的政治发展指数。(22) 20世纪60年代前后,“现代性”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民主性”逐渐被西方学界看做评估一个政治体系发展程度最为核心的价值与标准。在针对政治发展不同维度的评估与测量领域,民主无疑是最为关注也是着力最多的方面。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对民主进行定性乃至定量的评估与测量的尝试始终是西方政治发展评估领域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对“多头政体”的分析与论证过程中,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政治体系在民主化层面所应具备的一系列基本要件或标准,而其核心就是竞争性的选举。(23)由此,“选举”民主成为西方民主评估与测量领域最为核心的标准与传统。这种所谓标准与传统也直接影响着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学界对于民主的一系列测评尝试。 20世纪70年代前后,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所谓“传统”政治发展道路进程的受阻,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停滞甚至衰退,相对于传统上对民主价值的强调,“权威”与“秩序”逐渐成为衡量政治发展不容忽视的新标准。在这方面,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以西方民主政体的标准来衡量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是不科学的。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除政治结构专业化、政治文化和民主化推进等常规事项之外,必须将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政治的“有效程度”放在更加重要与突出的地位来加以对待。 在学者们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针对政治发展的评估与测量的实践也在不断深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学者、研究机构或其他组织纷纷加入到针对政治发展的评估与测量活动之中,相应的测评指标、指数、排名等也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在名目繁多的指标、指数中,具备较大世界性影响力的主要包括美国“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Freedom House:Freedom in the World)、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的民主指数(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Democracy Index)、全球清廉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ertelsmann:Transformation Index)、失败/脆弱国家指数(Failed/fragile States Index)、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的民主评估(IDEA:Democracy Assessment)、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全球和平指数(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Global Peace Index)等。 此外,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推出了各自的评估及其指标体系。这类指标体系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组织针对各成员国所展开的调查与评估最具代表性,其目的主要是针对成员国开展有计划性的民主治理咨询与援助,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治理指标项目(Governance Indicators Project)和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这两大项目均面向成员国展开涉及面极广的调查研究,并且每年都会形成相应的研究评估报告。与学术色彩较为鲜明的测评指标体系不同,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测评更加倾向于治理等较为宽泛的概念与指标,相应地其针对性也不如前者突出。例如,世界治理指标就以治理为切入点,通过对民众要求与政府责任、政治稳定度与暴力控制度、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和反腐等六个维度来对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治理绩效进行具体评估。 应当指出,在经历了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革命”后的今天,西方学界关于政治发展评估的研究虽然看似在体系化和实证性方面日臻完善,但其背后的一系列实证与价值方面的弊病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一方面,一国或地区的政治发展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它与该国或地区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西方关于政治发展的评估研究却大多只强调西式理论与模式的普适性,忽视非西方的政治发展评估的价值,并从根本上拒绝将其与西方主流理论等量齐观。另一方面,在具体测评体系的构建方面,西方现有的绝大多数成果在指标选取和测算等方面的片面性、武断性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实证分析,西方学者仍潜移默化地采用着他们固有的价值标准和发展模式。由此,在这种西方本位主义的背景下,其所构建的各种测评指标也必然无法准确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社会现实,遑论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四、历史与逻辑反思 回顾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发展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传统的西式政治发展理论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劲。在当前西方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国际政治评估体系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不断“被排名”的尴尬。即使在政治社会发展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往往也会被西方既有的评价体系选择性地忽略,甚至是被贴上“异类”的标签。事实上,近些年来这种片面的评价体系暴露出的弊端已经日趋严重。从政治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角度出发,上述单一、片面的评估方法与指标体系亟待反思与重构。 一方面,从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传统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第三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现实之间显然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西式政治发展评估在这方面犯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错误。因此,西式政治发展这种单一的、片面的评价标准与维度必然无法真实地评估与衡量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60年代,受整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西方政治发展领域的相关学者大都乐观地表示,通过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必然能够发展出一套足够严密、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来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进行科学的评估与预测,就像经济学领域所实现的那样。(24)但是,简单移植西式理论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政治衰败与社会动荡,使得相关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严重发展悖论。 另一方面,西方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在理论预设方面存在着难以避免的逻辑缺陷。在深受西方社会进化论影响的思维理络中,作为政治发展理论源泉的现代化理论存在着两个互相联结的假设来作为其论证的根基,即“假设一,当下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根据西方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而被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便是人所熟知的‘传统—现代’两分观;假设二,人类历史注定沿着单一轨线发展,此一轨线由前后相续、性质严格区分的阶段构成;依据上述‘传统—现代’两分观,这种发展就表现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25)由此,西方传统政治发展理论从其论证与评估的逻辑起点开始就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国际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尤其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不断走向均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深刻地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模式的深层次矛盾,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西式自由民主一元论的终结。然而,面对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传统的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学者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以福山为例,面对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针对自由民主主义越来越多的批判与挑战,他的“历史终结论”虽然也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从以往的乐观态度更多地转向对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总结与反思。但是,客观地看,福山的核心观点和思想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例如,他认为,“现在对自由民主挑战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结合了威权政府和局部市场化经济,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是,这一模式不可能真正成为东亚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替代性方案。另外,这一模式能否持续,这也是一个疑问,因为它缺乏法治和负责任政府两项原则”。(26)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长河中,历史从来不会出现所谓的终结。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关于不同政治发展理论的争论与竞争就会持续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发展新形势与新格局的不断出现,必然要求人们在评估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破除西式理论陈规的束缚。 五、小结与启示:政治发展评估的中国立场与实践 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破解政治发展评估困局的终极之道,必然是对中国立场与实践的创新与回归,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成功发展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主流模式显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对于少数掌控国际政治评估话语霸权的西方大国而言,中国的发展显然会被视为“另类”,并遭遇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价。2016年1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社公布了2015年度全球民主指数评估报告。在纳入统计的167个国家或地区中,中国排名第136位,继续被强行贴上“专制独裁”国家的标签。(27)可见,对于充满单一、线性色彩的西方评估体系而言,中国在政治发展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足以改变西式政治发展评估固有的傲慢与偏见。因此,破除西式评估话语陷阱,积极拓展自身国际话语权,仍将是未来我国在该领域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挑战之一。 相比西方学界,国内关于政治发展及其评估的理论研究普遍起步较晚。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政治发展的相关研究大体还停留在对西方经典理论的译介与阐释方面。90年代中后期,不少学者开始陆续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政治发展评估已经日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一些有意识的、系统性的测评尝试也正在逐步显现。 进21新世纪以来,随着“治理”概念的兴起,国内学界开始出现从治理和善治角度展开政治发展评估与测量的相关研究。其中,俞可平、何增科等人针对中国政治发展评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相关的具体维度出发,俞可平等总结出了三套治理评价体系框架,即中国善治指数评价体系框架、中国低收入人群优先和性别敏感的民主治理评价体系和中国公共治理评价体系框架。在这些框架之内,分别又包括若干二级和三级指标。(28)区别于国家治理,张树华从全面考察政治发展过程的角度指出,“政治发展包含三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变量和价值追求,即民主(公平、权利、自由)、效率(廉洁)、秩序(稳定)。只有民主、效率、秩序三组价值要素间协调进步、相向增长和共同发展,才是科学的政治发展观的本质要求”。(29) 在理论探讨的同时,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和科研机构也在尝试从不同角度构建政治发展的评估框架及其测量指标体系。其中,以俞可平为首的“中国治理评估框架”课题组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以“国家治理评估”课题为依托,推出了“中国国家治理评估框架”。(30)关于中国的国家治理评估,他共设立了12个维度,其下又有多达116个关注点或具体指标,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评估指标体系。(31)俞可平等的研究虽然形成了总体性的评估框架,但基本上属于对国内外现有评估指标体系的简单汇总,其评估框架中相关各项指标的科学性以及评估内容的可测量性等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张树华从树立正确的民主观与科学的政治发展观的思路出发,通过对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经验与教训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构建中国版的“各国政治发展力指数”的构想。(32) 在国家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方面,以高奇琦等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指数”(National Governance Index,简称NGI)颇具代表性。从指标构成上看,该指数包括基础、价值、可持续3项一级指标,以及设施、秩序、服务、公开、公正、公平、效率、环保、创新等9项二级指标。(33)2015年12月,《2015国家治理指数年度报告》正式对外发布。该报告共对全球111个主要国家的治理指数进行了比较和排名,其中新加坡位列第一,中国位列第十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国土面积、经济总量等方面来看,中国均是唯一一个以“发展中大国”身份入选前20的国家。从全面反映政治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该指数对近年来中国在治理层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出了大体客观的反映与评价。可见,以治理为切入点和着力点,未来我国在政治发展评估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无疑将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国际上关于政治发展评估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相应的测评指标体系也在日益丰富和完善。然而,当前国际政治发展评估领域的话语权却几乎被少数西方大国所垄断,未来“西强中弱”的局面仍将持续下去。对此,我们应有冷静、辩证地看待,尤其不可操之过急,刻意在短时间内与西方既有指标体系争一时之长短。同时,也不能期待通过某几个或某几次指标的制定与发布便可以在相关领域确立优势地位。国际政治发展评估领域的具体实践告诉我们,围绕政治发展的评估与测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必须树立长远的战略性眼光,以稳健、可持续的方式积极推进。未来,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治发展相关成就与经验的不断积累与升华,中国必然能够突破西式话语霸权的束缚,确立起自身的特点与优势,从而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作出实质性贡献。 注释: ①〔美〕鲁恂·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②Lucian W.Pye,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58,New Nations: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1965,pp.1-13. ③〔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74页。 ④〔美〕戴维·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⑤〔美〕鲁恂·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2009年,第53页。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2~110页。 ⑦Leonard Binder,et al.,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73-100. ⑧Gabriel A.Almond,Political Development:Essays in Heuristic Theory,Boston:Little Brown & Company,1970,p.291. 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⑩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26~27页。 (1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008年,第Ⅱ页。 (12)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瑟夫·古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和S.N.艾森斯塔特(S.N.Einstadt)等。 (13)Samuel Huntington,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World Politics,Vol.17,No.3,1965,pp.386-430. (14)Richard A.Higgott,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83,p.18. (15)该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学者包括:〔美〕保罗·巴兰(Paul Baran)、〔德〕弗兰克(A.G.Frank)、〔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埃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 (1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2页。 (17)Robert T.Holt & John E.Turner,Crisis and Sequence in Collective Theory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9,1975,pp.979-994. (18)〔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褚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9~150页。 (19)〔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2007年,第20~24页。 (20)〔美〕鲁恂·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2009年,第63~65页。 (21)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No.1,1959,p.74. (22)Philhps Cutright,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Measurement and Analysi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8,No.2,1963,pp.253-264. (23)〔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慧荣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24)Vernon W.Ruttan,What Happened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39,No.2,1991,pp.265-292. (25)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1~92页。 (26)Francis Fukuyama,The Future of History: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Foreign Affairs,No.1,2012. (27)http://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 Handler.ashx?fi=EIU-Democracy-Index-2015.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Index2015. (28)何增科:《中国治理评价体系框架初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29)张树华:《中国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3期。 (30)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2009年。 (31)俞可平:《关于国家治理评估的若干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3期。 (32)张树华:《民主化悖论——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73页。 (33)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5466.标签: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评估标准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科学论文; 现代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