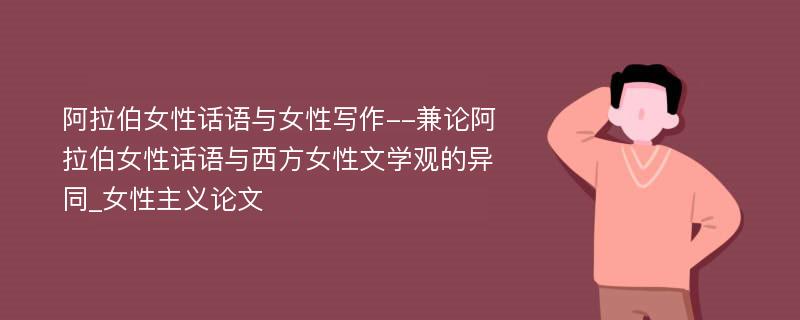
阿拉伯的女性话语与妇女写作——兼论其与西方妇女文学观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阿拉伯论文,异同论文,话语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许多国家里都曾出现过优秀的女性诗人和文学家,但她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不如与之才华相当的男作家那样地位显赫,“因为女性文学在文学史家看来始终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注:王宁著:《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这种情况在阿拉伯社会也不例外, 甚至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科威特著名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Souad Al—Sabah 1942—)对此深感不满,同时努力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思考应对的策略,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实。
一、从女性失语状态中走出
在为数不多的阿拉伯女诗人行列中,苏阿德·萨巴赫意识到妇女在文艺创作领域仍然处于极端的弱势。这种弱势的实质在于妇女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她明确指出:“在漫长的各个历史阶段里,女性的声音总是与羞耻、体面和贞节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有些偏激的老古板甚至认为女性声音都是一种耻辱,不可以暴露给听众。……禁止女性出声,并把它置于监护之下,使阿拉伯社会仅以一种声音说话。那就是男人的声音,粗哑、咸涩、金属般的声响。”(注:苏阿德·萨巴赫:《爱情诗篇》序言,苏阿德·萨巴赫出版社,1994年第3版。)直至现代社会,妇女被强迫禁声,被剥夺写作权利的现象仍在延续。
虽然现代社会对女性话语与妇女写作的压力多为隐形的压迫,但对女性创作欲望和创作能力的发挥所产生的打击作用却是巨大的。而公开、明确地剥夺女作家写作权利在现代社会简直是骇人听闻,然而这种事情的的确确在阿拉伯社会发生了。埃及女作家艾莉法·里芙阿特(Alifah Rif'at 1930—)的遭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她从1947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如《两个女人的事》、《夏娃把亚当带回天堂》和《我的隐秘世界》等小说,描述了女性同性之间痴迷与疯狂的情感历程。小说在《解放》、《文化周刊》和《花》等期刊上发表以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她的出名却激怒了她的丈夫。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妻子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更不能忍受妻子比自己强(起码在文学方面比他强),便粗暴地禁止她再写任何一个字,不让她的作品发表。从1955年到1974年丈夫去世,她没能发表任何东西。然而丈夫能禁止她发表作品,却无法禁止她偷偷地写作。每当她产生要创作的强烈愿望的时候,她就只好跑进洗手间,把自己锁在里面,趴在地上,迅疾挥笔顽强地写作。1974年她的监护人丈夫去世以后,对她发表作品的“禁令”随即解除,她一口气发表了18 个短篇(大多刊发在《文化周刊》上)。(注:See Miriam Cooke:"Arab Women Writers",M.M.Badawi ed.:Modern ArabicLitera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458.)如果说这种明目张胆的压制在现代阿拉伯社会只是少数,那么对女性作家、女性诗人的冷嘲热讽或恶毒攻击等隐形的、间接的压迫则比比皆是,苏阿德·萨巴赫本人就曾为此遭受精神上的伤害。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话语权的争夺。男性对话语权的控制导致了女性的失语症及其它种种不良后果。因此在苏阿德·萨巴赫看来,阿拉伯历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都只是男声乐队独自演奏的“交响乐”,这样的交响乐是不完整的,是一种“残缺的交响乐”。
女性的禁声,女性的失语,是男性权力话语压迫女性的结果。在男性权力话语的一统天下,女性因丧失说话的机会而无法显示其女性意识,从而掩盖了女性的真实存在,掩盖了女性的本质所在。男性牢牢地把话语和写作的权力控制在手中,把写作看作男性的特权。苏阿德·萨巴赫在她的诗中对这种现象予以大胆的揭露:
他们说:
言论是男人的特权,
你不要说!
调情是男人的艺术,
你不能卿卿我我!
写作是深不可测的大海,
你不要自我淹没!(注:《女人的悄悄话》集(Fataafitu'Imra'ah),London,The Paul Press Ltd.,1987,p19.)
(《女性的否决》)
“他们说”构成了男性建构主体文化的语境。他们在这一语境中把妇女的声音拒于千里之外。他们同样在这一语境下,“说诗人是男性的同义语,/怎么会有一个女诗人诞生在部落?”并搬出神权的上方宝剑悬在妇女的头顶上,告诫她们:如果女性从事写作,会使真主生气,也会使先知对她们感到厌恶。对那些执意不从、立志写作的妇女,他们甚至发出了欺骗性的威胁:
写作是一大罪恶,
你不要写作!
拜倒在文字前也是罪过,
你别那样做!
诗的墨水有毒,
你千万别喝!(注:Ibid.,p17.)
(《女性的否决》)
男性作家及其所延伸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妇女写作的限制在文化领域彻底地排挤了妇女,延续了男性权力话语对女性的压迫,法国女性主义评论家在分析这种现象时指出:“迄今为止,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广泛而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我认为这就是对妇女的压制延续不绝之所在。这压制再三重复,多多少少是有意识的,而且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因为它往往是藏而不露的或者被虚构的神秘魅力所粉饰。我认为在这里粗暴地夸大了一切性别对立(而不是差别)的标志。在这里妇女永远没有她的讲话机会。”(注:[法]埃莱娜·西苏:(Héléne Cixous):《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Medusa), 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阿拉伯女性也面临同样的状况。她们在文学领域没有多少讲话的机会,直到如今,她们试图打破男性权力话语的禁锢时,总是一再受到封杀。苏阿德·萨巴赫对此是深有感受的。她的声音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的时候,受到许多女性读者的欢迎,也得到一些具有民主意识的男性评论家和读者善意的接受,但与此同时,对她的写作进行非难的声音也以巨大的压力围住了这一颗刚刚升起的“明星”。在她刚走上创作道路的初始阶段,她得到的反馈更多的是讥笑、嘲讽、谩骂和攻击。“他们说:/女性就是软弱,/最好的妇女总是知足满意。/自由是万恶之首,/最美的妇女是驯顺的奴婢。/他们说:/女人舞文弄墨是标新立异,/原野没有这种草的立足之地。/女人若是写诗,/岂不成了歌伎。”(注:《女性的否决》,《女人的悄悄话》集,第23页。)当种种手段都不能迫使诗人放弃写作时,“他们”甚至给诗人罗织了一系列破坏社会道德与社会秩序的罪名,“说我砸碎了自己墓穴的石板”,“说我杀死了自己时代的蝙蝠”,……其实这不只是对苏阿德·萨巴赫一个人的指控,而是对所有独立特行的知识女性发出的威胁信号。
男性权力话语对开始冲破束缚大胆言说的阿拉伯知识女性进行的围剿,反而使苏阿德·萨巴赫和许多阿拉伯女性作家认识到妇女写作和建构女性话语的重要性,认识到争夺文学这一阵地的必要性。法国著名的女文学家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西蒙·德·伏波娃曾说:“文学这个领域是那些反女性主义者们似乎掌握着诸多王牌的领域”。(注:《妇女与创造力》,见张京缓:《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51页。 )在阿拉伯世界同样如此,争夺文学这个领域实质上就是为了获得话语的权力。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话语权赋予了男性在文化领域的话语理论创造权、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和语言意义解释权。“在这个庞大的封建伦理体系中,女性要么在‘孝女节妇’和‘女妖祸水’之间进行选择和角色认同;要么自造一座精神炼狱,因沉默而蒙昧,因蒙昧而‘失语’,最后彻底丧失主体地位——‘人’,而成为异化之‘物’;要么进入男性话语领域,失却女性独特的体验和言说方式,运用男性的口吻、词汇、意向、立场和符号去言说,以丧失女性特性而成为木口木面的‘准男性’进入理论话语,分享一点窃来的话语权;要么,以中心话语的‘补充’形式运载女性独特的情思,并以男性可以接受的方式‘言说’,在本文的空白、缝隙及错位处,透露几丝女性体验的信息(中外女诗人、女作家大抵如此)。这样,女性的话语权的拥有以女性本质的失落为代价,文化压抑的外在律令被转换成女性内在的自觉,对女性的剥夺变成赐予,对女性的排斥变为接纳。父亲社会终于使女性作为能指纳入社会谱系等级中,而女性的真正性别和精神内涵却被剔出在文化语境之外,并逐渐消隐在历史盲点之中。”(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385页。)而写作恰恰可以改变阿拉伯女性失语的历史。“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注:Héléne
Cixous:"From
the Scene of the Unconscious to the Scene of History",in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New Yorkand London:Routledge,1989,p.8.)阿拉伯知识女性可以通过妇女写作去锻造反理念的武器,去发行现行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使之成为反叛思想的跳板,以争取阿拉伯女性的“天赋人权”。
苏阿德·萨巴赫一直在执着地寻找阿拉伯女性自由解放的道路,寻求对策。在寻找的过程中,她逐渐认识到女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首先必须建立与男性话语平行的女性话语,必须找回女性那曾一度迷失的主体。但是如何重新获得女性的主体性呢?萨特说:“没有什么真理能比得上我思故我在了,因为它是意识本身找到的绝对真理。”(注: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对于女性诗人来说,“诗之思”是可以构建女性话语,揭示女性意识,找回女性迷失的本真,促成女性主体性的回归,从而获得女性的存在的关键。对于诗人萨巴赫来说,写作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她把写作当成改变阿拉伯人,改革阿拉伯社会的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如前所述,她认为写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阿拉伯人的身心和民族性,从而进一步改变阿拉伯社会的落后面貌。
二、妇女写作的策略
萨巴赫对女性话语和妇女写作策略的理解,与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也有重合的共同的地方。埃莱娜·西苏等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妇女必须写作,必须写自己、写妇女,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向一直由男性崇拜所统治的言论发起挑战,而后才能确立妇女自身的地位。妇女写作的行为将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接近其本原力量。写作的行为还将恢复女性的能力与资格,恢复她那锈迹斑斑的嗓子的言说,恢复她的欢愉,重现她那一直被封锁的内在情思。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苏姗·古芭(Susan Gubar )通过《空白之页》的故事叙述者自称讲过一千零一个故事分析了“女性话语”的功能: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叙述者山鲁佐德,正是以其非凡的叙述能力延续了自身的生命,推迟了死亡的降临,她的文学才能不仅使自己幸免于难,同时也拯救了这块土地上所有受到生命威胁的年轻姑娘们。(注:‘The Blank
Page’and the Issues of Female Creativity,in Elaine Showalter,ed.TheNew Feminist Criticis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相比之下,苏阿德·赛巴赫除了承认女性话语对于妇女的特殊意义以外,更加重视写作的普通职能。在这一点上,她和阿拉伯世界的女性作家和诗人们的观点更加接近。沙特女作家法姬娅认为只有通过写作才能“超越一切”,而埃及女作家奈娃勒·萨阿达薇则认为“写作能代替公正,而公正是美,是爱”。(注:程静芬:《阿拉伯女作家谈人生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1993年第8期。)
在《爱的诗篇》(其一)中,苏阿德·萨巴赫表白了她对于妇女写作的理解:
我要书写,
以保护我女性特质的每一寸土地,
是殖民者将它建起,
至今仍未走出去。
书写就是我的方式,
要摧毁我曾无法摧毁的
中世纪的城堡,
摧毁禁城的墙壁,
和检察院的断头台。
我要书写,
从他们绕着我的脑袋圈画的
千万个方圆中解放出来,
从毒化了所有河流
和所有思想的
安全隔离带走出去;
它隔离了千万本书,
和千万个知识分子。
我要写给你,
写给别人,
写给任何一个自由的男人。
我要对着信纸说出
不能对他者讲的东西。
十五个世纪以来的
他者
一直谋害女性特质。
我要给天空的肉体凿开一个洞。
我所居住的城市,
唱出的只有公鸡的啼叫,
潇潇的马鸣,
和斗牛的喘息。
我要书写,
要去掉我的面纱,
放下我母亲自束胸之日起
就顶在头上的奶酪袋和橄榄串。(注:阿拉伯妇女习惯把重物放在头顶上,而不是手提肩扛或背负。)
以便稍作休息……(注:《爱的诗篇》,第21—25页。)
在认识到写作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以后,苏阿德·萨巴赫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重大使命感的女诗人,虽然看到前行的路上荆棘丛生,困难重重,但她仍然选择了要“面对话语”,希望将自己“种植在话语中”(《将我种植在话语中》(注:《将我种植在话语中》,《本来就是女性》集(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men),London,Riad El— Rayyes Books Ltd.,1988,p45.))她在写作的尝试中所表现出的决心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从思想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角度看,她拥有一种男性作家与思想家可能不具备的刚毅与勇气。她越来越多地涉入到各种敏感的和困窘的社会问题、女性问题,甚至文明与进步的问题,毫不犹豫,毫不退缩”。(注:转引自[科威特]阿卜杜一穆哈辛·纳缓尔·居安:《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历程》(该文为1995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阿拉伯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作者为科威特驻华大使。)她不顾一切地投入诗歌创作,欲为女性代言。她不怕保守势力对她的种种攻击,不怕因此而成为一只“受伤的羚羊”,不怕他们把她“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果真如此,她觉得“那倒要感谢他们”,因为这样的待遇“同待基督一样”,起码说明社会已经不得不面对女性,注意到女性问题的重要性。(注:《女性的否决》,《女人的悄悄话》集,第22页。)而这正是她的写作所要达到的初步目的。而后,她才可以向更深远的目标迈进:唤醒女性也唤醒男性,以女性的解放促成人类整体的解放。
阿拉伯的男性评论家们也渐渐地为苏阿德·萨巴赫的顽强毅力所感动,对她的创作勇气感到佩服,终于认同苏阿德·萨巴赫自己的说法,认为她的诗歌创作是在狂暴的飓风、猛烈的暴雨中向着激流游去。我们从她的诗中涉及到许多敏感的问题也的确可以看到诗人面对“飓风”、“暴雨”和“激流”时所充满的信心和勇气。
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创作历程,实际上也是争取为女性讲话而打破关于妇女写作之种种禁忌的过程。她“喝了很多墨水”,但她发现自己并没有中毒。她写了很多诗歌,“在每颗星球上都点燃大火”,却并没觉得获罪于真主和先知。她没有像男性权力话语宣示的那样,因涉入创作而受到来自于人类主宰的惩罚,没有因此而损伤一根毫毛,她还是原来的她。她在所谓“深不可测”的会淹死人的写作之大海中“已经畅游过很多”,“与一切大海拼搏而未被淹没”,反而锻炼成一位“游泳的能手”。她“舞文弄墨”,“标新立异”,却并不像男人们当初所预言的那样将无“立足之地”。(注:《女性的否决》,《女人的悄悄话》集,第24页。)恰恰相反,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扬名科威特文坛,并逐渐扩大影响,在当代海湾文坛、在整个阿拉伯文坛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妇女写作究竟要写什么的问题上,苏阿德·萨巴赫也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强调妇女写作应集中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写妇女的性特征及其无穷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写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写妇女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她们的旅行、跨越和跋涉,写妇女的觉醒,突然和逐渐的觉醒,写妇女在某个曾经视为畏途然而将会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她们的身体有关。所以,妇女写作的重点应放在她们的身体上。在埃莱娜·西苏看来,“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注:《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苏阿德·萨巴赫亦曾在她的作品中写妇女的身体:
在你的双手中,
我第一次发现
我身体的地质图:
一座又一座的山冈,
一个又一个的源泉
一朵又一朵的白云
一处又一处的丘陵
我是你的一座城市,
附带我所有的
扁桃、
苹果、
和李子。
我是你的一座城市
附带我所有的
区域里这许多东西,
和我水果的甜蜜。
我是你的一座城市,
附带着
长在我眼睑上的每一颗麦粒
和每一颗神话般的珍珠,
在我的海湾闪光熠熠。
……(注:《爱的诗篇》(其二),《爱的诗篇》,第32—34页。)
但是,这类作品在苏阿德·萨巴赫的作品整体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其他的阿拉伯女性作家也有写女性身体和她们的性爱,如莱拉·芭阿莱贝姬的长篇小说《我活着》、奈娃勒·赛阿达薇小说《不求赦免的女人》,和库雷特·扈莉的小说《日月穿梭》等,但她们都不喜欢过份地渲染女性的隐私,表现出了她们与西方女性主义者巨大的分野。即便是写妇女身体及其性爱,阿拉伯女性作家们也不像一些西方女作家那样重视感官的和物欲的刺激,而是体现出了东方女性优雅含蓄的美学特征,反映出东方女性独特的品味与品格。
总体上看,苏阿德·萨巴赫和大多数的阿拉伯女性诗人和女性作家一样,侧重于对纯真爱情和平等婚姻的追求,从存在的角度描写女性的命运,以私人性生活凸现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愿望。这也就决定了阿拉伯女性话语建构的独特性,再一次显示了阿拉伯女性的温和、柔婉的东方特性,与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表现出的那种强调女性差异的性咄咄逼人的写作策略有着明显的不同。尤其是法国的女性主义者主张以一种基于女性躯体的女性语言进行文体上的试验式的写作。这种被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Derrida )称为“女性话语”的特殊的言语方式着重表达女性躯体和妇女生理的独特性尤其是女子性欲。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朴维做出了具体的解释:“这种语言赞美多元化和语义上的不确定性、由矛盾引起的语义滑移,以及问题式的变化无常,因为这些现象‘类似’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女性生殖器”。(注:Mary Poovey:"Feminism and Deconstruction",in Feminist Studies,Vol.14,No.1,Spring 1988.)法国的女性主义者依利格瑞也对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进行阐释:“妇女永远与自身相异。毫无疑问,这就是她为什么被形容为变幻无常的、不可理解的、烦扰人的、任性的——更不要提‘她’那伸向四面八方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他’无法找到任何意义的连贯逻辑……在她的陈述中——起码当她敢于发言时——女人时常重新接触自身。她仅仅从自身分离出一些闲言碎语、一个感叹号、半个秘密、半吞半吐的一句话——当她返回自身时,只能从另一个快乐或痛苦的角度再次出发。人们必须不同地倾听她的谈话,以便觉察出‘另一个意思’,这个意思经常处于编织着自己的过程中,不停地接纳言词,却又抛弃言词以免变得固定不动,因为‘她’说话时,她的话已经不再与她想要表达的意思相同。她的陈述不再与任何事物相同,其显著特征是相邻状态……当她的陈述从相邻状态游荡得太远时,她停顿和重新从零开始:从她的躯体/性别器官开始。”(注:Luce Irigaray:"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转引自张京缓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37—338页。 )在这样的写作策略指导下的女性话语必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对社会历史惯常的框架造成极大的震荡,对男性权力话语的“真理”和法律都将造成剧烈的冲击。
苏阿德·萨巴赫和一些阿拉伯女性作家虽然也期望打破男性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但她们作为东方女性,更倾向于温和地对待男性。她们不希望把自己作为“第二性”与另一性别隔离开来,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期望得到男性的理解,让男性接受以往被遮蔽的女性内在意识及其价值体系。她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压迫女人、反对女人的事业。一位阿拉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著名的女作家指出,“在这个无序的时代,挖苦女人的居多,支持女人的也不少。他们是那些心胸宽广有头脑的人,是我们时代最高尚的男人。他们尊重女人的努力,承认她的权利,肯定她的引人注目的改变,钦佩她的勇气和坚定,从她的奋起看到了减轻灾难有益人类的新的有效力量。”(注:〔黎巴嫩〕梅·齐雅黛:《女人与文明》(1914年6月在开罗东方俱乐部的讲话), 引自李琛选编:《四分之一个丈夫》,第7—8页。)我们看到,苏阿德·萨巴赫和绝大多数阿拉伯女性作家所构建的女性话语与欧美世界的女性话语是有区别的。阿拉伯女性作家敞开自我,坦露女性个体经验和个人历史记忆的女性话语,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又和主流话语有重合的和相通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女性话语的鲜明特征。就苏阿德·萨巴赫而言,她常常选择富有象征意义的语汇营造形象,激起读者的想象能力,从中得到美的感受。那些人们十分熟悉的、简洁朴素、平平常常的词语在她的笔下汇成动听的旋律。“苏阿德·萨巴赫所有诗歌成就的基本目标,是重新拆解阿拉伯世界,在把它拆解之后,通过在象征这个世界的碎片和成份的语汇和想象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来重建阿拉伯世界。而这些碎片和成份通过互相之间的崭新关系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注:〔埃及〕奈比勒·拉希布:《弹奏紧绷的琴弦——苏阿德·萨巴赫诗歌研究》,埃及图书总局,1993年版,第359页。 )也就是说,苏阿德·萨巴赫十分巧妙地使古老的语言通过重新的组合变成清新的语言。这样的女性话语自然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