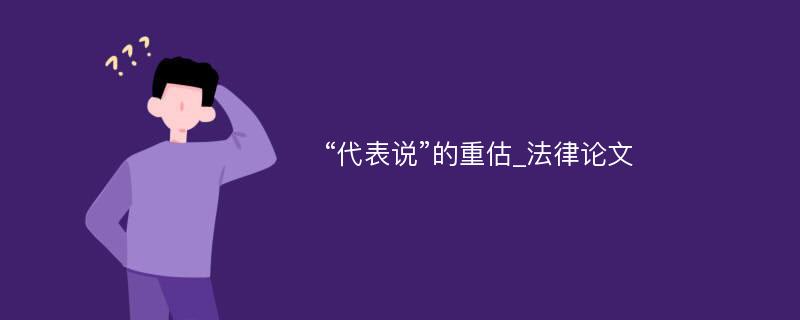
重估“代表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定代表人与法人的关系是法人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此理论上有“代表说”与“代理说”之分(注:“代表说”认为,法人是一个组织体,其本身享有的民事权利以及承担的民事义务,需要通过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的对外行为来实现。法定代表人从事法人业务经营活动的行为,是法人的行为。因此,在法人与法定代表人之间,不是代理关系,而是法人与其负责人的关系。法定代表人对外以法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无须委托,他的行为就是法人本身的行为,其行为后果由法人承担。“代理说”则以代理关系界定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主张在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对外行为时,法定代表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代理关系,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法人的权利是基于法人的委托授权而产生。)。在我国,“代表说”不仅为学界倡导,也为立法确认,属通说。尽管“代表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都有其优越性。但与“代理说”相较,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因此,我们无法继续心安理得地把“代表说”作为建构法定代表人与法人关系不可质疑的金科玉律。本文拟对“代表说”产生的背景及其运作实际作以分析,进而提出在民事立法中以“代理说”取代“代表说”。
一、转换了的背景:问题的提出
在肇始于中国八十年代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中,“代表说”之所以能成为法定代表人与法人关系之通说,我国悠久的集体主义传统及因此形成的传统思维定式不能不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集体主义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社会以伦理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核心,宋明理学的“克己复礼”、“正心诚意”曾经是长久的社会统治意识和官方正统哲学,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文化心理,个人之于集体的独立利益和地位一向不被确认。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旧的黑暗社会和生活形态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唤起了也培育着人们对革命、对革命道德、对集体主义、对自我牺牲精神的忠诚的热情和极度的信任。于是,个人利益以至个人本身当然包括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不仅都是渺不足道的;并且作为异己的有害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清算。真正重要的是集体的、国家的、革命的事业和利益,“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也就是“先公后私”“一心为公”和“舍己从公”。(注: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3页。)当时不仅个人的价值只能体现在其对集体的作用上,而且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唯一源泉。集体也确实包办了个人的一切,从工作、迁徙到婚姻、恋爱,完全吞噬了个人的独立生活。在泛道德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否认或忽视人的利己动机,而代之以对人性的利他和集体主义假设,个人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得到凸现和放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经济行为动机则或被抑制或被视而不见。
囿于这种思维定式,立法上,个人通常被认为是其所属集体的组成部分,是集体的依附性存在,主体地位仅在很小的范围内得到确认,根本不可能与集体作为平等的主体。在此背景下,法定代表人也只能是法人的组成部分,丝毫没有独立性可言,它的其他人格未得到承认。在以忠诚为核心的道德信念的长期熏陶下,法定代表人也很难产生利用其在集体中的地位谋取私利的动机,“代表说”是必然的选择和当然的结论。由于当时集体生活对个人生活的全面吞噬,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状态,个人独立生活的消解,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客观上呈现高度一致性,“代表说”很和时宜,其诸多缺陷无从暴露。
加之,当时实行“先生产,后生活,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政策,个人的收入来源和数量均十分有限,个人所得除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几乎没有剩余可言,也即不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实际能力。因此,即使采用“代理说”,并据此要求法定代表人对其行为给法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也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难有补偿法人损失之实,因此当时“代表说”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随着中国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集体主义虽然仍被提倡,但不再以排斥甚至抹杀个人的独立性为前提。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就是承认个人逐利动机,赋予个体的独立利益以合法性,并以此为前提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引导、鼓励个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必然要求个体利益得到与集体利益同样的尊重,并同时带来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并列乃至矛盾逐渐显化,并成为市场经济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维度,对集体和个体生活均产生重大影响。与此相应,上述传统的与统制经济相适应的以忠诚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受到根本冲击,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信任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尚未发育起来,形成道德的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不发达的经济极可能迫使也可能诱惑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贪婪,加之特权与法权并存,道德的、制度的约束又出现漏洞,这种贪婪就极易变为现实。(注:参见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吞噬国家和集体利益往往成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便利途径,这是当代中国一个无法回避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而且,截止2000年1月,我国居民储蓄逾6万亿元,(注:见《经济参考报》2000年2月22日,第1版。)超过1995年底的国有资产总量(57106亿元),(注:谢次昌:《国有资产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是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5倍。这表明民间已经积聚了相当的财力,通过追究法定代表人的民事责任,补偿因其过错行为给法人造成的损失,已不单单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且实质的内容和功效。
因此,当代中国较“代表说”确立之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成了时代主题的转换。“代表说”得以产生和存续的背景不复存在,于是提出了审视“代表说”能否回应新的时代要求,对其进行重新认识评价的问题。
二、说短论长:聚焦“僭主现象”
按照“代表说”,对于法人,法定代表人无独立人格,而是构成法人实体的机关,是法人的组成部分,法定代表人从事业务经营活动的行为,是法人自身的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均由法人承担。据此,“代表说”在逻辑上,排除了在法人与法定代表人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可能性。该说的利弊得失均渊源于此。
“代表说”将法定代表人在职务范围内的行为笼而统之地作为法人行为,使得法人和与法人交易的第三人在具体交易中不需要顾忌法定代表人与法人的关系,审查法定代表人行为的不同效力,这符合市场经济对交易迅捷与安全的要求。一方面,能够确保法人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对市场信号作出迅捷反应,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法人的活力和应变能力,进而有利于增强法人在经济交往中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第三人与法定代表人交易的风险,当然地由财力较为雄厚的法人承担,有利于保障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取信于社会公众,保护没有任何过错的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较快地建立起以形式合理性为支柱的社会信用体系。因此,“代表说”顺应了效率居先这一现代法精神的价值指向。这是我国民事立法采用“代表说”的主要考虑和基本理由。(注: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在法人制度的实际运作中,“代表说”的这些优势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坚持“代表说”的立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只要客观上在代表范围之内,即使代表人为了谋求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而滥用代表权,其代表行为本身也是有效的,(注:石慧荣:《法人代表制度研究》,《现代法学》1996年第4期。)对代表权没有任何有效的限制,且法定代表人无须因此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代表说”获得以上价值的同时,却顾此失彼,带来了法人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不利益,突出地表现在法定代表人愈演愈烈的“僭主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和法人因此蒙受的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僭主现象”是自然界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某些寄生虫(僭越者)侵入动物(宿主)体内后,把持宿主的大脑,迫使宿主产生有利于僭越者的自损行为。如蟋蟀被马尾虫感染后会奋不顾身地跳入水塘,扑腾一番精疲力竭地死去——水塘成了蟋蟀葬身之处,却正是马尾虫的向往之所。(注:参见应韶荃:《自然界的身体僭越者》,《南方周末》2000年3月3日,第9版。)作为系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蟋蟀的悲剧也发生在一些法人身上。这里借用“僭主现象”表征法人在窃居其决策机关的法定代表人的操纵下,反常地作出与自己利益相悖的行为,而法定代表人却因此从中获取私利。在“代表说”指导下的实践中,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上演了一幕幕“僭主现象”,社会系统中的法人同自然界的蟋蟀一样身受僭越者的危害,却无以为济。
“代表说”的成立,需要一个基本的外在支撑,即法定代表人与法人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法定代表人能够竭尽忠诚为法人服务,以维护法人利益为其唯一的行为动机,这可能是二者关系的常态。但问题是一旦这种支撑不存在,即法定代表人与法人利益出现某种程度的背离,法定代表人的自利行为动机,就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使其象侵入蟋蟀体内的马尾虫一样,利用自己居于法人决策机关,形成法人意思的有利地位,为实现自己的私利,而置法人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损公肥私,掠夺法人的财产和商业机会。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是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的经济,加之现代企业与家族企业法定代表人多由本家族成员担任不同,多实行所有与经营相分离的管理体制,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多采用聘任制,由不是企业所有者的职业经理担任,客观上使法定代表人与法人在利益上存在二元化的倾向,二者的利益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彼此独立,如果一旦条件适宜,按照理性人假定,“僭主现象”作为市场经济和法人所有与经营分离管理体制的伴生物,其发生似乎不可避免。湘潭电缆厂总经理、党委书记陈海燕涉嫌贪污、挪用公款一案,就是明证。陈海燕利用担任湘潭电缆厂总经理、党委书记的机会,肆无忌惮地操纵电缆厂及其所属子公司与其个人所有的十几家湘潭大阳系列私营公司进行不公平交易,采用前者对后者放帐、让利、高价购进低价卖出等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其担任湘潭电缆厂总经理、党委书记1000天,该厂亏损三亿多元,日亏损额达三十六万元。(注:参见刘利君:《国企是被这样蛀空的》,《南方周末》1999年10月9日,第5版。此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也曾报道,影响很大。)该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绝非偶然,不仅证实了上面的理论分析,也表明法定代表人的“僭主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既然“僭主现象”难以避免,问题的关键则转换为如何消解其给法人带来的消极后果,降低其危害,并借此遏制这一现象的发生。“代表说”恰恰在这方面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
基于“代表说”,法定代表人在与法人的关系中,没有独立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其行为即为法人自身的行为。即使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给法人造成损失,由于其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不被确认,其与法人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因而也就没有民事义务可言,更遑论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为保证民法不致因自身的逻辑混乱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采用“代表说”,同时就必然封死建构法人与法定代表人民事法律关系的路径,无法对法定代表人之代表权施加范围上的限制,也无法建立法定代表人对法人的民事义务体系,因而就不能就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给法人造成的损失,追究其民事责任,使法人的损失得以填补。这样一来,民法只能望“僭主现象”兴叹,对僭越者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这正是我国民事立法面临的尴尬局面。从对陈海燕案的具体处理也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由于故守“代表说”的逻辑,对于这种情况,只能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在事后追究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责任,使类似马尾虫的陈海燕们受到制裁。但是刑事责任解决的仅仅是对罪犯的依法制裁,而无法解决受害法人损失的填补问题。对此,江平先生有过中肯的分析:我国《民法通则》这一规定(指《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笔者注。)已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实际上确有一些公司的经理、工作人员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经营活动而公司无法追究其财产责任。(注: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代表说”虽有效率和安全的功效,但过于僵化的构造不能容纳对法人与其法定代表人间复杂关系的周全安排,直接的表现就是在法定代表人过失甚至故意给法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场合,导致无法通过追究法定代表人的民事责任,使受害法人的损失得到补偿。
为消解“代表说”的这种负面效应,种种权宜之计被理论界采用了。迄今为止笔者见到的最有力辩护是:法律为维护法人整体性的价值,在外部,将机关的独立性消除,名义上只有法人,法人与机关的关系不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是一体的关系。——但是,在法人的整体性的内部,关系是复杂的,在成员与法人之间或成员与法人机关之间,如果没有内部的约束,对于社员来说,是不符合正常的心态的,个人成员设立法人并任命法人机关,均与特定目的的保持和实现有关,说的更具体一些,成员具有近似维护目的的委托这样的意欲表示。传统民法在这里很实际地引入了解决方法,民法上均规定法人机关与法人在内部关系上应准用委托关系,即对法人机关准用受托人规则,使其在内部分担法人责任。(注:江平、龙卫球:《法人本质及其基本构造研究——为拟制说辩护》,《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依笔者看来,这种解释无法令人信服。首先,将同一的法人与其机关的关系划分为性质上截然有别的两种关系,有违逻辑一致性。按照民法的什么原则,将法人与其机关的关系划分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原本不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却转眼之间变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其间的机理何在,这些问题实在叫人弗解。如果不能清晰地指出这种转换的逻辑路径,那么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理论,必然在上述追问下崩溃瓦解。其次,根据笔者后面的分析,由于委任是代理最为常见的基础法律关系,(注: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传统民法引入委任制度规范法人与法人机关的关系,其合理的逻辑延伸应该是采用“代理说”以代理权授予解释法人机关的行为后果何以由法人承担。最后,上述理论试图用“准用”的技术解决“代表说”面临的困难似巧实拙。“准用”确实是一项精巧的技术,但是使用它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因此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如果采用其他直接简洁的途径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实在看不出费尽心机、迂回曲折、弃简就繁维护“代表说”的必要。孤立地看,这种辩护并没有实质的危害,但从民法体系的整体看,如果让这种不顾逻辑一致性、对特定制度随心所欲调适的作法大行其道,必然的后果是无法建立体系化的民法典和民法学,法学的作用也只能局限于设定一些孤立的、不成体系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民事规则。因此,这种理论的通行证就是民法体系的零乱甚至崩溃。
还有学者提出了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职权范围的方案,借以强化对法定代表人的制约,遏制“僭主现象”。但是按照“代表说”的内在逻辑,限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无异于限制法人的能力,束缚法人的手脚。而且由于市场交易的广泛性、多变性以及法人的个体差异性,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范围法定化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实际运作中都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通过追究法定代表人的民事责任补偿受害法人损失方面,“代表说”已陷入“山穷水复”的窘境,我们是否可以把“柳暗花明”的希望寄托于“代理说”,答案是肯定的。
较之“代表说”,“代理说”由于受到民法中委任和代理法律资源的有力支撑,在运作上极具弹性,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为大陆法系国家立法所确认。(注:我们见到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或商法典,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通常有“董事就法人事务,对外代表法人”的规定,不少学者将此解读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采用“代表说”的明证。据笔者考证,上述法典之所以如此表述意在表明董事之代理权为法人概括授予,以区别于一般代理权。参见陶百川、王泽鉴、刘宗荣、葛克昌编撰《最新综合六法全书》,三民书局1995年印行,180页。)如《德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董事会在诉讼上和诉讼外代表社团,其具有法定代理人的地位。”
“代理说”以代理制度构造法人与法定代表人间的关系,暗含着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法定代表人与法人是各自独立的主体,二者的利益和意志存在差异,从而为建构法人与法定代表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预留了空间,回应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趋势。事实上,正是因为采用了“代理说”,承认法定代表人之于法人的独立性,大陆法系国家才有可能把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视为委任关系,英美法系国家也具有了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视为代理关系或者信托关系的余地,并据此建构董事对公司的义务,发展出以“善良管理义务”和“忠实义务”为核心的董事义务体系。(注:参见石少侠主编:《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基于此,无论法定代表人对内处理法人事务,还是对外代表法人为法律行为,因其故意或过失给法人造成损失,法人均可请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人的损失,还可以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有力的约束,缓和“僭主现象”的危害,乃至消除这种现象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代理说”实有一箭双雕之功效,不可小视。
在法人的对外关系上,“代理说”将法定代表人与法人分别置于代理人与本人的地位,二者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按照代理的基本法理,作为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的后果并不必然地由作为本人的法人来承担,只有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未超越权限时,或者虽超越权限但事后经法人予以追认,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才由法人来承担。反之,其行为后果则由法定代表人自身来承担。
由此观之,“代理说”确与现代商事交易的效率、安全要求有相悖之处。按照“代理说”,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是否能对法人产生约束力,其法律后果是否由法人承担,取决于法人的授权范围,第三人若要保证交易的安定性,必须首先审查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这势必影响交易的效率。若不审查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则有交易因法定代表人无权代理而无效之虞,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进而害及交易安全。与“代表说”相较,“代理说”失之复杂、繁琐,但这一缺陷,已为民事立法有效弥补。首先,基于委任的法理,委任人可以概括地委托受任人处理一切事务。如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任人处理一切事务。这就为法人概括地授予法定代表人代理权奠定了基础,法人籍此可以通过一次性概括授权的途径,解决法定代表人权限过于零散,不利于交易效率的问题。这构成了法定代表人的代理权与其他代理人的代理权的根本区别,也正是基于此,学说和立法上通常将法定代表人的代理权称为代表权。其次,采用“代理说”的国家普遍强化了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董事代表权所加之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也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就妥贴地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免去了其奔波劳顿,审查法定代表人权限之苦。
此外,理论界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代表说”根源于法人实在说,而“代理说”只能在法人拟制说那里找到依托,进而认为因为法人实在说较法人拟制说具有理论优势,(注:石慧荣:《法人代表制度研究》,《现代法学》1996年第4期。)按照“血统论”的逻辑,“代表说”自然优于“代理说”。且不说这种推理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这种观点对两类不同问题的混淆。法人实在说与法人拟制说的理论指向是法人的本质,着眼于法人整体,解决的是法人何以具有人格和权利能力并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问题。况且更有学者指出整个法律世界都是构造而来,而不是对现实反映而成。无论现实世界中团体的性质如何,都无法回避法人概念的法律拟制性质,在法律层面,法人组织体和有机体说都显得过于简单。(注:江平、龙卫球:《法人本质及其基本构造研究——为拟制说辩护》,《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代表说”与“代理说”的理论指向则是法人的对外行为,着眼于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解决的是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效果归属问题,这是解决了法人本质之后,才予考虑的问题,二者处于不同层面、不存在彼此对应的关系。承认法人拟制说,并不一定要在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上排斥“代表说”、采用“代理说”。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人实在说的故乡——德国根本未采纳“代表说”,这使我们更有信心地坚持上面的结论。
三、“代理说”的就位:可以商榷的结论
“代表说”与“代理说”在处理法定代表人与法人的关系上,都有把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归于法人的功能,使法人制度得以在现代社会存续发展。但“代表说”采用的是一种绝对主义的逻辑,对法定代表人的独立利益和意志视而不见,虽保障了交易的安全和效率,但排除了通过在法人与法定代表人间建立民事法律关系完善法人制度的可能性,其因此造成的缺陷无法弥补。比较而言,“代理说”与法定代表人和法人间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相安共存,合理地平衡了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与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虽然对交易迅捷安全有一定影响,但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机制予以弥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致使自卫能力较弱的法人利益有过大的牺牲。按照哈耶克关于检验法律的“内在批评”方法,为了改进法律系统,一种特定规则就只能根据它与整个法律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它与由此而来的行动秩序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来加以评判。
(注:参见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3页。)走出幼稚的民法学,也应该在民法体系的高度,研讨具体规则的设定,只有贯彻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为制定民法典储备必要的理论资源。在以上意义上,笔者认为在未来的民事立法中应摒弃“代表说”,按照“代理说”构造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
标签:法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代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机关法人论文; 代理问题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民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