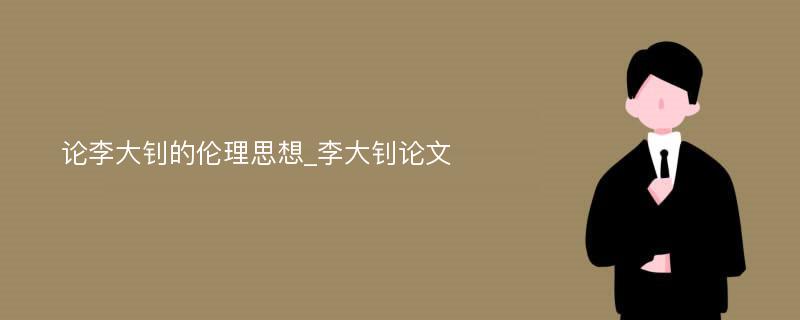
李大钊伦理思想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李大钊文集》第5卷,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不幸的早年生活,使李大钊养成了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和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他五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十一岁时,义和团运动爆发,冀东各地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很快,八国联军侵略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区。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青年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上)。在法政学校,李大钊阅读了大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和西欧资产阶级的著作。毕业后,李大钊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那里,李大钊开始较系统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李大钊影响很大,成为他反旧倡新的有力思想武器。他认为宇宙是不断进化的,新的总要战胜旧的。他强调随着社会的前进、时代的变化,一切伦理道德、规范法度,都要随之变化,即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的内容也要遵守新的代替旧的、青春战胜白首的历史准则。所以,他以极大的热情号召广大的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李大钊文集》第1卷,194页)
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利用天演一说,确实振奋了当时的进步思想界,对于鼓舞国人奋发图存、自重自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五四以前的社会现实证明,从西方舶来的进化论的思想武器未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尤其当李大钊发现“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庸俗进化论甚至成了为帝国主义侵略遮幕的工具时,对进化论思想愈加怀疑。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强烈的爱国热忱促使他开始了更加自觉的新的探索。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正在积极探索中的李大钊看到了希望。他于1918年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确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潮流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号召人们“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指出“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标志着李大钊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分析国家命运的工具,初步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二、唯物史观成为摧毁旧道德建立新道德的有力武器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开始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对道德问题的分析上,对道德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学理问题作了科学的说明,并且阐明了新道德之建立、旧道德之覆灭的必然趋势。
(一)“道德”的经济史观界说
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2)历史的唯物主义;(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4)经济的决定论。李大钊对以上四种提法进行了比较,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妥当些。……只是‘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仍之不易”。本文在这里采用了“经济史观”的提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李大钊思想的原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李大钊在1919-1920年间先后发表的运用唯物史观论述道德问题的光辉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得以建立的奠基之作。
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李大钊开始用其所掌握的初步的唯物史观思想对“道德”的起源、本质、历史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分析。关于道德的起源,他明确指出:“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李大钊文集》第3卷,104页)关于道德的本质,他认为“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同上书,111页)。此种观点,对现在的人来说,虽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当时来讲,不啻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关于道德的历史变迁,李大钊比较准确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旨,即“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的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同上书,104页)这样,将道德及其变更与物质、经济等的变化联系起来的科学的唯物史观的伦理思想,为李大钊所接受。
与此同时,李大钊还通过对社会上风俗习惯演变的考察和研究,总结道:“故就物质论,只有开新,断无复旧;就道德与物质的关系论,只有适应,断无背驰。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同上书,111页)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王法”、“纲常”和“名教”的“万事不变”论,明确地肯定了道德是最终受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一种上层建筑,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动而不断变更的,从而以深刻的理论性给予现实中定孔教为国教的复古势力以当头一棒。
(二)批判旧道德
正是依据上述基本观点,李大钊指出孔学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两千余年,“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而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同上书,142页)“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同上书,141页)所以,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动摇、大家族制度的崩溃,孔学及以此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也必将面临崩颓粉碎的命运,这是历史规律使然。
李大钊以此为思想武器,批驳了康有为的道德“无新旧之殊”,不必“以新易旧”的观点。既然道德是因时因地而变动的,所以,发生“新旧的问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而在当时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已在发生改变,即“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由此得出了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也“绝不是‘万世师表’的结论。
李大钊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同上书,115页)。他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进一步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动,孔子学说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就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不管几个尊孔的信徒如何天天去曲阜巡礼、去祭孔,“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这种变化是由新的经济势力引起的,是不可抗拒的,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这样,他就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上论证了旧道德消解,新道德再生的必然趋势。
曾有不少思想家对纲常名教等封建旧道德提出了质疑和激烈批判,五四时期,孔孟之道更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众矢之的,不过,像李大钊这样从经济的角度来揭示其存在的根源,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李大钊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也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呼唤新道德
李大钊并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上,他在运用唯物史观对旧道德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还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伦理观进行了合理的建构,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观以及新“大同”社会道德理想的阐述上。
1.“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观
李大钊分析了近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指出随着封建经济的崩溃和地主阶级的没落,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伦理观已成为过时的旧道德了。他对我国旧道德贱视劳工的等级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他说,孔门学派总是把劳动者阶级放在被统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两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所谓纲常名教,所谓道德礼义,都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同上书,142页)。
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去其价值,变成了旧道德了。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它的新道德,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是断断不能遏抑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成长,李大钊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崭新的伦理道德,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新道德。这种新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同上书,116页),而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是“大同的道德”(同上)。他说:“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同上书,146页)李大钊论证了新伦理产生和发展的不可抗拒性,既具有科学的说服力,又充满着思想的战斗性。
2.新“大同”的道德理想
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曾经畅想过在中国实现“大同”社会:消灭财产的私有制、消灭剥削,使人们都能过上一种富足、幸福的生活。然而,美好愿望的真正实现不仅需要善意的理念,同时更离不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现实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使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李大钊作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在中国大地上播撒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火种,并冠之以中国化的称谓“大同”,从此,“大同”的理想不再是纸上谈兵。
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年2月1日发表于《新潮》第1卷第2号)一文中,比较完整地阐明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结合的新组织。在1923年1月的《平民主义》中,他又再次重申了四年前的社会构想,认为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李大钊文集》第4卷,253页)
唯物史观立场的确立对于李大钊以上构想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康有为等的大同理想强调“博爱”、“互助”不同,李大钊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并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达到阶级的消灭,大同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他认为,阶级斗争与“博爱”、“互助”,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可以统一的,他指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文集》第2卷,18页)“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改造经济组织”(《李大钊文集》第3卷,35页),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改造人类精神,必然没有结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改造经济组织,同样也不会成功。所以,他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是“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李大钊文集》第2卷,18页),只有如此,方能打碎剥削的制度,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实行“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的原则;同时,本来受到限制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将得到发扬,“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李大钊文集》第3卷,13页)。这样一个实现了物心两面改造、灵肉一致的社会,就是大同世界。
(四)妇女观的唯物主义阐释
妇女问题是中国近现代众多思想家都涉及过或重点提出过的,许多思想先锋也曾经为改变妇女的地位而振臂高呼过。但是,在当时似乎只有李大钊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此进行理论分析,为妇女解放找到了正确出路。
第一,对妇女地位的形成及变迁,他开始用经济的观点作深层分析。首先,李大钊认识到妇女受压迫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私有制下的阶级剥削是广大妇女受奴役的根源。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他鲜明地提出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动而变动”的观点。他首先从纵向上对妇女地位的变化从经济角度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他指出在母系氏族时期,妇女的地位不仅不比男子低,反而高于男子,因为当时男子主要进行狩猎,而猎物的多少很不稳定;而女子主要从事农业,农业耕种的收获相对稳定一些,所以女子的地位比男子要高。后来“牧畜与农业渐渐专归男子去做,妇女只做烧煮裁缝的事情,妇女的地位就渐渐低下”(同上书,110页),而“到了现代的工业时代,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家内手工渐渐不能支持,大规模的制成许多无产阶级,男子没有力量养恤妇女,只得从家庭里把他们解放出来,听他们自由活动,自己谋生。一方面因为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为妇女添出了许多与他们相宜的职业,妇女地位又渐渐地提高了”(同上)。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又从横向上对中、西妇女的地位进行了比较,从而对我国妇女长期以来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农业是本,农业耕种决定了团体聚居,从而造成了大家族的产生,此种社会经济结果易出现妇女过多的现象,妇女除了管“阃内的事”以外,无须承担什么风险;而在西方,工商业为主,常常迁徙不定,西方妇女地位,以个人为主,家族简单,所以西方妇女承担风险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经济地位。(参看上书,140~141页)
李大钊不仅透视到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并且由此作出了大胆的预言:随着西洋的文明打进来、西洋的工业经济渗入到东洋的农业经济中来,“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所以,过去的所谓节烈贞操等观念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崩溃。(参看上书,145页)
第二,李大钊在从经济上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的同时,还从经济上找到了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由于李大钊认识到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根本上是阶级压迫,所以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便成为妇女获得真正解放的惟一出路。李大钊认为,仅仅女人向男人争夺权力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男人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而有产阶级的女人也剥削其他人,所以,妇女运动的属性应该是阶级斗争,“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制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李大钊文集》第2卷,282页),即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应该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
李大钊对妇女问题的解决是一种根本的解决,他认为,参政、女子教育之类,“都是些治标的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造,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同上书,317页)。
李大钊将唯物史观运用在对道德问题的分析上,为我国伦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唯物史观取代了两千余年来在道德问题上的唯心史观,“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
标签:李大钊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道德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