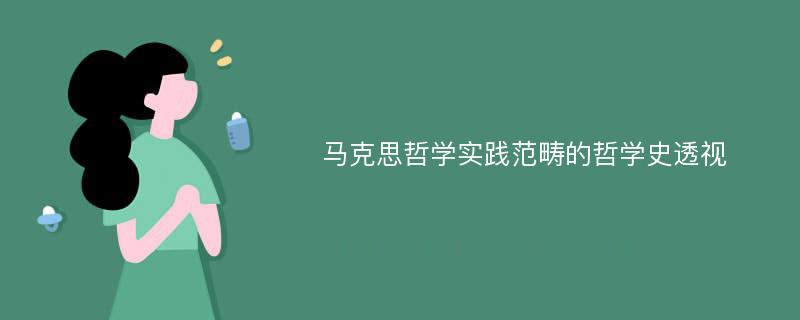
摘 要: 马克思全新的哲学世界观是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创立的。因此,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史中寻求理解马克思哲学实践范畴是不可缺少的理论视角。通过思想史的批判性考察,在实践这一概念和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终极存在的关系中,在它和知识、理论的关系中,在它和感性的制作生产活动的关系中,在它和价值、伦理秩序的关系中,在它和形式逻辑、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关系中,我们能够体会实践概念错综复杂的内涵及其历史命运。
关键词: 哲学史; 马克思; 实践; 诠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所理解的三种实践类型可归结为两种: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和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因为科学实验终究是以技术的方式服务于生产实践,依附于生产实践。那么,这两种实践方式有没有内在的统一性,从而是否蕴藏着全新哲学意义的实践观念?如果因处理对象的不同(一个是自然,一个是社会)而认为两种实践为并列关系,这两种实践概念实则蕴藏以自然和社会的二重化为前提的传统形而上学。再者,如果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理解为生产实践就是“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那么“生产实践”这个概念同样囿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之中,甚至由此导致在现实中混淆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进一步,如果我们把实践置放于认识论的领域,把实践当作认识的来源、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那么,实践仍然不过是依附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工具性、手段性的概念。概言之,流行的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话语不过是传统形而上学话语体系内部的碎片而已。
降水井的深度的确定有很多种方法,如刘广仁[3]在西气东输二线盾构施工降水方案中所采用的方法,也可以根据降水井结构必须满足的技术要求来综合确定。本工程根据《管井技术规范》(GB 50296-2014),降水管井的深度按疏干井公式计算:
显然,这些问题提示我们,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展现其哲学变革的真实意义,必须以哲学史的逻辑发展为坐标,始终以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为基本参照系。
一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一系列哲学著作表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形而上学始终是他对话的目标,是激发他思想活力的理论源泉。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54可见,我们越是理解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本质,就越能够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到底继承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什么”,又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什么”;就越能够理解马克思哲学实践范畴全新的哲学意义,乃至可以合理地将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实践哲学” [注]“实践哲学”这一概念在使用中显得十分混乱。有人把它理解为“有关实践的哲学”,即西方传统有关伦理、政治意义的哲学。有人是从“关于实践的哲学”这一角度,把实践活动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来使用该概念。下文逐步表明,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实践哲学”,内含两层意义: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中隐匿地、自然地生发的价值和伦理秩序。。相反,如果无视传统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对问题解答的合理性及其缺陷,特别是其解答问题的思路,那么对实践范畴的理解,要么重陷他们的思想误区,要么给这一范畴无意识地塞进经验常识性的看法。
如果说巴门尼德以前的自然哲学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序曲,那么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萌芽,而随之而来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成为传统形而上学最早的体系化形态。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在后者上大体都得到了体现。之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和近代的主体性哲学不过是传统形而上学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而已。那么,传统形而上学具有哪些本质特征?第一,在存在论上,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以二重化世界的方式,追求世界的终极存在。二重化世界的具体表现形态尽管各不相同,但大致包括:经验世界/理念世界、此岸/彼岸、形式/质料、普遍性/特殊性、精神/物质等。第二,在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上,传统形而上学同样坚执一系列的二元分立:主体和客体、现象和本质、理性与感性、真理和意见等。第三,在理论建构方法上,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体现为一个完整的形式逻辑系统。从巴门尼德“能思维和能存在是同一的”开始,世界“是什么”的存在论问题就以命题和命题的逻辑系统的方式得以呈现。第四,传统形而上学追求世界的终极存在是为了寻求对世界的意义做出终极解释,从而为人的安身立命寻找支撑和庇护。传统形而上学的上述四个主要特征具有内在一致性:在二重化世界的基础上对世界终极存在断言的合理性,需要在认识论层面展开论证,而认识论本身的建立又是以二重化世界所确立的终极存在为前提、根据。换言之,终极存在确立的过程就是终极存在通过认识论,即命题逻辑展开的方式得到确证的过程,所以形式逻辑就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拐杖。当以形式逻辑的方式所追求的终极存在得到确立之时,人们便认为掌握了世界的内在秩序和意义,实现了生命的“善”。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哲学以实践范畴为理论平台和逻辑支撑点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那么,这种超越就必然同时是对传统形而上学以上四个方面的超越。也正是借助传统形而上学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反过来启示我们: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马克思哲学实践范畴,必然在相对应的这四个方面具有全新的存在论意义。第一,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实践范畴当然有着对“世界之为世界”的解释,但一定不同于以二重化世界来追寻终极存在的方式对世界所做出的解释。第二,认识并不是脱离实践活动的静观。内在于实践活动之中的“认识”不是对象化的、以命题判断方式所体现的静观性的认识,或者说实践活动中的认识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活动。如果非要说有认识、有精神,那么这样的意识、精神也只能是实践之中必然发生的觉悟——实践智慧(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第三,存在于实践活动中的认识和精神,作为“实践的人”对世界的觉悟,本身就是内含于世界的“道”,即逻各斯。因此,作为传统形而上学体系表征的形式逻辑系统也就转化为实践活动之中所内含的“实践逻各斯”。第四,实践范畴对“世界之为世界”的解释同时就是生命意义的实现和表达。即,“真”和“善”在现实实践活动中完全一体化、一致化。
二
柏拉图尽管已经意识到其理念论存在着矛盾(普遍与特殊),但他宁愿以强硬的形式逻辑的方式论证理念世界的真实性,也不愿意放弃可见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分有和模仿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柏拉图的理念论对具体可感事物的轻视,肯定具体事物存在的真实性。他认为,个别事物作为“第一实体”,其自身的实现有赖于“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的联合。即是说,当事物潜在的质料在某种生成因的作用下获得某种具体的形式时,事物就实现自身为有某种目的的个体事物。显然,形式不仅是质料运动变化的动力,也是事物的现实本质;事物取得了形式,也才算是实现了其目的性。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一方面,形式和质料的区分是相对的,内含形式与质料的具体事物又作为更高级事物的质料追求更高级的形式,直至独立于任何质料的纯形式——也就是世界成为世界的第一因;另一方面,形式的相对性、等级性也使可感事物的目的因构成一个无限的目的链,直至独立于任何具体目的的世界目的本身——也就是世界成为世界的最高目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真正解决柏拉图哲学的问题:当他认为普遍理念不能与个别事物相分离时,他肯定了经验生活的价值;当他认为形而上学是探讨“存在之存在”第一原理的科学,追寻世界的普遍性原理,说“可感觉的个别本体既不能有定义,也不会有证明”[2]174时,他的“最高因”“第一因”又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没有什么区别了。其实,第一因和最高因作为“思想的对象”,二者在绝对现实性中所达到的统一,就是绝对实体:从存在角度是世界的第一因;从价值角度是世界最高目的,即至善。
水轮发电机组的转速往往比其他旋转机械的转速较低,使得水轮发电机组振动故障属于渐变性或者耗损性故障,突发恶性事故较少,振动故障往往是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
知古明今。知“实践范畴”于哲学史之根深,才能领会其内蕴意涵之枝繁叶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相较之于传统形而上学所可能具有的全新哲学意义的判断,能得到哲学史的支持吗?马克思哲学实践范畴所具有的意义,是如何在传统形而上学不断克服自身的理论难题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得到彰显的?
综上所述,MCN-IC总体发病率较低,年龄≥60岁、腹痛、CA19-9≥37 U/ml、病灶边界不清、壁结节和无分隔预示MCN-IC的可能,宜尽快手术治疗。如无以上危险因素,则MCN-nIC的可能性更大,进行随访或非手术治疗是可行的。
上述哲学史的回顾,使我们能够体会到,在实践和传统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关系中,在它和知识、理论的关系中,在它和感性的制作生产活动的关系中,在它和价值、伦理秩序的关系中,在它和形式逻辑、先验逻辑以及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关系中,实践这一范畴具有错综复杂的内涵及其命运。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可以说是以往哲学隐秘的憧憬。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没有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当然,无论如何马克思的文本是最重要的依据),通过对思想史的批判性考察,依照思想史的逻辑我们就能初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何以在哲学史上实现了根本变革,具有革命性意义;这种新型的实践哲学具有什么本质内涵等等。同时,勘定了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思想史坐标,也有助于我们避免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误读。
康德作为近代启蒙思想的代表,对知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使其搬掉了以往形而上学的认识合法性根据(物自体不可知),给传统形而上学以致命的打击。但康德又说,形而上学作为主体心灵的倾向并不能真正消灭而只能改变其存在方式。其论证知识何以可能的先验演绎恰恰宣告了一种内在的形而上学(主体主义形而上学)的诞生:先验统觉自我不过是一种变形了的终极存在之一。进而认为,尽管不能从知识上论证世界终极存在的实在性,但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自我”“上帝”“灵魂”“世界”作为信念存在于人的自由得以体现的实践领域。于是,和亚里士多德基本一致的是,康德既严格划分理论和实践,又把实践理解为具有价值和伦理意义的活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是,一方面,康德认为实践具有不同于内在形而上学的道德形而上学性,且因为在实践领域“人为自身立法”,所以实践高于理论;另一方面,制作、生产性活动因其不纯粹性,全然不在他的视野之中。
亚里士多德划分理论和实践正确的地方在于:一方面,他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生活世界的遮蔽和轻视,把实践当作人实现自己为人的内在目的性活动,试图以实践的价值和伦理内涵恢复经验生活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他确认形而上学追求的终极存在及知识并不能保证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善——显然这是对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反动。他划分实践和制作活动正确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制作、生产性活动的技术性、工具性和获得产品的外在目的性,只能使人成为某种人而不能使人成为人。他的缺陷在于:一方面,他的形而上学内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矛盾最终导致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另一方面,他把制作、生产性活动完全从其伦理学意义的实践中清除了出去,不仅是他出于奴隶主贵族蔑视奴隶劳动的偏见,更是他形而上学知性思维的结果。
比特币地址=Base58{Hash160||前4字节(SHA256(SHA256(Hash160||地址版本号)))}
既然康德将知识限制在现象界,阻断了知识和此前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存在的任何关联,那么,他就掏空了知识此前在形而上学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伦理意义,使知识沦为向自然宣战的纯粹工具性、手段性的知识。显然,这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意义上的知识——尽管培根的知识是人进行经验逻辑归纳的结果。对于身处新旧时代转折的培根而言,“自然的发现”的时代氛围使他竭力批判此前形而上学的空疏和无用,而“人的发现”的时代强音使他坚信知识就是主体驾驭外物以实现现实福利的力量。所以,他拒绝和经验生活无关的形而上学知识,认为知识应该来自于经验生活的归纳并且在经验生活中发挥作用。可见,在培根的语境中,“实践主要是一种科学实验活动和生产性活动”[4]。由此,他把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制作、生产性活动当作实践,以实用的名义强力勾连亚里士多德所区分开的理论(知识)和制作、生产性活动(实践)的关系,既掏空了知识的价值和伦理意义,又掏空了实践(制作、生产性活动)的价值和伦理意义。进而,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知识)、实践和制作三种活动简化为理论和生产实践两种活动。事实上,这种沟通理论(知识)和经验活动的努力在康德那里同样存在。这一点,从形而上学之中蕴藏的形式逻辑因形而上学自身的矛盾而发展出先验逻辑、经验归纳逻辑就可得到理解:人们越来越发现,不能无视经验生活质料的存在。在纯粹理论理性批判,即知识批判中,康德的先验逻辑之区别于形式逻辑,是因为形式逻辑全然抛开了知识的任何经验生活内容。先验逻辑论证知识得以实现的过程,就是先天的直观形式、先天知性范畴与经验材料相结合的过程。所以,在康德看来,理论(知识)总是包含经验生活内容的知识,而不是形而上学内在形式逻辑演绎的抽象知识。但是,应该强调的是,一方面,康德知识论视野中的生活内容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和伦理意义,理论和他所理解的作为价值、伦理意义的实践之间依然是断裂的。另一方面,康德的先验逻辑是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形式逻辑基础上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就是以形式逻辑框架为基本结构的),其欲弥合形式/质料、先天/经验、感性/理性等二元对立的努力(先验演绎过程)是建立在知性的形式逻辑分离这一切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说,康德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以其内含的形式逻辑演绎的抽象知识来论证形而上学绝对实体之不可能成立,把形而上学实体作为信念置于他所理解的实践领域。但是,他的先验逻辑始终是以形式/质料、先天/经验、感性/理性等二元对立的形式逻辑思维为基础的。概言之,立足于形式逻辑的先验逻辑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形式逻辑的。
第一,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理论和实践的区分,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形而上学对世界的理论建构及其知识,并不能解决人作为有限生命的实践问题,最多不过是对世界作出的一种理论解释。事实上,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4。尽管康德试图在道德形而上学中确认实践的合法性,但他所谓的“道德奠基”是纯粹理性的自我立法。于是,原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现实人的幸福被排斥在外,道德不再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关。所以,康德的实践不过是理性形式主义的实践。尽管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当作实践活动,对传统形而上学做了最后的挽救,但他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最终窒息了自己的精神实践。
黑格尔当然不满意康德以形式逻辑为基础所造成的一系列二元断裂,也不欣赏其欲弥合断裂所做的努力。黑格尔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在于确认思想和经验的一致……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5]43“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自身。”[5]120在黑格尔看来,真实的事物作为思想不仅是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6]10。终极存在并不在彼岸永恒静止,而是在经验世界通过自己的历史性活动实现自己。“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为自身的中介时,它才是个现实的存在。”[6]11于是,黑格尔哲学中,精神/物质、主观 /客观、知识论/存在论、理论/实践、真理(终极存在)/价值包括伦理秩序(终极意义)都在世界精神的展开过程中得到了内在统一。这个动态的统一过程,一方面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永恒不动的终极存在以辩证发展的方式实现自身为绝对的过程,是辩证逻辑超越先验逻辑、形式逻辑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实现自己为绝对的实践过程。显然,黑格尔的实践概念依然处在理性主义精神的视野中,实现着传统形而上学的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只知道并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7]117
三
亚里士多德认可经验生活的价值,他就必然肯定幸福是我们生活本身的目的。他说:“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指幸福——引者)本身而追求它,而绝不是为其他别的什么。”[3]53在他看来,幸福是人的持续生活或行动,即“活得好”、“做得好”。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他认为,唯有以不变的第一原理、把握世界的终极存在、终极目的为目的的活动才能获得至善,实现最高的幸福。所以,这个活动,就是理性在纯粹沉思中的理性德性及其所实现的理论活动。然而,就像在形而上学中既肯定存在最高实体又肯定个体事物为实体一样,亚里士多德在其灵魂学说中既肯定人的灵魂中的理性能力,又肯定灵魂中非理性的感性欲求能力。所以,他认为幸福作为“活得好”“做得好”也存在于理性对感性欲求能力进行规训和引导的伦理德性之中,存在于以具体事物作为对象的生活经验之中,即存在于以生活行为本身的“妥当”为目的的实践之中——尽管在这一活动中人只能获得有限的、相对的善。于是,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是以人的活动之目的、对象之不同划分理论和实践的。并且,我们也能看到他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理论之高于实践,不仅是因为只有极少数天才能通过理论沉思窥探到至善,也是因为理论沉思既无须他人的参与也无须借助感性欲求能力及其具体事物,更是因为伦理德性在养成和实现活动中,始终以是什么欲求是最值得的以及如何实现欲求等理论的“知识”为前提。进一步,根据人的活动之目的的不同,亚里士多德还将实践活动同制作、生产性的活动区别开来:实践遵循生命自由的原则,以生活行为的善为目的,而制作活动必须遵循自然的原则,以人之外的产品为目的。
1.抓住网络民众的互动点,发展高效的网络电视平台。电视曾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媒体之一,但是由于网络的迅速崛起,削弱了电视原有的功能。而网络电视平台是将网络与电视直播相结合的新兴产物,它不同于传统的电视,能够做到电视节目实时回看,可以完全根据网民自身的喜好进行节目观赏,这是网络电视平台的一个大举措。网络电视平台的电视节目可以在直播的过程中接受网络民众的点评与讨论,影响着网络电视平台的转变。网络电视平台根据网络民众的点评,可以进行网络电视平台的优化与改革,真正做到“来源于民众,服务于民众”,与网民的积极互动是发展网络电视平台有效而灵活的手段之一,值得重视。
从经验生活看,传统形而上学对终极存在的追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表象看来,感性世界生灭变化,无数各具特性的、具体的事物均显现为偶然性的存在。它们存在的根据,亦即世界的秩序只能在有限背后的无限、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中寻找。因此,认识,就其真理性、普遍性而言,只能是对终极存在的认识。不仅如此,作为真理性和普遍必然的知识,就其表现形态来说,也只能是保证其合理性论证的形式逻辑系统。进而,这种能通达终极存在的形式逻辑系统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秩序。于是,求“真”意志背后涌动的对“善”的追求随之实现。然而,哲学史的史实却告诉我们:传统形而上学无论在存在论、知识论、价值论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
第二,由此,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也就走出了各种意义的精神王国,成了感性活动。马克思把实践当作感性活动不仅针对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针对康德的理性主义的“应该”,针对亚里士多德以生活行为本身的“妥当”为目的的实践(本质上是理性精神的),而且也针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费尔巴哈将感性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实践中拯救出来,但“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54。所以,他既不理解现实的人,也不理解属人的社会、历史和自然。实践在他这里“只是从它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1]54。培根把实践作为“感性活动”的生产实践尽显其合理性,但是,培根和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一样,并不理解实践中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54。
第三,针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马克思指出,实践是“对象化活动”。显然,马克思是在扬弃黑格尔“对象化活动”精神外壳的基础上,对其合理因素作了肯定。马克思说:“黑格尔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7]116。因此,马克思的实践作为“对象化的活动”并不是单纯工具性、手段性的实践,而是“自由自觉的”的感性活动,具有价值和伦理意义。
第四,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具有价值和伦理意义说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把价值和伦理意义纳入实践范畴有其合理性。感性活动并不混乱和邪恶,不需要神圣的灵魂来拯救。生活的价值和伦理意义只能发生和展开于生产实践活动之中。换句话说,真正的实践并不是个别的、纯粹逐物的活动而是具有其普遍的社会性意义:感性活动、对象化活动的展开过程,就是自然资源、劳动力、权力、技术等社会要素的有机结合过程,必然形成全新的社会秩序、价值趋向和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即形成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社会伦理关系。事实上,当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54,赋予劳动以解放和自由的意涵时,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第五,由此,真正的“对象化的活动”“感性活动”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生产劳动。不同性质的劳动不过是马克思哲学实践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样式。在私有制前提下,劳动不过是非本质的、手段性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其中充斥着各种断裂: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断裂、人和物的断裂、劳动者和劳动的断裂,最终,导致人们相互之间的断裂。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不把制作性的生产活动理解为实践,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制作性的生产活动过程和产品的断裂。显然,真正的实践指向活动过程本身而不指向活动以外,其根本意义在于成就生命的善、意义和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才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总之,哲学史的逻辑表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真理与价值等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它既是全新的世界观,包含全新的实践逻各斯,也是人本真的存在方式,还是一种根本不同于二元分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全新的非对象性[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实践表述为对象性的活动。本文中的非对象性和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只是为了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本文才把存在于对象化活动中的思维称之为非对象性思维。非对象性的意思绝不是思维没有对象,而是意在强调人和对象的新型关系。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 1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 3 ]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邓安庆,译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4 ] 丁立群.实践哲学:两种对立的传统及其超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2):81-83.
[ 5 ] 黑格尔.小逻辑[M].贺 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 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7 ]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A Perspective from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Karl Marx’s Philosophical Practice Category
Shang H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Karl Marx’s philosophical world view is built on the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Therefore, it is an indispensab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try to comprehend this philosophical practice category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In line with thought history, we could understand the intricate connotation and historical destiny of concept of practice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ltimate existence pursued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with knowledge and theories, with perceptual production activity, with value and ethical order, and with formal logic and Hegel’s speculative logic.
Key words: history of philosophy; Karl Marx; practice; interpretation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8)05-0014-06
收稿日期: 2018-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WW022)
作者简介: 尚 欢,博生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日本现代文学研究。
DOI: 10.13317/j.cnki.jdskxb.2018.054
(责任编辑 张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