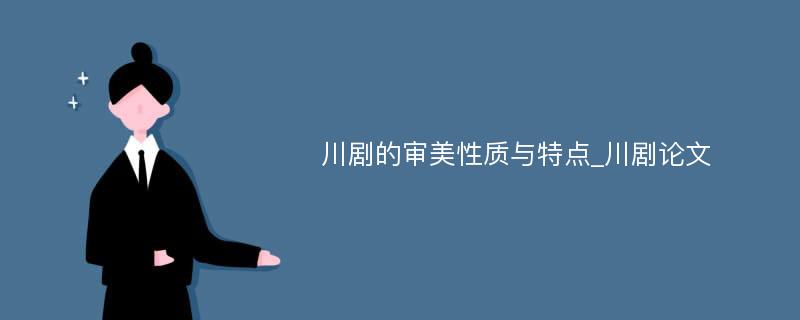
川剧的美学本性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川剧论文,美学论文,本性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数十年来,人们在论及川剧时往往多注意川剧某些局部或表面的现象,或多侧重于某些剧目及文、音、表、导、美等艺术方面的记录整理和一般分析。而对于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以及川剧整体美学精神的理性把握方面却重视不够。川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几乎是“瞎子摸象”:即一方面过多依赖于一些记录整理的、陈旧琐碎的、局部表面的实践经验,另方面又常常用一些过时的、不成体系的、它种学科的只言片语来阐释这些经验。值得重视的是,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往复循环已成为一种不良习惯,不仅使川剧的审美活动长期陷入了固步自封、举步维艰的境地,同时还使川剧的史、论研究也陷入迷茫之中(例如邓运佳所著的《川剧艺术概论》将“川剧”与“四川戏曲”等同看待,演绎为“狭义的川剧”与“广义的川剧”,并继而出版了实为“四川戏曲活动史料”的《中国川剧通史》),连众所周知的作为中国戏曲一个地方剧种的川剧的基本涵义也变得似是而非了。为了改变川剧实践落后于时代而理论更落后于实践的状况,逐步建立一种源于川剧和符合川剧自身发展规律的、并能指导川剧实践和促进川剧繁荣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文仅从戏剧美学角度切入,对川剧美的形成、川剧美的本性、川剧美的特征等有关问题作一点粗略的探讨。
一、川剧美的形成
什么是川剧美?从美的构成因素而论,川剧美是中国戏曲美与四川地方美、现代美的有机统一。中国戏曲美不是指历史上具有美的基因的一切戏曲形态,而是指戏剧化与民族化相一致的具有“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审美特征的成熟戏曲的戏曲化之美;四川地方美也不是泛指四川地域有史以来的某些地方性表象,而是指四川地方化的现实(生活)美(包括自然美、社会美)与艺术美的总和;现代美不是指现代艺术的生搬硬套,而是指现代审美观念、审美意识支配下的独创之美。从美的形态特点而论,川剧美是中国戏曲美与四川地方美不断融合、共同衍化的新生之美。从川剧美表里一致的生命过程而论,川剧美作为一种戏剧艺术美,归根结蒂不过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生存主体审美意识的物态化,其生命过程即是20世纪初以来四川地域生存主体本质力量的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的感性显现过程。
关于川剧剧种的形成,笔者已在《川剧形成于现代》(见《四川戏剧》1997年第6期、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剧、戏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有所论及。 这里需进一步强调的是:当我们将川剧作为一个独树一帜的地方剧种来进行研究的时候,绝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些零星、表面的现象罗列。既不能以一首诗、一句话、一个词语或个别人、个别戏班的演出活动为依据而牵强附会,也不能以某些上演剧目、表演技艺、声腔音乐等艺术方面的相似之处来追本溯源。因为,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论的阶段论来鸟瞰我国及四川的社会发展历程,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来辨析中国戏曲与川剧剧种的相互联系,川剧与清代以前的戏曲(包括四川曾经出现过的两汉的“百戏”、隋唐的“蜀戏”、南宋的“川杂剧”、明代的“川戏”等)不存在任何渊源关系的可靠证据。其次还必须指出的是:川剧的形成是一种广泛性的社会行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四川生存主体审美心理定势的一种外化反映。清代戏曲诸腔剧种相继入川流汇以及落户衍变,主要是由清初以后数次“移民填川”而大规模改变四川人口、改变四川经济文化的社会动因引起的(1282年的元代,四川人口约60万。元杂剧未见半点踪影。1644年的明代至1680年的清代,全川仅约50万人。明传奇未闻广泛流行。乾隆十四年至嘉庆二十四年的70年间,四川人口由250余万增加到2560万。 诸腔剧种相继入川。1850年,四川人口跃居全国第一。诸腔已渐趋“川化”。至1911年全川人口增加到4344万时,诸腔戏班才大量汇集于大、中城市)。也就是说,艺术是人为,人是一切艺术形成以及发展变化的本源。四川人口数量及其质量结构的巨大变化,必然会给四川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艺术等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此外更应该重视的是:不少人虽然注意到清代中叶戏曲“花部”勃兴以及诸腔流汇四川与川剧的渊源关系,但一般都忽视了诸腔剧种(群体)与川剧(个体)的区别,误将诸腔剧种“川化”的渐变过程(如川昆、清戏、川梆子、丝弦子等)当成了川剧剧种“形成”的突变过程。正是这种将主体审美心理定势与其外化信息的错位攀比,造成了川剧剧种纵、横两个方面的界限不清,导致有人将清乾隆时期川旦魏长生所演之“秦腔”(亦作“琴腔”)硬说成川剧“弹戏”,将魏长生等秦腔演员硬说成川剧演员(如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清代川剧的盛衰》)。进而将所有出入四川的戏曲剧种都统称为川剧。其实,大量资料表明,诸腔剧种相继入川以后,在“五方杂处、错用乡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其衍变过程经历了大致两百年的漫长岁月。散流于农村乡镇的戏班,如要生存发展或扩大活动范围,必须以社会的经济发展及交通便畅等为基础,以人们语言、音乐、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审美要求等方面的相对一致为前提。其衍变过程的阶段性描述大致为:诸腔戏班先多是各自在本省移民比较集中的农村庙台或广场演出,后来才逐渐搬演于城市移民的“会馆”(如成都、绵阳、自贡等地的陕西馆、江西馆、江南馆、湖广馆、福建馆、浙江馆、河南馆、广东馆等)之中。不同声腔剧种或戏班以“两下锅”、“三下锅”的方式同台演出大致在清代中叶以后,而汇集于四川大、中城市长期驻留并成为市民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是清末民初的事了。不少历史文献与客观事实证明:作为中国戏曲一个地方剧种的川剧,孕育于晚清改良运动背景下的“戏曲改良公会”活动之际(“公会”1905年成立后,省城成都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官方出面组织、文人参与创作、名伶示范演出、集资兴建剧场的社会性重要行为),在震撼全国全川的辛亥革命的有力“催生”下,脱胎于进步戏曲团体“三庆会”成立之时(即1912年。最早的川剧前辈以及川剧创作只能追溯于此时)。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川剧才完成质变而渐趋成熟定型(已涌现大量川剧创作剧目,已形成“四条河道”)而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唐幼峰于1937年出版《川剧人物小识》,1944年才出版“事属创举”的“介绍川剧之各方面”的《川剧杂拾》)。
毫无疑问,川剧的“先天”十分丰足。其形成有如元王朝统一中国而“催生”的元杂剧汲取了当时金元院本、诸宫调等多种民族、多方地域文化的情形一样,不仅承继了父辈即当时四川戏曲的剧目、表演、音乐等诸方面美(包括内容与形式)的基因,同时还汲取了母体即当时四川现实(生活)美(包括自然美与社会美)和艺术美(特别是源于四川本土的民间灯戏和曲艺)的基因。因此,川剧自诞生之日便具有起点高、形体壮的特点。然而,由于川剧毕竟属于“一次性”的舞台艺术,在戏曲的审美活动中并不像一个“婴儿”那么具体确定而清晰可辨,所以“川剧”之名也是其趋于定型期间由人们逐渐约定俗成,然后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如果说川剧的戏曲美与地方美是“先天”所赋予,那么川剧“后天”的现代美,则是现代四川人审美意识的一种补充和发展(主要通过包括“时装戏”在内的现代戏和新编古装戏),因而今天的川剧之美,即是一种“先天”与“后天”相结合的、趋于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相统一而发展变化的美
二、川剧美的本性
马克思主义美学十分强调人类社会实践在美学中的重大意义。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观点、感情、趣味、理想等)都产生和发展于人类改造自然界以实现人类目的的社会历史劳动实践中。是“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马克思语)。当我们将川剧美的生命过程视为20世纪初以来四川地域生存主体本质力量(即改造生存环境、创建美好生活的感受、认识及能力)的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的感性显现过程的时候,会从四川人的审美心理定势与被对象化的川剧美的辨证关系中,惊奇地发现“兼容”这一本质特性的决定性意义和巨大作用。
“兼容”是神州大地中华民族的本质特性之一。中国戏曲之所以兼容了古往今来的种种故事内容(包括诗歌、话本、小说、经文、民间传说等的思想内容)及技艺表现形式(包括歌、舞、乐、戏、剧及杂耍、武术、魔术、绘画、建筑、雕塑、曲艺等),皆因是这种“大一统”的本质特性所定。四川幅员广大而山川错落,人口众多而源流复杂,因而具备了继承和发扬这种主体特性的最好条件。川剧之所以能够沿袭戏曲艺术的美学精神,几乎保留和发展了戏曲剧目及文、音、表、导、美等各个艺术方面,其基本原因正在于此。应当看到:在戏曲古今并存、大小共济的300余个剧种中,川剧是近现代戏曲总体的一个典型缩影。 川剧最为全面地坚持了古代戏曲“中和”的艺术创造原则和审美理想,最为完整地体现了“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的审美规范。在戏曲的大家庭里,也正主要是川剧的“兼容”特性使之与其它弟兄剧种相对有别(尤其是剧目、声腔、表演方面),长期保持着“独树一帜”的大剧种的地位。
川剧美的“兼容”特性不仅表现在戏曲美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四川的地方美方面。巴山蜀水特有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形成四川地方现实美的自然质,是四川地域“人化”的自然美滋生的土壤。四川位于中国西南腹地,是中国唯一的与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八省区毗邻的省份。在总面积达56.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代代相传的四川人在生理、心理、性格、习惯等方面的相对一致,也就是四川人与外省人相对存在的明显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是由生存环境自然质的不同所决定的。所谓“重庆人火暴”及“山地意识”,所谓“成都人内向”及“盆地意识”,都足以说明自然环境对于生存主体性格、意识的深刻影响。这种自然质的差异一般被人们称为“地方性”或“地域性”。川剧的地方风格、地方特色,实际上也就是四川的“地方性”在川剧风格、特色方面的表现。由于川剧的“地方性”表现最为全面、最为集中、最为强烈而最具有代表性,所以一直被视为四川“地方化”的戏曲剧种。虽然生存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变化的(例如生死、迁移),对于区域的划分也可以根据需要而加以改变(例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庆已不属于四川),甚至包括剧种的名称等一切外部形式都可能改变(例如根据需要给川剧更名或创立新的剧种)但只要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依然存在,其“地方性”总是会通过生存主体及其艺术传达的形式顽强、恒久地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找到川剧何以在四川长期存活并流播邻省部分地区的基本原因;可以推论终有一天“川剧”之名确实会如元杂剧、明传奇那样地“消亡”;可以得出即便川剧已不复存在而其艺术精神将会永存的结论。四川特有的社会环境,是四川地方现实美的社会质,是四川生存主体改造客观世界、共建美好生活的社会劳动实践中社会美产生的基础。在“美不美,家乡水”的感觉中,在“亲不亲,故乡人”的感情里,四川人思想、语音、志趣、行为等方面及表达方式的相对一致,构成了四川社会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语言美等方面与其它省份相对有别的内容与形式。四川地方的艺术美,实质上也就是四川的现实美(又称生活美,包括自然美和社会美)的艺术表现。川剧作为一种戏曲化而又地方化的艺术形态,在与戏曲总体的艺术精神相表里的同时,又总是不断从四川的现实美和艺术美(主要是四川民间的灯戏、曲艺)两方面汲取营养来丰富和完善自身,保持着“兼容”其它而不被其它“兼容”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是其它戏曲剧种(包括国内其它省份的地方剧种和四川境内的京剧、四川灯戏、四川曲剧以及歌、舞、话剧等)所难以其备的。所以川剧无论是文、音、表、导、美方面还是表现手法、表演技艺、创作方法等方面,无论是艺术风格方面还是艺术特色方面,都显得尤其丰富多彩。川剧如何兼容戏曲美、四川地方美而变成川剧的艺术美的实例俯拾即是。例如我们把大家熟悉的川剧《秋江》与其它剧种同名剧目加以比较,并从那些种种不同之处去寻根究底,就可以明白一个并不起眼的戏曲剧目何以能变成一个富于川剧美的川剧名剧的诸多道理。川剧《秋江》的川剧美绝不只是表现在唱、念、做等戏曲的形式方面。那剧中人幽默机趣的性格以及助人为乐的品行,那悠扬的“川江号子”以及那湍湍急流中驾舟行船的娴熟的劳动方式,难道不是四川社会实践中生存主体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么?观众所感受的川剧《秋江》的自然美并不是“秋江”之美而是“川江”之美,所感受的社会美并不是“江浙”人之美而是“四川”人的心灵美、行为美、语言美。川剧的审美主体正是象编演《秋江》一样,通过川剧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观照存在于自身的思想、性格、情感、意志、理想及聪明、才智等本质方面,来传达自己在改造生存环境中的种种感受与认识,来兼容戏曲美和四川地方美,来创造川剧美、欣赏川剧美的(对于其它剧种甚至歌、舞、话剧剧目,几乎都可以象《秋江》一样通过“移植”或“改编”的办法加以“兼容”)。所以,川剧艺人常说:“其它剧种有的我们都有,其它剧种没有的我们也有。”
川剧的现代美,是川剧与生俱来的发展变化之美。如果以上说川剧兼容中国戏曲美与四川地方美主要是从横向而论,那么现代美则主要是从纵向联系方面而言。因为川剧美的形成、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边横向兼容、边纵向发展的过程。川剧的现代美表现在川剧审美主体现代审美意识支配下的创作与欣赏方面。川剧的“兼容”本性,使川剧一开始就具有开放的品格。可以说,从西方话剧途经日本入川(成都春柳社)之日起,川剧即注意学习借鉴话剧以反映和表现现代生活了。我们可以从川剧的时事戏以及后来的时装戏、现代戏的演变轨迹中,去追溯川剧主体的现代意识、地方意识,去跟踪川剧现代美的形成演变过程(参见拙文《川剧现代戏的历史演进》,刊载于《四川戏剧》1990 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曲研究》1991年第1期)。 川剧现代美表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川剧的传统戏和新编古装戏。除了黄吉安、赵熙、冉樵子、尹仲锡等一代早期著名作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爱国的、民主的、地方的现代意识外,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推陈出新”的传统戏主要表现在文、音、表、导、美艺术形式的现代审美时尚的追求上(如文学剧本的加工改编、现代音乐的渗入,话剧表、导演手法的应用,现代舞台美术的设计及服装道具、灯光布景的运用等)。新编古装戏则更加注重现代社会意识的涵盖力与现代艺术手法的表现力。尤其是川剧作家魏明伦、徐棻的剧本及其二度艺术创作群体的“探索剧目”,真可谓以古人之“形”传今人之“神”的戏曲美、地方美、现代美有机和谐的川剧美。这种撼人心魄、耐人寻味的川剧美,是一种兼容古今中外、富于时代气息而给人以新的美感的独创之美。它所张扬的主体意识,它所显示的人格力量,它所呈现的艺术魅力,集中地展露出川剧“兼容”的博大胸怀和永不衰竭的生命活力(当然,“兼容”也有弊端,如何兴利除弊和扬长避短的问题,这里暂不探讨)。
三、川剧美的特征
不少人常凭感觉来概括川剧的艺术特征,如所谓四川方言、五腔一体、大锣大鼓。如果只是从听觉角度而言,似乎也有道理。但川剧是一种视、听觉综合的直观艺术,因而此类感觉判断的片面之处就不言而喻了。值得重视的是,在认识一个戏曲剧种艺术特征时,绝不能停留于表面的形式。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方言、声腔、锣鼓在内的一切表面形式都会发生变化。例如随着普通话的推广、现代音乐的渗入、城市剧场的兴建,川剧的方言、声腔、锣鼓等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假如将川剧某一发展时期、某些表现形式视为艺术特征,实际上等于把川剧凝固起来,扼杀了川剧的生命。过去,那些强调川剧“正宗”而抱残守缺的老人与那些强调社会发展而否定戏曲发展的青年之间的种种争端,实际上都是只看到一些暂时的表面现象,把仍在发展变化中的戏曲视为一成不变的了。
由于川剧存活于现实的审美活动中,当我们把川剧作为一种鲜活的审美对象来加以研究时,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应是动态的、立体的而不应是死板或平面的。也就是说,审视的目光应当投放于戏剧剧目的舞台呈现上,观察的注意力应当集中于剧场观众的反馈效应中。戏剧剧目的舞台呈现与剧场观众的相互交流,才是探寻川剧深层次审美特征的大门。
川剧美的“兼容”本性,使川剧象滚雪球一样形成了兼收并蓄、纵横向前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决定了川剧美的“内聚型”积累和“散发型”表现的方式。不断地“内聚”与不断地“散发”的相互循环,构成了川剧美双向流动的感性时空,并通过许许多多对应而辩证统一的关系中活泼的显现出来。我们将这种建立在“兼容”基础上的双向流动的显现征象,称为川剧的“双向性”审美特征。
“双向性”不是一般所论之“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等外部表现的戏曲审美特征,而是深层次的贴近“兼容”本质特性的内部表现特征。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有许多带有哲学意味、表示两种对应关系的术语,例如真与假、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雅与俗、庄与谐等,曾在包括戏曲在内的艺术论评中广泛使用。所谓意、境、风、骨、趣、韵、味等种种美的形态,皆是由审美主体体验于不同的两种对应关系之间。所以诗人陆游曾有“功夫在诗外”的名言,画家齐白石也有“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妙语,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认为,中国戏曲是“给观众一种美的感觉的艺术”。那么,这种“美的感觉”在哪里呢?川剧开山祖师康子林曾经比较确切地作出过回答,他指出:“不象不成戏,真象不算艺;悟得情和理,是戏又是艺。”“演员一身艺,千古一剧情;既是剧外人,又是剧中人;剧外和剧中,真假一个人。”在川剧的艺术创造中,必须“重大体,尽精微,心领神会形附,贯连虚实相随,一变能应万变。”(转引自胡度《川剧艺诀释义》)。康子林不仅从艺术经验的感性直觉出发,比较深刻地阐明了如何创造川剧“美的感觉”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戏艺并重、神会形附、贯连虚实等一系列审美创造原则与方法,指出了川剧之美表现在不象(生活)与真象(生活)之间、情与理之间、形与神之间、虚与实之间、一变与万变之间,是诸多两种对应关系的辨证统一。
其实,“美”在两种对应关系之间的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从上古天地之间的“气”、“道”,乃至以后诗、书、画、歌、舞、乐论评中常常提及意境、风骨、情趣、韵味等形容“美”或美感的不能言尽只能意会的种种认识,无不是产生或蕴含于主、客体两者的相互作用之间。所谓真与假、虚与实、文与质、形与神、情与理以及体验与表现、表现与再现、写实与写意等等对应概念,实际上不过是人们为了便于进行审美把握而设置的两个互相流动的交叉点,而一切真、善、美,都是以两个交叉点互相循环的方式显现出来的。
在当今的戏剧或戏曲论中,不少人往往根据两种对应关系的某些侧重来判断某种戏剧的特性或特征。例如美学家李泽厚认为:“各剧种受到该主导因素本身的或表现或再现的特性的制约与支配,便各自形成自己的美学本性和独特规律,应当按照它们的这些客观规律来发展变化。”并引用梅兰芳先生的话说:“如戏曲便‘是建筑在歌舞上面的。一切动作和歌唱,都要配合场面上的节奏而形成自己的一种规律。’”(李泽厚《美学论集》1980年版)这些话与旧时王国维的“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王国维《戏曲考源》)是一脉相通的。对于各位大家之言,这里不打算妄论轩轾。只是就川剧美显现特征的实际情况而论,大可不必削足适履。因为,川剧美的创造与呈现总体上并不强调某一种因素的主导而侧重于某一方面。种种对应关系都是“双向性”流动的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辨证统一的逻辑关系。强调的是真(生活真实)美(艺术真实)同一、戏(剧目内容)艺(艺术形式)并重、形(外在)神(内在)兼备、虚(虚拟)实(摹拟)相生、情(戏情)理(戏理)相随、声(音乐)情(感情)并茂以及雅俗共赏、悲喜相间、刚柔相济、庄谐有致、张驰有度、快慢有节等。强调的是再现与表现的结合,是写意与写实的结合。
川剧美诸种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对应关系,决定了川剧总体的“双向性”审美特征。而双向流动过程中所引起人们审美注意的某些局部因素,却因具体剧目和观赏者的不同而显得各有主导或侧重。例如,我们将作为川剧载体的剧目按“古装”和“时装”统分为两大类,可以看到古装戏一般偏于表现、偏于技艺、偏于虚拟、偏于抒情、偏于写意;时装戏一般偏于再现、偏于故事、偏于摹拟、偏于言理、偏于写实。借用京剧艺术家阿甲的说法,即前者是将“米”酿成“酒”,后者却是将“米”做成了“饭”。这种区别大概是因为后者已无法借助服装、头帽、砌末等变形表现的缘故。但这种区别仅仅是川剧总体发展中不同层面或侧面的区别。尽管两类剧目的社会意义及审美价值各不相同,但却不能视为川剧本质特征的区别。混淆这些区别或将川剧美总体的特征统统一刀切于某一方面,都是犯以偏概全的常识性的错误,都将会违背川剧美的发展规律而妨碍川剧剧种的繁荣。过去,一些人只讲古装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的审美特征,看不到或不承认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时装戏(现代戏)的审美特征,从而否定了川剧美中的现代美,实际上为“博物馆艺术”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相反,由于西方话剧及“以歌舞演故事”等一类陈旧观念的影响,一些人又将“体验”派的“刻画人物”、“塑造典型”等不分青红皂白地硬用于阐释传统戏。这样一来,“象”与“不象”之间的川剧演员似乎完全变成了运用技艺手段来达到刻画人物和塑造典型的材料和工具,“演员中心”就变成“角色中心”了。其实,包括川剧在内的戏曲,技艺与故事之间、演员与角色之间并非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观众看到的,是两种相辅相存的对应关系中艺术美的生命律动及观照者的本质显现。由于观众审美经验及生活体验的不一,对于同样一个剧目,有的侧重于看故事、看人物,有的侧重于看演员、看技艺的情况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如根据剧目特点及观众视角的不同,可以将某些剧目称为“以技艺演故事、演人物”(主要是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的剧目,将某些剧目称为“以故事、人物演技艺”(主要是代代相传之传统戏)的剧目,(即所谓“看角”的剧目,这种剧目扮演者的名气往往大于角色)。但如果不加区别统而言之,并概括为川剧总体的审美特征来作为指导艺术实践的理论,就必然会背离川剧美发展的规律。
“振兴川剧”以来,川剧美的创造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90年代涌现的《山杠爷》、《中国公主杜兰朵》、《死水微澜》、《变脸》等剧目,展示了川剧美崭新的时代风貌。必须看到这一点,不然就谈不上提高川剧主体的自觉性,增强其审美创造能力和艺术鉴赏水平,使川剧在群芳争艳、多样选择的大众审美氛围中长久不断地保留“一席之地”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