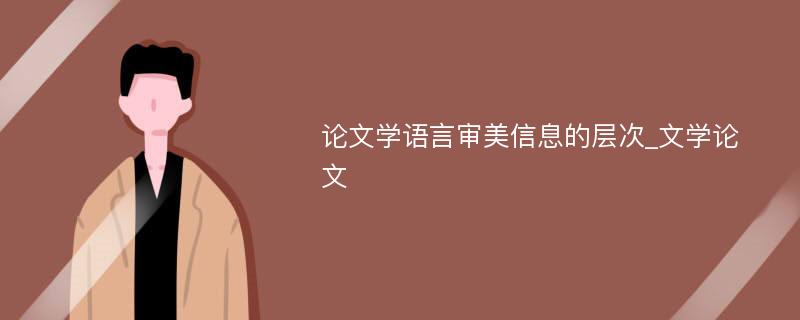
文学语言审美信息层次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语言论文,层次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文学语言客观地承载着两种信息形态,即语义信息和审美信息。文学语言所负荷的审美信息表现为一种多层复合体。有的贴近语义信息,可称为表层审美信息;有的隐匿在语义信息或表层审美信息中,可称为深层审美信息;有的飘浮或笼罩在文学语言外围,可称为外层审美信息。文章对每一层审美信息的审美特征及其形成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 表层审美信息 深层审美信息 外层审美信息
一、审美信息及其层次
文学语言一方面作为一种语言形态存在,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存在。文学语言的这一双重特性决定了它所传递的意义信息也具有双重特性。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我们一进入审美领域,我们的一切语词就好象经历了一个突变。它们不仅有抽象的意义,好象还熔化融合着自己的意义。”〔1〕这里“抽象的意义”指的就是语言意义, “自己的意义”即审美意义。日本学者川野洋曾引用两种不同的信息概念对此加以界说。他说,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作为意义的传达者深沉用来标示、解说、陈述、阐发他物,是一种确定意义上的信息,即“维纳的信息”,叫做“文学的语义信息”;而语言在文学作品中更经常地用来表现、抒发、咏叹创作主体的心绪、情思、意蕴,语言此时又是作为一种不确定的信息,一种内指向的信息存在着的,是一种“申农的信息”,叫做“文学的审美信息”。〔2〕循此我们可作进一步的描述。 文学语言客观地承载着两种信息形态,即语义信息与审美信息。语义信息所传递的是语言的“理性意义”或“词典意义”,具有称谓和叙述功能,是文学语言信息的基础和核心,是一种确定意义上的信息,审美信息依附它而存在。审美信息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信息,它建立在语义信息基础之上并联系语境而形成。审美信息可以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因而它的信息量比语义信息要丰富深厚得多。它隽永而富有意味,能引起人们的审美愉悦,使人得到感官与精神上的满足和理智上的启示,具有表现功能,是文学语言艺术生命之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尽可能地增大文学语言审美信息的蕴含量也就成了作家们的自觉追求。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玉楼春》)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就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审美信息。这句诗所提供的语义信息仅仅是“红杏开花了,春天到了”,但透过这一层语义信息,通过“闹”字而触发联想,可以捕捉到如下审美信息:春天里姹紫嫣红,红杏枝头绚烂多彩,花香扑鼻,引来蜂飞蝶舞,小鸟鸣唱,大自然春意盎然。这些审美信息的丰富性以及给人带来的审美愉悦是不言而喻的。
文学语言所负荷的审美信息表现为一种多层复合体。有的贴近语义信息,由语义信息直接表现,可称为表层审美信息;有的隐匿在语义信息或表层审美信息中,由语义信息间接表现,可称为深层审美信息;还有的飘浮或笼罩在文学语言的外围,附加在语义信息之上,可称为外层审美信息。各层信息互相联系,共鸣共振,产生强烈的审美效应。如臧克家的《老马》一诗,由字面意义精细入微地刻画了一匹忍辱负重、在鞭子下苦苦挣扎的老马的艺术形象,这个完整的艺术形象由字面的语义信息直接提供,是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表层审美信息。在它之下,隐含着深层审美信息,这是作者的真意所在,即用“老马”这个艺术形象来象征旧中国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亿万劳苦农民,象征他们在封建制度的重轭下当牛作马、含辛茹苦的悲惨命运。〔3〕渗透在字里行间、 蒸腾在全诗意义外围的外层审美信息是丰富而回味无穷的:诗句流露出诗人同情与热爱劳苦大众、仇恨剥削阶级的情感情绪,笼罩着一种沉重悲怆的语言情调,表现出含蓄深沉的语言风格。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语言审美信息的三个层次并不一定同时出现,它们或分别单独出现,依附于语义信息,或同时出现某两层审美信息,或三个层次并存。每一层审美信息都可单独加以分析。下面逐一分析每一层审美信息的审美特征及其形成。
二、表层审美信息
表层审美信息是由语义信息直接表现的美学信息。它通过本身具有审美价值的语词和语词链作用于人的各种感官,使人产生联想,唤起美感。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诗句,本身具有美质的词语有:色彩词“黄、翠、白、青”;音响词“鸣”;动态词“上”;形貌词“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这些词语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器官,唤起人们对这些词所代表的事物产生联想,在脑际整合成一幅绚丽多彩、有声有形、动静俱备的美妙画面。这就是这两句诗所传递的表层审美信息。表层审美信息在语言的表层创造出来,由语义信息(字面义)直接提供,接受者可以通过对辞面的直接破译在较短的时限内获得较大的审美愉悦。
本身具有审美价值的词语是传达表层审美信息的重要语料,这些词语从形貌、性状、色彩、声音等方面对客观事物作精细入微的描摹,“随物宛转”,“属采附声”,“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漉漉’学草虫之韵,……”〔4 〕词语自身均表现出了很高的审美价值。这类词语因其形象色彩鲜明突出可称之为形象词。形象词以其外显的形象色彩向人们发出一种信息,刺激人们的感官,在人们的大脑意识中很容易唤起关于某类事物形象的联想,产生出鲜明而又真切的形象美感来。
大致说来,形象词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表示视觉形象的,这一类最多。有的表示事物形貌:珍珠、翡翠、霞光、彩虹、涟漪、清泉、轻烟、柳絮、珠光宝气、花容月貌等。有的表示动作状态:雀跃、蜂拥、风吹草动、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抓耳挠腮、摇头晃脑、亭亭玉立、打躬作揖、健步如飞等。有的表示颜色或性状:碧蓝、玫瑰红、金灿灿、绿油油、白花花、婷婷袅袅、滔滔等。这些词语均具有“可视性”,词语本身能唤起清晰如画的形象,让接受者从语言自身“看到”某种图景。
表示声音形象的:丁咚、扑通、响当当、哗啦啦、噼哩啪啦、叽哩咕噜、布谷、喳喳、潺潺、汩汩、哑然失笑、嚎啕大哭等。词语逼真地摹拟了客观事物或人发出的声音,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获得如闻其声的审美感受。
表示味觉、嗅觉、触觉形象的:甜丝丝、酸溜溜、麻辣、香喷喷、软绵绵、硬梆梆、沉甸甸等。这些词语都能强烈地刺激人的感官,使人产生某种感官上的快感。
当然,任何一个单独的形象词语,其审美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它们携手结合起来后(这时往往构成各种修辞方式),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效应。为了说明问题,试以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一段描写为例略做分析。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丰致了。
这段话把大量的形象词语组织在一起,有的还构成了比喻、比拟、通感等修辞手法,将一幅绚丽华美的动人画面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有形象、色彩、声音、味道,有动态、静貌、情致,让人感到美不胜收。
显而易见,这段话所产生的审美信息量并不是一个一个形象词语涵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远远大于单个词语涵义的总和。吕叔湘先生说过:“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它的意义决不等于一个一个字的意义的总和,而是还多些什么。按数学上的道理,二加二只能等于四,不能等于五。语言里可不是这样。”〔5〕在语言组合中, 每一个词都有作用于其他词的能力,也都潜存着接受其他词的作用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种组合序列中词的作用力所能达到的空间范围叫做词的言语义场。每个词一投入使用,它就进入了言语义场,便有了影响其他词和接受其他词影响的可能,词语涵义的增殖因此而产生。
词义增殖有两种情况:
一是形象词语审美涵义的扩大。形象词语在语言组合中不光本身的审美涵义得到实现,而且其涵义会在言语义场的作用下得以扩大。如前例“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和“歌声”是形象词。单独的“清香”和“歌声”所产生的美学价值都很有限,而它们一旦结合起来,进入对方的言语义场,意义互相感染,审美涵义就具体化并增殖:微风中清香成缕,断断续续不时扑鼻而来,伴随着远处高楼上隐约传来的轻美歌声,使人同时从嗅觉和听觉上感受到清香的飘散远逸,歌声的渺茫动听。这时的“清香”是伴奏着歌声的清香,“歌声”是熏染着清香味儿的歌声,各自的涵义均已增殖。同样,前例中的“曲曲折折、田田、亭亭、舞女、白花、袅娜、羞涩、明珠、碧天、美人、缕缕、渺茫、凝碧、脉脉、丰致”等形象词语一进入具体的审美语境,其审美信息都扩大化了。
二是普通词语审美涵义的增生。这由两方面手段获得。一方面是在言语义场制约下词义感染的结果。普通词语一经与形象词语结合,便会被感染上形象词语的色彩义而导致审美涵义增生。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其中的“藤、树、鸦、道、风、马”本无显露的形象色彩,它们一旦与“枯、老、昏、古、西、瘦”等形象词结合成“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后,均被赋予了浓重的凄凉悲苦的情感情绪色彩,整体描绘出了一幅阴暗冷寂的画面。《荷塘月色》中有“田田的叶子”、“脉脉的流水”的组合,“叶子”、“流水”是普通词语。“叶子”在“田田”的词义感染下增生了视觉形象色彩:“田田”状荷叶繁多貌,“田”的字形又描绘出了每一张荷叶肥肥大大如“田”字形。“流水”在“脉脉”的词义感染下增生了温柔缠绵的感情色彩。普通词语神美涵义增生的另一方面是:普通词语所蕴含的次要感性义被激活形成审美涵义。普通词语虽然没有显露的审美涵义,但它们在本质上都具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其审美价值被掩盖是由于词义概括化抽象化的结果。语言中的词义是对词所指对象的最本质最主要特征的概括反映,这种概括反映的结果是词义被高度概括化抽象化,舍弃了词义中的许多非本质次要特征,而这些非本质次要特征恰恰是词义中具有审美价值的活性元素。如“水”一词的概括义(词典义)指“最简单的氢氧化合物,无色、无臭、无味的液体”,这是对“水”的本质特征的概括反映。这种反映滤去了“水”的许多非本质次要特征:清澈、透明、纯净、(静水)平静、柔和、(流水)绵延不绝等。这些具有审美价值的次要义潜存在“水”的词义中,在文学语言中人们可以根据需要运用各种修辞手段组织成不同的话语结构去诱发它的任何一项审美涵义。在“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 和花上”(朱自清)中,以“流水”喻“月光”,诱发出了“水”的“柔和”、“明净”的审美涵义;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中,以“水”喻“愁”,则诱发出了“水”的“绵延不绝”的审美涵义。这时,“水”的这些次要义已被激活上升为主要义。
三、深层审美信息
表层审美信息发生在辞面上,比较浅露,容易理解。文学家在艺术创造中并不满足于传达表层审美信息,他们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运用语言,将情意寄于物上,隐于字里行间,选择言辞进行迂回的间接表达。这样,文学语言便蕴含了深层的审美信息。深层审美信息隐匿于表层审美信息或语义信息之中,是作者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需要接受者结合特定的语境展开联想才能捕捉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深层审美信息含蓄、深邃,独具魅力。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所提供的表层审美信息是:一片孤帆渐渐远去,消失在蓝天的尽头,只剩下浩瀚江水向远处流去,水天相接,茫茫无际。这是一幅可视而运动的画面。但作者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并不在此,而是对挚友的一片依依惜别之情,这便是作者所要传达的深层审美信息。作者将深层信息寄寓于表层信息之中,意在言情,字面却未著一“情”字,接受者需透过这幅画面并联系送别这一背景展开联想,才能捕捉到深层审美信息。
深层审美信息可产生于平实的表达之中。如下例: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鲁迅《祝福》)
这是一句平平常常的话,但祥林嫂听了却“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这句话有这么大的威慑力量,说明它的含义远不止字面上的语义信息,而有着十分丰富的深层信息。在四婶他们看来,祥林嫂嫁了两个丈夫,“败坏风俗”,祭品一经她沾手,就“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当祥林嫂用她的血汗钱捐了门槛、自以为已经赎了罪之后,四婶仍大声吆喝制止她摆祭品。这一声便如晴天霹雳,给了祥林嫂极大的刺激,宣判了她的死刑。这就是这句平常话语所传递的震撼人心的深层审美信息。
深层审美信息更多地借助于各种语言表现手法和修辞技巧去传递。象征便是一种常用手法。如臧克家的《老马》、茅盾的《白杨礼赞》、杨朔的《荔枝蜜》、《雪浪花》、陶铸的《松树的风格》等,均运用象征手法,托物言志,传达深层审美信息。古典诗词常用通篇喻况的手法传达深层审美信息。如屈原的《离骚》多用香草美人比喻正面的理想人物,用恶禽臭物比喻谗佞小人,传达作者品德高尚、热爱祖国、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深层信息。辛弃疾词《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也通篇喻况,表面写女子伤春、失宠,而所要传达的真实信息则是作者对主和派的愤慨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衬托、反语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也有利于深层审美信息的传递。如《祝福》的结尾着力渲染祝福的喜庆气氛,这是反衬,以喜衬悲,表面上写喜,而深层信息则是悲愤。勤劳、朴实、善良的祥林嫂惨死在地主们祝福的爆竹声中,作者有意让这个悲剧掩盖在喜庆气氛之下,表达了作者对吃人的封建社会的无比愤慨之情。这一段中“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是反语,其真意也即深层信息恰好与之相反,是作者心情的沉重、悲愤与内疚。
有时候,反复的修辞手法也可带来深层审美信息。如鲁迅散文《秋夜》的开头: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开头。既然是两株同样的枣树,作者为什么不一笔写成“墙外有两株枣树”,而要分开来写呢?原来作者的本意并不是要告诉读者后花园窗外有些什么树,而是另有深意。枣树在文中用来象征顽强战斗的革命者。分开“一株”“一株”地写,表达了作者当时孤独、寂寥的心情与处境;另一方面,复沓的句式又可起到强调的作用,表明作者尽管孤身只影却仍要顽强战斗的韧性斗争精神。可见在简单重复的表层信息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深层审美信息。
此外,运用双关、婉曲、借代、比拟等修辞手法均可传递深层审美信息。
四、外层审美信息
真正的文学语言,应当是有着深厚底蕴的语言。巴尔特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没有底的语言”,在文学语言中,“能指”下边并不是一层固定而确切的“所指结构”,而是由一系列“虚设的意义”所支撑的“纯粹的暧昧”。英伽登曾经从语言学的角度将文学作品的构成划分为四个层次:(1)语言层次;(2)意义单位;(3)系统方向;(4)被展现的客观世界。还有一个非常“不清楚”“不精确”的第五层次,一个可以称为“形而上的品质”的层次,这一层可以体现出“崇高”、“光明”、“宁静”、“神圣”、“超凡”、“悲伤”、“恐怖”、“妩媚”、“迷人”等莫名其妙、难以言传的东西。〔6 〕巴尔特所说的“ 纯粹的暧昧”和英伽登所说的“第五层次”,都很象是中国文论中说的“氛围”、“意味”、“神韵”,一种“意外之意”、“弦外之音”的东西。这是文学家们凭借着他们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对他手中的字词语句进行天才的选择和组合创化出来的东西,可以称为外层审美信息。这种由语言本身表现出来的氛围、情调、韵味并不是作者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它附丽于主要信息之上,飘浮或笼罩在语言的外围,让人久久玩味,沉醉在美的氛围中,产生快意。如高晓声《陈奂生进城》的开场白: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在“陈奂生今天上城来了”的语义信息外围,洋溢着一种轻松幽默的情调,笼罩着浓重的喜剧气氛,给人以审美愉悦。再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该诗抒发了作者胸怀大志却报国无门的孤寂苦闷的感情。于这种感情之外,全诗还笼罩着一层悲凉慷慨的语言情调,一种深沉博大的语言的氛围。这种情调氛围就是文学语言传递出来的外层审美信息。
很显然,外层审美信息是“暧昧”、“不清楚”和“难以言传”的,这与外层审美信息所由产生的作家的心灵状态本身的复杂微妙分不开。作家心灵深处对生活万象的精微感受,对社会人生的原初体验,那一团团说不清的感觉、经验、潜意识,是无法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的,却往往能被高明的文学家巧妙地砌进字里行间,营造出语言的氛围来,让人们在这种语言的氛围中感受到它的丰富性,感受到它的妙不可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不可言传的东西就越能引起人们的审美注意,激发人们去寻幽探胜,而这种美的探索、美的发现行为本身就足以抬高外层审美信息的美学品位。
外层审美信息既然是“难以言传”的,因此对它做进一步的分析也就难免费力不讨好。下面我们只就两类相对易于把握的外层审美信息加以说明。
1.情感情绪类信息
作家在用语言表达思想的同时,伴和着主观情绪的宣泄,让心灵深处的情感情绪、体验感受等投射在语言上,使语言带上某种情调:忧伤怅惘的、甜蜜缠绵的、欢快轻松的、悲怆压抑的、嘲讽诙谐的、平淡旷达的,等等。譬如: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鲁迅《故乡》)细细咀嚼,不难领悟到这段话所流露出来的忧伤怅惘,悲凉沉重的语言情调。作者将自己的心绪投射在景物上,编织进字里行间,在语言的外层形成一股悲凉的情绪意味。又如: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象火,粉的象霞,白的象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象眼睛,象星星,还眨呀眨的。(朱自清《春》)作者在这里营造了一种欢快愉悦的语言情调和语言氛围。
语言情调是作家的情感情绪投射在语言形式上凝结而成的,它的形成因此也就离不开语言本身的运用。语词的选择和排列组合,句式的剪裁,种种语言技巧的运用,都是生成语言情调的重要手段。如《故乡》例中,“深冬”、“阴晦”、“冷风”、“呜呜”、“苍黄”、“萧索”、“荒村”等词语的选用便是形成悲凉的语言情调的重要基因。《春》例中选用了带有调皮意味的口语词语:赶趟儿、甜味儿、眨呀眨的;采用了活泼明快的口语短句;运用了孩子味儿十足的比拟“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以及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渲染整合出活泼欢快的语言情调。
2.语言风格类信息
语言风格类信息指文学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独特的风貌和格调,它是作家运用语言的种种特点的综合。由于不同的作家的气质、性格、经历不同,每个人运用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就决定了文学语言风格信息的多样性:有的藻丽,有的平实;有的明快,有的含蓄;有的庄重,有的幽默;有的繁丰,有的简洁;有的豪放,有的柔婉。不管哪一类风格信息,只要适合题旨情境,都是美的信息。而这类信息如风行水上一般,飘浮于辞面之上,升腾在语言的外围,因此可称为外层审美信息。如郭沫若《屈原》中的《雷电颂》,作者火山爆发般地怒吼:“……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这段文字在表达作者追求自由与光明、要求彻底毁灭黑暗这种感情的同时,还传递出了一种气势高昂、吞吐宇宙的粗犷豪放的风格气息。这是一股震撼人心的文气,它激荡于辞面之上,与读者共鸣共振。而朱自清《荷塘月色》的语言(例见前)则在写景抒情的信息之外,传递出了细腻含蓄、柔婉清丽的风格信息,韵味深长。
关于语言风格的分类与语言风格的形成,行家多有研究,此从略。
本文主要从生成和传递的角度讨论文学语言审美信息,如何接收或破译文学语言审美信息,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收稿日期:1994—11—08
注释:
〔1〕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1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8年6月。
〔2〕参见鲁枢元《超越语言》第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11月。
〔3〕一说“老马”的形象寄托了作者的身世、遭遇、 情怀和理想。参见张惠仁《以形写神,亦马亦人》,载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
〔4〕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5〕吕叔湘《语文常谈》第46页,三联书店,1982年。
〔6〕参见鲁枢元《超越语言》第75页,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