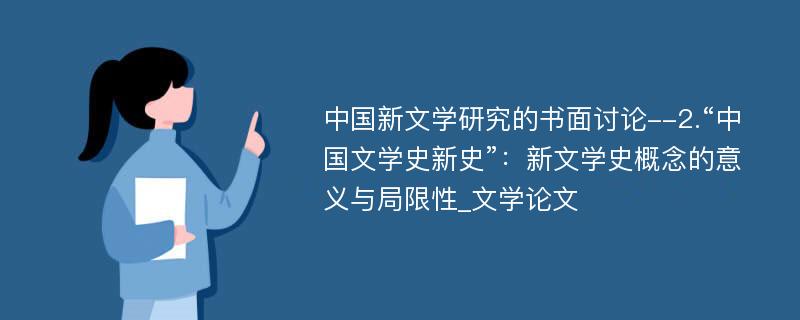
汉语新文学研究笔谈——2.“汉语新文学史”: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的意义和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文学史论文,新文学论文,笔谈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受到多方面质疑和挑战,人们试图用一个更为科学、准确、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取而代之,并为之付出了不少努力。“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概念的相继提出,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这些新出的概念无论曾经多么红火、多么眩人眼目,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面前,这些概念都显得有些短命。除了各种难以改变的积习之外,这些新出概念的自身缺陷也是它们短命的主要原因。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再去用“20世纪中国文学”或“百年中国文学”概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从常识上就很难通过了,所以,“汉语新文学史”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得以提出并产生共鸣。与“20世纪中国文学”相比,“汉语新文学史”并不以取代“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目的,而是把两个独立的学科——“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整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研究平台,从而拓展出新的阐释空间。这一初衷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发展、兴盛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迄今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并展示出了极为广阔的研究前景。但是,必须看到,“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研究队伍相互重叠、交叉,就从创作来看,二者也存在互动关系:如现代文学史上的“留学生文学”,被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作家的迁徙,很多大陆作家移居港台或国外成为华文文学作家,像现代的梁实秋、张爱玲,当代的北岛、高行健等,都成为“华文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说,“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根本不存在清晰的学科边界。但长期以来,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极力凸显“华文文学”学科的独立性,甚至以消解“中国中心论”、“大陆中心论”的名义建构“华文文学”的独立王国。这样一种用意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华文文学学科逐渐强大之后,这种人为的分离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就世界范围内的华文写作而言,其中心在中国大陆,这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欧美的华文写作也能够产生出优秀作品,有些作品在质量上超过了大陆作家的作品,但这依然不能改变大陆中心的位置。也就是说,大陆汉语写作的中心地位,不是一个文学质量或创作水平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域和文化的概念,也是一个市场的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最优秀的华文文学作品不一定产生在中国本土,但中国本土(含台港澳地区)却有着人数最多的华文文学读者群,最为广大的华文文学图书市场,以及最深厚的华文文学背景”[1]。简单地说,中国本土以外的汉语写作,其根基在中国大陆,所以,不顾及这些实际情况,简单地将“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分隔开来,必然造成对一些基本事实的遮蔽。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新文学史”的概念就避免了这一不足,它把世界范围内的华文写作(含中国本土)看作是一个有着密切关系的整体,在研究中超越地域的界限,进行综合考量和评估,无疑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发现和新的惊喜。
“汉语新文学史”突出强调“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汉语写作中的中心地位,这是这一概念最为核心的精神,也必然是它最招致非议的地方。这一概念有意突破国族界限,以“现代汉语”(白话)为基本的立足点,在世界范围内恒定“汉语新文学”的成就,考察其演变轨迹。这看上去很符合全球化的时尚与潮流,但在这概念背后,恰恰有着另外一种怀抱,这也是这一概念最让人心动的地方。朱寿桐教授在解释为什么要写一部《汉语新文学史》时说:“目的不仅不是所谓的‘消弭国族意识’,而是相反,要从世界汉语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突出和确认习惯上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部分,从而有效地凸显出处在现代化变革中的中国本土文学建树和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主流地位和先导地位。以此为核心,理清汉语新文学向台港澳以及海外辐射的层次序列。”(朱寿桐《汉语新文学史编写指导思想》,电子稿)这样一种诉求,体现了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也符合汉语新文学的发展实际。尽管长期以来不断有人批判华文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中心/边缘”模式[2](P4-5),但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华文文学无论是在汉语的使用上,还是在文学思想和审美风格的追求上,都体现出了大陆主流文学的辐射作用。当然,这里也确实存在着一个互动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不断汲取异域质素,并向外扩张,这可以看作是一个不断向海外华文作家靠拢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夸大这种靠拢的力度和影响。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虽然追慕西方,但归根结底它是一种植根于本土文化、应对中国现实的文学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脉传统,然后再不断地向外辐射产生影响。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汉语写作中的核心地位是历史铸成的事实,尤其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的汉语文学与五四以来的大陆新文学更有着密切关系。一大批现代作家曾经辗转于这些地区,直接将新文学的传统带到了这里,培育了一批新文学的作者。以台湾为例,当五四文学革命爆发之后,一些留日的台湾学生于1920年创办了《台湾青年》,引发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1923年,东京又出现了《台湾民报》,报纸采用白话,宣传大陆的文学革命。所以在海峡两岸,文学呼应联动,而大陆往往处在领先的位置;香港的情况与台湾也十分相似。而身居异邦的华裔作家,每每魂系祖国,关注着大陆的变化,并将所思所感渗透到他们的创作之中。所以中国本土即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根基,也是他们情感和思想的泉源,其位置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汉语新文学史”可说是整合世界汉语写作的一个理论平台,它不仅有助于对已有文学的研究,对世界汉语写作的发展也一定会产生某种深远影响。
还应看到,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某些汉语写作,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即使一些发达的地区和国家,汉语写作也常常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在作家所隶属的国家里,这些“外语”作品难以广泛流传,也很难进入主流文学的河床;而大陆的读者因为生活环境的隔膜,对他们的创作也常常难以亲近。在学术界,尽管华文文学研究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但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广度上,都还有很大差距。而且,研究者也往往条块分隔,有人倾注一生精力研究马华文学,有人集中研究美国华文文学等。研究者盯着一个地域,往往容易忽视世界其它地方的汉语写作,把这一地域看作一个独立的整体,去探求文学发展的脉络,评估其成就等。在我看来,研究海外某一地区的现代汉语写作,如果没有大陆现代文学为基本的价值参数,没有把世界其它地方的汉语文学作为参照,那就很难得出中肯的结论。而汉语新文学史正弥补了这一不足,它试图以大陆现当代文学为中心,建构一个世界现代汉语写作的整体框架,这样一个框架可以有效地研究、析示文学的内在价值和外在风貌。这无疑会避免一叶障目的局限和尴尬。
提出“汉语新文学史”这一概念,还将意味着对汉语的重新理解和定位。当今世界,汉语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边缘的语言(尽管这种趋势正得到某种程度的扭转),且不说互联网上通行的英文,就在中国教育界,英语已经成为中国人获取个人前途和利益的必备手段,中国人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往往是汉语的几倍,而汉语则变得无足轻重。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提出“汉语新文学史”的概念,对重新认识汉语的思想史意义也十分重要。对中国大陆的作家而言,用汉语写作顺理成章,没有太多值得追究的复杂内含,而对身处海外、熟练掌握外语或以外语为母语的华裔来说,用汉语写作,就成为一种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抉择。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是存在的家,所以海外华裔选择汉语写作,就是一种文化姿态,说明他们的心中永远有着一颗不死的灵魂——汉字。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民族,始终在用这样一种文字来书写自己的历史,他们的集体记忆、情感和思想都隐含在这些象形文字之中。所以,当他们写出一个个汉字的时候,就是在与自己的祖先对话,就是在体验着一个民族数千年来的艰难和悲悯。这样一种写作所承载的意义,值得认真考析。
当然,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汉语新文学史”还需要进一步的阐释和论证。就像过去的“华文文学”隐含着诸多的理论陷阱一样,“汉语新文学”也许有着很多需要进一步论证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这一概念的边界问题。汉语新文学史以“汉语”作为遴选论述对象的惟一标准,必然就面临着一些难题:如非华人、华裔用汉语创作的作品,是否列入论述范围?海外华人、华裔多用双语进行写作,那么在对他们进行论述的时候,若只关注他们的汉语作品,又如何能够理解其创作的全貌?但我认为,每一个文学史概念,都有一个模糊的边界,如何取舍,决定于文学史写作者自身的评判尺度。任何一个文学史写作者,都不会过于拘泥概念本身所决定的论述对象,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气度,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划定论述的范围。所以,“汉语新文学史”这一概念边界的模糊性,反而给文学史写作者留下了自由取舍的空间。就像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郁达夫、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海外创作纳入论述范围,将林语堂、老舍等人的外语作品也作为研究对象一样,文学史写作者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是不会被概念本身的局限性束缚住手脚的。
其次,是这一概念中的“汉语”一词隐含的语言学背景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汉语新文学史将“汉语”置于词首,目的是要考察文学史的语言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汉语新文学史”不是“新文学汉语史”,所以这里的“汉语”仅仅是为了确定文学的语言形式,并非为了对文学进行语言学考察,语言问题应不是这一文学史概念的核心问题。
当然,这并非说这一概念就完美无缺了,事实上它自身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这里的“汉语”和“新文学”两个词汇,就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在中国大陆,“新文学”专指五四之后的现代白话文学,是与“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旧”文学)相对使用的概念。当“汉语”一词被置于“新文学”之前的时候,“汉语”就变成了“现代白话”,这在中国大陆很容易理解,也是不言自明的;但一旦离开中国大陆,尤其到欧美地区,这样的“不言自明”就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在远离中国大陆的地域,汉语写作并不截然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部分,文言与白话也不像在中国大陆一样出现过明显的两军对垒。所以,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所谓“汉语”(白话)“新文学”有时候可能会没有着落,成为缺乏实际意义的“先入之见”。从已出版的《汉语新文学通史》来看,有关大陆以外的部分,着重论述的是在大陆辐射区以内的台、港、澳及东南亚地区,至于欧美等地的汉语写作只在最后一章中稍作论述,由此就可看出这一文学史框架在兼容性方面的不足。
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但“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仍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对推动文学观念的更新,对探求新的文学史写作的思路,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