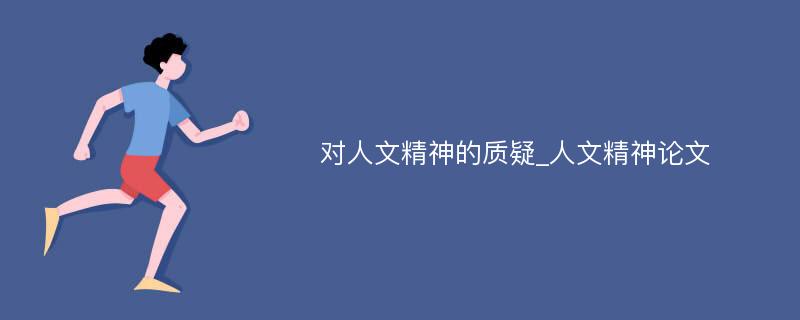
人文精神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人文精神”的提法颇为模糊,歧异,人言人殊,但关于它的讨论在文学界已持续了一年多,说明它毕竟碰触到了我们时代最迫切的精神问题。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场讨论又似乎很难深入下去。我在读了一些讨论文章后,困惑与疑窦日增。我感到,有些众口一词的判断好像并不是从当代复杂的生活实际和文学创作的基本事实中生长出来的。倒更像是一种先验的预设和高悬的条律,一旦离开了真实的文化背景和作家必须直接面对的创作问题,讨论就难免不在抽象精神的迷宫中捉迷藏了。我还担心,由于判定文学高低真伪的标尺据说是有无“终极关怀”,凡不“终极关怀”者即被归入俗流,而能够领到“终极关怀”入场券的人又微乎其微。广大的作家和读者会不会因事不关己而茫然木然?目前,参与争论的人已渐趋定员化,圈子不大,能不能使讨论更深广也更切实一些呢?我希望讨论的视线再开阔一些,离老百姓的生存和当代文学的实践再贴近一些。也许就更“人文”一些。这里,作为一个争论圈外的读者,我愿把我的困惑和想法陈述出来,以就正于“人文精神”的方家。
一、背景的意义
首先要充分肯定人文精神问题提出的合理性和适时性。不能说过去的文学界没有关注过人文精神,也不能因为没有使用“新人文主义”,“新理性精神”,“新理想主义”之类的新术语而看不到文学界曾经表达过的重建价值,呼唤理想的热望。但在今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提出问题,却有着全新的意义和历史与文化的新的冲突内容。不过,能敏锐地提出问题,未必能深刻地意识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也许问题是对的,藉以提出问题的依据是偏颇的。比如说,你可能因为某些文人面对市场的无操守所激起的义愤而提出问题,也可能因眼见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部分事实而提出问题,还可能因为文学的客观发展与你心目中的文学蓝本大相径庭而提出问题,这些都是可以理解并予以尊重的。然而,文学的发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人文精神的矛盾为什么日益突出了,我们今天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座标和向度上提出人文精神问题的,这些,却是我们不可不追问的第一个问题。
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是:之所以提出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乃是因为九十年代的文学“后退”了,“有一种共同的后退倾向”,“精神立足点”后退了。既属后退,指的自然是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后退了。的确,当前的文学存在着种种可忧的、可气的、棘手的问题,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时代,总体上还显得被动,一些重大的时代精神问题和现实矛盾,未能进入作家的视野,它缺乏清醒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对民族灵魂的深刻思考,它也缺乏参预现实干预生活的主动姿态和充满热烈爱憎的主体精神。但是,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就叫“后退”,在我看来,与其说九十年代的文学后退了,不如说它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随着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以不同于往昔的姿态进入市场,其生态环境变了,背景变了,其内在精神、结构和功能也不能不发生若干变化。不是有个“精神立足点”的问题吗?九十年代文学的立足点不是简单的“后退”了,而是“位移”了,只是很多作家尚未意识到或者尚难把握罢了,而这恰恰是需要大力倡导人文精神来加以改观的。
八十年代文学确有许多令人留恋和自豪之处。从总体上看,它是充满生气的,由于全民族刚从“文革”的噩梦中走出,它的精神主干还是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它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强烈,它进行着深沉的政治文化反思,它为恢复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而呐喊,它与解放生产力相适应,反封建、反封闭、反禁锢,充满改革开放的气息,充分肯定人的感性欲望和个性人性意识的觉醒。我们可以随手举出像《芙蓉镇》、《乔厂长上任记》、《绿化树》、《活动变人形》、《厚土》、《古船》、《人生》、《你别无选择》、《浮躁》、《烟壶》这样的作品,它们无不典型地代表着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然而,当我们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以来(市场经济是比一般的历史分期重要得多的分界线),我们发现世界和文学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就世界范围看,被称为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冲突渐趋平和,文明的冲突却加剧了,一度掩盖的文化意识问题更加突出;就国内情况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一切,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冲突日趋激烈。为了抗拒物化,人们已痛切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于是,有人在着手整理“文明的碎片”,有人严峻地审视家族文化,有人到宗教的心灵史中去寻觅反抗异化的武器,有人则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寻求灵魂的寄托,“国学热”方兴未艾,关于“新儒家”的争论日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已成为最重要的话题。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主要面对的是政治文化的挑战,九十年代文学就主要面对的是经济文化的挑战,八十年代文学主要面对民族国家因历史政治所形成的独特主题,九十年代文学的主题就确乎有点国际接轨的味道,力图超越物欲和感官的压抑,追寻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努力,是更能与世界文学对话和交流的(“后现代”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大约也与此不无关系)。我想,这才是我们在今天提出人文精神问题的真正背景。物质在发展,精神也在发展,用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标尺来应对九十年代大大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创作问题,是不现实的。更何况,文学界也一直没有放弃精神追求,从“文化关怀小说”、“新市民小说”、“新体验”、“新状态”等等的提出,不难见出这种努力。转型期新人文景观的生动展现,不是遥遥无期的。
二、内涵的追问
欲使讨论深化,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什么是我们需要重建的人文精神,或者说,失落了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在现在的一些讨论文章中,我们只能捕捉到诸如理想、良知、崇高、正义、终极关怀一类的字眼,倘要深究起这些字眼后面的具体涵义,就不得要领了。当然,要建设与市场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人文精神谈何容易,那是极其复杂艰巨的重任,单靠文化自身尚无法解决;但我们也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些美好的字眼上,满足于表面的热闹,不触及问题实质。我们总得设法靠近人文精神本身。比方说,理想是美丽的,伪理想却是要不得的,那么什么才是今天坚实而绚烂的理想?崇高是可敬的,伪崇高却是误人子弟的,那么什么才是令人神往而感动的崇高?当然,它们都不应是单一的,而是多姿多彩的。我想,假若我们能够进入精神生活和创作实践的内部矛盾去展开艰苦细致的辨析,而不仅是站在问题的边缘上呼吁,这场讨论将会有意思得多。
曾有同志认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人文精神”,何来失落?这是就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外来词源而说的。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运动确实从未发生过,也确实没有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跑出来,领导一场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人学反神学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就没有广义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事实上,中华文化是非常注重人本、民本的文化,其人文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人文精神决不是洋人的专利。据查,连“人文”一词早在“易经”里就出现了,所谓“刚柔交错,天文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于天文以察时变,观于人文化成天下”,可见我们比洋人的“人文”早得多。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有人文精神的传统,而在于我们今天怎样继承和扬弃,吸纳和重铸,从而建构新型的现代人文精神。应该看到,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信仰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即使粗略分析一下也有几大板块:一方面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近代价值观的流播,这些年意志哲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新托马斯主义的影响力不容低估,另一方面是支配人们行为几千年的传统人文精神仍在起作用,这包括儒道互补的正宗文化和许多民间民俗文化;最重要的当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革命传统,这是主导方面。试想,在这些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冲突和交汇中要建设起我们丰富多样的、优美高尚的新人文精神,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操之过急,或呼喊几声空泛的“理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比较起来,在人文精神问题上,哲史界要比文学界踏实许多。它们没有停留在空谈人文精神上,而是认真辨析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对已有的或现实的思想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研析,这就易使讨论落到实处。举例来说,虽然他们认为本质上属于封建文化和小农经济文化的传统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不合拍,难相容,但也不是没有宝贵的可用成份,有人举出明人伦,讲执中,求致和,举出诚信,得仁,重义,认为这些大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传统馈赠给现代化的一份厚礼。也有人重新界说家长制是否导致腐败,血缘文化是否导致腐败的家族化、裙带化,官商不分是否给中国式的贪污开了方便之门等课题。凡此种种,说明这些研究者没有把人文精神当作死物,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讨论它的发展。文学界可没有这份耐心,我们绝少看到有文章对某部作品的人文精神进行解析和梳理,看到的多是义形于色的激昂或旋点旋飞的潇洒。
文学界的讨论,对传统部分基本置之不顾,对现实中的人文精神问题又怎样呢?我认为,因道德义愤而影响视力,干扰判断的情况是存在的。有些朋友在谈到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问题时,表现出绝对化、二元化的偏激,好像市场是一切精神下滑、道德堕落的渊薮,在它面前决不能投降、妥协、失节。本人对市场也怀着恐惧,对市场时代一些人的败行深感忧愤,但想一想计划经济的大一统时期,我们今天毕竟从单调而多样,从空空而务实,从百花凋零到五色杂陈,从唯意志论到承认发展生产力是目的,从萎缩、依附、忍从到渐渐生长出独立人格。当然,与此同时,市场的“恶”和负面也在日益暴露。我们总得把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区别开来,不能因为几个文人放利偷合,良知泯灭,洗出一身污水,就连市场经济一起冼掉。我们的人文精神要真正富有感染力,是不能脱离市场经济背景的。讨论中的另一偏执也很触目,那就是靠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老思维模式。有些逻辑很是不通:文学不景气,就把责任推到搞评论的朋友头上,社会风气不良,又把罪衍加诸文人的操守不好。文人自己有了这种以身作则、满怀忧患的精神当然好,但要真正解决问题,途径不会这么单一。如果没有政治、经济、法制诸条件的支撑,单独的文化因素能起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更遑论文学。
但我还是非常赞赏一些朋友大呼猛进,倡言人文精神的激情,沉闷的文学界太需要振聋发聩的新声了。“精神萎缩症”也确实存在。为了疗救这种疾患,我主张宽容精神,而不是“拒绝宽容”,应该让文学的精神空间无比广阔,只要不失其审美特性,应该允许各式各样的眼光、视角、价值立场的存在。文学的人文精神应该比人文学者的人文精神更宽泛、更丰富,艺术家应该比科学家的个性更缤纷。你可以持历史的尺度写得冷静而理智,我也可以抱道德的爱憎投去批判的冷眼,你热衷文明的喧嚣,我偏要回归自然,你沉缅于世俗的欢乐,我神往于宗教的高洁,你隐人历史的暮霭,我迎着现实的太阳……这一切不但允许,且越多样越好。问题是,现在有种“终极关怀”崇拜,大有以“终极关怀”与否划线的倾向,这就又有点不宽容了。“终极关怀”一词的出处我还不太清楚,大约源自宗教教义,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去关怀人,也即人文精神的顶峰。要求所有的作品都“终极关怀”是不现实的,也是奢侈的。我是比较相信马斯洛的塔尖式的“需要说”,也相信老祖宗的“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对一个饥饿的农夫来说,你一手拿着“终极关怀”,一手拿着馒头,我看他还是首先要馒头。文学也分层次、也是多功能,如果认为只有表现了塔尖上的需要的文学才是文学,文学岂不显得太清冷了么。
三、文学的时态
看一些讨论文章,我最不解的是,有些人几乎不由分说地对当前文学现状采取了近乎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近年来的文学迷乱、颓败、下滑、后退、庸俗、浅薄,根本没有人文精神。在一些论者笔下,文坛到处是媚俗的嘴脸和堕落的身影,一片荒芜,没有什么作品可看。当年的“样板戏”尚且有八个,如今只剩下两个作家,这好像已是毋庸置疑的定评,立论的基础,驳论的起点了。事情真的糟到这种地步了吗,人文精神真的已经丧失殆尽了吗?
前面说过,我对当前文艺创作的现状也不满意,但我同时认为,不能忽视近年来众多作家为重建精神价值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他们的成就和不足尚未得到认真总结,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遇到的真正难题,也许对未来文学的生长和发展很有参考价值。如果把人文精神的标准定得过于高玄,能够寓目的作品自然极少甚至没有,如果不那么高不可攀的话,人文精神丰沛不丰沛、深刻不深刻的话题也就变得可以讨论了。
在我看来,近年来的文学中人文精神不但有,还很不少。这就牵涉到怎样理解人文精神了。我想,所谓人文精神,核心应该是人,是对人的关切,尤其是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无告的人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是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的关切,舍此之外到哪里去寻找人文精神呢?倘若文学不能反映人民大众最迫切的愿望,不能对时代最重要的精神问题发言,人文精神就会落空。就拿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小说而言,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风景》的作者对河南棚子里“贱民”所倾注的同情和怨责,能说没有人文精神吗?《烦恼人生》写一个普通工人的生存窘境,能说不是人文精神,《单位》、《一地鸡毛》都很琐细、麻烦,其中有没有人文精神呢?近年的长篇里,《曾国藩》剖析了一个“三立完人”的人格结构和文化人格,《白鹿原》正面观照家族制度和宗法文化,迸而探究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命运,它们有无人文精神无需多言。事实上,近年来的文学外观平静,内在结构则变动剧烈。一部分作家经受了由中心而边缘,由上层而下层,由先生而学生的变化,强化了平民意识,平民视角和体验性,而在都市、乡土、历史、知识分子等题材领域,都有新的萌芽增长,作家们对新的市民意识的描写,就含有新东西。至于文化视角的广泛运用,整合趋势的出现,都还没有得到认真梳理。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当今的文学好得不得了了,相反,我认为它有明显的薄弱和严重的缺憾,但我主张,人文精神只能在生活实践中建设,文学也应该在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寻求出路和发展,而不可将自身封闭起来。王晓明同志认为,今天的文学要发展,“有一条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回到真正的纯文学传统”。晓明写过不少优秀论文,我很看重他的观点,但他的这一看法,却是糊涂的。什么叫“真正的纯文学传统”,怎么个“纯”法呢?若说非功利的艺术精神,我可以同意,无奈这里真正“纯”文学的含义是剔除非文学的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等到把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市场、社会问题的因素全剥离光了,还剩下什么呢?曹雪芹“纯”吗?并不。鲁迅“纯”吗?也并不。鲁迅曾针对朱光潜所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说道:“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恕我直言,在古今中外第一流伟大作家的行列中,是从来没有“真正纯文学”者的位置的,他们中的佼佼者,顶多只能达到二流水平。
人文精神当然不止表现于创作,它同时表现于作家和文人的人格精神,品性操守,道德理想,这方面我很赞同许多论者的“不投降主义”。我曾表述过大致相同的看法:“负荷沉重的现代作家,既无法摆脱锱铢必较的市场的笼罩,也不能脱离现代人文环境而遗世独立,他们怀着比古人更发达的七情六欲,注定了要在物质与精神的二律背反中忍受更大的煎熬。然而,他们的存在困境又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如果他们坚持不让物欲主宰心灵,并且深刻地写出了人们挣不脱物欲的痛苦和反抗物欲的勇气,他们就展现出古典作家不曾有过的现代魅力,就在通往终极关怀和人的自由的路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蔓丝藉实》19)。这段话正可作为本文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