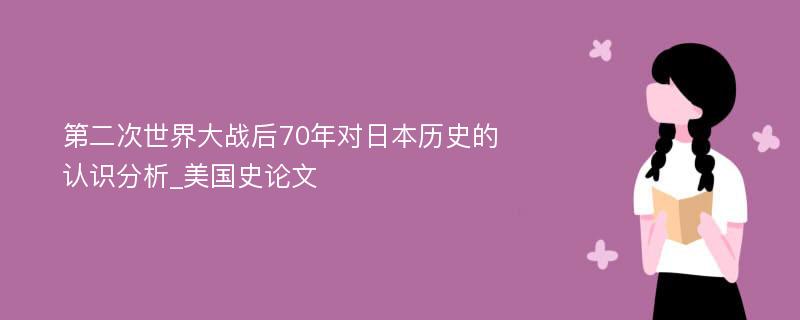
战后七十年日本历史认识问题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七十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七十年来,中日虽有近半个世纪的邦交,却未能在实质上消解黄遵宪“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的感慨。①尤其近十年来,中日每次发生纠纷,中方媒体和民众的愤怒与普通日本人的反应之间,总会呈显出一道不甚对称的“风景线”——他们对侵华战争的近乎无知甚至一脸“无辜”,让中国人对日本人无视血腥和淡忘罪恶的史观大为错愕。由于近年来日本当局不断在中日之间拨弄是非,且有意无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因此,一位外籍华人在愤懑无奈之余竟主张要反躬自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②其不乏情绪化的系列问题中或许隐含着各种答案,但对中国学者而言,认真研究战后日本的历史观念及其演变辙迹,才应该是更重要的: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却要知道它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终究是不可能的。 一、临场体验下的细微观察 实际上,比起管制并改造日本达七十年之久的美国,我们对日本的真实想法及其由以发生的社会环境,还缺乏动态的把握、详细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这也许不怪我们:素以侵华和反共著称的日本,把战后的一切——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素颜,全部托付给了美国而不是中国。然而,战败初期,日本面临的生存危机和举国失序乱象,却一点也不比德国好。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写道:“满目疮痍的国土、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与支离破碎的梦想”,当然,如果“我们从战败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将会学到更多:不仅是悲惨、迷茫、悲观和怨恨,还有希望、韧性、远见与梦想”。这促使他“试图‘从内部’传达一些对于日本战败经验的认识”,进而“关注这一进程中最难捕捉的现象——‘民众意识’”,亦即“试图通过还原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声音获取一种认知,即:在一个毁灭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③ 日本人在形容战败瞬间的国家情状和国民心理时所使用的“举国虚脱”和“茫然自失”语词,曾经以“潘潘”(パンパン,美军慰安妇与街头娼妓)、“黑市”(闇市,私人不法市场)和“粕取”(粕取り,酗酒浇愁)等绝望生存实况,展示给世人。昨天还信誓旦旦要“一亿一心”和“一亿玉碎”的天皇效忠者,一夜之间变成了利己主义和败坏风纪的典型代表。④除了无知尊皇者的切腹自杀和激烈如太宰治等自害自毙者外,大部分日本人选择的是如何迅速洗心革面、告别过去,以示“辞旧迎新”。对此,官方“一亿总忏悔”或“全体国民总忏悔”令⑤的发出时间,与老百姓的疾速转向,几乎同时发生。由于其中真情和表演都有,所以,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多少被日本人的妩媚所“迷惑”和“诱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已经无法从中看出更多的表演成分——他们宁可相信日本人的眼神和表情全是真的,因为这至少可以满足美国最想扮演的解放者和救世主心理。⑥与此相应,日本人的说法和做法也似乎变得更加乖巧,其拥抱占领军的程度甚至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在战败前一刻,还是“鬼畜英美”骂个不停的死硬分子。 1942年,日本画家加藤悦郎曾把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下半身描绘为野兽,并将亮闪闪的日本刀戳在他们的屁股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居然一夜之间就把可憎的敌人变成了解放者,其变化之遽,几乎不需要过程。与此同时,许多前帝国军人竟自发地向美国人揭露曾经虐待过盟军战俘的日方人员,而那些未能按照盟军最高司令官命令上缴私藏家传刀剑的人也频遭举报。有些人来信说,天皇才是日本最大的利己主义者,是个“吸血鬼”;另有人写信要求,日本至少还有十万军国主义分子应当被处以绞刑。最令道尔感到吃惊的信件,竟然是来信者迫切要求日本被吞并,或者成为美国永久的殖民地。他们断言,不如此,则美国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将很快破灭。然而最有趣的还要数道尔的以下记录:“(这些信)暗示了占领的潜在的——有时也不是那么隐蔽的——性的维度……在这点上,最露骨的是一些女性写给麦克阿瑟的独特来信,被困惑的专家们分析为‘我想给你生孩子’的类型。在这里,拥抱征服者的愿望,如果不能在现实中达成,至少是在字面上实现了。”⑦当这些一时还“分不清楚接受麦克阿瑟、接受家长制的权威与接受民主之间的区别”的草根式反应,经过日本的“头脑们”——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思考后,一系列不乏理性色彩的发言似乎给战后日本如何走出困境提供了某种具有内在说服力的方向性指导。于是,道尔想到了“进步的文化人”丸山真男及其所谓“悔恨共同体”。道尔认为,对于许多像丸山这样的学者和文化人而言,战败与被占领,包含着对未来欣喜的期待,还掺杂着对过去深深的悔恨。这也是他们何以会决意重新开始,并将占领军当局“配给的自由”变成自发拥抱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原因。当然,道尔也同时指出感情与理性即便在知识人身上也未能完全剥离的事实,他甚至暗示,所谓“进步的文化人”的上述转变,其实也反映了某种不得已心态。⑧ 然而无论如何,战败初期的日本,无论是官弁走卒,还是知识精英,几乎均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让美国人“震惊”的价值转向:“战败显示了多年来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竟然可以被如此迅速地丢弃。”⑨可是,这同时也使学者们特别是那些穷年研究日本学问的专家的学术观点和智库建议,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对日政策制定上,显得有些多余。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麦克阿瑟的政策出自哪个学者或哪家智库之手。据称,1946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版的成名作《菊与刀》,曾直接决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策略。但是,人们除了发现其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想法发生某种巧合的一致性外,却无法找到麦克阿瑟参考过该书的直接凭证。事实是,“标志着保守的日本专家失去权威的时间,可以被精确锁定”,即“1945年8月11日”。这一天,美国国务院为麦克阿瑟指定的第一位政治顾问,竟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而非国务院的资深日本事务专家。在此后数年间定期往返于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顾问团中,也很难觅到日本专家的影子。有资料证明,麦克阿瑟从不与日本人交往,也不听学者之言。据他身边的一位人士说,只有16位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麦克阿瑟只是通过一些由美国军方摄影师拍摄的关于日本的新闻纪录片,使他至少在银幕上跟他所统治的国家保持联系。除了情报机关提供的报告书外,他并没有涉猎过有关日本的书籍,也从不向部下询问有关日本的问题,当然也不从日本人那里寻求情报。当一位在德国出生并且只在德国受过教育的法学家前来应聘监督日本全部民法和刑法的修订任务时,曾谦虚地对统帅部一个陆军上校说:“尽管我精通欧洲事务,但是我对日本的情况毫无所知。”上校的回答简直可以用“意外”来形容:“噢,那样正好。如果你对日本了解得太多,你可能就会有成见了。我们不喜欢日本问题的老手。”道尔在分析麦克阿瑟所谓“有华盛顿、林肯、耶稣基督、他,再加上天皇的帮助,就能将日本民主化”这一说法时指出:“尽管可以将麦克阿瑟的这种信念归为偏见、假设和陈腐的豪言壮语的混合,但是它却没有受到日本或亚洲问题专家们的干扰。”⑩他暗示,如果仅仅听凭某些人的评价就断言麦克阿瑟全然不了解日本,那就过于冒险了。事实上,前面所揭示的日本人战后表现诸相,已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对自己治理对象的细微了解、渊博学识、自我改变及其独有的事物掌控能力。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获得支持。(11)1945年10月中旬,一位访问东京的特使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称:“(麦克阿瑟)将军声明说,东方人具有一种自卑情结,使得他们在战争胜利时会‘像孩子般的残忍’,在失败时则会像奴隶般地顺从和依赖。”(12)有关“孩子”的说法,还出现在麦克阿瑟的另一个发言中。1951年5月,在美国国会举行的长达三天的听证会上,统治日本近6年的麦克阿瑟,一方面赞美了日本,认为单纯的日本国民比老道的德国人更可信,但同时,他也十分感性地宣称,在现代文明的标准下,如果45岁是一个成人的年龄标志,那么,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却很像12岁的孩子。话语间或许没有贬低日本人的用意,因为在他看来,小孩子的头脑中没有固定的思维框架,这样才容易从零开始,学习和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世界规范。(13)但日本人的反应显然比较激烈,他们甚至动用广告为自己证明,说“我们不是12岁的孩子”!(14) 二、复杂而离奇的反省装置 1946年2月2日,麦克阿瑟把一张纸条交给民政局局长惠特尼。这张被称为“麦克阿瑟便笺”的纸条,日后成为日本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并最终凝结为“和平宪法”最核心的第九条。(15)尽管不拘小节的美国人以这种传纸条的方式决定了日本的未来,但经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颁布的新《日本国宪法》给日本带来了巨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由于非战条款的最初建议者是时任日本首相的币原喜重郎,(16)因而直到今天,当有人要对“放弃战争”和“否认交战权”等日本新宪法第九条提出反对甚至修改意见时,都会遭到严守宪法和爱好和平的广大日本民众的抵抗和奋争,表明此时的日本与往日穷兵黩武和侵略成性的“帝国”相比,已呈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7)但是,正如《菊与刀》的作者试图以“耻感文化”来总括日本国民性的做法有些书生气一样,麦克阿瑟给日本人的“12岁”定性,也不乏政治天真。这两种失之简单的评价,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战后日本人“从善如流”态度的廉价好感。在不排除相当多的人对战争深表悔恨的同时,研究者却不可低估潜伏于某些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另一价值指向。由于保国保种才是战后日本的头等大事,因此,美国人从这个战败国脸上所能看到的表情,事实上充满了求生本能下的保护色。丸山真男曾将政府发出的“一亿总忏悔”令,戏谑为乌贼鱼遭遇险情拼死逃生时所喷出的“墨色烟幕”。(18)而美国占领军对这一现象的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无视,还表明“耻感”与“12岁”形象,不过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美国人的期待与日本人的迎合之间所形成的默契。这意味着,一个同样影响到今天甚至可能演变成日本思想主调的“无罪”低音,也将通过从“加害”到“被害”、(19)从“大东亚战争”到“太平洋战争”、(20)从“法律审判”到“政治审判”的严重误导,(21)逐渐赢得从暗颂到高歌的时间和空间。它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本的学术界,包括对战争有过深刻反省并号召日本人民“脱胎换骨”的学术大家。 1942年,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等人提出了“近代的超克”的命题,其宗旨是克服欧美文化,从欧美的“近代”中解放亚洲并最终肯定“大东亚战争”。对这场讨论兴趣浓厚的竹内好,本是一位学界公认的中国学和鲁迅研究者,也是对中国革命抱持相当同情的日本思想家。他用“大东亚战争”而不用“太平洋战争”称谓的行为,或许有反对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神道指令”并提醒日本不要忘却侵略亚洲历史的正面用意,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同时对“近代的超克”命题寄予超常的热情。这种矛盾决定了其有关中国说辞的拗口和怪异:“作为存在物的支那终究在我之外,但因为在我之外的支那是作为应予超越的存在在我之外的,所以在终极意义上说它必须在我之内。自他对立毋庸置疑是真实的,但这种对立只有在成为我的肉体痛苦的时候它才是真实的。就是说,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被否定。”(22)有学者指出,“右翼思想”几乎贯穿了竹内好战前战后的学术活动。L.奥尔森甚至认为,竹内有将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予以合法化的倾向,其中国论的理论基础则是亚洲主义。(23)竹内氏忽左忽右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显然不易使竹内本人被简单地定性为左翼或右翼。早在1948年,他曾通过鲁迅研究而严厉地批判过日本的“脱亚”式近代主义,并将亚洲的未来寄托在中国身上。(24)尽管如此,关于日本对外战争的认识问题,却已在他发表于1959年的长文中,有过相对定型的表述,即“大东亚战争,既是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尽管这两个侧面事实上已被一体化,但我们却必须对其做出逻辑上的区分。日本并没有要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它虽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殖民地,却并无夺取荷兰本国的想法。由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由帝国主义来裁判帝国主义,也同样鲜存可能”。(25) 也许不是偶合,作为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沟口雄三教授曾对中国近代化运动所开辟的有别于西欧和日本的第三条道路——“王道式近代”,给予较高的评价;其以“日本知识分子的良心”承载者身份广泛活动于中日学界的学术形象,也时令中方学者和普通民众感动有加。(26)但是,这一切似乎同样无法构成他在战争性质解读上的任何妨碍。所不同的是,与竹内好不承认“帝国主义裁判帝国主义”的合法性却认可“大东亚战争乃殖民地侵略战争”的战争表述有异,沟口教授在谈到1931年以来的侵华战争性质和1945年向谁投降之“意义”等问题时,却巧借“日本人”或“某些日本人”之口,提出了他本人的疑问,并给出了离奇的解释和意外的答案:“我们日本人对于战争要谢什么罪?谢罪到什么范围?是仅就残酷暴行谢罪,对出兵侵略中国本身谢罪,还是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全过程谢罪?可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过程就这样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罪孽,这难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吗?”当说到南京大屠杀中死亡人数是否成立时,他还制作了一个离奇的“比喻”:“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入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士兵。这个比喻揭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于是,“南京大屠杀‘被害者三十万’”的说法,就成了“复杂的政治性数值”,而这一“数值”又“足以显示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通,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27)他大概想说明,既然与战争有关的“明治维新”是东亚公认的文明进步事件,既然战争的后果已被解读为“政治性数值”而不是“事实性数值”,既然要求谢罪者的谢罪根据只出自“感情记忆”而不是“事实记录”,一言以蔽之,既然这一切都发生于“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之“认识上的错位”,那么,侵略一方便无需对被侵略者谢什么罪,无论是代表“近代化”的日本历史“全过程”,抑或“两米高”士兵的“强奸罪”与“三十万人”的屠杀罪等,似乎均应作如是观。这一理论装置,与部分日本学者研究中日战争时的惯用常套之间,似乎已不分轩轾,即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其中,最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利用“近代文明”之“善”来消解对外侵略之“恶”的学术手法。沟口教授的设问是:“为什么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呢?……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以近代化的迟早、先后为衡量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优劣标准的历史,而且,基于这种历史意识上的记忆仍以现在时态存在着。”于是,“不管中国人是否意识到,通过控诉日本人的残酷暴行,中国人是在对从自尊心上无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优越意识之傲慢进行焦虑的抗议。而且,当中国人站在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上,身处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的优越性这一两难之境时,则更加焦虑。所抗议的对象轮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议之矢不知何时如同‘归去来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这时其焦虑便越发严重。”(28)在如此框架下再来讨论谁是战争的受害者,则片面的“历史健忘症”在战后日本人身上周期性发作的反应频谱,也就不再难以捕捉,即比较起“南京”,他们只记住了“广岛”;相对于日本对亚洲的涂炭,他们只记得“下町烧夷弹”和“东京大空袭”。于是,在讨论战争胜负时的以下说法,在日方看来似亦不违逻辑:“日本是与欧美对抗、与欧美争战,最后败于欧美特别是美国,而非败给了亚洲。”惟此,一连串潜在的反问也似乎同步成立:既然日本自己才是“受害者”,又怎么可能会变成“加害者”?既然日本没有败给亚洲,干嘛要向亚洲谢罪?既然“帝国主义无权裁判帝国主义”,那么除了实力不逮于其他列强外,日本人又错在哪里?这些反问仿佛在提醒那些曾与日本交战过的相关国家包括英美,你们其实并不了解战后日本人的复兴动力和真实想法,即日本人的上述质疑,“同时也成为从战败中站起来之不屈精神及国民困苦与勇于奋斗的象征。而诱导这些思考的就是关于近现代的历史认识”。(29)他试图在帮助中国人逆推:被强奸少女对施暴者身高的放大,只表现了中国人的群体性“被害妄想”;而在“事实记录”的强调下,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三十万人的问题,似乎也应在“感情记录”的归谬中讹为虚诞。在“定量”不等于“定性”的被害国呐喊声中,日本或许会一时谢罪,但这种谢罪好像也很难逾越沟口教授的“坦言”范围:“日本人就本国的侵略行为向中国人谢罪,并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中日甲午战争这一事实进行反省时,即使未必是有意的,但仍是以‘资本主义化的成功’这一优越性为潜在的前提,而其谢罪本身亦是寓于‘谢罪之傲慢’这一认识中的。而就同一问题的另一面而言,中国人如果视日本的近代化为成功而给予肯定性评价,在逻辑上便完全可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从而使自己陷入两难之境。”然而,既然谈“逻辑”,并且假如是“学者良心”在独白,那么,沟口教授的上述观点或许只有在否定明治近代意义的前提下方能成立:“我很久以来就主张这样一种近代史观:以未受到欧美压力的16、17世纪为日中两国近代过程的起点,两国近代构造的架构在‘西洋的冲击’以前即已形成了”。(30)可由于这一学术假设不啻“以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而无奈之下假设者也只好去续写假设不成立时自己的真实反应了:想要日本人认错,恐怕还需要“少则半个世纪,长则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责任问题”而不是其他。(31) 三、潜之弥深的思想伏流 日本A级战犯对所谓“政治审判”的不服及其“无罪”宣言“遗产”,显然已衍生出为数可观的学术饶舌者,也消费了一大批强化“独立自尊”、“国家的品格”和主张“摆脱自虐史观”的御用文人包括他们的反对者。但是,如果仅凭这些现象就以为上述研究已触及到问题的本质,那就过于天真了。事实上,那些不动声色地潜伏于日本肌体中并足以规定日本人全部表象行为的非表象结构,才应该是战后日本人史观的终极制约者。日本学研究者神岛二郎在《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之开宗明义处指出:“我这里所提出的‘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问题,并不是现代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问题”,换句话说,“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个人的精神构造,而是‘现代日本’之‘集合主体’的精神构造”。(32)其中,他所提出的关于“非武装国家问题”和“单身者本位体制问题”这两点,需要研究者给予特别关注。 该文发表于日本战败后的第40个年头,也是日本“和平宪法”颁布的第38个年头。无论是战败的后果还是和平的要求,“非武装国家”的定位,对当时的日本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一在本质上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隐性强制与日本人主动表态之间所达成的不对等默契,在神岛氏看来却符合历史上日本的自身经验,并且是主动选择意义上的自身经验。这一看上去出人意表的讲法,依托的是下面的历史和逻辑过程:虽说日本国的非武装化条款是占领军统帅部的强制产物,但在该条款未尝废弃而新一轮武装军备已导致宪法空洞化的今天,非武装宪法的精神却依然存活于日本国民当中,并且国民也不会允许执政党自民党去实现已被提上日程的所谓修宪纲领。可当问及非武装宪法何以会落脚于日本时,佩林·诺埃尔(Perrin Noel)的《抛却铁炮的日本人:日本史中的军缩》一书,为神岛提供了历史性佐证:1543年葡萄牙人把步枪(鉄砲)传到种子岛后不到一年,日本人便仿制成功并迅速将这种新式武器普及到全国。在佩林看来,16、17世纪时,日本已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工业国,其产品的优质度不但远超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已凌驾于欧洲之上。尽管如此,当国内和平局面得到确立后,日本显然有意地关闭了这条迈向现代化军备的道路。直到黑船事件发生后,才接续起当年的能力,并且到1900年,其军事装备再度追赶上了西洋列强。佩林由此认为,日本人具有控制技术选择方向的能力:它可以完全中止兵器的发展甚至令其倒退,而将这种能力转向其他领域,并使之走向发达。这意味着,近代以降的日本尽管可以应对军事化时代的要求,但日本同时还有技术选择上的非军事化经验。神岛于是得出结论说,这才是战后日本可以选择并维护非武装宪法的历史远因。(33)问题是,这是否也意味着当某一天再有需要时,日本也会同样带着技术选择的基因式天分,在军事领域重新披挂上阵呢? 与“非武装国家”有所连带的关于“单身者本位体制”问题,还为神岛提供了另外一个对战后日本的观察视角。他指出,在前近代的家族走向崩解而近现代家族又无法成立的情况下,以往的组织形态只能转化成“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并逐渐演变成日本社会的现实。在神岛看来,近代日本单身者集团的典型体现,便是军队。近代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为止,日本之所以会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并迈向军国主义道路,都是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基础使然。战争的失败,固然使军国主义国家走向崩溃,但作为其基础存在的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却非但没有解体,反而更加彻底化了:战败前被编入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中的人员只有男子,可是战败后,随着占领军对妇女的解放,女子也颇具讽刺意义地被编入该体制当中。而且,相对于战败前的“国家”,战败后以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来彻底吸收社会成员的装置,则是“企业”。就是说,战败后,企业在吸收单身者的行为中已代替了往日的国家职能,其所带来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意味着,曾经的军事大国和当下的经济大国,其实是建立在相同的社会体制基础上的。值得注意的是,就社会将“家族”化为单身者本位的分解能力而言,企业比国家还要彻底,所谓“一亿一村”的说法,形象地道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实存状态。(34)然而,无论我们怎样观察神岛氏的分析,战败后的日本“企业”功能都容易被直观地解读为战败前“军国”结构的接收器。如果有人要继续追问:既然军国主义的国家组织形式可以轻易变身为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方式,并且这种变身还为日本国民日用而不知,那么,一旦当外部条件要求日本去实现“军国”对“企业”的“逆接收”时,坚持和平宪法的“应然”口号和实务主义的“必然”选择之间,还会形成持久的“张力”吗?由于这在神岛氏那里不过是一个“设问”,因此,他在总结自己的观点时指出:“因战败而理应回到原点的日本,却在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中再度挺立于文明的前沿。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日本似乎已不再是什么‘追赶’,而是步入了‘领先’的行程。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局面,亦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应该是支撑日本战争过程的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另一个则是非武装和平宪法,而且事实上是二者的乘积使然。但是,这两者也恰恰是相互矛盾的东西:前者优位,则后者必将改变;而后者牵制,则前者亦将倾覆。”(35)在神岛“变与不变”的两难构图中,日本好像随时都存在着被推向险境的可能。 神岛上述观点之矛头所指,显然是欧美世界。他所推出的一系列“事实”和“不得已”,试图收到足以让那些总想改造日本的欧美人对日本固有性格的“无可奈何”和“放弃努力”之功效。(36)不过,由此而呈现的“只看战后看不懂战后”和“只读历史读不懂历史”的研究方法,却为学界的历史反思和哲学建构提供了某种“型范”启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丸山真男及其“原型论”,应该是首次进行这种尝试的学术实践者。 被约翰·W.道尔誉为“进步的文化人”的丸山真男,曾经是战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他明确将反省日本国战败原因的焦点,集中于天皇的权力结构——日本“国体”上。在他看来,明治以降,作为兼具权威中心和道德源泉的“超国家主义”的核心装置——天皇体制,曾利用时间性的延长和空间性的扩大之巧妙逻辑,恶性发作为“日清、日露(日俄——引者注)、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等系列兵燹。从这个意义上说,给日本军国主义打上终止符的8月15日,也同时意味着“超国家主义”总基盘——“国体”的绝对性的丧失。(37)然而,由于日本所造成的空前巨大灾难总要有人负责,而且必须负责,因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丸山便明确指出:“我们日本人无论在何种意义或何种形式上,都要承认并担负起战争责任,而且要与责任者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对决。如果回避或隐匿之,那么和平运动也好,护宪运动也罢,都将寸步难行。”他认为,“一亿总忏悔”这一意识形态式的非白即黑转向和“二分法”的草率处理方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随意自我原谅与其实不思悔改之恶性循环,不要说在历史的理解上是错误的,即便对人们今后的思考和行动,也未必能发挥积极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要区别对待“统治者”与“国民”的主张固然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可以否定“国民=被统治者”的战争责任:对于外部,日本国民至少在给中国人生命、财产和文化所造成的严重破坏面前,不能全部免责;对于内部,倘若可以对“昨日”迎合邪恶统治者的国民免却罪责,那么,也就不要指望他们还会对“明天”的邪恶支配势力去作积极的抵抗。然而,在所有的战争责任承担者中,最应被问责的,乃是“天皇”和“日共”,特别是天皇。丸山指出,远东军事裁判没有对天皇问责,显然不是依据法律的结果,而是政治考量的产物。然而,一个作为“大日本帝国”的主权者、政权总揽者、大臣任免者、统帅权掌握者和终战决定者,居然可以对日本数十年政治进程及其后果没有责任,这即便在政治伦理常识上,也无法被接受。有人以政治傀儡为由为天皇开脱,但战争期间的天皇并不是傀儡。对一个并非傀儡的最高权力者免究战争罪责,那么,那些盲目盖印的大臣之责,又从何谈起呢?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天皇只负道德责任的论调中有哪些国际政治的原因另当别论,关键是日本人如何看待之。可怕的是,在国民的心目当中,天皇本身已被视为“非政治的”或“超政治的”存在。如果说,将自身地位粉饰成非政治存在却能发挥最大政治功能的手法已构成日本官僚制的传统机密,那么,这一机密的集中体现者,便正是位处官僚制顶端的天皇。这意味着,确认并继续追究天皇个人的政治责任,直到今天依然是剔除日本民主化之不治之症——官僚统治方式及其精神基础的紧要课题。对此,天皇承担责任的唯一方式,就是“退位”。实际上,天皇对皇位的蒙混恋栈,才构成了战后“道义颓废”行为的头等典型。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这种放任很快就可能变成不知廉耻的日本帝国诸神死灰复燃的先兆。(38) 然而,“非政治存在却能发挥最大的政治功能”这一独特的政治结构,与其说是“日本官僚制的传统机密”,不如说是日本传统天皇制特别是明治天皇以来日本国体的“机密”。该“国体”及其“意识形态”在战后的“一举崩溃”固然值得庆幸,(39)但天皇乃“非政治存在”的“无责任者”这一认识本身,已透露出日本“国体”在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反现代和反民主本质。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已构成了丸山真男“原型论”或“古层论”出台的最初触媒。从下面的简要梳理中不难看出,这种研究已开始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部分地触及了日本的本质。根据丸山本人的回忆,“原型”的说法,始于他1963年的讲义。但有学者指出,“原型论”提出的最早时间点,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末。理由是:在1961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的思想》后记中,丸山曾写过“过去的事物——极言之即上古的事物——之执拗持续”这样一段话。(40)然而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日本战败后不久,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1946)(41)和《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1949),(42)就曾用“超(极端)国家主义”和“无责任体系”的视角,追问过战争前后日本国民的“精神形态”。尽管丸山当时还无力从“道”的层面对日本人的思维类型作出形而上的抽象,但这项工作却较早反映了他试图从根本上挖掘战争原因的学术初衷。 对“国体”的苦恼,使丸山将“原型”的思考更多投向了日本的“政治意识原型”,即古代天皇的祭祀与行政功能在“政事”上的二元分立与矛盾统一结构。“政事”一词,在日本语中被写作“まつりごと”:既是“政事”,也是“祭事”。但是,在日本的“记纪”经典中,却出现了与中国政治原则截然相反的祭政分离倾向。由此而形成的“二重权力结构”,乃如“卑弥呼与男弟”、“神功皇后与武内宿祢”、“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等政治关系格局不一。由于具体行政事务往往由天皇交给他人处理,因此,在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天皇似乎不需要承担根本性责任。(43)行文至此,人们不难发现,丸山似乎已在日本传统的政治体制中找到了天皇作为“无责任者”的原始根据。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日本传统的“二重权力结构”一直持续到明治乃至昭和时代,那么,对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行为的主要负责者,恐未必是天皇,而只是担当具体事务的政府和军部呢? 然而,一个微妙的变化,也刚好发生于丸山在印证日本近代天皇政治思维的有害性时与中国政治及其理论装置——儒家思想体系的频频对比中。在他看来,儒教政治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使道德与政治直接连通”的思维,“在使政治权力无界限地侵入精神领域的同时,正像儒教家族内部伦理所显示的那样,也产生了将伴随强制力的统治关系植入道德领域的倾向。于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权力的强制竟被粉饰以道德,反过来,(政治本身)亦夺走了道德的内在性,使之堕落为顺应(conformity)共同体或集团(利益)的道具。”这意味着,儒家的“政教混一”和“公私不分”,曾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天皇制度的近代转型。由于这种转型的萌芽发育于江户时代,因此,这种“思考方式究竟使儒教主义这一江户时代的通念产生了怎样的病理现象等问题,已经在《劝学篇》中遭到过福泽(谕吉)的明确批判”。(44)这使人想起两点。首先,丸山在追究战争责任时称:天皇仿佛是长着两个头的怪物,即“立宪君主”和“绝对君主”之一体两面。而这种30年代后越发明显的“政治病理”现象,绝不是明治期未尝发生过的情况;(45)其次,是丸山的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他本人学术思想走向上的底色性规定。这部由发表于1940—1944年的几篇大论文汇集成册的学术著作,通过解构朱子学在江户思想界之影响过程,搭建起一个日本早期近代论的象征——“徂徕像”及相关思想结构。在这个构图中,丸山已把近世儒家学说之总代表“朱子学”,视为与近代化原理相悖的思想体系,并将其定性为“旧体制”——德川体制的帮凶。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接近近代日本思想的“古学”(荻生徂徕)和“国学”(本居宣长)勇敢地站出来,对这种旧体制的思想载体展开了有力的批驳,并初步完成了日本早期近代化的思想准备工作。 实际上,对“儒教—东洋旧体制”的否定和克服这一丸山图示,矛头所指乃是近代以来的天皇政治集团。明治以降,曾造成过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国家主义国民道德论”思潮及其凝结物——明治天皇颁布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是被朱子学作过极致发挥的“五伦”教义和道德形而上学。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1891)及其对近世朱子学作出首次系统性哲学诠释的作品——《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显然极富成效地支持了明治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鹈沼裕子在谈及井上的工作“效果”时指出:“一般说来,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国民道德论’,指的是明治四十年代因国家统制而被倡导的国家主义的道德运动。但实际上,该运动的风潮,却上可溯及明治十年的儒教道德复活意识,下可延至太平洋战争末期风行的国粹思想”,时间相当“漫长”。(46)这意味着,津田左右吉在昭和时代的反儒教言行,注定会引发反对天皇体制的联想,其遭遇某种“不幸”甚至酿成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津田事件”,亦应在意料之中;(47)而丸山因现场庇护津田而受到牵累的体验,则决定了他本人在学术领域上的转向——其江户思想史研究与其说是导师南原繁的建议,不如说是政治压力所致更合乎实际些。它教会了丸山如何采取学术“迂回”的方法,既批判了导致“圣战”的原因,又不去直接触动炙手可热的军国主义。于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丸山给津田写信称,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给津田以“暗默的支持和声援”,并同时寄去他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代表作——日后被集结成《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的主干论文开篇——《近世儒教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与国学的关联》。丸山十分希望这篇研究德川朱子学解体过程的文章能够引起西洋社科专业出身者津田的惠顾,哪怕是些微的瞩目,也“幸甚至哉”,(48)只因为这篇文章首先确立的自明式标准,便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对中国事物的批判性叙事。(49)当然,丸山的理论构图明显比位处对立两极的井上和津田要巧妙得多:其出发点虽然与津田思路极其贴近,但他先是把研究视角远投江户时代,然后在强调朱子学在幕府初期之“崇高”地位的同时,旋即给朱子学赋予被“捧杀”的命运。这种做法,既没有重蹈儒教虚无论的老路,也避开了招致当下政治风险的一般可能性。但是,“津田事件”时他们逃离现场后津田博士的自言自语,却给丸山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若听任这帮人闹下去,日本皇室可就危险喽!”(50)这大概意味着,原本在祭政高度一致的中国皇帝身上才会出现的责任追究问题,将因为儒教的集权和极权导向而使日本固有的“祭—政”二元“国体”改弦易辙,并给天皇本人带来可以逆料的灾祸。丸山于是乎通过所谓日本“政治意识的原型”,给日本人之所以对“易姓革命”和“万世一系”同时并存现象提出质疑的历代言说赋予以结论,认为那是中国人平行但对立的两种传统政治思维联袂涌入日本后给日本人带来的政治信仰上的混乱。(51)他之所以通过“徂徕学”来次第裁断朱子学的“连续性思维”,(52)并推尊“古学派”所谓“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公私相分”、“物我相分”这“五大斩断”,(53)所要解决的也正是上述问题。 丸山的研究,不但勾勒出“古学派”特别是徂徕学派对肢解和瘫痪朱子学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对津田的“暗默”呼应,这一叙事还着力强调了“国学派”及其集大成者本居宣长与荻生徂徕之间的间接继承关系,并为他日后推出的“原型论”(“古层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54)于是,在构成“原型论”底色的学术构图中,对于“文明”,丸山抑“中世”而扬“近代”;对于“国体”,则重“自统”而斥“外来”。对欧洲文明的激赏,使他必须反对“近代的超克”;而对“革命”的警惕,又使他必然要远离儒家。战败的不堪,使他对天皇的唾弃连带着对儒教的反感;而面对国体的崩溃,又使他痛感到日本人认同上的危机。这种由“近代”与“中世”、“本土”与“外来”之张力所形成的思想上的“两难”困局,使他在努力追究天皇及国体的战争责任的同时,又无法不自陷于所谓“日本近代的窘境”:“日本究竟‘欧化’到何种程度还依然是日本?对于这一问题,即使到今天也并未得到解决。一般的情况下,改变过去或在变化中前行,或者将同一性保持下去,是国民或民族的认同问题,而这又恰恰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实际上,近代日本的国体论,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其难点正在于隐含其中的日本认同问题。战败时围绕‘国体护持’而引起的巨大骚动,也只因为一点,即如何保持与统治层的利害难以拆分的民族认同问题”,简言之,在“民族认同或同一性问题上”,真不知如何才能处理好“传统与欧化或者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55)这段发表于1986年的文字与1956年揭载于《思想》第381号的《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以及1940—1944年间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的系列论文之间所呈显的变化,反映了丸山真男的真实心理活动,也反应出许多日本思想者的心理状态,有时还导致他们在战争责任追究问题上的茫然(56)甚至诡辩。(57)然而,作为对战后日本知识界特别是思想界发挥过长期影响的学术大家,丸山等人在天皇和国体问题上由战败之初的激进逐渐走向暧昧,甚至无奈于分散责任说和消解责任论等态度,对研究者准确把握战后日本史观的流变轨迹,应不无意味。 四、对战后七十年的再省思 用“左翼”和“右翼”的标签让日本人对号入座,是战后国际社会对日观察时的习用方法。但是,日本人中既有对美意义上的左翼和右翼,也有对华意义上的右翼和左翼;有人在超越的价值层面上是左翼,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则是右翼(反之亦然);政治上是左翼,文化上是右翼(反之亦然);历史观是左翼,当下观是右翼(反之亦然);来华或访美时是左翼,回日本后是右翼(反之亦然);上午还是左翼,下午就变成右翼(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左”和“右”的标准和尺度,用来表现政治或无不可,用来研究学术却不知其可。然而,战后日本“疾速转变”的虚实现象和“形亡实存”的自身结构,却是人们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首先,我们了解某些公开否认战争责任者的言行并斥之为“右翼”,却不太了解那些承认罪责而否认自身变化、承认战败却未必拥抱战败的反美理论。日本战败之初,美国人曾乐观地相信了日本人的“一亿总忏悔”表态,并认为他们很简单,至少没有老道的德国人那样复杂。于是,出于占领后日本国内之安定计,美国在作出免除天皇战争责任的决定(58)后,又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美苏冷战等对峙寒流中,释放并公开接纳了被指控为A级战犯的岸信介等人,且以之为首相或部门大臣。毋庸讳言,那些能将日本迅猛复苏的精英们,几乎全部是经历过战争过程和战败体验的那代人。但是,道尔的观察显示,“当谈到日本的极端暴行时,许多人都坚持否认。事实上,所有的人都真诚地悲恸那些为国捐躯的亲友和熟人。他们也还记得战败后数年间,白人胜利者轻蔑地将他们看作‘小男人’而引起的迷茫困惑”。尽管今天这些人大都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对于裕仁统治的前20年间日本所犯下的掠夺罪行,此时正当需要明确承认和道歉的历史时刻,而在他们身后却只留下了糟糕的历史记录。在他们心目中,承认这个,就包括必须承认‘东京审判史观’,而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爱国心,为他们的国家招来了多数外部世界的轻蔑和不信任”。(59)这或许意味着,不太长于作公开表态的战争参与者们——那些比例还不在少数的日本“战争遗民”,他们对战争性质的复杂认识以及由美国人所谓“双重标准”所造成的认知困惑等思想问题,战后并没有因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日军的和平遣散和对天皇的无罪赦免而获得有效的解决,而美国人的功利性考虑也只好使他们对接下来所发生的大量事实有意视而不见:20世纪60年代近千万人参加的“安保斗争”和时断时续的反美集会,是日本各界的共同行动;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凸显美国一家对日意义的目的下禁用“大东亚战争”而力倡“太平洋战争”的结果,在使日本人忘掉其在亚洲罪恶的同时,还让他们牢牢地记住了美国人两次空前绝后的“无差别杀戮”;而日本每年在“珍视和平”名目下一定要举办的“原爆”纪念活动,说到底,也不过是对美国的无声控诉和仇恨记忆的强化装置而已。然而,美国的“重返亚洲”和“亚洲再平衡”等一系列挑拨东亚各国关系的战略举措,却有效地控制住了日本的反美情绪,当然也同时被日本方面主动地利用了。一个人所共见的事实是,在战后日本,一方面是从“道歉反省”到不知“侵略”为何物,从“防卫厅”到“防卫省”,从“保护国民知情权”到《特定秘密保护法》的颁布,从“军人不得干政”到新版《防卫省设置法》正式废除“文官统领”制,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到“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政策和制度的推进,另一方面则是反对战争、捍卫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保护运动。在日本政治整体发生问题的情况下,“九条会”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和平主义力量,其行动也是令亚洲各国人民感动备至的义举。可是,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九条会的组织方式非常独特。它有异于一般的社会政治团体,没有严格的内部组织形式,也没有为增强团体内在凝聚力而设定的各种规章与制度,只要是支持和赞成宪法第九条的人都可以动员自己身边的同道者组织起来,九个人就可以组织某一地方或某一领域的九条会,再通过各地、各领域的九条会来组织关于宪法第九条的各种学习会、讲演会。”(60)于是,在日本社会中,步步为营的制度推进和可圈可点的信念坚守这两股力量之间,事实上已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失衡格局。当神岛二郎的论著传递出来的信息让人感到许多日本人在战后的“变”不过是出于隐忍生存甚至是卧薪尝胆之需时,潜伏于该观念下的“不变”和积蓄已久的逆向能量,将是巨大和可怖的。日本战败之初,竹内好在对比日中两国接受西方价值和制度的不同表现时指出:“转向,是发生在没有抵抗处的现象,它缺乏化外物为自身的欲求。固守自我的事物,是不会改变其方向的,而只能走自己的路……转换(回心)则不同。它看上去像似转向,但方向却相反。如果说,转向是向外的动作,那么,转换却是内向的归趋……转换以抵抗为媒介,而转向则无需媒介;转换发生的地方不会出现转向,而转向出现的场所也不会有转换发生。转向法则支配下的文化与转换法则支配下的文化,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简言之,“日本文化就类型学而言是转向型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转换型文化”。(61)由此反观神岛氏的“不变论”,那么,其所谓“非武装国家”的要求与明治和昭和、战前与战后一以贯之的“单身者本位体制”在社会结构上并不存在矛盾的认识,其实已暴露出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工作并未触及、也无力触及其社会基础这一事实;而所谓“单身者本位体制”乃建立于前近代家族和自然村落解体基础上的说法所构成的事实与理论盲点——军队或企业中并未消亡的、以拟家族和拟村落化的形式转生而来的共同体纽带及其价值本质,还足以让人在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勾起超时代的连贯兵燹记忆,尽管我们仍愿意对道尔的良好预测乐观其成:“在不久的将来,宪法很有可能被修改,但是其中涉及的问题,仍然可以反映出当今日本民众的政治意识。尽管宪法第九条已经被扭曲变形,以维持‘自卫’能力的名义被不断扩充阐释,但它毕竟仍然作为具有强制效力的不战理想的宣言,与宪法导言中强烈反战的言辞一同留存了下来。”(62) 其次,我们了解那些追责天皇者的正义呐喊并誉之为“左翼”,却不太关注其“国体”否定行为已经发生的两难困局、对华归谬和责任外推倾向。天皇制对现代中国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存在。这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对其展开深入的现场调查和国民心理分析。丸山真男的相关研究表明,前近代日本的政治制度长期呈“祭”“政”分离的“二元”权力结构。这种观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历史的某种实际。但是,当这种原本符合日本自身风土的“二元”体制首次遭遇西方列强的武装压迫和殖民威胁时,日本人却突然发现,面对庞大如清朝的中国都难以抵御的西方力量,倘不思凝聚、一任松散,则不但会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国土不及中国二十五分之一的日本全土,恐亦将直面被吞噬的命运。“公武合体”、“大政奉还”、“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事件和政策的发生与出台,就本质而言乃根源于此。至于所谓面向西方的“文明开化”行动,也与对中国价值期待的整体“幻灭”有关,这一点毋庸讳言。日本要想生存,在强权的新世界规则下就必须“辞旧迎新”。何况,这对于日本打破“华夷秩序”、取代中国的东亚地位而言,又何尝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长期习惯于权威与权力、宗教与行政分家的日本旧有政治,想在一夜之间把全国民心聚合为一,单靠宗教意义上的精神纽带——对天照大神的神道信仰,显然是无法做到的。这就使江户中晚期以来持续受到批判的新儒学体系“朱子学”,突然被派上了用场。他们发现,在继续强化天皇与国民之纵向关系——“神人纽带”的前提下,只有加强横向“人际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日本的内部凝聚,而堪任这一凝聚之功者,却非“忠孝一本”之儒教德目而莫属。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往不易了然的系列现象:日本近世时期,在看似德川“体制意识形态”的朱子学体系下,幕府却容忍甚至部分地遵循了“古学派”的“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等价值取向。这其中,不能说没有公武分离时代幕藩制度的体制性考量在内——它需要借助这些思想来论证“二元”政治结构主要是自身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可是,当西方势力压来后,作为象征性大案的“樱田门外事件”,俨然使“水户浪士”和“萨摩浪士”联手走上了“尊王攘夷”的皇统独尊道路;而完成“公武合体”、“无血开城”和“大政奉还”之历史转折任务的,除了西南诸藩的压力外,人们恐怕还应特别关注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重大出身背景:庆喜是水户藩第九代藩主、以力倡儒教道德和尊攘思想而闻名内外的德川齐昭的子嗣,而庆喜自幼所受到的水户学“皇统”教育,则让人无法否认,他所作出的历史性决断其实并不突然。庆喜的行动,有效地排除了明治天皇在“二元”体制和观念结构上的政治和学术障碍,而明治政府对德川遗产的处理方式也十分耐人寻味:“文明开化”,使具有早期近代化倾向的“古学”并未遭到排斥,且通过西周和福泽谕吉的继承获得了近代性转换;而“体制一元”的绝对化要求,又同时复活了与后期水户学关系至密的“儒教”。结果当然是人们所熟知的,除了日本近代化在东亚地区的一枝独秀外,还有日本帝国的对外系列战争直至1945年的收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丸山将近代以来的天皇制国体变化归谬给儒教作用之言说,或许不乏一定的根据,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否定儒教的全部意义,(63)并且也仅仅因为这一点便连同福泽谕吉一道去厌华、排华、脱亚,甚至不惜拿傲慢的近代性来重新竖立一道与中国之间的“价值隔离墙”,则显然不应是一个战争反省者的应有态度,却很像是连接于“无责任体制”延伸线上的新型“责任外推”。黑住真教授在谈到日本近代儒教时指出:“我们可以把日本近代儒教大体分为如下三种形态:(1)广义上知性的、道德的、作为文化教养的儒教,(2)参与了民族国家形成和帝国主义的儒教,和(3)在学院学术中形成的儒教。”他承认“近代天皇制试图把以权威、权力极度集中于天皇一身的形式来实现立宪”的事实,也注意到“在近代日本,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儒教参与并袒护了近代化中的暴力和帝国主义,它绝不是无垢的’”等说法,但他同时强调,“这里所说的儒教,是指‘某种近代日本儒教’,而并非是近世日本儒教或者日本以外的儒教。但是,当前者(某种近代日本儒教)的印象被投射到后者(近世日本儒教或者日本以外的儒教)时,便滋生了贬低儒教、警戒儒教的倾向”。(64)由于这关联着足以倾动战后日本思想界全体的丸山真男及其系列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已衍生出明显的中国轻蔑意识,因此,黑住教授的长视角观察,还具有了深中肯綮的警示意味:“丸山的‘原型论’由于被视为‘转向’和‘踅足’,而评价很差。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转向’,而不过是把原本暗伏于《研究》(指《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引者注)中的潜形存在变得表面化了而已”,因为“在《研究》中,有一种面向近代的单线发展史观。这里,只是把西欧和日本捆绑在一起,而中国却未被连接。中国被包裹于停滞论的议论框架里。这种中国停滞论,是包括丸山在内的五十年前的通念。在这里,中国不但被轻视,连最初还有的对中国和亚洲的关心,也消失了”。(65)至于部分日本学者对中日问题的“学理”编织之所以能做到超级细密甚至不乏牵强,显然与他们要竭力回护某种事物的潜在意识有关。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注意到,“日本有人”喜欢“把政治问题说成是技术问题”。(66) 再次,我们尽可以强化邻交敦睦、中日通谊,甚至为此已做到了忍所难忍和容所难容,却忽略了中方的努力和日方的响应之间无论在前提还是在程度上均不甚对等或者结构失衡等事实。然而,让日本朝野难以想象的是,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日本有过怎样的历史表现,中国领导人仍能以宽阔的胸襟和超然的站位,对日本人民释放过真诚的善意。(67)毛泽东的对日态度,来自他宏阔的历史视野、高端的现实考量和跨国的阶级意识。(68)这一态度不但极大地超越了民族主义,而且伴随着中国对日本国内反“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有力声援,(69)还使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博大气象和正义力量,寄予了强烈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以至日本民众在反美游行时,竟高高擎起“毛沢東万才(万岁)”的标语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日三国的政治和解,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逐渐被淡化,各国之间的往来也越发频密。但是,90年代“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中日间的误解越发深重,两国关系甚至被世界舆论夸大为战后以来最糟糕状态!然而,面对日本政界的极度不负责任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巨大损伤,中国政府却始终将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在第一位。2015年3月3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受邀在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以“日中关系: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为题作了专题报告。他说,日中间误会的例子很多,例如日本民众认为“习近平一直对日本强硬”,但是习总书记于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发言却是非常积极的,很多日本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70) 这意味着,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东亚世界中,在超越性的价值已变得越发稀薄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和平主义传统和国际主义优长,其实更需要来自周边国家的呵护和鼓励,而不是刺激和贬损。日本学界最近有极端舆论称:当代中国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混合体。(71)问题是,把这一曾经在明治—昭和期集中出现于日本的污泥浊水不负责任地泼向中国的行为,是否暗含某种希望中国也和当年日本一样发动一场对外战争呢?历史学家郭廷以曾讲:“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中国绝无负于日本,日本大有愧于中国。八十年前的两千年,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于中国者独深。”(72)这意味着,如果蒙受过如斯大灾难的国家到头来不但连句“侵略”和“谢罪”之类的道歉话都听不到,还要无端受辱、横遭诟病,那么,国际社会将不知依据何等指标去预测中国官民不计前嫌的宽容之心还能够坚持多久。但有一点,即当我们回首外籍华人雪珥所提出的问题时却必须思考:在一个经年对外侵略的战败国家最需要也最应该形成正确历史观的关键时期,日本为什么反而会选择一条不惜与中国和亚洲其他被害国为敌的“险途”呢?如果可以尝试性给出回答,则笔者以为,战后七十年来,日本无论有过怎样集团性的忏悔“转向”和学术上的思想“反省”,都未尝完成过政治上的价值“转换”。它决定于日本政要念兹在兹的“近代优越”意识和前赴后继的“正常国家”追求,也决定了其扭曲的战争观念和错误的历史认知。其不断制造中日摩擦、以所谓“中国威胁”来利用和倒逼美国对己松绑并试图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思想和行动,不但使“左翼”、“右翼”等国际社会的对日观察标准屡遭颠覆,也使亚太地区被再度置于险象环生的境地。 ①黄遵宪:《近代爱国志士歌》,《人境庐诗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9页。 ②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自序”。 ③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序言”,第6页。 ④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26页。 ⑤《朝日新闻》1945年8月27日、9月6日。 ⑥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09页。 ⑦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207—208页;袖井林二郎:《拝啓マツカ一サ一元帥樣:占領下の日本人の手紙》第一章,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 ⑧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208—209页。“悔恨共同体”的说法,最早出自1977年10月丸山发表于《学士会会报》(特别号)的《近代日本的知识人》一文中,意为:值此战争甫毕之际,日本的知识人应通过各自立场和不同领域,就迄今自身的存在方式是否正确以及如何从根本上反省过去等问题,进行集体省思,以结成“自我批判”的学术共同体。(丸山真男:《近代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真男集》第10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254頁) ⑨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94页。 ⑩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178、195—197页。 (11)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第161—191页。 (12)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195页。 (13)U.S.Senate,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May 1951,Part 1. (14)講談社編集:《昭和:二万日の全記録》第9巻(昭和25年-27年),東京:講談社,1989年,第142—146頁。 (15)鈴木昭典:《日本国憲法を生んだ密室の九日間》,東京:創元社,1995年,第294頁。 (16)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01页。 (17)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18)丸山真男:《戦争責任論の盲点》,《丸山真男集》第6巻,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160頁。 (19)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87、11页。 (20)松本健一:《丸山真男:八·一五革命伝説》,東京:勁草書房,2008年,第126—127頁;焦兵:《拨开近现代日本对外战争的迷雾——访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6日,第A02版;吉田裕:《占領期における戦争責任論》,《一橋論叢》105巻2号,1991年2月,第134頁;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492—493页。 (21)巣鴨遺書編纂会編:《世紀の遺書》,東京:巣鴨遺書編纂会,1953年,第683—685頁;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497、493、501、495页。 (22)竹内好:《中国文学の廃刊と私》,《竹内好全集》第14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455頁(译文参考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注⑩)。 (23)Lawrence Olson,Ambivalent Moderns:Portraits of Japanese Cultural Identity,Lanham,MD:Rowman & Littefield Publishers,Inc,1992,p.65;诸葛蔚东:《战后日本知识共同体的流变》,《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24)竹内好:《魯迅》,東京:未来社,1961年;《中国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魯迅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東洋文化講座》第三巻《東洋的社会倫理の性格》,東京:白日書院,1948年。 (25)竹内好:《近代の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7《近代化と伝統》,東京:筑摩書房,1959年,第253頁。 (26)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1頁;沟口雄三:《历史认识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页。 (27)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 (28)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 (29)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 (30)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 (31)沟口雄三:《历史认识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第16页。 (32)神島二郎:《現代日本の精神構造》,《戦後日本の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25頁。 (33)神島二郎:《現代日本の精神構造》,《戦後日本の精神史》,第26—29頁。 (34)神島二郎:《現代日本の精神構造》,《戦後日本の精神史》,第29—32頁。 (35)神島二郎:《現代日本の精神構造》,《戦後日本の精神史》,第38—43頁。 (36)Tetsuo Najita:《戦後日本における社会科学と人間の挑戦》,《戦後日本の精神史》,第19—20頁。 (37)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增補版),東京:未来社,2004年,第26—28頁。 (38)丸山真男:《戦争責任論の盲点》,《丸山真男集》第6巻,第159—163頁。 (39)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丸山真男集》第12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117頁。 (40)水林彪:《丸山古代思想史をめぐつて》,《日本思想史学》第32号,日本思想史学会,2000年。 (41)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增補版),第11—28頁。 (42)丸山真男:《軍国支配者の精神形態》,《丸山真男集》第4巻,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97—142頁。 (43)丸山真男:《政治的諸観念の原型》,《丸山真男講義録》第7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114—115頁。 (44)丸山真男:《近世儒教の思想的地位と政治的諸観念》,《丸山真男講義録》第7冊,第251頁。 (45)丸山真男:《戦争責任について》,《丸山真男集》第16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327—328頁。 (46)鵜沼裕子:《国民道德論をめぐる論争》,今井淳、小澤富夫編:《日本思想論争史》,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第356頁。 (47)丸山真男:《ある日の津田博士と私》,《丸山真男集》第9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121—130頁。 (48)丸山真男:《丸山真男書簡集》第1巻,東京:みすず書房,2004年,第3—4頁。 (49)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第3頁。 (50)丸山真男:《ある日の津田博士と私》,《丸山真男集》第9巻,第130頁。 (51)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7冊,第224頁。 (52)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5—26、30頁。 (53)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67—378页。 (54)韩东育:《丸山真男“原型论”考辨》,《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55)丸山真男:《日本近代のデイレンマ》,《丸山真男集》第13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54—55頁。 (56)丸山真男:《戦争責任について》,《丸山真男集》第16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323—333頁。 (57)加藤周一:《日本社会·文化の基本的特徵》,《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東京:岩波書店(岩波現代文庫),2004年,第26—27頁。 (58)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第180、183页。 (59)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551页。 (60)刘晓峰:《“平成日本学”论》,《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当然,“九条会”所采取的运动方式,起到了或试图起到在日本现有政党政治框架中在野党无法或无力起到的作用,学界对此需要关注和分析。 (61)竹内好:《中国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1993年,第47—48頁。 (62)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550页。 (63)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7冊,第242—248頁。 (64)黑住真:《近代化经验与东亚儒教:以日本为例》,《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 (65)黑住真:《日本思想とその研究——中国認識をめぐつて一》,《中国一社会と文化》第11号,1996年6月。 (66)《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27页。 (67)《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56—460页;《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6页。 (68)《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9—224页。 (69)《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9页。 (70)http://japan.people.com.cn/n/2015/0305/c35469-26641394.html. (71)西岡力、島田洋一、江崎道朗:《歴史の大転換:戦後70年から100年冷戦へ》,《正論》総力特集《戦後に終止符を》,東京:產経新聞社,2015年5月号,第86—104頁。 (72)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