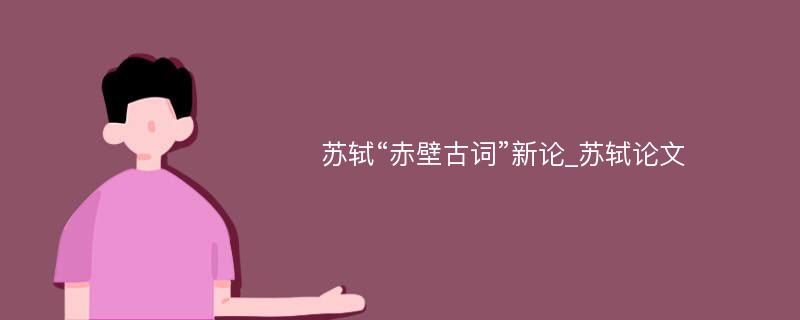
苏轼赤壁怀古词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壁论文,新论论文,苏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4)05-0141-05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首千古传诵的名作,关于这首词的主题,一般认为是表达了作者对周瑜功业的向往与赞颂之情,抒发了“人生如梦”的感慨与彻悟。但是,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小乔嫁给周瑜则是在建安四年(199年)[1]1260,前后相距十年之久。那么,在这首风格豪放雄壮的作品中,熟稔三国历史的作者为何要将赤壁之战十年前发生的故事穿插进来呢?“小乔初嫁了”与周瑜赤壁建功和作者赤壁怀古有何关系,为什么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而非“小乔初嫁时,雄姿英发”呢? 对以上问题的解答,还关系到词中其他语句的解读,尤其对这首词的主题思想的理解。“浪淘尽”既是指“千古风流人物”生命的消失,也是指他们功名的湮没,但“周郎赤壁”存在的本身又说明了什么,为何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羽扇纶巾”究竟指谁,这种“谈笑”与“樯橹灰飞烟灭”之间有何关系?“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应如何断句,“多情”指谁,因何“笑”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作者赤壁怀古为何不祭奠赤壁或周瑜,而要向“江月”洒酒致敬呢?关于这些问题,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换一个角度,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整体内容与逻辑结构出发,结合赤壁之战的历史背景和苏轼创作这首词的时代背景来解读,避免定式化的理解和单薄的情感体验。 一、乌台诗案与赤壁怀古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根据对变法的不同态度,朝野分成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讥刺新党,抒发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的怨望之情,引起新党人物的忌恨[2]654。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诗文中的一些语句,指责他“愚弄朝廷”、“指斥权舆”,“包藏祸心,怨望皇上”,“无尊君之意,亏大忠之节”,将其逮捕系狱①。后经多方营救,苏轼免于死刑,贬充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区,且无权签署公文。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到达黄州。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一说元丰四年十月)创作了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主要描写的是三国时期的人物与故事。苏轼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据《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记载:东坡自黄冈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3]王安石建议苏轼重修《三国志》,不仅因其才学优异,更因为苏轼对三国历史特别熟悉和别有见解。苏轼虽未允应,但念兹不忘。据《曲洧旧闻》载,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4]刘壮舆是刘道原之子。苏轼先后鼓励两代人重修《三国志》,足见对这件事的重视。他还给刘壮舆推荐了参考书《三国志注》,说其中“好事甚多”。《三国志注》是南朝宋裴松之在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的基础上详加增补、注释而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征引文献是西晋虞溥撰写的《江表传》,赤壁词中多处用典出自此书。 作为北宋最高阶层(皇亲国戚除外)的宰辅在选择姻亲时,“尚门第”或“尚官”,目的就是“攀权势、猎富贵”。通过门第相当的高官大族结成姻亲,在朝廷上相互奥援,相互提携,形成牢固的姻亲网络,借以巩固自身的地位,维护本家族既得的以及潜在的经济、政治的利益[5]。“乌台诗案”中,迫害苏轼者主要是以王安石为领袖的新党成员。当时,以王安石家族为中心,存在一个势力庞大的姻亲集团。王氏家族通过与“乌石岗吴家”、“蒲城吴氏”(宰相吴充、吴育家族)、“仙游蔡氏”(宰相蔡京家族)、“钱塘沈家”(宰相沈遘家族)、“南丰曾氏”(宰相曾布家族)、富阳谢氏(谢绛、谢景温家族)等联姻[6],权倾朝野,炙手可热。 王氏姻亲中,许多人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甚至状元。这些人少年得志,固然因其天资颖慧,但更受益于其家族及姻亲关系。王安石及其姻亲多次任主考,沈括就是在王安石任主考时得中进士。谢绛之子谢景温与王安石相善,“景温妹嫁与其弟安礼,乃骤擢为侍御史知杂事”[7]9847,此后一直是唯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忠实干将。此外,宋代本有“封荫”传统,当官家族的直系子孙可以得到封荫,甚至由荫亲发展到荫外亲、荫门客。 以王安石为中心的姻亲势力,本是当时舆论批评的焦点。熙宁三年(1070年),谢景温入台谏重地,司马光上奏云:“安石素恶(苏)轼,陛下岂不知?以姻亲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8]5202熙宁四年(1071年),杨绘弹劾曾布“不时拔用”时说:“其缘王安石姻家而进”,并指责王安石“亲故则用”,以塞贤道[8]5481。相对于少年得志的新党后进,苏轼等新党人物却君臣不遇,仕途坎坷,“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7]10819。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数被外放,9年间(1071-1079年)迭经杭、密、徐、湖四州,继而沦为阶下囚,几死台狱。熙宁初,又因多次直言批评新法,“论其不便”,引起当权者不满。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欲以苏轼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因王安石反对作罢。熙宁三年(1070年),御使谢景温弹劾苏轼居丧贩货入川,“穷治无所得”,苏轼为避患,“遂请外,通判杭州”[7]10808。处此政治生态中,其心情之忧愤,可想而知。 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的主要原因是在《湖州谢上表》中说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的话,表明对那些少年得志的新党人物的不满。苏轼出狱当天,曾写《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诗二首,其一云:“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2]1005“少年鸡”指贾昌少年时曾因善斗鸡而深得唐明皇宠爱,以至时人传诵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里比喻少年得志的新党人物。“不斗少年鸡”,就是不再与这些少年得志的新党小人争斗了。 黄州时期,苏轼处于人生低谷,忧谗畏讥,心情抑郁。这从他当时所作诗词中可以看出来,如《卜算子》词云:“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临江仙》词云:“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曾将《前赤壁赋》寄给友人,信末写道:“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9]2455为什么“未尝轻出以示人”,正是畏惧文字狱,担心传出招灾惹祸。 二、“小乔初嫁了”之后 了解该词的写作背景之后,再回到词的文本中,先看下阕换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建安四年(199年),周瑜攻陷吴县后,“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1]1260。孙策死后,其弟孙权当政。周瑜是孙权之兄孙策的连襟,因此,他与孙权外为君臣,内为姻亲,从而获得了孙权的绝对信任。据《三国志》记载:“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1]1264这种姻亲和信任正是周瑜得以建功的基础。赤壁大战前,孙权曾对周瑜说:“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1]1262孙权表明已将抗曹大任和东吴安危托付周瑜,自己甘愿做周瑜的后盾与靠山。 那么,周瑜又是如何看待他与孙氏兄弟的君臣关系呢?孙策死后,鲁肃一度有另投明主的打算,周瑜得知后,劝阻道:“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搆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1]1268周瑜对孙氏兄弟的选择,是基于建功立业的考虑,为“攀龙附凤驰骛”。 由此,或许可以理解苏轼因何在词中穿插进“小乔初嫁了”这一幕。正如王季思先生所说:“‘小乔初嫁了’的‘了’字本来是动词,是了结,完了的意思,到南北朝的时候,逐渐变成紧接在动词后面的语气词,表示动作的完成状态。‘了’字连在上句读,意味着周瑜娶了小乔,婚姻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孙吴政权更加信赖周瑜,他‘雄姿英发’,建立了盖世功业。”[10]至此,“初”、“了”两字的含义便凸显出来了。周瑜的建功立业和新党人物的权倾朝野,至少在此方面相似,即姻亲是他们重要的政治资本,而这正是苏轼及多少豪杰所没有的。 再看“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句。关于“羽扇纶巾”之所指,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指周瑜,一说指诸葛亮。如果指诸葛亮,且看是否合适。首先,全词上阕讲“三国周郎赤壁”,下阕讲“公瑾当年”、“故国神游”,都是在写周瑜,若再插入诸葛亮的故事,未免横生枝节。其次,赤壁战胜的两个最大功臣,周瑜时年34岁,诸葛亮年仅28岁,如果同时出现,无疑是对周瑜年轻有为形象的削弱,在艺术上是一种败笔。最后,“羽扇纶巾”是汉末魏晋时期的士人和儒将的常见装束,不仅限于诸葛亮。羽扇,是用鸟羽制成的扇子。魏晋时期盛行清谈,为了助兴,他们手上常执着一些“谈具”,如麈尾、如意、羽扇等。汉末魏晋时期的将领常有头著纶巾、“手挥羽扇”的形象,如《晋书·顾荣传》云:“(陈)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11]1813《晋书·谢万传》云:“万著白纶巾,鹤髦裘,履版而前。”[11]2086因此,“羽扇纶巾”应指周瑜,而非通常认为的诸葛亮。 那么,“谈笑”与“樯橹灰飞烟灭”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1]1265苏轼曾有《周瑜雅量》一文,记载了“(蒋干)乃布衣葛巾,自讬私行、诣瑜”的故事[9]2020。这个故事先是出自《江表传》,后为《三国志注》征引。赤壁之战前,曹操有意招降周瑜,就派蒋干过江劝降。其中,对周瑜设宴欢送蒋干一事的记述颇详: 后三日,瑜请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讬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干但笑,终无所言。[1]1265 “外讬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在周瑜看来,他与孙权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姻亲关系,所以孙权对他绝对信任。在欢送蒋干的宴会上,周瑜谈笑风生,表明大战前东吴君臣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赤壁作战的另一方——曹操阵营恰好相反。曹操为人生性多疑,战前误斩大将蔡瑁、张允,是导致曹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周瑜全力辅佐孙权,孙权对周瑜绝对信任,苏轼正是借用这个典故来说明君臣和衷共济、上下同心比借东风更为重要。甚至这种“谈笑”背后的姻亲和信任就是“东风”,是周瑜战胜敌军、赢取功名的最重要原因。苏轼因“君臣不遇”而被贬黄州,时刻处于忧谗畏讥之中。身临其境,作词抒怀,既有对孙权周瑜君臣亲密关系的无限羡慕,内心也不无感伤、忧愤之情。 三、周瑜的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 结合以上分析,再看《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文本内容,其中许多语句,都可以重新解读。如“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般有两种断句方法:一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二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其区别在于,前者的“多情”,可以是指苏轼本人,也可以代指他人,而后者的“多情”,只能是另有所指。那么,应以哪一种断句为准呢? 第一,从格律上看,《念奴娇》词牌中这一句式都是断作前四后五。徐乃为曾遍检唐圭璋所编《全宋词》之《念奴娇》词牌,没有一首词断句例外:“翻检《全宋词》中的所有的《念奴娇》(包括异名同调的《酹江月》《壶中天》《百字令》《百字歌》《百字谣》《大江东去》《赤壁词》等),得三百十余题,计四百九十余首词。这两句的句读,只见到一首是‘前五后四’的,但那是编辑或排字工人的失误。”[12]其中,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作品,都是四五句式。苏轼另一首《念奴娇》“凭高眺远”词,亦不例外。 第二,在《东坡乐府》一书中,“多情”一词除本词外,还在以下词作中出现:《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满江红》(天岂无情)、《泛金船》(无情流水多情客)、《醉蓬莱》(笑劳一生梦)、《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渔家傲》(皎皎牵牛河汉女)、《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浣溪沙》(道字娇讹语未成)、《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江城子》(玉人家在凤凰山)、《蝶恋花》(花褪残红春杏小)等,共计十一处。除《采桑子》外,其余均非自指。王木曾检《词综》四至十卷,计用“多情”一词者十五例,除毛谤《蝶恋花·寒食》一例外,其余也非自指。“由此可见,苏轼和与他约略同时代的人,对‘多情’一词的习惯用法是指旁人(物),而不是用以自指。还需说明一点:苏、毛词中的两个例外,均仅是兼有自指而已,它们全还可以作不是自指的解释。”[13] 第三,“多情应笑”的上一句是“故国神游”,“故国”即赤壁之地,能将赤壁称为故国的,只有周瑜,而不是苏轼或诸葛亮。既曰“神游”,便知此“游”是虚拟的,是揣度和想象中的,而非实地游览。 第四,“多情”与周郎的历史形象相符。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周瑜少时精意于音乐,“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1]1265。以周瑜之聪明,不可能不知侍女们故意借弹错琴来诱其回首,而他却“知之必顾”,一盼一顾之间,其风流多情形象跃然纸上。再联系到他用美人计来对付刘备,“赔了夫人又折兵”,自身又得益于与小乔的姻亲关系的风流形象,用“多情”指代周瑜,顺理成章。同时,“多情”一词也是对周瑜姻亲背景的一种暗示。 作者假想周瑜故地重游,与正在赤壁游览的苏轼相遇,一定会取笑他。那么,周瑜为什么要“笑我”呢?周瑜的“笑”,显得意味深长:表面上是笑苏轼年近半百,头发花白,却一事无成;深层上是“笑”他不识时务,不知妥协和委身权贵。其实,这也是作者的一种自嘲。 至此,再看词的开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多少风流人物的生命和功名都被大浪淘尽,随风流逝,但“三国周郎赤壁”之名还在,显然不属于被大浪淘尽的“多少豪杰”之内。有人说苏轼不相信这里是真正的赤壁,借“人道是”来抒情。那么,苏轼是否知道黄州赤壁是假赤壁呢?据记载,他也不确定:“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9]2255但他还是接连写了前、后《赤壁赋》以及多篇与赤壁有关的诗词文,说明这并非简单的真假问题。童勉之先生说过:“苏轼在与《赤壁怀古》同一时期写的《前赤壁赋》也写了由黄州赤壁联想到‘曹孟德之困于周郎’却没有用‘人道是’之类的字眼来声明是传说,赋的容量比词大得多,为什么在五百多字的赋中不声明,而在才一百字的词中竟用了三个字来声明?”[14]可见,这一句的关键不是“人道是”而是“人道是”的内容,即“三国周郎赤壁”。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人们却说那是“三国周郎赤壁”,言外之意,是周瑜的功名尚在被人传诵。“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作者看来,赤壁战场对垒的各方,都是“豪杰”,奈何单说是“周郎赤壁”?郭沫若先生曾感叹说:“使多少豪杰成了一个周郎!”为何周瑜能功成名就,没被大浪淘尽,还在被人传诵呢?下阕正是对周瑜成功原因的探讨。 对于周瑜的功成名就,历史上不乏质疑之声。据《江表传》记载:“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1]1265不仅曹操,甚至盟友刘备也怀疑并说他的坏话。在同一地点,晚唐诗人杜牧任黄州刺史时,也曾写下《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15]杜牧认为,假使没有东南风给予方便,周瑜赤壁之战未必能够取胜,只怕二乔都要成为曹操铜雀台中的俘虏。周瑜侥幸成功,表面上靠的是自然之风,实际上是来自君臣遇合的人力之风。身处同一场境,史书和诗文对周瑜的评价,以及周瑜和自身境遇的反差,不能不让苏轼有感而发。由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也不再仅仅是景物描写,而是以景写情。“乱”、“穿”、“惊”、“拍”、“卷”等激烈的字眼,表达了与周瑜处于同一时代的“多少豪杰”的不平和不满之情。 词中的周瑜只是一种文学形象,而非历史形象。周瑜作为一个与作者和“多少豪杰”相对比的形象而出现,不一定就说明苏轼对周瑜本人的鄙薄。文学形象的塑造,是为情感表达服务的。如苏轼曾抨击过曹操的残暴,但在同年所作《前赤壁赋》中,又赞其“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周瑜走上层路线,通过姻亲而获得信任(婚姻强化了这种关系),少年得志;相形之下,苏轼却因为惹恼了上层,被囚乌台,继贬黄州,“无枝可依”。出于对周瑜历史形象的维护,尤其后来文学作品中对周瑜风流倜傥形象的美化,使得人们很难接受对周瑜的负面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对这首词的理解。 四、“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 词的最后一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卒章显志。作者赤壁怀古,为什么不向赤壁或者周瑜,而向江月洒酒致敬,并且要加一个“还”字呢?“江月”化用了唐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中的语句:“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16]这里指不被历史湮没的真正英名与品格。“江月”在苏轼诗词中,常作心志的象征。如宋英宗治平二年直史馆时所作的《谢苏自之惠酒》诗:“我今不饮非不饮,心月皎皎常孤圆。”宋哲宗绍圣四年所作《和陶杂诗》之一:“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和陶杂诗》之四:“作书遗故人,皎皎我怀抱。”以及徽宗元符三年北归时所作《藤州江上夜起对月》诗:“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等等。说明在苏轼的诗中,经常通过将月比心来表现自己的高洁情操。 苏轼在同年所作《前赤壁赋》云:“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9]6面对周瑜式的嘲笑,苏轼认为,人生如梦,你们这些功业,也不过将被大浪淘尽,就像当年被焚烧的樯橹那样“灰飞烟灭”。他宁愿像“多少豪杰”那样被大浪淘尽,也要保持光洁的人格,去追求那种不被时间和历史磨洗的真正“功业”[2]1641。 “一樽还酹江月”,至此,这个“还”字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就是祭奠大江中的“被淘尽”的英魂,是表明自己像明月般的忠贞之心和光洁人格,而不是面向赤壁故垒或周瑜洒酒致敬。“江月”意象的含义,正如张福庆所说:“苏轼的将心比月,却是用月来比喻他光明的理想,象征他一颗高洁的心。而‘酹’也者——洒酒祭奠,悲挽哀悼,却正表现了他对理想的苦恨执著!正因为诗人在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始终不能放弃理想,所以他的精神才那么痛苦,他的胸中才会掀起那么汹涌的感情波澜!”[17] 这种选择在苏轼的另一首诗,即《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也有体现。诗云: 与君饮酒细论文,酒酣访古江之濆。 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 “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既然孙权和周瑜不值得凭吊,那么,谁值得凭吊呢?伍子胥曾因忠于吴王夫差而被赐死,君臣不遇又甚于苏轼。因此,在作者看来,更值得伤悼的是伍子胥和他自身的不幸遭遇。此后,苏轼在《乞郡札子》中又说:“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9]829从中不难看出,苏轼被贬期间动辄得咎、忧谗畏讥的忧愤心情。 元丰三年(1080年)十月,苏轼在与好友王定国信中说:“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仆虽不肖,亦尝庶几仿佛于此也。”[9]1517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第二年,苏轼与好友李公择的信中又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9]1500虽然仕途不顺,但他仍是忠心耿耿。因此,后来宋哲宗看到了这首词,将《念奴娇》这个词牌名改为《酹江月》,显然对其老师这首词的思想内涵有所会意。 鲁迅曾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8]将苏轼的赤壁怀古词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结合作者的经历来解读,可使得该词主题更为明确,逻辑更为通顺。同时,也使得词中的一些易为传统解释一带而过的关键字眼,如“人道是”、“初嫁了”、“羽扇纶巾”、“谈笑间”、“多情”、“还酹”等,含义得以落实,意味深长。 苏轼的赤壁怀古词以周瑜的少年得志与作者的老无所成形象作对比,探讨了功业成否的背后原因,即由君臣关系所决定。而君臣关系的亲疏,在某种程度上还受一些超越君臣关系的影响,如姻亲关系。由此看来,全词既具有较深厚的历史内涵,又呈现出较强的逻辑关联;既对比强烈,又形象鲜明;既前后呼应,又中心突出,不愧为为词史第一名篇。 根据以上分析,将东坡赤壁怀古词译述如下: 大江滔滔东去,千年前的多少英雄豪杰都被淘洗一空。但在古战场的西边,还有人说那是“三国周郎赤壁”。我看那里乱石林立,白浪滔天,如怒如诉。在这如画的江山,一时间聚集了那么多英雄豪杰,为何最终却成就了周郎功名呢? 遥想当年,小乔嫁给周瑜之后,周瑜得以与孙吴统治者联姻,一时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因为他与当权者关系亲密,才能获得统治者的绝对信任,上下同心,从而击溃了敌军。如果周瑜故地重游,这个多情的人应该会嘲笑我年近半百、头发花白,却不识时务、一事无成吧。但是人生如梦,功名如烟,我还是宁愿向那湮没在滚滚长江中的英魂和象征光洁人格的明月凭吊、致敬! 总之,该词名为赤壁怀古,实为借古写今。不是怀念和赞颂周郎功业,而是感慨君臣不遇,表达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被理解的忧愤心情。他艳羡周瑜与孙权的特殊君臣关系,但却不愿像周瑜和当时新党人物那样趋炎附势,追名逐利。因此,赤壁怀古,作者更为怀念的是古代那些失败失意的英雄、不被理解的豪杰志士,并借以表明自己不屈的独立人格和耿耿忠心。 注释: ①苏轼的诗歌确有讥刺时政的内容,包括抨击变法过程中的问题。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称“乌台”。标签:苏轼论文; 三国志论文; 周瑜论文; 念奴娇·赤壁怀古论文; 三国赤壁古战场论文; 赤壁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古词论文; 前赤壁赋论文; 宋朝论文; 孙权论文; 江表传论文; 黄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