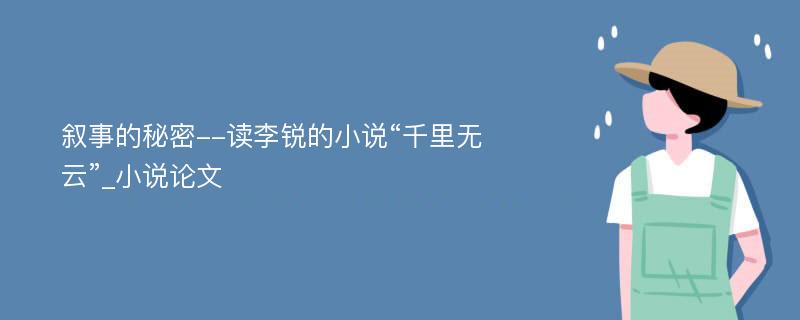
叙述的秘密——读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里无云论文,长篇小说论文,秘密论文,李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穿越
“影响的焦虑”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论断。冲破文学史上一系列大师所缔造的强大传统,这是诸多后辈作家的迫切心愿。然而,还有多少作家察觉到另一个问题:穿越自己所设置的罗网?
一个作家的成熟通常标志了一种风格的定型。这可能是一种独异的个性,一种个人与现实对话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一种隐蔽的重复,一种轻车熟路掩护之下的停滞。因此,对于一个作家说来,改变习以为常的写作半径,闯入另一片陌生的艺术洞天,这不仅需要才能和经验的积累,而且还需要勇气——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一种冒险。
可以看到,李锐仿佛正在信心十足地同自己的既定风格搏斗。他耗费了六年的时光撕下了《厚土》系列所形成的紧身衣,如同一条蛇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蜕皮。向自己的既定风格赎回了自由之后,李锐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应声而出。《无风之树》的叙述隐含了一种解放的欣悦,《万里无云》更像是一阵哗然地扑面而至的语言潮汐。
《厚土》系列的叙述简约,节制,内敛,凝重,一如《厚土》这个词语所产生的联想。编织于叙述之间的精致修辞时常显示出某种暗中控制的迹象。精心的锤炼致使这批短篇小说如同一串不含杂质的脆响。相反,《万里无云》却是嘈杂的,喧闹的,汹涌的,种种风格的话语单元密不透风。尽管小说的句式还不可避免地保持着“厚土”式的利索,但是,小说的叙述话语——句子的组织——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种叙述话语与小说情节的单纯构成了一种有趣的紧张。这样,《万里无云》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风格:既拥塞又明朗,既含混又简单,既丰富又逼仄。
李锐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样的叙述使他心满意足:“从原来高度控制井然有序的书面叙述,到自由自在错杂纷呈的口语展现的转变中,我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丰富。”[1]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叙述并不是情节之外的一种实用性工具;“语言是和我们的四肢、五官、心脏、大脑一起组成的重要的一部分。”他甚至不无极端地声称:“叙述就是一切。”[2]
同样的理由,《万里无云》的叙述话语成为分析这部小说的起点。
话语类型
如果采用概括的语言重述,人们甚至可能想象,《万里无云》仅仅是一个短篇小说的情节。这样的情节容量似乎无法填满长篇小说的巨大框架。因为久旱无雨,五人坪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祈雨活动。可悲的是,这场祈雨不仅未使龙王显灵;相反,突然而至的山火焚毁了仅存的树林,并且烧死了祈雨仪式之中扮演金童玉女的两个少年。于是,参与这场祈雨活动的若干有关人员锒铛入狱。的确,这样的故事轮廓怎么能够抽取出长篇小说的纷歧线索,制造一波三折的起伏?
《万里无云》的纷歧、起伏和容量——一句话,《万里无云》的丰富来自叙述话语。我将《万里无云》视为一个恰当的例子:特殊的叙述运作迫使一个简单的故事现出纷杂的涵义。
叙述话语的神秘功能诱发了剧烈的分析愿望。如同许多孩童对付那一台令人迷惑的自鸣钟一样,我企图根据一定的规则将《万里无云》的叙述话语拆卸开来。毫无疑问,叙述话语不是简单的词汇堆砌。如同罗兰·巴特所指示的那样,人们首先可以在叙述话语之中发现种种叙述单元[3]。
叙述单元同语法意义上的语言单元——例如句子,词组——无关。罗兰·巴特进一步证明,切分叙述单元的衡量尺度是语义,特定的语义担负了叙述话语长链上面的每一个功能性环节。叙述单元可能由几个句子组成,也可能小于一个句子。这些叙述单元的相互协助保证了叙述话语自始至终的完成。
然而,后继的分析之中,我不想继续从事巴特式的严谨分类,重复序列、核心、催化、迹象、情报等一系列术语,并且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叙述层次描述一个金字塔式的叙述结构。我的兴趣依然保持在语义层面上。我试图考察的是,这些叙述单元的语义如何归属到种种更高级别的话语类型之中得到解释。这样,我就有可能从这部小说的叙述话语之中分解出几种主要的话语类型。考察这些话语类型的内涵,考察这些话语类型在叙述的链条之上所占据的位置,考察这些话语类型相互作用的规则和关系,这显然有助于人们洞悉《万里无云》叙述话语体系的构成秘密。
在这里,话语类型的核心是相对稳定的语义规定。话语类型的结构依据仍然保持在语义学的意义上。叙述话语内部,诸多叙述单元拥有种种具体的释义。这是正常阅读的前提。然而,在更高的层面上,这些零散的具体释义还将汇集于一些更为概括的语义标题之下,诸如科学话语,商务话语,外交话语,礼仪话语,如此等等。显而易见,后者均属话语类型的层面。通常,这样的语义业已在叙述之中形成不言而喻的共识,没有必要诉诸多余的解释。譬如,人们可以将一片沙漠、一丛茅草、一口池塘的描写一律解读为自然环境的描写——“自然环境的描写”即是作为二级的语义规定划出了某一个特殊话语类型的边界。标明一部小说的叙述话语包含了哪些话语类型,这也就是指明叙述话语运行的文化层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万里无云》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对话;然而,人们无法在小说的叙述话语之中发现“科学知识”的话语类型——无法发现诸如“人工降雨”或者“气象预报”之类的词语。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
人们已经看到,《万里无云》废弃了一个固定的叙述人,废弃了一种貌似中性的局外叙述;所有的故事段落不得不在众多富有个性的口吻之中曲曲折折地延伸。尽管如此,这些富有个性的口吻依然汇聚成为一个统一的语境。这样的语境不仅提供了这些口吻相互交流的对话空间,也不仅意味了服从于某种一致的情节逻辑,同时,语境的统一还喻示了某种共同认可的文化假定,某种潜在而又自发遵循的价值观念体系,某种说与听一致了解和使用的代码。这样的语境代表了五人坪对于整个世界的阐释模式。显然,这样的语境所预设的一套上下文关系同时包含了一种强制性的语义规范。它不仅将某些五人坪式的解释强行赋予种种词语或者叙述单元,而且,它的独特语义规范甚至划分出五人坪所独有的话语类型。例如,日常的城市用语之中,“五斤鸡蛋和十斤白面”并没有固定的涵义;人们只能在具体的描写之中解读这两个数词和名词。可是,对于五人坪说来,“五斤鸡蛋和十斤白面”表示了相当可观的财物。作为一种礼品,赠送者和接受者无不感到了沉重的分量。对待食物的时候,五人坪的语义学单独列出了一个话语类型。这表明了五人坪对于食物的特殊重视。五人坪之外的人未曾察觉这个话语类型的存在,他们的某些解读将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误差——例如,他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五斤鸡蛋和十斤白面”竟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为什么一块猪肉就能够成为勾引他人妻子的诱饵。
《万里无云》的叙述话语之中潜藏了哪些重要的话语类型?
“我”
“我……”
《万里无云》之中充满了以“我”为主语的句式。“我”的语义不必继续诉诸更高一级的话语类型——这个字眼本身即可构成一个单独的话语类型。
“我”是第一人称,个体的自我指代之词。《万里无云》的叙述话语之中,“我”的功能不仅是主语;这个字眼同时还从另一些方面支持了叙述的完成。
《万里无云》之中诸多的“我”代表了一个个迥异的人物性格。但是,“我”这一人称代词下面呈现出的性格与无人称叙述不同。无人称叙述通常拥有全知全能的视域,叙述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任何一个方向描绘这一性格——描绘的对象可以是肖像,可以是心理,可以是对话,也可以是行动。相对地说,第一人称仅能描绘人物的内心,其他方面的描绘不得不通过人物的内心中转。但是,人物的内心隐藏了什么?
结构主义理论的“移心”学说将独立的人物性格视为一个神话。依结构主义,人物并非一个个性化的实体;人物不过是各种语言系统或者代码汇聚的空间。罗兰·巴特宁可将有血有肉的人物置换为一个语言学的名词。在他看来,人物性格如同一个“专名”,“专名”作为一种强烈的特征组织了一系列分散的“性格素”[4]。这个意义上,人物的内心空无所有——除了形形色色的话语片断。性格的分析与其求助于心理学,不如求助于语言学。
这无疑是一种语言学基础上的人物观念。尽管许多人可能产生种种疑问,然而,至少《万里无云》充分地体现了这样的人物观念。这部小说里面,人物性格即是语言的汇聚;性格与性格之间的差异导源于不同话语类型的选择,导源于种种话语类型组合的不同比例。这有效地破除了人物的神秘性。《万里无云》之中不存在那些面目不清的人物,一切都在语言的层面上摊开了。在一个更为普遍的意义上,结构主义即是一种否弃神秘的语言学理论。
这样的人物观念同时还带来了另一个叙述运作的后果。不难发现,众多人物内心的种种话语片断均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横向组合”的功能,多数话语片断都程度不同地在情节的纬线上前呼后应。这保持了叙述话语的强大连续性。或许,种种具有“纵向组合”功能的话语片断已经被过滤殆尽。换喻取缔了隐喻。人们没有看到那些游离于情节逻辑的话语片断,没有看到那些证明人物纵深的冥想、思辨或者无意识的涌现。也许,这无宁说是李锐对于五人坪的某种定位——五人坪的人物不存在深度心理。
最后,“我”的大面积使用让口语充分进入了这部小说的叙述话语。李锐将《万里无云》的叙述话语称之为“口语倾诉”;口语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5]。不过,我的兴趣在于另一方面:口语是五人坪消化一切外来文化的标志。《无风之树》里面,刘主任宣读的文件使用的是标准的政治术语,这些政治术语同矮人坪那些瘤拐们的日子格格不入——格格不入的特征即是,这些政治术语组成的话语从来就无法进入瘤拐们的口语。两种词语体系的分裂象征了两种现实之间的距离;政治术语居高临下地覆盖了口语,征服了矮人坪——但是无法融汇于矮人坪。相反,《万里无云》的叙述让口语吞噬和改造了五人坪之外的词语体系,这再度证明了五人坪语境的强大压力。口语在叙述话语之间所占据的主导位置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部小说的的确确叙述了一个典型的五人坪的故事。
自然环境
“……旱得李子从树上一颗一颗往下掉,脚底下滚了一片绿珠子。”
“……一颗太阳把天上地下烧了个彤红彤红,眼见着就把西天给烧漏啦……这狗日的老天爷是一滴滴雨也不给人下啦他!”
“……她就看见这一大铺子西番莲了。红的血红,白的雪白。叫月亮一照,冷冷的,沉沉的,银亮银亮的。”
“他一眼就看见了村口那棵虬枝盘绕高大无比的老杨树。……在漫山遍野的黄土中搭起一栋哗哗做响的绿色楼宇。”
“风太大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整整一条沟的林子全他妈的烧光了,整整一条沟都叫烧成了乌黑一片啦。”
上述引文均可以归入“自然环境”这个话语类型。
一种简约的情节理论认为:情节的叙述即是打破一个稳定的开端,经历了一系列混乱之后重新恢复到另一个水平面上的平衡[6]。这样的意义上,“自然环境”这个话语类型承担了首要的叙述功能。干旱破坏了既定的生存秩序导致了祈雨仪式,这是全部叙述的初始契机;山火焚毁了一切作为这场仪式的告终,新的平衡意味了情节的结束。这个话语类型在叙述运作之中的重大功能暗示出人的渺小和无奈。人无法以现有的方式掌握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按照自己的逻辑规定了故事的结局。
这个话语类型的另外两个次要涵义是神秘和审美。
那一棵高大无比的老杨树让初到五人坪的张仲银一怔,他仿佛感到了某种难言的震颤,这即是神秘。后来,老杨树上出现的黄裱纸与蝌蚪文让张仲银走向第一次灾难,这隐含了某种宿命的意味。对于《万里无云》说来,神秘的意义到此为止。叙述话语并没有让神秘在五人坪占据更多的位置。
自然环境的审美涵义在叙述话语之中更为微弱。除了那一大铺子西番莲,五人坪的人无法察觉自然之美。五人坪的文化还未产生自觉的自然审美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的奢侈品,审美不可能介入五人坪的重大事件。
传统文化
“……一个兜兜绣了三天了,还是绣不完,三朵花,五片叶,两条鱼,花是荷花,鱼是金鱼。……”
“……那个说书的瞎子说,好汉武二郎一手握了白闪闪的牛耳尖刀,一手揪住淫妇潘金莲的头发,……你以为我他妈×的比武大郎还憨还傻还窝囊呀你。”
“……你说这大胖和尚他咋就这么坏呀他?他为啥就扣住人家白蛇的男人不给人家呀?……”
“……我三把两把就把这个用扫炕笤帚扎的草人从她手里夺过来了。”
“……那是天书,那黄裱纸上写的字叫蝌蚪文,老神树这是显灵啦这是!快点跪下,快跪下……”
“后来一场大雨把石头冲出来,历史才历历在目:‘五人坪村居平阳府西南隅……大明永乐十年八月吉日’。”
“……我就抡着宝剑走到龙王牌位前边,……掐诀念咒,掐诀念咒。”
《万里无云》之中,传统文化这个话语类型下面汇聚了丰富的叙述单元。从民间工艺、诅咒、说书和戏曲到碑文、祈雨仪式,这个话语类型分布在叙述话语的每一部分。分析之后可以看出,这个话语类型成为各种场合一系列对话的内在依据:人与自然对话,人与人对话,人与历史对话。
祈雨仪式是五人坪向自然发出的吁求。这个仪式内部包含了请求,许愿,承诺,祈祷,威胁。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之中幼稚的前科学知识主宰了五人坪的所有想象和实践。一切都在原始的象征形式上进行:金童玉女,水漫金山,进贡龙王,火烧旱魃……这样的对话意味着,自然环境的真实面貌并没有进入五人坪的视野;在五人坪的心目中,自然的存在同样是一种象征形式。
或许,五人坪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真实得多:家族,血缘,性,经济利益共同体,如此等等。祈雨仪式上面的募捐,建造学校的筹款,这一切无不依循了众所周知的现实法则。在货币、财产与权力面前,人们坚持明晰的确认,任何含混的象征都可能引致危险的冲突。然而,涉及人与人之间某些更为深刻的关系时,传统文化又悄悄地恢复了发言权。牛娃对于张仲银的仇恨寄寓在武松杀嫂的故事之中,翠巧借助白蛇传的故事转述她在满成面前的不安,哑巴婆婆信奉古老的传说,利用草人诅咒她的媳妇红盼。五人坪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爱或者恨的表意策略,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将种种强烈的情绪托付给某些夸张而又简单的现成形式。这样,他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传统文化的空间。
《万里无云》之中,人与历史的对话体现为张仲银对于那块石碑的阅读。遥远的知音致使张仲银倍感现实的孤独。张仲银在这样的孤独之中产生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感,并且作出种种惊世骇俗之举,于是,历史的某些片断依附于张仲银插入了现实的叙述。相对而言,陈三爷对于历史的借用远为粗陋。他伪造了某种历史形式,试图将这种形式作为指引现实的圣谕。虽然这不过形成了一种漫画式的历史感,但是,这却制订了五人坪表述自己反抗现实的方式。
传统文化对于五人坪的全面支配形成的结果是,传统文化成为编织在叙述话语深处的网络。
政治话语
“……你现在宣了誓,你就是党员了,你是咱们九十里乱流河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你以后就得永远跟着党走,一辈子跟着党干革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四旧’,你们还是要搞封建,你们这是不把新社会放在眼里,你们这是想造反……”
“……你越给她脸,你越给她做思想工作,她倒是越来劲了她,她倒是越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她……”
“张老师说,这是叫你们听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组织红卫兵,写大字报,游行喊口号。……”
《万里无云》之中的政治话语十分稀少。能够娴熟地掌握政治话语的人仅有三个:张仲银,赵荞麦,赵万金。相对地说,张仲银的记忆里贮存了最多政治话语;可是,这些政治话语基本上已经过时——这些政治话语是上一个时代的语言遗物。现实之中,张仲银所熟悉的政治话语间或还可能出现,但是它们的涵义和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卫东竟然用毛主席的像祈雨——上个时代最大的政治人物如今竟然变成了神话人物,他所制定的种种政治话语同样成了历史。
不难看出,赵万金与赵荞麦都拥有掌握当今政治话语的身份。然而,赵万金已经卸职,他丧失了昔日那种权威的口气;只有赵荞麦是五人坪的当朝人物。可是,他什么时候正经地使用过政治话语呢?
罗兰·巴特曾经细致地将叙述话语的叙述单元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叙述话语内部的真正铰链,称之为“核心”;第二个类别在于填补铰链之间的叙述空隙,称之为“催化”[7]。《万里无云》之中,政治话语仅仅是一种“催化”,政治话语不再具有改变事件方向的功能。至少在这部小说之中,它已经被传统文化的话语淹没了。
学识
“……北京有个金太阳……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毛主席说,‘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毛主席说,‘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团中央委员邢燕子。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独沧然而涕下……”
“……面对四壁,面对自己,面对一只口琴,和一只口琴细如蚊声的独唱。……”
“……他说,《辞海》上说,旱魃,古代传说中能造成旱灾的怪物。……一说为旱神,见孔传。”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这是一些五人坪之外的语汇,只有张仲银一个人独享。“只要一抬头,‘已是黄昏独自愁’的自豪和孤独就有安放处。偶尔有人来问问,仲银笑而不答,只说那是一句诗。有一次支部书记兼队长赵万金问他,仲银,这疙疙岔岔的写的是啥呀?仲银就把《毛主席诗词》拿出来说,都是这上边写的,是诗,毛主席喜欢的诗。赵万金就谦恭地笑了,赵万金说,呵呵,仲银真是有学问。看这字写的,看这字写的,我连一个也认不得。……”在五人坪的眼里,张仲银使用的种种令人惊奇的语汇统一叫做“学问”。“学问”代表了所有难以通晓又不可轻视的外来文化。显然,这个话语类型同样是五人坪语境的独特产物。
尽管“学问”仅仅由张仲银独享,可是,这个话语类型却带着不可抗拒的权威投入五人坪的语境。产生这种权威的中介是传统文化之中的师道尊严。于是,如同赵万金一样,整个五人坪无不对张仲银的言论保持敬畏。
但是,这决不是意味着五人坪将这些语汇纳入自己的语境,遵从这个话语类型的内在尺度。五人坪对于这个话语类型的态度无宁说是敬而远之。这个话语类型不协调地悬浮于五人坪的语境之上,无法进入五人坪,改变五人坪种种事件的逻辑。这个话语类型不过是让五人坪了解到,外面还存在着另一种世界。
不仅如此。一个更具反讽意味的情节是,祈雨仪式甚至利用了“学问”,——这即是“旱魃”的辞条。这个情节可以看作是五人坪的传统文化对于“学问”的一个试探性招安,尽管这样的招安披上了师生之情和经济利诱的外衣。
所以,虽然张仲银独自据有这个话语类型,他仍然不可避免地感到了孤独。
失语
“失语”的意思是,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表述语言。因此,“失语”没有引文。
孤独意味了缺少对话的对手。这是个体话语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中断。但是,张仲银不仅如此。他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同样残缺不全。他的某一部分内心世界找不到倾吐的语言出口。
张仲银觉得,呆在茫无涯际的荒山野岭独对孤灯,这使他对许多词汇产生了深刻的理解。但是,他的词汇量仍然不足。“有一次,仲银独自一人走到山顶上,放眼四望,起伏的群山掀起胸中壮阔的诗情,仲银觉得自己很需要一些诗,于是放声朗诵道,站在山头望北京,……有了这一句,一时又想不起下面的,只好再喊——站在山头啊——望北京……四野茫茫,群山无语,吕梁山一瞬间吸干了仲银的诗情。仲银低下头看看母亲亲手为自己缝制的方口布鞋,仲银用母亲做的布鞋踢踢吕梁山的石头,仲银实在想不起下面应该说些什么,想不起说什么的仲银只好空落落地再独自一人走回到村庙里去。”这是失语的悲哀。无处话凄凉。孤独表明张仲银身陷五人坪,失语却表明张仲银走不出五人坪——他同样没有具备同一个更大世界相互沟通的语汇。
但是,张仲银内心世界的冲动并没有因为失语而止歇。他终于在这种隐晦的冲动压迫之下挺身而出,代替陈三爷进了监狱。虽然张仲银未曾清晰地自叙这一场作为的动机,但是,小说的叙述话语却清晰地暴露出诸多话语片断之外的一个心理存在——这个心理存在甚至足以让他毫无惧色地在政治上自焚。显然,这个心理存在即是“失语”的所指。
因此,解读这部小说叙述话语的时候,我有理由将“失语”视为一个特殊的话语类型。
国家机器
“……老张就把那个明晃晃的手铐给他带上了。老张就把那个黑亮黑亮的手枪也掏出来了。……”
“……他一从监狱里放回来……”
“……你现在在这张拘捕证上按个手印吧。……”
手铐,手枪,监狱,拘捕证,这一切均是国家机器的象征。这些名词从属“国家机器”这个话语类型。
这些名词仅仅偶尔出现在叙述话语之中,但这些名词却毫不含糊地宣布“国家机器”的到场。这些名词是叙述运行的坚硬框架,不可逾越。故事经历了高潮之后,这些名词就将出动,收拾后事,清理场地。
这个话语类型承担的叙述功能是,截断故事之中多余的枝杈,提供一个无可非议的结局。
性
“……我就憋足了力气,我就死命地撞进去,我猛一下子,猛一下子的。……”
“……她就哭,我就进。她就哭,我就进。我就给她狗日的进到底了我就。”
“……他就在我怀里拱。他就在我怀里一口一口地喘气。……月亮和我脸对脸地躺着,月亮看着我和满成在水里升上来,又沉下去。……”
“我就弄。我就弄。她不理我。我就弄。她干得就像是白嘴吞炒面,又噎人,又涩巴。……”
“……来,起——,起——!行,你老伴现在还有把子力气,还能背得动自己的老婆。来,……”
谁都能看得出来,上述这些引文属于一个力图隐蔽而又难以回避的话语类型——性话语。
然而,分析之后可以察觉,这部小说之中的性话语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重要。性话语并没有成为叙述话语的某种轴心,充当冲突的焦点;事实上,这种话语类型仅仅处于附属的位置之上。
在赵荞麦的眼里,性不过是权力的战利品。掌握了五人坪的领导权,同时就拥有了对于异性的权力——正如他姐姐荷花说的那样:“他不把五人坪的女人都睡了他就不算歇心。”也许,赵荞麦本人的另一句话恰好可以作为注解:“我赵荞麦一个村长,一个男人,我就不信我连自己被窝里的事情也他妈×的管不了啦我!”这无异于暗示出,男性向往的是权力,女人甚至连争夺的对象也算不上。
似乎有一场围绕女人的争夺战——牛娃不断地提防着张仲银对于荷花的吸引,他甚至每天想象着用杀猪刀宰了张仲银。然而,这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夺。张仲银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荷花——他从来不把没有文化的荷花放在眼里。因此,牛娃仅仅是为自己所制造的悬念迷惑了。但是,这一场虚假的争夺之中却隐藏了一个真实的出发点:没有人关心荷花想什么。张仲银对于荷花的爱慕之心淡然处之;另一方面,牛娃又从来不想尊重荷花的意愿和情感。张仲银与牛娃的一个共同点即是,荷花本人的心情无足轻重。这一场虚假的争夺同样证明,五人坪的女人没有地位。
翠巧和满成在自家院子的西番莲底下做爱,这是一个象征——尽情尽意的性爱如同回归自然一样美好。可是,象征仅仅是象征。性爱早已被分离出自然范畴,成为社会与世俗权力插手最多的一个区域。也许,五人坪的理想爱情同样摆脱不了五人坪的现实条件。赵万金为瘫在炕上的哑巴老伴擦干褥疮,背着她到村子里看一场《白蛇传》——这就是五人坪的爱情范本。
乡村景象
“熬水烫出来的猪毛味儿就臭哄哄地从大锅里冒出来。……一眨眼,四只蹄子都卸下来了。”
“……黄牛们全都慢悠悠的,全都不着急,全都撇着两瓣蹄子慢慢地晃悠。木桶就在驮架上摇过来摆过去的,咕咚一下,哗啦一下。咕咚一下,哗啦一下。”
“他忽然听见一阵铜锣的敲打声。随着锣声,张仲银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簇拥着一个男人从树后出来。……”
这是一些典型的乡村景象。这个话语类型穿插在叙述话语之间,四处可见。它点缀着故事的环境和气氛。按照罗兰·巴特给出的术语,这个话语类型可以称之为“迹象”:迹象“使人想到的不是一个补充的和一贯的行为,而是一个虽然多少有些模糊、但对故事意义必不可少的概念。比如有涉及人物性格的迹象,与人物身份有关的情报,‘气氛’描写,等等。……要懂得一个迹象‘有什么用’就必须过渡到高一级的层次(人物行为或者叙述)去,因为只有在那里迹象的含义才得到解释。”[8]《万里无云》之中,乡村景象并没有在最为基础的层次上面成为推进故事的齿轮;但是它们在更高的层面上使故事的空间与叙述语境协调一致。
“他者”的话语
“打开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中国地图册》,……仲银说得对,那些山根本不像泥丸。山就是山。”
这一段引文是《万里无云》的末章——第五章。
第五章补叙了前面情节的种种间隙、遗漏,尤其是重述了有关张仲银的背景、来历和他第一次入狱的原因。第五章当然包含了诸多业已得到分析的话语类型。但是,考虑到这一章所承担的语义功能,我倾向于给予单独的注视。
这一章的叙述人是五人坪的知识青年李京生。这不仅是引入了一个新的人物性格,更为重要的是引入了一个五人坪语境之外的词语体系。这一章的叙述没有严格地遵循第一人称的视野,同时,叙述的书面语风格还暗示了另一种文化渊源。这一章的叙述解开了张仲银挺身而出的一个悬念——另一个女知识青年刘平平的嘲笑剧烈地刺激了张仲银的自尊心,促使他义无返顾地跨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时,这一章对于许多事件的重述无异于给出了五人坪之外的参照系。这使许多的情节和细节获得了不同的解释,产生了不同的重点。
仅仅从叙述的意义上也可以说,知识青年李京生是五人坪的“他者”。第五章是“他者”的话语。
“他者”的话语作为另一种背景显示了五人坪的文化坐标所在。
重提叙述
分解出一系列主要的话语类型之后重提叙述,无疑是为了重提叙述的聚合功能。叙述的聚合功能是神奇的;拆卸出来的种种话语类型将在叙述之中融于一炉,浑然无迹。叙述不是相加的总数,叙述的横向组合是使单列的各项叙述单元获得一种共同的内在逻辑。
我的拆卸仅仅说明了《万里无云》所包含的多重涵义,以及这些涵义的来源。当然,我的拆卸时常察觉到一种有力的抵抗。这样的抵抗来自叙述本身。叙述即是反拆卸。否则,这一部小说不可能如此强烈。
注释:
[1] 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无风之树》代后记,见《无风之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 李锐:《我们的可能》,《上海文学》1997年第1期。
[3]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叙述学研究》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参见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54页,71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5] 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
[6] 参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7]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叙事学研究》14页。
[8]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叙事学研究》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