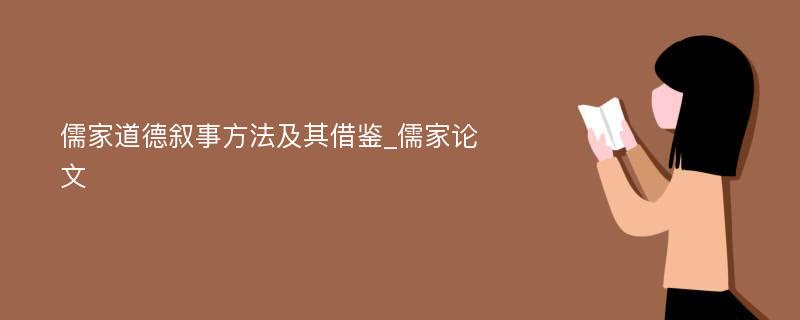
儒家的道德叙事方法及其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道德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现代的道德教育中,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人们注重理性化、抽象概念、系统的知识灌输等,忽略了道德教育的生活性、经验性、体验性、感性感染力。现象学提出的“回到实事本身”,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回到生活世界”及语言学转向,日益影响到人们对道德教育的思考。教育叙事成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教育方式,从这一视域反观儒家的道德教育,我们发现,叙事和叙事的话语方式恰恰是儒家道德教育的特点和长处,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尽心下》)即道德教育要运用浅显的言语、常见的事情。儒家的道德叙事方法,在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对此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解读儒家道德教育的成功所在,而且还可以为当代道德教育提供诸多借鉴和启示。
一、隐喻式叙事
隐喻式叙事是《春秋》的叙事方式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司马迁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之意于历史记述中,被称为“春秋笔法”,《左传·成公十四年》较系统地概括了“春秋笔法”:“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在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言少而意显,记录史实而蕴含深意,语言表达方式委婉而顺理成章,史事实录而不隐瞒歪曲,批判恶行而引导人们向善。可见,《春秋》叙事的明确目的是“借事明义”,寻找和反思历史故事背后的伦理意义,以达到“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它采取“微”、“晦”、“婉”等隐喻式叙事的话语方式,以“微言大义”解读历史事实和建构事实背后的意义。“微言”注重字词的选择,往往以一个字的表述,隐含某种道德评价、意义判断,即“一字见义”或“一字褒贬”,如:国君被杀曰“弑”,弑君则是对臣下强烈的道德谴责。吴楚之君以子国而自称王,《春秋》则贬之为“子”,以彰示其僭越。
《春秋》还运用缺书寓意的方式,如:僖公十九年,“冬……梁亡。”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应当讲述人物和情节,但是这里却没有说明何国、何人灭梁,必然引起人们的疑问,在追问记述背后的意义时,便显示出记叙者对梁自取灭亡的贬责,梁大兴土功,滥用民力,使人民疲惫不堪,引起公愤,秦攻梁,人民溃逃,梁遂灭亡。再如,《左传·襄公三十年》:“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左传》补充了参加澶渊之盟各国大夫的名字,并且说明不载姓名的原因是由于参与国不守信用,未履行盟约,所以名字不见于记述,以示讥讽,“信其不可不慎乎!”
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国联合齐、秦、宋等国于卫地城濮打败楚、陈、蔡联军,即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晋文公随即在践土大会诸侯,并召周襄王与会,让其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而《春秋》记为:“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子狩于河阳。”河阳属晋地,不是天子狩猎之所,这样的记述表明晋文公以臣召君,有违于君臣名分。正体现了“《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的宗旨。
隐喻式叙事偏重于记叙的客观性、真实性,因此记叙者一般不进行单独的道德评说和显性的道德教育,所隐含的道德意义往往需要读者自己结合事件或人物进行解读、剖析,自己关注意义的生成,由此造成道德信息的传递和接受。这种道德教育方式由于隐匿目的性,往往使受体在第三者“客观公正”的叙说中,更易于被同化。
二、解释性叙事
这是儒家道德教育中最常用的叙事方式,通常以第三者较全知的解释,对故事进行分析、引申和联想,这种叙事的指向性明确,所以选择的事情要有问题性,才可以通过解释生成意义。解释性叙事根据道德教育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第一,传递明确的道德信息,如:孟子所讲的孺子入井的故事,当人们看到小孩将要掉到井里,任何人都会产生惊骇和同情之心,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推动人们救助小孩的动机不是为结好其父母,不是要在乡里、朋友之间博取名望,也不是厌恶小孩的哭声,而完全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天生的恻隐之心,由此可见人性本善。
又如:“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齐宣王怜悯牛无罪而死,孟子通过对这件事的剖析,说明齐宣王具有恻隐之心——仁的萌芽,这是君主实行仁政的基础。齐宣王对自己行为的道德动机缺乏认知,经孟子的解释,豁然开朗:“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
第二,澄清道德是非,叙事者往往选取较复杂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解释,如:管仲之事。齐桓公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齐襄公无道,二人惧怕牵累,鲍叔牙奉桓公逃往莒国,管仲和召忽奉公子纠逃往鲁国,襄公被杀后,二人争入齐为君,桓公先入齐国,立为君主,于是兴兵伐鲁,逼鲁国杀了哥哥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管仲非但不能死节,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所以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认为管仲不具备仁的品德。孔子也曾经批评管仲的器量狭小;又收取大量租税,手下人员不兼差,所以没有节俭的美德;他还抨击管仲不知君臣之礼,国君宫殿门前立有塞门,堂上有招待外国君主放置器物的反坫,管仲也建塞门和反坫。但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尽管管仲不知礼、不节俭,又不忠主,但是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很少称许人为“仁”,却称管仲有仁德。对管仲一生诸多重要事情的解释和分析,孔子教育人们分清大是大非,评价人重大节,不能纠缠于小节,从而否定一个人。
第三,进行道德诱导,这种方式所选用的故事,大多不直接讲述道德问题,而是通过叙事者的叙说和解释,引发联想,使人们形象而贴切地理解或领悟其道德意蕴。如:孟子叙述的楚人学齐语的故事,楚国官员要其子学齐国话,不请楚人教习,而必请齐人教习,“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达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达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这件事引导人们关注道德环境问题。再如:弈秋学弈的故事,使人们认识道德修养要专心致志,才能有所成就。拔苗助长的故事,以生动的情节,引发人们领会道德修养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渐进过程,“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故事至今仍为人们广泛引用,印证了儒家道德叙事方法的成功。
三、感染式叙事
这类叙事借助于故事内容和情节的感染力,激发人的道德情感,引起心理共鸣和移情,使人乐于去倾听,在倾听中受到教育。一是创作一些寓言故事,故事构思奇巧,含义深刻,又韵味隽永,引人遐想,极富渗透力。如:孟子创作的偷鸡贼寓言,讽刺那些知错不改的人,“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再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我将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厌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最后,孟子评论说:“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位者,几希矣。”(《孟子·离娄下》)这则寓言对缺乏道德羞耻心进行了辛辣讥讽,使人心理上自然而然地对此产生强烈的厌恶感和排斥感。
二是叙述者在场,而且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这种在场叙事,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感性感染力,如:王守仁讲述自己早年信奉朱熹的格物说,对着竹子格物穷理,格到第七天,不但没有领悟天理,反而病倒了,由此认识到朱熹格物说的错误。这一亲身经历,对王门弟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后人在这一故事的影响下,解读朱熹的格物说时,也不能不对其道德教育的路径产生质疑和反思。
再如: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详述了自己少年丧亲失教、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思想困惑与斗争等事,以自己的曲折经历教育子孙,剖心置腹、袒露无遗,其关切之情所包含的教诲之义,令人感动而受之。“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塗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颜氏家训·序致》)
四、事迹—符号互动式叙事
历史上某些人物及其突出的事迹广为人知,世代流传,久而久之,当人们只要提及这一人物时,便会联想到他的事迹,并且把这种事迹抽象为一种伦理精神,于是典型人物的事迹在人们的传述和时间流转中积淀为一种符号,完成了事迹的符号化过程。
某一人物或某一子情的符号化过程必然会过滤掉一些东西,使它脱离传统语境、某些具体的历史情景和情节,而更多地关注于某种精神和意义。当人们在新的语境下接触这一符号时,他们必然要完成由符号到事化的过程,即把符号还原成事迹,在这一还原过程中,就要转换语境,采取新的话语方式叙述和理解、解释该人物的事迹,这样,符号的事化实际上就是新意义的产生。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开放的过程,而很多优秀的传统道德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从而流传至今。所以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如:禹是儒家的一个叙事符号,他为天下治水,13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一种为公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具体内涵,各个时代、甚至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具体的阐释。“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孟子·万章下》)伯夷、叔齐的事迹体现了一种清高的人格境界,至于他们反对武王伐纣、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具体做法,孔孟及后代人则多不重视;伊尹和比干的事迹则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在做着新的叙述和阐释。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存储着诸多的叙事符号,这与儒家的这种道德叙事方式有关,同时也为儒家道德的现代转换提供了通道。
总之,儒家道德叙事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关注故事如何展现意义和意义的生成;在叙事方式上,注重不同的情景、对象,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叙事目的的隐性与显性的交叉出现和交互作用等等,这些成功的做法值得认真加以发掘和借鉴。
标签:儒家论文; 管仲论文; 道德教育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道德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春秋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