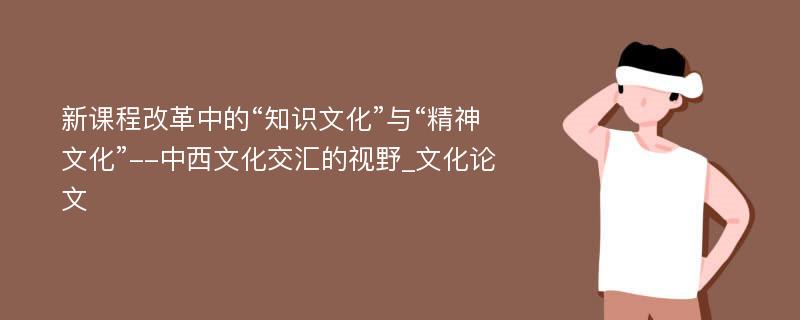
新课程改革中的“知性文化”与“精神文化”——中西文化交汇的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西文化论文,知性论文,视野论文,新课程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两条线路:一条明线,属于知性层面的文化,即人们能够意识到的“文化”,主要代表了人们主观的文化主张;另一条线是暗线,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人们往往意识不到的,但却时刻影响着人们言行的客观的文化存在状态。两条线路的发展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知性层面的文化寄希望于引入西方的文化来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一直处于焦灼不安和奋力追赶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充满了批判、鄙视,甚至试图与之决裂。反映在教育上,教育改革也随之在不断的变革,不断摇摆。由于总是在西方文化的背后亦步亦趋,中国的教育理论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主观否定和批判而中断,始终静悄悄地流淌在文化的血脉之中,在教育中,传统文化主要以“教育民俗”的方式在不断延续。此次的新课程改革也是如此,在知性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有着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
一、文化意识的焦灼不安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对中国极大的一次打击。亡国的危机使得中国充满了焦虑不安和惶恐,为了救国,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尝试:从魏源的“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设计,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热心的洋务事业到后来的兴学校、废科举、造铁路,酝酿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改革发展,必须根本抛弃固有文化,索性走另外一条路。应该说“五四”运动是在精神和文化上把我们的旧传统冲破了一个大口子。
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乎从没有间断。胡适认为从现代学术的立场评估,现代欧美文化较中国文化更为先进,但从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来看,对于中国来说,欧美文化也不是可以盲目引进的,更不可能以欧美文化取代、替换中国固有文化,而必须使欧美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真正连接起来,而不发生“排异”反应。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三种不同“路向”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路向,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的路向,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路向,三种文化平行发展,没有优劣之分。他比较了三种文化后认为,西方文化弊端显著,处于不得不向第二种路向转变中,人类文化将“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
张东荪在《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中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古今之异”,而且也认识到了中西文化的“中外之别”,即民族性差异。这是他对中西文化比较观的重大飞跃。他说:西方思想的根源,一个希腊,一个是西伯来。其后发展起来,便成为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宗教。而我们中国却只有一个人生哲学,把政治经济法律等浑然包括在内。换言之,那只有一个做人问题。[2]
总的来说,人们虽然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国的文化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为自己所用,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中国文化的自卑情结比较严重,虽然很多人都在讲要保留、完善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大家肯定的成分究竟有哪些?与此相关的令人信服的论述并不多。
二、文化追赶中的教育“摇摆”
正是由于缺乏文化的“自主性”,所以中国文化的发展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一个阶段学习这国文化,过一阶段又转而学习那国文化。这种文化“自主性”的缺失在教育发展的摇摆不定之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前后。在输入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主要输入了欧美教育理论,其中以“杜威教育学”为主要取向。
建国初8年,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又一致把学习和移植教育学的方向从西方转向前苏联,视凯洛夫教育学为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范例,我国的教育学遂成为“苏化”教育学。“1956-1966年这十年时间,在既不想学苏,又不能学欧美的情况下,中国教育学被迫走上一条自立之路,但此时依然摆脱不了苏式教育学的模式与思路,使之成了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与“政策法令汇编”,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中国“化”掉了教育学[3]。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横扫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遭到进一步破坏,处处用政治、意识形态来制约人的言行,割裂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那时中国的教育理论如同荒漠。从1978年开始,刚从“文革”苦难中走出来的人们开始大量译介在我们“关门”的20多年里西方教育理论工作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结构主义、人本主义等教育理论相继传入中国,到90年代中期,西方建构主义以及诸种后现代流派的教育理论又一波接着一波地在我国得到引进和研究。正是这最后一次的遭遇,西方“历时性的话语系统”以“共时性”的特征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播甚至泛滥,几十年的话语仅用几年的工夫就进入我国。
在借鉴和运用国外的各种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中国也在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教育改革。人们在理想上不断追逐着西方的各种教育理论与文化,但在实践中却一直延续着中国的传统教育文化。比如说20世纪初到20年代这段时间里,从我国中小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课程设置已有较大改变,并已开始引进了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但在教学实际上仍然保留着我国的旧教学传统。讲书、读书、背诵、记忆仍是主要模式。至于杜威的名字,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已经为许多人所熟悉,但在当时中小学的教学实际中,并未形成气候。
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在钟摆似的不断变革中始终摇摆不定,充分体现了我们在“知性文化”层面的困惑,即对于如何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外来教育理论与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这一问题的迷茫,另一方面,在隐性的“精神文化”层面,传统教育文化以其固有的节奏不紧不慢、不愠不火、无声无息、缓缓流淌在文化的血脉之中。
三、新课程改革中的“知性文化”
从文件和文件解读读本中我们可以发现,新课程改革倡导的是一种与我们原有的文化相区别的一种新的文化,在《纲要》中,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体目标中提出了六个改变,这六大改变批判了我国教育中无法令人满意的现状,显示了我国课程改革与传统决裂的毅然决心,而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后现代主义观点以及建构主义等从西方引进的一系列理论则成为了此次新课程改革的主要支撑性理论。
这些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因为充满了人本主义的光芒和浪漫主义色彩,在“知性层面”获得了大多数教育者的认同与追捧。一线教师们也非常努力地将这些理念贯彻到自己的教学中去。为此,新课程改革伊始,我们听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变了、变了”,教师的行为变了,课堂教学变了,学生变活了,教材也变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我们的教育似乎真的改头换面,“新”了起来,很多人都滋生了“革命即将成功”的喜悦。但是,随着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等到人人都会使用“课改专用术语”的时候,学者们的兴奋点已经不在对于这些专用语的使用和吹嘘上了,他们转向了对课改的冷静反思和批判。等到每一位教师都知道“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的时候,我们发现课堂教学并没有因为这些“振奋人心”的课改理念而发生传说中的实质性变化,生活仍然在有条不紊的重复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当我们已经迈进高中的新课程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教育行政领导们纷纷又把目光和兴奋点聚集在了高中,小学、初中的课程改革被当作“已经常态化”而不再给予过多的重视。其中也有一些高中的教师反映经过了三年课程改革的洗礼,从初中升上来的学生不管在知识还是能力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多少课程改革的成效。新课程改革似乎只是为我们的教育穿上了一件新衣,化了一点妆,脱下衣服,卸了妆,好像还是老样子。特别是当新课程改革进入高中以后,高考体制的束缚使得新课程改革举步维艰,人们更为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文化的阻力以及对前进方向的困惑。
四、来自“精神层面”的文化阻碍
当校长和教师们口口声声地说:“我们的教育理想是以人为本,为了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时候,学校的橱窗里张贴的却是学校近几年的高考升学率等统计数据。教师们普遍对“学生主体”的思想表示赞同,但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是高中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们“一讲到底”的现象普遍存在……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说的、想的往往与我们做的背道而驰,而且,我们经常毫不察觉。这其实是精神层面绵延不绝的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体现,它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差序格局下的等级文化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用以说明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他说:“差序格局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规范要素,所有行为的价值标准,都无法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4]差序格局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模式。客观地说,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如此,差序格局从农村进入了城市,从家族走进了学校、工厂,这一概念对于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互动行为,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只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差序格局的内涵、范围、特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5]
差序格局在教育文化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到处体现的都是差序的人伦关系,支持这种差序格局的就是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度、权威文化、控制文化、统一的文化。为此,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新课程倡导的民主、平等的教育文化是缺乏现实根基,很难真正得到落实的。
(二)“无我状态”中的求同文化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认为,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独立人格不可辱,自由意志不可犯。一个人的独立人格,他最后的底线在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个体的价值是要通过群体的价值来体现的。所以中国人不能脱离群体而生存,家庭是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小、最基本、最不可分割的单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我”的文化,“我”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看看汉语就更有趣,几乎所有的人称都与人有关,唯独第一人称例外,根据顾颉刚的考证,第一人称“我”的古代象形字是一尊刑具,与人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有间接的关系,是惩罚人的工具。为什么惟独我字与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呢?中国文化把我看做自私的(连日本也受中国文化影响,把我写成私),即为万恶之源,难怪得动用刑具。但社会是由一个个的我组成的,如果把我都赶尽杀绝,其结果是连对我使用刑具的社会也不复存在。[6]
这种对“我”的忽视也同样存在于当前的社会文化、教育文化中。虽然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也就是要重视每一个“我”,但事实是教师作为单个的“我”都得不到充分的自主,缺少个性发展的空间,学生作为单个的“我”更是被忽视与控制,学生的“主体性”很难得到发挥,学生的个性也无法得到张扬。中国文化的“无我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三)消费社会中的功利文化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追求利润、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文化渗透到了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首先,国家对于利润的追求大大超过了对教育的关注,因为“百年树人”,人的培养周期太长,投入再多,其利润的回报无法立竿见影,所以,虽然政府一直在强调“科教兴国”,强调重视教育,但对教育的投入却并没有为此而增加。相比较学校的内涵式发展,政府更加关心的是可见的“教育效益”;相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校长更加关心的是学校的升学率。只要是跟学生的升学率无关的事情,很难引起校长和教师的兴趣。比如说在实践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很难得到贯彻落实;研究性学习也很难真正被排进课表;音体美的课时经常是“缺斤少两”;学校开发出来的校本课程、校本教材往往成了应付各种检查督导的重要摆设;教师们进行教学研究更多的是为了评比职称的需要……相比较追逐浪漫的教育理想来说,追求现实的经济利益来得更加实惠一点。
(四)科学主义、效率至上文化
伴随着科学而来的统一性、标准化等科学意识日益侵入到人们的日常思维之中,科学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力量表现出与人抗衡、控制和左右人的行为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效率主义、标准化测量、重视理科忽视文科、强调可控等思想影响到了教育的方方面面。
课堂教学讲求效率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的塑造只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共性”——它是一种身份的生产,文凭的生产,所谓的个性发展只能是美丽的谎言,至于全面发展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学校这个“工场”要计算生产成本。至于生产出来的少数“奢侈品”,也只能向特殊阶层进行“特供”,大多数人的命运,只能是消费社会的“大众消费品”。在科学主义的控制下,教师的个性发展、学生的个性发展、学校的个性发展其实都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著名学者唐君毅在谈到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时指出:西洋学术文化之重分门别类与主义派别之多,皆西方人分析概念之精神之表现。中国学术文化传统重统绪而略类分,重各类学术文化之精神之融合。而之所以形成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化之形成为多元,其所历之文化冲突多,而中国文化之形成,几乎可谓一元,其所历之文化冲突少。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也使得中国文化特别注重自己的“统”,这种“统”对中国文化来讲是文化的“根”。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仍然绵延不断,因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强大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具有“家的意识形态”的含义,[7]对于中国文化来讲,这种“家的意识”尤为强烈。近一百年来,人们总是难以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可能也是因为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