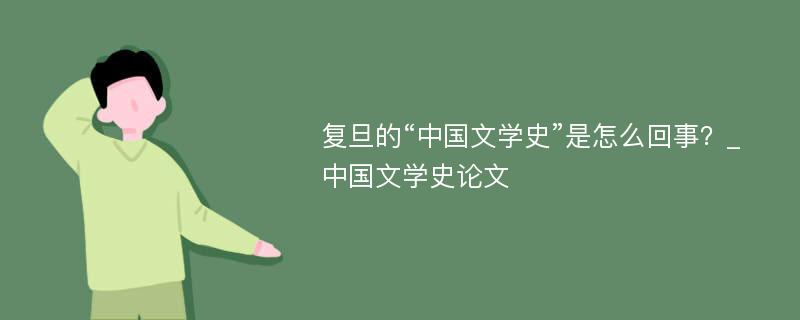
复旦版《中国文学史》怎么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旦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打开近期的《文汇读书周报》,看到十分显眼的专页:“点题征文:一本买了感到后悔的书。”还没细看这页整版的内容,我脑子里已冒出一句:最近买的书中,要说后悔吗,最后悔的当然要算章培恒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了。这后悔,可能还代表着五十万以上的读者的后悔,——这书已发行五十万套了。一套拥有一个读者,五十万读者;兄弟俩、夫妻俩买一套,那就是一百万读者;集体买、单位买的,那拥有的读者就更多了。这套近时期火热的书,买了才几个月,怎么就后悔了呢?因为主编之一的章培恒已宣布:这套书“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它“几乎没有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以至“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必须“另起炉灶重写”,而且“重写”已经完成,“一九九七年第二季度我们将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增订本”。花了68元,买了本三分之二有毛病、而且毛病不轻、必须推倒重写的书,你能不后悔吗?
然而,后悔只是后悔呢,还是也可以付诸行动?这部书是作为商品花钱买来的。要是别的商品发现三分之二有毛病,消费者将会怎样对待呢?图书从书店卖出来,难道不也是商品吗?是否可以要求消费者协会一类团体、组织,出面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呢?是否可以联合起来诉诸法律保护呢?
或许主编者会说:这是学术著作,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学术著作的不断修订,是很正常的现象。
然而,作为消费者的人们必然要问:学术著作固然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把三分之二存在“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的书稿匆匆忙忙抛出来让人购买,这叫不叫粗制滥造?现在又以几个月的时间“另起炉灶重写”了七十来万字。如此匆忙,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章培恒还这样告诉大家:“复旦大学出版社因恐出版修订本的时间距离原本的出版时间过近,被读者误解为捞钱的手段,所以同意我们将修订本交给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平心而论,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这说明这家出版社多少还想到了读者。换了另一家出版社来出这部书,读者是否就不会“误解为捞钱”了呢?恐怕不见得。当然,原出版社是没有“捞钱”的嫌疑了。新的一家出版社是为“捞钱”的嫌疑也不大。因为新的“另一家出版社”至少还得冒两种风险:1、初版已发行五十万册,主编可以十分轻松地宣布三分之二篇幅另起炉灶重写,读者是否还会像对初版那样的信任呢?要是“增订本”推销不出去又怎样呢?2、如果“增订本”销路仍好,编写者为了“不断完善”,再次宣布三分之二要推倒重写,你必须像新的著作那样再给一次稿酬,否则他可以再去找“另一家出版社”,那又怎么办呢?老的出版社已不可能“捞钱”,新的出版社至少还没有“捞钱”,那么谁在这中间“捞钱”或为了“捞钱”呢?在商品大潮中,一些教授、学者不为“捞钱”所动,宁坐冷板凳,在孜孜兀兀的从事学术研究;也有一些学者教授为了“捞钱”真是挖空心思,甚至不顾体面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来。章培恒先生等是为了“捞钱”或不是为了“捞钱”,我都不敢妄论。但世上的事情,人们总会明白真相的。
在这本《中国文学史》刚出版之际,曾有八位著名的专家学者参加此书的“研讨会”,他们的发言纪要整版地刊载在报纸上。有说此书“石破天惊”的,而且是两个人说的;有说“材料充实,论点新颖,填补了六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的;有说“本书的出现是文学史研究走向成熟、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的;有说“这部文学史完全能够代表新时期的研究水平与状况”的;有表示要向两位主编“致敬”的。正当这些响当当的评语还在读者头脑中“余音缭绕”之际,主编之一章培恒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必须“另起炉灶重写”;而且这么一部大型文学史,竟然“几乎没有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这样的宣布,实在使我们平时十分敬仰的好几位专家学者猝不及防地陷于颇为尴尬的境地。
粗粗翻翻这部《中国文学史》,导论的编写确是花了点功夫的。好比一个人的外套,一碗盖交饭的交头,马虎不得。至于文学以表现自我和人性为贵,这恐怕不是什么破天荒的观点,倒是老调重弹了。编写者也不否认,他们的某些主要观点,三十年代就有人提倡过。例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他因此把整部中国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分为“言志”和“载道”两派。言志者,即表现自我的思想感情,表现个性和性灵,表现人性。周作人是推崇“言志派”的。但是仅把文学分为“言志”和“载道”,许多作品和文学现象是并不能说清楚的。就是被某些人奉为经典的周作人的这部大著中,就有不能自圆其说的例子。章培恒等从马克思的一部著作的一条注脚的半句话中,为文学应表现自我和人性找到了理论根据,这当然是周作人做不到的。因此而说导论有点“新意”,大概也是有根据的吧。再翻一翻这部书的正文,老面孔、老话、不是新意的老意也有不少,在写法上不少章节各有庭径,就是文字疏密程度也大相异趣,甚至有些章节之间的文字都衔接不起来,表现出不少仓促成书的痕迹。毫无疑问,这部书的进一步修改的空间是不小的。如果能在此书出版后,认真地听一听学术界的意见,认真地听一听把此书作为教材的广大执教者的意见,花点时间作些认真的研究,精益求精地真正把此书改好,读者是会欢迎的。可是现在仅以几个月的时间,竟已推倒重写了七十来万字,实在是仓促得令人不可思议。
不久前看到一篇大约是出版社和发行部门总结这部文学史何以能销售到五十万册的文字。其经验是:开始怎样利用传媒发布消息,再是请记者专访,编写者发表谈话,专文介绍主编者,发表专家座谈会发言,又在一张文学类报上作整版的宣传,等等。看了这篇文字,好像了解了一些“宣传”的底细。现在章培恒的一整版的文字又发表了。不久前还在宣传这部《中国文学史》怎样怎样“突破”了以前的同类书,如今他又宣布“增订本”对几个月前出版的初版本有着怎样怎样的“突破”。人们不禁要想:是不是新的一轮“宣传”又开始了?
亲爱的读者,我们在五花八门的“炒”的面前,是否能冷静一下呢?应该吸取眼前惨痛的教训,对被“炒”得火热的东西,能否“看一看”,“等一等”,来个“冷处理”呢?譬如买书吧,看它一年二年,再决定要不要买什么“增订本”,为时不迟,免得再次买上三分之二有毛病的书。可要珍惜自己的或父兄的血汗钱啊!
(编者注:本刊设立“切磋篇”,是为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对本文如有不同意见,只要言之成理,我们当乐于发表。至于已购买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要求,请写信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认真处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