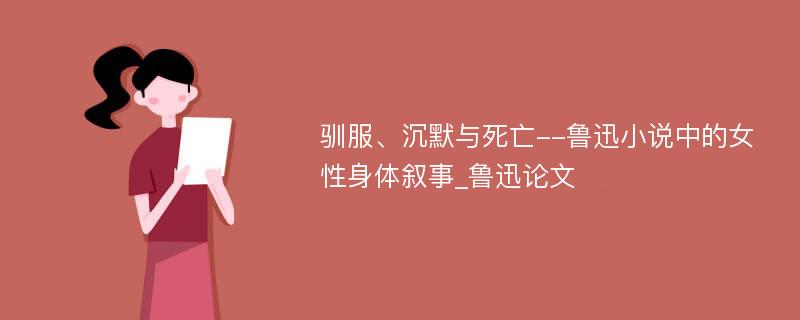
驯顺、缄默与死亡:鲁迅小说的女性身体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驯顺论文,鲁迅论文,身体论文,女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3.01.030
中图分类号:I210.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13)01-0130-06
现代身体美学认为,正是人的身体而不是精神成为人在世的根基,并且成为人认识自我、确认自我的出发点。梅洛·庞蒂指出,“正是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外向观察才得以开始——如果不承认这一身体理论就不可能谈论人对世界的感知。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取决于我们的身体。”[1]身体以某种形式出场则代表了某个特定时代人们是如何体验和认知自己的身体,也即是说,“身体”作为一个能指,在不同语境中其所指是不同的。按照福斯的说法,身体始终已经是“文化上勾绘好了的,他从不会以纯粹的或未经编码的状态存在”[2]。身体不仅始终处于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而不断地被管控与形构,而且也时时呈现出性别的区隔与压迫。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指出,“对身体的控制从本质上是对女性身体的控制。”[3]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女性生存困境与精神解放的理性沉思或诗性想象也指向女性身体,虽然女性始终处于被言说、被代言和被叙述的缄默状态,但对于女性身体文化符码或符号象征的阐释与想象却十分犀利与生动。鲁迅在他的女性身体叙事的文本中,撕裂了遮蔽在女性身体之上种种神秘的帷幕,透过对女性驯顺之躯、沉默之躯和死亡之躯的叙述,不仅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管制与形塑,而且极力恢复女性的地位和尊严、肯定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透射出男性角色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作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
一、驯顺之躯:男权文化的“驯顺”与女性的“内化他性”
福柯权力“微观层面”的技术分析,由关注权力宏观层面上的运作,转变为更加注重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参与和渗透。“当我考虑权力的机构时,我想到它存在的细微形式(毛细血管),权力深入个体,到达他们的身体、渗透他们的姿势,他们的姿态,他们的话语,他们怎样学会生活和与他人交往。”[4]福柯所说的权力不是来自国家宏大的、暴力式的政治权力,也不是来自某个单一源泉的权力,而是来自聚焦于身体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综合,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习俗等因素。所重点分析的不再是权力对人身体的“管控”和“抹去”,而是权力对身体的“凝视”和“渗透”。女性主义借鉴福柯“微观权力”概念分析施加在女性身体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发现社会对女性身体和行为的规范远比对男性严格,认为文化礼仪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压迫。正如巴特克所言:“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5]女性主义的洞见并不仅仅在于发现了权力对女性身体和行为的压迫和压抑,更深刻的在于发现现实存在于两性之间复杂、隐蔽的权力关系,通过女性对权力关系的“内在化”使之自动地施加于自身,自觉接受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驯服”,使身体呈现出“非我”的异化形态,而不是精神意义上的具有独立自我人格的自我掌控的“属己”的身体。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未能给国人提供任何有希望的理想和行为模式,相反却使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东西在现代形式下“死灰复燃”,形成阻挠社会进步、扼杀国人精神与灵魂的罗网。正如鲁迅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6]鲁迅所处的社会野蛮残暴、文化腐朽荒诞,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伦理文化使国人丧失了主体意识,男人成为伦理文化的附庸。腐朽荒诞的男权伦理文化为女性预设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贤妻良母”的身份角色和“三从四德”的行为规范,使女性的地位更卑贱。在鲁迅关于女性叙事的文本中,透过对“乡镇”世界的扫描和缩影,揭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之际宗法伦理文化依然通过各种“细微形式”侵蚀社会肌体的黑暗现实,揭示了伦理文化的隐蔽性、渗透性和腐蚀性,彰显了鲁迅社会批判与文明批评的深刻与犀利。更重要的是,鲁迅超越性别局限,在对女性身体和行为的“超性别”叙事中,揭露了男权伦理文化的性别压迫和压抑。
首先,“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对女性的压抑。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社会的运行,基于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的维系,而“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又是等级社会的一个基础和恒定范式。《周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从宇宙到人类社会,把男女的关系定位在和阴阳关系相应的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关系上。《列子》云:“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礼记》曰:“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些“男尊女卑”的伦理等级秩序,都是用来禁锢和残害妇女的精神枷锁。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揭露和讽刺了“男尊女卑”等级秩序的普遍性:“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最下贱一等叫做“台”,“‘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同时揭示了等级秩序对国人(尤其女性)精神的腐蚀性和酷虐性:“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7]在《离婚》和《伤逝》等小说文本的叙事中,弥散着“男尊女卑”等级秩序的阴霾对女性的身体禁锢和精神腐蚀。
《离婚》中,慰老爷子家厅堂离婚调停的场景,俨然一幅乡村社会等级秩序的一个微型缩影。位于厅堂最上首的是与“知县大老爷拜过帖”的七大人,依次是衙役、洋学堂的学生、众帮闲、慰老爷子、爱姑的公公和丈夫等,最下首的是爱姑和她的父亲。在这个微型缩影里,不仅投射出政治权利与知识权利的合谋对偏远乡村社会的渗透而造成底层人群心理的威压和恐惧,而且最卑微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心理的威压与恐惧的共同作用也注定了爱姑最终“走散”的悲剧命运。《伤逝》中,子君勇敢地冲出父权的藩篱却又无奈地卒于父权的牢笼,暗示出父权的强大与残酷。即使在子君与涓生的“新家”里,子君也处于被支配的被动地位。涓生依凭新知识的诱惑,不仅“读遍了她的全身,也读遍了她的灵魂”[8],而且常常因为生活的重压和“向外去”的巨大诱惑而厌恨子君。子君在日常平庸的生活里,逐渐沦为一个为“吃”而劳神费力的庸常妇女,知识女性固有的知性、灵气在日常“烟火气”里消散殆尽。
其次,“贤妻良母”的身份角色对女性的驯化。在中国几千年社会文化传统中,经反复实践、积累而形成的最典型的女性形象是“贤妻良母”型。男权社会只肯定女性的“母性”、“女儿性”身份,而回避男权社会压抑的“妻性”,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别的荒诞偏见和残酷压迫的写照。鲁迅先生写道:“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9]“女性是人类新生命的载体,女性从事着人类生命的创造,但是这种创造在相当意义上并不是女性主动的有意识的,而只是一种被动的无意识的生产。”[10]在男权的性别政治偏见和压迫下,女性被贴上“贤妻良母”的标签,这种性别政治最终使女性沦为维系男权社会繁衍的生殖机器和操纵工具。女性也顺应社会性别制度的“驯化”,把自己置放于从属地位的生存环境下,通过相夫教子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祥林嫂和单四嫂并未因失去丈夫而绝望,因为她们还有儿子,失子的打击却使她们最终失去生活的支柱。男权社会的性别压迫和压抑与“贤妻良母”说教的不断渗透,使女性将被压抑的情感都集中在母爱这份情感上找到抒发的渠道。
再次,“三从四德”的行为规范对女性的禁锢。“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的需要,是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女性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鲁迅揭示了父权制伦理文化压迫与压抑女性千年的黑暗历史,她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头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11]。
祥林嫂将“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内化”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律令而遵守不悖,因此在被迫改嫁时她大哭大闹,拜天地时仍以死相争。她强烈的反抗与其说是对婆婆人身买卖的隐性反抗,抑或是女性因性别意识觉醒而争取人格独立的果敢行为,毋宁说是为了维护“三从四德”道德律令下“从一而终”的感性冲动。爱姑的所有反抗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维护自己那已经死去的婚姻,不接受被丈夫抛弃的现实,其最充足的理由即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嫁到夫家后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在她的观念中,“明媒正娶”、“三从四德”即可稳固自己做奴隶的地位。子君的婚姻形式是新的,其实质却并未超越封建社会的“夫为妻纲”的旧规,把自己未来的一切完全寄托在涓生身上,甘心情愿做丈夫的附属品。
二、缄默之躯:男权话语霸权与女性的话语缄默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12]。借鉴拉康的欲望理论、德里达的语言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权社会抹杀女性存在的最有效的手段是男权制社会的表意手段——语言。他们认为,在男权“象征秩序”里两性没有共同语言,现有的语言完全受男性的控制,传达男性的权利、体验和意愿。在男权“象征秩序”的话语系统里,女性是缺席或缄默的。正是由于男性控制了话语权,女性失去了欲望表达的冲动与可能,最终使女性“不能发音”(Unpronounceability)或“陷于困境”(awakwardeness)[13]。透过对《祝福》《离婚》和《伤逝》中的话语分析,我们可以窥见男性话语霸权和女性在话语上被歧视与挤压而陷入“不能发音”的困境。
《祝福》里,祥林嫂被包围在“主人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诸多话语所织成的话语网里。鲁四老爷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讲理学的老监生”,是男权制的一个典型象征。实质上,他是被儒理、道教混乱理论教条和文化唾液涂抹粉饰而毫无精神操守的一具行尸走肉。但他确是鲁镇的“主政者”,他的话语具有拉康式的“主人话语”的特征,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制度化表述,控制着其他话语模式。小说通过鲁四老爷的两次皱眉(身势语言)三次短话,表露了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话语控制权。柳妈等鲁镇人的“民间话语”沦为鲁四老爷“主人话语”的帮佣,共同构成了“无主名的杀人团”在话语上歧视和压抑祥林嫂。当祥林嫂遭遇“灵魂”“地狱”有无的困惑和恐惧时,对“识字的”“见识得多”的“出门人”的“我”却寄予厚望,但“我”面对祥林嫂关于“魂灵”的询问却暧昧矛盾、犹豫混沌。在模棱两可的话语伪装之下,不仅显现出“知识分子话语”遭遇“主人话语”时毫无对抗之力,而且往往也存在着无处不在的“主人话语”对祥林嫂这样底层妇女的压迫姿态。鲁迅对话语权力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犀利的,而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以及自我生存危机的重新审视。
小说中祥林嫂疯癫之后的诸多“歇斯底里话语”,比如儿子阿毛被狼吃掉之后反反复复的唠叨“我真傻,真的”,典型地反映了她在“主人话语”长久压迫下的精神谵妄。鲁镇人对“阿毛”的悲剧故事由好奇、打听、鉴赏到视若“渣滓”、烦厌、唾弃与戏仿。祥林嫂充满悲伤的话语诉说并不能换取众人些许同情,不仅揭示庸众麻木冷酷的病态心灵,更重要的是揭示女性话语的空洞和无意义,男性话语对女性的压抑。当话语言说成为毫无意义的空洞所指时,祥林嫂只有再次缄默。
《离婚》的话语纠结与较量主要存在于两个场景内,一是船行水上,爱姑与众乡邻的话语纠结;另一个在慰老爷子家的厅堂上,爱姑一方与七大人及众帮忙、帮闲者的话语较量。在第一个话语场中,存在着主人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与女性话语的复杂纠结。在民间话语系统里,爱姑父亲“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弟兄多、势力大,并且在三年闹离婚过程中拔掉了婆家的灶台、拒绝了慰老爷子的多次调停。所以,众乡邻对爱姑及其父亲的讨好、恭维甚至不敢“说三道四”,都表示了爱姑及其父亲的话语地位高于众乡邻,也高于爱姑婆家及慰老爷子,爱姑才敢肆无忌惮地在公众场合大骂公公、丈夫是“老畜生”、“小畜生”。这里知县大老爷、七大人所代表的“主人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并没有直接呈现,而是经由“民间话语”和“女性话语”的转述发挥作用。“民间话语”与“女性话语”的转述透露出对“主人话语”的敬畏和对“知识分子话语”的迷信和幻想。正因为如此,爱姑才说:“我倒要对他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且看七大人说谁不错。”“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破人亡。”[14]爱姑这种表面的话语强势根基十分脆弱,无论如何泼辣、如何高声大调,实质是话语弱势者“话语焦虑”的一种装腔作势,隐藏着失败的危机。
在第二个话语场中,爱姑的话语遭遇了“知识分子话语”合谋围攻,七大人旧式“知识分子话语”——“鼻塞”、“新坑”、“水印浸”等使爱姑觉得神秘难懂,“无意,而且也不敢去研究什么‘水印浸’。”“要不然,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15]渗透着“主人话语”的“知识分子话语”又得到所谓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尖下巴少爷“毕恭毕敬”的认同。新旧“知识分子话语”的合谋,使爱姑觉得自己处于弱势、完全孤立了。爱姑向七大人的辩白话语,显然不是女性自己的话语,“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和“三茶六礼”、“花轿抬来”等话语重复的是男权社会里“主人话语”里“明媒正娶”、“从一而终”的道德律令,用“主人话语”来为自己向男权社会争取权利,必定是一种虚妄。爱姑对婆家公公、丈夫的破口大骂“歇斯底里话语”不仅没有人倾听,反而使人烦厌。“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她这时才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所以太放肆,太粗卤了。”[16]爱姑“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17]的话语,宣告了自己的彻底失败,也宣告了女性话语权的彻底丧失。
《伤逝》文本简直就是一个男权话语构筑的圈套,新女性知识分子被围困其中,窒息而死。就文本整体而言,以新男性知识分子涓生的日记组成的小说文本,只传递男性一种声音,尽管这种声音饱含着同情、爱恋和忏悔、自责,但无处不充斥着狡辩的阴谋,女性声音被完全遮蔽也是不争的事实。就文本中具体的话语而言,新女性知识分子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语,对旧制度的父权制具有十分尖锐的穿透力。即使面对来自“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满脸“雪花膏”的小东西们等民间的觊觎、凝视和指指点点,也表现出“目不斜视”的骄傲姿态。那是因为“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等资产阶级知识话语,在子君和涓生的心灵里引起了共鸣,他们具有平等的话语地位和话语趋向。当这种话语体系遭遇现实生存困境的打击、“男主外,女主内”父权制分工模式的无形渗透和更高话语体系不断诱惑的合力夹击下,子君和涓生的话语地位和话语趋向发生错位,产生裂隙。在错位与裂隙之中,子君只能无言“回来”、无声地死去。相对于无知无识的祥林嫂与爱姑,新知识女性子君被男权话语窒息而死,显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三、死亡之躯:男权社会的戕害与女性的隐性反抗
死亡是对生命终结的“大限”,人唯“舍生才有活路”,唯有找到一定的目标,才能感受到最强烈的生命意义,也才能克服死亡的恐怖挑战,从自己生命中感受到最强烈的生存意义。正如席莫尔所言:“对死亡的认知犹如一股撬开生命与生命内含的神力,使生命内含得以‘客观化’,有如替生命内含注射疫苗,使它不受‘生命的短暂’所侵害,让生命内含强过生命本身。简言之,即‘生命内含不朽,生命却必朽’。”[18]鲁迅的一生体现的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向死存有”(being-toward-death)生存样态。他这种“舍生才有活路”的生死观不仅限于个人范畴,也扩展到对整个民族生命延续发展的思考,而把民族的绝续放在全体人类进步的更广大脉络下审视。鲁迅对死亡的认知是“即生即死”,他通过文学想象进入死亡之域,站在想象的死亡之域中观照他所处的“此世”,进一步渗透、瓦解这一“并非人间”的“此世”“存在”。在鲁迅关于女性叙事的文本中,透过对女性死亡之躯的叙事,不仅渗透、瓦解了“并非人间”的“此世”“存在”,而且揭露了在“并非人间”的“此世”“存在”中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戕害与精神的虐杀,更重要的是在女性无法救赎的死亡命运中预示着女性对男权社会与文化执著、坚韧的隐性抗争。
《祝福》中孤苦伶仃的祥林嫂,在鲁镇充满“祥和”、“喜气”的新年祝福中倒毙在风雪之夜,也许这对祥林嫂来说是一种彻底的解脱。活着的祥林嫂一生满载着无穷无尽的痛苦与灾难,饥饿、欲望和疾病等的折磨使她非“属己”的异化身体由“端庄”、“周正”蜕变成“木偶人”,精神始终处在身体干净/不净、道德守节/失节、灵魂与地狱有/无、认同/拒斥、生存/死亡等悖论的焦虑之中,在“虚拟社会认同”与“实际社会认同”的巨大裂隙中,承受强加的“污名”而感到巨大的精神“窘境”,精神彻底分裂而死[19]。拖着疲惫身躯倒毙在冰天雪地之中的祥林嫂,的确使人震惊和扼腕,本应获得鲁镇人的同情与怜悯,但事实恰恰相反。死去的祥林嫂仍然遭受众多“噪音”包围:主政鲁镇的鲁四老爷诅咒她的死:“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可见是一个谬种!”鲁镇的“庸众”在“毕毕剥剥的鞭炮”“祝福”中,彻底遗忘她[20]。作为“新党”却同样被鲁四老爷视为“谬种”的“我”,不仅以自己“说不清”模棱两可的回答逃避祥林嫂死亡应该承当的责任,而且还为自己对事实的经验性假设的应验而沉迷:“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正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21]鲁迅在此的批判具有三重性:批判了道貌岸然的鲁四老爷沉浸在男权文化腐朽烟雾里,害人害己的冷漠与残忍;从祥林嫂的痛苦和悲哀中得到的不是伦理的,而是审美满足和快感的鲁镇众人的麻木与冷酷;一个背着因袭重担的觉醒了的“人之子”,一个在意识深层并未与故乡秩序完全割断联系的“新党”,对于祥林嫂之死的那种负罪感和与环境的同谋关系,以及其极力想摆脱道德责任的紧张不安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祥林嫂的死亡叙事为何置于鲁镇众人最隆重的新年“祝福”之际?为什么要把祥林嫂的死亡叙事前置?这显然不仅仅是小说叙事的技巧问题,而是潜藏着复杂的文化符码与解码的深层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有研究者认为“谁能说祥林嫂在‘祝福时节的死亡’,不是给‘鲁镇世界’发出的一声恶毒的诅咒呢?”[22]“她不再顾及‘鲁镇人’的那些清规戒律,就是要用自己的死给他们的‘祝福’‘添堵’。”[23]问题是,并不是祥林嫂“不迟不早”“偏偏要在这时”死亡,而是有人“偏偏要”把祥林嫂之死置于此时此地。这个人显然不是鲁四老爷、鲁镇众人或者作为“新党”的“我”,因为这些人对祥林嫂之死大都怀揣着禁忌和恐惧。这个人只能是作者鲁迅,鲁迅就是要安排祥林嫂“不迟不早”“偏偏要在这时”死在鲁镇人的“祝福”之际,给他们的“祝福”“添堵”。也只有这样,才显示出鲁迅批判的犀利和快意。针对第二个问题,鲁迅采用倒叙手法,把祥林嫂的死放在前面,并非只是出于单纯的技巧方面的考虑,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犹如先找到的女性的尸体,然后再寻找凶犯主谋,进而予以构罪和判决。以女性的尸体作为“物证”来抵达对“父权”的无情审判的深度,在凸显鲁迅批判深刻与犀利的同时,也深藏着鲁迅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悲凉,饱蘸着鲁迅对女性无法救赎的死亡命运的人本主义同情,对女性以身体死亡为证向男权社会和文化隐性抗争的由衷赞许。
《伤逝》关于子君的死亡叙事相对于《祝福》对祥林嫂的死亡叙事更加复杂和隐晦。经过新文化洗礼的勇敢的子君却如同无知无识、孤独无助的祥林嫂一样,走向死亡之地,这的确令人震惊和困惑。首先,子君的死亡来自父权的阻挠和冷漠。子君的父亲阻挠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子君的胞叔甚至气愤到不再认她作侄女。即便如此,子君分明地、坚定地、沉静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毅然决然地走出父权的牢笼,因为子君拥有涓生的爱情。在爱情的感召和诱惑下,新女性的子君不仅意识到自我身体的“属己”性,而且也觉醒了女性的主体性。但当爱情不再、遭遇涓生弃绝后,子君不得不回到“父亲家”,在“她的父亲——女儿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在威严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24]
其次,子君之死来自夫权的精神虐杀。在手记中,涓生一再反复强调和忏悔子君之死自己的责任在于将“不爱”的“真实说给子君”。这是谎言,其实涓生自始至终爱着子君。热恋时,“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生存危机时,“在无言中,似乎又都能感到彼此的坚韧倔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离开子君的日子里,“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2。涓生的责任在于他的自私、虚伪、怯懦和残忍。当面对生存困境时,涓生十分清楚应该“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却选择了弃绝子君而“奋身孤往”[26]。在生存与爱情、道德与责任的悖论选择上,涓生的自私性昭然若揭。为掩饰自己的自私性,竟以追求“人生要义”、“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等冠冕堂皇的漂亮言辞和“我已经不爱你了”等言不由衷的虚伪谎言来遮蔽,却暴露了自己的内心虚伪和人性怯懦。遮蔽与掩饰的真正企图是让子君“勇猛的觉悟,毅然走出这个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27]。涓生的确是一个“忍心”的人。
反观子君,她是勇敢、无畏和执著、坚韧的。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遭遇生存困境时,并非涓生认为的似乎也较怯懦了,而是充满希望。即使感受到涓生对自己冰冷的冷漠和厌弃,也无怨无悔,主动离开冰冷的家,并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28]。子君曾经在父亲家觉醒的身体意识和女性意识并没有丢失在丈夫家,相反在与涓生的强烈的对比中越发清晰和浓烈。在此,鲁迅不仅批判了对新青年的生存制造困境的黑暗社会,也批判了新青年男性知识分子的道德缺陷与人性弱点,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知识女性道德高度与情感厚度的由衷赞许。当涓生们孜孜以求“活命”时,子君们却以尸体为证宣告了与父权、夫权的彻底决裂,子君身上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被“毁灭”,的确让人触目惊心。子君之死“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之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证明了”[29]。倘要寻求子君之死对于将来的意义,就在于此了。
《伤逝》叙事同样具有“前置死亡”的特征,甚至在进入叙事之前,就已先期宣判了子君的“死刑”。文本至少有三处预设子君的死亡:当涓生觉得他们的“生路”在于分开时,想到子君的死;当涓生向子君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之后,也很快想到她的死;当子君被父亲领走以后,再次萦绕涓生心头的是还是“我想到她的死”。然后在子君缺席的情况下,作品直接以出自男性的“手记”形式——一种类似于祭文、悼词和悔过书的文体,为涓生的忏悔抑或辩解留下大片的余地,从而使男主人公完成了一次象征性的精神卸重和灵魂救赎,以女性(子君)的死,赋予了男性(涓生)的生。整个过程犹如一个遗体告别仪式,以便使这位男主人公尽快摆脱子君之死给他带来的精神负累,把子君彻底地埋葬掉,重新建立起道德自信,从而较为心安理得地活着,并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