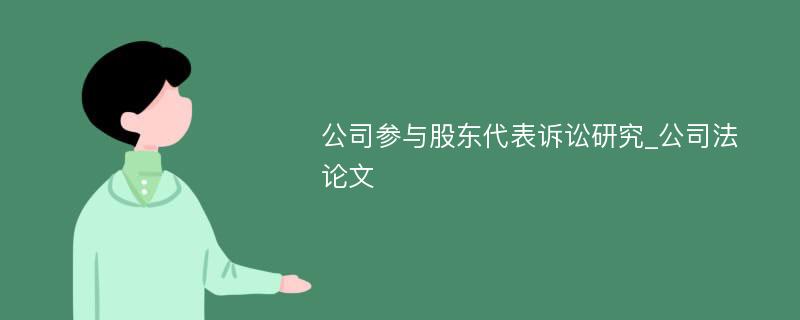
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诉讼参加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东论文,代表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所在
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提起的,追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之责任的诉讼。虽然诉讼的直接当事人为原告股东和被告董事等,但由于诉讼的标的是董事等的违法行为给公司带来的损失,诉讼中真正的权利人为公司而非原告股东,且诉讼的结果也归属于公司,因此不可能完全排斥公司以某种身份参加到代表诉讼中。此外,由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持有大量与诉讼相关的证据和资料,如果公司参加诉讼,会对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2006年1月开始实施的《公司法》中并不存在与公司诉讼参加相关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就股东代表诉讼的公司参加制定特别规则,这必将会对实践中法院审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造成一定的困难。
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诉讼参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当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公司参加诉讼究竟为公司的一种权利,抑或为一种义务?即是否应强制要求公司参加诉讼?第二,公司在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其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应如何确定?近些年我国学者在探讨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的地位时,提出了共同原告说、名义被告说、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说、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说以及特别诉讼参加人说等不同的观点。在中国人民大学江伟教授等编制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中,也提出“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法院应当通知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之立法建议。但是,笔者认为,由于公司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目的、诉讼案件的类型各不相同,其参加诉讼的方式也必然会产生差异,需要对不同情形下公司参加诉讼的形态分别展开研究。第三,公司是否可以辅助被告参加诉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与股东代表诉讼的立法宗旨以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何协调?其参加诉讼的公正性又如何确保?以下,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对公司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问题,结合公司法与民事诉讼法的理论展开探讨。
二、公司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强制性问题
探讨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时,首先必须明确是否应当然地将公司列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即公司法是否应强制公司以某种身份参加代表诉讼。在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是诉讼中“名义上的被告”(a nominal party defendant),是诉讼中必要的参加人。①这是因为:第一,公司没有亲自追究被告的责任,意味着已经作出了拒绝成为原告的决定;第二,公司不当地拒绝了股东的诉讼申请,属于对信托义务的违反,所以公司必须成为诉讼中的被告。虽然我国公司法中的代表诉讼制度也源于美国,但与美国的制度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
依照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的规定,虽然原告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前,应事先向公司提出诉讼申请,但公司处理股东提诉申请的决定却丝毫没有受到公司法的重视。
日本学者佐藤铁男也认为应该强制公司参加诉讼,其理由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由于股东代表诉讼与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其判决结果对公司产生直接的效力,要求公司参加诉讼,对确保公司经营的合法性、妥当性有积极的意义;相反,如果允许公司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参加诉讼,可能会给公司及全体股东造成损失。第二,强制公司参加诉讼,可以充分利用公司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防止原告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使案件的审理工作变得更充实。②但上述观点仅仅阐明了公司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价值和意义,而并不能成为强制公司参加诉讼的合理理由。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下,强制公司参加诉讼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各国公司法赋予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公司怠于行使追究董事等对公司的责任,保护公司利益。而在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就可以充分维护公司利益时,公司也就没有参加诉讼的必要;其次,民事诉讼的特征就是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公司有权自由选择是否参加代表诉讼;③再者,民事诉讼法上的强制参加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扩张判决的效力,使那些没有受到既判力或执行力影响的人也同样承担判决的效力,而股东代表诉讼中判决的效力本身就及于公司,所以强制公司参加诉讼缺乏足够的理论根据;最后,可以有效防止原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观点,也不能成为强制公司参加诉讼的理由,因为股东提起的代表诉讼并不当然地产生恶意串通行为。
当然,由于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没有将“代表的适当性”作为判断股东是否符合原告资格的要件,因此当原告股东没有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公正而且适当”(Fairly and Adequately)地行使其代表权时,法院也无法否定该股东的提诉资格,驳回该股东的诉讼请求。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公司参加诉讼可以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
对于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特别诉讼参加人。④即公司不是绝对的诉讼当事人,只是在公司认为必要时参加诉讼。但遗憾的是,上述观点并未就特殊诉讼参加人的具体内容,以及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展开进一步的探讨。特殊诉讼参加人的观点只是用一个模糊的概念暂时回避了现行法下公司在代表诉讼中地位不清的问题,而公司在试图参加股东已经提起的代表诉讼时,既不可能同时具有多重当事人的身份,也不可能脱离民事诉讼法中的当事人类型。笔者认为,当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公司决定参加诉讼可以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是认为股东的提诉行为妥当,通过诉讼可以实现自己对被告的权利,但为防止不利于公司的结果发生而参加诉讼;二是公司认为股东的提诉行为不当,希望通过参加诉讼防御股东不当的诉讼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公司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形态也各不相同。
(一)公司认为诉讼行为妥当时的诉讼参加
由于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追究董事等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作为股东代表诉讼中真正的权利人,公司本身具有实际原告的诉讼地位。但是,在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即使公司认为股东的提诉行为妥当,也无法基于同一诉讼原因再提起诉讼,否则将构成二重诉讼,这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悖。而此时,公司作为原告的参加人一同追究董事等的损害赔偿责任,在理论上并无不妥之处。另外,由于即使胜诉也不可能获得直接的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很容易与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因此公司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权利,也需要通过参加诉讼来监督、牵制原告股东的行为。
笔者认为,在公司认为股东的提诉行为妥当而要求参加诉讼时,其参加的形态应当属于共同原告,其理由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公司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原告股东在诉讼中所主张的权利和公司参加诉讼所主张的权利并无区别,而且胜诉利益亦归属于公司,公司无疑是实体利益的享有者和归属者,即使公司自己没有提起诉讼,也无法否认其在股东代表诉讼“真正的原告”的地位。因此,如果公司提出加入原告方展开诉讼,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共同原告。第二,从防止原告股东在诉讼中与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应将公司追加为共同原告。否则,在原告股东撤销诉讼请求或者诉讼请求被驳回时,公司就无法通过继续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⑤第三,虽然有学者指出,与一般的民事诉讼不同,由于股东向法院提起代表诉讼时,已经表明公司拒绝以公司名义直接提起诉讼,可以理解为公司已经放弃了自己追究被告责任的诉讼权利,因此公司本身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不能将公司列为共同原告。⑥但是,公司没有直接行使自己权利的原因也存在种种可能,并非就一定意味着公司放弃原告的地位。比如,在股东向公司提出诉讼申请后,公司没能在法定的调查期间内找到董事等存在违法行为的证据,在股东提诉后又发现了;⑦或者发现原告股东与被告间有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可能等。第四,如果公司认为股东的提诉行为妥当,也表明了公司参加诉讼的目的与原告诉讼中主张的权利是一致的,公司不存在独立的请求,也就无法成为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
此外,有日本学者指出,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虽然公司没有自己提起追究被告责任的诉讼,但诉讼的结果却对公司同样产生效力,因此为了防止诉讼产生对公司不利的结果,可将公司视为原告的辅助参加人。⑧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并无辅助参加人的概念,学者们认为它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一种,而且被称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⑨笔者认为,虽然公司以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辅助原告开展诉讼,在理论上并不存在矛盾,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告股东提出撤诉或者处分诉讼权利,公司将不具备继续诉讼的资格,也不能产生独自的请求权。这样,即使在原被告存在恶意串通,公司也很难采取救济措施,公司参加诉讼也就失去了意义。
(二)公司认为诉讼行为不当时的诉讼参加
不当的股东代表诉讼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原告明知被告对公司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盖然性很低仍然一意孤行地提起诉讼;二是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单纯是为了满足某些个人的利益,与公司是否存在权利没有直接的联系;三是被告等的行为虽然也对公司造成了损失,但行为本身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若要被告对此承担责任,则会严重打击被告等在经营中的勇于冒险的精神,将导致公司经营萎缩的后果,不提起诉讼或者被告胜诉可能更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佳利益。在我国现行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除了对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设置了“股份连续持有(连续180日)”以及“少数股东权(1%以上股份)”的提诉资格限制外,并不存在有效的滥诉防止措施,也不存在经营判断原则等董事责任的救济手段。而且,当股东向公司提出诉讼申请时,公司的意见也没有得到公司法足够的重视。因此,面对股东不当的诉讼提起行为,公司可以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辅助被告董事等展开诉讼防御。此时,公司辅助被告的形式不仅局限于为被告作证人,还可能直接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原告与被告的恶意串通诉讼,与不当的代表诉讼,都会损害公司的最佳利益,但两者在性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是通过减少损害赔偿请求额,或者将本应胜诉的案件故意造成败诉的结果,以既判力来阻止其他股东行使权利,从而达到帮助被告逃避责任或减轻责任、损害公司应有权利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以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对原被告的诉讼行为进行牵制和监督。而在不当的代表诉讼中,原告与公司事实上处于一种相对立的立场,公司不可能再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同时由于原告也没有对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因此公司也并非共同被告,只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民事诉讼法上的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日本学术界,认为公司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的地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之第三人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力。⑩这种观点与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构成要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日本民事诉讼法上的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可以仅对原被告中的一方提出诉讼请求。(11)这样在股东提起的不当诉讼可能会给公司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时,公司针对原告一方提出的停止违法行为的请求也满足有独立请求权之第三人的要件。而与日本法不同,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般理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而参加诉讼的人,第三人必须对原被告双方提出诉讼请求。(12)由于在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是原告在诉讼中所主张的权利的实质意义上的享有者,因此公司对诉讼标的不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同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第三人可以只对原被告中的一方提出诉讼请求,因此公司参加诉讼不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构成要件。此时,如果公司向法院提出要求原告股东停止违法行为的请求,应该被视作为一起新的诉讼。
相对于有独立请求权之第三人的参加方式,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体系下,如果公司认为原告的提诉行为本身不当并希望参加该诉讼,可以采用以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的身份辅助被告。但是,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辅助被告展开诉讼防御,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公司的这种行为是否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相背离?为保证公司作出的辅助被告参加诉讼之决定公正、合理,须满足什么条件?
四、公司作为被告之辅助参加人的问题
(一)公司对被告的辅助参加与股东代表诉讼的法构造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代表诉讼和代位诉讼的双重性质。从代位诉讼的角度来看,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提起的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诉讼,诉讼的利益也归属于公司。如果允许公司辅助被告参加诉讼,意味着在原告股东胜诉时,法院就要判决被告向被告的辅助人(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这种结果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而且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宗旨相悖。因此,很容易导出的一个结论是,公司既不能成为共同被告,也不能成为辅助被告的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此外,期待公司参加诉讼的目的之一是因为公司原本持有与诉讼相关的大量证据或诉讼资料,但如果允许公司辅助被告参加诉讼,那公司可能只提供那些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和资料,这样对原告不利。因此应该禁止公司对被告的辅助参加行为。
但是,上述结论是建立在股东提诉行为本身妥当的基础上的。如上所述,即使此时公司希望以辅助参加人身份参加诉讼,也只能在诉讼中辅助原告。如果在公司认为诉讼行为不当,提起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时,原告股东仍一意孤行地继续诉讼行为,那么公司为防止诉讼产生对自己不利的结果,辅助被告进行诉讼防御也并非难以理解。此外,股东代表诉讼虽然具有代位诉讼的特征,但同时也具有集团诉讼(classaction)、代表诉讼的性质,单纯以代位诉讼去解释代表诉讼中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从股东代表诉讼的代表诉讼的性质看,与其说原告是在代替公司行使权利,不如说是代表全体股东行使权利,公司作为与全体股东不同的主体,无论其辅助原告参加诉讼,还是辅助被告参加诉讼,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上都不存在问题。(13)至于证据和诉讼资料问题,也与公司对原告提诉行为是否妥当的判断有关,如果原本公司就不支持原告股东的提诉行为,那么期待公司提供不利于被告的证据本身也不现实。
(二)公司辅助被告参加诉讼的利益
是否允许公司辅助被告参加诉讼在民事诉讼法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司是否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虽然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此处所谓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该被理解为是与本诉争议的法律关系存在牵连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既包括诉讼标的的牵连,也包含诉讼理由的牵连。(14)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如果原告股东胜诉,胜诉的利益归属于公司,相反,如果被告胜诉,反而会导致公司自身的不利益。在这样一种构造关系下,必然会使人对公司作为被告的辅助人参加诉讼是否存在利益产生怀疑。
公司作为被告的辅助人参加诉讼并非没有任何利益,特别是当股东提起的诉讼属于诉权的滥用或者不当诉讼时,公司的参与可以更好地防御原告股东的不正当行为。如果董事等胜诉,可以减少社会对公司的不良印象,减轻不当的责任追究对管理层所造成的威胁和压力,进而防止公司经营萎缩。此外,面对原告的不当诉讼,被告董事等必须以个人身份进行诉讼防御,在时间、金钱、精神等方面承担巨大的负担,公司辅助被告参加应诉不仅可以牵制原告股东,而且可以使被告董事的应诉负担转移到公司方面。在公司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的情况下,被告的防御费用也属于保险公司补偿的范畴,相反,股东胜诉时公司需要补偿原告的诉讼费用和律师报酬可以因被告胜诉而免除。(15)
对于公司辅助被告参加诉讼的利益,日本学者伊藤真教授从另一个侧面进行了分析:即原告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所主张的被告等对公司负有责任的行为,不应都理解为是由该被告基于其独自的判断作出的。因为被告所实施的行为,可能依据的是董事会的授权,也可能本身就是在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代表诉讼的焦点也由被告的行为是否合法转变成公司的意思决定是否合法。对于公司而言,这可以被认为是辅助被告参加诉讼的利益。(16)
(三)公司辅助被告参加诉讼的条件
如上所述,允许公司以被告辅助人参加诉讼的前提是公司认为股东的提诉行为存在权利滥用,或者诉讼不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但考虑到公司内部人之间特殊的关系,在判断是否应作为被告的辅助者参加诉讼问题上,与被告董事或者监事同在一家公司任职的监事会或者董事会,能否从公正、独立的立场上作出决定,也值得怀疑,如何确保公司上述决定的公正性就成为了新的问题。
笔者认为,从股东代表诉讼的制度利益出发,当公司提出以被告之辅助参加人身份参加股东已经提起的代表诉讼时,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一是公司有明确的理由相信诉讼为不当诉讼;二是公司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参加的请求,并阐明诉讼参加的理由;三是当诉讼的被告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代表公司参加诉讼的法定机构为监事会;当被告为监事时,由董事会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四是公司参加诉讼的决定须经过监事会或董事会成员的一致同意;五是当被告败诉时,监事会或者董事会要对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与公司诉讼参加相关的其他几个问题
(一)第三人侵害公司利益时的诉讼参加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中诉讼的被告不仅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内部人员,还包括公司外第三人。当股东以第三人侵害公司利益为由提起代表诉讼时,公司参加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利于自身利益的结果发生,因此,此时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应为共同原告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考虑到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从更好地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共同原告身份参加诉讼更为妥当。此外,由于即使股东滥用诉权或者诉讼行为不当,也一般不会对公司造成直接损害,因此应禁止公司辅助被告参加诉讼。
(二)原告的诉讼告知义务
由于在原告提起代表诉讼后,公司无法就同一诉讼请求提起诉讼,但却要受判决结果的约束,为防止原告与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原告股东需要及时向公司履行诉讼告知义务。原告股东的诉讼告知义务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前首先应向公司提出诉讼申请;二是当公司拒绝或者放弃追究董事等的责任,股东提起诉讼后也应立即告知公司。我国《公司法》没有对第二种情况作出规定,这就会对公司及时作出参加诉讼的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公司法应明确规定,当原告提起代表诉讼后,应立即告知公司和全体股东。
(三)公司的诉讼参加
公司的诉讼参加虽然可以在防止原被告恶意串通,保护公司利益,以及补充诉讼证据和资料方面有重要的意义,但如果公司参加诉讼将使诉讼程序不适当地拖延或显著加重法院负担,其诉讼参加行为当然应被拒绝。
2006年开始实施的新公司法引入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这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强化董事经营者的责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相关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必然会使法院在具体审理相关案件时产生诸多困难。除了本文所涉及的公司诉讼参加问题外,代表诉讼的案件受理费问题、原告的诉讼费用补偿问题、诉讼和解问题、以及诉权滥用的防止问题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注释:
①刘俊海:《论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载《商事法论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②[日]佐藤铁男:《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参加及其形态》,载日本《法学家》(Jurist)1995年第1062号,第21页。
③汤维建、戈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 com.cn/weizhang/default.asp? id=16124,访问日期为2006年12月20日。
④汤维建、戈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 id=16124,访问日期为2006年12月20日。
⑤[日]大隅健一郎、今井宏:《公司法论》(中卷),有斐阁1992年版,第277页。
⑥刘俊海:《论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载《商事法论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⑦依照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第2款的规定,股东向公司提出诉讼申请后,公司应在30日内作出是否亲自起诉的决定,即《公司法》赋予公司的调查期间只有30天。期待公司在短短的1个月期间对案件作充分的调查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
⑧[日]松田二郎、铃木忠一:《条解股份公司法》(上),弘文堂1951年版,第316-317页。
⑨刘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⑩[日]谷口安平:《股东的代表诉讼》,载铃木忠一等编:《实务民事诉讼法讲座(5)》,评论社1970年版,第107页;[日]中岛雅弘:《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参加》,载小林秀之、近藤光男编:《股东代表诉讼大系》,弘文堂1996年版,第197-204页。
(11)《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7条第1款。
(12)田平安:《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13)[日]吉野正三郎:《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辅助参加》(下),载《商事法务》1994年第1358号,第26页以下。
(14)刘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15)[日]吉野正三郎:《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辅助参加》(下),载《商事法务》1994年第1358号,第28页以下。
(16)[日]伊藤真:《辅助参加的利益再考》,载日本《民诉杂志》1995年第41号,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