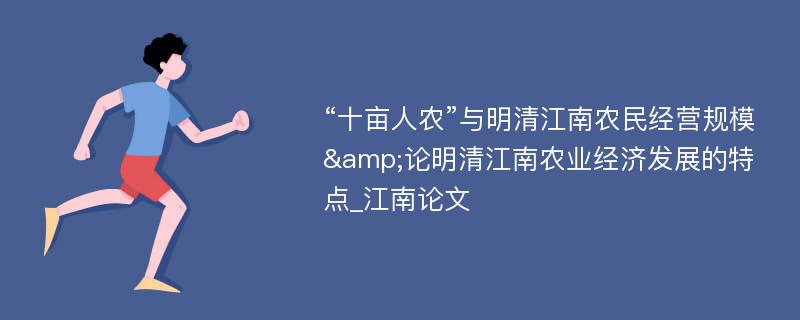
“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明清论文,之五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耕十亩”是明清人对当时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的一个大概估计。本文通过对明清江南耕地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宏观分析和对近代江南农户耕田数量的考察,指出“人耕十亩”这一农户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确实存在于明清江南,但在时空分布上却很不均衡。只是到了清代,它才成为占压倒性地位的普通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与普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其中农民耕作能力的变化、农家妇女脱离大田农作的增加和农民阶级的“中农化”作用尤为重要,而过去所强调的人地比例的变化,相比之下反而是次要的因素。
“人耕十亩”,是明清人对当时江南农民耕种田地一般数量的一个大概估计,用现代的语汇来说,就是他们对当时农民的普通经营规模的一种形象化的描述。
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通常以单个的小农家庭为经营单位,一个农场就是一个农民家庭所耕种的田地。从明清江南的情况来看,一个普通的小农家庭,一般仅包括一对夫妇及其未成年的子女和丧失了劳动力的父母,总人口约在五口上下(即所谓的“五口之家”)〔1〕。 其中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就是这个家庭中的丈夫和妻子。因此,一般而言,一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即一个家庭农场的规模),也主要指的是一对成年劳动力的所耕种的田地的数量。
虽然农民的经营规模问题是农业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奇怪的是,在过去关于江南农业经济史的研究中,尽管许多著作都涉及这个问题(例如,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或倾向于认为:明清江南农民经营规模狭小,有的学者甚至将经营规模狭小视为明清江南农业停滞的主要原因),但是专门讨论的论著却不多。就史籍中所说的“人耕十亩”而言,不少学者相信这是明清江南农民的普通经营规模的写照,但是他们大多只是将史籍中的成说加以引用,并未对此说可靠与否的问题进行论证。晚近比较流行的看法,以“人地比例关系决定农业经营规模”作为立论基础,即认为人口增加快,耕地增加慢,人均耕地减少,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就必定要下降。早在明代以前,江南就已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自明末以来,直至太平天国前夕,江南社会长期安定,人口数量有很大增加,而耕地数量则几乎没有多少变化。因此,许多学者都相信: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就一直在缩减。所谓“人耕十亩”之说,只不过是泛泛之言而已,并无任何实际意义。此说确有相当的道理,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也尚未见到持此见解的学者,对明清江南农民经营规模问题做出深入的专门研究。因此,尽管上述两种看法出入颇大,但实际上仍然还都只是未经证实的假设而已。
对于这两种看法,我们的意见是:由于地权和劳力、财力不均,即使是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各个农户之间在经营规模上也有颇大区别。因此之故,在史籍中关于农民经营规模的具体记述很多而且出入很大。如果依靠这类记述来对某时某地农民的一般经营规模作判断,结论自然会千差万别。更何况由于明清江南人口增加颇多而耕地总数变化很小,人均耕地确实不断下降,所以倘若“人耕十亩”之说成立于明代后期,就肯定不能成立于清代中期;反之亦然。因此,仅凭明清江南有一些“人耕十亩”的说法就断言情况如此,确是难以服人的。然而,我们也认为:这种以“人耕十亩”为标准模式的农民经营规模,在明清江南是确实存在的。否则,此说频频出现于这个时期,又应作何解释呢?因此,我们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而不是笼统地断言“人耕十亩”之说是对还是错。
在本文中,我们拟依次讨论以下问题:首先,从宏观的分析入手,探讨“人耕十亩”这种农民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是否可能存在;其次,从生产能力的角度,来分析决定这种经营规模模式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再次,因为这种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的出现与普及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还应对这种经营规模模式的分布作一时空分析。
一
作为一种对明清江南农民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的形象化描述,“人耕十亩”之说是否能够成立,关键不在于从史籍中能够找到多少条支持此说的记载(因为在史籍中同样也可以找到许多否定此说的记载),而在于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明清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然后根据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判断这种经营规模是否可能存在。这种宏观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只会是一个平均数,而且肯定会与各种具体情况下的农户耕田数有所出入,但是这个平均数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判断的参照系。很明显,如果史籍中的有关说法与此平均数出入过大,那么就很难相信这些说法能够成立。因此,这个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应当是很有帮助的。下面,我们就对明清江南的人口、耕地及农业中的人均耕地问题作一扼要分析,得出结果后,再用近代的调查结果进行旁证。
(一)
一般认为:人口数量是决定农民经营规模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严格地说,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真正对农民经营规模起作用的,只是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因此人口与经营规模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只是涉及农业劳动力的问题。
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人口确有相当的增长,但我们要指出的是:首先,这个增长的幅度并不像许多学者所想象的那么大;其次,江南城镇人口增长比农村快,因此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低于总的人口增长速度;再次,由于农村妇女日益脱离大田农作而转向手工业,所以农业中劳动力的增长慢于农村人口的增长。总而言之,相对于明清中国人口的变化而言,这一时期江南农业劳动力的增长是相当缓慢的。下面,我们对上述情况作一简要讨论。
1.关于明清江南人口变化的问题,我已有专文讨论〔2〕。 在该文中,我指出:在明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期(1620年前后),江南总人口大约为2000万左右。由于有效的人口控制, 使得人口年均成长率仅在3‰左右,所以到了太平天国战争前夕的1850年, 江南的人口才达到3600万上下。因此,较之同时期或近代中国总人口的增长情况而言, 江南并未出现“人口暴增”或“人口爆炸”。
2.众所周知,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化有重大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人口城市化的数量资料却很匮乏,因此迄今为止,学者们只能根据不同资料和分析方法作出一些大致的估计。其中,饶济凡(Gilbert rozman)估计清初江苏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3〕,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估计1843年“长江下游经济巨区”中330 个“中心地”(Central place)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7.4%〔4〕。 但刘石吉和刘翠溶都已指出这些估计太过于低〔5〕, 而且饶氏所说的江苏与施氏所说的“长江下游经济巨区”的地域范围,都远大于本文所说的江南。那两个地区的城市水平,也无疑比本文中所说的江南要低得多。因此他们的估数,对于江南来说,肯定都太过偏低。 徐新吾先生估计1860年松江府“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15%。〔6〕但是我们知道,当时江南正处于太平天国战争后期,人口损失极大,城镇人口尤然。另外,在19世纪后期近代上海兴起以前,松江府没有像苏、杭、宁这样的大城市,其城市化水平在江南八府中只能算是一般。因此在战前繁荣的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肯定要比1860年松江“非农人口”所占的比重更高。然而,正因为松江府没有大城市,所以对于江南大多数府来说,松江的城市化水平,可能比有大城市的苏、杭、宁三府的情况更具代表性。如果我们从低估计,认为1850年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外的整个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仅为1860年松江府的水平(15%),然后再加上三大城市的人口(约占江南总人口的5 %),那么江南城镇人口的比重应当在20%左右。这个估数和刘石吉所作的估数一致(见刘石吉1978),我们认为应当是可以接受的。明代后期的城市化水平,未见有人作出估计。李中清根据施坚雅和刘翠溶的有关研究,估计1700年全中国的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5-10%, 而江南的比重二倍于此〔7〕。他们所说的“江南”, 地域范围都大于本文中的江南,城市化的水平肯定也较本文中的江南为低。不过,鉴于没有更可靠的数字可资校正,所以我们仍然采用李中清的估计。取其中数,全国的平均数约为7.5%,而江南的相应比重约为15%。据此, 我们可知1620年和1850年江南的农村人口所占有的比重, 分别大约为85 %和80%,即1700万和2900万。
3.农村人口并不是全部都从事农业生产。虽然史料中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但是从明清时期的一些记载来看,江南农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的比重相当大。例如嘉靖后期何良俊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已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8〕。 康熙时靳辅也说务农者仅占百姓的十分之五〔9〕。道光时林则徐明确指出:在江南东部, “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10〕。同时代的湖州南浔镇,据温丰所说,“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11〕。 这些估计可能有所夸大,但是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农村非农人口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而且不断增加,则是可以肯定的。据1930年代的调查,江南农村中不从事农业的家庭约占总户数的10%〔12〕。而在1940年代初,据满铁调查,江苏南部农村无地可耕的居民也占同样的比例〔13〕。由于此时江南农村手工业已衰落,所以这个数字肯定大大低于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的相应比重。这里,我们仍然沿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比例,假定明清江南农村不从事农业的家庭占农村总户数的10%,应当说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按一家五口计〔14〕,1620年前后江南从事农业的农村家庭(即农户)数量,大约为310万户,而1850年则为530万户。以每户有两个成年劳动力(即农夫与农妇)计,1620年共有劳力620万人,1850年则有1060万人。
(二)
江南耕地的变化,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变化。关于这些的变化,我已作过讨论〔15〕这里集中分析数量方面的一些问题。
在1950年代以前江南所有的耕地数字中,以洪武26年和万历9 年两次调查所得的数字最为可靠。但是这两个数字相比,前者却又比后者高不少。那么,到底哪一个更为可靠呢?很明显,要判断哪一个数字更为准确,首先应了解造成两个数字之间差别的主要原因到底何在。我们认为:这个原因,主要在于这两次调查对“耕地”所定的标准不同,而非调查本身的问题所致。
依照滨岛敦俊的看法,明代江南的土地开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前,是“外延式开发”,即以扩大农田面积为主要目的的开发;而在此以后,直至明末,则为“内涵式开发”,重点是改良农田品质,提高耕地的利用率。〔16〕在前一阶段,主要采用“圩田”(或“围田”)的手段,将大片低洼土地用堤岸圈围起来,建成农田。明初圩围范围甚大,例如宣德时的苏州府,一圩“多则六七千亩,少则三四千亩”〔17〕。在这种大圩之内,包含着不少荒地、沼泽、池塘。但因为朝廷(特别是明太祖本人)假定所有未耕地,在将来某个时候都会被开垦为农田的缘故,在作田亩统计时,整个圩通被视为耕地,因此使得田亩统计数高于实有耕地数。到了后一阶段,目标是农田改良,所用的主要方法是“分圩”(即将大圩分为小圩)。在“分圩”的过程中,同时也消除大圩的“内部边疆”(internal frontier 即将原来大圩内存在的大量荒地改造为田),并实行“干田化”,改造低湿耕地。因此,尽管“分圩”时修筑圩岸和开挖沟渠,可能也要占用一些耕地,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被占用的耕地数量不会太大。因此,较之洪武时的情况,万历时的实际耕地数量可能有相当增加。但是,与洪武调查不同,万历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使田赋负担更为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丈量出来的是实际的耕地数字。因此,尽管万历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可能比洪武时增加了,但统计数字却有下降,这是可以理解的。又,江南土地的“外延式开发”在万历之前已结束,所以万历清丈之后,耕地实际数字纵有变化,其幅度也不会很大。正因如此,清代江南官方耕地数字也基本上是沿用万历数字。我们也因此而采用万历九年前后的统计数字,作为整个明清时期的耕地数。据万历《大明会典》卷15中苏、松、常、镇、宁五府和康熙《浙江通志》卷17中杭、嘉、湖三府的万历清丈数字,江南农田总数大约为4500万亩。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就把这个数字作为明清江南的耕地总数。
(三)
根据以上人口与耕地数字,我们即可求得明清两代人口最多时期的农户平均耕地数:在1620年前后大约是每户(即一个家庭农场)平均有耕地14.5亩,而1850年时则是每户约耕8.5亩。 以“户耕十亩”为标准来看,前者比这个标准多出45%,而后者则仅只少了15%。换言之,后者与此标准十分接近。因此,就清代中期的情况而言,“户耕十亩”之说是可以大致成立的。而在清代前期,由于农户数比1850年数少,户均耕地更接近于10亩,因此此说之能成立,更无疑问。然而,从明末情况来看,由于差距颇大,此说较难成立。至于在明代前中期,由于农户数明显少于1620年数,户均耕地数当然更应当大大超过10亩的标准。虽然人口与耕地数字失实,难以深究明代前中期江南的农民经营规模究竟有多大,但一些零星的数量记载来看,显然普遍大大超过10亩。例如,如果按洪武二十六年户数与田地数,苏州府户均耕地为20亩,常州府为52亩;而按万历六年户数与耕地数,则苏州府户均耕地为15亩,常州府为25亩。〔18〕如果除去各种非农业人口,那么一个农户平均耕地数还应更多。因此在江南,“人耕十亩”之说不适用于明代大部分时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此说只是到了明末才开始出现于个别地区,而到了清代中期,已普遍于各地。这一点,与我们上面对农户户均耕田数所作宏观分析得到的结果是相互吻合的。
(四)
从人地比例(严格地说,是农业劳动力与耕地的比例)来看,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耕十亩”的经营规模的普遍存在,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由于缺乏实际调查资料,尚难确知这种经营规模是否真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得不借助于近代的调查,来进行推断。然而,在运用近代调查资料时,首先应当注意到:由于江南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遭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破坏和人口损失,许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近代调查反映出的情况,与清代前中期的情况肯定有所不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近代调查所涉及的时间去清未远,较之清代中期,近代江南农业和农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从近代调查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的轮廓。而近代调查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又恰恰证明了“人耕十亩”之说,确实是成立的。
1.据《江苏省农业调查录》第99-104 页中的有关数字计算(将各乡作算术平均),1920年代初,在原松江府、太仓州属各县及原苏州府属嘉定县农村,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耕户)的百分比分别为:
县别调查乡数1-5亩5-15亩
15-20亩
上海 7
29% 61%
9%
奉贤 62% 44% 51%
南汇 76% 40% 48%
川沙 4
14% 58% 26%
太仓 6
16% 47% 35%
宝山 5
41% 42% 15%
松江 77% 37% 54%
青浦 5
30% 50% 15%
金山 55% 34% 55%
嘉定 8
14% 50% 33%
崇明 9
48% 35% 13%
由于不知道每个耕户内有劳力几个,是否用牛等,所以对于在本文讨论中被当作标准的那种小农户(即户内仅有成年男女劳力各一人、不用牛耕的农户)的经营规模到底有多大,难以作进一步了解。但是,从上面的数字也可以看到,尽管各地的差别颇大,但是大体而言,农户的经营规模,仍然以10亩上下(5-15亩)者为最多。
2.据卜凯(Buck)调查〔19〕,1920年代末江宁县和武进县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为:
地点江宁(淳化镇)江宁(太平桥) 武进
种田数 28.3亩 35.6亩15.9亩
这里的户均耕田数都大大超过了10亩,但是如果按照每个标准成年男劳动力(工人等数)来计,上述数字却变为:
地点江宁(淳化镇) 江宁(太平桥)武进
种田数 15.3亩
11.4亩 16.0亩
此外,在以上三地被调查农村中,农户均使用耕牛每个农场平均拥有耕牛数如下:江宁淳化镇——1.01头,江宁太平桥——0.48头,武进——0.92头。如果每个农场平均拥有的劳动力和耕牛的数量不是这么多,农场的规模也决不会如此之大。例如,按照江宁太平桥的例子,如果每户只有1个成年男劳力而较少使用耕牛,其耕种田地的数量就只有10亩上下。
3.黄炎培1932年在川沙县农村进行的调查表明:当时该地水稻生产情况几乎如清代之旧,稻田亩产量也差不多。关于农户的经营规模,黄氏指出:“大概夫妇二人,两三个幼童帮助,可种十亩田,但农忙时仍须雇工”〔20〕。
4.据原浙江大学农学院抗战前在嘉兴地区所作的调查,一般农户(小经营)平均每户种田11.27亩。与此同时,在小经营中, 而有牛户仅为0.2%。〔21〕
5.据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抗战前在无锡所作的调查,贫农每户平均种田8.17亩,中农9.05亩。〔22〕
一些村级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根据费孝通1935年对吴江县开弦弓村种稻农户生产能力所作的调查,一个普通农户大约种稻7亩, 而该村妇女都不参加大田农作〔23〕。
由以上调查资料观之,尽管存在着时间和地点的差别,但在抗战以前的江南,大体而言,一个无牛农户通常种稻10亩上下(换言之,一个农户的经营规模近乎10亩)。尽管与清代前中期相比,1920 年代和1930年代江南的人地比例和其他一些条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人耕十亩”的经营规模在江南仍然很普遍。这从一个方面也证明了: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耕十亩”这种经营规模的普遍存在,是完全可能的。
二
“人耕十亩”这一经营规模之所以能够出现并普及,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人地比例是这些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简单地把人地比例当做首要的原因,我们就很难解释以下情况: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江南人口减员近半,人地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尽管如此,“人耕十亩”的格局仍然保持了下来,依然是江南农民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因此,我们应当摆脱这种简单化的狭隘观点,从更广泛的方面去分析原因。
(一)
决定农户经营规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户的耕作能力。各种特定的生产方式,都要求相应的经营规模。反过来说,某一特定的经营规模,是由农民在某一耕作方式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
尽管经济作物的种植在明清江南有重大发展,但毫无疑问,一直到清代中叶,水稻生产依然是江南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就江南整个地区而言,无论从种植面积还是从事该项生产的农户数量来看,水稻对其他作物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江南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很大程度上是由种稻农户的经营规模所决定的,而种稻农户的经营规模则又取决于稻农的耕作能力。
明代前中期江南平原大部分地区仍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24〕。在这种耕作制度下,一个无牛农户可种稻25亩上下。因此耕田20亩以上,是符合当时农民生产能力的〔25〕。也正因如此,明代前中期江南盛行的大经营中,一个劳动力(僮仆或雇工)的平均耕种面积有多达数十亩的例如明代前期吴江县大地主王天奖“尤善治生,动不失时,薄种厚获,…田且数十顷,僮仆千指”,〔26〕而一个农户耕田25亩上下,也在一些地方成为普遍情况〔27〕。
自明代中期以来,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28〕逐渐推广,但是一直到清代中期才在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全面普及〔29〕在这种耕作制度下,一个成年男劳力只能耕种10亩上下〔30〕。如果超过了10亩,农民就无力耕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就只好将超出的部分出租。因此,农户耕作能力的上限,决定了其经营规模的上限——10亩水田。这一点,早在清初,张履祥就已明确地指出了。他说:“吾里田地,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十亩。故田多者,辄佃人耕植而收其租”〔31〕。两个世纪之后,陶煦又说“吴中之田,…上农不过任十亩”;在计算种田成本与收入时,他更进一步指出:“试以佣人耕者推之:人耕十亩(原注:佃农而一家力作,夫耕妇盍,视佣耕者为胜,或可逾十亩以外。然如是以佣于人,则又必增益其佣值。故不以佣耕者与佃农比例,无由得其概也…”〔32〕。两段文字合观,可知不论上农还是雇农(长工),一人最大耕作能力不超过10亩。佃农一户或可超过10亩,但如超过,就要雇工帮助。因此就一个农户而言,其经营规模的上限仍然只是10亩。
应当强调的是,上引张履祥与陶煦的话,都是在十分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说的。《补农书》成书于顺治后期,其时承明清之际严重天灾人祸之后,人均耕地肯定比明代后期承平之日要多。《租核》则成书于同治、光绪之际,更是江南人口经空前减员之后。在这两个大乱甫定、人口锐减的时期,农户本有可能扩大种田面积,但其所能耕田仍未超过10亩,多则就只能出租或雇工帮种。可见大体而言,自明末至清后期,江南农户一户能种田十亩的格局,并未随人口的起落而发生很大的改变。其原因则正如张、陶二人所言,在于农民的耕作能力如此。
(二)
除了耕作方式外,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也对经营规模具有重大影响。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农家妇女劳动的变化,对“人耕十亩”这一经营规模形成的影响。
很明显,一个普通农户的成年劳力通常为农夫和农妇二人,因此农妇劳动是否投入农业或投入多少,都是决定农户经营规模大小的主要因素这一,一般说来,农夫的工作,只有在农妇帮助下,才能顺利完成。这从长工劳动的情况亦可见之。由于长工只是单身出雇,其劳动通常没有自己家属的帮助。但是地主雇长工种田,在某些生产环节上(如插秧最紧张时),可能还要另雇短工或忙工帮助(例如沈氏的田地是雇长工耕种,但《沈氏农书》中在计算人工成本时,除了长工工钱外,又谈到“田壅、短工之费,以春花、稻草抵之”,可见沈氏仍然雇佣短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短工(或忙工)起到了农妇通常所起的作用。此外,长工在生活上可以获得主人家提供的各种服务(例如炊事及农作时送饭即史籍中所说的“饁饷”), 故得专力于农作(《沈氏农书》与《补农书》里均有关于此方面的论述),而在普通农家,这些也是农妇的工作。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一年二作制下,只有在农妇的帮助之下,一个成年男劳力方可种田10亩。如果农妇完全不参加大田农作,或者如果没有农妇提供的生活服务,这个农户的种田数很难达到10亩。但是,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妇女是否参加大田农作对农户经营规模的影响。
农家妇女是否参加大田农作(至少是最主要的大田农作,如整地、插秧、收获等),情况依时依地而异。在明代后期以前,江南农妇普遍参加大田农作;但是自明代后期起,越来越多的农妇日益转向养蚕和纺织。因此,江南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并未与农户数量的增加保持同步。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养蚕仍属农业,但是在生产方式上与大田生产差别颇大,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其与缫丝合为一体,视为手工业。从此意义上来说,明清江南农村手工业的主体是蚕业(养蚕和缫丝)和纺织业;第二,明清时期江南的蚕业和纺织业虽有很大发展,但在地域上变化并不很大。蚕业以及丝织业一直集中于太湖南部地带的蚕桑区,而棉纺织业则主要是在沿江沿海高田地带的植棉地区。因此,蚕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主要也是集中在这些地区的农村。由于这些工作主要由农家妇女承担,所以江南蚕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些地区农村农家妇女越来越深地卷入农村手工业。根据吴承明先生的估计,清代中期江南苏、松主要棉布产区的棉布产量比明代后期大约增加了一倍〔33〕。而按照范金明的估计,在此时期内江南丝绸的年产量更增加了三十余倍〔34〕。由于蚕业与纺织业的重大发展,因此而脱离大田农村妇女的数量,肯定很大。依照我所作的估计,在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的三百来年中,江南从事蚕业和纺织业的农村妇女的人数大约增加了近一倍。当然这些妇女并不全都脱离大田农作,但是其中脱离大田农作的人数确是与日俱增〔35〕。
如果妇女劳动不投入或少投入大田农作,农户平均种田数当然要减少。因此,在蚕业和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农户耕田数确实较少。即使在明代,已经有一些例子表明情况如此。例如,明代苏州府昆山县大地主周某雇工种田,“耕地常数百亩,日饁百余人”〔36〕, 平均每人种田仅数亩。又如明代苏州府嘉定县疁城乡农民阮胜,一家三口(一母一妻),种田为生,“有五七亩田,又租人几亩田,自己勤谨,早耕晚耘,不辞辛苦。那妇人有好得紧,纺得一手好纱,绩得一手好麻,织得一手赛过绢的好布”〔37〕。即一个有家室的农夫,农妇专力于纺织业,农夫种稻田近于10亩。到了清代中期,情况更为清楚,所以张海珊说:乾隆时江南“一夫耕(田)不能十亩”,又说:“(苏州府)人浮于田,计一家所耕田不能五亩”〔38〕。姜皋说:道光时松江的许多佃农“自种租田三五亩”〔39〕。苏、松是江南蚕业和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妇女大多不下田劳动,所以农户耕田之数也大大少于10亩,这是顺理成章之事。整个江南的情况虽然不一定如苏、松那样典型,但总的来看,到了清代中期,也正在像苏、松的情况靠近。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尽管江南人均耕地大大增加,但因农作方式未变,而且妇女仍然专力于养蚕和纺织,所以农户经营规模并未相应扩大。1888年(光绪十四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第25卷发表英国领土与传教士对江南个别地区与个别事例的调查报告, 指出在江苏南部一个农业雇工仅耕种水田6亩,杭州亦然〔40〕, 与张海珊和姜皋所说情况并无多大差别。其根本原因,当时人已清楚地看到。因此薛福保总结说:“往时(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江南无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亩者称上农,家饶裕矣。次仅五六亩。次三四亩,佐以杂作,非凶岁亦可无饥。何者?男耕于外,妇人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41〕。
当然,由于一年二作制的普及和妇女脱离大田农作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在地域上分布也不平衡,所以在清代前期江南的许多地方,也有若干例子表明农户的经营规模超过10亩的标准。例如康熙时靳辅奏称:“臣访之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只可种稻十二三亩”〔42〕。这种情况,如果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看,是不足为奇的。
此外,在分析农户经营规模的问题时,还应注意到不同农户在生产能力上的不同所起的作用。对于农户之间在生产能力上的这种明显差别,明清人并非没有注意到。例如尹会一说:江南农民,“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43〕,把农民按耕作亩数分为两类。章谦存更进了一步。他说:江南佃农,“工本大者不能过二十亩,为上户;能十二三亩为中户;但能四五亩者为小户”〔44〕。把佃农按生产能力分了三类。前引薛福保语中所体现出的差别亦与此大同小异。这里所说的“上农”生产能力较强,每人能耕种稻田远不止10亩;“下农”生产能力较弱,仅能种田数亩。方行先生指出:从农民对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收入来看,清代前中期江南农民出现了一种“中农化”的趋势,即“中农”在农民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45〕,而依照我们的看法,这种“中农化”的趋势又是农民生产之趋于均衡的表现。“中农”的耕作能力大约为10亩,因此代表“中农”的耕作能力的“人耕十亩”之说,也随着“中农化”的进展而普遍了起来。
考虑到以上因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耕十亩”的经营规模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其中,耕作方式的变化和农家妇女劳动的转移,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农民的“中农化”,又为这种经营规模的普及创造了另一条件。
三
“人耕十亩”的经营规模,其形成和发展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均具不均衡性。这一点,我们应当予以足够的注意。关于在时间方面的不均衡性,前面已有涉及,因此此处讨论的重点,是空间方面的不均衡性。
正如我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明代时期,随着资源合理利用水平的提高,在江南最主要的部分——江南平原(或称太湖流域平原)上,逐渐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作物区:东部和北部沿江沿海地带的棉区,太湖南部低洼地带的桑区和太湖北部地带的稻区〔46〕。由于桑、棉、稻三种作物在种植栽培方面有颇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对于农民的经营规模又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在考察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问题时,应当对这三大作物区的情况分而论之。
(一)
农民的耕作能力,与农民的作物选择有密切关系。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必须对专业化的桑农、棉农和稻农的耕作能力,进行探讨。
关于明清时期江南专业桑农与稻农的耕作能力问题,我过去已有专文讨论,兹可不赘。简言之,一般而论,自明代后期以来,在湖州、嘉兴和苏州等主要蚕桑地区,一个专业桑农(成年男劳动力)的治桑能力,通常在5亩上下〔47〕。至于稻农的耕作能力, 我也已指出:在合理调剂和使用人畜力资源的条件下,江南一个成年男劳力大约可种稻10亩左右〔48〕。也就是说,在明代后期以来江南的耕作方式下,一个专业桑农和专业稻农(以成年男劳力计)的最大耕作能力之比,大约为1:2。这个比例最早出现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关于长工工作定额的规定中,自此以后一直没有多少变化。当然,明末湖州精明的经营地主沈氏为其田庄上的每个长工(即成年男劳力)所确定的治桑和种稻亩数,分别为4亩和8亩。〔49〕均略低于我们所得的5亩和10 亩的一般数字。不过这个差异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沈氏所奉行的经营田地原则是:“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只要生活作好,监督如法,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也”。实际上,如果功夫细些,一个成年男劳力能治桑4亩或种稻8亩已很不容易了。例如,《广蚕桑说辑补》卷下末附《新增蚕桑总论》六条之二说:“蚕桑不可过贪,…宣知节,贪多则有害。何也?…蚕桑并多,更防工力不敷,反至糟蹋。大约一人之力,可以植桑三亩”。清初张履祥为友人遗属策划生业,也认为一个农户种桑至多以3亩为限〔50〕。一般农户的耕作似乎没有那么精细, 因而每个劳动力所能治桑或种田之数,也多于沈氏的标准。例如,据万历时代湖州人庄元臣《曼衍斋草》“治家条约”的“立庄规”条,他的长工专业种桑,3人治桑地20亩,平均每人6.7亩。又,在水稻生产方面,据张履祥《补农书》“总论”,在明清之际的桐乡农村,“上农夫一人只可治田十亩”。可见,即使是在与沈氏生活的时代相近的湖州和嘉兴地区,一般农民的治桑或种稻的亩数都略多于沈氏田庄上的长工。有鉴于此,故兹以5亩(桑)和10亩(稻)为一般农民的耕作能力标准。
关于明清江南专业棉农的植耕能力,有关记载极少,也未见有学者对此作过探讨,因而在此需要作一些考证。此方面的材料,我在江南史籍中仅见以下两条,反映的都是乾嘉时期松江地区的情况。一条是钦善《松问》所说:“种棉之农,夫夫妇妇,洒汗坳硗,人踖二亩”〔51〕。另一条则是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所说:“下农种木棉三五亩”〔52〕。两条合观,可以推知当时松江一个种棉农户(应属“下农”)的耕作能力甚小,大约4亩上下。此外, 一些零星的史料也表明农户种棉确实不多。例如,顺治时上海姚廷璘家种棉只是数亩〔53〕,而乾隆时常熟郑光祖家种棉也不过3亩而已〔54〕。下等农户每户种棉在 3-5亩之间,中等农户应多一些,兹以下等农户之上限计,为5 亩或略多。这里要指出的是:种棉农户的生产情况,与种桑和种稻农户的生产情况,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在种棉的生产活动中,妇女参加大田劳动的情况比在种桑和种稻生产活动中普遍(特别是打心、摘花等活动,更主要是妇女的工作),因此难以单独计算男子的耕作能力;第二,棉田不一直种棉,每种棉数年就必须改种稻一次。因此即使是专业棉农,为轮作的需要,也必须种一些水稻。曹幸穗对1940年代初江南农村种棉情况的研究表明:一个成年男劳动力通常种棉、稻各3亩〔55〕。 如加上妇女辅助,应当稍多一些。 这与我们在此所谈情况颇为接近。
(二)
正如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说明的那样,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出现的三大作物区,并非仅止种植某一种作物的“单一型专业化”种植区,而是以一种或两种作物为主导、几种作物并重的“宽广型地区专业化”种植区〔56〕。在桑、棉、稻三大作物区内,大多数农户也并非单一种植某一种作物。由于农民在桑、棉、稻等作物种植上的耕作能力不同,所以如果他们的生产同时包括不同的作物的话,那么他们的耕作能力自然也就不同于专业桑农、棉农或稻农的耕作能力。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上述三大作物区中,一个成年男劳力的耕作能力究竟有多大。
1.在明清江南桑区,几乎所有农户都养蚕。但是在他们当中,专业桑农只是少数;同时也有一些农户只种稻而不种桑,他们养蚕所需的桑叶通过市场而获得。但是大多数养蚕农户既种桑、又种稻。为了简化分析,这里我们假设所有的农户都养蚕,而且桑、稻兼种。
如前所述,种植桑、稻主要是农夫的工作,而一个成年男劳力的耕作能力限度为治桑5亩或种稻10亩,又,桑区的绝大多数农户桑、 稻兼种。因此,这里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此地区,一个农户究竟种桑、稻各几亩呢?很明显,既然绝大多数农户都是自己种桑以供给自己所养之蚕,故决定桑、稻种植比例的,主要是农户养蚕的能力。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一个农户可以养几筐蚕?要养这些蚕需要几亩桑园?
明清江南农村养蚕(包括缫丝)主要是妇女的工作。一个成年妇女能够养多少蚕?史料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例如, 据《警世恒言》卷18《施润泽滩阙遇友》所言, 嘉靖时吴江县盛泽镇小机户施复(即施润泽)之妻,“每年养几筐蚕儿”,而镇郊滩阙村农民朱恩之母、妻二人,“常年…养十筐蚕,…今年看了十五筐”。两条合观,可知那里的蚕妇一人,大约养蚕5-8筐。张履祥《补农书》“总论”说:“且如匹夫匹妇,男治田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据此,一个成年农妇的养蚕能力的上限,大约为10筐。就一般情况而言,农妇一人养蚕8筐左右, 应属比较普遍的情况。据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所作的考证,在一般情况下,明清江南中等桑园每亩所产之叶,可养蚕8-9筐。〔57〕农妇一人养蚕8筐,大约需要中等桑园1亩。但是,正如乾隆《湖州府志》卷37“蚕桑”说:“蚕事…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且为时促而用力倍劳,方蚕月,…农夫女红,尽昼绵宵,竭蹶以祁蚕事之成”。在江南桑区农村,养蚕是头等大事,农家其他成员常常都也全力投入,辅助农妇工作。若将农妇之外的其他劳力(主要是老幼劳力)合起来以一个成年女劳力计,那么这个农户所能养之蚕,就需要2 亩桑园才能供给。我们已知一个成年男劳力可以治桑5亩或种稻10亩, 为满足其家人养蚕须治桑2亩,此外他就只能再种稻6亩了。桑园与稻田合计,一共8亩。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平均数,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出入, 但不会很大。所以在《杨园先生全集》卷19《凭耕末议》所附“授田额”中,张履祥对奴婢授田的合理标准是:“一夫一妇,授田三亩,地二亩,…代主人耕田二亩,地一亩”。亦即一户奴婢夫妇二人, 仅能耕田5亩,管地3亩(即桑园)。二者合计共8亩,与我们的估数相近。 如果这个人家还有未成年的劳动力,那么这个总数还可以有所增加。总之,一个农户耕种田地的总数,大约接近10亩而略少。
2.在明代后期以来的江南棉区,随着耕地使用技术的进步和为防病虫害的发生,棉田三年一轮作(即二年种棉,一年种稻)的“翻田制”逐渐成为了主要的种植方式。在这种种植制度下,棉农必须每年将其三分之一的耕地用来种植水稻。因此,如果一个普通农户每年种棉5 亩,那么它还将同时种稻2.5亩,即总计耕种田7.5亩左右。总之,一个种棉农户耕种田地之数也是接近而略少于10亩。
3.桑区和棉区不种桑、棉的农户以及稻区的农户(后者大多不种桑、棉)的耕作能力,在明代颇有差异。例如,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4“史十”,嘉靖后期松江西部水稻产区一个种稻农户的耕种面积,通常为25亩左右,而东部棉花产区一个种稻农户的耕种面积,却只有5亩左右。但是到清代中期,各地种稻农户的耕作能力的差别似乎已变得很小,都趋向于每户10亩左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一个原因是资源利用的合理化,使得那些不适合种稻的耕地(如松江东部地势高亢的耕地)退出了水稻生产,从而消除了特别的不利条件对农民种稻耕作能力的限制。另一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水稻和春花(麦、豆、油菜)轮作的一年二作制的普及,而在这种种植制度之下,一个成年男劳力的耕作能力大约是10亩。再一个原因,是由于农家妇女越来越多地退出大田农作,从而种稻也越来越成为农夫一人的工作。因此一个种稻农户种田10亩左右的情况,也普遍了起来。
由于桑园和棉田的经营比稻田的经营更加集约,因此桑农和棉农的户均耕作面积也肯定要比稻农少一些。从上所作分析可见,桑农和棉农的耕作能力都略低而接近于10亩。所以“人耕十亩”之说先出现于桑区和棉区,然后方逐渐扩张到稻区,这是很自然的。据我所见的史料而言,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万历时代的湖州〔58〕,随后是康熙初期的嘉兴〔59〕,接下去是康熙时期的苏、松〔60〕、乾隆时期的江南〔61〕,等等。在以后的时期里,这一说法仍然流行不改〔62〕。这种时空分布特点,与农民生产情况的变化是相一致的。
因此,“人耕十亩”之说的出现与流行,在时空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而这种不均衡性恰恰证明了:这种经营规模的形成,与农民生产方式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决定这一经营规模出现和普及的首要原因,是农民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是人地比例的变化。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对明清江南农业劳动力和耕地数量的宏观分析,可以证实“人耕十亩”这一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完全可能存在的。从近代调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种经营规模肯定在近代以前曾经广泛流行于江南。因此,否定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其次,尽管“人耕十亩”之说曾经存在于明清江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论何时何地情况都如此。相反,这种经营规模在时空分布上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只是到了清代,它才成为占压倒性地位的普遍模式。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注意。
再次,“人耕十亩”的经营规模模式的出现和流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农民耕作能力的变化、农家妇女脱离大田农作和农民的“中农化”等,都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简单地把原因归之于人地比例的变化,是不全面的。
最后,我们还想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一看研究明清江南农民经营规模问题,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近代以前农业和农民经济行为,具有何种意义。
一般而言,只有在最佳的经营规模下,才能获得最理想的经济效益,因此经营规模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在研究农业经营规模的问题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首先,任何一种既有的农业经营规模,都是各种特定的条件的产物,因此所谓“最佳经营规模”,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相反,由于各种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最佳经营规模”的标准也因时因地而异。其次,即使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商业化水准较高的江南地区),农民为了获得最理想的经济效益,也在不断地努力追求某种最佳经营规模。“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从此意义上来说,每个时期和地区农民的经营规模,相对于其所处的特定条件而言,都可以说是在向“最佳经营规模”靠近。简言之,一种经营规模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普及,最根本的原因,是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明代后期以来江南所具有的各种条件下,以“人耕十亩”为代表的经营规模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普及,乃是因为这种经营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63〕。也正因如此,它能够经受住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内乱外患和各种社会危机的严峻考验,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从而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才能对过去的农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特点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判。相反,站在一种我称之为“近代优越论”的立场上〔64〕,否定近代以前小农经济和小农经营行为的合理性,或从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出发,把“人口压力”当做分析近代以前农业和农民经济问题的钥匙,肯定是难以说明问题的。
本文中的“清代”,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指自清军占领江南至太平天国军到达江南前夕,即西元1644-1850年。“江南地区”则指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包括明清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和从苏州府折出的太仓州。这样界定的理由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注释:
〔1〕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Memillan Press(London) 1996.第二章第一节。
〔2〕李伯重《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载于《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3期。
〔3〕饶济凡(Rozman.Gilbert),《Urban Networks in ChingChina and Togukawa lap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219,273页。
〔4〕施坚雅(Skinner,G.Williem), 《Regional Urbanizatin inNeneteenth Century China》,收于Skinner 主编《The City inLate ltoperin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5〕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载于《思与言》(台北),第16卷第2期,1978。 刘翠溶:《明清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与人口特征》,载于《经济论文期刊》(台北),第14卷第2期,1987。
〔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92。
〔7〕李中清:《中国历史人口制度:清代人口行为及其意义》, 收于李中清与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四友斋丛说》卷13“史九”
〔9〕《生财裕饷第一疏》,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26。
〔10〕《太仓等州卫帮续被歉收请缓新赋折》,收于《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2。
〔11〕温丰《南浔丝市行》,收于咸丰《南浔镇志》卷31。
〔12〕〔14〕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Delta,1620-1850,第二章,第二节。
〔13〕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家庭农场的规模效应研究》,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1990年第3期。
〔15〕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1994年第4期。
〔16〕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的投资活动》, 收于《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
〔17〕况钟《明况太守治苏政绩全书》卷9 《修浚田圩及江湖水利奏》。
〔18〕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434页附表3。
〔19〕卜凯(Buck.Joho Lossing);《Chinese Farm Economy》,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nd the China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南京),1937;第445-447页, 表15-17。
〔20〕民国《川沙县志》卷5农业。
〔21〕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3。第43-44页。
〔22〕同上。
〔23〕费孝通: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Willian Clowers & Sons Ltd (London and Beccles),1937;第162-165页,第170页。
〔24〕李伯重:《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于《中国农史》(南京),1986年第2期。
〔25〕同上。
〔26〕赵宽《半江赵先生文集》卷9《乐善堂记》。
〔27〕《四友斋丛说》卷14《史十》。
〔28〕北田英人:《宋元明清中国江南三角州农业の进化と农村手工业た关よる发展研究》,载于《1986-1987年被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报告书》(高崎),1988。
〔29〕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0〕同〔2〕。
〔31〕《补农书》“总论”。
〔32〕《租核》“推原”、“量出入”。
〔33〕吴承明、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77-279页。
〔34〕范金民:《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载于《史学月刊》(上海),1992年第1期。《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 载于《清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2期。
〔35〕以上讨论,详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clopment in theYangzi Delta 1620-1850》,第8章,第1节。
〔36〕《震川先生文集》卷2,《周子嘉唐文孺人墓志铭》。
〔37〕《三刻拍案惊奇》第17回。
〔38〕《积谷会议》与《甲子救荒私议》,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39、43。
〔39〕《浦泖农咨》。
〔40〕引自李文治:《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收于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合著《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41〕转引自方行《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1996年第1期。
〔42〕《生财裕饷第一疏》,收于《皇朝经世文偏》卷26。
〔43〕《敬陈农桑四务疏》,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36。
〔44〕《文誉》“通论”。
〔45〕同〔42〕。
〔46〕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于《农业考古》(南昌),1985年第2期。
〔47〕李伯重:《对〈沈氏农书〉中一段文字之我见》,载于《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48〕李伯重:《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于《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49〕二者不可得兼。见李伯重《对〈沈氏农书〉中一段文字之我见》,载于《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50〕《策邬氏生业》。
〔51〕《皇朝经世文编》卷28。
〔52〕《上海掌政丛书》第一辑。
〔53〕《历年记》顺治六年条。
〔54〕《一斑录杂述》卷2。
〔55〕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家庭农场的规模效应研究》。
〔56〕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57〕李伯重:《明清江南桑蚕亩产杂考》(将刊稿)。
〔58〕崇祯《乌程县志》卷2“赋役”引万历时县人沈演语。
〔59〕《补农书》“总论”。
〔60〕光绪《川沙厅志》卷4载汤斌疏略。
〔61〕尹会一《敬陈农事四疏》。
〔62〕张海珊《甲子救荒私议》、陶熙《租核》“重租议”。
〔 63〕关于这种经营规模的经济效益问题的讨论,
详见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Edlta》第8章第2节。
〔64〕更确切地说是“近代西方优越论”,参见李伯重《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的人口行为》,载于《新史学》(台北),第5 卷第3期。
标签:江南论文; 明清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农民论文; 经济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三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