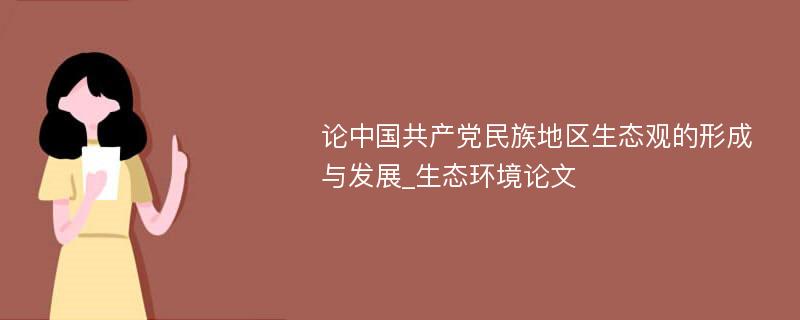
试论中国共产党民族地区生态观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试论论文,民族地区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2-0043-03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要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10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环境建设在民族地区开发中的地位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但纵观我党在民族地区开发和建设的历史,党的民族地区生态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和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生态观的忽略、误识、形成到发展四个阶段。本文将侧重论述生态观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即第三、第四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地区生态观真正形成和逐步完善的时期。
一、民族地区生态观的忽略期
这一阶段大致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至1958年“大跃进”前夕。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一直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建设,这些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纲领、政策及其主要领导人有关民族地区发展的讲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53条就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1954年的宪法也同样规定自治地方的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事业”的条款。与此同时,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发展民族地区的方法及其重要性。1951年,朱德同志指出:“学会和自然作斗争的本领,多想办法,多出注意,多种粮食,多养牛羊,用我们辛勤的劳动逐步把高原变成沃土。”[1](P71)1954年,刘少奇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谈到“汉族人民必须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各兄弟民族以真心诚意的帮助,特别是派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更必须时时刻刻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设想。”[1](P110)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十大关系之六,强调“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2]
应该说,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有限性,我国所处的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同时也因为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问题并不十分明显等原因,致使我们党在开发和建设民族地区时井未也不大可能更多地考虑或重视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二、民族地区生态观的误识期
这一时期大致以1958年的“大跃进”为起点,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客观地分析,这一阶段我们党还大多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民族地区的发展。如1962年周恩来在《不断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中提出“应该继续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农业、牧业生产。”[1](P199)然而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在客观上给我国尤其是西部广大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严重忽视了经济建设中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大跃进”时期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是配合“以钢为纲”的工业建设方针,在发展钢铁工业条件不足的西北、西南地区,通过行政命令来发展工业基地,一批批土炼钢炉遍布民族地区,成片成片的森林被砍伐,废水、废渣和废气严重污染水、大气和土地资源,给原本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民族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此后,虽经过了1963年至1965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情况有所好转,但好景不长。与之几乎同时进行的“三线建设”,尤其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包括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正如云南的历史资料显示,从公元1900年到1960年的60年期间,金沙江下游洪涝重灾每14年一次。但从1960年到1980年期间,洪涝灾害出现缩短为4-6年一次的逼人境地,这主要是由于其中上游森林面积锐减与水土大量流失等原因造成的。
这一时期主要由人为因素给民族地区的生态造成的不良后果。为日后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对我党树立正确的民族地区生态观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民族地区生态观的形成期
这一时期大致从“文革”结束至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此阶段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认识或兼顾时期。其实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中央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专门召开了工作座谈会。在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牧业畜牧业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重申“以牧为主”的方针和“禁止开荒,保护牧场”,发展畜牧业等政策规定。同年8月,周恩来在医院接见了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时,嘱咐他要告诉在藏区工作的同志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自此,民族地区的经济等各方面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我们党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一规定说明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观上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也为民族地区的环保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护。1985年,李鹏同志在《发展经济培养人才繁荣西藏》中提出“西藏的同志要认真贯彻森林法和草原法,把保护森林和植被当作一项战略任务来抓”。[1](P203)1987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纪要》,明确牧区要坚持畜牧业为主、草业先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提出牧草是畜牧业的基础,必须加强管理,合理利用,保护和建设草原,发展草业,逐步做到草畜平衡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领导我国民族地区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样,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得到更进一步的关注和改善。上任伊始的江泽民同志于1989年9月20日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性脱贫工作,一定要同当地的资源、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还要十分注意防止污染环境”。[1](P216)1992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再次强调“同时,注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1](P253)此期间,由于国内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以及国际上对生态的特别关注,我们党在进一步加快民族地区各方面发展的同时,对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提高到了一个高度重视的阶段。
四、民族地区生态观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大致以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一直延续到现在即党的十六大的召开,这一阶段也可以认为是我们党在民族地区开发中生态观的大发展阶段。自建国后,由于主客观原因,我们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出现了不少的失误,尤其在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时未能很好地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协调起来,致使大量森林被伐、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和空气质量严重下降等等。如四川省建省初期森林覆盖率约为20%,到1987年仅存13%,川中丘陵地带58个县已是无木可伐了。与此同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人们不能为了自己眼前生活得好一点,就向大自然无限索取。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发大会”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就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搞好环境保护,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子。正是在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下,加之中国共产党人自身认识的不断提高,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表现在把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世纪之交,中共中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党的领导人一再强调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充分调动西部地区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西部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应该是全面的,要把水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放在突出位置。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都要统筹兼顾。”[3]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要“切实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要加大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天然保护林工程的实施力度。陡坡耕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要抓住当前粮食等农产品相对充实的有利时机,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综合性措施,以粮换林(草)。要坚决制止新的毁林毁草开荒。”[4]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青海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中也指出,在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中要下大力气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要通过退耕还林还草,治理水土流失,逐渐改善生态环境。可见,民族地区(即主要指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在跨世纪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始终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其次表现在把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法律高度。主要体现在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该法与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相比,其体现的主要精神之一就是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指明了少数民族地区今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如修订后的自治法在原第45条的基础上写进了“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的新内容。并专门增列了第66条,用三款的内容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一款是“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把民族自治地方的重大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的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一部署”。第二款是“民族自治地方为国家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国家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第三款的内容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民族自治地方开采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此举从法律的角度为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实现人类、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
最后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到一个新的政治高度。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中国民族地区大多位于西部,不少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生态平衡十分脆弱。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要注重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要把它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5]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高州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也同样是我党开展民族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三个代表”所含内容丰富,其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的“先进文化”就包含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特别是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不仅再次强调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6]而且意义更深远的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一伟大目标必将为全国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指引出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
由于我党、特别是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近几年来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使得我们在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方面取得或正在取得显著的成绩。据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在十六大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自实施西部大开发3年来,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显著增大。在2000年,开始实施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试点,3年投入专项资金20亿元。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地区生态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地区的长期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它必将随着我党对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建设而日臻完善,为广大民族兄弟创造一个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生态环境。
收稿日期;2003-10-11
